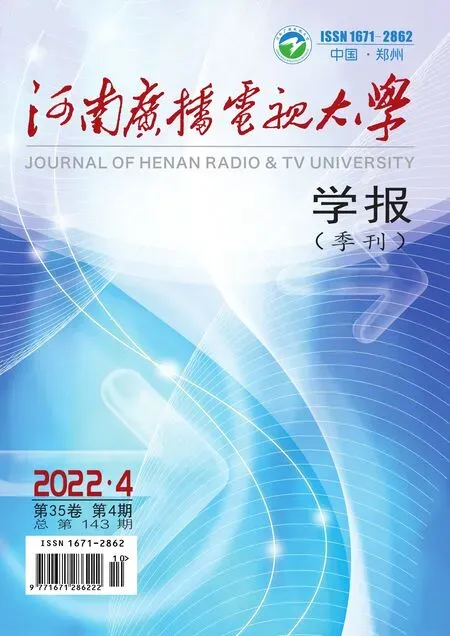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的关系书写
姬亚楠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河南 郑州 450002)
进入新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城乡间的差异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务工来改变生存现状,弥补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在 “城市—乡村” 之间,乡土社会的伦理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留守者与返乡者的关系书写自然成为作家密切关注的话题,而在众多留守者与返乡者中,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更成为作家着重书写的对象。这不仅是因为女性对外界环境的改变更为敏感与细腻,也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话题属性,更在于女性作为较为稳定的 “集团” ,在流动性的乡土社会中,自然形成 “出走” 与 “留守” 两个价值 “集团” ,对其关系的考察与书写,便于更好地观照乡土社会及其价值流变,反思现代性。
一、 “围城” :返乡女性的精神创伤与留守女性的欲望想象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伴随 “进城/返乡” 热潮,乡土社会成为一座 “围城” ,返乡女性与留守女性则成为这座 “围城” 中的人,里面的人想出去,出去的人想回来。在这座 “围城” 中,乡土伦理也面临巨大的考验。进城女性在追求优越物质条件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城市对她们的 “改造” ,自身对金钱的欲望反过来成为操纵她们行为的工具。当她们饱受挫折与伤害,幡然醒悟那刻,城市成为她们渴望逃离之所,乡土成为她们希冀重新开始的地方。返乡,成为进城女性梦寐以求的选择。然而,当返乡的步伐敲击乡土大地时,映入留守女性眼帘的却只有她们光彩照人的外表。于留守女性而言,返乡女性的一切都是如此神秘和新鲜,在她们身上,留守女性展开了对城市充满欲望的想象。
在叶弥《月亮的温泉》中,作家讲述了第一个前往 “月宫” 度假村工作的女人芳,在她再次回到村里时,女人们对她投来的是羡慕的眼光。她 “穿着让女人们看一眼忘不掉的漂亮衣裳,嘴巴上涂着鲜艳的口红”[1]。除此之外,芳更是给娘家人带来了商机与财富,兄嫂建起了村里唯一的麻将室、弟弟开起了发廊。女人们艳羡不已,纷纷跟着芳去往 “月宫” ,唯有少数女性留在村里,特别是谷青凤甘心守着她的20亩万寿菊。然而,丈夫态度的转变以及不动声色的暗示都在提醒她应该去 “月宫” 。谷青凤对 “月宫” 的好奇愈加强烈,她想弄明白 “月宫” 有什么好,能让女人变样,让男人心心念念。作品没有露骨地揭穿 “月宫” 的内幕,也没有清楚地交代芳在 “月宫” 的工作,而是在作品的结尾通过芳的自杀和周围人的笑谈,完成了谷青凤对 “月宫” 的诸多幻想与猜测。我们很难知道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不难想象芳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以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痛心地发现,在留守女人们对芳光鲜亮丽的 “月宫” 生活思慕艳羡、趋之若鹜时,芳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完成了自我的 “回归” 。
同样,在刘庆邦《月子弯弯照九州》中,作家通过 “我” ,一个从北京来月朦胧度假村工作的记者的视角,讲述了单纯善良的姑娘罗兰沦为作陪小姐,最终锒铛入狱的故事。 “我” 告诉她: “转变观念的事也不是谁想叫变就变,谁不想叫变就不变,社会走到这一步了,谁也得跟着走。”[2]如果说 “我” 的点化是将罗兰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第一步,那么月朦胧度假村里的作陪小姐们则是罗兰欲望滋长的催化剂。刘庆邦平静地讲述着乡土社会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留守女性在面对异质文化时不自觉地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推动下,内心的窥探欲望不断萌芽生根成长。当欲望不断蔓延生长之时,留守女性根本无暇顾及,也可以说是轻易忽略掉返乡女性内心的创伤,执着于追求欲望的满足,终将她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在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中,作家塑造了一个在村人眼中的 “榜样式” 人物许妹娜。不同于芳、谷青凤和罗兰,许妹娜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成为城里人,为此,她不惜嫁给了曾经坐过牢的城市小老板。但婚后的生活痛苦不堪,她不仅要接受丈夫的不忠,更要忍受丈夫的毒打。即使如此,回村的许妹娜在女人们的眼里,仍是值得羡慕的对象,是适婚女孩的榜样。作品中,孙惠芬借返乡女性许妹娜在城市与乡村中的不同生活,发出深刻的疑问:难道在城市里过痛苦的生活就真的比乡村好?许妹娜作为村人眼中 “榜样式” 的人物,就真的是留守女性对未来生活的最优选择?在孙惠芬的另一部作品《天河洗浴》中,作家以吉佳的视角讲述两个小姐妹在城里以及返乡的生活点滴,细腻地记录着吉佳对自己、对吉美态度的转变,却对吉美心态的改变只字不提。直到吉佳痛恨村里女人们将她与吉美做比较,甚至母亲都羡慕吉美带回来的金戒指时,作家才将吉美这条隐形线索浮出水面,为自己发声: “吉佳,我做梦都羡慕你……我根本就不想再回去了,可是,可是我妈不让!”[3]作品的最后,吉美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呼声,这是返乡女性渴望逃离欲望之城的真挚呐喊,然而却不足以惊醒在这座 “围城” 中的留守女性。
在方方《奔跑的火光》中,作家塑造了性格要强、目标明确的乡村女孩英芝,然而她从始至终都未能走入正途。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英芝扭曲的价值观,她 “是不安分的。她是不想读书的。她是不喜爱劳动的。她是喜欢以轻松的方式赚大钱的”[4]。对于英芝来说,凤凰垸是她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 “围城” ,她简单地认为赚钱是她摆脱贫困、走出社会底层的捷径,同时又错误地认为女性解放是对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禁区的反叛与突破,而忽视了自身价值的实现以及自我的珍视与自爱。她错误的认知与价值判断,使她如一头困兽始终在 “围城” 中打转,无法逃脱,以致终酿恶果,在一团火焰中不仅葬送了婚姻与年华,更葬送了自己。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像英芝一样在 “围城” 中做困兽之斗的又何止一人?在刘继明《送你一束红花草》中,作家以沉痛的笔调塑造了令人心疼的乡村女孩樱桃,她将青春和生命都留给了自己深爱的土地。为家里拼命赚钱的樱桃,回家后终日要以注射 “赛瑞特” 续命。[5]留守女人们的闲言碎语、父母的不解与怨恨让本已虚弱的她日渐憔悴,她搬进废弃的小破房里,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装作不在意。作家并未过多地描写樱桃病入膏肓时的痛苦,而是以孩童的视角观察着留守女性对樱桃态度的转变。樱桃的返乡顺理成章地将乡村变成一座 “围城” ,乡村是身染重病的樱桃最终的也是最期待的归宿;而最初不明真相的村人却对城市充满欲望,羡慕樱桃父母。到后来樱桃的事情败露,女人们又聚在一起对她指指点点,此时的乡村成为一座 “牢笼” ,一座樱桃渴望以死亡来挣脱的 “牢笼” 。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家笔下,返乡女性内心的伤痕隐藏在她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不易察觉与触碰;而留守女性对城市的欲望与向往则来自返乡女性。这就决定了她们之间必然形成一种 “围城” 状态:留守女性想离开,返乡女性想进来。彼此审视、彼此羡慕、彼此怨怼,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又进不来,她们之间由 “围城” 变成 “牢笼” ,而想要改变现状需要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
二、 “看/被看” :鄙夷、羡慕与理解
在新世纪乡土书写中,伴随 “进城/返乡” 热潮,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一种 “看/被看” 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对女性变化的观察,更是对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审视。从最初乡土小说叙述返乡女性时的羡慕、鄙夷,再到后来对返乡女性的包容和理解,这种转变既是乡村价值观念的转变,更是返乡女性的自我和解和内心秩序的重建。
在艾伟的《小姐们》中,大姐兆曼为了帮助母亲承担家庭责任,很早便进城打工,然而受限于学历和技术的她却并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最终为了能凑齐妹妹的学费,她不顾做人的底线从事卖淫活动。最初,兆曼和父母受到了来自村人羡慕的眼光,然而好景不长,当兆曼不光彩的工作被村人知道后,村里的妇女们扎堆议论,并对兆曼一家投以敌意与排斥,划清界限表明自己的端庄与高洁。作品中,艾伟将 “熟人社会” 为典型特征的乡村展现出来,每个人特别是女性,在谈论家长里短的女人堆里议论别人,同时也被人议论。兆曼在女人们的观看中,犹如被扒光了一样,毫无隐私和秘密可言。母亲在他人鄙夷的眼神中,内心日渐愤怒,她不理解女儿为何要卖淫而让自己蒙羞,更无法原谅她的自轻自贱,母亲坚决不收兆曼从城里寄回来的钱和东西,更不允许兆曼踏进家门,甚至在临终前也留下遗言不让女儿参加葬礼。从艾伟的叙述中,我们更看到兆曼的无助与痛苦,以致她在母亲去世后带着六位小姐跟她一起回乡。兆曼内心是恐惧的,与其说这六位小姐是来帮忙,不如说她们六位的存在是给兆曼壮胆的。母亲的专制、蛮横,村人的鄙夷、厌弃都是兆曼无法正视的困境,她害怕将自己置于 “看/被看” 的关系之中。他人的评判于兆曼而言,何尝不是地狱呢?
同样,在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 “看/被看” 是女性关系书写时一把尖锐的带着血的刀子。在留守女性一次次的 “看” 中,返乡女性内心的伤口被一次次撕开,遍体的伤痕在留守女性的 “看” 之下无处可藏,人生境地也彻底发生扭转。作品讲述了返乡女性李平认识了留守女性蟠桃,二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李平将自己的不堪过往向蟠桃倾诉,蟠桃对她心生怜悯,然而蟠桃却在无意间将此事泄露。李平与蟠桃之间平衡、和谐的关系在秘密泄露后彻底被打破。其他人,特别是留守女性,并未像蟠桃一样包容李平的过往。李平从过去在她们口中人人称赞的好媳妇,变成了被她们指指点点、侧目鄙夷的对象。对于李平来说,乡村是她最后的避难所与栖息地,然而在村人嫌弃的目光中,她再次堕入黑暗的深渊。正如她自己所言: “我迷失了家园,我不知该向何处去,城市不能使我舒展,乡村不能使我停留,我找不到宁静,没有宁静。”[6]李平是可怜的、可悲的,在乡村 “看/被看” 的关系中,她卑微得仿佛一粒微尘,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除此之外,在何顿《蒙娜丽莎的笑》中,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礼却成了他人竞相嘲笑、鄙夷的闹剧。婚礼当天,曾经作为嫖客的副乡长将新娘卖淫的过往肆无忌惮地全盘托出。新娘金小平在众人面前极度尴尬、无地自容,最终她拿起屠刀愤怒地杀死了副乡长,并毫无留恋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何顿以激进的方式书写了返乡女性金小平 “被看” 的窘境,他人的敌意如尖刀一样将她刺穿,当她想余生守在乡下的卑微愿望被他人撕碎时,她的生命之光也就此彻底熄灭。在叶弥《月亮的温泉》中,女人口中的 “一个人就能托起咱村里的半边天”[1]的 “榜样式人物” 芳,最终却以跳桥自尽的方式了却一生。作家并未过多提及芳的死因,但是在叶弥笔下能看到女人们对这个 “榜样式人物” 的羡慕、崇拜与追捧,她的点滴变化都在女人们的 “放大镜” 中。这于她而言,或许只是枷锁与禁锢,绝非温暖与抚慰。在魏微《异乡》中,恪守本分的许子慧在父母和留守者的猜疑中渐失自信,甚至精神恍惚: “这是什么世道,现在连她自己都不信任,她离家三年,本本分分,她却总疑神疑鬼,担心别人以为她在卖淫。”[7]作家毫不避讳地将血缘至亲对女儿的猜疑、和睦乡邻对女孩的议论比作禁锢少女的牢笼,返乡姑娘许子慧不得不做困兽之斗。
无论是《小姐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还是《蒙娜丽莎的笑》《异乡》,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返乡女性身体与心灵的创伤是如何经受着乡人的审视与评判。返乡女性就如同留守女性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一方面艳羡追求返乡女性的光鲜亮丽,另一方面又窥探着返乡女性的过往,一旦发现她们不贞的事实,又随即嗤之以鼻,在这一过程中,留守女性感受到自己的崇高和纯洁,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作家们对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的书写并未仅仅停留在艳羡或鄙夷的层面,而是用悲悯的笔调书写返乡女性的内心创伤,挖掘返乡女性不为人知的人生困境,关注留守女性对返乡女性的同情与理解。
在朱山坡《陪夜的女人》中,陪夜女人在夜间以善良包容之心不厌其烦地听行将就木的老人絮叨他已亡故的妻子。在她的陪伴下,回荡在凤庄夜晚的尖叫声消失了,凤庄人对女人充满感激与敬佩,是她让凤庄的夜晚恢复了宁静与美好。不仅如此,老人的被褥被洗得干干净净,也洗了久病以来第一次澡,生活变得自在舒适。但很快凤庄的女人们得知陪夜女人曾从事过卖淫,纷纷向她投去嘲讽与冷眼。在随后的几天里,女人不再出现在凤庄,老人凄厉的尖叫声又回荡在夜晚。在那些不眠之夜,凤庄人重新审视女人:一个人的过往就那么重要吗?他们从心底里 “原谅” 了女人。几天后,女人再次出现在凤庄,陪伴着老人直至老人离世。老人死后,凤庄的女人才得知女人的遭遇,原来女人的丈夫早亡,儿子又生着病,她们深深同情这个可怜的女人。作品中,作家并未过早提及女人的艰难与不易,而是让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感受女人的善良,发出 “一个人的过往就那么重要吗” 的自我诘问。女人的离开是对自我过往的 “告别” ,凤庄女人们对女人命运的叹惋既是与旧有观念的 “决裂” ,更是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之间的 “和解” 。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对进城女性与返乡女性的关系书写,从最初留守女性鄙夷进城女性牺牲贞操获得财富,到后来留守女性对此不以为意、习以为常,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令人扼腕的转变。作家书写着在城市文明冲击下,乡土社会一方面面临伦理秩序的崩塌,不能为返乡者提供精神力量与支撑;另一方面新的价值标准又没有建立起来,人们只能靠着 “本能” 与 “习惯” 做出价值判断。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乡土社会在求新求变中向好向善,怜悯之心并未消散,人们愿以最大的善意来谅解返乡者的艰辛与不易。
三、结语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作家们饱含深情地对返乡女性的 “无家” 状态投以同情与悲悯。最初她们选择进城源于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渴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在城市中,她们无依无靠、居无定所, “异乡者” 的身份增加了内心的漂泊感,她们渴望在城市所受的伤痛能通过 “返乡” 得以疗愈。但是,留守者怀着对都市的好奇,一方面她们审视着返乡女性的 “异地” 特质,渴望通过返乡女性的 “故事” 满足自己内心对城市的窥探和欲望,于是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之间便形成了 “围城” 的关系模式;另一方面,不光彩的过去、伤痛的记忆都是返乡女性挥之不去的梦魇,留守女性的过分关注让她们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在这种 “看/被看” 的模式中,返乡女性成为乡土世界的 “可怜人” 。值得庆幸的是,在作家笔下越来越多的留守女性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包容返乡女性不堪的过往,并渴望以此抚平返乡女性内心的伤口,疗愈她们的心灵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