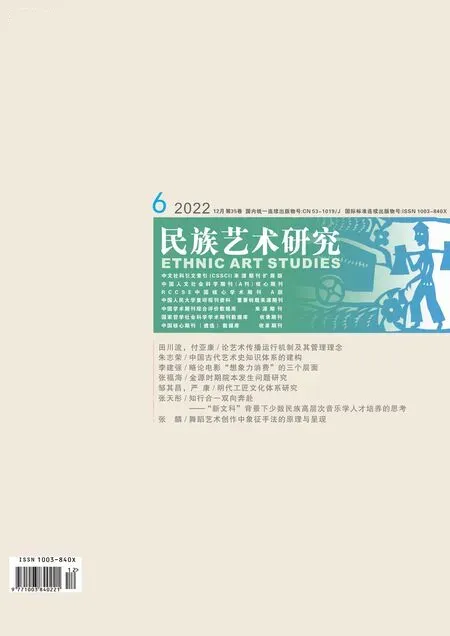对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的反思与批判
穆海亮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源于2002年岁末剧作家魏明伦在凤凰卫视 “世纪大讲堂”所做的谈话。这次谈话激发了 《中国戏剧》编辑的职业敏感性,于是便以此为题,在该杂志开设专栏进行探讨,持续一年之久。此后又趁热打铁,于2003年底在广东佛山召开专题研讨会,为此次讨论画上句号。
从2002年至今,已经过去20个年头。我们之所以重返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的“现场”,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这是21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戏剧理论讨论。不能不承认,理论批评滞后于创作实践是中国戏剧的固有态势,现代中国的戏剧理论批评曾被视为“残缺的戏剧翅膀”①参见宋宝珍 《残缺的戏剧翅膀: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可无论如何,20世纪终究还是出现了诸如五四时期新旧戏剧论争、戏剧大众化、话剧民族化、戏曲现代化以及80年代 “戏剧观”论争等影响深远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一定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真正从整体上关注戏剧自身建设、集中探究戏剧艺术发展规律的理论批评几乎难觅其踪,而“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恰是较为难得的甚至也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次有意识的理论探讨,其参与人员之众、涉及范围之广、观点交锋之激烈都引人瞩目。其二,20年的时间尽管并不算长,但对学术探讨而言,就时间来说,已经具备了 “历史化”的基本条件。当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可以以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其中的理论得失:当年的讨论中所做出的种种 “预判”,在今天得以证实还是证伪?当年探讨的诸多理论问题,对戏剧艺术产生了哪些影响,对今天有何启示价值,或呈现出何种思想局限?当年讨论所涉及的艺术实践问题,今天是圆满解决了还是沉疴依旧?因此,20年后重返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就不单单是在进行理论的反思,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讨论的三个向度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主要围绕一个论题的三个向度而展开。一个论题,即当代中国戏剧的命运 (现实处境与未来出路);三个向度,即戏剧命运怎么样?为何出现这样的命运?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换而言之,也就是当代中国戏剧的命运 “是什么”“为什么”与 “怎么办”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向度,参与讨论者几乎众口一词地承认,当下中国戏剧确实面临重重危机。至于危机的表现及程度,则有不同看法。魏明伦认为,当代中国戏剧之危机并不在于创作的困境,而在于观众的稀少。“当代戏剧的一度创作、二度创作都可以与历代戏剧媲美”,“从剧本到演出,从内容到形式,从发扬传统到紧跟新潮,从京津沪渝到南北省会,人才辈出,好戏连台”①魏明伦:《当代戏剧之命运——在岳麓书院演讲的要点》,《中国戏剧》2002年第12期,第5页。;但问题是,即便戏再好,观众也不上门。魏明伦将这一现象归纳为 “台上振兴,台下冷清”②魏明伦:《当代戏剧之命运——在岳麓书院演讲的要点》,《中国戏剧》2002年第12期,第5页。。一石激起千层浪,魏明伦此言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反响:观众流失、“台下冷清”的说法引起绝大多数剧人的共鸣;至于说 “好戏连台” “台上振兴”,则引来众多戏剧人的反驳。
林克欢认为,魏明伦的观点过于武断和简单化。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中国的戏剧现状,远谈不上人才辈出,好戏连台。台上未必振兴,台下也未必冷清。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剧种,不同的剧目,不同的体制与运作方式,盛衰盈亏,差异极大。”③林克欢:《文化生态与戏剧生存空间》,《中国戏剧》2003年第2期,第18页。刘平认为,所谓 “台上振兴,台下冷清”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从戏剧史的经验来看,如果台上真的 “振兴”、佳作频传,台下的观众一定是非常踊跃的;如果所谓的 “振兴”仅仅是某种外力推动所带来的舞台上一时的“热闹”,那 “台下冷清”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刘平进而指出,“当代戏剧的一度创作可以与历代戏剧媲美”之说不符合创作实际,“今天的观众不愿去剧场看戏,就是因为好戏太少,而好戏少的根本原因是好的剧本太少,再好的导演也做不成 ‘无米之炊’的事”。④刘平:《要 “莎士比亚化”,还是 “席勒化”——关于中国当代戏剧之命运的思考》,载姜志涛、晓耕主编 《叩问戏剧命 运—— “当代戏剧之命运”论文集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362页。基层戏剧工作者黄森林结合自己多年担任县剧团团长的切身经历,指出魏明伦的这种观点 “欠妥”,他自己在工作实践中最深切的感受恰恰是 “好戏太少”:老戏过于陈旧,新戏则大多短命夭折。⑤参见黄森林 《戏曲必须与时俱进》,《中国戏剧》2003年第5期。就连曾做过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曲润海也并不讳言,所谓 “台上振兴”存在虚假的一面,即使获过大奖的戏也不见得好,有些貌似 “阳春白雪”的作品获奖之后就 “寿终正寝”,“雅俗共赏的戏却没有真正受到提倡和支持,广大基层群众能看到的新戏并不多”。⑥曲润海:《从台上台后看中国当代戏剧之艰难》,《中国戏剧》2003年第3期,第24页。谭霈生也认为,戏剧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观众不愿进剧场,而在于戏剧界没有提供足以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优秀作品。⑦参见谭霈生 《生机与自救》,《中国戏剧》2003年第12期。傅谨有所保留地赞同魏明伦所说的戏剧危机之根源不完全在戏剧创作的观点,又做了一分为二的辨析。一方面,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传统戏剧作品 (“好戏”)和戏剧艺人,却缺乏在这样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将优秀剧目和名角传达给大众的途径和手段;另一方面,我们当下对所谓 “好戏”的评判标准存在偏差,不是尊重观众的趣味,而是遵从文化主管部门和 “专家评委”的趣味,尤其是当戏剧的 “赛场”压倒 “市场”之后,“戏剧表演团体与一般观众的审美趣味之间越来越显疏离状态”。⑧傅谨:《工业时代的戏剧命运——对魏明伦的四点质疑》,《中国戏剧》2003年第1期,第14页。在傅谨看来,这才是戏剧危机最主要的表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当下戏剧的危机,大家的争论是建立在某种共识基础上的观点分歧。这一共识就是,当下戏剧确实处境艰难,观众流失严重,但并非只有死路一条,只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戏剧仍能维持其正常的、哪怕是 “一席之地”⑨魏明伦语。参见高扬 《关于 〈当代戏剧之命运〉的几点补充》,《中国戏剧》2002年第12期。的生命延续。既然如此,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要给戏剧望闻问切、寻找病因了。
这就涉及到论争的第二个向度——戏剧为什么会遭遇危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真可谓针锋相对、不可开交。魏明伦将戏剧危机归咎于当代人生活方式、文娱方式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以电视、电脑为代表的 “斗室文娱”和以体育比赛为代表的 “广场文娱”,将戏剧艺术挤压到 “时尚”之外。在这种情势下,戏剧界向来引以为自豪的戏剧注重观演之间当面交流的优势,完全转化为致命弱点,进入剧场交流恰恰成为戏剧欣赏的极大不便;再加上戏剧自身缺乏 “一本万利”的商品属性,与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很难融合,因而 “荧屏时代、网络世界、商品社会、斗室文娱、广场游戏,以及转型阶段人心浮躁等多种因素,导致当代戏剧观众稀少”。①魏明伦:《当代戏剧之命运——在岳麓书院演讲的要点》,《中国戏剧》2002年第12期,第5页。林克欢则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探讨戏剧的生存问题。他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休闲娱乐、艺术欣赏方式日渐多样化的商业时代,观众的分层与流失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演艺市场的重新洗牌也并不令人担忧;但是,今天极其复杂的文化生态确实给戏剧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处在这样的现实场景与整体氛围之下,受着多重压力与多种困惑的戏剧艺术家们,一方面要拆解国家神话的宏大叙说,一方面又要抵制戏说、滑稽模仿、无厘头逗笑的泛滥;既要抗拒日渐物质化、商品化、平面化的生存环境,应对消费文化的大肆扩张,又要克服名誉与经济利益的种种诱惑,努力创造出某种有利于当地戏剧发展的新局面,真是谈何容易。”②林克欢:《文化生态与戏剧生产空间》,《中国戏剧》2003年第2期,第19页。马也从整体上接受了魏明伦的观点,又从全球化和大众文化的学理角度做了更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全球化导致的美国化、快餐化、同一化,以及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传统和经典的消解,都使得文化格局乾坤颠倒,戏剧能够偏居一隅、苟延残喘就已经不错了。于是,马也得出了比魏明伦还要悲观的结论:“‘戏剧的命运’从根本上说,是掌握在 ‘时代需求’这只看不见的手中。如果是时代不需求、不怎么需求、很少需求、少部分需求、大部分人不需求,戏剧自身再努力,也难以走出困境。”③马也:《当代戏剧命运之断想》,《中国戏剧》2003年第6期,第8页。
傅谨则明确反对魏明伦的 “斗室文娱”说。他认为,将电视的兴起乃至于多元娱乐形式的出现看成戏剧陷入困局的原因,“这样的论断实在是肤浅、皮相之至”。其理由是,电视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它固然可能使得一部分人改变去剧场看戏的习惯,但也可能成为非常有效的传播工具,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戏剧表演,进而因喜欢上戏剧而走进剧场;更何况,如果文化娱乐更为繁荣的欧美发达国家并未出现今日中国戏剧这样的危机局面,如果当下中国同样受到电视等多元娱乐形式冲击的出版等行业也没有陷入戏剧这样的危机中,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今天中国戏剧的危机是由多元娱乐形式的兴起造成的呢?因此,在傅谨看来,戏剧危机另有原因。他论述较多的,一是非市场化的体制弊端,二是传统的断裂:“中国戏剧确实存在危机,一方面是悠久浓厚的戏剧传统只有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另一方面是经过 ‘文革’前后十多年的断层,演艺人员的表演艺术水准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些历史造成的原因,加上戏剧长期处于非市场化的体制之中,很难吸引一流人才 (优秀编导人才的流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都决定了目前中国戏剧的艺术水平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高度。”④傅谨:《工业时代的戏剧命运——对魏明伦的四点质疑》,《中国戏剧》2003年第1期,第14页。曲润海也不认同魏明伦的说法。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戏剧管理的文化工作者,他很坦诚地指出,管理体制和指导思想的陈旧与死板,是造成戏剧危机的重要原因。⑤参见曲润海 《从台上台后看中国当代戏剧之艰难》,《中国戏剧》2003年第3期。
当很多戏剧家把戏剧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多元娱乐、大众文化、商品社会、管理体制等外部环境时,也有少数戏剧人将对戏剧危机的思索指向了戏剧自身的艺术生态。彭奇志首先承认,戏剧危机当然有其外部原因——民族认同危机和戏剧消费主体社会边缘化;同时,中国戏剧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一是艺术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多年亏欠,艺术产品有效供应不足;二是艺术生产单位体制性矛盾突出,使文化没有形成利益驱动下的多元化投资体系;三是戏剧的功能在当代起了潜性的变异,民间的、自娱的、自发的功能被无形地隐藏,微妙地取而代之的是宏大的教化的功能。”①彭奇志:《在重构中重生》,《中国戏剧》2003年第10期,第6页。
既然关于戏剧危机的 “病因”众说纷纭,因而针对 “病因”而讨论的第三个向度——戏剧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大家提出的 “救治”方案自然也就各不相同。大体而言,可分为三类。其一,强调国家政策对戏剧的支持与保护。比如魏明伦指出,既然戏剧的危机主要不是由其自身造成的,而源于外部环境的挤压,那么戏剧在这一特殊困难时期,更需要有人来 “养”,国家必须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扶持。这一说法得到了多数讨论者的赞同,尤其从那些基层戏剧从业者的发言中,更能体会到其渴望得到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的强烈愿望。至于具体的扶持策略,则在大同之中又存小异。其二,呼吁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尤其重要的是把戏剧推向市场,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戏剧适应市场的能力。这一观点以傅谨为代表,同样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戏剧不能完全脱离市场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当然,讨论者同时指出,在市场本身尚不成熟、机制尚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戏剧暂时仍然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但扶持不是最终目的,暂时的 “供奶”是为了以后更好地 “断奶”。其三,倡导从整体上优化戏剧生态,营造有利于戏剧发展的空间,这就需要内外兼修。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如彭奇志指出的——既要优化戏剧的外部环境,使其能够面向市场;同时戏剧自身也要通过内在调整,完成戏剧本身的现代性重构。王蕴明则强调:“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化、现代化与多元化、大众化与小众化、面临市场与坚守文化品性、创作自由与导向性的关系。”②王蕴明:《近视与远瞩——也谈当代戏剧之命运》,载姜志涛、晓耕主编 《叩问戏剧命运—— “当代戏剧之命运”论文集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336页。
二、戏剧 “向外转”的理论倾向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早已落下帷幕。当喧哗过后,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回顾这次讨论,坦诚地讲,我们的感受不免有些复杂。一方面,从参与讨论的诸多文章看,不管是面对戏剧危机的焦虑、无奈甚至哀叹,还是为振兴戏剧而摇旗呐喊、出谋划策,都体现着艺术家和理论家们维护戏剧艺术的拳拳之心,这着实令人感动;而且,其中的某些论述确实扣住了戏剧发展的脉搏,甚至闪耀着思想的火花,时至今日仍能引人思索,并引发一定的回响。比如,戏剧人在讨论中发出呼吁,希望以国家政策扶持戏曲发展,这在今天已有现实的响应,尤其是包括国务院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还有国家艺术基金等各个层面对戏曲艺术的持续资助,戏曲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甚至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此背景下,理论家当年倡导的对戏曲之 “传统”的高度重视,在今天也已成为剧界的共识,乃至全社会已形成了尊重和弘扬戏曲传统的良好氛围,并正在自上而下地促进戏曲传统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再如,傅谨等理论家大声疾呼戏剧体制改革、推动戏剧艺术的市场化,这些声音今天仍然值得重视,尽管戏剧市场化的过程十分艰难,改革的效果也尚未充分彰显,但无论如何,这一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相关工作实际上也在逐渐推进中。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这场21世纪以来绝无仅有的大规模戏剧理论探讨,在理论建设方面并未结出真正的硕果。更有甚者,其中不少参与讨论的文章,由于与戏剧艺术本体、创作实践有着较多隔膜,几乎仅仅成为一纸空文的话语狂欢,因而也就难以对当时乃至此后的戏剧发展 (尤其是戏剧创作),产生真正强有力的理论指引。究其原因,固然与戏剧生态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但同样不容忽视的因素还在于,本次讨论呈现出显而易见的甚至颇有些极端化的 “向外转”的倾向。这就是说,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戏剧危机的外在表现、造成危机的外部原因、解决危机的外部策略,而真正围绕戏剧艺术本体所展开的学理性探讨则远远不够深入,因而使得其理论建构存在明显局限性或错位。
首先,这次讨论 “向外转”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由论题本身决定的。“当代戏剧之命运”这一带有 “悲壮感”和 “预言性”的论题,几乎注定了其讨论的焦点被置于戏剧的外部环境。这从肇其端的魏明伦宏论中就显示出来了。既然在魏明伦看来,中国戏剧的危机并不是没有好戏,而是戏再好观众也不来看,那么,这就不是戏剧本身的原因了,其 “罪魁祸首”必然在于恶劣的外部环境。因此,此后的讨论主要就围绕戏剧危机的外围因素而展开,将戏剧危机的表现归结为观众流失,戏剧危机的原因归咎于斗室文娱、商品社会、大众文化的影响和体制的束缚,将解决危机的策略寄托于政策扶持、市场化改革,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外部阐释的必然结果。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是对戏剧外部生态环境的讨论,原本也可以触及诸多方面的问题,但这次讨论却把重心放在了诸如时代更替、社会变迁之类客观环境造成的 “外部问题”上,而很少论及人为原因导致的戏剧艺术本体自身的 “内部问题”。其实,正如署名 “朝问”者所指出的那样, “三分人祸”即戏剧创作出现问题是 “导致戏曲从 ‘危机’走向更大的 ‘危机’,直至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①朝问:《生于民间 死于殿堂》,《中国戏剧》2003年第10期,第15页。然而,在具体的讨论中,更多讨论者都倾向于将其归咎于 “外部问题”,而有意无意地规避人为原因导致的 “内部问题”。关于 “外部问题”,可以畅所欲言;而一涉及 “内部问题”,大家就心照不宣地顾左右而言他。
其三,即使只论 “外部问题”,原本也可以富有学理性,正如傅谨、马也那样真正呈示深层探讨的文章,即使我们不能认同其观点,但其思考的深刻性也能给人以启示。可遗憾的是,在这次看似十分激烈的讨论中,真正在深刻的学理层面展开论述的只是少数,更多的讨论并无学术及实践价值。有的是一些浅表化的泛泛之论;有的是为了辩论而辩论,看似针锋相对,其实是断章取义;有的是自说自话——如:编剧强调自身的创作成绩,基层院团领导呼吁资金支持;有的看似深奥,实则故弄玄虚——如:对 “场”之问题的纠缠不清,看起来颇有些吓人,但实际上距离戏剧艺术的本体相当遥远。等等。
对戏剧而言,外部环境固然不能说不重要,尤其跟其他艺术门类比较起来,戏剧所受的外部影响恐怕是最为明显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有着独立审美价值和完整艺术自律性的艺术门类来说,如果仅在外部环境里打转,而对其艺术本体的关注和思考不够深入,其讨论就难免遭遇理论的错位,戏剧自然也是如此。过多地关注外因 (外部环境)而忽视内因 (戏剧本体),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在讨论 “外部问题”时,过多意气之争而较少理论建树,可以说是隔靴搔痒。指望本末倒置、避重就轻、隔靴搔痒的讨论产生深刻价值和深远影响,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关于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这一 “向外转”的倾向,谭霈生在当时就意识到了:“如果我们把 ‘外部问题’视为高于一切的关键,而忽视对 ‘内部问题’的正视,并不利于讨论的深入。”②谭霈生:《生机与自救》,载姜志涛、晓耕主编 《叩问戏剧命运—— “当代戏剧之命运”论文集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刘平也在讨论中明确指出,戏剧的危机不在观众,而在自身,并不是因为有了 “斗室文娱”观众才不进剧场,而恰恰是戏剧创作者把观众从剧场里 “赶跑了”,“不是观众 ‘很难安心坐下来陪同台上演员对面交流’,而是有些舞台创作 ‘割断’了观众与演员交流的渠道和机会,使得观众无法与台上的演出交流。所以,观众才没有了看戏时的审美愉悦,从而产生了失望情绪,而远离了剧场。”①刘平:《要 “莎士比亚化”,还是 “席勒化”——关于中国当代戏剧之命运的思考》,载姜志涛、晓耕主编 《叩问戏剧命 运—— “当代戏剧之命运”论文集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页。
那么,戏剧的内部问题究竟是什么?其实这又回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戏剧创作的困顿。刘平认为:“理论偏颇和创作思想的狭隘造成了作品内容的浅薄,创作上的‘一窝蜂’造成了艺术上的公式化与概念化,创作观念的陈旧导致作品中缺乏思想。”②刘平:《要 “莎士比亚化”,还是 “席勒化”——关于中国当代戏剧之命运的思考》,载姜志涛、晓耕主编 《叩问戏剧命 运—— “当代戏剧之命运”论文集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368页。这些观点并不新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影响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痼疾,进入21世纪之后也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如果戏剧创作停滞不前,那么戏剧危机也就不太可能得到缓解,当戏剧家无法提供优秀作品时,想把观众吸引进剧场就只能是一种痴心妄想。所以,观众的流失是戏剧创作出现问题的结果,而不是戏剧危机的原因。但遗憾的是,“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一窝蜂地指向外部环境,一味地对戏剧的恶劣环境倒苦水,真正属于戏剧本体的问题反而被搁置了。
三、戏剧危机与 “理论疲劳”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的 “戏剧观”论争和21世纪的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贯通起来考察,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当代戏剧理论 “向外转”的清晰轨迹。早在 “戏剧观”论争开始时,戏剧人已经意识到戏剧危机的原因在于戏剧本身,陈恭敏将其归结为 “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和 “公式主义的形象图解”③参见陈恭敏 《戏剧观念问题》,《剧本》1981年第5期。,前者指向戏剧审美形式的僵化,后者指向戏剧思想内容的庸俗社会学。既然如此,如果要真正解决戏剧危机,也就自然需要内容与形式双管齐下。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戏剧观”的论争主要集中写实与写意、舞台假定性等戏剧形式方面的问题,而戏剧题材内容的维度则被有意无意地悬置了。从反思内容转向讨论形式,可以说是戏剧理论的一次 “向外转”;不过,由于形式毕竟也属于戏剧本体的范畴,所以在突破机械的写实主义、探索剧作风格及舞台样式多样化方面,“戏剧观”论争终究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到了21世纪的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其则不仅很少关注戏剧内容,而且就连20世纪80年代热衷讨论的戏剧形式问题,也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大家都集中“火力”去讨论戏剧的外部环境问题了。这显然是戏剧理论建设又一次的 “向外转”。颇有意味的是,马也在1986年对 “戏剧观”论争的形式化转向所作的机智风趣的描述,也十分具有前瞻性地 “预言”了21世纪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的走向。马也这样说: “从‘假、干、浅’转到 ‘形式呆板’ ‘手法老化’,从公式主义的观念图解转到 ‘公式主义地套用形式’,从 ‘不真’转到样式的 ‘不新’,从内容转到形式,从内科转到五官科,从内里的不美转到容颜的不美,从容颜的不美转成镜子的不作美。”④马也:《理论的迷途与戏剧的危机》,《戏剧》1986年第1期,第5页。如果说 “戏剧观”论争是 “从内科转到五官科,从内里的不美转到容颜的不美”,那么,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就确实是 “从容颜的不美转成镜子的不作美”了。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呈现出这样的局面,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关于戏剧题材内容的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就被“疏导”了,这在21世纪同样不大可能深入展开,即使要谈,也只能是谈诸如概念化、公式化、工具主义等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另一方面,关于戏剧形式的开拓在20世纪80年代是困扰戏剧家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之一,但在21世纪剧坛,随着戏剧叙事与结构方式的灵活拓展、戏剧风格的新奇绚丽呈现、技术手段的突飞猛进,舞台形式早已变得极其丰富,戏剧形式早已不再成为问题,自然也就不大能够引起人们讨论的兴趣了。既然形式问题不必讨论,而内容问题仍然不便讨论,所以面对越发严重的戏剧危机,戏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理论疲劳”。更何况,当20世纪80年代 “戏剧观”论争时,人们意识到危机,也能看到解决的途径,大家就对理论抱有很高的热情;而20年过去,当戏剧危机已深入骨髓 (已经到了要探讨 “命运”的阶段),甚至如果真的像某些戏剧家所预言的那样,戏剧已经不被 “时代”所 “需要”了,那么,戏剧人对于理论研究不仅会感到“疲劳”,更有甚者,任何理论讨论都可能是“徒劳”的。
在新时期戏剧40年之际,著名导演王晓鹰以亲历者的身份重新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戏剧的创新问题,说了下面一段话:
今天的戏剧艺术所面临的创新课题肯定要比当年多得多也广泛得多,譬如院团管理机制的创新、优质资源整合的创新、社会合作乃至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以现代理念进行宣传推广和市场开拓的创新、持之以恒的观众教育培养计划等方方面面的创新。但是戏剧的根本问题还是创作问题,如果只从创作层面上讲,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面对30年前的 “新时期戏剧”遗留下来的那个问题,即突破在创作中妨碍我们更好地表现人的深刻性、复杂性、独特性的思维模式,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藩篱,现在还要加上突破政绩化、功利化、浅薄化、庸俗化的羁绊,以争取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表达的自由。①王晓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戏剧 “创新”问题再思考》,《文艺报》2018年7月23日。
在王晓鹰看来,今天戏剧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固然有很多不得不依赖于戏剧外部环境的优化来解决,诸如剧团管理、资源整合、市场开发、宣传推广、观众教育等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终究还是戏剧创作,尤其是在旧有的公式化、概念化痼疾尚未根除的情况下,又叠加了政绩化、庸俗化的羁绊。在这样的语境中,王晓鹰所期盼的 “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表达的自由”,仍然是一种美好而遥远的愿景,而 “当代戏剧之命运”讨论的 “向外转”与 “理论疲劳”,就更是难以避免出现的必然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