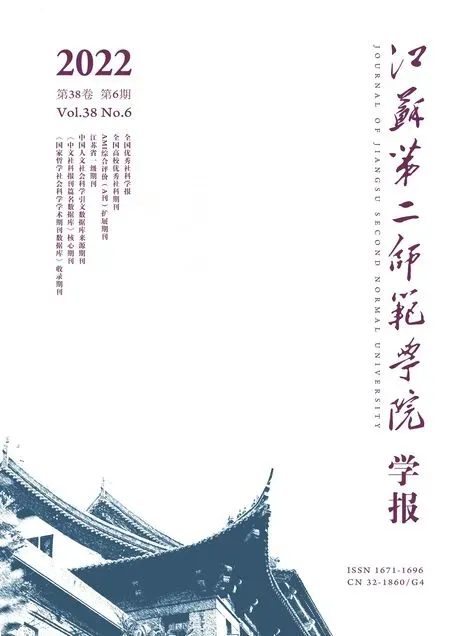论金圣叹评点中“梦”的观念
吴 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古今小说评林》中说:“中国小说,无一书不说梦”[1]650。明清时期小说、戏曲创作中“梦”的元素颇多。小说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红楼梦》,戏曲诸如《西厢记》“临川四梦”《清忠谱》《长生殿》,书写梦境的场景逐渐隆丰,发展形成明清文学的一大特色。评点家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与《西厢记》,使两部作品均以梦境作结,凸显了“梦”意象所具有的特殊意蕴和审美价值。因此,有必要对金圣叹此举进行深入考察,以了解其思想动机和本质意义。
一、《水浒传》释梦
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十三回的总评里说道:
一部书一百八人,声施烂然,而为头是晁盖先说做下一梦。……然而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尽大千世界无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觉者,自大雄氏以外无闻矣。真蕉假鹿,纷然成讼,长夜漫漫,胡可胜叹![2]262
这段话首先从小说的虚构性特征入手肯定了其独立艺术价值。明清以前,小说文体长期处于史传文学的附属地位,“历史文本所拥有的强大权威性,决定了它在中国叙事文类中的绝对权威”[3]。然而金圣叹却认为作为“稗史”的《水浒》更胜《史记》一筹,原因是《史记》是有“事”在先,是作者“以文运事”;《水浒》是作者“心闲弄笔”,杜撰出来若干故事,是“因文生事”。故而欲说水浒“一百八人”,先说“一梦”。与纪实性文体不同的是,小说创作遵循的是“情感逻辑”,从追求“历史真实”转向追求“艺术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圣叹对“梦”话语的重视,将小说从“正史”的遮蔽带到了阳光之下。
其次,对“梦”的呈现,保证了“大千世界”的完整性,正如金氏所说“大千世界无不同在一局”,由此引申出的虚实、有无、真假等概念也时刻处于循环往复、不断变动的关系之中。此章还说:“晁盖为一部大书提纲挈领之人,而为头先是一梦,可见一百八人、七十卷书,都无实事”[2]272,出于这样的认知,金圣叹在他的评点工作中也做出了理所当然的个性化创作,即“腰斩”了《水浒传》,有如“大梦初醒”一般,让叙事停留在最富于包孕性的那一刻:
或问:石碣天文,为是真有是事?为是宋江伪造?此痴人说梦之智也,作者亦只图叙事既毕,重将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来,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聚一百八人于水泊,而其书以终,不可以训矣。忽然幻出卢俊义一梦,意盖引张叔夜收讨之一案,以为卒篇也。[4]1234
在金圣叹看来,“晁盖七人以梦始,宋江、卢俊义一百八人以梦终,皆极大章法”[4]1249,这是指作者叙事文法之高蹈。对于故事情节而言,晁盖之梦看似祥瑞,实是悲剧之开始;卢俊义之梦看似凶险,却是“真正吉祥文字”[4]1250,这种意义上的颠倒置换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
与此相关,在艺术真实里“梦”的书写也为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形象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以第四十一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为例,这是以宋江视角呈现的一个梦,金圣叹认为这个梦是“春秋笔法”,揭橥宋江的真实动机。明明是危难之际幸得神灵庇护的场景,却写得鬼影幢幢,令人惊惶难安;小说中用了数处“抖”字来刻画宋江的慌迫情态,这显然与他在人前那种正气浩然的形象是大相径庭的。至于宋江所得玄女所授“替天行道”的三卷天书,金圣叹认为这完全是“宋江权术”:
玄女而真有天书者,宜无不可破之神师也;玄女之天书而不能破神师者,耐庵亦可不及天书者也。今偏要向此等处提出天书,而天书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则宋江之所谓玄女可知,而天书可知矣。前曰:“终日看习天书。”此又曰:“用心记了咒语。”岂有终日看习而今始记咒语者?明乎前之看习是诈,而今之记咒又诈也。[4]931
也就是说,宋江口中的这个梦是假的。通过此梦,宋江取得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顺理成章成了水泊梁山/江湖世界的“僭主”。为了证明这一点,金圣叹解读了第六十四回“托塔天王梦中显圣”的内涵:“晁盖走而宋江之毒生,晁盖死而宋江之毒成。至是而大书宋江疽发于背者,殆言宋江反状至是乃见,而实宋江必反之志不始于今日也。观晁盖梦告之言,与宋江私放之言,乃至不差一字。”[4]1150因此可见,“梦”里所表现的是某种不能宣之于口的情感,是现实的隐喻和镜像,犹如冰山一角,在潜意识中浮沉闪现,却遥指梦者的“心”。
二、《西厢记》释梦
无独有偶,金圣叹不仅让《水浒传》止于“惊梦”,也让《西厢记》止于“惊梦”,这种形式上的切割使我们坚信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行为。他还为此做出了长篇的陈词说明,择要辑录如下:
今夫天地,梦境也;众生,梦魂也。无始以来,我不知其何年齐入梦也;无终以后,我不知其何年同出梦也。夜梦哭泣,旦得饮食;夜梦饮食,旦得哭泣。我则安之其非夜得哭泣,故旦梦饮食,夜得饮食,故旦梦哭泣耶?何必夜之是梦,而旦之独非梦耶?
……吾闻周礼:岁终,掌梦之官,献梦于王。夫梦可以掌,又可以献,此岂非《西厢》第十六章立言之志也哉,而岂乐广、卫玠扶病清谈之所得通其故也乎![5]1080
金圣叹分别从几个层次谈“梦”的价值:其一,“梦”来自文学传统。他引用了《列子·周穆王第三》“蕉叶覆鹿”的典故来说明,梦境与现实一线相牵,互为因果。能够分辨梦境与现实的,恐怕只有圣人而已。然而圣人已矣,普通人又岂能够妄言参悟呢。所以,“至人无梦”,和其光、同其尘,“随梦自然”,不抱执念,醒后即淡然忘却;而“愚人无梦”,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以梦为实,以假作真,从而陷入业障。他又举“庄周梦蝶”的典故,指出庄子以“物化”的方式来处理“梦”与“觉”之间的联系与界限,最终达到人我尽泯,万物共寂的境界。“蕉叶覆鹿”和“庄周梦蝶”这两大意象母题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被反复征引,金圣叹用于此处是劝喻读者不必执着于“西厢”一段情事,但却需仔细领略其中缘法滋味。并且还将《西厢》书写一段情事的立意,由老生常谈的“才子佳人”说升华到“生死”“有无”的哲思层次之上。其二,“梦”来自巫史传统。《诗经》有言:“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6]146就是说,在古时候,“梦”是用来占卜祈愿的,人们凭着质朴的经验来预测尚未发生之事、以及可能发生之事。孔子“不梦周公”久矣,不惟不梦见周公,亦存有“忘我”之义,将世上一切名利现象一并抛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可以虫则虫,可以鼠则鼠,可以卵则卵,可以弹则弹,无可无不可,此天地之所以为大者也。”[5]1083在金圣叹看来,人生在世,即便成为国王,成为后妃,其前身不过由一熊一蛇幻化而来。因此,形式为何,是最不重要的,不要沉溺于梦境幻想,只要关注当时当下,“歇担吃饭,洗脚上床”,这就足够了。
此外,圣叹所说“梦可以掌,又可以献”是指:“梦”的设置在文本中起到的是工具性的作用。以“梦”为基点来形成某种氛围,或建构一种情境,这是一种符合艺术规律的创作技巧。高明的写作往往有如“羚羊挂角”,不着一丝痕迹。与解读《水浒传》相应,在解读《西厢记》时,金氏更加直接点出“梦”即是由“心”幻化而来:
夫天下后世之读我书者,彼岂不悟此一书中,所撰为古人名色,如君瑞、莺莺、红娘、白马,皆是我一人心头口头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无极,醉梦恐漏,而至是终竟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之人之事以自传,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来,七曲八曲之委折乎?[5]893
“岂红娘今日在梦,抑或红娘前日在梦?”[5]999金圣叹不断提醒读者,莺莺事无迹可寻,不过像庄生之蝴蝶那样,仅仅是一名称、是一符号而已。不过与直接“腰斩”《水浒传》的做法不同,金圣叹在评点之时保留了《西厢记》后四篇,但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知道,续本刻意追求“佳人配才子”那种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局,正是陷入了愚人思维,是东施效颦、狗尾续貂:“使普天下锦绣才子,读《西厢》正至飘飘凌云之时,则务尽吹之到于鬼门关前,使之睹诸变相,遍身极大不乐,而后快于其心焉。”[5]1113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水浒》《西厢》中“梦”的论点并不只是他一人见地,在他之前王圻也曾提到:“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独活耳。”[7]503这说明,正是因为“梦”的存在,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能够一波三折、迂回演进,使故事中的人活动起来、生动起来,同时为读者制造出朦朦胧胧、亦幻亦真的阅读感受。(1)关于王圻此说中提到的“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曾经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界引发了对“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一说的争议。王齐洲《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无可怀疑——与周岭同志商榷》一文认为,王圻所谓“梦事”并非即指七十回本之恶梦,也有可能指百回本之“美梦”。本文引用此例意在说明,无论其究竟所指为何,“梦”在文本当中的虚构意义和功能性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三、“梦”的审美意涵探源
由是观之,在金圣叹的评点理论中,“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实际上,这种“梦”的意识不仅体现在他对小说、戏曲等文学体裁的评价中,在他其他论述中也经常可见。这首先与他的哲学见解相关联。如前文所述,“庄周梦蝶”之掌故也出现在圣叹内书《杂华林》之中,用以阐释《易经·系辞》“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三句:
庄周生出来时,也是“大哉乾元”,偶然入梦,焉知庄周不错做庄周?蝴蝶亦然。庄周入梦,不图蝴蝶;蝴蝶出梦,又一庄周。前身化后身,竖里边化;彼身化此身,横里边化。“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道”者,范围之道也。[8]834
《杂华林》可视作熔铸金圣叹禅学、玄学和儒学修养为一体的思想论纲,其中蕴涵了他理解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其艺术和审美观念的基石。此句所说“庄周生出来时”,就是生命的起点,是自我意识萌发的时刻,即是“大哉乾元”;而“庄周梦蝶”作为人生此在一桩偶发性的事件,又激发了对于身心关系的思考,从而进入到“性分”与“物化”的理论范畴。他又引用《论语》“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说明“万物有序”这一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基本法则。从心而起,归于自然,这也是艺术世界生成和运行的法则。
金圣叹在解读唐才子权德舆《待漏假寐梦归江东旧居》一诗的“南宗长老知心法,东郭先生识化源”时,又再次提及和申明了释道同源的观念。他说,“十年江浦卧郊园”是作者个人际遇,是一念所起,是“梦之宿根”;“舍下烟萝通古寺”是作者眼前所见,是“梦之现量”。在似梦似醒的片刻,“我”蘧蘧然、栩栩然回到了旧时寓所,身心飞扬有如蝴蝶自在自为,摆脱了形体的拘役和束缚;梦醒之际又认清自己的所处,正襟正色,守住本己本分,素位而行。从这些评点内容来看,道心禅思确实是金圣叹“梦”之理论的思想底色。
其次,“梦”中充分寄寓了金圣叹其人的家国情怀以及社会理想,这与他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规训和濡化的儒家知识分子身份紧密相关。金圣叹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清易代之际,和所有身处末世的士人一样,生活无可避免地陷入离乱与怆恸。所以他评点杜甫《北征》一诗,即是将自身的情感境遇带入诗人的创作情境当中,从而更深切地体会到诗人的一片拳拳赤子之心:“题是北归,通篇诗全是忧劳朝廷,一片深心至计。虽十六解至二十三解稍叙妻女,然纯是心在朝廷,恍惚如梦语。读之悲感横生,涕泪交下”[9]662。对另一首杜诗《昼梦》他更直言:“世人皆醉,何我独醒;世人皆梦,我何不梦?只是眷恋君国之意,耿耿胸中,有不能睡者耳”[9]793,乱世荆棘、百姓流离,正是令诗人辗转难眠、魂梦相牵的心结所在,故而只能白日做梦、聊以抒怀。金圣叹感到自己也像杜甫一般,虽然对现实感到挫败和无力,但又心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好反身向儒家的圣人叩问,并将今古对比讽喻,认为世间一切种种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所以他在《小题才子书》对王锡“吾其为东周乎”一文解读时说:“尝怪杜丽娘是世间第一痴女子,岂料先师早已是世间第二痴先生耶?一路睡重梦深,哭笑聚集”[10]670,也是出于这种忧思深重的心意。
除此之外,在厘清“梦”生成的心理机制后,金圣叹做出趋于审美的判断。这也是他的评点理论颇具现代色彩的地方,即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梳理,精准捕捉创作主客体之间那种心神相会和本质直观的一瞬间。诚如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一文所谈到的那样:“当一个作家把他的戏剧奉献给我们,或者把我们认为是他个人的白日梦告诉我们时,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快乐,这个快乐可能由许多来源汇集而成”[11]33,批评家金圣叹也力图向读者揭示深藏在文本背后的情感秘密。例如,他评点唐才子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时说:“才睡得即又梦,才梦得即又觉。迷迷离离,恰似家中握手;淅淅沥沥,早是船背雨声也”[12]276,讲的就是由梦境而带来的恍惚惘然的心理体验;评点皮日休《病后即事》时说:“乃今病如得去,必当愁将又来,譬如初月再苏,终至渐渐盈满,可奈何?然我亦惟悉将春梦,尽付浮云,并弃笔墨,永除绮语”[12]517,形容的则是凝神沉思之际,将万事看淡看空,宁静邈远之境界。这种释读蕴含了明清之际审美鉴赏的一种转向,从传统对经世价值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守望逐渐扩展至对个体心灵与形而上先验世界的探索和体认。
不仅如此,在金圣叹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梦”意象也被反复抒写,《沉吟楼诗选》当中有27首诗都与“梦”相关。《赠夏广文》中“潦倒诸生久白头,十年梦断至公楼”表达久未入仕、报国无路的郁结;《骤寒有感》中“他国迢遥惟有梦,故乡酬对更无亲”表达家国动荡、老病无依的孤苦;《游龙门奉先寺》中“下民全梦寐,上界入玻璃”表达对晨钟暮鼓、山高境深之域的神往;《痴叔》中“应是池塘无限草,春来夜夜梦中生”表达对清新隽永、自然天成之韵的礼赞。以金圣叹为代表的评点家通过对小说、戏曲等流行艺术进行“净化”与提炼,又对诗词等传统艺术进行重新释读,从而转向对“梦”或曰心灵、情性的张扬,促成了明清之际的审美转向,启发了新颖又深刻的美学风尚和文艺思潮。
四、金圣叹“梦”观念之本质及影响
实际上,就对“梦”意象的重视和运用而言,金圣叹诚然是个很好的代言人和示范者,但“如梦似幻”的人生体验不仅深深存在于他一人的思想当中,更深深地镌刻进同时代士人的灵魂和心态当中。明末清初是“传统中国”最为绚烂、也最为动荡的一段历史时期。晚明边地叛乱迭起,政坛党祸不断,最终酿成鼎革易代的后果;但与此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也造就了精神世界的变革。
这一时期在思想领域,表现为理学的衰落和心学的兴起,其中还包涵了儒家与释家、道家思想的深度合流和异质同构。晚明高僧憨山德清作《梦游诗集》,序说“三界梦宅,浮生如梦,逆顺苦乐,荣枯得失,乃梦中事时”[13]381,佛家释“梦”为入世与出世的“法门”,这为当时很多的僧众参与到市井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而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一方面固有的儒家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风雨飘摇,一方面仍需要为了心灵有所皈依而孜孜以求,故而逃向佛老或其他。由于面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局面感到无能为力,佛家的视角或多或少为心灵正在焦灼地左突右进的儒士们带来一丝微光。为乱象的存在和出路为何寻找到合理的解释,成为文人笔墨价值所在。晚明张岱曾作《自为墓志铭》: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真如隔世。[14]159
由是可见,奢华和享乐成为人所共趋的生活方式,那种对日常生活所涉之物的精心照料,似乎有助于士人排解因外部世界冲突而导致的身心焦虑,从而制造出一个相对安逸平静的假象。但当国破家亡之际,逃无可逃,无所寄托,过往种种不过大梦一场,醒时烟消云散,四顾一无所有。也是在这种“梦幻”心境当中,张岱还写下《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文集,以寄托故国之思、黍离之悲。至于清初大儒王夫之所著《噩梦》为其政论文集,自序其旨是:“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故曰‘噩梦’”[15]549,这更表明,儒士的一腔愤懑孤心难酬,又无处宣泄纾解,只好向天叩问,寄托“梦”思。
在文艺领域,作家通过想象、虚构等方式构筑出现实之外的另一“理想国”,以弥补现实生活的缺憾,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之感。明清之际的“梦幻”文学广受市场的欢迎与追捧,小品文、小说、戏曲等文体也因此风靡一时,其中缘由即起于此。王望如对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深表服膺:“细阅金圣叹所评,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以‘天下太平’四字;始以石碣放妖,终以石碣收妖,发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抬举李逵,独罪宋江,责其私放晁盖,责其谋夺晁盖。其旨远,其词文,而余最服其终之以恶梦,俾盗贼不寒而慄。”[16]41尽管这不能概括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全部动机,但是也反映出经由他手裁定而刊行的作品能够占领市场的重要原因,即借梦中言、梦中事来隐喻自身的理想抱负,表达对国家安定和政治清明的愿景向往。
除了现实功用之外,梦书写体现出更多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正如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五回的总评:
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独是矣。耐庵忽然而写瓦官,千载之人读之,莫不尽见有瓦官也;耐庵忽然而写瓦官被烧,千载之人读之,又莫不尽见瓦官被烧也。然而一卷之书,不盈十纸,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须臾,三世不成戏事耶?又摊书于几上,人凭几而读,其间面与书之相去,盖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间,又荡然其虚空,何据而忽然谓有瓦官,何据而忽然又谓烧尽,颠倒毕竟虚空,山河不又如梦耶?[2]145-146
在金圣叹看来,瓦官寺一起一倒,只是作者乘兴杜撰,读者无须考证,也无从考证,只要沉浸在读书的一时一刻里,能够随物宛转、心有所动便是最好。要之,这种“梦幻”意识在社会思潮和文化观念的裹挟之下不断发展演进,对文学创作与鉴赏均产生重要影响。所谓“景之奇幻者,镜中看镜;情之奇幻者,梦中圆梦”[4]911,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如果说前期的作品还只是偶尔以梦为故事引子,那么到了后来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则是彻头彻尾讲“梦事”,将梦幻观念发挥至极致。正如《红楼梦偶说》所讲:“浮生若梦,《红楼梦》一书之所以名也。斋惟梦坡,院有怡红,而造楼高手,总属大观。大端即是在在以梦点醒,而又非沾滞如痴人说其间。是梦非梦,无非是梦,即是太虚幻境也,即无非阅世人真境也,即无非本性人心境也,则又以不梦为梦矣。”[1]125因此,无论以作者还是读者角度来看,对“梦”意象的把握,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心灵世界的本质直观。
从明清以来的小说、戏曲发展史来看,“梦”之创作逐渐由猎奇猎怪、增强故事可读性转向有意识的审美加工,从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改益创新,实现了文本价值的提升。作为评点家的金圣叹在这一进程中贡献了重要的力量。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梦”意象的阐释和运用,既是他个人审美观念的集中呈现,也反映了同时代士人的某种普遍心态,因此也影响了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转向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