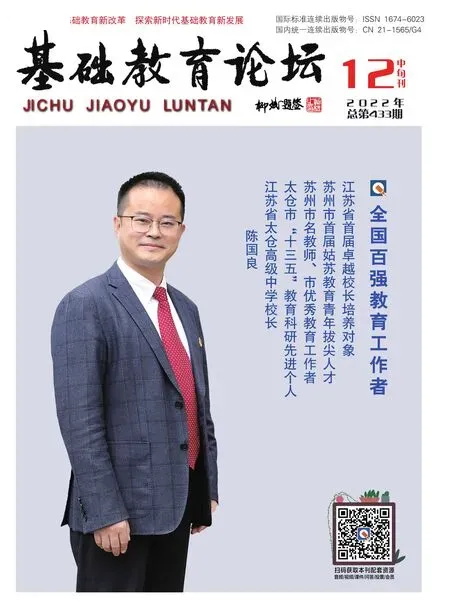立德为本重实效 育人为根促成长
——“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模式探索
张 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阶梯式发展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物质运动和人类的认识过程的发展是有阶梯性的,是从一个台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台阶。”[1]教育亦如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笔者所在校就明确提出“寓国家的教育要求于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之中”的教育哲学命题,并将学校的办学个性界定为:“学生个性发展教育,以此作为学校的文化品牌”,“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施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是在遵循教育规律及学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结构、身心发展水平划分成不同的教育阶段,在科学地提炼出每一个阶段学生的共性与个性特征的基础上,赋予一定的阶段性教育目标和内容,每一个阶段性教育目标和内容之间相互依托,螺旋式上升,使整体的教育过程呈现循序渐进、阶梯式发展的特征,促进学生逐步地从他律走向自律、跃迁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从而达到发展学生个性、塑造健康人格,培养良好素质的全人教育目的。
一、“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模式的探索是教育发展的需要
首先,新一轮课程改革为育人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课程”一词最早派生于拉丁语“Currere”,它的名词形式意为“跑道”,最早出现在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形象地说明了“课程”就是为学生成长设计的跑道。在课程改革深入实施的大环境下,课程结构的调整、个性化课程的选择,将成为必然趋势,它也终将倒逼育人模式的改变。
其次,让处于“高位引领”的核心素养进入“中位拓展”阶段,以保证其在“低位运行”阶段的实效性(《时事报告》微信公众号转载,2016.10.26)。《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对学校育人工作的高位引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并不可能兼顾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教育发展水平不同、学生身心发展水平不同等个体因素,如果学校要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核心素养体系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真正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必须制订出可以客观反映学校和学生发展实际情况的,具体的、细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育人目标和内容,并探索其处在低位运行阶段所需的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二、“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模式的探索是学生成长的需要
我们正处于一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个性发展的诉求日益彰显,人们更加关注个体的自身价值。在教育领域,日益凸显的学生个体差异、自主发展需求与现存的统一的、标准化的育人模式存在矛盾。
此外,我们的教育现状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培养模式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无法支持学生获得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评价方式单一,片面追求分数,“读书升学”被不断强化,造成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严重不足。这就为构建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模式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能性。
三、“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模式的相关探索
基于上述背景和原因,笔者所在校进行了“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模式的相关探索,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遵循教育和学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制定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模式在各阶段的育人目标及内容
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这一研究成果实际上回答了新时期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它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十八个基本要点(《时事报告》微信公众号转载,2016.10.26)。
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核心素养在“低位运行”阶段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具体化、可操作化。例如,在“社会参与——责任担当”中,初中学段育人的侧重点在于“国家认同”方面,即“……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高中学段则应该侧重于“社会责任”,即“……加快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利用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理念,构建校本德育课程体系,整合、更新育人的途径和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育的形式决定了最终的效果,很好的德育内容,因为没有好的教学载体,可能就会变成空泛的说教。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育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地位,对于德育形式的探索是德育工作成败的关键。
过往的德育实践中,不少中小学校习惯于在全班、全年级甚至全校开展大规模的教育活动,场面越大越好、气氛越热烈越好。这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在短时间内会有一定的效果,呈现出我们愿意看到,或者说愿意接受的效果,但是很难形成长效的影响。在这样的集体行动中,教师往往会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新的教育形势下,笔者所在校利用阶梯式自主发展的教育理念,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遵循教育规律、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前提,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引领,以“四礼”“四节”“四周”为总体活动框架,将育人活动的内容个性化,形式课程化,从课程内容体系、实施体系、评价体系三个方面,对学校原有的德育途径和方法进行梳理、整合、更新,从而更为有效地落实育人目标和内容。
(三)构建行政班主任和成长导师 “双线共建”的全员育人模式,并以此作为构建阶梯式自主发展教育的有力保障
传统的行政班管理,班主任具有绝对的权威,扮演着多重角色:学科教师、心理咨询师、警察、法官、保姆、妈妈(爸爸)、姐姐(哥哥)……每天在办公室和教室之间疲于奔命,不放心、不放手,大事小情一手抓,万一忙不过来,自动过滤筛选,抓两头、放中间。而学科教师往往又会觉得“育人是班主任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任务就是教好我的课”。随着行政班被打破,学校原有的以班级管理为前提的管理模式不复存续,校园中呈现出群体的多样性与个体的独特性并存的生态格局;“导师制”的尝试,让所有的教师都走到了台前,一位导师带领十几名学生,组成一个小的工作团队,除了传道授业解惑还要承担学生的人生规划和指导、心理疏导等工作。但是在转型期的初始阶段,从“班主任”到“导师”角色的转换,需要让教师自身、学生、家长都有一个接受改变的过程,所以,学校尝试探索“行政班主任”和“成长导师”的“双线共建”的育人模式,各有侧重、相互支持,相互作为、有益补充,尊重关爱学生,关注学生个体差异与身心健康,引导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从而落实学生主体地位,促进学生全面、自主发展,共同肩负起立德树人的教育职责。
教育的探索永远在路上,新时代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教育变革,而这场变革的根本则在于对学生个体的关注,在于学生是否能够发现自我,成为自我发展的主体。叶澜教授在主持国家级教育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时,就提出要“把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阶梯式自主性发展教育模式的探索正是赋予了学生 “成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创作者”的权利。在尊重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为每一位学生寻找他们的“最近发展区”,为每一位学生逐步完善自我提供最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