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失乐园
文|谷立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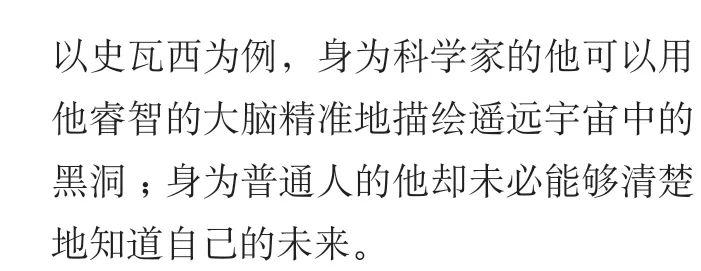
在这封信的结尾,史瓦西告诉爱因斯坦,“好像有种奇怪的东西”在他的身体里生长,它有种“遏制不住的力量,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变成了漆黑的”。甚至,在他的描述中,“这是一种没有形状也没有维度的虚空,一个看不见的暗影”,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毫无疑问,这个没有形状、没有维度、“看不见的暗影”就是战争。常常,它就像深不见底的黑洞,将所有一切统统卷了进去,又将它们变成漆黑。
身处如此困境,即便拥有一颗可以解读未知的聪明大脑,似乎也无济于事。具体到《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正是战争将书中几位科学家有机地串联在一起,更为他们赋予了相似的命运。在同名的短篇《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中,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从战场归来,面对被饥饿围困的维也纳,忧心忡忡地开始了他的研究。同样,《心之心》里有这样一位数学家,他热爱他的事业,却注定要为自己的热爱付出代价。
故事中,正处于学术巅峰期的数学家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彼时正值20 世纪60 年代。在愈演愈烈的反战浪潮推动下,他对自己热爱的数学开始有了一点怀疑——以往那些被他形容为河流、山川、海浪、光束的数理运算,如今早已褪去了所有浪漫的光晕,直接沦落为罪恶的代名词。格罗滕迪克相信,毁掉这个世界的不是大腹便便的政客,而是像他一样沉迷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手拿方程,排成一列,站在罪与罚的十字路口,“像梦游者一样走向末日”。
看到这里,千万不要责怪拉巴图特太过悲观。他不过是比我们更懂得科学的玄机。《普鲁士蓝》中,普鲁士蓝的由来成了他讲述的核心。这种诞生于1704年的美丽色彩,曾经是西方艺术家手中的宠儿。今天的我们似乎很难相信,如果离开了这种像天空一般纯粹的蓝色,十八九世纪的西方艺术界是不是会变得晦暗。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人见人爱的蓝色竟然是氰化物的源头。它的衍生物直接造就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杀戮。
不得不承认,格罗滕迪克说对了,科学就是普鲁士蓝。表面上美得一塌糊涂,值得我们耗尽一生去探究它的奥秘。但其实,如果不善加利用,任其盲目发展,人类就会沦为科学新知的牺牲品,为自己的任性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普鲁士蓝》的后半部分,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如约而至。与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哈伯就是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他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曾经从空气中提取氮气制成化肥,在一夜之间解决了数亿人的温饱。
另一方面,他又是劣迹斑斑的战犯,用氰化物制成功能强大的杀虫剂,亲手将他的犹太同胞送入死亡的深渊。然而,哈伯并没有因此感到羞愧,更不知道自己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因为相比复杂难测的现实世界,他更了解科学世界的运行规则。在他临终前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哈伯流露出深深的内疚。他自称,他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做法,改变了地球的自然平衡。
在哈伯的猜想中,世界的未来将不再属于人类,而是属于植物。正是有了他创造性的发现,植物才会违背自然规律,肆意疯长,“在地球表面蔓延开来,直到将它彻底填满”。科学何尝不是如此?说到底,科学从来不属于现实世界。尽管科学家很清楚,自己“在计算中每前进一步,就越发远离现实世界”,但他们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将演算进行到底。毕竟,身为科学乐园里的永久居民,科学家既不需要与世俗生活产生太多联系,也不需要为现实世界的崩塌负责,更不必勉强自己去理解外面那个复杂的世界。就像拉巴图特所说的一样,科学就是科学,“科学谈论的不再是客观世界”。■

本哈明·拉巴图特(Benjamín Labatut)
智利作家,1980 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在海牙、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利马度过童年,现定居智利圣地亚哥。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极洲从这里开始》获得2009 年墨西哥Caza de Letras 奖和智利圣地亚哥市奖。《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是他的第三部作品,也是他首部被翻译成英文的短篇小说集,英文版多次入围各种奖项,广受好评。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收录了五则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小说文本模糊了历史、回忆录、散文和小说的边界,创作出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