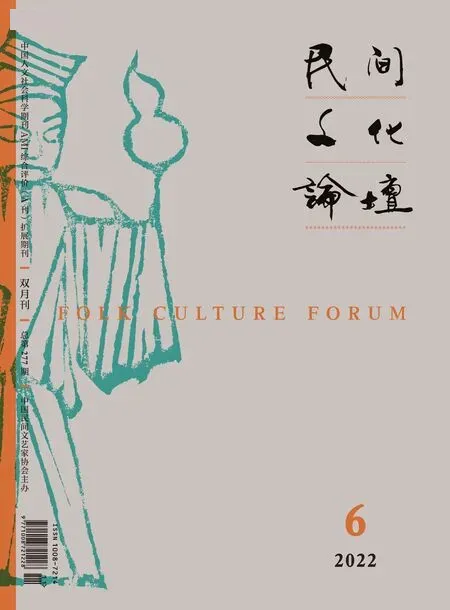江西赣中客家乡村送“镜”礼俗的变迁研究
张晓琼
《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在中国既指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准绳,同时也指践行该准绳的系列活动,即实践中人们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进行礼物交换。①晏兴成:《礼物的形式与礼物交换者动机的嬗变》,浙江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论文,2010年。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阐释了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居民利用 “库拉” 圈进行活动往来,学者阎云翔描述过中国东北下岬村由各类礼物流动形成的社会交往。本研究要讲述的是田野调查点客家村民在红喜事(婚礼、乔迁、祝寿仪式等)中运用 “贺镜” 随礼进行社会往来,而这种往来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礼俗。本文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尝试从“贺镜”礼物视角来探究一个正在进行的、易逝的送“镜”礼俗变迁的社会过程以及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圈变化。
江西客家地区姓氏众多,来源复杂多样。一是唐宋以来居住的“老客家”,二是明末清初时期从广东和福建回迁的“新客家”,主要分布于赣南、赣西北和赣中三大区域,赣中客家人主要分布于明清吉安府所辖的庐陵(今吉安)、龙泉(今遂川)、泰和、万安等县市。本次田野调查点吉安市遂川县五斗江乡三和村横坑组属于赣中区域,属于“新客家”村落中的村组。万芳珍和刘伦鑫根据江西1981年地名普查以来出版的各县市地方志书籍,总结出遂川县有1278个客家村,全县客家人约有36.7万。现横坑组有一百余户村民。据地方志和张氏族谱记载,该组村民在康熙年间应募入垦吉安府(今吉安市),从粤东迁徙到龙泉县(今遂川县),①《吉安地区志》卷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09页。在与土著人(本地人)博弈、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语言、生活方式、民俗文化。随着中国城市化推进,三和村从一个传统的农业乡村发展为一个现代性强的半农半工的乡村社会,送“镜”礼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送“镜”礼俗的发展变迁
(一)礼俗载体的嬗变
据访谈资料,送“镜”礼俗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贺镜”礼物为主,并发展为该礼俗的高潮期。“贺镜”是该礼俗实现的主导性符号与介质,从这个切入口来展现礼俗变迁的过程再合适不过了。

表一 不同时期的礼物形式
1.对联——过去盛行
对联有两个源头:一是具有巫术性质的中国古代桃符、门神风俗;二是汉语言特有的对偶句文学的演变发展。这两条线索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交汇融合一起,便产生了春联,现代意义上的对联是由春联演变而来。①林声:《中国匾文化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6期。三和村,在1949前盛行赠送对联以表祝贺。笔者采访了曾写过此类对联的老者。
被访者LZF(91岁):古代流行对联,对联讲究平仄、对仗、对偶。以前的“老书”(私塾教育)教这个,现在孩子读的是“新书”(现代教育),不兴这个了。
被访者ZSS(67岁):以前的对联按市场价1至3元价格不等。重要的亲戚送贵点的,一般的亲戚送便宜点。对联可以赶圩场时买,也可以托人写。大部分都托人写,一是圩场上卖的不能更好地表达客人的祝贺之意;二是对当地老先生的尊重;三是老先生写成本相对较低。
流行赠送对联是当时社会的文化产物和教育产物,也可反映出当时文化人地位比较高。这些能作诗写对的先生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年长者,则是读古文,习字,作诗文,且注重书法功底的培养。流行对联与当时的文化教育背景息息相关。如今,不兴对联礼物原因有三,一是读“老书”的人越来越少,能作诗写对的人也愈来愈少;二是纸张不易保存,易受潮;三是市场上能买到的物品种类越来越多,供老百姓的选择自然也多了。
2.匾——昙花一现
历史文献上有扁、额、牌、傍等单称,又有匾额、匾傍、牌额、牌匾等合称。《汉书大辞典》中如是说:匾额是上方题着作为标记或表示赞扬之字的长方形横牌。①林声:《中国匾文化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6期。这里说的匾和本文提到的木匾是同一类物体。木匾是雕刻师采用上好的木材雕刻而成,在木材上精心雕刻字或花样,后再喷漆。匾有软硬之分,硬匾就是木匾,一般刻四字,如龙凤呈祥;软匾不在匾额定义范畴内,软匾是红布做成的,成竖状,和锦旗相似,一般贺词写四个或八个,如:百年好合,永结同心。20世纪50年代,硬匾因价格偏贵没落,而软匾外表上不受村民喜爱,它们成为短暂性的随礼符号。村里几乎找不到这两种匾了,唯一一家还挂着软匾的老房子在2014年上半年被拆了。
3.“贺镜”——风靡一时
并不是所有的镜子都可以称为“贺镜”,被亲戚朋友之间当做“礼物”来赠送,被赋予祝贺之意的才能称之为“贺镜”。其必要元素:落款,表明赠者和主家的关系及赠者的祝福。“贺镜”的本体就是一面洁白的镜子,在前面冠以“贺”之名,必有其文化内涵。《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贺”作为动词,表示奉送礼物表示庆祝,《说文》中“贺,以礼相奉庆也。” “贺镜”可理解为含有祝贺之意的镜子,像卡片、电报、幛子一样,成为一种传播和象征的符号。
“贺镜”大体分为两类:一种暗镜(镜子里不可成像),如图1、图2、图3,有两个主体即镜子和装饰物,镜子覆在装饰物上;一种明镜(镜子里可以成像),如图4、图5、图6,只有一个主体即镜子,可以是空镜子,也可以有装饰物。“贺镜”只在婚礼、乔迁、祝寿这三种红喜事仪式性场合中馈赠。本文以横坑组现有房子为计量单位统计“贺镜”数量,据统计,横坑组“贺镜”现存数量总共为85面,婚礼“贺镜”65面,占比76%;乔迁“贺镜”20面,占比24%;祝寿“贺镜”为零。

图1 “画纸+木框”贺镜(摄影者:张晓琼)

图2 “玻璃+画+铝合框”贺镜(摄影者:张晓琼)

图3 “玻璃+效果字或钟+铝合框”贺镜(摄影者:张晓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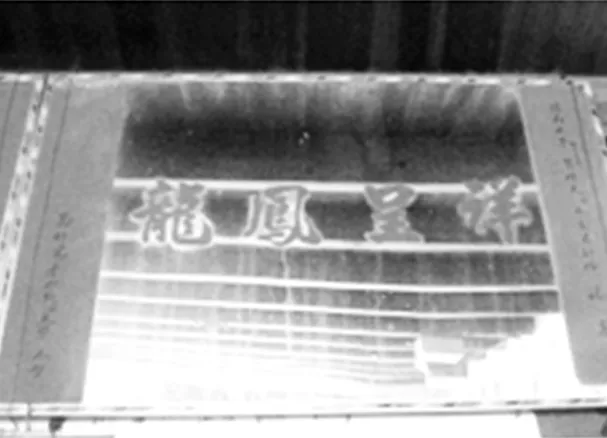
图4 “镜子+贴字+铝合框”贺镜(摄影者:张晓琼)

图5 “镜子+图像+铝合框”贺镜(摄影者:张晓琼)

图6 “镜子+铝合框”贺镜(摄影者:张晓琼)
在横坑组,婚礼“贺镜”数量占比最多。婚礼是农村生活中最重要的礼物馈赠场合,也是最频繁的仪式性场合。不同身份的亲戚朋友在婚礼中会赠送不同的礼物,最基本的常识是,“一席”和“二席”的客人贺礼必定不能少一面镜,也就是结婚方的舅舅和舅公这两个身份的亲戚必须每方赠送一面镜或“搭伙”合送一面镜,这被看作横坑组乃至三和村婚礼仪式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礼物或仪式。可见,“贺镜”在婚礼上既普通又特殊。
横坑组乔迁“贺镜”数量是婚礼“贺镜”数量的三分之一。盖了新房就要“进火”,但是否举行仪式还得看主家的考虑,村里有五家未办乔迁仪式。访谈后发现,他们有些是房屋还未完全竣工,先搬来住,房屋还没建好也不好意思举办宴席;有些认为办酒的成本太大,收到的礼包还不及办酒的开销,加之盖房可能还欠着债。所以,横坑组的乔迁之镜会比较少。
令人惊讶的是,寿镜为零,即使扩展到整个村子,也找不到几面。老人一般在61岁、71岁、81岁、91岁才会办寿宴,也只有部分儿女肯花钱为父母操办,说到底,还是个经济成本的问题。有些老人自己不想搞得这么奢华,只想家里儿女齐聚一堂简单吃个饭,人们对于仪式的需求渐渐淡化,这使得寿宴仪式与寿镜也跟着消失了。
(二)礼俗的发展周期
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如同人的生命,必须历经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四个周期。送“镜”礼俗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在其存在的100年左右时间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
第一,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是其形成期。被访者提到说1958年“镜”就出现了,“国家把村庄的经济社会结构方式和社区发展规划安排得非常具体, 村庄也完全按照国家的安排展开生产生活。农民们怎样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活、生活的主要内容决定于国家的制度供给与安排。”①郭俊霞:《当代中国乡村互动关系的演变》,《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村民们在当时政治环境中因时制宜,对于传统的坚持与传承使得习俗被保留下来,“它是一种传统,祖辈们传下来的,不能丢”。只是当时 “贺镜”送得少也制作简易,如图1。
第二,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其成长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村民们回忆,当时一是能购买的东西非常有限,二是村民挣的工分主要解决生计问题,他们根本无剩余财力去购置这些额外的东西,且当时反对大吃大喝,办酒席也是有标准,如十桌为限,送镜礼俗在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发展起来。67岁的老奶奶JZY一直叨咕说:“以前天天做功夫(干农活)都吃不怎么饱,现在不做功夫吃都吃不赢(完),你说这奇不奇怪!”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送“镜”礼俗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其成熟期,也即高潮期。究其原因,一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以后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彻底解放了农民,1987年开始试行村民自治,农民除了缴纳相关税收外,其余都归自家所有。二是宗族在改革开放后重生、变异和复兴,②周建新:《人类学视野中的宗族社会研究》,《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宗族祠堂再次登上舞台,各种客家习俗在乡村社会也恢复了常态,对于礼节仪式的追求愈演愈烈。三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市场的实行使得商品种类繁多,市场交易变得频繁。四是新的耕种技术(包括化肥的使用等)广泛运用于农业耕种,吃饭问题的解决让村民们有剩余时间去考虑其他的事。五是镜子的生产技术提高,产量提高了,有足够的市场供应量。送“镜”礼俗在这一时期爆发式地发展,风靡一时。
第四,90年代末期至今衰退比较明显。在90年代初,货币就具备了成为仪式性礼物流动场合中礼物的条件,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货币关系的不断泛化,使得经济交换成了人们社交的主要内容。另外农村人口向外流动也是导致该礼俗衰退的重要原因。农村人口规模性移动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以后加剧,农民工主要从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安徽等为打工大省。③周大鸣:《中国农民工研究三十年——从个人的探索谈起》,《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据村民们回忆,90年代村中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已婚者家庭有参加亲戚朋友喜事随礼的义务,他们干脆包个现金礼包,既省事又实惠。
从对联到“贺镜”的符号转变,跨越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时期。“贺镜”的发展历程中展现了政治特殊时期农村的景象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和政策的开放,诸多新事物不断进入农民生活,村民们逐渐融入到现代化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该礼俗的发展也呈现衰弱趋势。
二、送“镜”礼俗关系圈变迁
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情关系的传统熟人社会,村民之间存在着血缘、地缘、情缘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①于伟峰、崔纯、张建:《礼物在农村红白喜事中的变迁》,《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在面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村民们如何调整送“镜”行为及选择与维护随礼圈(关系圈)呢?本部分试图真实地还原村民送“镜”礼俗交往的面貌,在阐述过程中揭露村民礼尚往来的文化动机。关系圈的形成与维护是该礼俗进行的前提与根源,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动力,此处探讨的关系圈主要围绕“贺镜”而发生的。

表二 “贺镜”礼俗不同时期的赠者
随礼者所有礼物均是以男性家长所代表的家庭名义来赠送。表2显示,“贺镜”礼物形成的关系圈由宽泛到变得窄小甚至是固定,客家村子为代表的宗亲关系圈被淡化出局,其他类型的关系也悄然退场,姻亲关系圈突围而出,成为送“贺镜”的固定赠者。其中,姻亲关系圈是指通过女人的流动建立起来的两个父系家族之间的关系群体,本文所涉猎的姻亲指外婆家(舅舅家:一席)、老外婆家(舅公家:二席)。人类学家将组成婚姻家庭的两方归纳为讨妻集团和给妻集团,②王开庆、王毅杰:《大礼帐:姻亲的交往图景——以陈村为个案》,《青年研究》,2010年第5期。本文的讨妻集团是接受“贺镜”的丈夫家族,给妻集团指赠送“贺镜”的娘家家族。而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组织。③周建新:《人类学视野中的宗族社会研究》,《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宗亲,指同宗的亲属,村民们用“祠堂子叔”来称呼宗亲。
1.宗亲关系圈被淡化
宗亲赠送“贺镜”是一种集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是至亲族人一起凑钱买一面相对较好的镜子送给主家。这种集体行为没有针对性和特殊性,只要哪家做红好事,这种集体仪式行为都会发生,族里的和主家血缘关系比较近的男性家长会参与到当中来,宗亲送“贺镜”在某种意义或某种范围上是集体对个体的社会交换,如图7所示,形成一种循环关系结构网。其他远亲可以选择礼物的形式,没有固定要求是“贺镜”,但都比较倾向于当时流行的礼物镜子。

图7 循环关系结构网
宗亲间礼物循环往复,形成一种“给予”“亏欠”“还人情”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让宗亲因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构成了一个“自己人”的社会,成为一个“亲密社群”。就像费孝通说的:“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9页。而横坑组的客家宗族观念更是加强了这种群体的凝聚性和互动性。中国原有的深厚宗族传统,宏大而持续的移民运动及客家地区贫瘠的自然生存环境,促成江西客家地区强烈宗族观念和形成了相对严谨的宗族社会结构,他们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修建了祠堂、祖坟,修编了族谱等物态文化,形成赡族、祭祖等行为习俗。传统乡村社会具有“互助”和“亲密”特点,村民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联系紧密,关系亲密,相互信任,“贺镜”礼物的流动正是他们社会交往的一部分。
1949-1979年,国家权力向农村的延伸,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活动、村政的运作,都是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安排来进行。②郭俊霞:《当代中国乡村互动关系的演变》,《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虽然乡村以往宗族组织管理模式在形式上已经消失,而实际上却仍然存在于乡村生活的许多层面。赣南和粤东的宗族一直没有消亡,③曾国华:《宗族组织与乡村权力结构——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个案的研究》,《思想战线》,2004年第1期。利益关系和权力结构还在, 红白之事照样在祠堂举行。基于地缘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依然是以宗族为群体基础的组织,“贺镜”礼物流动得以在祠堂亲族间继续进行。
80年代开始,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乡村宗族复兴重建,在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民俗活动等方面表现活跃。④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0页。这些活动重新唤起了族人间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客家农村出现一番新景象,村民的交往圈子也往外发展,人脉延伸得越来越宽,礼物交往活动也愈发频繁。宗亲是村民送“镜”礼俗关系圈的群体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
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客家乡村社会结构正在逐步解构,“家族的泛化”正在逐步瓦解以宗亲为核心的群体,姻亲关系与拟血缘关系群体正打破原有乡土社会差序格局。⑤刁统菊:《亲属制度研究的另一路径——姻亲关系研究述评》,《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在经济发展的助推下, “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原本紧紧地以血缘关系(家族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化、理性化。⑥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和农村家庭的空壳化,导致宗族维系的原有基础被掏空。当送“镜”礼俗走向衰落时,宗亲赠送从过渡期偶尔赠送到低潮期未赠送,“贺镜”的随礼主体固定为姻亲,宗亲的地位被弱化。
2.姻亲关系圈被重视
表2中有一个明显趋势:在结婚和乔迁喜事中,送“镜”礼俗的随礼者由姻亲、宗亲等组成的群体转变成以姻亲给妻集团为主。给妻集团中又分为内戚和外戚,内戚是指主家妻子系的亲戚,如岳父、内弟,也即一席;外戚是指主家母亲系的亲戚,如外公、舅舅,也即二席。也提到三席,是指主家家长奶奶系的亲戚,如果奶奶还健在或平常与她的娘家联系比较多,这类亲戚需要维持。以下使用“姻亲”一词指代内戚和外戚,也即给妻集团。
目前“贺镜”赠送的流动方向见下图:

图8 “贺镜”赠送格局
综合来看,这是一种以男性家长为核心的树形结构关系图,但却是由女性为连接点而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婚姻为桥梁而外扩的人际圈。它的形成情况如图9所示:

图9 树形关系结构网
树形关系结构网是无限扩展的,赠者与被赠者不是对称型的礼物流动,是纯粹的单向流动,就像树枝一样不断往外生枝,这使得姻亲关系圈不受限制。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特征时,在对家庭、家族及其结构和观念进行深入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序格局”的理论。他认为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由父方亲属和母方亲属共同结成了“差序格局”的网络,以自我为中心,通过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0页。这离中心最近的人也自然是最亲的人,讨妻集团很看重内戚和外戚是这两方亲戚。所以,至今送“镜”礼俗以这两方亲戚为主。
人类学家葛伯纳夫妇指出,姻亲之间的交流有一个基本的行为模式和关系结构,其中体现出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①转引自刁统菊:《亲属制度研究的另一路径——姻亲关系研究述评》,《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赠送“贺镜”既是时代给予姻亲的一种权利,也是姻亲之间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一席和二席的称谓来源于坐席的安排,他们被安排坐在酒席中最显眼的位置。农村办喜事把一席和二席看作是最重要的客人,是酒席中必不可少的一道“门面”,这是姻亲独享的权利。但义务是无论姻亲有何原因或困难都必须出席酒宴,没有履行义务是姻亲很丢面子的一件事,这种行为受道德上的约束。主家和姻亲双方的门面都要撑起来的必要之物就是“贺镜”,用村里的话说是没有“贺镜”不成席,这酒席办得也不光彩,客人也会说闲话。笔者认为这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制衡是“贺镜”礼俗还保存至今不可缺少的缘由。
亲戚双方都非常注重这些礼节的来往,LQG告诉了笔者一个关于他们家的故事:
我姐姐结婚的时候,我舅公家穷得揭不开锅。我爷爷去他们家请酒时说,“礼我会包好,镜我会买好,你只要来出席吃酒就可以。”他解释说,如果他没镜没礼过来,他也会觉得没面子,别的姓氏也给他带来巨大压力。反过来,我家没请他来吃酒,别人会认为是我家不懂事,会议论两家是否有矛盾。在农村,最好不要让别人说闲话,弄得名声不好。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研究中,宗族制度和组织是研究的主线。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把对中国宗族制度的研究发展成了宗族范式,并提出从宗族组织解读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后来学者不断追随他的研究,多数是基于地方性个案对该模式进行验证或提出修正。但单从宗族组织这一视角去创建一个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具有普适性的解释话语,则是非常困难的。除了宗族组织,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结构有重要影响,如超宗族的地缘性组织或亲属群体。姻亲关系就是其中之一,它没有进行体系化规定,只是在行为层面上得到了习俗化认可。郭于华提出“亲缘关系”概念,将姻亲关系包括在内,用以表述当前社会条件下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宗族关系的人际关系网络。②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费费孝通指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亦发生了变化,姻缘关系渗入到差序格局中。”③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对关系主体的选择和重组变得更自由,在日常的社交互动中,人们的关系延伸到姻亲、朋友等范畴,其中姻亲关系在这个关系圈的重要性和作用性不断加强。
3.个案分析:婚礼送“镜”礼俗中的姻亲关系
横坑组数量最多的贺礼非婚礼“贺镜”莫属,最具有代表性。以一户人家2012年婚礼好事中被“馈赠”的“贺镜”为例。需要解释的是,这种馈赠是象征意义上,而不是真正程序上的。因为镜子是主家自行购买,买什么品质和类型的都是主家决定。购买回来后好事当天贴上了落款。据他说,这面镜子一共花了200元,再加上装框费20元,算是中等的镜子。它长2m,宽1.5m,偏正方形。(见图5)
这面婚礼“贺镜”有以下几个构成元素:
镜子本体是主要的承载媒介,它由图像、对联(铭文)和灯笼组成。图像是由青绿的迎客松、红色重峦起伏的群山和正旭日东升的红日组合而成。图像抽象地映射了主人家的迎客之道。对联映衬了图像的象征意义,上联:门迎东南西北客,下联:户纳春夏秋冬财,横批:迎客松,也具象地阐明了主家的待客之理。而镜子左上角和右上角的灯笼“福”字烘托了吉祥喜庆的气氛,为婚礼增添喜气。镜子本体的选择是非常有目的性的,主家说,“就是因为他儿子结婚才挑了这样的,看着喜庆。”
而成为“贺镜”的关键在于主家贴上落款,位于对联边上,成对称型。
右(方向) 张府光薇贤妹夫次子厚贤为小儿声玉新婚庆烛 誌囍
张府光薇尊姻侍次子厚贤为小儿声玉新婚花烛
左(方向) 愚 外兄江城(亮乐来财华林良) 仝侄鑫文峰 仝贺
姻春弟肖世(海何明伏生平生) 仝侄东华永久
通过图10更能理解“落款”的内涵:

图10 “贺镜”上的姻亲关系
图10主要描述了主家与他的外戚和内戚的关系(以男性家长为节点)。图中称谓以父亲为尊称,说明主家的父母还健在。赠者分别为父亲的内戚和亲家(主家的妻系亲戚),称父亲为贤妹夫和尊姻侍,他们以赠者口吻先叙述仪式事件,“张府光薇贤妹夫次子厚贤为小儿声玉新婚庆烛 誌囍”,“张府光薇尊姻侍次子厚贤为小儿声玉新婚花烛 誌囍”。因为此仪式的发生,两方亲戚要来道喜,“愚 外兄江城(亮乐来财华林良) 仝侄鑫文峰 仝贺”,父亲内戚称是父亲的外兄,携父系兄弟一起来道喜;“愚姻春弟 肖世(海何明伏生平生) 仝侄东华永久仝贺”,亲家公已不在,以亲家的儿子为代表,称是主家的姻春弟,携他们的父系兄弟一起贺喜。整个“落款”的语境是以他父亲的立场来体现主家母亲系和妻子系的亲戚“贺镜”的馈赠。
以此来看,姻亲关系是从男性的视角铺展开来的,女性在仪式性场合的重要地位以女性在娘家的男性家人突显而出。在三和村的已有宗族观念中,男性是一个家的主心骨,是对外“说话”的核心人,是村里公共事务的执行者,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弱于男性。如横坑组的新建祠堂所用的费用是平摊到组里的每一个男丁2000元/个,家里有几个男丁就捐几份钱,女性被排除在外。在很多公共的正式的场合中,女性承担更多的是辅助角色,如建祠堂来帮工,做好事帮忙做些轻松的活。但是在仪式中,女性角色的重要性从侧面反映出来,即给妻集团被重视。在姻亲关系的范畴内,实质上,给妻集团比讨妻集团享有较高的地位。这种地位不平等,根本原因是姻亲关系的构建以女性从夫居为基础,女性的流动形成了一种失衡的“债务关系”。马丁指出,嫁出去的女儿是给别人生育、抚养后代延续血脉的,由此讨妻集团欠下无法偿还的债务,此种关系在亲家间的交往中体现得很明显。①王开庆、王毅杰:《大礼帐:姻亲的交往图景——以陈村为个案》,《青年研究》,2010年第5期。特别是亲家间说聘礼时,给妻集团经常以“不能白给了你一个女儿”为话头,在聘礼上会提出众多要求。在送“镜”礼俗中,讨妻集团“请”给妻集团吃酒,并让他们坐在最高的席位上,以表尊敬。
人们在言谈之间已经表现出对姻亲的重视,更有一些谚语表达了姻亲关系的重要性。在一些出版的民俗志里,有很多对舅舅角色的描写,譬如“天上雷公,地下舅公”。实际中,很多人喜欢把舅舅看作是公证人,家里发生了矛盾,请舅舅过来主持公道;家里要分家,请舅舅来做见证人;家里被谁欺负了,回娘家请兄弟来讨回公道。姻亲对于个体家庭而言,其分量丝毫不比宗亲轻,其亲密程度甚至超过宗亲。
结 论
礼俗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交往的纽带维持着村落自身社会秩序,客家村民在不同时代积极践行送“镜”礼俗。“贺镜”这个符号,超脱其作为礼物载体自身的“物”性,具有与人相关的社会属性。它不仅折射出送“镜”礼俗的兴与衰,实质上展现出一个客家乡村从传统的农业形态到现代半农半工社会形态的变迁和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贺镜礼俗反映了一个客家宗族社会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被解构,村民在随礼中为何打破原有乡土社会差序格局,逐渐淡化宗亲圈,更重视姻亲圈的往来,这也生动形象地还原了村民礼俗往来的文化逻辑,如对礼尚往来中权利与义务的实践、对人情与面子的顾及。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频繁,文化和市场环境对随礼行为和随礼观念影响加剧,十字绣、钟表、电子显示屏(可播放图片和视频)正悄悄地取代贺镜,但村民们坚信礼物形式的改变并不会导致该礼俗的消亡,相对稳定的社交理念和文化观念保障了送“镜”礼俗的延续。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
——松滋礼俗——毛把烟、砂罐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