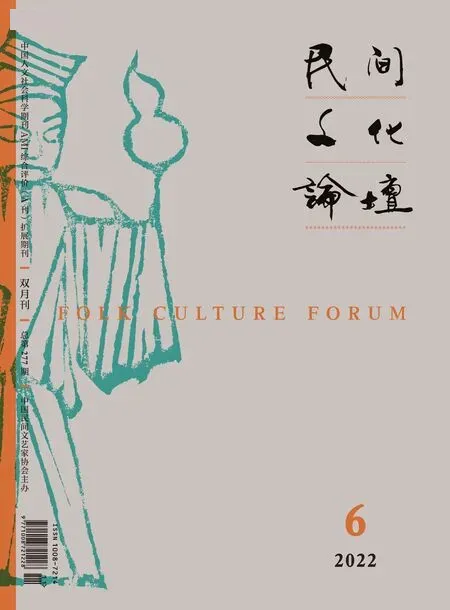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机制鸟瞰
—— 以2003年《公约》名录体系的发展现状为中心
巴莫曲布嫫
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或2003年《公约》)框架内,国际层面开展的申遗实践一直是公共场域乃至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以致各种讨论和争议此起彼伏。这一内卷现象大抵也反映了人们对《公约》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准则、概念、措施和机制尚缺乏必要的了解。有鉴于此,本文仅结合在2003年《公约》框架内奠定的四重国际合作机制,重点说明在该机制下设立《公约》三重名录体系的法理依据和运作方式;同时从成绩到问题再到挑战,考量“申遗”作为缔约国实施《公约》的关键路径与《公约》名录列入机制全球反思进程之间的复杂关联。由此,或可为进一步厘清申遗实践的基本方向提供一定的前鉴和助益。
一、从《公约》到《操作指南》:四重国际合作机制的形塑
首先有必要回顾《公约》第一条所确立的四项宗旨:“(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四)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概而言之,保护、尊重、提高认识并相互欣赏、合作这四组关键词正是《公约》核心价值观①朝戈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绎读与评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5期。的集中表述,亦为国际社会实施《公约》建立了共同行动的基线目标。《公约》第二章“在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章“国际合作与援助”彼此贯通,为各缔约国全面履行其法定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第十九条从内外两个向度对“合作”进行了界定:一则“……国际合作主要是交流信息和经验,采取共同的行动,以及建立援助缔约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机制”;二则“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及其习惯法和习俗的情况下,缔约国承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保证为此目的在双边、分地区、地区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
自《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于2008年出台以来,已先后经过7次修正,从多方面体现了国际社会为保护人类共同遗产不断调整行动方向的努力,也反映了各缔约国在实施《公约》的主要行动领域中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操作指南》开宗明义,第一章便以“国际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合作与国际援助”为题,与《公约》相关条款环环相扣,在“四重国际合作机制”(fou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以下简称“四重机制”)的整体框架内,为这部国际法在各缔约国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制度化的决策方向和治理路径。如图1所示,该机制包括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简称“急需保护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②详见巴莫曲布嫫《遗产化进程中的活形态史诗传统:表述的张力》,《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申报(nomination)和列入(inscription),“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简称“优秀保护实践名册”)的推荐(proposal)和遴选(selection),以及国际援助的申请(application)和批准(approval)。在操作层面上则按计划性方法(programmatic approach)一同构成为国际社会共同保护非遗的四项并行措施——具体目标各不相同,但互为关联。

图1 四重国际合作机制中的《公约》名录体系示意图
进一步讲,《操作指南》作为《公约》的实施细则,为各缔约国有序开展两个名录的申报、一个名册的推荐和国际援助的申请提供了共同的行动准则和不同的实践路径,并对列入/遴选/评选的强制性标准、申报/推荐/申请的受理程序和时间表作出了严格规定(第1—56段),总体上包括技术检查(秘书处)→标准审查(审查机构)→总体评审(委员会)三个基本程序,以确保四重机制互为补充,由此为保护各缔约国领土上存续的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提供了进入国际承认和国际理解的平台,也为基于社区而得以确认和界定的各种非遗项目经由缔约国申报进入人类共同遗产(common heritage of humanity)开启了多重通道,而优秀保护实践和在国际援助资助下开展保护项目则有益于范例推广、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因此,对缔约国来说,在国际合作原则下开展非遗保护理当包括国家层面的申遗工作,而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申遗实践作为缔约国的国家行为也部分构成其履约的法定义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四重机制在过去十多年的并行发展过程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应,这与《公约》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乃至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中加以实施的复杂进程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特别是当今全球正遭遇百年激变,各种危机并存,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制约下,国际合作机制乃至其实践方式和工作模式自然会面临种种制约和挑战。
二、三重名录体系:发展现状与问题扫描
国内已通用的“申遗”一词实难完整含括四重机制,其语用范围的限定与许多国家从未使用过国际援助机制相关;而该机制与保护已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遗产项目或在紧急情况下申请筹备性援助有紧密联系。因而,人们经常讨论的“申遗”话题主要围绕《公约》规定的两个名录和一个名册;且因重视程度不同,不少国家至今仅使用过代表作名录机制。在《公约》法定文件中经常使用“2003年《公约》名录”(the Lists of the 2003 Convention)或“2003年《公约》的三重名录列入体系”(threefold listing system of the 2003 Convention,以下简称“名录体系”),而在实际运作中逐步成型的工作模式则概称为“名录列入机制”(listing mechanisms)。究其名实,以“2003年《公约》”作为所有格对名录体系进行严格限定,也昭示了其间潜含的国际合作深意:一方面,名录体系本身是为实现《公约》宗旨而专门设立的国际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名录列入机制的持续性运作还需与“定期报告机制”(periodic reporting mechanism)对接,从而约定了各缔约国及其相关社区和群体、《公约》执行机关、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各有关行动方的责任和义务。
2008年11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第三届常会通过决定,将《公约》生效前由教科文组织先后分三批宣布的90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并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后便开始筹备三重名录第一个周期的申报和受理工作。因而,现行名录列入机制正式启动于2009年。从直观上看,图2反映了《公约》名录列入机制从无到有的13年进程,但实难承载其背后丰富而又复杂的讯息,尤其是在多轮浪尖与波谷之间跌宕前行的发展态势遮蔽了数字变动下的荆棘之路。这里仅从整体上对名录列入机制取得的主要成就作一概览性扫描。

图2 《公约》名录所列遗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统计图(2008—2021年)
从地方层面上看,通过缔约国提交的遗产项目申报日益多样化,不仅从整体上极大地提升了非遗的可见度(visibility),而且从地方到全球的遗产化进程中所彰显的相关社区的当代实践已成为确认、界定和保护非遗项目的基本尺度和共同行动。从国家层面看,活态遗产保护对各缔约国在文化政策、立法和体制上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和计划有直接推动作用,同时对缔约国内部的非遗清单编制和定期更新,包括社区参与其进程的每一阶段,也形成了相应的责任约定。从国际层面看,三重名录的不断更新和拉长对《公约》已接近全面批约作出了直接贡献,而每一批名录的产生都会通过具体的非遗实践不断加深人们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理解,由此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得以大幅度拓宽。特别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申报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彰显了非遗保护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联系,同时促进了非物质遗产保护(safeguarding)与物质遗产保护(conservation)之间的协合增效作用。在经审查机构推荐和委员会确认的申报范例中,一些案卷涉及保护少数群体、边缘化或原住民的活态遗产,并展示了活态遗产与教育、环境和性别等若干行动领域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此外,近三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相关申报实践也表明传统知识和民众智慧可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解决办法。以下结合图2并以委员会历届常会有关其年度申报评审工作的决定为循证范围①本文的总结参考了委员会历届常会(2006—2021年)有关四重机制形成的一系列决定,涉及《公约》名录的列入标准、发展进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以及改进措施乃至具体建议,可通过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专题网页(https://ich.unesco.org/en/decisions)查询或获取。若非必要,行文中不另作说明。,集中对长期存在的现象级问题作一简要归总。
其一,三重名录之间的取舍趋势。从列入情况看,急需保护名录71项,来自38个国家,占比11.27%;代表作名录530项,来自140个国家,占比84.13%;优秀保护实践名册29项,来自22个国家,占比4.6%。显而易见,绝大多数缔约国优先考虑代表作名录申报,必然以舍弃其他两个机制为代价。列入急需保护名录多年的遗产项目至今仍旧“原地踏步”地留在该名录中,而其实施已久的保护计划及其有效性便会令人质疑。为遴选和推广优秀保护实践而专设一个机制的愿景,也几乎消弭在占比最低的事实面前,大抵因其论证难度最高,还须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且因要求以成效评估机制作为依托,对潜在推荐国的能力建设也形成了挑战。
其二,区域分布失衡。从选举组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第四选举组)203项,占比31.1%,总量最高,这与中日韩三国在未设受理上限的2009年周期分别有25项、9项和5项列入名录直接相关。西欧与北美区域(第一选举组)122项,占比18.7%;东欧区域(第二选举组)121项,占比18.6%。接下来的占比渐次下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第三选举组)86项,占比13.2%;非洲区域(第五a选举组)63项,占比9.7%;阿拉伯区域(第五b选举组)56项,占比8.6%。“非洲优先”是教科文组织部门间联合行动的主题领域,也是《公约》全球能力建设战略的重心,但非洲国家的增长幅度最慢。阿拉伯国家略有胜出则得益于委员会优先支持的联合申报,共有14项。此外,截至2020年7月,已有180个国家加入《公约》,但《公约》名录中至今还有40个缔约国处于“缺席”状态。
其三,五大领域与遗产项目之间存在弱相关。若按一个或多个非遗领域计,其中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21项,表演艺术336项,传统手工艺324项,口头传统与表现形式314项,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228项;基本覆盖五大非遗领域的遗产项目计290项,对应90个国家。这些数字至少说明许多申报材料所勾选的非遗领域过于偏狭,难以反映活态遗产内在互联的多样性,也未能反映遗产项目与遗产领域之间存在的互涉关系;有的领域选择则缺乏信息的准确性、一致性和连贯性,不利于公众社会对遗产项目的性质和社区范围形成全面理解,也不利于在整体上提升非遗的可见度。①详见郭翠潇《构建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数据库的统计分析为中心》,《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其四,多国联合申报的信息提供不对等。目前,国别申报共569项,来自125个国家;联合申报61项,涉及100个国家。2020年联合申报冲顶,多达14项;2021年,“训鹰术——一宗活态的人类遗产”经第三次扩展,24个国家先后加入,跨全球三个大陆。在提交国数量激增的同时,联合申报却面临如何界定“跨境共享遗产”的挑战,毕竟类似的或相似的遗产(similar heritage)不能等同于共享的遗产(shared heritage),只有后者才能为“相关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公约》第二条)。有的联合申报案卷按国家逐一罗列碎片化信息,而如何开展联合保护行动,同时确保各自社区事先知情同意并全程参与合作,则成为证据链环上的缺憾。毋庸置疑,联合申报已成为次区域、区域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行动,在申报规则中享有优先权重。但藉此规避每个周期的受理上限,似乎已成为助推联合申报不断上涨的潜在动因。
从总体上看,在《公约》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处于国际合作最前端并发挥关键作用的四重机制已成为全球能力建设战略中的支柱。委员会在其提交给缔约国大会(以下简称“大会”)的双年度(2012—2014年)工作报告中,曾郑重呼吁各缔约国、大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关注四重机制的使用权重:(1)促进急需保护名录,将其重新定位为缔约国对保护非遗和实施《公约》的承诺之体现;(2)促进国际援助,将其作为保护非遗和实施《公约》的工具;(3)尊重并促进代表作名录的宗旨和最佳使用方式;(4)通过开发专用网站、电子通讯、在线论坛等其他更为便捷的方式分享保护经验,对优秀保护实践名册进行补充。(ITH/14/5.GA/4.1, para.24)①文中所涉部分《公约》法定会议文件,可按随文括注的文件代码在教科文组织数字图书馆(http://unesdoc.unesco.org/)查询或获取。但此后6个审查周期的实践表明,尽管委员会一再重申其以上关切,这种失衡格局非但没有改变,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三、名录列入机制及其全球反思进程:触底与转机
《公约》名录列入机制的运作和发展事关各利益攸关方,也最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2012年以来,鉴于缔约国在申报实践一再遇到相关列入标准带来的问题和障碍,委员会就反思《公约》名录列入标准多次提出建议,也采取过相应举措,但收效甚微。而在《公约》名录体系的建设进程中长期存在的横向问题与相继发生的“例外”(on an exceptional basis)事件,在不同向度上形成重重压力,逐渐在下述几个重要关节上“触底”,最终推动了名录列入机制的全面反思。
其一,从申报到审查。2009年以来,在申报/推荐/申请案卷中反复出现的横向问题一直在挑战咨询机构(现为审查机构)的工作方法、评判尺度和职权范围。尽管问题林林总总,但在整体上折射出诸多类似的观念错误或认识模糊,以致屡屡步入行动误区。(1)背离《公约》宗旨和原则,错误理解各名录的具体目标。例如,将列入代表作名录等同于建立其专属的所有权、物主权、地理标志乃至品牌认证等;在遗产叙事阐释中频繁使用“真实性/本真性/真确性/原真性”“唯一性”“原创性”“纯粹”“正宗”等排他性不当用词,往往在社区之间乃至国家之间埋下相互竞争乃至造成紧张关系的隐患。(2)去语境化现象有增无减。在确认和界定遗产项目时未能在“实践”与“产品”之间作出区分,将保护重心落到具体的“实物”之上,而非社区的实践过程和代际传承,同时忽略了遗产项目之于社区和群体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而博物馆化、剧场化、舞台化、民俗主义的作品化等倾向,不仅脱离了遗产项目所植根的文化语境,也背离了实践之于社区的本旨和意义;(3)社区参与不充分。在编制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包括在已提出乃至已实施的保护措施或保护计划中,乃至在国家内部的清单编制和更新过程中,缺乏自下而上的包容性参与机制或带入机制,对性别因素和性别作用重视不够。(4)缺乏有效的风险监测和评估机制。对过度商业化、商品化和不可持续旅游业可能给社区实践带来的负面作用失察,对列入代表作名录本身可能会对遗产项目存续力造成不可预期的潜在影响也有不同程度的低估。(5)混淆教科文组织不同文化公约之间的保护对象和保护方法。其典型表征是错误使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框架内的概念或术语,如世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濒危等,乃至出现世界级/世界人类非物质遗产等拼凑用词。上述问题的长期存在往往会构成审查机构、委员会和申报国之间的潜在颉颃,即便最后以“翻案”方式在委员会评审阶段最终得以列入名录②详见本刊同期刊出的朱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研究——以审查机构及其运作机制为中心》一文。,也会在更大范围内造成认识上和行动中的混乱。
其次,从审查到评审。2017年,委员会常会在决定将“越南富寿省唱春”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的辩论中,其程序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③详见朱刚《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动向:以越南富寿省唱春项目的名录转入为个案》,《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审查机构内部对首次受理程序“例外”的案卷也有不同看法,但从大局出发采取了变通措施。此举促成委员会提出动议以全面反思名录列入机制的性质和目的,同时围绕《公约》实施以来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寻找解决方案。2018年,通过教科文组织的积极斡旋,朝鲜和韩国各自独立申报的传统摔跤“希日木(Ssirum/Ssireum)”突转为“合并审查”,最后“联合列入名录”(joint inscription),再次成为程序上的“例外”,但事件本身彰显了共享遗产具有建设和平的内生性动力。
再者,列入名录后。早在2012年的常会期间,委员会就建立有关申报工作的信访机制通过了相关决定(Decision 7.COM 15),但此后一直苦于缺乏具体的响应性机制以采取主动跟进行动和适当程序。“屋漏偏逢连夜雨”,2017年以来,相关社区或第三方对若干已列入名录遗产项目的现状和影响其存续力的事态发展表示了关切,秘书处收到的相关投诉大幅增加,其中多起涉及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歧视,有悖于社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2018年常会期间,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反思对已列入名录遗产项目的跟进行动和适用方式,同时承认反思跟进行动本身与持续思考《公约》名录的性质和目的之间存在相关性,遂而决定正式启动“《公约》名录列入机制全球反思进程”。2019年3月,教科文组织发表公报谴责比利时“阿尔斯特狂欢节”一再出现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花车;同年12月,委员会常会通过决定,将该遗产项目从代表作名录中除名,成为捍卫《公约》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反面例证,但同样缺失具体程序。会议期间,针对迫在眉睫的一连串复杂问题,委员会因势利导,确定了以下主要反思点:(1)名录列入机制的整体方法;(2)列入标准的相关问题;(3)对列入名录遗产项目的跟进行动及其相关问题;(4)申报的审查方法。
2021—2022年是全面推进全球反思进程的关键期,通过在线磋商问卷调查、专家会议、三轮政府间开放式工作组会议等包容性进程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①相关成果文件可通过以下专题网页进行查询,https://ich.unesco.org/en/global-reflection-on-the-listing-mechanisms-01164,发布时间:不详;浏览时间:2022年9月16日。。其中,专家会议的背景文件首先肯定了《公约》三重名录体系的重要作用:“该体系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有助于使全世界的国家当局和社区认识到活态遗产的多样性和重要性,以及保护活态遗产的必要性,并动员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同时文件也承认,“经过十多年的实施,各利益攸关方发现了与这三个机制有关的大量复杂而又彼此关联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涉及面很广。”(LHE/21 EXP 2 Rev.4, paras.1-3)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直反复出现在委员会和大会在各自历届会议期间产出的法定文件中,主要涉及:(1)相关名录列入标准的修订;(2)遗产项目在两个名录之间转入或除名的程序;(3)对已列入名录的遗产项目之现状采取跟进行动;(4)年度审查周期可受理申报案卷的总量上限;(5)多国联合申报材料的编制及其扩展列入程序;(6)通过名录列入机制推动活态遗产保护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Document LHE/22/9.GA/9 Rev., note 2)
2021年12月和2022年7月,在第十六届常会和第五届特别会议期间,委员会在全球反思框架内分别审议了开放式政府间工作组的多项建议,并决定提议大会通过专门针对名录列入机制的《操作指南》修正草案。随后大会在第九届会议期间宣布三年反思进程结束,同时批准了委员会提出的《操作指南》修正案(Resolution 9.GA 9),所涉具体条款突显了对既有问题的实质性回应,也弥补了程序正义上曾出现的短板,并将规则细化到以下实操层面:(1)对已列入名录遗产项目的扩展或缩减;(2)遗产项目从一个名录转入另一名录,或从一个名录中除名;(3)申报材料的提交、审查、评审,以及时间节点的前移。其中有两处重大调整:一是明确规定了每年受理三重名录申报的总量,其上限从之前默认的50项左右提升到60项之内,包括同时申报急需保护名录和申请超过10万美金国际援助的综合案卷,而所有的国际援助申请改为由委员会主席团评审。二是遗产项目可以在三重名录机制之间实现转入,其灵活性广受欢迎;同时为“加强跟进”行动,对除名程序作了进一步规范。近期在线发布的2022年版《操作指南》(暂时只有英文和法文两个语种)已载入所有详细规程,除了须符合既有的相关标准外,社区事先知情同意和全程参与被置于重中之重。此外,针对优秀保护实践名册的遴选标准及其相关问题,新版《操作指南》第7段已删去遴选标准P.9,即“该计划、项目或活动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需要”,可看作为该机制“松绑”的第一步;同时,针对其他未尽事宜,委员会决定在2023年启动有关《公约》第十八条的专项反思行动。
应当承认,《操作指南》的最新修正乃是对《公约》名录列入机制中累积多年的沉疴进行的一次大面积清理。而让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Audrey Azoulay)颇感振奋的规则性突破正是来自活态遗产的内生性动力:“事实上,就像其捍卫的遗产一样,《公约》也是鲜活的,正在发展和扩大,以涵盖新的实践和新的工作方式。……现在,遗产项目可以在《公约》的三个国际合作机制之间转入: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名录和优秀保护实践名册。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每一遗产项目的监测就更有力、更精简。”(CLT-2022/WS/3, “Foreword,” p.v.)由此或可推知,今后针对《公约》名录所列遗产项目的监测管理将成为常态,而遗产项目在三重机制之间的转入及其后续的运作方式和保护成效亦有待在多个审查周期的实际运用后才能得到检验。
总之,在国家层面实施《公约》的能力建设一直是委员会长期支持的优先考虑事项,而有效实施则取决于对《公约》及其概念、措施和机制的全面了解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与名录列入机制一同构成“申遗—履约”双向实践的定期报告机制,同样也是为各缔约国全面实施《公约》规定的法定义务。换言之,从申遗到履约,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也需要以国际合作机制为背景,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双向观察中方能全面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政策制定和遗产治理战略。本文的鸟瞰仅力图在申遗与履约之间建立初步的相关性,或可为进一步讨论和评估中国现行四级非遗名录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及其前进的方向提供可资拓展的循证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