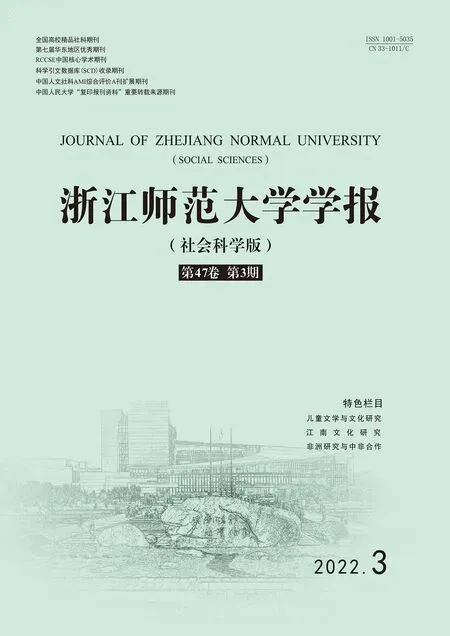《长物志》生活美学思想探微
张春华
(山东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晚明的江南,经济富庶,文化成熟,名门望族云集,能工巧匠迭出,文人们对精致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彰显着自己的生活品位,士大夫文化成为主流。他们遍访能工巧匠,为自己营造园林,布置居室,定制陈设器物,又将自己的审美品位诉诸笔端,形成文字,于是生活雅居著作迭出。文震亨的《长物志》便是这样一部佳构。
文震亨生于簪缨之家,为文徵明曾孙。文氏家族自明朝成化、弘治以来就享有巨大的声望。文氏家族自文洪一代为官至文震亨出生,在长洲(今苏州地区)已有近120年的历史。世系承袭,位高权重,财富积累,又加之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都为文震亨在文化鉴赏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如果说文徵明在书画领域表现出文人的清雅俊逸之风的话,那么文震亨则将这种文人意趣渗透在对日常生活审美趣味的追求中。他品行高洁,尚古好雅,受家族耳濡目染的影响,有着很高的艺术素养。他把日常生活高度艺术化、审美化,从中寄托了个人的品格情志,浸润着浓浓的士大夫文化气息,实现了精神的自由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长物志》可看作文氏家族百年文化艺术的积淀与传承。
《长物志》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全书共包括《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十二卷,分别涉及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赏、游等方方面面,在这一点一滴、一事一物中,传达出一种高远、旷达的士人情怀,表达了一系列的生活美学思想,为晚明士人提供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审美范本。诚如沈春泽在《长物志》序中所言:“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细碎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1]10《长物志》参考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凡闲适好玩之事,纤悉必具,大致远以赵希鹄《洞天清录》为渊源,近以屠隆《考槃馀事》为参值,明季山人墨客,多以是相夸,所谓清供者是也”。[2]陈从周先生评价说:“盖文氏之志长物,范围极广,自园林兴建,旁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金石书画,服饰器皿,识别名物,通彻雅俗。”[1]1
晚明文人的重情尚趣不仅表现在文艺领域,还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这种以情感物、以趣观物的视角,给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赋予了独特的情调,并获得了丰富的美感。正如陈继儒所说:“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令人古。”①这些日常之物被文人赋予了独特的审美感受和体验,表现出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独特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在《长物志》中得到了充分具体的呈现。
晚明的江南,经济富庶,风光秀丽,手工业发达。明自中叶以来,海外贸易发展,白银普遍使用,都促使江南的商业经济渐趋繁盛,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转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日益商品化,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这进一步推动了商业发展。商人们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过着豪奢阔绰、纵情挥霍的生活,社会风气逐渐变得浮华奢靡,追求享乐和炫耀,这就促使一些文人开始反思当时的社会风尚及生活方式,文震亨在其《长物志》中便通过对文人生活美学的强调来反对这种奢华的消费风气,从而影响乃至引领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因此,《长物志》中的生活美学在当时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一、清雅之美
文震亨把“雅”作为品物的首要标准。在他看来,人们在制作器物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物的形制、结构及材质是否符合“雅”的标准。这种“雅”,不仅体现在器物之外观形式,更是表现在器物传递出的精神文化内涵。
文震亨凭着他对生活之美的发掘与品鉴,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平淡、刻板与媚俗,以文人独特的眼光审视着日常的点点滴滴,以清新、雅致的审美趣味对日常生活展开布置与设计,对庸常的生活进行了审美性的再发掘与再创造,使审美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宫廷或富豪强调的奢华生活方式不同,也不同于市民百姓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文震亨所营造的是一种清静雅致的生活情境,这里有文人对品位与格调的追求,彰显着其独特的清雅自然的审美品位与文化素养。
文震亨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以“雅”统摄全局,对雅的推崇处处可见。如对琴室,文震亨认为应于“层楼之下,盖上有板,则声不散;下空旷,则声透彻。或于乔松、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清境绝,更为雅称耳!”对于街径庭除,则以“石子砌成,或以碎瓦片斜砌者,雨久生苔,自然古色”为妙。在论及榻的制作时,文震亨云:“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1]225他又云:“有古断纹者,有元螺钿者,其制自然古雅。”对当时流行的“大理石镶者”“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新螺钿者”,文震亨认为皆非雅器。再如:“方桌旧漆者最佳,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者,以供展玩书画,若近制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1]233-234“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更须莹滑如玉,不露斧斤者为佳,近见有以五色芝黏其上者,颇为添足。”[1]230用具不但要满足实用功能,更要符合精神层面的审美追求,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文氏对雅致生活的欣赏。哪怕对脚炉的造型花纹,文震亨都有要求:“脚炉旧铸有俯仰莲座细钱纹者,有形如匣者,最雅。”[1]254对香球式样的被炉,则认为其“俱俗,竟废不用”。[1]254
文震亨认为,理想的清居之地应以自然清雅为宜:“局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土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1]18文震亨在这里举出了四种居处,分别为:山水之间,山村,城郊,城市。在他看来,最好的居住环境是山水之间,但既然无奈生活在城市,那就需要讲求门庭雅致洁净、房屋清静美好、种植嘉木修竹,陈列金石图书。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才会达到“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的境界,沉浸在清幽雅致的居住环境中,方是幽居的妙处,才能与世俗庸常的人生区别开来。“室中精洁雅素,一涉绚丽,便如闺阁中,非幽人眠云梦月所宜矣。”[1]354这里注重了幽人雅致、人生适意,也可见出文震亨对审美对象的精准的直觉判断。
作为传统文化中一种常见的文化符号,鹤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绘画和传说中经常与高人雅士相伴出现,鹤飞翔时流畅舒展,鸣叫时清亮悠远,舞蹈时翩然优雅,文震亨对鹤也是欣赏有加:“空林野墅,白石青松,惟此君最宜。其余羽族,俱未入品。”[1]121士人在鹤身上寄托了自己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故而往往对鹤情有独钟,以表明自己乃志存高远之士。
二、简净之美
晚明时期科举考试的竞争更加激烈,读书人的仕途步履维艰,很多屡试不第的文人干脆放弃科考,选择乡居归隐。又加之晚明政治腐败昏暗,统治集团内部你争我斗,异常残酷,很多文人在党争中惨遭屠戮。官场凶险,政坛腐败,也使得部分文人心灰意冷,渐渐远离政治。这群文人放弃了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之后,转而对日常生活审美意趣进行了挖掘与品赏,以此安顿身心,调适心情。他们兴建园林,品茗制香,鉴藏书画古玩,品赏日常器物,清谈雅集,修身养性。
晚明的手工业也高度发展,日趋成熟,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产经验不断丰富。像家具制作、纺织技术、陶瓷工艺、金属工艺、印刷技术等在晚明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长物志》中涉及的陶瓷、服饰、家具及文房清玩、生活器用等都有赖于手工业的发展,就连《长物志》本身的精美刊刻也是离不开印刷工艺的发展的。明代涌现了一大批能工巧匠,正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所说:“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3]文震亨也强调生活美学的建构需要工匠精神的支持与协助,只有靠工匠的巧手匠心才能将文人的审美趣味付诸实施,变为现实。
宗白华说中国美学史上有两种不同的美感,有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有雕缋满眼、错彩镂金的美。文震亨选择了前者。在器具的制作过程中,他反对“专事绚丽,目不识古”,那样会导致“轩窗几案,毫无韵物”,[1]246如他对香筒的装饰,“略以古简为贵;若太涉脂粉,或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1]255又如对研匣的选择:“研匣宜用紫黑二漆,不可用五金,盖金能燥石;至如紫檀、乌木及雕红、彩漆,俱俗,不可用。”[1]301他反对在窗、竹床及研匣上使用彩漆,认为这种装饰有张扬炫耀之嫌,会迷乱人心,与他所倡导的简洁素净不相符。他对当时流行的奢靡之风进行了批判:“宁必饰以珠玉,错以金贝,被以缋罽,藉以簟茀,缕以钩膺,文以轮辕,绚以鞗革,和以鸣鸾,乃称周行、鲁道哉?”[1]339“侈靡斗丽,亦岂诗人粲粲衣服之旨乎?”[1]325
在居室的空间布局方面,文震亨认为应以简净为美,不盲目追求华丽堆砌,应充分考量人工与自然环境之关系,造园匠师应把几榻、器具、饰品按照顺序依次安排,令其秩序井然,具备合理的功能、恰当的比例和舒适的使用空间。如《长物志·位置卷》中写道:“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书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云林青密,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高雅绝俗之趣。”[1]347由此可见,室内家具、器物的陈设与摆放,实际源自文人对简净高洁人格的追求,本质上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营造出一种素洁高雅的文化艺术氛围,反映出中国传统文人对简朴、疏朗、高逸、雅致的审美情趣的向往和追求,是人文品格的一种外在的物化表现,文人们借此安放自己无枝可依的灵魂与对理想人格的向往追求。
三、自然之美
人们往往在远离自然的时候,才开始眷恋和怀念自然之趣。
明中叶以来,随着政局的动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有所松动。阳明心学崛起,提出了重建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要求。王阳明在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提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4]给僵化了的程朱理学带来很大冲击,使文人们由崇尚外在的道德理性转向关注内在的自然人性,促进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重视自我的独立,高扬个性的自由解放,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涵养精神。文人们迫切要求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因此追求自然、重情尚趣也就成了晚明文人反抗传统伦理教化的有力武器。
文人们一边享受着城市带来的繁华与舒适,一边向往着回归自然,于是纷纷选择了园居的生活方式,将自然山水引入园居生活,既能领略大自然的野趣,也能在热闹的城市中闹中取静,怡情养性,力求在有限的空间里营造出无限的自然野趣。“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要须回环峭拔,安插得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又须修竹、老木、怪藤、丑树,交覆角立,苍崖碧涧,奔泉汛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乃为名区胜地。”[1]102文震亨通过庭院中的缩微景观,传达出自然山水的风貌与神韵,将有限的渺小的自我汇入到无限宽广的大自然中,达到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并借此涤荡身心,实现个体精神世界的扩展、超越与升华。
此外,文震亨还将动物纳入到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再加之各种植物的合理配置,建立起一个万物共生共存的和谐的生态系统,平添了几分生活的乐趣。如《长物志》卷三《水石·广池》中云:“凿池自亩以及顷,愈广愈胜。最广者,中可置台榭之属,或长堤横隔,汀蒲、岸苇杂植其中,一望无际,乃称巨浸。若须华整,以文石为岸,朱栏回绕,忌中留土,如俗名战鱼墩,或拟金焦之类。池傍植垂柳,忌桃李间种。中畜凫雁,须十数为群,方有生意。最广处可置水阁,必如图画中者佳。忌置簰舍。于岸侧植藕花,削竹为阑,勿令蔓衍。忌荷叶满池,不见水色。”[1]102-103在文震亨看来,即便是人造的景观,也不要去随意侵扰自然,应尽量减少人的活动痕迹,对待动物不应采取实用功利的态度,而应以审美的态度去观赏并呵护它们,达到“竟日忘倦”的审美效果:“语鸟拂阁以低飞,游鱼排荇而径度,幽人会心,辄令竟日忘倦。顾声音颜色,饮啄态度,远而巢居穴处,眠沙泳浦,戏广浮深;近而穿屋贺厦,知岁司晨,啼春噪晚者,品类不可胜纪。丹林绿水,岂令凡俗之品,阑入其中。故必疏其雅洁,可供清玩者数种,令童子爱养饵饲,得其性情,庶几驯鸟雀,狎凫鱼,亦山林之经济也。”[1]102与现实中对功名利禄的追逐相比,禽鱼的自由自在、悠闲洒脱无疑更令人神往,召唤着文人将自己的心灵融入自然情境当中,以求得精神的自由解脱。
文震亨对自然之美的追求还表现在对生活日用品的设计审美之中,他力求获得人心之自然真实的状态,如婴孩般纯真无瑕,干净自然。如禅椅的制作,应不露斧斤之痕为佳;他反对有人种植芙蓉将靛纸蘸花蕊上,裹其尖,使花开呈碧色的做法;反对有人将凤仙花的五色种子一同纳入竹筒,使其开出五种颜色的做法。可见文震亨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中秉持着一种尊崇自然、不刻意改变自然的理念。
文震亨就是这样通过布置、营造外部环境,把人文的山林隐逸思想、器物玩赏文化、园林艺术与现实社会互相融合,使艺术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传达出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中国老百姓在普通的、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都着意去营造一种美的氛围……我们从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和今人王世襄的《锦灰堆》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可以看到中国美学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紧密的联系。”②《长物志》所呈现的,是江南文人在富庶繁华的经济基础之上所追求的一种既闲且隐、优雅精致的生活美学状态。文震亨的生活美学思想,是晚明时期江南商品经济萌芽的背景下产生的文人士大夫对美好精致生活的欣赏与追求。
注释:
①参见陈继儒《岩栖幽事》,明万历绣水沈氏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
②参见叶朗《中国美学在21世纪如何“接着讲”》,见《教育部2010年全国研究生“文艺学、美学前言问题”暑期学校会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