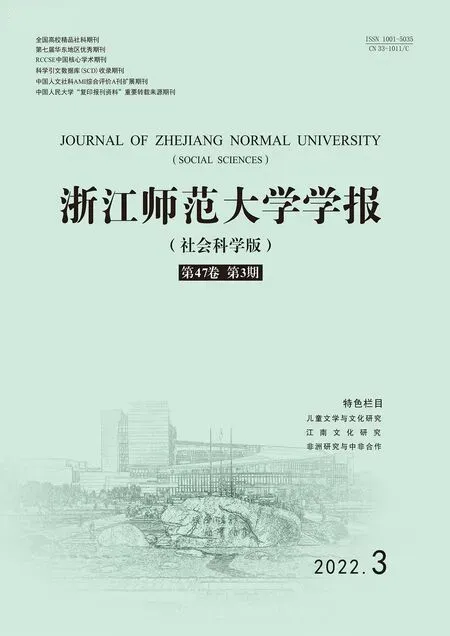理论争鸣与诗学建构
——探微“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论
龚游翔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2011年,罗钢撰文指出王国维诗学体系的核心观点“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是“经由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中国现代美学家的推进与深化而建构起来的‘学说的神话’”。[1]该观点一出即引发学界激烈争鸣:童庆炳、张郁乎等学者赞同罗钢的观点,认为其学案研究大胆而创新,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是具有强烈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学术建树。但是,彭峰、姜荣刚、孙仁歌、毛宣国和刘锋杰等学者却持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罗钢在研究方法上误用了错位的文献研究法:在实践层面上,忽视了“意境”与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的关系这一基本事实;在理论层面上,过度援引西方学术理论即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从而阉割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形成了阐释的错位,以致于归纳出错误的结论,从而弱化了中国近代诗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对“意境说”是否德国美学的变体这一观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论辩双方,他们分别从“意境”源头的追溯、内涵深蕴的挖掘、建构方式的辨析,以及演变路径的探究等方面开展研讨。
事实上,争鸣的反方替“意境说”辩护的理由是认为“意境”的内在审美经验根植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而罗钢认为“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的观点则强调“意境说”建构的学术话语机制是舶来品。因而,这表面上一正一反的论点最终都是趋向于同一目的,即探讨中国诗学建构的当代学术机制问题,进而完成中国文论与诗学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型,激发出中国古典美学的当代价值。“意境”范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体现的是情景结合、气韵生动和虚实相生的中国古典美学内涵,但其在“西方诗学中心主义”[2]的冲击下日趋边缘化与羸弱。而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美学家借鉴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论重构“意境说”的话语体系,对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与融合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鉴于此,理论争鸣的双方围绕着这一变体的观点,依据不同的证据来源,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立足于各自的理论立场而触发持续的争鸣,但其终点都是在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和文化理论自信的语境中,为寻求中国文论与诗学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型与当代建构而努力。因此,以“意境说”为代表建构起来的王国维诗学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诗学“失语症”的学术背景下意义重大,其理论内涵在持续不断的争鸣中生发出更多新的价值。
一、“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引发的争鸣
在“反思五四,重寻传统”的背景下,罗钢学案研究的意义是突出而显著的。他基于对比较诗学中的阐发性研究方式的探讨来解构王国维以降中国近代学者建构的诗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并且认为这一体系的核心观点“意境说”并非来源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而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因而,根据“意境说”而建构起来的中国近代诗学与文论话语体系则是康德、尼采、叔本华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在中国的嫁接与变形。罗钢敢于质疑学术权威,并且试图解构由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美学家建构的“学说的神话”,希望在中国诗学的当代转型视界中谋求重构更适合中国本土实践的诗学话语体系。罗钢认识到现代诗学话语体系的转型与重构必须寻找失落的传统,原生性的民族文化是推动当代学术研究话语重启的坚实土壤。而这一传承的延续曾遭遇破坏,传统文化的断层应该归咎于以往过于彻底地摒弃对传统的吸纳。鉴于此,童庆炳认为“罗钢《人间词话》学案研究是最有代表性的回顾性与反思性的学案、文案研究”,[3]回顾了五四激烈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典传统的遗失与缺漏,反思了其造成的后遗症问题。因而张郁乎称:“罗钢对王国维的一系列研究是近十年来此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之一,其批判的锋芒显而易见。既反思‘境界论’与传统诗学的关系,又反思嫁接中西美学(诗学)、援西释中的中国近代美学建构方式。”[4]他以王国维的“意境说”为个案推翻了由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一系列学人建构的中国近现代学术话语机制,并且提供了大量殷实的资料来佐证其观点。[4]李春青认为,罗钢的研究以大量的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5]这就是说,罗钢学案研究的学术意义就在于以思想探源和考证研究的方式回归《人间词话》中缺失部分的文本,以批判与创造性思维审视王国维以降近代学人的理论建构,通过归纳论证、逻辑推演来提出自己新颖的理论观点。他从始源处回溯中国近代诗学体系的建构模式,自然有极大的可取之处。但是,这种锋芒毕露的观点亦有纰漏,反对者从方法论选择、艺术实践和理论基础三个维度与其商榷。
从方法论维度分析,姜荣刚认为罗钢采用的“文献研究法”[6]的逻辑错位误导了对“意境说”的源头探寻。因为“意境说”内涵的西学因素无法于中国传统典籍中考证,王国维受德国美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只以其美学接受的相似性来判断,这是机械的唯物主义。罗钢分析《人间词话》中缺失的文本,将之与德国美学思想逐条匹配,并断言王国维深受其影响,这是典型的文献研究方式。夏中义曾言:“文献学比较最后会因望文生义式的逻辑错位而走向思维内讧。”[7]抛却文化层面的思考,单独文献的陈列是机械与静态的,文献的对比会产生错位的解读,难以断定其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意境”是一个复合性理论范畴,其具有“内在对抗性、复合性和立体性”,[8]并且生长于全球性学术合流的语境下,故而必然携带普遍的西学理论痕迹,比如罗钢认为的王国维诗学中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受席勒“感伤的诗与朴素的诗”影响,“能观”直承叔本华“直观”(intuition)思想,“写境和造境”是来自“理想与写实”。因而,罗钢在相似比较法下捕捉到王国维诗学体系与德国美学的共同处是正常的现象,但他却将之作为证据来源把“意境说”认定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进而更是得出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后学者共同建构了“学说的神话”的结论,从根本上忽视了意境本质上虚实相生、情景结合和韵味无穷等古典美学特征。为此罗钢自身曾辩护道:“西方以理论的身份,中国以材料的身份进入,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文化的介入,而是说现代意境概念并无传统意境概念的渊源。”[9]然而,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即使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继承,但生存于民间现实意识中的审美文化观念并不会荡然无存,因此现代意境概念是传统意境概念的演变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现代意境概念上残存的西学痕迹而判定其为西学变体,那么传统审美观念在意境上的再现为何就应该被置若罔闻。罗钢或许想说的是西方提供了现代学术机制,中国传统中并无这种理论形态的研究框架。但是他也可能忽略了中国诗话、书话、词话等点评方式虽不构成系统的理论,却也是理论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所以,现代意境概念里中国不仅以材料的形式进入,而且也同样以理论的身份进入,它与传统意境概念一脉相承、渊源颇深。
在实践层面上,毛宣国认为罗钢“对‘意境说’的概念定义和理论归属之争,漠视了‘意境’与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的联系”。[10]罗钢将“意境说”中的“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写境与造境”等完全类比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卡西尔等提出的德国美学理论,忽视了在中国古诗与书画等艺术实践中对意境所蕴含的虚实、情景、动静等审美形式的运用。类比的目的在于以相似性显示出差异性,若断然将两者等同,不顾中国文化自身的艺术实践,会导致阐释的错位。“意境说”蕴含着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实践和审美鉴赏,对其进行概念定义和理论的追寻忽视了作者与接受者的实际创作与鉴赏批评。
在理论层面上,刘锋杰、赵言领认为“罗钢虽质疑西方理论的普适性;但又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等西学资源证明王国维的理论不是原创”。[11]孙仁歌认为:“他操持着以西释中的话语,全盘洋化了意境说,忽视其现代创新实践。”[12]罗钢以西学的视角分析类比王国维“意境说”与德国美学的理论渊源,这种逻辑论证的确立会使中西诗学的平等对话交流处于被动的地位。刘锋杰等人以现代西方理论话语的视角反思与审视罗钢此说背后的西学印记也不无道理。
综上所述,由“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一说引发的争鸣,使我们重新回归和探讨王国维“意境说”本土建构的当代价值。罗钢指认的“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并非意味着将“意境说”的内涵完全认作是西学的产物,而是认为其背后存在的学术话语机制是舶来品。从其立场而言,罗钢基于对当代学术机制的思考,转而反思“五四”,重寻文化传统。他认为近代的文化运动导致中华民族的传统出现断裂,进而指出王国维等学人过度地将西方理论引进中国并且采用“援西释中”的阐释模式将中国本土文化全盘西化。所以,他不得不以“意境说”为“靶子”来解构西学东渐影响下中国近代诗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机制。从方法论角度而言,罗钢采用思想探源和考证研究的方式,以《人间词话》中被删弃的部分为证据探源王国维思想中的西学痕迹,借以论证“意境说”的变体原理。反对者也正是从这一维度质疑其研究的缜密性,指出文献研究法存在着误读的可能性以及阐释的错位等问题。他们认为“意境说”内在的美学内涵是自古承传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经受西方思想的冲击发生现代裂变,但并没有丧失其文化内核。在中西合流的近代语境下,王国维“意境说”必然带有世界性理论话语建构的特征,但并不能否认其内在的民族本土性根基,它与中国古典文论的“神韵说”“兴趣说”和“性灵说”等依旧一脉相承,是中国文论与西学理论融汇和演变下的现代学术范式。诚如黄键所言:“‘境界’说是一种充满矛盾与裂缝的理论系统,却仍然处于中国传统思维框架之中,仍然葆有中国文化身份。”[13]因此,不可因其携带西学元素而忽视东方元素,“意境说”仍然是“东方情调”的产物。[14]罗钢的学案研究试图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方式仍旧沿袭西方的模式,他希望抛却西方学术研究的机制,以中国传统的话语来建构适合于本土的学术体制,进而建构文论、美学与诗学等崭新的学术话语体系。他意识到遵循西方科学与哲学思维的学术机制并不适合中国人的文化实践与生活观念,而且其话语权也必将受制于人,因而他采取了更彻底的方式全盘否定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的建构。争鸣的反对方则持相对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王国维等学者们的努力对中国现代学术机制的建构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现代“意境说”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意境的部分内涵,当代诗学话语的建构亟需在原先基础上再做精进,另起炉灶的难度不容小觑。因而,争鸣的两者都在探讨中国当代诗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的问题。
二、探寻“意境说”争论的源头
基于比较的方法论视域下商讨中西诗学互鉴的可能性是论辩“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观点的可行性维度。王国维“意境说”诗学体系的建构占据着比较诗学领域的核心问题,即如何规避中西文化的异质性进而建构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的世界性诗学理论。王国维“意境说”建构之路的学理脉络中潜隐着三个维度的策略,呈现为三种观点:“中心范畴论、中西融合论、横向移植论,或称正统说、西来说、演化说。”[15]中心范畴论(正统说)认为“意境”概念内含的是中国古典诗学虚实相生的审美文化质素与注重“象”思维的中国传统意象抒情模式的媾和。此种观点暗含中国诗学话语范畴不掺杂任何西方元素之意,“意境”包括与之类似的其他中国古典美学或诗学范畴纯粹是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产物。这一策略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特征,从内部否认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同一性。横向移植论(西来说)认为“意境”是现代学者借鉴西学资源建构的现代理论范式,其内在逻辑结构是西式话语,是近现代学人建构的一种“学说的神话”,不具有中国诗学的原生性涵义。此种观点倾向于中国近代诗学话语的全盘西化,将中国文化元素完全排除在外,其中略见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缩影,这是一种带有虚假意识形态符码的文化策略。中西融合论(演化说)认为意境是中西文论互通的结晶,是中西融合的典范。演化说内部又分为两种:其一“突变说”认为“意境”并不具有古典美学的内蕴,是后人的现代建构,它与传统是断裂的;其二“渐变说”认为“意境”来自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发展与演变,与传统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观点持相对中性与温和的折衷调和立场,他们始终坚持中西异质文化是可以通过某种结构方式融合贯通的,其内部的两种分歧则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融合方式。以上三种关于现代“意境说”来源的观点,显示出中西比较诗学的三种策略: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中西融合,而“以西释中”归属于阐发性研究方法,其内部又可分化为“以西套中、以西带中”与“以西融中”两个极点。我们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视角窥探王国维诗学体系建构中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认为其诗学体系的建构采用影响研究(以蒋寅、罗钢为代表),他们认为王国维受到西学理论的影响,建构的“意境说”是“以西释中”的产物,他者文化的变体;二是认为“意境说”采用平行研究(以曹顺庆为代表),他们认为王国维诗学体系是“以西融中”的产物,将中国的重“意”传统与西学的学术范式耦合催生出“意境”的现代理论内涵。曹顺庆认为王国维诗学是阐发性研究的产物,他反对文论研究中“以西套中”和“以西带中”的学术方法,强调“以西释中”和“以西融中”的中性阐释策略,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创新成果大加褒扬,他“把王国维的个人旨趣之学推崇为平行研究之阐释变异与文化创新的典范”。[16]因而,罗钢采用了“以西释中”中较为极端的“以西套中”和“以西带中”策略,曹顺庆强调的是“以西释中”中较为中性的“以西融中”策略,并且认为王国维诗学理论建构对比较诗学中“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具有开拓性的借鉴意义。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方式已然从单向阐发与双向阐发的研究方式(如刘若愚的跨文化诗学体系建构),向“异质文化对话”[17]的形式过渡(基于叶维廉文化模子理论的提出)。中西文论的比较应该从各自文化结构的异质性出发探寻其家族相似性的特征,从而建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美学与诗学话语体系。这种策略更倾向于在保证中西文化异质性的基础上,选择有条件的部分做尽可能的融合,但是不敢奢求能够建立统一的、一般的世界性文学理论。因此,在当代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现代转型中亦需要有准确的认识与灵活的思维转变。西方的学术话语机制不可完全应用于中国诗学体系的建构,中国古典话语在当代全球性语境下亦无法独善其身而不受影响。我们应该在最大限度上既保留自身的文化基因,又寻求人类共性的某些基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与转型。
从意境的词源学视角,可以探析现代意境概念中葆有的传统意境内涵,意境本身亦非永恒不变的概念,它深受儒释道三家学说的影响,经历了三家观念的有机融合与演变。重“意”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象”“意”三者是中国传统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意象又有其不绝如缕的传承性;“境”即“境界”,是一个源自于佛教的术语。[18]随着佛教东传的深入,“晋宋齐梁对佛教经典的接受已经从‘格义’为主转移到‘镜彻(阐释)’‘综採(归纳)’和‘融冶(比较融合)’为主”。[19]故“意境”一词是中国古典“意象”融合佛教思想产生的美学范畴,是中国本土性滋长与印度佛教术语媾和的话语,经历了唐宋明清的演化又吸纳了禅宗的韵味,最终晋升为古典诗学的最高范畴。姜荣刚认为:“‘意境说’是中国本土义理拟配外来观念的格义现象,类似于佛教东传中的典型例子《鬼母子与九子母杂考》中的‘鸠占鹊巢,殊源合流’。”[20]近代学人标榜“意境”根本仍在于对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重“意”传统与“象”哲学的重视。西学“意境”的语源是“idea”,注重思辩,中学“意境”则具有释道融合的禅宗意味,中西“意境”的融合类似于佛教东传时的文化融合。中国古典美学的抒情传统长久以来是分散的,并未在理论上形成严谨的体系。从王弼《周易·略例》提出的“言意象”到王昌龄的诗有三境“物境、情境和意境”、刘禹锡的“境外之象”、皎然“取境”,再到严羽《沧浪诗话》的“兴趣说”、王渔洋的“神韵说”和袁简斋的“性灵说”,等等,中国传统诗学体系的零散如道家哲学一般空灵、随性,没有西方国家严谨而缜密的美学和诗学研究的学科分类和框架体系。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东渐和世界性美学理论建构的需要,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希望从中找寻具有普世性的美学理论。西学为中学提供一种现代的学术范式,在此研究模式中将中国古典美学的特性汲纳其中。王国维的“意境说”便是“格义”手法下中西文论互释、归纳和比较融合的典范,他把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美学融合贯通,系统性地建构具有民族本土特色的近代美学范式,因而其理论具有本土化特征。
鉴于上述研究,从“意境说”争论的源头去探寻,发现其原本也是多重文化多次融合的结果。罗钢的观点源于横向移植论(西来说),与其争鸣的学者主要持中心范畴论(正统论)和中西融合论(演化说)。探微两个阵营的学术动机和逻辑思路,罗钢认为“意境说”沉潜的话语策略是西式的,即王国维借鉴康德、尼采和叔本华等理论家的思想及其学术研究方式;反对者则认为“意境说”虽应用了西学框架,却是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作物。而笔者认为王国维“意境说”是西学范式激发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意境”在现当代美学和诗学批评实践下的本土理论重构,在当代世界文论合流和文化多级制衡的语境下对中国文论和诗学话语的当代转型具有借鉴意义。罗钢“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一说并没有否认王国维诗学体系建构的理论意义,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认为其背后存在文化话语霸权的现象,目的是指向中国当代诗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转型;反对者更是在捍卫王国维“意境说”隐含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意义上与其商榷,他们共同试图探寻中国当代文论与诗学话语转型与建构的新向度。
三、围绕“意境说”争鸣的当代意义
围绕“意境说”引发的争鸣需要置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当代复苏和中西诗学与文论比较互鉴的视角中,才能凸显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意义。
首先,中国古典美学以诗话、词话、书话和画论等点评类文章为主要内容,对文学艺术的批评散落于各类点评文章之中,并无西方体系化的学科建构的概念和实践。近代以来,西方美学、艺术与文学理论相继涌入中国,王国维参照日本学者将Aesthetics一词翻译为“美学”,开始将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与感性内涵的学问归入美学学科,自此有了中国现代学科建制的先例。但是,就学科分类而言,美学、艺术学和文艺学在国内学界仍然是互相交缠与媾和的。哲学美学研究美学的一般问题被归于一级学科哲学之下,包括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研究;文艺学研究文学的审美经验和一般的文学理论问题被归于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而学界研究美学的学者大多出自文艺学科;艺术学自2011年开始独立成科,包括艺术理论与各级门类艺术的具体研究。艺术的审美问题既是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又属于美学的领域,而美学与文艺学的交叉地带亦延伸出“文艺美学”的概念,总之三者之间相互交缠、犬牙交错。然而,文艺美学的思想和学术建构却要追溯到20世纪初的王国维,他的贡献就在于“用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展开文艺研究和评论,在理论建构和文本批评两个方面为中国文艺美学的建设提供了崭新的样式”,[21]其后在宗白华、朱光潜和李泽厚等人的著述中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而,以“意境说”为代表的王国维诗学体系的建构对中国的学科体制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尤其是海外汉学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将中国古诗词介绍到西方世界。但是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外国人读懂中国古典诗词,因而需要建构一种普世性的诗学理论,以解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现代化转型”问题,[22]实现中国古典诗学体系的现代转型。刘若愚建构了跨文化的诗学体系,但也引发了比较诗学中对“以西释中”“以西援中”等方法的反思。海外汉学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兴起,让我们又回溯到王国维诗学体系的建构方式,发现其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叶维廉的《中国诗学》亦探讨了中西诗学互译的问题,提出两个文化模子的理论。我们发现对“意境说”建构问题的审视需要在现代汉语诗学语境下进行探讨,中国诗学的语言语法逻辑规则和西方以逻各斯理性建构的语法模式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在中西比较诗学中,以西释中和以西融中的方式都存在相应的局限性。中西诗学如何展开平等而有效的对话是中西学术交流摆脱“文化霸权”的重点。从古今对话而言,中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互间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这使得中国近代诗学和传统诗学之间出现裂缝,现代读者无法深刻把握和全面领会古诗的意蕴,无法对古诗进行有效的填补空白。当代的阐释机制是建立在现代汉语的思维模式之下,与传统古汉语的思维模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中国当代诗学话语的建构主要是以白话文和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为基础,进而重构文论话语的主体性规则。两者的核心都是要处理好中国诗学话语与西学话语,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关系。因而,王国维以降宗白华、朱光潜等学者建构的意境说引发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解决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型问题。罗钢的说法引发的争鸣,旨在让我们思考中国古典诗学话语如何在西方“他者”话语策略下型塑当代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建构起自身本土的诗学话语体系,或许这种吁求才更为迫切,而王国维诗学体系的建构也在这个意义上变得突出而重要。亦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认为“意境说”的本土建构具有标志性的开创意义。
再次,随着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发觉中国古典美学自身所潜藏着的能量宝库。在新世纪文化自信的战略下,激发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内在能量和保持其在当代艺术批评中的活力成了重要的学术追求。中国古典美学范畴除“意境”之外仍有多种文类点评术语,如《文心雕龙》中的“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又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雄浑、冲淡、沉着、典雅”等。每一个精练性词组所构成的批评术语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如何使其在西学范式的激发下唤醒其审美内涵,这将是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重要工作之一。当今,中国当代文论在处理古典美学范畴时往往面临误读的现象,因而需要思考“在后现代之后,如何理解和阐释面临的新的问题,尤其是审美阐释如何可能”[23]的问题。而构建中国当代文论和美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必要步骤,曹谦认为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处理好弘扬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与接受西方现代理论范式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发掘、整理中国古典文论精华与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论走向世界的关系”。[24]因此,立足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学术范式和概念术语,建构体系化的理论和学术框架是实现古典美学精神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呼吁进行“本土话语再造”的新世纪,[25]可以借鉴王国维以“意境说”为核心的近代诗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方式,将古典文论中点评的术语、美学的范畴与批评的机制放入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和发展,使其对中国当下的美学和文学批评实践发挥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功能性作用,以此为基础来建构中国本土的文论、诗学与美学话语体系。罗钢“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一说引发的持续争鸣使我们重新审视王国维“意境说”的本土建构,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通过争鸣共同导向一个问题:如何激发中国古老诗学话语范式于当代美学的价值。王国维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利用现代学术范式重构传统诗学体系,激发出中国古典美学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新活力,这或许是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话语现代转型的有效方式。
最后,我们回到罗钢与姜荣刚等人关于“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展开的争鸣。他们虽然在表面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都是在思考相同的理论问题: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挖掘中国传统精神的内核,建构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论与诗学话语体系,达成与西学理论的平等对话,解决中国诗学“失语症”的问题,从而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使命,进而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中西诗学与文论的互鉴因其文化结构的差异性母质,难以奢求所谓一般的具有普世性的文学理论。因此,五四之后,全盘西化的借鉴模式被中国学者重新审视与批判,中西诗学的交流与对话中的平等思想日益凸显。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增长迅猛。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亦进入新的阶段,以往我们趋之若鹜的西学理论而今成为反叛与批驳的对象,王国维诗学体系也是在此语境下被纳入罗钢的批评视野之中。中国审美现代化的启蒙在一定意义上有其卓越的贡献,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思考破而后立的问题,这就是姜荣刚等人维护王国维学术贡献的根本立场。前者是大胆的推翻与小心的求证,后者是坚定的维护与缜密的辩驳,此学术争鸣引发学界的激烈讨论,深化了中西诗学如何有效互鉴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已构成学术事件。
结 语
罗钢与其争鸣者回顾王国维的“意境说”,对其诗学体系的建构呈现出一正一反的态度。罗钢希望打破五四以来近代美学与诗学体系的建构方式,彻底颠覆原有的西方学术范式下的理论体系,从零做起重新挖掘,找寻失落的古典文化传统。而姜荣刚等人则认为应该肯定王国维的贡献,在其基础上展开现当代文论的重构。一方是更为彻底的斗士,一方则是相对保守的卫士。争鸣双方在结论的准确性上无所谓正误,只不过在探究“意境说”建构的立场、研究方式和证据来源上存在着差别。罗钢试图扭转西式美学观念的植入和全盘西化的文化霸权,以“意境说”内含的西式观念为切入点,批判其西学成分,是值得肯定的。而姜荣刚等人为“意境说”的中国成分辩护,认为其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说亦过于西化,也不无道理。故两者的争鸣实则是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出发,一个否弃西化,一个肯定本土化。然而,双方在“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一说的争鸣与商榷中,实则是在探讨中国诗学建构的当代学术机制问题。中国古典诗学体系的现代转型、中西比较诗学与文论的有效互鉴,以及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现代阐释等问题,被进一步深化与推进。这一争鸣已经构成学术事件,不仅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为学界注入了思想的活力,对中国当代文论、诗学和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学术争鸣的影响仍然在不断持续,讨论的视域越扩越大,伴随相生的问题亦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