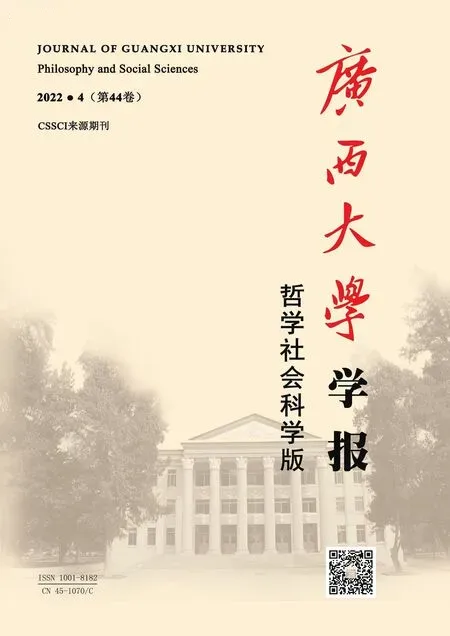公允之花与偏狭之果:裨治文译介晚清基础教育述论
邓联健
19 世纪以前英美两国的中国知识,多辗转来自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等语种的作品,直接以英语译介中国的著作较为罕见。19 世纪后,一批来自英美等国的传教士和世俗西人,基于在华现实交往,全面开启中国国情在英语世界的直接传播,其中相当长时期内传教士是主要的参与者。据笔者粗略统计,来华新教传教士中发表过汉籍英译作品者就有100 余人,其译介内容涉及儒家典籍以及历史、文化、科技、宗教等各个方面。主要任务在于宗教传播的新教传教士,为何将精力投向译介活动?传教士身份对相关译本的样貌和译介效果会产生何种影响?考察这场译介活动,或许能成为我们深入理解近代中西交流史的一个特殊路径。美国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1801-1861),是传教士译介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中,就中国教育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而言,他无疑是用力最勤、成就最大者,在基础教育方面尤甚。百多年来,研究者对这位基督新教来华先锋传教士关注有加,相关重要研究主要从裨氏生平传记、中国研究、文化交流、翻译工作等方面展开,而对于其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基础教育的努力,尚未见专门研究和深入考察。本文拟结合裨治文所处时代背景,描述分析其译介中国基础教育、英译中国蒙学教材之基本情况,梳理其对中国教育的主要观点,进而揭示新教传教士译介中国活动的基本特征。
一、知识与“福音”:“儒生”裨治文的教育译介动机
美国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堪称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裨氏自1830 年起在华传教30 余年,长期担任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主编并完成大量中英文著译作品,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以及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等人同为新教在华事业奠基人物,并常被后人称为美国汉学开山鼻祖。鉴于裨氏的受教育程度、行事风格以及其文字事工成就等,有学者称其为具有“儒生”风范的传教士,这实不为过誉。①参看张静河:《裨治文的“儒生”风范》,《书屋》2017年第12期。
在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开展双向译介等知识传播活动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影响。在被称为“知识的世纪”的17 世纪,西方迅速兴起科学革命,随之而来的是18 世纪后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这对基督教的权威构成根本威胁。到19 世纪初,理性对信仰的胜利、科学原理对宗教“真理”的胜利业已成为常识。这一革命性的时代变化,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知识。基于对知识和理性之重要性的认知,以约翰· 卫斯理(John Wesley)为代表的基督教学者打破加尔文主义的故步自封,掀起新教复兴运动,强调信仰和理性的并行不悖以及人的理性在神学信仰中的重要性。成长于美国第二次新教复兴运动兴起时期的裨治文,少年时期便深受该运动思潮影响,②E.C.Bridgman,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Bridgman,New York:Anson D.F.Randolph,1864,pp.4—5.尤其受复兴运动重要人物萨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影响至深,甚至正是在霍普金斯“知识的拯救力量”思想的激励下来到广州,并将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作为传教战略的主要支柱。③M.C.Lazich,E.C.Bridgman and the Coming of the Millennium: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Knowing The Time,Knowing of a Time”——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Milllenniial Studies,Boston University,December 6-8,Conference Proceedings,1998,pp.2—4.
正因为此,知识及教育成为裨治文来华后一段时间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丛报》的早期文章显示,在裨氏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对中西关系问题的诊断与展望中,知识都是居于中心位置的概念。他在《中国丛报》创刊号《导言》开篇即指出东西方长期交往中“知识和道德交流”之稀少罕见,④E.C.Bridgman,“Introductio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No.1,1832,p.1.在该刊第二卷《导言》中又陈说中国现实中“最令人痛心”的问题是“知识的停滞”或“知识的衰退”。⑤E.C.Bridgman,“Introductory Remark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No.1,1834,p.4.纵览《中国丛报》第一、二、三卷(1832—1835)《导言》,裨治文相当密集地运用与知识相关的语汇、概念和内容,反复强调知识增长和知识流通的重要性,并将知识的“交流”“封锁”“沟通”“传播”分别跟国家社会的“进步”“停滞”“退步”等密切关联,让人感受到知识在“改善”“净化”“征服”“拯救”等方面的力量。而频繁出现的“智力的和道德的”“道德和宗教”“科学和神圣的真理”“有用的知识和神性的真理”等概念组合,则说明裨治文对知识之影响力的关心主要集中在智力、道德和宗教领域,充分体现了裨氏对知识、智力之于宗教信仰影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三篇《导言》鲜明反映出裨氏对知识、传教二者关系的理解:科学或世俗的实用知识并非信仰的障碍或挑战信仰的工具,而是通向信仰的道路或桥梁。知识传播与福音传播紧密相连,是信仰传播最有效的媒体,拯救灵魂的力量在于知识。
对知识的影响力有着深刻认识的裨治文,自然深知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曾在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大会上申言: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培养一整代人……它在一定时期内定能对一国道德水平、社会性质、国民性格产生巨大影响,其影响将胜过任何军事力量,胜过最发达商业的刺激,胜过任何其他单一手段甚至所有手段之和。⑥E.C.Bridgman,“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No.8 (1836),pp.378—379.
正是在他的倡议推动下,新教在华差会联合驻穗外侨于1834、1836 年相继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和马礼逊教育会。裨氏对教育于传教之重大意义的理解也超出其同侪。其时,美部会秘书长安德森(Rufus Anderson)认为裨治文等人在华组织的教育活动大多与基督教精神了无关涉,并对其作用深感怀疑,而裨氏则致信安德森说,“教育乃是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最主要手段之一”。⑦M.C.Lazich,E.C.Bridgman,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0,p.217.裨氏对教育之传教功用的洞察从此可窥一斑,其译介中国教育的强大动力由此可找到源头。
美部会曾在给裨治文的书面指示中要求他“将有关中国人民性格、状况、风俗、礼仪的情况悉数写信告知”。①E.C.Bridgman,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p.26.于是,对“知识的拯救力量”和教育之传教功用有着深刻理解的裨治文,在到达广州后的头几年里,将相当多的精力集中于中国教育问题。相关情况的调查与分析、系列专文和译文的发表、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和马礼逊教育协会的创立,以及相关教育改革行动的酝酿,各项工作系统推进、环环相扣,成为裨氏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其中基础教育是他中国教育叙事的核心议题,②关于中国的教育问题,裨治文曾说:“我们当前主要关注的是基础教育,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参见E.C.Bridgman,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6,No.5,1837,p.232.中国基础教育的译介和蒙学教材的翻译是其重点所在。
二、“如实传递”:中国基础教育译介
在19 世纪初,西方常有人质疑相关汉学著作的可信度,认为外国作者是“不可靠的目击者”,于是“许多作者都力图证明自己的资格”。③罗伯茨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海林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强调通过亲身经历和实地调查获取信息、不持偏见地传递信息,一直是裨治文树立话语权威的有力武器。他在《中国丛报》创刊号《导言》中即清楚展示其译介态度和立场。知识来源方面,鉴于基督教国家跟东亚精神文化交流之稀少以及西方早期中国学作品之不可信,④E.C.Bridgman,“Introductio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No.1,1832,p.2.他提出要充分借助中国本土丰富的权威文献以获取准确客观的中国知识:
因外国书籍总是互不一致、矛盾百出,我们深感有必要求助于中国最权威著作,并尽力确认其水平与可信度。当前每一个领域都能获得数量众多的权威著作……还应参考历史著作和统计文献以展示其过去与当下。⑤Ibid.,p.3.
紧接着,他以自然史、商业、宗教等领域为例提出应如何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真实信息。⑥Ibid.,pp.3—4.译介态度方面,他表示“我们将不带偏见地开展工作,考虑的只是责任,而非回报”,⑦Ibid.,p.4.并宣称“只能如实记录”中国相关情况。⑧Ibid.,p.2.这充分表明,裨治文试图扭转西方人此前常常依赖听闻、转述、转译以及“想象”的风气,显示出他尽力求真求实的基本姿态。
裨治文关于中国的著译文章主要刊于他自己主编的《中国丛报》。因裨氏本人十分倚重本土权威文献,该刊相当比重的文章是对中国文献的摘译或编译,或含有翻译、摘译、编译的内容。为数众多的教育相关专文、书评、报道等,实为翻译含量不一的译介之作,内容涵盖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譬如,其对晚清教育的介绍就包括学校数量、教育覆盖面、教育管理、教学方法、学生规模、教材选用、师资状况、教师待遇等。虽然《中国丛报》大量文章在刊发时并无著译者署名,但我们可以确知涉及教育的重要文章大多出自裨治文之手。⑨《中国丛报》封刊时所出《二十卷〈中国丛报〉所含主题总索引》(General Index of Subjects Contained in the Twenty Volume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按主题列出该刊各篇专文的信息,其中包含作者信息。从该索引看,有关中国教育的专文、译作几乎皆为裨治文完成。其所撰多篇全面介绍中国教育总体状况的专文,实为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教育之发端。其中《中国人的教育》一文,①E.C.Bridgman,“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4,No.1 (1835),pp.1–10.描述了古代中国的辉煌教育成就以及社会高度发达的情形,②其实裨治文在该文中对中国古代的辉煌也持有怀疑态度。对于中国人和部分西方人将中国古代描绘得“在每个方面都很完美”,他认为还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持中国古人所达到的智慧和知识水平。参见E.C.Bridgman,“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p.6.回顾了“近代”教育发展,并找出“近代”教育各方面停滞不前甚至不如古代的系列明证:未有任何一种艺术、一门科学取得显著进步,语言进步甚微,甚至发生倒退,“近代”天文学历史几乎为一片空白,等等。裨氏该文之重点,是对包括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成效等在内的中国教育传统的全面否定,并最终认定中国的教育体系与正确的教育及真理、知识的传播是背道而驰的。中国自身无法推动教育变革,而必须借助外部力量,至少“最初的推动力须来自国外”。③E.C.Bridgman,“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p.9.裨氏另一篇重要专文《在马礼逊教育会首届年会上的报告》④E.C.Bridgman,“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pp.229–244.指出,须“尽早摸准中国人真实的教育状况”。⑤ibid,p.232.其主体是一个覆盖面甚广的调查报告,包括十八个部分,即全国人口、社会阶层、男女比例、学校类型、男性识字率、女性识字率、入学年龄、蒙学读本、教学方法、在校年限、每日学时、教学场所、学生人数及特点、教师素质、教师待遇、考试、奖励、惩罚。通览该报告,中国晚清教育可谓一览无余。
在《中国人的教育》一文中,裨治文透露了他全面介绍中国教育国情的目的:
若能向全世界完整充分地介绍中国的文教历史和教育体制,不仅能抹除关于中国人智慧状况的盛行错误观点,还大可助益中国人摆脱那些古老荒唐惯习的束缚。⑥E.C.Bridgman,“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p.5.
正因为此,在上述两篇专文以及其他文章中,除对教育事实的描述外,裨治文还指出中国教育存在的系列问题,其中反复论及的问题有四个。一是受教育人口比例低。他多次提及中国人的识字率问题,⑦E.C.Bridgman,“The Sacred Edict”,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No.8,1832,p.305.⑧E.C.Bridgman,“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p.7.各处数字虽不尽相同,但结论如一:教育覆盖面窄,识字人口比例低,女性更是极低。二是教育内容偏狭。对于以入仕为导向,始之以蒙学读本、继之以四书五经的国士教育,裨治文认为其内容极不全面。他指出教育应为全人教育,须在体、智、德三方面加以全面训练。三是缺乏合格启蒙教材。裨治文极不认可将儒家经典作为教材的做法,认为以《三字经》为代表的蒙学读本虽“所涉主题并不深奥”,但语言“晦涩难懂”,⑨E.C.Bridgman,“Santsze King,or Trimetrical Classic”,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4,No.3 (1835),pp.116.例如《小学》就存在“语言大大超出年幼者理解水平”之弊端⑩E.C.Bridgman,“Seaou Heo,or Primary Lesson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No.2 (1836),pp.81.。四是汉字阻碍教育普及。裨氏认为,汉字的奇特性使得孩童脱离意义进行背诵,而这既不能增进知识,也无法培养心智,机械的识字能力强化训练容易束缚、扭曲思维;费时费力的阅读能力培养易挫败学习者,并浪费了孩童求知速度最快的机遇期,导致中国人各方面知识贫乏,自然科学知识尤甚。我们发现,裨治文介绍中国教育的各篇专文,虽然文章标题并未冠以“基础教育”字样,但其关注点显然主要在于基础教育,这与他“一国命运系于代代青年之早期教育”⑪E.C.Bridgman,“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Formation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No.8(1836),p.378.的认识应有很大关系。
上文的叙述显示出裨治文在纠正以往不实描述、力求客观准确方面的追求。他熟悉并善于利用中国教育制度文献、教育史籍以及西人相关著作,注重亲赴广州等地书院、学堂、科举考场考察相关情形,并能从亲身听闻中收集素材。这种基于中国本土权威文献和本人亲身经验的知识获取路径,与他在《中国丛报》创刊号《导言》中的宣称相当吻合。正因为此,裨氏各篇文章中展示的中国教育事实和数据等,虽因作者偏居广州而未能全面反映全国状况,且不能完全排除其有意选择论述对象或裁剪过滤考察范围,但就各文所涉对象而言,其相关描述并未见有远离实情者。此外,从他所指出的系列现实问题看,其认识和判读基本准确公允。时至20 世纪,慈禧下诏废除科举,民国时期废除经科提倡新教育、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教学采用白话文,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汉字简化运动,这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虽不能说是应裨治文的呼吁而生,但至少有力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
三、“原样呈现”:中国蒙学教材英译
裨治文在一篇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的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无法接近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特质了解甚少。即使西方人能与中国人直接往来,但由于他们的荣誉、德行、福祉、正义、良心、是非等观念与西方人迥异,双方交流中的误解与问题必然层出不穷。①E.C.Bridgman,“Intellectu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7,No.1,1838,pp.6–8.而要理解中国人的心理特质,重要手段之一便是翻译中国各类型著作,特别是主导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儒家作品。不过,在其他西方人士相继翻译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时,裨治文在儒学著作英译方面的努力主要集中于蒙学系列读物。究其原因,裨氏大概有两个考虑。一是蒙学读物较四书五经拥有更大的受众群体和更广的影响面,二是裨氏本人十分关心中国的基础教育,而蒙学读物是其核心教材。
清一代的基础教育其实就是蒙学教育。自宋代以降,蒙学教材主要为俗称“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并辅以其他读本。作为最早向英语世界翻译中国文献的人士之一,裨治文的翻译选材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蒙学教材,包括《三字经》②E.C.Bridgman,“Santsze King,or Trimetrical Classic”,pp.105–118.《千字文》③E.C.Bridgman,“Tseen Tsze Wan,or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4,No.5,1835,pp.229–243.《鉴韵幼学诗帖》④E.C.Bridgman,“Keenyun Yewheo Shetee,or Odes for Children in rhym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4,No.5,1835,pp.287—291.《孝经》⑤E.C.Bridgman,“Heaou King,or Filial Du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8 (1835),pp.345–353.《小学》⑥E.C.Bridgman,“Seaou Heo,or Primary Lesson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No.2,1836,pp.81–87;Vol.5,No.7(1836),pp.305–316;Vol.6,No.4 (1837),pp.185-188;Vol.6,No.8 (1837),pp.393–396;Vol.6,No.11,1838,pp.562–568.等五种蒙学核心读本。各读本英译文于1835 年至1838 年间先后刊载于《中国丛报》,另有介绍《百家姓考略》⑦E.C.Bridgman,“A Brief Inquiry Concerning the Hundred Family Name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4,No.4 (1835),pp.153–160.的专文。至于裨氏为何未译出“三百千”中的《百家姓》,并非因为他对该书未予重视,而是“其内容的独特性质导致无法翻译”使然。在他看来,若将《百家姓》中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译成英文,只会成为像“雪、李、鸟、枪,石、木、黑、岩”般毫无意义的文本。⑧Ibid.,p.154.翻译也好,介绍也罢,裨治文终究是较系统地完成了中国蒙学读物的译介,而且在中国古代基础教育教材向英语世界的直接传播史上,裨氏上述译本均属首译或是最早译本之一。⑨这五种中国蒙学读本的英译,在他之前仅有马礼逊于1812年译出的《三字经》,以及修德(Samuel Kidd)和麦都思分别于1831年、1835年译出的《千字文》。马礼逊《三字经》译文收入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一书,修德《千字文》译本题为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s,由马六甲传教书社(Mission Press)印行,麦都思《千字文》译本收入其编纂的《朝鲜委国字汇》。
包括蒙学读物在内的中国典籍多是内容深邃、意蕴丰富的作品,处于不同时代语境、出于不同译介目的的诠释者,往往对同一著作的知识内涵和现实功用各取所需,造成差异悬殊的解读。以《孝经》翻译语境为例,裨治文的英译完成于“中西教育比较”语境之下,跟卫方济(François Noёl)的“中国礼仪之争”语境、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的“中华帝国”语境以及理雅各 (James Legge)的“比较宗教”语境均不相同,因而各人对《孝经》的性质定位悬殊,所选底本也不一样。①参见潘凤娟:《介于经典与蒙书之间的民间教材——裨治文与中西教育脉络中的〈孝经〉翻译》,《汉学研究》2016年第4期。作为一名关切中国基础教育并有意促进其教育体制改革的中国观察家,裨治文对“三百千”乃至《孝经》和《鉴韵幼学诗帖》等的译介,都只是为了向西方展示中国蒙童教育的教学内容。马礼逊的《中国通俗作品译文集》(Horae Sinicae: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也译录了《三字经》。从该译文集的“告读者”可知,马氏的选录标准是“大中华帝国的人们阅读最多的书籍”,其翻译目的则是“满足过去二十年来所激发出的对这个奇特国家的关注与好奇”。②R.Morrison,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London:T.Williams and Son,1812,p.iii.显然,马礼逊的《三字经》性质定位及其译介目的均无关教育。而同样是面对包括《三字经》在内的儒家著作,裨治文在《鉴韵幼学诗帖》译文按语中说的是:“中国学校目前采用的教材,三部已经呈现于本刊读者面前,这部《鉴韵幼学诗帖》为其第四部。”③E.C.Bridgman,“Keenyun Yewheo Shetee,or Odes for Children in Rhyme”,p.287.裨氏按语中的“三部”指的就是他业已译出或介绍过的“三百千”,可见其对《三字经》等著作的定位跟马礼逊明显不同,裨氏眼中的“三百千”就只是教材。值得注意的是,裨治文这句按语同时也表明了他译介中国启蒙教材的计划性。
裨治文对各部教材的英译,鲜明显示出“原样呈现”的努力。他尽力“原样呈现”给西方读者的,首先是书籍相关信息及其外在形式。其各个译本均有一个或详尽或简短的前言,内容主要译自本土权威著作,大致包括作者简介、成书历史、书籍性质、目的功用、语言特征、版本信息、书籍形制等。其中《三字经》译本前言最能体现其让读者直观感受原书样式的努力。该前言列出原书首页“人之初,性本善”等六句计三十字,交代自右向左的阅读顺序以及每列两栏、每栏三字等细节信息,六句皆用拼音形式竖行排列展示。这种让西方读者感觉怪异的展现方式,却反映出裨氏真实准确地呈现原作的追求。在《小学》译文的前言,裨氏宣称“努力保留中文的习惯用法,尽管这样常会使英语译文变得不那么漂亮”。④E.C.Bridgman,“Seaou Heo,or Primary Lesson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No.7,1836,p.305.又如在《千字文》译本正文中,他常对原文限于形式而未表达出来的意义作出增译,但所有增译均置于方括号内。这一独特处理方式既有助于读者更好理解,又不失真于原文实际内容。⑤E.C.Bridgman,“Tseen Tsze Wan,or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p.231.
裨氏这种追求在其翻译副文本的运用上也有一定体现。他在上述五个译本的前言中从未添加带有价值判断的引导性话语,也不像马礼逊、柯大卫(David Collie)等人那样在译文中时常夹杂注解来表达批评意见。⑥一个称得上例外的情况是,裨治文在《千字文》英译文本之后提供了大量注释,其中部分注释中加入了他自己的理解和评价。不过,因为所有注释均列于译文之后,并不影响原文的“原样呈现”。他还如此解释自己不给《孝经》译本加注的做法:“我们本想在《孝经》的某些地方加些注解,但受版面限制而不得不省去。建议读者参阅原著,那里有全部详细解说和注释。”⑦E.C.Bridgman,“Heaou King,or Filial Duty”, p.346.其《鉴韵幼学诗帖》译文更是既未添加注解,也未作任何评论,裨氏对此也有解释:“据我们所知,从未有人对此书做过评论。同样,我们在此也仅将译文呈现给读者自行研读,而不添加任何注释和评论。”⑧E.C.Bridgman,“Keenyun Yewheo Shetee,or Odes for Children in Rhyme”,p.287.这两处解释的前半部分实乃无足轻重。前者“版面限制”的理由其实站不住脚,因为同样是刊于《中国丛报》,马礼逊的著译作品却随处可见注解和点评。后者“从未有人对此书做过评论”也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这两段说明的关键在于各自后一句的潜藏意思:应让读者自行关注事实,作出判断。关于这一层意思,其在《孝经》译后评论中有着更为明确的表达:翻阅几页经典后便给出权威意见,这并非难事,但我们希望先让读者掌握事实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结论。①E.C.Bridgman,“Heaou King,or Filial Duty”, p.353.
裨氏这种在前言里不做评价引导、在译文中几乎不加注解的操作,跟其“不带偏见地工作”的宣称相一致,或许还有借此争取话语权威的功用性考虑。对于倚重本土文献以传送中国“可靠”知识的裨治文而言,用英语原样呈现这些对于中国人影响至广至深的蒙学读物,不仅可以直接传递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道德行为的渊源所在,还能以此为据找到中国人“低劣”国民性的根源。而译者不加评注、让读者“自行掌握事实”的做法则可自证译作的客观公允,有助于塑造一个权威的中国知识传播者的形象,增强译介文本及其系列话语的可信度。这在当时西方各路人士对中国问题话语权的争夺中至关重要。
既然坚持让读者通过自行研读译文获得结论,那么译本就应该不失真、不走样。裨治文的译文的确反映了这方面的努力。纵览裨氏各个蒙学读物译本不难发现,就意义和文学性而言,译者重点关注意义的传达,至于原作中的对仗、押韵等文学特征,并不是他的重点考虑。在翻译方法上,裨氏多取直译,并常采用字面翻译的方法。以《孝经》为例,他将“孔子居,曾子侍”句中的“侍”直译为“by his side(立于其身旁)”,将“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中的“一人”简单处理为“one man(一个人)”,将“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中的“社稷”照字面译为“produce of their lands(他们土地的出产)”。②Ibid.,p.346.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虽忠实于原句字面,但意义跟原文相去甚远的译文,主要原因当然是裨氏中文水平较低,但也不能排除是因他过于追求“原样呈现”所致。
四、偏狭之果:基督教有色眼镜下的中国基础教育
上文的叙述表明,裨治文在译介中国基础教育过程中,无论是追求客观准确的公开宣称,还是在译介实践中对晚清教育国情的“如实传递”和蒙学教材的“原样呈现”,都体现了他纠正以往中国叙事之偏颇失真、追求客观公允方面的努力。加之其十分强调自身中国知识之“现场性”权威,③裨治文曾在《中国丛报》对那些间接获得的中国知识表示质疑,以彰显“现场性”知识的重要性。他说:“现代以来,有谁去过中国各省?谁跟中国居民有过广泛接触?谁读过他们的书?”参见E.C.Bridgman,“Intellectu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p.2.裨治文建构的似乎是一个客观公允的中国基础教育形象。或者说,裨氏这方面的努力至少开出了迷人的“公允之花”。然而,深入考察裨氏著译作品便会发现,在其“公允之花”的下面,是深厚的基督教土壤。正因为这一土壤,“公允之花”最后结出的果实是“偏狭之果”。
在《中国人的教育》一文,当裨氏转述中国古代辉煌的知识和教育成就时,这些叙述很容易被理解为他对中国古代成就的高度赞赏。我们认为,他接下来的保留立场才是重点所在。文中提到,有西方学者将中国圣贤与圣经人物等同看待,而且这种看法跟“中国人的祖先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有登峰造极的造诣”的观点遥相呼应。④E.C.Bridgman,“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pp.5—6.裨氏述及此事,并非因为对其真伪的关注,而是由于他对中国学术被无意中提升到跟西方辉煌成就相匹敌的程度而耿耿于怀。究其原因,裨治文早在《中国丛报》创刊号《导言》中就已表达过对中国人学问水平的基本判断:
窃以为,我们对本土文献总体上还重视不够。一方面需让其发挥应有作用,但也应尽力避免走向另一极端。我们不太指望能找到大量足以跟西方国家的艺术、科学和制度媲美的东西,更不奢望在中华帝国汗牛充栋的文献中能发现价值和权威性足以撼动圣经地位的作品。①E.C.Bridgman,“Introductio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No.1,1832,p.3.
这段文字的意义不可小觑。需要说明的是,写下这段话时,裨治文在华时间刚满两年。对中国文化还仅有皮毛知识,却对中国文献作出如此武断的结论,透露了他先入为主的观念预设:“异教”的中国必定不如基督教的西方。裨治文等新教传教士之所以有着如此的预设观念,原因当在于其基督教立场和传教目的。事实上,裨氏对其基督教立场并不十分隐晦。同样在这个《导言》,裨氏就在表示对中国情况“只能如实记录”之后,紧接着又说“我们是带着特殊情感来做此事的”。②Ibid.,p.2.从语境判断,他所说的“特殊情感”无外乎就是基督教的立场和传播基督教的目标。在这种立场和目标下,传教士们坚信“对中国作出正面评价,将会危及传教事业的合法性”。为获得传教合法性,他们需要塑造一个因缺乏“神的启示”而处于黑暗落后状态的中国形象。道理是明摆着的:“如果一个民族因其文化道德水准高而无需拯救,又何苦费时费力去帮助他们?”③M.A.Rubinstein,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1807—1840,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Inc.1996,p.131.
上文的叙述显示,裨治文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译介以及对蒙学教材的英译,其事实描述和文本翻译均在忠实再现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诚意和努力,在描述分析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时也大体客观准确。但是在这些称得上客观公允的描述和评价之外,其著译作品中还夹杂着大量建基于基督教立场的评论性话语,对中国教育予以全面否定。
《中国人的教育》中的一段评论,可谓让中国教育无法翻身的致命一击。裨治文在剖析中国教育存在的诸方面问题后,从古代圣贤学说开刀,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历史、现状作出根本否定:
中国圣人的政治—道德体系运行已数千年,而现在大家一致公认的是,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每况愈下。对于一个存在根本缺陷的教育体系而言,这是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中国从来就没有很高的道德水准……整个国家全无一种力量足以促使改变产生,将其国人提升到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水平。④E.C.Bridgman,“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p.9.
这段文字的背后,潜藏着“(基督教西方)进步—(异教中国)落后”二元对立下的俯视视角,这一视角下的中国教育体系是存在根本缺陷的。至于这个“根本缺陷”是什么,裨治文接下来隐约给出了答案:中国缺乏那种能够让人思考、使人有智慧的学校和教育,因为它存在着“阻止光和真理进入”的障碍。⑤Ibid.,p.9.裨氏意在告诉读者:儒学是基督教的天敌,是导致中国停滞甚至倒退的根源。在他眼里,正因为儒学“鸠占鹊巢”而使得基督教的“光和真理”一直未能在中国传播。
实际上,跟同时期其他许多传教士一样,裨治文在分析中国各种问题时,都会在其基督教教条化的线性思维中迅速地在“上帝缺席”中找到一切问题的“根源”,教育问题也概莫能外。在其多篇专文中,对中国教育的否定批评和“上帝缺席”的简单归因模式随处可见。
关于裨治文的蒙学教材英译,因在他着手翻译之前就已在《中国人的教育》一文对中国教育作出全面否定并意图促进其教育改革,我们可以揣测其教材翻译之目的之一就是要让英语读者切实感受这些文本作为蒙童教材的缺陷所在。手中随时紧握基督教标尺的裨治文,对其“中国启蒙教材极不合格”的判断显然是自信十足的。前文提及,为追求“客观公允”效果,裨氏从不在译文前言中对原著作价值判断。在《三字经》译文前言,裨治文说“该书的内容和风格是否适于用作启蒙教材,读者在研读我们提供的译文后将会有更好的认识”。⑥E.C.Bridgman,“Santsze King,or Trimetrical Classic”,p.107.不过,裨氏追求客观公允、让读者自行判别优劣的宣称并未贯彻到底。在《三字经》英译文之后,他最终还是按捺不住,添上了一段极富基督教色彩的评论:
该书虽然风格清新、语言纯正,但道德情操和信仰准则方面的内容十分欠缺,全书无一字一句引领孩童的思维去超越时间与感官。书中对天父、造物主、万物之主宰完全不着一字,学子们只能在一片漆黑之中摸索通向永恒之路。①Ibid.,p.118.[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第116页。
这明显是在批评《三字经》缺乏神学内容或宗教关怀。在《小学》译文之后,裨氏也作出大意如此的点评:作为中国教育的根基,内容“不完备、不牢固”,中国先哲“从未达到知识的起点水平,浑然不知敬畏上帝”,自然不会将上帝关怀融入教学之中,“仅是这一事实便导致他们所有伦理体系的巨大缺陷”。②E.C.Bridgman,“Seaou Heo,or Primary Lesson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No.2 (1836),p.87.[英]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第149页。
在上述有关中国教育的评论中,裨治文显然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教育,而几乎完全未给予“理解之同情”。于是,中国教育的先贤人物、经典教材、思想根基,在一个充满宗教偏见的译介者笔下成为不堪一击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