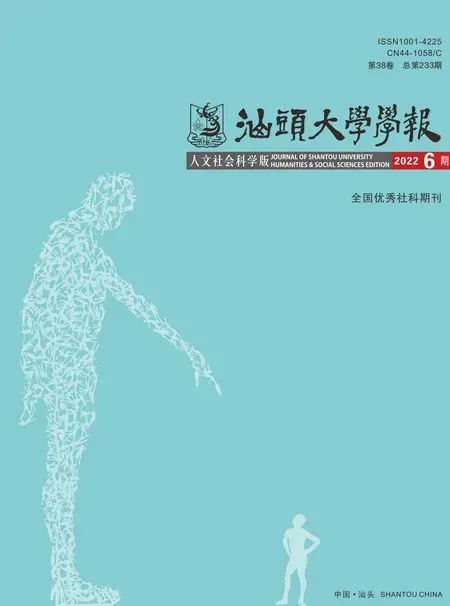《柳毅传》重写过程中报恩母题与“龙女”形象的嬗变
杨庆杰,刘心怡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龙女报恩”是中国民间叙事中的一个重要母题。龙在中国神话中很早就出现了,它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是糅合了其他动物特征后被创造出的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龙”下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1]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图腾。”[2]在封建时代,“龙”的形象出现于各种图案之中,并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由此可见,虽然中国传统语境下龙的形象与后起故事中的龙王以及龙子龙女很不一样,但中国早期神话中描绘的“龙”无疑为我国龙女、龙王的故事提供了现实土壤。龙王、龙女最早出现于汉译佛典。当学者将梵文Nāga(那伽)译成汉文的“龙”时,佛教中以蟒蛇为原型的Nāga(那伽)便和中国本土的龙合二为一,从而给龙的传说注入了新鲜内容。我国关于龙女报恩的故事,就是在佛经的影响下产生的。①参考许彰明的《宋代龙女报恩型故事的世俗化演变及其小说史意义》第一章,此章节对龙、龙女形象的起源与汉译佛经中龙女的形象特点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3]《大唐西域记》[4]中就记载了一则相关的故事:被驱逐的落难公子释种在逃难过程中偶遇龙女,发愿将其变为人形。龙女的父亲为了报恩赠给了释种宝剑让他得以杀死国王自立,龙女也因感念释种的恩德嫁给了释种。然而由于“宿业未尽”,龙女每次与释种欢会时都会变回原形,释种因此非常厌恶龙女,最终将龙女的头颅砍了下来。②除《大唐西域记》外,在中国的佛教典籍中,讲述龙女报恩故事影响最大的是被《太平广记》《法苑珠林》等类书引用的《商人驱牛以赎龙女得金奉亲》一文,记载了龙女为报商人救命之恩,赠送商人宝物“八饼金”之事。这些故事中的龙女虽然有珍奇的宝物和变形的神通,但依旧是前生犯错,今生受苦的畜类:“生时龙,眠时龙,淫时龙,瞋时龙,死时龙。一日之半,三过皮肉落地,热沙抟身。”(引用自《商人驱牛以赎龙女得金奉亲》)在早期的汉译佛经故事中,受“人畜殊途”观念影响,龙女通常以一种丑陋、淫秽、低人一等的姿态出现。她们与凡人较少因报恩产生情感联系,哪怕选择以身报恩也很难得到一个美好结局,这与中国文人笔下美丽、善良的龙女形象完全不同。
在文人早期创作的龙女故事中,唐传奇《柳毅传》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借鉴了印度龙女报恩故事的相关人物情节,却挣脱了佛教思想的影响,率先打破了佛经故事中对龙女的刻板描写和模式化的情节走向,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类型的神异故事。因此,《柳毅传》流传颇广,对后代文学和戏剧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后世据此重新创作者,为数众多。在一次次的再创造过程中,《柳毅传》的情节主旨不断变化,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龙女”这一符号化的形象也在一次次的文人重写过程中,发生了多次变迁。
《柳毅传》是一篇质量上乘的唐传奇,研究者不在少数,但相较明清小说,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截至目前,学术界对《柳毅传》文本嬗变、母题方面的研究虽然比较零散,但也均有研究成果出现,如程国赋的《〈柳毅传〉演变过程》、胡秀峰的《柳毅故事嬗变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果大都集中于探讨故事情节的历史演变,对人物形象和母题书写的时代嬗变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试图从龙女形象变迁这一角度切入,对《柳毅传》及后世嬗变作品进行研究,探寻其嬗变过程中“龙女报恩”母题书写和龙女形象的变化历程及变迁原因。①后世嬗变作品选择的标准参照程国赋在《唐代小说嬗变研究》附录(唐代小说嬗变一览表)中明确的标准:“注重人物、情节与唐代小说的相同或相似。”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选取了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四篇作品进行研究,即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明传奇《橘浦记》、清代传奇《蜃中楼》与短篇小说《织成》。其他如《柳毅洞庭女》《龙绡记》《乘龙佳话》等作品或流传亡佚,或文本低劣,影响有限而不具代表性,因而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一、《柳毅传》——龙女形象的创新与报恩母题的限制
唐传奇《柳毅传》讲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浪漫奇幻故事:洞庭湖龙女奉父母之命远嫁泾阳却被婆家虐待,在孤立无援时遇到书生柳毅。柳毅不避艰险,传书相救。龙女对柳毅心怀感恩并自愿以身相许,结为夫妻。小说将报恩主题与婚恋主题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不仅表达了作者自身对世俗爱情的美好向往,还体现了作者对当时寡妇再嫁、科举不易等社会问题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人物设定的创新是《柳毅传》的一大亮点。受印度佛经故事和中国神话传说的影响,龙或者是皇权和民族图腾的神圣象征,或者是人们心中凶猛乃至残暴的神秘动物。《柳毅传》却创造性地赋予了它们人的特征,并弱化了其“兽”的特性。身为龙族的洞庭君、钱塘君具备真诚善良、知恩图报的美好人性,泾阳君作为反面角色,则有着人类统治者中残暴的一面。龙族中发生的包办婚姻、夫妻不和乃至婆媳矛盾问题都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问题如出一辙,作者对于龙宫的描写则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皇宫,处于故事中心的龙女可以被想象成皇族中地位尊贵却惨遭夫家抛弃的公主。在整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龙”与“人”的关系是和睦而非对立的,男主人公柳毅对龙族的看法始终是好奇大于鄙夷。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对神鬼之类超自然物质的包容态度。如此设定人物一方面给柳毅和龙女的结合提供了合理动机,另一方面也赋予了这段奇幻爱情故事深刻的现实意义。
龙女的形象塑造是整篇小说的重中之重。故事一开始,龙女就以一种美丽悲惨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5]2850作者通过柳毅的视角交代了龙女的狼狈处境,也为后来柳毅传书解救龙女埋下了伏笔。龙女得救返回龙宫,华美的出场昭示着她作为龙族公主的高贵优雅:“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恰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5]2852在龙宫与柳毅尽享宾主之欢后,虽然柳毅拒绝了自己以身酬恩的想法,但龙女依旧没有放弃,选择化身卢氏,在人间与柳毅再续前缘,且给柳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永生的能力:“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5]2856毋庸置疑,《柳毅传》中的龙女形象塑造是非常具有开创性与颠覆性的。作者用细腻深刻的笔触赋予了龙女出身和精神上的双重高贵,这完全突破了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对异族兽类可畏又可鄙的描写,也大大扭转了六朝志怪小说留下的神秘、猎奇的写作传统。李朝威对龙女的“拟人化”描写让整部作品迸发出现实主义的光辉。作品中的龙女善良勇敢、重情重义,哪怕深陷包办婚姻的泥潭却依旧向往自由,是封建社会里善良多情的少女化身。小说高度肯定了龙女的善良品质,深切同情其悲惨遭遇,体现了作者对残酷封建婚姻制度的厌恶和对婚恋自主的向往,也侧面反映出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与践踏。李朝威笔下的龙女几乎拥有封建社会女性应该拥有的所有美好品质,也面临着封建社会女性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种种问题。某种程度而言,她与现实社会中的贵族女性已没有什么分别。唯一不同的是,作者保留了龙女的神异属性:她能够长生不老,永驻青春,也能够帮助自己的夫君获得永生之术,尽享富贵。在这样的描写下,龙女成为一个兼具“人性”与“神性”的完美角色,寄托了唐朝士族文人对婚恋对象的审美理想。
然而,在肯定人物创新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柳毅传》成型于唐朝,小说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远算不上成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柳毅传》的人物塑造必然会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明确知道《柳毅传》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报恩故事,龙女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报恩者”,但受佛经报恩故事叙述传统的影响,作者依旧选择将整篇小说的叙述重心完全放在柳毅身上。在“报恩”母题的限制下,龙女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角色。她的存在一直是次要、被动且只为男主人公服务的,哪怕实际上龙女才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由于作者并没有对龙女的内心活动进行细致刻画,读者无从得知龙女是否真正对柳毅产生了情意,以至于她排除万难也要嫁给柳毅似乎也仅仅基于“回报男主角”这一个动机。除此之外,因为被作者赋予了太多理想化色彩而缺乏更多细节的刻画,龙女被塑造得比较扁平。她更像一个集体性格的象征性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人物。
哪怕存在诸多瑕疵,我们仍然不能否认《柳毅传》的首创之功。作者对龙、龙宫的“拟人化”描写使得整部作品能够更加贴近人类社会,将神魔题材与现实题材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柳毅传》的出现标志着“龙女报恩”这一故事母题与婚恋题材的融合,为之后的婚恋报恩故事创作提供了模板。
二、《洞庭湖柳毅传书》——女性形象世俗性与主体性的增强
两宋时期,柳毅故事以各种形态的文学形式流传。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大多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①据《唐代小说嬗变研究》附录(唐代小说嬗变一览表)统计,两宋期间以《柳毅传》为母本创作的作品有宋杂剧《柳毅大圣乐》(已佚)、宋元戏文《柳毅洞庭龙女》(已佚)和金代《柳毅传书》诸宫调。,流传下来的作品则因为因袭柳毅故事的痕迹非常明显,艺术造诣不高。②参考胡秀峰的《柳毅故事嬗变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宋元文言小说,话本和戏文中的柳毅故事”。此章节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两宋时期的柳毅相关故事,文中提到的以小说形式存在的《柳毅娶洞庭龙女》(出自《绿窗新话》)和《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出自《醉翁谈录》)故事情节与《柳毅传》几乎完全一致,没有创新性。[6]直到元代,柳毅与龙女的故事才重新焕发活力,被作家以戏剧这样的文学形式加以展现,赋予了故事不同的时代意义,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相比于篇幅短小的《柳毅传》,共有四折的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有了更大的叙事空间将故事情节进一步完善。剧中添加了大量的人物动作与人物对白,也让龙女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和丰满。
与《柳毅传》相比,《洞庭湖柳毅传书》中的龙女显得格外泼辣、主动。她在受丈夫冷遇,被公婆刁难时,会与夫家正面对抗:“公公,非关媳妇儿事,这都是小龙听信婢仆,无端生出是非。媳妇也是龙子龙孙,岂肯反落鱼虾之手?”[7]567态度非常强硬,而不是一味哭泣,只等着柳毅救援。面对柳毅时,她不再卑微顺从,甚至带着些骄傲与任性,在柳毅拒绝自己一片痴心时会在心中暗暗埋怨柳毅“无情无义”:“既不得共欢娱伴绣衾,还待要献殷勤倒玉樽,只怕他阁着酒杯儿未饮早醉醺醺。”[7]578化身卢氏再见柳毅时也会半瞋半喜地在心中编排柳毅认不出自己:“他那里絮叨叨则管问行藏,咱两个相见在泾阳。欲待对官人说个明降,又恐怕肉身人道我荒唐。不俊眼的襄王对面儿犹疑梦想。”[7]580在尚仲贤笔下,一个敢爱敢恨、活泼热情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龙女不再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仕女,而是充满了市井气与烟火气:面对不公她会全力反击,面对爱情她也会主动争取。她有了自己的想法与脾性,更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龙女对爱情、婚姻的追求已经打破了原始的“报恩”母题,充分地体现了女性生命的自主和自由追求。
可以看出,虽然在故事情节上《洞庭湖柳毅传书》并没有多大创新,但故事中的女主角却被作者赋予了新的性格特色。这与作品主题、体裁的转变和创作背景都不无关系。首先,虽然“报恩”依旧是《洞庭湖柳毅传书》的主要线索之一,但“婚恋”才是元杂剧的最主要主题。作品没有将柳毅的义气与龙女的知恩图报作为叙述重点,而是通过大量心理描写展现柳毅与龙女之间涌动的情愫。龙女非柳毅不嫁绝不仅仅是为了报答救命恩人,更是因为她与柳毅擦出了爱情的火苗。作品主题的改变使龙女在故事中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性,也使她追求柳毅时展现的热情执着合情合理。其次,相较短篇小说,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在完善龙女形象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尚仲贤打破了之前龙女报恩故事中第一主人公为施恩者的惯例,确立了龙女主人公的地位,使龙女站在了剧本结构的中心,摆脱了唐传奇中的从属地位。加上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原则,龙女在作品中有了更多表达自我的权力。体裁的转变带来的还有语言风格的转变。唐传奇《柳毅传》篇幅短小、用词考究,虽然也是小说的一种,却几乎没有俚俗与口语的表达。元杂剧的书写体制让叙述空间变得更大,敷演性质更强,这使得《洞庭湖柳毅传书》的语言表达可以不再讲究凝练,但一定要自然本真,利于人们理解。杂剧中的口语化表达非常之多,大量生动泼辣的语言描写与心理活动描写使龙女大胆直接、至情至性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
除了体裁的转变,唐朝到元朝创作背景的巨大转变也是龙女形象变迁的主要原因。唐传奇虽是古代小说的一种,是现代人眼中的通俗文学,但由于当时传播媒介的不发达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唐传奇归根结底还是贵族文学,不会在民间流传。据李富强考证,《柳毅传》的作者李朝威大约是中唐时人,可能是唐宗室蜀王后裔,“在蜀王房,渤海王房第七代有名‘朝威’者,无官职”[8]。作者本身出身贵胄,他的作品就更加不会是娱乐大众之作,而是自己和其他官员仕人的赏玩作品。他创作传奇不是为了让平民传播阅读,而是为了展现自己超人的文学才华;他笔下的人物也不是为了讨好读者而生,而是寄托自己完美社会理想的载体。这样看来,《柳毅传》中的龙女被创作成一位永远带着优雅与矜持的贵族女性,一位道德毫无瑕疵的完美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到了元朝,社会局势大变,汉人的科举之路被全部阻断,写作元杂剧的作者大多是落魄文人而不是高官贵族,生活的窘迫和生存的压力使他们的创作不再是为了取悦自己,而是为了能够敷演成功,养家糊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传播途径的进步,小市民与普通人拥有了更多的娱乐消遣方式,他们成为元杂剧的主要观众。创作者和受众群体的改变使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不可能继续高高在上,柳毅与龙女的故事便逐渐变成了平民文学。龙女的形象也就不必完美到失真,摇身一变成为市民想象中有缺陷、敢争取的龙族公主。
总体而言,《柳毅传》奠定了龙女形象的基本基调,而《洞庭湖柳毅传书》则真正让龙女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作品中龙女的公主身份虽然还未改变,形象却朝着大众化、市民化的方向前进了许多。
三、《橘浦记》——报恩母题的强化与女性形象的弱化
明朝以《柳毅传》为基本素材改写的作品集中在戏曲方面,有黄维辑的《龙绡记》、周侍御的《传书记》和许自昌的《橘浦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只有《橘浦记》被保留了下来,可供今人阅读研究,其余两本传奇均已见不到完整的著录。《橘浦记》是明朝许自昌据《柳毅传》敷演而成的传奇剧本,与《洞庭湖柳毅传书》相比,其情节建构有较大的差异性:戏文在保留了柳毅替龙女传书的基本情节的同时,增入了虞世南女(湘灵)与柳毅的感情线。故事的后半段则添加了白鼋、猿猴和蛇报柳毅救生之恩,而丘伯义却陷害恩人柳毅以求富贵等情节,讽刺忘恩负义之徒不如禽兽,说教意味浓厚。在理学盛行的大背景下,《橘浦记》不再宣扬自由与爱情,而是重新将“报恩”作为故事最重要的主题。
因为《橘浦记》增添了许多支线与新的人物,龙女不再是剧中唯一的女主角,柳毅传书、龙女报恩也不再是作品的唯一主线。虽然与元杂剧和唐传奇相比,共二十二出的《橘浦记》叙事空间进一步扩大,作者用来描摹龙女形象的笔墨却大幅减少。许自昌选择柳毅作为全戏的唯一主角,对龙女的刻画比较潦草,心理描写与神态描写几乎没有,龙女一角的塑造在戏中自然也谈不上圆融饱满,几乎沦为“背景板”般的存在。如果说叙事重点的转移使龙女形象得不到充分刻画,走向扁平,那么作者在情节上的改动则使龙女彻彻底底变成一个几乎没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思考能力的被拯救者。龙女在洞庭君问她再嫁之事时,就明言想要嫁给柳毅,以身报恩:“女孩儿前日托柳郎致书时节,便面与他有婚姻之约。女孩儿情愿嫁这柳生,若有别选东床,女孩儿情愿不嫁,以守柳郎便是。”[9]102然而真正促成两人婚事的,却一直是洞庭君与钱塘君,龙女只是被动等待,听命于长辈。龙女与柳毅不得见面时,是洞庭君想办法让女儿与柳毅相会:“如今闻得他上京应试,船泊此地,不免先扮作客船同女孩儿在船里待他到来,将计就计强逼那柳生成就这段姻缘。”[9]158与柳毅一夜欢会后,龙女却因为自己再嫁的身份,姿态放得极低,不敢主动追爱:“相公你若中了一任相公,择取高门,愿为奴为婢,以侍节栉。”[9]167故事的结尾,龙女又因柳毅已有婚约,在他人撮合下甘愿做一位妾室。
从情节的大幅变动可以看出,许自昌想要在《柳毅传》的基础上生发出一个新的柳毅故事。然而囿于作者本身的才华和时代的局限性,《橘浦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远远比不上前作。虽然柳毅故事发展到了明朝,传教意义被大大削弱,世俗性大大增强,但儒家思想对“报恩”行为的重视与宣扬丝毫不逊于佛教。许自昌的儒生身份让他深受程朱理学浸染,将戏剧当作教化世人的工具,极度宣扬“善恶有报”的理念,“报恩”主题在《橘浦记》中得到了空前强化。作品对报恩母题的回归与强化导致龙女重新回到“报恩者”这一被动地位,彻底丧失了勇敢追爱的能力,也没有了贵族女性应有的矜持,只是一个一心想要报恩却不被作者赋予任何主动权的功能性角色。同时,在龙女形象世俗化的过程中,她的道德标准与行事准则也逐渐向儒家主流价值观靠拢。《橘浦记》中龙女形象的塑造深受明代理学文化笼罩下的儒家礼教观念的影响,龙女从一而终、誓不再嫁、男尊女卑、伏低做小等婚恋观体现了明代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女性意识。戏文中龙女的身份虽然未曾改变,表现出的形象却更像一位被封建礼教束缚住手脚的贤德妇人。总而言之,与前人珠玉相比,《橘浦记》中的龙女一角显然黯淡许多。
四、《蜃中楼》与《织成》——女性形象的多样化与报恩母题的再度突破
随着通俗文学的兴盛和龙女故事的大范围传播,清朝时期据《柳毅传》改写的小说戏曲不在少数,出现了至今仍继续流传的短篇小说《聊斋志异·织成》和传奇剧本《乘龙佳话》《蜃中楼》。其中《乘龙佳话》是清末古越高昌寒食生创作的传奇剧本,因主要情节与母本大致相同且艺术价值不高,传播度和研究价值不及另外两部作品。因此,本文仅对《蜃中楼》和《织成》进行具体分析。
清传奇《蜃中楼》由明末清初的戏剧名家李渔所创,是明清交际之时有关柳毅故事再创作作品中文学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在明清“言情”小说盛行的大背景下,李渔完全舍弃了原作中的“报恩”主题,延续了自己“写情”的传统,以《柳毅传》为底本,糅合《张生煮海》的部分情节,将《蜃中楼》变为了一部专写爱情的才子佳人剧。同时,为了演出的丰富与可看性,李渔对共三十出的传奇《蜃中楼》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创新,颠覆了之前的单线叙事结构,使剧作中一共出现了两条主线和两对主要人物。《蜃中楼》讲述了士子柳毅与张羽同住而皆无妻,柳毅在访友途中偶遇在蜃楼观景的舜华和琼莲二位龙女,遂与舜华订婚,并替张羽与琼莲订婚,然而因龙女的叔父钱塘君鲁莽答应泾河龙王亲事,舜华被逼嫁与泾河小龙,后张羽传书龙宫,钱塘君同泾河龙王大战,又经逼婚、煮海等曲折,两双情人终成连理的浪漫爱情故事。从创作动机分析,《蜃中楼》是作者为了“鼓风化之铎”[10]207、劝人向善创作的剧本,剧中的人物设置带着强烈的理想色彩,龙女更是被作者当作女性楷模来描摹。这促使李渔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将龙女“弃妇”的身份进行改动并在剧中一再强调两位龙女对“贞节”的重视。然而,正是李渔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设置的改动,使龙女摆脱了“被拯救者”的身份和以情酬恩的道德规范,在作品中拥有了更为纯粹的爱情和更加完整、独立的人格。
《蜃中楼》中一共有两位龙女,即舜华和琼莲。作为爱情剧的女主角,二位龙女重新回到了故事中心,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李渔巧妙地改动了人物出场顺序,使舜华与琼莲初登场时就是妙龄少女,而不是被抛弃的牧羊少妇,两位龙女对情人的好感不再来源于恩情,而是纯粹地欣赏:“(丑)公主,你看海边上立着一个男子,好生标致。(旦望介)果然好个俊雅书生!远观那样风致,近看还不知怎么样风流?”[10]210柳毅登上蜃楼求娶舜华时,对待爱情大胆主动的舜华没有禀报父母,便与柳毅私订终身:“孩儿见他才貌非凡,将来定有好处,一时情不自已,将身子许他过了。”[10]226琼莲在听闻张羽才貌双全后,也选择将婚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没经家人允许就直接应承了婚事:“(小旦)知他是怎生的模样?(生)若论才貌,小生还不及他。(小旦背对旦介)姐姐,看他怜香至性,惜玉真情,料不把虚言相诳。凭你做主罢了。(旦对生介)舍妹也许了。”[10]244舜华被逼与泾河小龙拜堂成亲时,作者通过一系列动作描写展现了舜华的坚贞不屈,对不公命运的勇敢反抗:“(扯丑与旦同立,末赞礼,丑拜,旦不拜介)(副净)怎么儿子倒肯拜了,媳妇又不肯起来?你们扯他拜。(众扯旦拜,旦不拜介)。”[10]252面对柳毅诘问自己为何不以死明志,反而屈嫁他人时,舜华的回答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旦)不宽父母之优忧,反加老母之罪,一不便也;柳郎不知我为死节之妇,反以我为失信之人,二不便也;不但埋没妾身名节,又且耽搁舍妹终身,三不便也。那柳郎家在潼津,闻得潼津去泾河不远。奴家图到泾河,觅便寄一封书去。一来使他知我万不得已的苦情,二来叫他早完妹子、张生的亲事,然后自尽,岂不名实两全?”[10]268在作者的细心描摹下,两位龙女有胆有识、有才有情的形象跃然纸上。姐姐舜华对待爱情热情似火,敢于追求,对待父母朋友也能做到有情有义,不失分寸。面对强权逼压,她能坚守本心并谋划策略,面对朋友爱人的指责,她仍能够冷静处理,以理服人。小妹琼莲虽然不像舜华一般理性周到,甚至一度错怪姐姐,但她对爱情的忠贞与执着同样令人感动。虽然《蜃中楼》中两位女主角的性格与遭遇有所差异,但她们都摆脱了报恩母题限制下的被动地位,成为真正能够拥有爱情并有勇气有能力追求爱情、守护爱情的女子。她们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婚姻自主的追求与抗争父权的勇气是前所未有、令人钦佩的,这也是《蜃中楼》思想价值和时代进步性的最大体现。
与其他改写《柳毅传》的作品不同,《织成》是清代作家蒲松龄依据《柳毅传》续写而成的短篇文言小说,这让整篇小说在沿用母本的叙事框架和人物形象之外,获得了更大的自主创作权。与李渔一样,善写志怪爱情故事的蒲松龄也选择放弃母本故事中的报恩情节,将“爱情”作为小说的叙事重点。小说讲述了柳生在落榜返乡的路上路过洞庭湖,醉酒之后偶遇龙宫的婢女织成并对织成一见钟情,几经波折终于在一起的浪漫爱情故事。
“女性主人公身份地位的改变是《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的最大区别之一”[11]。在蒲松龄笔下,织成只是一位小小的龙宫侍女,而不是尊贵的龙族公主。没有了贵族身份的限制,龙女在蒲松龄笔下成为一位举止活泼跳脱、爱笑爱闹的青春少女,哪怕奉命下凡寻找柳生也要捉弄他一番:“生见翠袜紫履,与舟中侍儿妆饰,更无少别。心异之,徘徊凝注。女笑曰:‘眈眈注目,生平所未见耶?’生益俯窥之,则袜后齿痕宛然,惊曰:‘卿织成耶?’女掩口微哂。”[12]织成身份的转变使龙女的形象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她没有了贵族身份的光环,也不必再背负诸多责任。作者没有过多描写她品质的宝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使得织成与传统龙女形象产生了背离。从《柳毅传》开始,各个朝代中的重写作品中,龙女都以美丽善良、重情重义的龙族公主面貌出现。龙女精神与地位上的双重高贵使得它不仅仅是士大夫阶级眼中完美妇女形象的化身,更是女性道德楷模的标杆,织成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龙女的刻板化描写。虽然美丽天真的织成依旧是能够寄托作者对完美妇女想象的符号化人物,但落第书生蒲松龄显然不想对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做更多的道德规范和身份幻想,这一变化使得龙女形象在平民化与世俗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总之,关于《柳毅传》的二次创作发展至清朝,主题与情节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龙女的形象也随之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蒲松龄与李渔笔下的龙女虽然性格特点与社会地位不尽相同,但在人物塑造层面还是有许多相通之处。《蜃中楼》和《织成》中的龙女都拥有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龙女不再继续作为小说重写过程中的一个文化符号存在,而是一个具备特殊性和独立性的角色。故事主题的转变则使龙女与柳毅之间的情感纠葛不再依附“受恩—报恩”这条主要线索进行,而是相对纯粹的互相吸引,倾慕对方的才华或者美貌。虽然小说中的人物被赋予爱情不一定能代表她们的形象会更加丰满,但单从《柳毅传》小说文本重写的角度出发,对报恩母题的突破与新变确实能使龙女在小说叙事中得到更多的主动权。
结语
柳毅故事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之一,也是学界关注的一大焦点。柳毅故事数量众多、内容多彩丰富,其文本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柳毅故事从开始形成到发展成熟,再到继承传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龙女的形象也随着柳毅故事的不断重写逐渐丰富完善。
从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版本来看,龙女形象的变迁主要遵循以下几条规律:一是不同作者对作品主题的不同选择影响着龙女形象的呈现。佛经中的“龙女报恩”故事虽然是作者创作《柳毅传》的主要灵感来源,但在漫长的嬗变过程中,除了《橘浦记》选择重新回归“报恩”母题之外,“爱情”“婚恋”等主题在其他作品中被不断强调,故事原本的传教特色与说教性质则不断被削弱。龙女在作品中的位置逐渐从被动的“报恩者”向主动的“追爱者”过渡。二是龙女形象的变化与创作背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龙女形象和遭遇的几次变迁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催生出的对“异物”、对“寡妇”和对“贞洁”的不同态度。三是小说、戏曲的普及和创作者、受众群体的变化使龙女的性格特点和社会地位越来越接近普通人,龙女形象在文本嬗变过程中逐渐平民化与世俗化。四是在不断重写的过程中,龙女的人物弧光逐渐丰满,人格逐渐独立,性格逐渐鲜明。虽然在明传奇中龙女一角的塑造有呆板僵硬的趋向,但大体来看,挣脱“报恩者”身份的龙女不再作为一个衬托男主人公的工具性角色而生,而是逐步拥有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自主选择权。这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人物形象技巧的不断成熟,也从一个侧面让读者们看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角色能够在作者笔下呈现出更加复杂、完满的人物特质。
《柳毅传》重写过程中“报恩”母题书写的不断丰富与突破是本文研究的另一大重点。总体而言,不同时期作者对“报恩”母题书写的不同选择受到时代思想浪潮的影响,并反作用于龙女形象的塑造。《柳毅传》是一篇集“报恩”与“婚恋”主题为一体的小说,在文本不断世俗化的过程中,除了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橘浦记》强化“报恩”主题教化世人,其他作品都选择了高扬爱情与人文的旗帜,努力挣脱“报恩”母题的限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清代的《蜃中楼》与《聊斋志异》完全摒弃了故事母本中的报恩情节,将《柳毅传》敷演成了一出纯粹的爱情故事。《柳毅传》重写过程中主题思想由“报恩”至“婚恋”的转变也进一步证明了小说文本思想层面的平民化与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