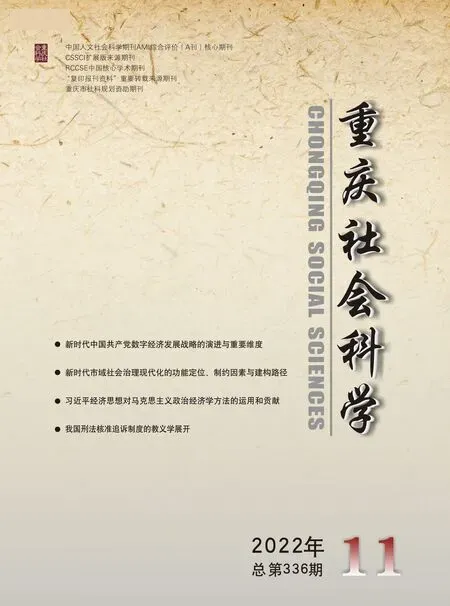农民工民俗“反哺”行为与乡土文化认同分析
——基于四川BM 镇调查为例
谭富强 王竹君 陈 希
(1.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深圳 518060; 2.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澳门氹仔 999078)
一、问题的提出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28 560 万人,比上年减少517 万人,下降1.8%,规模为上年的98.2%。 其中,外出农民工16 959 万人,比上年减少466 万人,下降2.7%;本地农民工11 601 万人,比上年减少51 万人,下降0.4%。 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 101 万人,比上年减少399 万人,下降3.0%[1]。 随着农民工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大,研究者们加大了对这一群体关注的力度。
社会文化认同对农民工研究来说一直甚为重要, 其内涵十分广泛。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社会认同是在相关文化特质基础上的建构过程,是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社会群体并实现自我归类的过程,是对周围群体和环境的态度[2]。 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城乡双重外推力作用下,身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没有真正的归属感,越来越被“双重边缘化”[3]。 一方面,他们面临在城市定居不下来、乡村又难以回去的状况,这种状况将逐渐让农民工群体在自身的社会定位上产生怀疑,导致定位模糊,出现“认同模糊化”等困境[4]。 这种“认同模糊化”导致该群体处于受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双重制约的中间状态[5]。 他们对自身社会认同的丧失会使该群体对城市和农村都产生一定的隔离和抵触情绪,从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6]。 另一方面,他们积极认同家乡的民俗活动,向往着回到家乡去享受民俗生活。 王剑论述了民俗节日对人们群体归属感的整合问题[7]。民俗文化具有独特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8]。出自乡村的农民工虽然自身定位模糊,但对家乡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民俗活动却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显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家乡的民俗活动。 这使得通过民俗探讨农民工身份整合成为可能。
在我国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当下, 农民工的乡土文化认同与社会自身定位正在随着社会转型而进行着调整。 当前我国发展实际是城市较之于农村的发展在物质与生存上存在差异。 很多农民工需要离开家乡到城市里工作且持续时间较长,因为来自乡土社会,长期外出工作的农民工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对乡村文化和习俗的想念, 时刻激励着他们回乡去享受民俗生活,并激发他们传承自己家乡民俗、积极宣传地方文化的想法。 这使得回乡享受传统民俗的农民工对民俗传承与发展的“反哺”行为也就随之展开。
二、文献综述
自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被学者们广泛关注以来,民俗文化为乡村治理、乡村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依然被深入挖掘,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将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介入到乡村发展的过程中达到从文化-行动的角度解释乡村振兴发展行为逻辑的目的已经具有了可能性。 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农民工反哺等方面。
关于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的研究表明,民俗文化属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之一。景婧和韩鹏杰的研究表明, 民俗文化可以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资源并对乡村文化振兴作出相应的共享,他们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民俗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承担推动乡村文化空间发展以及提升民众自信等多重社会意义,因此作者们强调充分关注到民俗文化的发展语境及其本来样态,并认为关注民俗文化与乡村民众心理之间的互动关联能够更好地推动地方民俗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的协同[9]。 这一研究表明,民俗文化内嵌于乡村振兴之中,并且承担了文化资源供给的重要角色。 赵艳的研究也表明,民俗文化作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是当下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之一,一直发挥着凝聚民心、教化民众的作用,并且在推动乡村和谐发展等方面也具有一定意义[10]。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乡村振兴资源,它本身就包含了乡村生态、乡村生活、民间信仰等多种形态,因此,民俗文化在嵌入乡村振兴发展后,它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 萧放认为,民俗文化主力乡村振兴需要遵从“民俗文化本质性”,即需要尊重民俗文化的本真性,不能过于简单地将其他文化直接与民俗文化进行融合,导致在乡村振兴中使得民俗文化失去了原有的人文生态环境[11]。 显然在乡村振兴视角下,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乡村振兴的资源它的应用既要遵循一定的文化生态原则,也要积极参与到乡村的振兴发展之中。
关于乡村振兴中的民俗文化发展模式研究。在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发挥了怎样的价值以及民俗文化该何去何从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重点问题。 桂胜和陈山的研究指出,在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提供处理人文关系以及民俗空间再造的价值, 并且通过民俗空间再造的路径,民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已经逐步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发展模式[12]。 陶维兵提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家关注的重点,对于民俗文化的合理利用需要建构起民俗文化传承创新模式,如通过对民俗文化变迁以及民俗文化带动乡村振兴等路径的探究,为今后民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模式化以供参考[13]。 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这为民俗文化建构乡村文化振兴模式提供了契机。 段友文的研究给出了一些启示,民间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典型的文化驱动价值,通过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化)进行谱系建构,能够找出在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的发展新模式[14]。
关于农民工“反哺”的研究表明,“反哺”是建立在乡土认同上的对家乡或家庭的帮助与支持。 王培刚的研究指出,进城民工的科学知识和现代观念、休闲娱乐倾向等文化因素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原有家庭的“文化反哺”[15]。 季中扬发现农民工虽然进了城,生活的空间转换了,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基于乡土的关系网络和组合方式却一直在延续着,形成了诸如“浙江村”“河南村”等生活社区或生产与经营的集聚地,他们甚至比留守乡村的农民更为执着地保持着某些文化习俗,坚守着乡土文化的精神信仰[16]。这种乡土文化的延伸状态显示了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和适应性。由此观之,“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并没有摧毁以往的乡土传统,没有把农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连根拔走。 事实上,乡村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延续着,乡土文化在不断转换形式的过程中也在发明着传统[17]。
三、研究结果
本文以四川省中部地区的BM 镇为研究对象。 该镇地理位置特殊,距离市中心城区30 多公里,距离区政府30 多公里,属于亚热带湿润性气候,耕地面积达36 468 亩,辖区面积76 平方公里,共有28 个行政村,一个社区居委会。 该镇人口43 555 人,外出务工人员达81.2%。 该镇保留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民俗活动——PL 寺庙会,这使该镇成为西南地区民俗文化活动的一个缩影。 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X 镇,正在经历着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现代生活与传统民俗生活的相互融合、调整、变化,对其进行研究可作为当下民俗“反哺”的一个典型参照。 本文采用田野调查的深度访谈法,访谈对象包括10 名在外务工青年、10 名务工中年人所在的家庭成员及其本人,另外访谈村民若干,为了符合社会学调查研究的规范要求,本研究将村名和人名进行了匿名处理。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优化、人口流动较频繁的社会结构化转型时期。 我国政府也积极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号召,并随后出台了一系列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BM 镇是“出门工作为主,种地养猪为辅”的劳动生产模式,由于在乡村参与农业劳作很难赚到钱,很多乡村劳动力外流现象严重,形成典型的“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孤守阵地这一现象,农户经济来源也大部分靠家里中青年的外出务工收入而来。 通过访谈发现,BM 镇外出的农民工大都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收入较为可观。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家乡的民俗活动,这使BM 小镇中本应呈现整体衰败的各项民俗因大量外出农民工的“反哺”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可以说,他们的“反哺”行为推动了乡村民俗活动的发展。
(一)经济反哺现象
BM 镇自然环境较为恶劣、道路蜿蜒曲折、交通不便、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2010年后政府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将公共用地出租等一系列方式整合资源,最终将该村建设为交通便利、贸易兴盛之地。 政府采取与民间合资的办法修路,使得许多人家的门口有了水泥路。 从政府权责方面来看,修路属于基础性公共设施,是当地政府的职责与义务。 但是由于民间民俗活动的保留与传承——PL 寺庙会的兴盛不衰,很多农民工在外出务工前都会去许愿,之后,经多年努力,衣锦还乡时,就要前去还愿,在还愿的行为中自愿性的捐款行为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由于道路不便,许多经济较为宽裕的乡民(包括外出农民工)开始筹钱建路,并形成一个管理委员会与政府协商,最终修通了镇中心前往PL 寺的道路。 据调查,这些资金约有八成来自所属地人民的筹集,还有些乡民捐献了自己的土地、山头、田地等。 捐助的所属地人民有当地留守村民、外出农民工和一些私企老板。 该镇的农民工“经济反哺”作用于庙会,在修通了道路的同时也起到稳定当地社会心理的作用。 对公益事业包括PL 寺的捐献, 外出农民工大都愿意,当然,多少由人家的心意。 正如受访者王建国说:“修桥补路,都是我们最喜欢的,为后代图方便。 以后去PL 寺也方便。 ”①王建国,男,65 岁,普通村民。
(二)族群、民俗圈的反哺与整合
BM 镇有个较大的宗族祠堂,即蔡氏祠堂。 该区域主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全镇人口20%都是蔡姓族人,宗族意识影响较大。 对于蔡氏乡民而言,自小耳濡目染宗族文化,他们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他们团结、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该镇一直被传为佳话。至今,虽外出农民工多,但他们对宗族的归属感很强烈,尤其表现在修缮宗族祠堂和提供资金支持本族小孩上学方面。 农民工外出务工一般是亲戚带亲戚,访谈显示,大约70%的蔡氏族人都在深圳一带务工。许多族人聚集在某一城市甚至同一工厂劳作,他们形成了鲜明的族群互助链:年龄稍大的农民工在回乡过节或是回乡举行宗族祠堂修缮仪式后都会带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出去。这样的互助链可以解决族人生存、亲属就业的困难。 而每过几年宗族就会举行较大型的宗族事务,如修谱、修祠堂、建庙、劝学、助学等,很多外出农民工都会回来投身其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蔡氏族人对本族公共事业及未来人才的培养都十分尽心,正如今年春节回来的刘巧说:“我们老一辈出去再怎么苦都无所谓,只要能把宗族发扬光大,能把那些晚辈送去读书就对了。 ”①LQ,女,52 岁,进城务工人员。
该镇较边远的其他区域还有一些以业缘为基础的民俗活动圈。 A 村的张师傅是远近闻名的艺人,他会雕刻菩萨、给菩萨“穿金”②穿金,当地方言,系为新塑菩萨开光。等一系列礼佛仪式,以他为主形成了一个民俗文化圈[18]。张师傅的技艺在过去带有一定迷信色彩, 现在政府大力提倡以民俗文化为特色的旅游活动,不但摘掉了“迷信”的帽子,还将他特聘为PL 寺的旅游顾问。 在一些重大的日子里,张师傅会率领众弟子在该寺进行民俗活动表演。 全镇有什么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也都会请张师傅前去。 现在甚至有很多没能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前去向他拜师学艺。
(三)构建乡土记忆的“文化反哺”与民俗整合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反哺”就是“反向社会化”,正向社会化和反向社会化作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互补的两种基本模式,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方式[19],这种后喻文化现象在出门在外的农民工中尤为突出[20]。 在BM 镇,外出农民工是该镇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大多完成了高中教育。 他们对该镇的文化反哺体现在:认为参与民俗活动应该有更多元且更现代化的因素。 以婚姻习俗和交通习俗为例。 在婚姻习俗上,他们力求与外界的习俗相同,不在家中置办酒席而去镇上酒店办。 而因有在外的经历,更多时候,他们极力劝说家人取消对自己的相亲习俗,力求恋爱自由。在交通习俗上,以前大家都是过着“通信靠吼,交通靠走”的落后生活,现在年轻人开始教老年人使用现代通讯及交通工具,如手机、摩托车甚至小轿车等。随着外出农民工的社会文化反哺,不知不觉间已经在重构着他们对乡土的记忆。 当然,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域长期形成的文化现象,其表达方式以及表达内容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1]。 对老一辈而言,他们的民俗观念是很难改变的。 受访者蒋涛就说:“有些老年人嘛,去PL 寺非要走路,说的是走过去才诚心,我们年轻一点的都是直接坐车过去。 有时候没得办法,他们一个人走又让人担心得很,还不是要陪着一路走。 ”③JX,男,24 岁,市区理发店老板。可见,尽管有了较为发达的物质基础,但在老一辈的心中,对于一些民俗活动的参与方式仍然是难以改变的。
(四)经济反哺背后的“深描”
农民工虽常年生活在外地,但对家乡的民俗活动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积极推动宗族或民俗活动走向繁荣。 这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致使他们这样做? 这么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他们在外地与家乡之间常年来回穿梭, 其意义何在? 要想了解他们作为家乡民俗文化活动参与者的深层原因, 一方面对其从小的生长环境与所受的民俗文化熏陶要有精确的把握, 另一方面也要明白这与农民工在城市里艰辛劳作却被城市所排斥的现状有关。
对农民工经济反哺的背后进行深入思考,可以总结出一定的经济理性规则。有受访者对于他们的经济性反哺是这样认为的:“修了路,好走嘛。 我们自己的娃娃也要走这边去读书,落雨天老年人要去赶庙会走泥巴路确实很危险。我们捐钱一起弄一下,大家都走的心安理得。 ”①CCS,35 岁,农民。另一受访者李某说:“很多人对庙子(指PL 寺)的菩萨许愿了,好多都想娃娃读得书,自己挣得到钱,所以一说修路大家都愿意去。也有些人没出钱,他们不信这个,不过只有个别的人。”②TJM,65 岁,农民。也有受访者说:“有些大老板自己信佛,给很多钱,图个面子。 ”③TJF,62 岁,村主任,高中学历。可见,乡民愿意去修到寺庙的路还是经过理性思考的。首先,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到修路确实能方便自己或家人。 其次,个别人是出于证明自己能力的角度,捐款时冲着“面子”去的。 费孝通在“差序格局”下对农民“自我定义”行动逻辑有较为准确的定位,乡民会拿自己的经济付出与各方面收获来进行对比[22]。 也有乡民在外挣了大钱, 会通过捐大钱的方式来获得别人的夸奖与羡慕。 这种把自身经济优势转换为当地威信优势的做法在大部分乡民中都有一定的体现。 这是一种社会支持的增益渠道,不仅满足了大部分乡民渴望得到认可的心理,同时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五)族群、民俗圈背后的“深描”
社会网络实际上是一些支持性的社会关系的集合,它通过持续的社会交往而形成,并对网络的拥有者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23]。 族群、民俗圈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小型社会网络,乡民们在这个社会网络里生活。 该社会网络的价值取向是影响乡民行为的重要因素。 如受访者蔡祎林说:“我姓蔡,我屋头好几代人围绕着宗祠生活。 翻新宗祠啊,给蔡氏子孙捐款让他们去更好的地方读书我肯定是愿意的,虽然我在外头打工,但是我的根在这里,老了干不动了还是要回来的,大家都对宗族出力,以后肯定可以享福。 ”④CWL,男,57 岁,进城务工人员。另一受访者也说:“只有对宗族有作用了,出了力或者出了钱,大家才会对我们个人认可,不然哪个得理你? ”⑤CCQ,男,49 岁,饭馆老板。一位正在学艺的受访者说:“跟着张师傅学个手艺嘛,以后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能养活自己撒。 ”⑥CCL,男,21 岁,张得政手艺传人。在访谈中发现,“蔡氏”“族人”“一个姓的”“传统”“立足社会” 等词汇反映了这一群体社会受社会网络的价值影响很深。 这些受访者通过参与到宗族或民俗活动的方方面面, 不仅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也获得了社会网络对其价值的肯定。
对于自己宗族或是民俗文化圈的认同也影响着乡民对其自身价值的认知与评判。 尽管有些乡民以经济理性规则或是人们常说的“仗义”为出发点,但是这些都成为乡民被民俗“整合”的表现。
(六)城市工作背后的“深描”
分析农民工在工作地的生活,将更有利于我们了解他们通过民俗“反哺”行为来加强对乡土的认同这一事实。 一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与福利待遇较之农村明显优厚,这也成为许多农民工进城务工谋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城市务工收入比农村高出许多,又可享受到乡村无法享受到的各种便利,这使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十分向往。 一位受访者说:“那些大城市确实很发达,马路都要宽几倍,在那边上班嘛虽然工作累点,但是确实比务农收入要高得多。”①TYS,男,59 岁,城市清洁工。另一方面,城市的高速运转又让每个参与城市生活的人都有不堪重负感觉,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方式让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在闲暇之际更加想念家乡的乡土生活。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这也刺激了在外务工人员对家乡归属感的不断增强。 其实,在生活水平方面,由于进城务工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许多民工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自己的消费进行压缩和节制。 受访者ZX 就说:“在城市里头,那些工厂里,每天要干12 个小时才有钱。不然,就靠平时那点上班时间的工资,一个月都不够花。有时为了节约点钱,经常吃厂里头的食堂,没有油水,吃了老是吐清口水。 ”②CF,女,48 岁,工厂打工。
就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城市的社会支持明显弱于家乡的社会支持。 在城市里,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仅仅来自同伴之间,或是某些公益组织。 然而,在家乡,能得到的社会支持包括自己亲戚朋友的支持、对本地的归属感、熟人社会的相互认可和认同等,同时随着政府对乡村建设投入的加大,来自家乡政府的社会支持明显要高于在城市中所获得的。
(七)来自乡土记忆的“深描”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奈认为,乡土记忆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在BM 镇这样一个特定的民俗文化圈里,他们有着对PL 寺庙会的共同记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群体记忆会被不同程度地激活,从而影响乡民的行为与心理。 关于PL 寺庙会的记忆主要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上。 陈建宪认为,节日是时间与空间的元点重合。庙会给参与的乡民带来关于庙会时间空间的集体记忆。 调查显示,乡民在这个社会激荡转型的年代里,对于许多事情的记忆都呈现多元化,但是对于PL 寺庙会这个典型的集体参与事件大家都不会陌生。 通过大家对庙会的共同记忆,逐渐形成一套有着固定文本的说辞,并在乡民内部不断流转,让外出务工这个特殊的乡民群体对家乡民俗活动的兴趣不断高涨。 其实,乡民保持对庙会的记忆就是在坚守自身的身份认同。 在这里民俗活动展现出强大的凝聚整合力,与外出务工者对家人及家乡的思念融为一体,并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乡土的认同及对未来的规划。
总之,在对四川中部地区BM 镇外出务工者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第一,外出务工者在城市的生存压力大,活动空间窄,得到的社会支持小,他们的人际交往、社会归属、自我认同、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都受到很大的阻碍,需求的多元性得不到满足;第二,外出务工者在城市务工期间,他们像是凭空嵌入城市的社会网络中一样,其社交网络嵌入之时是多大拔出之时还多大,身在城市,接触的还是原来乡村的社交圈——只是这个社交圈凭空搬移到城市而已,根本融不进城市本身的社交网络,这不利于他们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社会互动;第三,外出务工者的民俗“反哺”行为在对家乡民俗活动的深刻记忆表象下掩盖的内在逻辑实则是冷漠的城市社会所感受不到的乡土熟人社会中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其乐融融的归属感。
(八)农民工乡土文化认同机制分析
在农民工研究领域中,文化因素一直备受重视,文化认同被视为影响农民工行为的关键指标[24]。 本研究通过对案例点的调查研究发现,案例点地区的农民工“反哺”行为主要遵循了经济因素、群体阶层因素、文化记忆因素。 分析认为,经济因素作为农民工“反哺”行为的重要支撑点,从经济到文化已经成为一定的稳定路径,其原理在于通过经济支撑来完成文化认同。 关于农民工乡土文化认同机制的分析具体如下:
首先,以经济回馈为支撑的乡土文化认同机制。经济因素作为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有力支撑了农民工经济“反哺”的行为。 家乡的民俗活动一方面需要农民工本人及家人亲自参与,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捐款捐物等行为)。 这说明,农民工的乡土文化认同的基础在于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其次,城市压力背景下对记忆中民俗文化的眷恋而产生的乡土文化认同机制。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是一种在城市压力背景下的产物,这说明在城市就业谋生的压力会刺激到农民工对于故乡中的文化集体行动的回忆。 因而,通过对大型民俗活动的回忆,能够缓解农民工的情绪压力以及生活压力,并能够再次增强农民工对于乡土文化的认同。
最后,以情感供给为主的民俗文化有效刺激外出农民工的乡土文化认同。农民工外出务工,在空间上和心理上与家乡都有一定程度的远离,在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上的迁移会产生一定的情感刺激,而这种刺激需要一种载体,伴随农民工从小到大的民俗活动就成为这种载体。当家乡的民俗活动开始时,他们对于家乡的情感需求被进一步刺激,而这种刺激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对乡土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同感。
四、讨论与结语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以乡土认同为基础的民俗“反哺”现象不仅是乡民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体现,也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 农民工在外务工时会选择优厚的物质条件,而回到家乡则更多的是被民俗所“整合”,重新找回自我,实现人生的意义。 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乡民向往设施条件优越的城市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与城市的疏离使得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与日俱增。 当他们撤离城市回到乡土社会后,实现生命意义的使命会让他们很快融入当地民俗活动中,不知不觉中,民俗完成了其使命。 辩证地看,选择去大城市务工与乡民自身的乡土文化认同并不矛盾,乡民带着民俗情怀出去打拼,在艰苦的奋斗后对乡土文化进行“反哺”,从而实现民俗对乡民的整合,在此民俗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合理利用民俗文化的各项功能,在应对现代化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