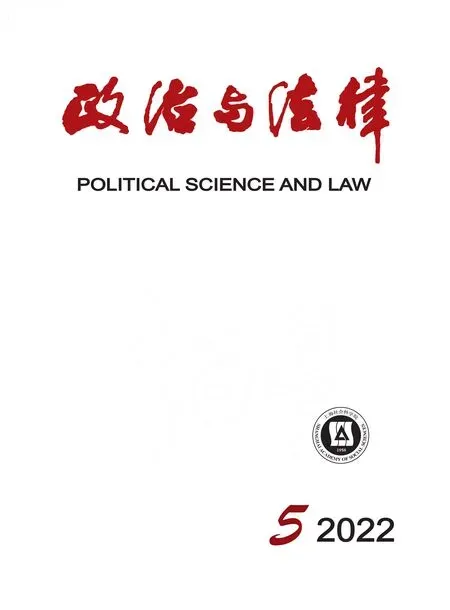“准合同”概念之外延考*
——对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李永军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我国《民法典》合同编的第三分编规定了“准合同”,但是,我国《民法典》制定前我国的学理和立法却一直不使用这一概念,甚至法国在2016 年的债法改革中,废除法国民法典上的这一概念的呼声非常强烈。结果,其尽管没有被完全废除,但被弱化了〔1〕参见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债之渊源(准合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版,第60-65 页。。如果仔细看看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之第三分编规定的“准合同”的基本内容,将其与合同联系起来确实有些困难——一个与合意或者意思表示完全无关的债的发生原因,为什么规定在合同编?难道也适用合同规则?因此,关于这一概念及其内涵外延有下列问题需要认真考察:第一,“准合同”的最初设计目的及内容是什么?其与合同真的有关系吗?历史法学派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梅因就曾经批评英国的许多学者不懂得“准契约”的概念而将其解释为契约。按照梅因的观点,“准契约”完全不是契约,“准”字放在罗马法的一个名词之前,是用来作为标志概念的概念之间的差别,在比较上仅仅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表面类比或者相似之功用。但实际上,它否定了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同一性的观念。〔2〕参见[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193-194 页。那么,准契约与契约的相似之处是什么?是否就是当事人的意思?第二,“准合同”的外延难道就是指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吗?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内容?第三,不当得利在自罗马法至德国民法典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是作为债的发生原因存在还是作为救济手段存在?它是如何表现出来的?第四,如何从体系上解释我国《民法典》第985条对不当得利的定义?如果按照该条的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为不当得利的话,所有的返还请求权都可以归属于不当得利。例如,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第235 条规定的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抵押权或者质权标的物的返还请求权等统统可以纳入不当得利。如此一来,民法典救济规则的体系性将荡然无存。那么,如何界定我国《民法典》上的不当得利?第五,2016 年的法国民法典第1303-3 条为什么要区分非债清偿和不当得利?德国民法典和学理为什么要区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其区分与民法体系有什么关联?我国《民法典》第157 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的返还”如何定性?第六,不当得利之救济与其他救济措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国《民法典》是否可以被解释出如同法国民法典第1303-3 条那样的排斥关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曾经在《中国法学》2020 年第6 期发表了《论我国民法典中无因管理的规范空间》,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主要考察不当得利。
二、关于“准合同”的历史考察
(一)“准合同”的制度史
尽管学者指出,“准合同是发源于罗马法的概念”,本来是指非因合同和侵权引起对的债〔3〕[日]加藤雅信:《作为立法论的“准合同”论——对中国民法典草案的三种修正提议》,吴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年第2 期。,但从罗马法的源头看,“准合同”一开始并不包括不当得利。对此,意大利法学家彼得罗指出,“当罗马人说债产生于准契约时,他们指的正是无因管理”〔4〕[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396 页。。我国有学者通过考证罗马法文献后指出:“就古代罗马法而论,直到罗马法的古典时期,就其债法所论而言,主要涉及的是契约与侵权,而不当得利没有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与契约以及侵权作为同等的私法范畴存在并作相应的编排与处理。”〔5〕苏彦新:《论格劳秀斯的不当得利学说与规则》,载《比较法研究》2016 年第6 期。罗马法上 “债要么源于契约要么源于私犯” 的这一观念对于后世大陆法系各国的债法影响很大,以致于缔约作为债的渊源长期被忽略。无因管理之所以被承认,应该说得益于其与契约的相似。无因管理起源于委托——未受委托而为他人管理实务的行为。因此,无因管理与委托往往“出现在一起”。从罗马法债法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委托与无因管理的关系。德国学者指出,委托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为他人利益而从事工作的诸多道德义务,这些义务是罗马社会加之于个人的。与此相应,基于委托而负担的义务是以“信义”为基础的,并且传统上认为不能通过合同约定以有偿为条件。“人们坚持认为无偿接受帮助是委托的特征。”〔6〕[德]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488 页。无因管理的名称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处理(他人)事务,在前古典法和古典法中包括了非基于特别法律关系——尤其是委托和监护(tutela),而实施的所有事务处理。无因管理(neg.gestio)是由[诉讼代理 人(cognitor)或者代理人(procutator)] 的诉讼代理发展而来的。它还包括:(1)由法律规定或者长官指定的保佐人(curator)与其被保佐人的关系;(2)代理人(procurator)与本人的关系。代理人是一种财产管理人,正如罗马富人通常认为的那样,并且,在古代常常是指自己释放的自由人,而这些释放自由人最初被认为是直接处于庇主权力之下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依附性松弛了,代理人也取得了人身独立,这样在他与本人之间就能够存在可以相互起诉的请求权了。代理人仍然是[通过命令(iubere)] 由单方指定的,所以,人们最初就将这种关系归入无因管理,后来才将以合同指定代理人归入了委托。自共和晚期起才有的独立代理人,则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自始就被认为是受托人。委托的内容根据协议确定,它可以包括个人全部财产事务(概括委托),也可以对它进行限制解释而使其只涉及当前事务,所以也可以存在特别委托。同时,代理人为实施个别事务而设定[所谓个别代理人(Proc,unius rei)],尤其是为了进行诉讼(所谓“诉讼代理人”)。代理人的无因管理之诉(actio negotiorum gestorum)进而限制在(未受委托)自愿为他人服务。自共和早期起,纯粹由于助人为乐而为他人服务者越来越多的情形被认为是对他人的无因管理,而这种现象背后是罗马社会制度中强大的道德义务。管理人的义务,与委托所产生的义务一样,是以信义(fides)为基础的。优士丁尼依照更古老的范本将无因管理解释为准合同(Inst.3,27,1)。对于保佐人和表见监护人(protutor)等情形,他则使它们从无因管理中独立出来〔7〕[德]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494 页。。
无因管理与委托合同的这种天然的历史渊源和逻辑结构,对于后世影响很大。像德国民法典这样抛弃“准合同”概念的模式,也是按照罗马人的传统思维和逻辑,将无因管理规定在委托合同之后。〔8〕《德国民法典》第三编第八章第12 节(第662 条至第676 条)为委托合同的规定,而第13 节(第677 条至第687 条)为无因管理的规定。
在罗马法上,在主人或者被经管人不知的情况下,经管他人事务,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无因管理”。这种事实的“债因”或者客观关系同委托很相似。罗马人说“债产生于准合同”时,他们指的恰恰是无因管理而不包括不当得利,因为它完全缺乏合同协议〔9〕参见[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396 页。。因此,可以说,真正的准契约实际上指的就是无因管理。从罗马法直到法国民法典,“准契约”一直不包括“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实际上一直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以“诉”的方式而非以“债的发生原因” 的方式存在。当代德国著名法学家Reinhard Zimmermann 指出,在盖尤斯的另一著作中,我们找到了一种答案:它没有出现在契约与侵权的清晰有序的总区分中,而是包括在其他的各种债中,他把不当得利作为第三类的债来对待。总体而言,早期罗马法的发展是通过诉讼(actio)方式与方法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罗马法中,诉讼与权利的特殊关系特别表现在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的相互对应上——罗马法中的每一种权利或法律关系都有着自己相应的诉讼形式作为保护措施和救济手段,甚至,人们经常以是否存在相应的诉权来判定是否赔偿了特定的权利所受的侵害。因此,早期罗马法并没有现代私法体系中债法体系框架下对不当得利的这种法律构造。〔10〕苏彦新:《论格劳秀斯的不当得利学说与规则》,载《比较法研究》2016 年第6 期。
至于不当得利,尽管我国《民法典》与2016 年后的法国民法典将其植入“准合同”,但与无因管理比较起来,就显得不那么“正宗”。按照罗马法,建立在不正当的原因或者法律关系基础上的财产增加称为不当得利。这种情况一般因为取得的近原因偶然与一个在法律上不存在或者无效的远原因相结合而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物权或者债权的取得得到承认,“但是,人们允许受损害者为从另一方获得对财产增加部分的返还而提起诉讼”〔11〕[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398 页。。不过,罗马法上并不存在独立的作为债的发生原因的不当得利,仅仅是存在一些与现代的不当得利制度功能相似的制度,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请求返还之诉和转化物之诉〔12〕参见傅广宇:《转化物之诉与不当得利——罗马法渊源及其变迁》,载《清华法学》2015 年第1 期。。
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不当得利作为债的发生原因。在“准契约”中,其仅仅规定了无因管理和非债清偿(第1371 条至第1381 条),直到2016 年债法改革后,法国民法典才于第1301条至第1303 条把不当得利明确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但是,法国的学理和判例却确认了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则。真正从学理上明确承认法国法中的不当得利规则是法国19 世纪后期的著名法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阿尔贝(Aubry)和劳(Ran)。受到德国法学家、海德堡大学Karl Salamon Zachariae的影响,他在1871 年的《法国民法教程》中,明确将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从无因管理之诉中分离出来。1892 年,法国最高法院在Boudier 案中,不再通过扩大无因管理的适用范围来救济不当得利之受损人,而是借用罗马法中的转化物之诉的概念,在衡平的基础上创设了一般的不当得利(enrichissement sans cause)规则,赋予原告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诉权(action de in rem verso,与罗马法中的转化物之诉用语相同,但此处之含义要远宽于罗马法中只适用于针对父亲或主人的转化物之诉,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之诉)。将不当得利作为与无因管理并列的独立诉权,亦将作为民法典明文规定之外的独立诉权。从此,无因管理有了其严格的适用范围,Boudier 案的判决亦成为法国私法史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里程碑。〔13〕参见刘言浩:《法国不当得利法的历史与变革》,载《东方法学》2011 年第4 期。
根据学者的考察,对“准合同”的理解,在法国民法典制定前本有两派观点。一派以波蒂埃(Pothier)为代表,认为“准合同”是一种类似合同,无因管理类似准委托合同,非债清偿类似准借贷合同。另一派观点“以庞波尼乌斯(Pomponius)为代表,认为所谓‘准合同’实质是一种利益不当变动的恢复机制,其基础为‘任何人不得在没有权利的情况下损害他人而使自己获利’的原则”〔14〕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准合同规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6 年第6 期。。“因奉行意思主义,1804 年《法国民法典》仅采纳了波蒂埃的理论,其第1371 条对‘准合同’的界定与不正当利益返还的理念毫无瓜葛。于是,相关债务来源于‘类似合同’的界定掩盖了其类型的共性(乃是对利益不当变动的恢复机制)。”〔15〕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准合同规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6 年第6 期。因此,法国主流学者就认为,准契约(le quasi-contrat)可以被定义为一项行为人自愿实施的合法事实行为,基于该事实行为对于行为人或者第三人产生债之关系。该法律思想表明了准契约与契约存在着相似性:一方面准契约与契约相同,行为人的意志(volonté)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由于其并非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合意(accord)的基础之上,从而又区别于契约。此外,准契约的核心要素在于其使他人受有一定之利益:该特征充分体现在非债清偿行为之中(le paiement de l’indu)。对他人事务管理(la gestion d’affaire)制度(即无因管理)的分析通常也在准契约的框架中进行。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准契约有两种,即非债清偿与事务管理〔16〕Jean Carbonnier.Droit civil,volume 2:Les biens Les obligations .Presses univerisitaires de France.Paris.1955.p.2419.。
时至今日,这两派观点仍引发着冲突。有一种观点非常直接地认为,法国民法典应当放弃“准合同”概念,设立独立的关于不当利益变动的恢复机制的法律规范。《泰雷债法草案》就根据这一观念,设计了所谓的“其他债之渊源”的规范单元来替代“准合同”这一概念,其第一章名为“从他人处获得不应得之利益”来专门规范“非债清偿”(第一节)与“不当得利”(第二节),第二章名为“无因管理”。另有观点认为,“类似合同”这种界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今天单纯的自由主义或国家干预经济均有所后退,越来越多的债务虽然来源于法律或者判例,但其制度与合同之债更为接近。最终,依《法令》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虽没有放弃“准合同”的概念,但有了较大的突破:第一,相关单元实际上仅规范了准合同的三种类型(无因管理、非债清偿和不当得利),却以“其他债之渊源”作为单元的标题;第二,虽也使用了“准合同”的表述,但特别突出了其对利益不当变动的恢复功能,从而缩小此概念的适用范围、弱化其地位。不论是否支持使用这一传统概念,法国各方对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均整体持肯定意见。其功能在社会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在社会连带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布尔茹瓦看来,准合同的概念比合同的概念更能建立和解释社会联系。他指出:“‘准合同’就是那些因某种必要性而彼此间建立起联系但先前又无法商讨协议条件的当事人‘对过去进行追认的合同’。他将有关‘社会连带’(solidarite)的理论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上,认为,个体之间的关联不仅是通过纯粹的合意为基础,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也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依赖性,而整体本身也依靠于内部彼此间的互通。债务以及社会联系,既可以来自于合意,也可以来源于利益的交换或变动。”〔17〕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准合同规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6 年第6 期。
英国法上也存在准合同制度,关于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英国也受到罗马法的深刻影响。但英国法上的准合同之内容与大陆法系不同,主要是指不当得利。有学者考察认为,在大陆法系,就调整“不当得利”问题的法域是从“法律事实”出发,称为不当得利法。在英国法中,类似于大陆法系的不当得利制度主要源于准合同,因此以纠正不当得利为目的的法在英国法早期被称之为准合同法〔18〕洪学军:《不当得利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年版,第27 页。。1999 年,Lord Steyn 在 Banque Financiere de la Cite v.Pare 案的判决词中写道:“不当得利是债法中仅次于合同与侵权以外的第三种独立的债的渊源。” 这一论断标志着英国法已经构建起以不当得利为原则的统一独立的返还请求权制度,取代了近代英国法中的准合同制度。究其原因,最主要是由于从根本上说,返还诉讼的基础不在于虚构的合同,而在于返还责任独立于合同与侵权的债的形式。从此,在英国法中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的作为重要诉因之一的准合同制度淡出了历史的舞台。随着返还请求权由单纯的救济方式发展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普通法的债法体系随之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更,债法构建于三大基本原则之上,即“有效承诺而生之期望应予实现”“不法侵害应予赔偿”“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这三大基本原则分别由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和返还法加以贯彻与体现〔19〕廖艳嫔:《英国准合同制度的演变之路——英美法系返还法的滥觞》,载《比较法研究》2014 年第5 期。。
真正将不当得利作为请求权基础,要归功于萨维尼为代表的潘德克顿学派,并在德国民法典中确立下来。也只有德国民法典,则完全抛弃了准合同的概念,按照自身法典的结构逻辑,将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单独规定,同合同与侵权一样,作为债的独立的发生渊源。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五卷中提炼出的不当得利一般事实构成,对19 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民法学影响很大,并因此影响了《德国民法典》有关规定的构造。“今天德国民法教义学上关于不当得利的一些争论,也可以归结为对萨维尼理论的不同理解。”〔20〕傅广宇:《萨维尼的不当得利理论及其渊源与影响》,载《中德私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8 卷,第51 页。虽然罗马法没有关于不当得利的一般理论,也没有将不当得利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但是,罗马法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原因理论”与实践。萨维尼的不当得利体系构建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将罗马法上的各种请求返还之诉置于同一标题即“基于原因的返还”之下处理。“萨维尼把给付(dare)看作各种请求返还之诉的基础,而给付就是某人的财产基于自由的意志而进入他人的财产。这种自由的意志也可以是因为错误而形成的,萨维尼还强调,给付最常见的情况固然是所有权的转移,但并不限于此,比如债权也可通过让与而移转。所以给付并不总是涉及所有权,而是涉及一般的财产权利。这样,萨维尼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各种请求返还之诉产生的两点共同要件:一是财产的移转;二是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即法律目的未实现。”〔21〕傅广宇:《萨维尼的不当得利理论及其渊源与影响》,载《中德私法研究》(第8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60-62 页。萨维尼的不当得利思想与其提出的“物权行为抽象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对抽象原则的承认,使得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成为必要。按照德恩伯格的名言,不当得利是为了治疗抽象原则自创之伤。德恩伯格这句话的广为流传,更多的是靠它表述的形象生动,而不在于内容的独创。萨维尼在《体系》中早已强调过请求返还之诉和物权行为抽象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22〕傅广宇:《萨维尼的不当得利理论及其渊源与影响》,载《中德私法研究》(第8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60-62 页。萨维尼提出了关于不当得利的一般构成理论之后,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不当得利”一词自从萨维尼开始才成为通用的法律术语。“萨维尼不当得利理论更为实质性的影响在于,在体系化过程中,它凸显了两条重要的法律原则,即法益保护和私法自治,奠定了给付型不当得利体系化的基调。一方面,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贯彻,使请求返还之诉取得了替代所有权之诉的功能,萨维尼也因此第一次表达了‘权利继续作用’(Rechtsfortwirkung)的思想。所有权虽然因无权行为而移转,但失利人的权利在不当得利法中仍然可以继续发生作用。另一方面,萨维尼将目的设定作为基于给付的请求返还之诉的重要因素,目的欠缺即意味着财产转移无法律原因。”〔23〕傅广宇:《萨维尼的不当得利理论及其渊源与影响》,载《中德私法研究》(第8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68-71 页。德国民法典无疑是采用了萨维尼的不当得利理论,甚至学者之间关于“区分说”与“统一说”的争论,也都源于对萨维尼理论的不同解读。现行德国民法典上已经完全没有“准合同”的概念,2016 年法国民法典中的无因管理被德国民法典规定在了“委托合同”之后(第677 条至第687 条);2016 年法国民法典中的“非债清偿”和“不当得利”被德国民法典纳入“不当得利”(第812 条至第822 条)。前者被德国学理和判例称为“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后者被称为“非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
我国没有关于“准合同”的法制史或者完整的理论,甚至很多民法或者债法的著作或者教科书都不提及这一概念,而是直接适用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因此,可以说,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做法大致是德国法模式。只是因为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由于我国《民法典》 没有“债法编”,也就没有债法总则,合同与侵权各自独立成编,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就没有了“立身之地”,于是,我国立法者把“准合同”这一概念从历史中“招”回,放在了合同编。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准合同与合同都没有任何关系——不能适用合同法的任何规则。
更为重要的是,从法国民法典的此次修改来看,法国法是有意淡化“准合同”的概念,甚至有人反对再继续适用这一概念。我国民法典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也反映出我国民法典在体系化方面存在自己的问题,更说明,没有了债法总则,或者说,不把“债的关系”作为合同、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的上位概念独立成编而与物权编相对,所带来的体系破坏和无奈。
(二)准合同的内容
如果抛开“准合同”的这种概念形式,仅仅从其所涵盖的内容上看,各国民法理论和立法也有较大差异——其差异就在于如何界定“不当得利”这一概念。以法国民法理论和学理为代表的一种模式为:准合同=无因管理+非债清偿+不当得利(狭义)。采取这种模式的还有意大利民法典、荷兰民法典。以德国民法理论和民法典为代表的模式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广义)。非债清偿作为不当得利的一种特殊类型。瑞士债务法实质上是采取了德国民法典的模式,将非债清偿作为不当得利(广义)的一种,只不过该法第63 条明确规定了“非债清偿”,而德国民法典第812 条、第814 条虽然涵盖了非债清偿,但没有明确列出来。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在于,首先,不当得利是否应当包括非债清偿?法国人为什么要采取“二元区分”?其次,“准合同”名下的这些种类共同特点(公因式)是什么?
2016 年修改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301 条至第1302-5 条、第1302 条至第1302-3 条、第1303 条至第1303-4 条分别规定了无因管理、非债清偿和不当得利,坚持非债清偿与不当得利的二元区分,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制度构建的需要。因为在法国民法理论上,非债清偿与无因管理在制度构建的层面上(即在构成要件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在法国法上,所谓的非债清偿,是指清偿了本不应给付的东西。就其所引起的法律效果看,从清偿人的相对人(受领人)的角度看,也被称为“非债返还”。“从返还的基础看,清偿系本不应给付的、系是没有原因的,也被翻译为‘不当清偿’或者‘不当支付’。”〔24〕李世刚:《法国新债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版,第83 页。法国判例和法学研究的长期积累表明:非债清偿与不当得利(狭义的)相比,限于当事人本不应当向他人支付(没有法律或契约上的义务)却直接对其支付并使得该他人获利的情况,获利者得利的不正当性、得利与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均非常清楚;在效果上,返回的客体即是当事人已经支付的内容。(狭义)不当得利则是涵盖除非债清偿以外的其他一方受损他方获益的情况;在构成要件上,得利的不正当性得具体从两个层面进行判断,一是要核查得利没有原因,二是适用“辅助性原则”;在效果上,返还受制于双重限制规则。法国新债法坚持“非债清偿”与“(狭义)不当得利”二元区分主义〔25〕李世刚:《法国新债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版,第65 页。。这里所谓的“辅助性原则”是指法国民法典第1303-3 条规定的原则:如果受损人享有另外一项诉权,或者该诉权遇到时效等法律上的障碍,不得以不当得利为基础请求救济。也就是说,只有在没有其他诉权救济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不当得利请求权。非债清偿,则没有这种限制。
另外的制度区分是,主观过错对于请求权的影响,尤其是与另外一项制度即赠与的关系问题。按照法国民法典第1302 条的规定,清偿应以债务存在为前提,当然这种债务也包括自然债务。如果没有这种原因,受领者受领了清偿,就应予以返还。“非债清偿”应当就是指这种没有“原因”前提的清偿,受领者应予以返还。按照法国民法的传统理论,非债清偿分为“绝对非债清偿”和“相对非债清偿”。前者是指清偿之“非债”或曰“无因”(即债务不存在的事实)是客观的、绝对的,清偿人没有债务,受领人也没有债权(绝对非债清偿)。后者是指“的确存在债的关系,但或者受领人不是债权人(不完全相对非债清偿),或者清偿人不是债务人(完全相对非债清偿)”。〔26〕李世刚:《法国新债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版,第83 页。类型化的主要意义体现在清偿者的错误认识是否是非债清偿返还的构成要件。2016 年修改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302 -2 条体现了这一规则。认识错误虽然不是构成要件,但是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02-3 条第2 款可能影响返还的范围。在并不完全相对的非债清偿中,认识错误也不是构成要件,却是影响返还范围的因素。然而,在完全相对的非债清偿中,即在清偿人并不是债务人却错误地清偿了他人的债务的情形中,则要求主观上的积极要件——清偿人的错误认识。
第二个理由是传统的因素。其实,在法国早期的理论和立法中,“准合同”仅仅包括无因管理和非债清偿,不当得利并不包括在其中。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就体现了这种观点,其第1371 条至第1381 条仅仅规定了无因管理与非债清偿,没有规定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法国最高法院于1892 年6月通过判例“并借助”罗马法上的“转用物诉权”将其归入准合同的。〔27〕参见李世刚:《法国新债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版,第59 页。
可以借用一个例子看出法国学理区分不当得利与非债清偿的意义:假如A 与B 签订一个合同,A 根据该合同向B 进行了履行。现在合同因为法定原因无效了,那么,AB 之间的关系按照法国民法典如何解决呢?显然,按照法国民法典第1302 条的规定,A 的清偿属于“非债清偿”,而非不当得利,原因如下。其一,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其二,当事人关系明确,且合同无效后,A 的履行就失去了基础(原因),B 的受益就是无原因。因此,应当返还。这里要注意的是:适用非债清偿与不当得利在法国法上的区别——按照2016 年后的法国民法典,如果原告享有其他诉权,则排斥不当得利的适用。在法国,因为不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所以,当合同无效时,所有权就没有有效转移,仍然属于原告。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既然可以享有所有权返还的诉权,就不能适用不当得利,但是,应该可以适用非债清偿。因为法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非债清偿受到其他诉权的限制。可以说,非债清偿是因直接给付发生的请求权,而不当得利可以是非因给付发生的请求权。
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法上的这种分类,与我国民法理论和法律,以及与德国民法典及学理,几乎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德国学理及民法典虽然采取广义的不当得利,即把法国法上的非债清偿包括进不当得利,但德国学理却将不当得利分为“因给付产生的不当得利”和“非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28〕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22-525 页。。德国民法典第812条也将不当得利分为因他人给付或者其他原因使他人损失而自己获益的两种类型。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而是直接表述为:“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那么,什么叫做“没有法律根据”?是否能够将其统一起来?其实,这正是德国民法典的适用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争议的问题:是否可以用统一的不当得利事实构成涵盖所有类型的案例,或者对其区别对待是必要的拟或是适当的〔29〕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20 页。?从现在来看,德国民法典和学理并没有采取“统一”的做法,而是进行“区分”——因给付与非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而法国民法典是用非债清偿与不当得利来解决——也是区分的。我国《民法典》的这种做法在具体实际案件中又将如何识别呢?
将不当得利区分为给付型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对于制度构建意义重大。例如,上面提到的法国民法典做出非债清偿与不当得利的区分;德国民法典上,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要讨论给付的目的(原因问题)、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排除问题等。然而,在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主要包括侵害型不当得利和其他特殊性不当得利,基本不考虑给付的目的或者请求权排除问题。因此,我国《民法典》中关于不当得利的界定远远没有完成,非借助于民法教义学难以认定。在我国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三、无因管理的正确界定〔30〕笔者另文对无因管理在民法典中的规范空间有专门的论述,在此不赘述,仅指出我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定义的不足及其漏洞。
我国《民法典》第979 条第1 款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显然,这是从管理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视角来界定无因管理的,这也是我国民法教科书长期以来表述的、被认为是“公理”的概念。然而,实际上,如果从整个民法典体系的视角看,这个概念却存在很大的漏洞和重新审视的必要。假如A 与B 签订了一个委托合同,约定了B 有义务以A 的名义从事某种法律行为,并授予其代理权。但是,B 为未成年人。B 的法定代理人拒绝承认委托合同的效力。B 为了A 的利益,以A 的名义从事了这种行为。B 显然属于“没有约定义务或者法定义务”,但在A 的授权范围内为A 的利益做出法律行为。那么,B 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B 是基于授权并非基于自己的意思自愿为A 管理事务。这也是说明,B 有权限没有义务从事法律行为也不构成无因管理。这一实例说明,我国《民法典》及学理通说关于无因管理定义是不准确的。
从制度渊源上说,无因管理源于罗马法,之后为许多国家所继受,但仅是继受的方式不同。界定无因管理这一概念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权利或权限说”。这种立法例以罗马法、德国法等为代表。二是“义务说”。其以我国和日本学理与立法为代表。笔者认为,在从教义学视角解释和适用我国《民法典》第979 条的无因管理构成的时候,用“无权利或者权限”的界定方式更符合立法宗旨和我国民法典制度体系,理由如下。其一,“无权限”更契合无因管理的制度价值和立法目的。一般而言,如果他人没有授权,行为人就不能介入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就可能构成侵权行为,但无因管理制度却正好属于特例——其本质即在于没有介入他人生活的权限。尽管日本民法典采用“无义务”的方式,但学者仍然认为,对待无因管理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没有权利比没有义务更重要”〔31〕[日]我妻荣:《债法各论》(下卷一),冷罗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2 页、第16 页。,因此,比较妥当的设计是管理人没有权限。德国学者即是用“权限”来定义无因管理,有德国学者直接指出,对于无因管理最主要的分类系将其区分为德国民法典第677 条至第686 条上的真正的无因管理(echte GoA)和德国民法典第687 条上的不真正的无因管理(unechte GoA),而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1)管理人实施了管理事务的行为;(2)所管理的事务是他人的事务即所谓“本人”的事务;(3)管理人既没有通过委托合同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被赋予管理事务的权利。〔32〕Manfred Wandt.Geseztliche Schuldverhältnisse.9.Auflage.Verlag Franz Vahlen.München.2019:14.曼泽尔教授也认为,无因管理指的是某人(管理人)照管他人(本人)事务,而无该他人委托或出自其他原因的授权,在承担事务管理之前,管理人与本人之间无任何涉及照管该事务的法律关系。〔33〕Mansel,Jauernig,Bürgerliches Gesetzbuch;BGB,17.Auflage 2018,Vorbemerkung § 677,Rn.1.其二,从“无权限”的视角入手来界定无因管理的概念更契合我国民法典的制度体系。否则,如前所述,我国《民法典》中的类似无权代理等许多无因管理的类型就生硬地被排除出去了,而有些制度却可能被不恰当地包括进来,如自然债务。此外,仅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来界定无因管理也不能从自身体系合理解释我国《民法典》第524条这种现象——根据该条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如果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人履行的除外。如果从“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而不是“没有权限”来界定无因管理的概念,那么,第524 条恰恰就构成了无因管理。我国《民法典》第719 条也有同样的问题:“承租人拖欠租金的,次承租人可以代承租人支付其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但是转租合同对出租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除外。”这里显然“次承租人”对出租人也无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但是,根据该条他却有“权限或者权利”来支付租金。因此,也不构成无因管理。其三,从比较法上看,多数国家采用“无权限”来界定无因管理这一概念。于罗马法中,在主人或者被经管人不知晓的情况下经营他人事物,采用的专业术语就是无因管理,〔34〕参见[意]彼得罗·彭凡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325 页。即它是自愿的和未经批准的、对他人事务的经营。〔35〕参见[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243 页。这里的“未经批准”指的就是权限或者权利。《德国民法典》第677 条是用“权限”来表达:“为他人处理事务未受他人委托,或者对他人无权以其他方式为之处理事务,必须在照顾本人真实或可推知的意思的情况下,以本人的利益所要求的方式管理该事务。” 德国学者指出:“行为人管理事务既可以是未受委托,也可以是不对本人享有任何权利。”〔36〕[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05 页。慕尼黑法律评注的作者舍费尔(Schäfer)先生指出,无因管理指的是,“管理人(Geschäftsführer)在没有合同或者法律的授权的情形下,以管理他人事务的意愿(Fremdgeschäftsführungswill)管理本人(Geschäftsherr)的事务”〔37〕MüKoBGB/Schäfer,8.Aufl.2020,BGB § 677 Rn.1-3.。日本民法典虽然采取“义务说”,但日本学理认为用“权利说”更合适。〔38〕参见[日]我妻荣:《债法各论(下卷一)》,冷罗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2 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我国《民法典》第979 条采用的是“无义务”的表述,但从我国《民法典》的规范体系及无因管理的制度目的看,完全可以用“无权限”来解释“无义务”。因为,如果对某人负担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自然也就可以推导出有对他履行的“权限”,即所谓“若存义务就肯定有履行义务的权限”的原则。〔39〕参见[日]我妻荣:《债法各论(下卷一)》,冷罗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16 页。例如,A 对B 负有债务,A 自然有向B 履行的权限。然而,在无权代理中,因为代理人对委托人(被代理人)有义务但无权限,他对于第三人没有义务,也没有权限。虽然在这里不能理解为“有义务就有履行义务的权限”,但此时亦可构成无因管理。因此,从“无权限”角度来扩大解释我国《民法典》第979 条更加合理。
总之,对于我国《民法典》第979 条的正确界定应该是: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权限(权利),以为他人利益的意思而管理他人事务,就构成无因管理。
至于无因管理之制度构造,有日本学者认为,合同的缔结是通过“要约+承诺”来完成的,但无因管理恰恰就是缺乏合意。“为他人进行管理的意思相当于无因管理者这一方的‘茫然的要约’,而来自本人的许可或不违背本人的意思,则可看作‘茫然的承诺’。通过这种‘茫然的要约和茫然的承诺的一致’,无因管理就成立了。并且,无因管理的法律后果,可以类推适用委托的相关规定,有类似于委托合同的一面。”〔40〕[日]加藤雅信:《作为立法论的“准合同”论——对中国民法典草案的三种修正提议》,吴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 年第2 期。应该把“不当得利”从我国《民法典》第三编中移到其他部分,以利于体系化。〔41〕参见[日]加藤雅信:《作为立法论的“准合同”论——对中国民法典草案的三种修正提议》,吴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 年第2 期。笔者理解加藤雅信先生的初衷为:(1)如果说无因管理还与合同有些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不当得利制度与合同真的就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并不能放在合同编中;(2)既然无因管理类似合同,就可以用合同成立的模式即“要约+承诺”来模拟其成立过程,但实际上,无论如何模拟,无因管理与合同都存在质的差别——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是通过双方合意来产生的,而无因管理中的义务则是通过法定产生的。当然,从仅仅缺乏“委托”来看,已经很类似合同了,称之为“准合同”也非常“准确”,正因为如此,德国民法典才将其规定在委托合同之后。显然,我国民法典将不当的得利规定在合同编中,确实在体系上存在问题。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准合同形式上被纳入合同编中,但是基于《民法典》第468条的规定,其实质上又游离于合同编之外,要适用自己的独有规则。从这个角度而言,形式上被纳入合同编的准合同,基于其非因合同产生的特质,呈现出置身合同编之中却具非合同之性质的情形,实际上导致准合同在合同编中难觅规范基础,处于被‘悬空’之状态”〔42〕费安玲:《我国民法典中准合同解释之罗马法因素》,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5 期。。如果从理想的逻辑看,我国《民法典》虽然没有债编,但可将债的内容分为“合意之债”与“非因合意产生之债”两编,将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规定在“非因合意产生之债”之编中最为合适。
四、不当得利的类型区分的价值及其与请求权体系的界分
如前所述,我国《民法典》没有区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而是仅仅以教科书上的“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来界定之,其实,对于司法实践将带来困惑——什么叫没有合法根据?因此,对于不当得利,必须结合我国《民法典》进行体系化解读。
(一)对于不当得利之性质的界定
由于我国《民法典》缺乏债法总则,如果仅仅从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来解释,恐怕连“物上返还请求权”也可以解释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应当返还,因此,可以说,如果不从体系上加以解释,我国《民法典》上的物权与债权的返还请求权将无法区分。因此,有必要首先界定,在我国《民法典》上不当得利的性质。
按照德国学者的解释,返还利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被称作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其针对的(反义词)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43〕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22 页。。加之,德国民法理论和立法均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至少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的情况下),阻止了物上返还请求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在德国法及学理上,不当得利为债权请求权是没有争议的。在法国法及学理上,如前所述,凡是有其他诉权者,不可以主张适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因此,在法国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也属于债权。由此,自罗马法以来一直有一个法谚:“物上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不得两立”。由此可见,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应该是债权属性,其核心是“给付”。
然而,在我国《民法典》上,对于第985 条如何理解,特别是其与第235 条、第462 条、第157 条之间区别及关联,就成为疑问。第985 条对于不当得利的界定仅仅是:“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第235 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462 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第157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我国目前的民法典体系及民法理论,第985 条的返还请求权与另三条的关系如何界定?因为,第235条、第462 条、第157 条其实都属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即使是返还原物〔44〕当然,我国《民法典》第462 条关于“占有”的规定中,准确地应该是“返还占有”而不是“返还原物”。这样的话,其实,第462 条与第235 条区别就不大了,甚至第462 条就变得多余了。,也可以是根据不当得利这一请求权基础。
第157 条的返还请求权基础比较简单,如果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则这里的返还请求权基础就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如果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则这里的返还请求权基础就是物上返还请求权。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面详细论述。
如果仅仅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作为请求权的支持,那么,大概所有问题(除侵权外)都可以涵摄其中,因此,必须对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的规定内涵进行限制。否则就会得出下列结论:(1)在第985 条规定下,第157 条、第235 条、第462 条统统为多余;(2)第985 条与第157 条、第235 条、第462 条发生请求权基础竞合。但是,这两种结论,无论从比较法的视角,还是从我国《民法典》的框架看,都与民法权利体系的性质不合。因此,必须认真地对第985 条进行限缩性解释。
第一,从第985 条的文义进行限缩解释。该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这里就有两个因素:一是没有合法根据,二是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是审查利益取得的“原因”是否存在,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下面详细论述。“取得利益”之关键在于“已经取得”。例如,在我国《民法典》第235 条下,“物”是否已经被取得?显然,从第235 条的立法目的和体系解释来看,该条是规定在“物权保护”之下,而我国《民法典》对于占有单独作为一个“分编”来规定的。因此,从体系上看,第235条中的保护对象显然不包括“占有的保护”,而仅仅是对物和物权的保护。甚至从该条的文义看,仅仅是对物的保护。这里的“无权”包括没有债权基础和物权基础。例如,按照租赁合同占有他人之物的,也可以成为该条的对立面“有权占有”;按照质权占有质物的,也是有权占有。无权占有动产或者不动产的,显然是没有取得占有物,因此,这里不能适用“不当得利”。当然,除了物本身之外,占有人有可能还会获得物之外的收益,这种收益有可能是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我国《民法典》第321 条的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在无权占有的情况下,天然孳息当然应该归物主所有;但法定孳息,例如,占有人将占有物出租获得利息,也应归物主所有。按照这一规则,也不发生不当得利的返还问题。例外的情形是:如果还有其他收益,例如,无权占有人利用占有物加上自己的劳动或者从事了有风险的活动的收益是否应当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具体来说,例如,占有人将占有物进行商业经营,赚得比原物多出几倍的收益,那么,该收益是否应当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对此,我国《民法典》并没有明确规定。甚至从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第986 条之规定看,似乎取得的利益都应当返还。然而,从第987 条的规定看,恶意得利人,不仅要返还利益,还要赔偿损失——“返还的范围=得利人所得利益+受损人受到的损失”。但这种解释似有不妥。笔者认为,这里应该解释为:如果恶意得利人返还的所得利益不足以弥补损失的,还应该在得利返还之外,赔偿受损人损失。联系第985 条与第986 条综合判断,应该解释为善意的得利人,在所得利益不存在的时候,免除返还义务;恶意得利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返还所得利益(无论其是否存在),并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对于善意得利人适用“损失大于得利的,以得利为限;得利大于损失的,以损失为限;利益客观上已经不存在的,免除返还责任”之规则;对于恶意得利人则适用“损失大于得利的,以损失为限;得利客观上已经不存在的,仍然负返还责任”的规则。不过,在得利大于损失的情况下,仍然以受损人的损失为限负返还义务。当然,在双务合同无效时,返还义务与风险负担的关系问题,笔者将在下面详细分析。
第二,从物权保护的立法目的和体系化出发进行限缩解释。从民法典的权利体系构成及请求权基础来看,每一种权利基本上都配备了自身的救济措施,只有在自身救济措施不足以救济的时候,才借助于侵权或者其他救济措施。从物权编(法)本身来看,如果物主之物仅仅是被他人侵占,但物还完整存在的话,就没有必要借助于其他救济措施,物上返还请求权就足以对物主进行救济。结合这一立法宗旨,再来看看我国《民法典》 物权编第235 条及第462 条之规定,显然不属于不当得利的救济领地,因此,在与第985 条的关系上,也就不能把上述两条的情形包括进去。当然,如果还有其他获利或者损失的话,有可能借助于不当得利或者侵权行为。
因此,我国《民法典》 第985 条的规定显然不能包括“物上返还请求权”和“占有返还请求权”。也就是说,对于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中的“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必须进行限缩解释,而不能扩大至物上返还请求权。
在这里笔者再一次体会到法国民法典第1303-3 条关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关系上的规则的正确性——在存在其他请求权基础的时候,排除不当得利的适用。法国最高法院民事庭1915年3 月2 日的判例规则也认为,只有当一个人无正当原因而获得财富利益,且此种财富利益的增加有损于另一人的财富利益,而该另一人要想取回其应得的财产,又不享有因任何合同、准合同、侵权行为或准侵权行为产生的诉权时,才准许提起返还财产(返还不当得利)之诉讼,并且提起此种诉讼的目的不能是为了逃避法律对特定合同明文规定其效力的规则。〔45〕罗国珍译:《法国民法典(下册)》,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62 页。
实际上,法国法及法院判例关于不当得利的做法,实际上等同于“间接得利”。但是,这种间接得利要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有无法律上的原因;二是有无其他诉权(辅助性原则)。由此,法国民法典不是采取如同我国学者的态度即动辄按竞合处理,而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样一来,尽管法国民法典上没有物权与债权、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的处理,但其“排斥”的做法以及三分法的分类,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和法律效果却与德国民法典相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须清楚不当得利在请求权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当得利制度是从“得利人”的视角来平衡这种不利益关系,而不是从受损人的视角来设定处罚制度的。就如德国学者所言,德国民法典第818 条第3 款规定“以受领人不再得利为限”,排除返还义务或者价值补偿义务。该条还应该扩及原初无不当得利的情形,该条款构成了不当得利责任的原本特质。这种特质主要厘清了不当得利责任与第346 条和第347 条规定的解除责任的区别与不同:如若不存在加重责任的理由,受领人一般应予返还或补偿的利益仅为其财产中增加的部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当得利请求权就构成了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对立面:损害赔偿请求权涉及的不是债务人增加的利益,而是债权人丧失的利益。”〔46〕[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53 页。这其实就是不当得利制度的价值所在:它既不同于物上返还请求权,也不同于侵权责任请求权。
(二)划分不当得利种类的重要性
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这样笼统地规定不当得利的做法,难以构建出制度规则,甚至难以与民法典体系中的法律行为制度相互配合。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不当得利类型众多,其所涉及的规则和问题难以用统一的根据来论述,只有进行合理的分类,才能进行有效的涵摄,从而使民法典体系性得以实现。因此,德国法上才有“统一说”与“区别说”,也就是根据不当得利是否是根据(与法律行为有关的)“给付”发生,来区分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与非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
至于区分的具体原因,德国学者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不当得利学说的争议远远超过民法的其他部分。争议点主要不在其结果”,而在其产生结果的理由,“即是否可以用统一的不当得利事实构成涵盖所有类型的案例”,或者对其区别是否必要拟或适当〔47〕[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20。。当然,德国学者的争议的出发点在于德国民法典的第812 条的解释,即该条是否对不当得利进行了类型区分。但这种争议属于具体民法典实然上的争议,与笔者讨论的问题即应然(应否规定)没有关系。笔者是在讨论:在民法典体系下,不区分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与以其他方式发生的不当得利,能否构建出可以适用的制度?对此,德国学者认为,应当区分,理由是:(1)“不当得利涉及的事实构成具有完全不同的外在表现”,而一个能够涵盖所有这一切情形的表述应当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高度抽象其实就难以构建制度和规则),如何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依照通说,仅为此目的就应对不同的不当得利类型进行分类;(2)“分类尤其有利于对于缺乏‘法律原因’的查证”〔48〕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521-522 页。。
根据德国学者的上述分析,笔者以我国《民法典》结构和制度设置为例来说明分类的必要性。
首先,分类有利于制度构建。按照通常的逻辑,一个概念的涵摄范围越广,其就应该越抽象;越抽象,就越难以形成规则——难以形成构成要件,也就是说,难以形成规范。民法典需要的是具体规范,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概念仅仅是民法典中规范的辅助性工具。我国《民法典》第985 条关于不当得利的“描述”可以说是“统一说”的典型表现——仅仅是抽象描述“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其弊端就是:在民法典体系下,难以与物上返还请求权相区分。
其次,有利于对于“没有法律原因”的确认。在大部分国家的民法典上,都是承认“原因”的,无论是德国民法典,还是法国民法典,都是如此。负担行为(债权请求权行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正当的原因,这种原则往往被理论称为“债因”。在私法体系中,私人行为无论是想获得债法上的效果,还是想获得物法上的效果,均需要得到法律的认可,但是,并非所有的私人行为都会得到法律的认可。在考虑是否认可私人行为,进而赋予这些私人行为以法律效力时,实际上存在一个评价与筛选的机制。〔49〕娄爱华:《大陆法系民法中原因理论的应用模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 页。被法律纳入这一机制中的因素众多,例如,法律行为的无效因素与可撤销因素等等,但是,有一种因素是这一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它既反映交易本质又决定交易效果,它就是“债因”。也就是说,一个法律行为除去无效及可撤销的因素外,还有一种限制私人自治的因素——债因。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债因或者原因仅仅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专利,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债因或者原因在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民事法律上都有体现,只是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法国法上称为“原因”,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为“约因”,德国学理与立法上众所周知的“有因”与“无因”之中的“因”,其实就是指“原因”,只有在债的关系中才要求有“原因”,称为“债因”。什么是债因呢?《学说汇篡》和《优士丁尼法典》断片所使用的“原因”一词具有相同的含义,是指给付进行的基础。“原因既可以是受领人的给付,也可以是任何其他致使给付作出的情形。”〔50〕[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189 页。意大利学者彼德罗·彭梵得指出,在罗马法上,“契约”一词除了指协议外,还强调作为债的关系的原因行为或者关系,因为这种“客观关系”在罗马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契约由两个要件构成:一个最初的要件是原因或者客观事实,它是债的根据;“另一个要件是后来由古典法学理论创设的,即当事人之间的协议”〔51〕[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307 页。。显然,彼德罗在这里所谓的“债因”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客观关系”,这种客观关系具体是指什么呢?依笔者理解,应该是指任何一种被罗马法承认的契约所反映的客观的交易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是当事人的契约目的。例如,在“合意契约”的买卖中,其客观关系就是表现为一方交付金钱,而另一方交付物。这种关系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不过,目的就不同了:我卖房子有两个目的,一是取得金钱,二是拿钱去经营生意。有人把前者称为“近因”,把后者称为“买卖的动机”,一般来说,法律只保护“近因”而不保护动机,除非例外的情况下。只有“近因”才是客观的,也就是罗马人所说的“债因”。“买卖动机”则因人而异,无法把握。因此,债因与目的是有区别的。德国学理中所说的“有因”或者“无因”,就是指“债因”——只有债的关系才要求原因,而物权关系上不要求“原因”即无因。虽无因,却发生不当得利。
区分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和非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就是在民法典体系下,在法律行为区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体系框架下,为查找“法律原因”提供方便。例如,A 与B 签订了买卖合同(负担行为),合同生效后,A 根据合同向B 交付了买卖标的物(B 接受,处分行为)。首先,买卖合同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存在原因,否则便不能生效。根据合同交付了标的物,属于处分行为。尽管处分行为不问原因如何,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然而,当合同无效的时候,原因丧失,尽管B 取得的标的物仍然属于“有权取得”,但却没有了“原因”,此时,B 的所得为“无法律原因的取得”,属于不当得利,A 有权请求B 返还该给付。这里的原因非常清晰。因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体会法国民法典为什么要区分“非债清偿”与不当得利:在“非债清偿”中,实际上就是“原因”清晰,而不当得利却要难得多。例如,在法国最高法院1892 条6 月15 日判决的一个案件中,就很有说明意义。该案中,某农民租种土地后,因无力支付租金而解除了租赁合同,并放弃了土地上的农作物以偿还他对土地所有人欠下的债务。不过,该农民用于耕种这块地的化肥系从化肥商那里购得的,且一直没有付款。于是,化肥商便起诉土地所有权人,理由很简单,后者从其化肥中获得了利益,并最终获得了法国最高法院的支持。法国最高法院借用了来自罗马法上的“转用物诉讼”,认为,对于“转用物诉权”,“我们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对其进行规制,该诉权的行使不受制于任何特定的条件”,只要请求之人能证明“通过其个人行为或者贡献,使得相对之人获得利益”即可〔52〕李世刚:《法国新债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版,第64 页。。不过,前已论及,这种间接得利要受到“双重限制”——有无法律原因和辅助性限制(是否具有其他诉权)。
我国《民法典》第157 条的规范,可以解释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属于因合同和其他法律行为所做的给付——当法律行为无效的时候,应当返还给付。尽管它也属于第985 条的统辖范围,但属于德国法上的给付型不当得利,或者法国民法典上的“非债清偿”——法律原因和得利人(被告)非常清晰。该给付即为第985 条所说的“无合法根据取得利益”。尽管我国学理对于我国《民法典》是否采取了无因性有争议,但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我国《民法典》是采取了无因性原则的,如果结合我国《民法典》第二编第一分编第二章关于公示公信原则的规定,应该说是采取了无因性原则。因此,我国《民法典》第157 条规定的这种返还请求权为不当得利的债权请求权。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有非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而这些非因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就与法律行为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无关了。因此,在审查其“无合法根据取得利益”的时候,就不能审查“债因”,例如,侵害型不当得利等。
五、结 论
准合同的概念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括的概念,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使用了这一概念,而1900 年的德国民法典抛弃了这一概念。2016 年修改后的法国民法典有意淡化了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准合同”是不“准确的”。我国《民法典》由于没有债法总则,因此将其收留在了“合同编”中,也是出于无奈的安排。从准合同的外延来看,实际上也不是当然包括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与准合同之间的关系比较“牵强”。即使在不当得利的具体分类中,大部分欧洲国家民法典也严格区分“非债清偿”与不当得利。例如,法国民法典严格区分非债清偿与不当得利,且明确规定:在有其他诉权的情况下,排除不得当得利的适用。这种严格的区分实际上有利于制度的构建和法律适用——什么叫没有合法根据(原因),容易查证。德国民法典和学理虽然没有适用“不当得利”的概念,但却区分“给付型”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与法国法在实际效果上是一致的。我国《民法典》在不当得利问题上,采取的是非常笼统的定义——没有合法根据。这样,几乎所有的请求权都可以融入,例如,物上请求权、无因管理请求权,甚至某些侵权请求权等。如此一来,法律体系精确性和体系性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将其限制在“债”的范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