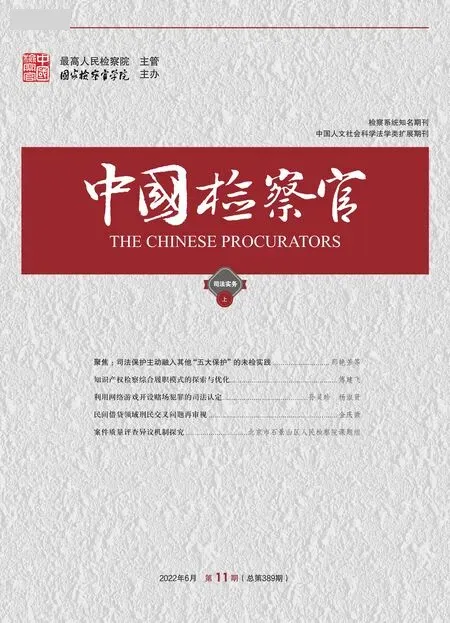到期债权执行异议的审查路径及救济方式
● 杨 悦 杨友学/文
一、对到期债权提出执行异议的制度来源
次债务人对到期债权提出执行异议法律制度的实体法基础,来源于已为民法典第535条所确立的债权人之代位权。债权人基于代位权获得代为诉讼的权利,次债务人则获得应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行使的各种抗辩权。次债务人对抗辩权的行使,旨在使其被附加履行的债务不超过“应然”范围。
该法律制度的程序法基础,来源于2008年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202条首次引入的“执行异议”制度。在2008年4月1日以前,对执行行为的异议,仅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向上级法院申诉,按照执行监督程序处理。及至现行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23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499条,已成为次债务人对到期债权执行异议的直接法律规定。
次债务人对到期债权提出执行异议时,应当通过何种路径进行审查?申请执行人、次债务人等权利人对审查结果又应当寻求何种方式进行救济?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区分次债务人对到期债权执行异议所处的不同阶段,选择正确的审查路径及对应的救济方式。
二、执行保全阶段执行异议之审查路径及救济方式
因被执行人已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查明被执行人在他人处享有到期债权时,人民法院可通过向次债务人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次债务人停止向被执行人清偿到期债务。因仅实施了保全措施,尚未涉及对次债务人财物的处置,一般不会损害次债务人的实体权益。此时,若次债务人认为该保全行为违法,则可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5条第(四)项中的“利害关系人”,就该保全行为提出异议。该异议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232条的规定进行实质审查。次债务人或申请执行人对该审查结果不服,可通过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或执行监督的方式,寻求权利救济。
若次债务人提出了诸如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债务已清偿完毕、存在抗辩事由等实体异议,又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次债务人提出实体异议,仍为否定该执行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前述实体异议经实质审查后,相关权利人仍应通过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或执行监督的方式,寻求权利救济。
因人民法院在此阶段向次债务人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并未告知次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期限,若该保全措施尚未被依法撤销或者解除,直至该执行程序终结前,次债务人均有权提出异议。但次债务人对执行保全行为未提出异议的,并不当然发生承认债务客观存在的实体法效力。[1]参见张文旺、苏州恒隆建设有限公司等与江苏四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 执复70 号执行裁定书。
三、债务履行通知书确定期限内执行异议之审查路径及救济方式
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享有的到期债权时,应当向次债务人送达《债务履行通知书》,该通知书应当载明15日异议期间。次债务人在该异议期间内,可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提出异议。笔者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区分该到期债权是否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
(一)对未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到期债权之异议
1.执行异议的审查路径及救济方式选择。结合《民诉法解释》第499条第2款后半部分,有关“利害关系人”[2]此处的“利害关系人”并非民事诉讼法第232条中的利害关系人,而应当认定为第234条中的案外人,如次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的异议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234条之规定进行审查可以看出,次债务人作为“该他人”所提出的异议应是与被执行人之间有无到期债权债务关系、到期债权具体数额、存在抗辩权等实体异议。依据该款规定,次债务人在异议期限内提出实体异议的,一经提出则异议成立,人民法院不予审查,也不得强制执行。即,次债务人享有实体上的“绝对异议权”。因次债务人在此种情形下享有“绝对异议权”,故应当防止次债务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通过虚假异议的方式规避、妨碍人民法院执行。与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232条规定的申请复议、第234条规定的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或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救济方式不同,此种情形下申请执行人可以通过提起代位权诉讼寻求权利救济。[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通知》(2017年)第3条。这与德日两国在对被执行人金钱债权执行立法中规定的“收取之诉”具有相似之处[4]参见[德]奥拉夫·穆托斯特:《德国强制执行法》,马伟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175页。,均是通过新的诉讼获取新的执行依据。
2.执行保全与代位权诉讼的程序衔接。申请执行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前,前述执行保全行为应否被撤销?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并未就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在执行到期债权时就明确提出,申请执行人若提起代位权诉讼,则无需解除之前的执行保全行为,可将执行保全转为诉讼保全。也有观点认为,此种情形下继续冻结到期债权的法律依据已不存在,故相应的冻结措施应及时解除,不应将执行保全转为诉讼保全。[5]参见高小刚:《到期债权执行问题研究——以执裁分立实践及典型案例分析为视角》,《法律适用》2019年第10期。
笔者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操作方式更为合理。首先,基于“审执分离”原则,人民法院仅对次债务人提出的实体异议进行形式审查,旨在将可能存在的实体争议交由诉讼程序进行裁判。因此,次债务人的实体异议并不具有结果上的终局性。[6]参见李哲:《到期债权执行若干理论和实务问题探析》,《人民司法》2021年第10期。其次,诉讼保全与执行保全设立的根本目的,均是为了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进一步解决“执行难”问题。再者,《民诉法解释》第168条明确规定,诉讼保全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自动转为相应的执行保全措施,故二者相互转化,在程序上也具有可操作性,不仅能节约司法资源,更便于促进审执衔接。
基于该解读,再参照有关诉前保全的相关规定,可以尝试建立由人民法院主动引导申请执行人及时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制度。例如,人民法院应当明确告知申请执行人,在收到执行裁定书后30日内怠于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将依法解除相应执行保全措施。该制度的设立,一方面,通过回归代位权诉讼,督促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方式救济自身实体权利;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因该到期债权久冻不解,影响其他债权人受偿;更甚者,还能避免被执行人与次债务人恶意串通规避执行。
(二)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到期债权之异议
因该到期债权已经人民法院实体审判进行了确认,故次债务人就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到期债权从实体上予以否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是对生效法律文书既判力的保护,也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有效维护。但是,也不能据此就盲目限制次债务人在此阶段提出异议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如法律文书生效后,次债务人已经就该到期债权向被执行人作出了实际履行,该到期债权已获得了部分或全部清偿,再或者已被抵消,次债务人仍可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7条第2款的规定,以债权已清偿或已抵消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对该执行异议的审查结果,相关权利人仍应通过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或执行监督的方式,寻求权利救济。
四、次债务人怠于履行后执行异议之审查路径及救济方式
(一)就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
在规定的异议期限内,次债务人既未提出异议又未主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对其强制执行。就该强制执行行为,次债务人可在该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并通过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或执行监督的方式寻求权利救济。
(二)就实体事由提出的异议
1.实体事由异议的审查路径。次债务人能否提出债务已履行完毕、享有抗辩权等实体异议?笔者认为,无论次债务人是基于主观还是客观原因未在限定期限内提出异议,次债务人在强制执行阶段就该到期债权履行情况提出实体异议的,人民法院仍应进行实质审查。[7]参见巴楚县教育局、盐城众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徐州飞虹网架(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异议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执异30号执行裁定书。首先,次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并不发生承认债务存在的实体法效力。[8]参见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崇文镇人民政府、李勇民间借贷纠纷执行申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执监254号裁定书。其次,次债务人因强制执行行为而被赋予了类似被执行人的强制履行义务,故其应享有不低于被执行人所应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在程序上得到救济的权利。[9]参见黑龙江明水康盈医院有限公司、上海筑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执行申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执监484号执行裁定书。最后,如前所述,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到期债权在已清偿或抵消后,仍可提出异议。若次债务人仅对债权数额存在异议,则可通过对账、审计等手段处理,提高执行效率。[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到期债权执行中第三人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异议等问题如何处理的请示的答复》〔2005〕执他字第19号)第3条。
2.实体事由异议的权利救济。若次债务人的异议被驳回,如何寻求救济?一种观点认为,次债务人在此阶段提出的异议仍然指向执行行为,故仍应通过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或执行监督的方式寻求救济。[11]参见王毓莹、沈建红、李炳录:《到期债权执行异议的处理路径》,《人民司法》2021年第10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以赋予次债务人提起“阻却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通过诉讼查清相关事实[12]参见陈明灿:《执行程序中对到期债权的审查》,《人民司法》2020年第35期。,如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第三人(即次债务人)可就“不承认与债务人的债权或其他财产权存在”“对债权数额有争议”“有其他可以对抗债权人的事由”提起异议之诉。[13]参见邢波、李弸:《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到期债权次债务人强制执行的制度》,《人民法院报》2021年9月3日。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如前所述,次债务人此时提出的实体异议依旧指向执行行为,而次债务人进入执行程序的依据系人民法院制作的执行文书,而非法院裁判,次债务人仅被赋予类似被执行人的地位,其所被赋予的法律地位尚不具备足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身份条件。
五、审查到期债权执行异议中应当注意的其他问题
(一)可执行的到期债权应为金钱债权
债权请求权包括给付金钱的请求权和给付种类物或者特定物的请求权。笔者认为,可执行的到期债权应限缩为给付金钱的债权。其一,从法律规定来看,《民诉法解释》第499条规定执行到期债权的前提是出具“冻结”裁定书;而从执行措施来看,只有针对金钱一类的债权才应当适用“冻结”措施。[14]同前注[5]。其二,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的权利基础实则来源于债权人的代位权,次债务人系因执行文书而非经生效裁判而进入执行程序,故对该制度的启动,应设定不低于代位权诉讼的限制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3条曾明确将债权人代位权可行使的客体,严格限定为非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其三,从法律实务层面来看,将可执行的到期债权限于金钱债权才更加符合提升执行效率的需要。若将其范围扩大到其他与财产相关的权益,将不可避免会启动程序更为繁琐的财产处置程序,甚至涉及执行标的异议,严重影响执行效率,违背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二)应严格区分收入与到期债权
收入属于债权的一种,具有经常性、连续性的特点,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往往具有劳动、储蓄、投资等权利义务关系较为简单明晰的特定关系;到期债权则具有一次性支付的特征,被执行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系基于合同、侵权等行为而产生的更为复杂的法律关系。二者因性质不同,在法律适用、审查路径以及权利救济上也存在差异。执行收入时,应当采取“扣留”“提取”措施;执行异议进行实质审查;救济方式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或执行监督。执行到期债权时,应当先依法采取“冻结”措施,再送达《履行通知书》;执行异议可能进行实质审查,也可能不予审查;救济方式还可能涉及代位权诉讼。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领域,将工程款作为“收入”予以“扣留”而非“到期债权”予以“冻结”的情况仍普遍存在,该执行措施适用法律错误,构成执行行为违法,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5]参见王东与吉林市为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李为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286号执行裁定书。
(三)未结算的工程款不应作为到期债权进行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