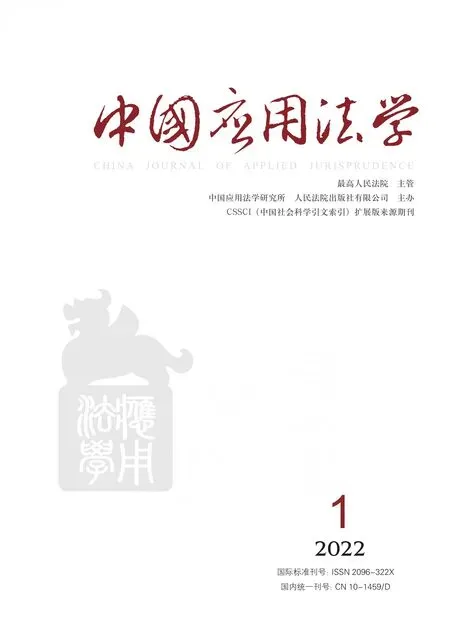网络仲裁程序的司法审查检视
——以接近“数字正义”为视角
汪 超 陈雪儿
引言
网络仲裁在数字经济时代逐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19年,我国31 家仲裁机构处理网络仲裁案件达20 万余件,占全国总数的42.21%。〔1〕《最高人民法院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2019年)》。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病毒,促使网络仲裁的使用频率得到大幅提升,网络商事仲裁也被运用到国际商事的争议解决。然而,网络仲裁存在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的情况。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2019年)》中指出网络仲裁案件中当事人程序保障不足的情况较为突出,〔2〕前引〔1〕,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对网络仲裁程序进行监督具有必要。对于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的不足,司法审查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保障监督机制。本文认为目前网络仲裁的审查标准遵循传统的商事仲裁审查标准,存在一定的瑕疵,无法完全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的网络仲裁。本文首先从“接近数字正义”理论结合网络仲裁特点及实践情况出发,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网络仲裁司法审查存在的困境并提供解决思路,为我国网络仲裁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提供理论及实践上的支持。
一、接近“数字正义”及其潜在问题
(一)从“接近正义”到接近“数字正义”理论的提出
西方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掀起以法院为主导的“接近正义”(Access Justice)运动。以美国为例,“接近正义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对民事司法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前两次的“接近正义”运动以法院中心论为依据展开,该理论认为法院能为当事人提供平等并且公正的救济机会,政府均有义务保障当事人接受裁判的权利。第一次运动旨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法律援助,重点在于克服“接近正义”存在的经济障碍。〔3〕Garth,Bryant G.,John Weisner,and Klaus-Friedrich Koch.,Access to justice.,Edited by Mauro Cappelletti.Vol.4.Sijthoff and Noordhoff,1978,p.36-42.为此,美国联邦政府经济机会办公室于20世纪60年代设立针对民商事法律援助服务部解决低收入人群的需要,后发展成为“联邦法律援助协会”(Legal Service Corporation),其主要管理联邦政府拨付的民事法律援助经费,截至1968年美国的民事法律援助机构发展至260 多家。〔4〕宫晓冰:《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 期。随着运动深入,第二次“接近正义”运动对诉权的保护范围从低收入人群扩展到中产阶级。随着财政资助的公益法律事务所出现后兴起的旨在消费领域和环保领域发展的公益诉讼与集体诉讼,〔5〕[意]莫若卡· 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刘俊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 页。也包括信用卡持有及房屋所有等问题。〔6〕Cappelletti,M.and Garth,B.G.eds.,Access to Justice:Emerging Issues and Perspectives;Edited by Mauro Cappelletti and Bryant Garth.Sijthoff and Noordhoff,1979,p.8在这一时期,原告适格理论得以突破,不再由于原告不适格而无法在民事诉讼中获取相应的利益。随着运动推进以及相应在公共领域中的法律修订,更广泛领域得到了司法救济从而实现进一步“接近正义”。以上两次“接近正义”运动都围绕着法院中心论展开,法院似乎成为唯一“接近正义”的纠纷解决途径。第三次“接近正义”运动则反映了对法院中心论的反思。随着诉讼爆炸,法院难以满足纠纷解决激增的需求,不再被视为唯一为当事人提供公平公正解决纠纷途径的机构。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通过多元纠纷解决方式解决,这离不开理论以及法规的支持。许多领域也产生了寓意更为广泛的关于正义的理念。〔7〕Galanter M.,Justice in Many Rooms:Courts,Private Ordering,and Indigenous Law,The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1981,13(19):1-47.多门法院〔8〕Sandefur R L.,Fulcrum Point of Equal Access To Justice:Legal and Nonlegal Institutions of Remedy,Loy.LAL Rev.,2008,42:949.以及不同纠纷应当应对不同程序的理论开始流行。联邦政府也于1983年修改《联邦民事诉讼法》第16 条,要求法官考虑运用司法程序外程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1990年颁布《民事司法改革法》,使得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联邦地区法院获得进一步的认可。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法》,建立各自的多元纠纷解决计划并制定相应的保障程序,美国大多数案件在审判程序已经被解决而较少进入审判程序。〔9〕张进德:《司法文明与程序正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52 页。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兴起在通说观点中被视为为当事人提供另一“接近正义”的途径。
在三次运动浪潮当中也衍生出围绕法院中心论及其反对观点的争论。法院中心论认为,法院被视为是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审判为当事人提供了在遍寻其他方式皆不可解决争议的情况下,获得公正解决纠纷保护基本权利的机会;没有作为基石和底线的审判,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难以真正地解决纠纷。〔10〕[英] Roberts,S.&Palmer:《纠纷解决过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形成决定的主要形式》,刘哲玮、李佳佳、于春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 页。有部分观点对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本身能否实现真正更快捷、更经济以及更少对抗性的解决纠纷提出了质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试图以减少经济上的困境减少接近正义的障碍,但是随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优势也消失殆尽。甚至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不能提升纠纷解决的效率,也难以形成公正的解决结果,从而违背“接近正义”的初衷。Owen Fiss 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为“用于精简案件程序进程的高度有问题的技术……虽然案件程序被精简了,但是正义不一定得到了伸张”。〔11〕“ It should be treated instead as a highly problematic technique for streamlining dockets…although dockets are trimmed,justice may not be done.”Fiss O M ,Against Settlement,The Yale Law Journal,1984,93(6):1075.
而法院中心论的反对者在不少纠纷解决的相关文献中往往会提及“金子塔”模型来阐述克服司法诉讼中遇到起诉障碍的必要性。强调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案件少之又少,以法院中心论为依据的“接近正义运动”忽视了大量无法进入正规司法系统的纠纷。〔12〕Miller R E,Sarat A.,Grievances,Claims,and Disputes:Assessing the Adversary Culture,Law and Society Review,1980,525-566.更有激进的观点认为,法院中心论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当事人不仅要承受诉讼高昂的成本和漫长的周期,并且诉讼具有对抗性及其救济作用具有优先性;诉讼可能破坏社会关系从而导致次优的诉讼解决过以及当事人对诉讼产生大体上的不满,这一类观点以Carrie Menjel-Mesdow 为代表。〔13〕Menkel-Meadow C.,Pursuing Settlement in an Adversary Culture:A Tale of Innovation Co-opted or the Law of ADR,Fla.St.UL Rev.,1991,19:1.相反,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了不同的程序选择,其允许有关利害关系人参与到纠纷解决当中,并且更注重当事人的感知和需求,而并非按照强制性规定判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14〕Sandefur R L ,Fulcrum Point of Equal Access to Justice:Legal and Nonlegal Institutions of Remedy,Loy.LAL Rev.,2008,42:949.
Katsh &Rabinovich-Einy 基于“接近正义”理论结合数字时代争议解决的特点提出“数字正义”(Digital Justice)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数字时代科技本身产生了大量的线上等纠纷,这些纠纷若仅通过司法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难以保障其被公平及效率地解决。因此在20世纪时,“自上而下的正义”被“自下而上的正义”替代,而在21世纪则需要逐步发展为“数字正义”取代“传统的正义”。接近“数字正义”强调利用互联网等其他科技方式实现“接近”,并且需要保障合理、合规的数据、算法技术应用实现“正义”(Justice)。“接近数字正义”与“接近正义”的差异体现在纠纷解决的“三个转变”,首先是从面对面的线下空间转变为在虚拟空间解决争议;其次是从人为第三方介入程序转变为以科技第四方辅助纠纷解决的形式;最后是从强调精简数据,数据保密转变为关注数据收集、使用和反复利用,〔15〕Rabinovich-Einy O,Katsh E.,Access to Digital Justice:Fair and Efficient Processes for the Modern Age,Cardozo J.Conflict Resol.,2016,18:637.甚至利用数据预测及防范纠纷的发生。〔16〕Katsh M E,Rabinovich-Einy O.,Digital Justice: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of Disput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52.
(二)接近“数字正义”的潜在问题及如何监督
接近“数字正义”旨在让更多的纠纷结合数字时代的特点得到公平的解决,同时预防纠纷的产生,体现了其积极的价值。同时接近“数字正义”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不能对潜在问题进行有效监督与纠正,则难以实现“接近正义”的初衷,对于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监督争论由来已久,并且随着互联网及其他科技,尤其是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相关理论也在不断地变更。笔者根据“接近数字正义”的三大转变梳理了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监督的建议。
首先,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将争议从物理空间搬到虚拟空间当中解决的这一空间上的转变,使争议解决空间虚拟化在某种程度感知也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到争议解决的结果;例如在虚拟空间上限制沟通,隐私、保密以及中立性,最终都会影响到程序以及结果的不同。〔17〕Assy R.,Briggs's Online Court and the Need for a Paradigm Shift,Civil Justice Quarterly 2017,36(1):93-108.因此,对其程序设计上有监督的必要性。Ayelet Sela 以自我辩护当事人(Self-represented Parties)为研究对象,发现在线争端解决机制暗含受到感知与行为所影响的电子化抉择建构(Digital Choice-Architecture),基于此机制设计者在设计机制架构当中应当通过科技帮助自我辩护当事人认识到争议当中自身权益及协助他们确定选择方案,从而参与到争议解决当中。〔18〕Sela A.,e-Nudging Justice:The Role of Digital Choice Architecture in Online Courts,J.Disp.Resol,2019:127.
其次,第二个转变主要体现在算法上的潜在问题,需要对算法进行有效监督。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强调借助科技第四方辅助纠纷解决有其积极的意义,例如利用算法辅助或自动处理大量的纠纷。Ethan Katsh 以及 Colin Rule 认为在线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最终阶段也许可以解决生活中大多数的争端,因为算法导向解决方式甚至比人工方式更容易得到信任。〔19〕Katsh E,Rule C.,What We Know and Need to Know about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SCL Rev,2015,67:329但是,算法也存在潜在的风险,理论上认为算法在争议解决方面存在潜在的三大风险。第一,对于程序上分配算法等科技以及人为责任是困难,软件设计仅仅做他认为应该做的,而极少对于法规上、道德上以及政策利益上的分析,也难以获取最佳的利益、价值以及对于争议解决过程当中当事人的考量。〔20〕Condlin R J.,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Stinky,Repugnant,Or Drab,Cardozo J.Conflict Resol,2016,18:717.第二,算法本身的不透明会引发结果偏见。算法在编写本身受到编写者自身的价值观、所处文化气氛社会制度又或者是外部因素所影响,最终影响到算法产生出先行存在偏见(Pre-existing Bias);〔21〕Goldman E.,Search Engine Bias and the Demise of Search Engine Utopianism//Web Search.Springer,Berlin,Heidelberg,2008,121-133.被引用于吴椒军、郭婉儿:《人工智能时代算法黑箱的法治化治理》,载《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1年第1 期。源于训练算法的数据偏见也会导致算法偏见,数据本身也存在时效性要求,当数据没有及时更新则难以保障结果精准。为保障算法的公平需要保障算法的透明可监督。然而,算法透明不等同一般的披露规则,其本身具有复杂性。算法的透明追求的是对算法的简要说明,在算法监督学术界中有算法备案、算法解释替代工具,还有对算法进行审计、评估与测试、算法治理以及第三方监管。〔22〕徐凤:《人工智能算法黑箱的法律规制——以智能投顾为例展开》,载《收藏》2019年第6 期。第三,算法并没有关注到当事人解决过程当中的心理活动。争议的解决时时刻刻都包含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及诉求。从心理角度出发去看待所有类型的争议解决是重要的——人类大脑中的活动异常于电脑运行(不仅仅是电脑运行速度更快一些的区分)。比方说当争议发生的时候,人类大脑无法完整地、客观地、正确地展现现象的全貌;在某种意义上大脑无法知道自己真正的诉求,或者也许知道自己真正的诉求但也无法通过良好的沟通作出正确的决定,因此争议解决是充满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一个好的运行系统必须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心理活动。〔23〕Sternlight J R.,Pouring a little Psychological Cold Water 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J.Disp.Resol,2020,1.
最后,对于第三个转变,在处理分析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涉及大量的数据收集,在监督上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及道德标准。面对大数据的不透明,目前缺乏专门针对在线争议解决机制标准的立法,主要依靠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标准及惯例;除强制性规定外,建立设计在线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道德体系具有必要性。在线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道德标准[国家技术和争端解决中心(2016)]提倡了该机制应有的价值标准,致力于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共享机制以及公开整合技术等。〔24〕Wing,L.,Martinez,J.,Katsh,E.and Rule,C.,Designing Ethical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s:The Rise of the Fourth Party,Negotiation Journal,2021,37(1):49-64.
二、网络仲裁可实现接近“数字正义”
(一)网络仲裁的释义
顾名思义,网络仲裁即网络技术与仲裁融合发展。实践当中,在我国网络仲裁初始应用于“亚洲域名争议解决”领域,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部分仲裁机构设立网络仲裁平台,尝试在网络平台上开展仲裁业务解决商事仲裁纠纷。随后,网络仲裁经历了整合阶段以及高速发展阶段;在整合阶段仲裁机构尝试进行深度合作,共享信息、互认仲裁员名册、共建案例库,高效、快捷、低成本地解决互联网争议;在网络仲裁的高速发展阶段,约束性网络仲裁平台与非约束性网络仲裁平台开展广泛的合作,将信息共享范围扩展至非约束性平台,如“易保全”“法大大”等非约束性平台体现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点参与到网络仲裁争议解决中,本文讨论领域仅为约束性网络仲裁,不涉及非约束性网络仲裁争议。
理论上认为科技与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的结合会趋向经历“技术辅助型”(Technology-Assisted)、“技术基础型”(Technology-Based)以及“技术推动型”(Technology-Facilitated)〔25〕Wahab M.S.A,Katsh,M.E.and Rainey,D.,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Theory and Practice:A Treatise on Technology and Dispute Resolution,Eleven International Pub,2012,p.399-441.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科技在争议当中起到辅助作用,一般作为资讯传播和交流,例如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通知、公告、送达,此种类型是技术与科技结合的初始形式。“技术基础型”强调技术已经可以成熟趋向于独立自主运行解决争议,对于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不但可以自主处理已经发生的争议,还可以提前预防纠纷,并对潜在风险及漏洞进行修补。网络仲裁目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结合以上三个发展阶段看,早期的网络仲裁研究均将网络科技视为将线下仲裁网络化的工具,仍然停留在“技术辅助型”阶段。学者根据互联网及其他信息技术与仲裁程序结合程度分别提出“全部说”“封闭系统说”“部分说”以及基于“部分说”基础上提出的“主要部分说”来对网络仲裁进行定义。以上对于网络仲裁的定义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基本将网络技术视为争议解决的一种工具。然而随着网络仲裁的发展,互联网及其他信息技术不再仅仅提供工具价值,甚至影响到争议解决当中的价值判断,例如智能仲裁部分程序通过自主运行方式解决争议,网络仲裁逐步向“技术基础型”阶段发展。结合网络仲裁实践上的发展及理论,笔者趋向于认为网络仲裁是当事人协议在公认第三方的主持下,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与争议相关的主要环节或者全部环节信息交换,并对争议进行评判裁决的争议解决方式,其中包含信息的收集与一定程度上的自动化处理。
(二)网络仲裁的特点
总体而言,网络商事仲裁与传统仲裁相比,最直观的特点体现在其争议解决是一种在虚空间所进行的虚拟程序。而虚空间中的仲裁程序背后需要有异于传统线下仲裁做法及方式支撑,网络仲裁程序与线下仲裁程序相比存在规则上〔26〕本文选取了广州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武汉仲裁委员会的网络仲裁规则为对比对象,对比整理其网络仲裁规则及仲裁规则的差异。以及实践中审理方式的差异,而差异又体现了网络仲裁的特点。
结合相关机构有关网络仲裁规则分析网上仲裁在仲裁规则上的特点,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首先,网络仲裁规则与仲裁规则的程序差异体现在送达方式——网络仲裁的送达方式主要通过仲裁平台以电子方式送达;网络仲裁平台是网络商事仲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期的网络仲裁并没有运用网络平台解决纠纷,其也是区别于线下仲裁的一个重要特点。综合相关仲裁机构对于网络仲裁平台的定义发现网络仲裁平台是网络仲裁特有的产物。其产生的原因是在传统的线下仲裁中,当事人将纠纷提交到仲裁机构经历申请立案、答辩、审理、裁决以及执行等整个程序都发生在实体空间,当事人面对面与仲裁机构、仲裁庭、仲裁员以及执行机构等人员或机构打交道,并不需要依托网络仲裁平台。而网络仲裁是一种在虚空间所进行的虚拟程序,网络仲裁平台的出现是为了更有效解决在虚空间程序所特有的问题,例如虚空间中特有的身份认证、送达等问题。网络仲裁平台功能基本涵盖了整个网络仲裁纠纷解决的主要过程,可以概括并划分为仲裁机构(仲裁庭)与当事人实施仲裁行为功能以及数据的存储和使用功能两大类功能。对于送达方式,网络仲裁的送达主要通过仲裁平台以电子方式送达。仲裁机构通常除了当事人要求纸质裁决文书外,基本的往来文书通过前文已提及的网络仲裁平台以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此种送达方式基本贯穿了整个仲裁程序。
其次,在审理方式上,网络仲裁规则将审理方式划分为远程庭审以及书面审理,一部分仲裁机构在审理网络仲裁案件时以书面审理为主、远程庭审为辅的方式,旨在保证裁决的公正性的同时提高仲裁解决纠纷的效率。目前审理方式在理论上可以划分为开庭审理、远程庭审以及书面审理。开庭审理模式中仲裁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均应到仲裁庭指定的地点,仲裁庭要当事人以面对面的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书面审理模式则不需要体现仲裁开庭审理中的直接言词原则以及集中审理原则。而远程庭审是一种介于书面审理与开庭审理之间的审判方式,〔27〕熊秋红:《远程庭审有哪些优势与不足》,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27 期。是一种利用互联网及其他信息技术将开庭审理模式搬到在线运作的方式。实践中二者的差异表现在线下仲裁审理的方式通常以开庭方式为主,开庭方式是传统仲裁的最基本模式,书面审理为辅助的一种审理模式;各仲裁机构的网络仲裁规则的审理模式均包含远程庭审以及书面审理两种模式,但是各机构的网络仲裁规则对于审理模式的规定则差异较大,从仲裁庭是否具有强势书面审理权标准可以将审理模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广州仲裁委网络仲裁规则为代表,〔28〕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网络仲裁规则》第24 条规定:“(一)仲裁庭对网络仲裁案件进行书面审理……(二)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庭审、网上交流、电话会议等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但应当确保公平对待各方当事人。”在例外的情形或必要的情形仲裁庭才主动适用远程庭审,一般采取用书面审理方式,而当事人在选择网络仲裁规则的同时也默认了仲裁庭书面审理的审理方式。与强势书面审理权不同,另一种仲裁规则赋予当事人在选择网络仲裁方式后仍有权利选择以何种方式审理,而不是默认书面审理为网络仲裁的审理模式。〔29〕根据《武汉仲裁委员会网上仲裁规则》第38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收到受理通知书或者仲裁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选择网上开庭方式。当事人未选择或者未能选择一致的,仲裁庭采用非同步电子交互形式进行网上开庭。”以上两种有关审理模式的仲裁规定的差异体现在强势书面审理规则更体现仲裁效率特点,但同时也有损害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嫌疑。
最后,在网络仲裁规则上规定了更短的纠纷解决的期间以及线上线下的转换方式。基于追求效率价值,各仲裁机构的网络仲裁规则当中将仲裁程序包含仲裁受理、通知、答辩与反请求以及管辖异议等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期间基本都短于线下仲裁程序。二者的差异还体现在程序变更上。线下仲裁不可以进行程序变更,当事人一旦约定仲裁协议则适用仲裁规则,实行线下审理不得转为在线审理。而网络仲裁规则中均规定程序变更制度,依据庭审需要可将在线仲裁变更为线下仲裁模式,适用一般的仲裁规则。
网络仲裁在实践中的特点:尽管在网络仲裁规则并未具体说明,网络仲裁在实践当中的审理方式也相较于线下仲裁而言更为多元化。根据与技术的结合程度简单划分为三类不同的审理方式,分别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流程在线的仲裁案件以及智能仲裁模式。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仲裁审理模式是网络商事仲裁最原始的模式,早期的文献对于网络商事仲裁的定义就是此种仲裁模式,将其概括为利用网络信息和电信技术,将常规仲裁程序中仲裁机构、仲裁员和当事人三者之间信息的处理与交换、仲裁文书以及证据资料的提交与传递等在尽量不损害其原有的法律内涵的前提下将传统的纸面文书信息与交换改为电子方式通过互联网数字化进行,从而实现无纸仲裁。同时利用同步网络技术即远程通信手段实现案件网上虚拟庭审以及仲裁员之间的网上虚拟合议等其他程序性事项。〔30〕卢云华、沈四宝等:《在线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 页。概括而言,这种网络仲裁方式的审理形式是将线下的部分或全部程序从线下搬到线上,其文书送达、受理、审理、质证、答辩环节与线下仲裁程序的审理环节并没有减少,需要处理的部分程序可能需要将纸质材料转化为电子材料,将传统的面对面开庭转换为通过在线视频等方式进行。在应用方面,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确保在疫情防控期间有效解决纠纷,仲裁机构及法院纷纷推出“非接庭审模式”进行纠纷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规定对于原本并非属于“网络诉讼”的常规案件,由于疫情而不能在线下开庭的,可以在获得当事人同意之后,改为网上开庭。〔3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20071.html,2022年1月10日访问。
其次为全流程在线仲裁案件,该审查模式与上述的网络仲裁审理的差异在于非开庭审查,利用网络仲裁云平台,部分机构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缩短纠纷解决所需花费的时间。在实务当中,此类网络仲裁模式解决的纠纷主要集中在网络贷、手机银行、电子银行等相关的争议解决,上述争议全部程序在网上进行。实践当中全流程在线仲裁案件与上文提及的第一类网络仲裁审理模式的案件相比,其电子数据具有电子化特点,并且其原件表现方式可通过电子签名等技术固化。〔32〕《仲裁之中的技术应用——从网络仲裁云平台到远程视频庭审,以规则、技术优势打造国际商事仲裁“广州模式”》,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网,http://caal.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1064.html ,2022年1月10日访问。
最后一种网络仲裁审理模式为智能仲裁,利用互联网技术、电子通讯技术以及其他计算机通讯技术,智能完成仲裁申请、文档送达、举证质证等环节,减少开庭审理、提高仲裁效率的仲裁活动。过去非智能仲裁已经实现了利用互联网通讯技术进行文件、信息的传递,但是智能仲裁体现在利用前沿技术主动采集包括双方当事人信息、合同主要条款信息、履行情况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智能生成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清单等文件,协助当事人进行仲裁活动,减少需要人工参与的环节,提升效率,〔33〕《什么是智能仲裁》,易保全网,https://www.ebaoquan.org/mobile/news/showNews?newsId=212,2021年9月13日访问。即将部分人工的工作用机器替代,转为自动化完成,此阶段的自动化仍为一种协助纠纷解决的工具。在实务当中,智能仲裁基本处理的案件为目标较小且高度类型化的案件,通过系统的机械“智能”与仲裁员的办案经验相结合实现批量仲裁模式。
(三)网络仲裁程序能否实现接近“数字正义”的分析
网络仲裁的程序能否实现接近“数字正义”,需要通过网络仲裁程序特点是否满足接近“数字正义”三个转变特征进行判断,笔者认为,网络仲裁程序可以实现接近“数字正义”。首先为空间上的转变,在前文所提及的早期文献中,从其对网络仲裁定义显而易见虚拟化是网络仲裁最初始也是最直观的特点。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仲裁程序能实现从“部分”到“全部”虚拟化。
其次,网络仲裁程序符合让科技第四方参与到争议解决当中的特点。以智能仲裁为例,智能仲裁中的技术不仅仅是纠纷解决的工具,还提供了价值判断。譬如智能生成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清单等文件,减少需要人工参与的环节,智能仲裁通过完善智能仲裁系统,对与案件有关的各类数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及分类,意在还原案件主要事实;在法律适用上,云平台累计海量案件,基于大数据技术对案件数据进行对比,系统对法律法规进行精准无误的梳理,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案件评判更加公平公正,合乎规则,并对双方提供的用于支持本方主张的证据基于以往的案例大资料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相关的处理结果及分析意见提供给仲裁庭参考,仲裁庭审核通过后即快速生成法律文书,并及时完成电子送达。〔34〕《智能仲裁的原理》,瀚骏程律师事务所网,http://www.hjclf.com/newsinfo/1181579.html,2022年1月10日访问。在此过程中,科技第四方已经取代部分人工辅助了仲裁庭解决争议。
然而智能化解决争议离不开数据的收集与处理,从而引申出接近“数字正义”的第三个转变——数据的收集与应用。网络仲裁并未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40 条规定,遵循“保密性”原则。部分仲裁机构在其网络仲裁规则上强调“案件数据的在线传输提供安全保障,并采取为案件数据信息加密的形式为案件信息保密”。网络仲裁的保密原则与线下仲裁相比结合了网络传送中数据保密的特点,对于保密要求更高,保密的范围更加宽泛。尽管仲裁机构享有保密义务,但是随着约束性平台与非约束性平台〔35〕约束性平台指的是仲裁机构,非约束性平台是指仲裁机构外的多元争议解决平台。的共同发展,双方开展广泛合作打破信息孤岛。比如,非约束性平台应用哈希值校验、电子签名、可信的时间戳存证以及区块链存证等技术存证保障数据真实性的同时也保障数据传输过程当中的保密性要求,部分仲裁机构也开展了与司法机构签署数据共享协议的活动。但目前而言,网络仲裁被认为仍然处于第三个转变的初始阶段,作为约束性平台,网络仲裁机构之间仍缺乏数据协调、共享与开放机制。法律大数据仍未形成,同时也并未将数据应用于纠纷的预防当中。然而网络仲裁尽管未能通过数据分析预防纠纷,未完全满足接近“数字正义”在第三个转变中预防纠纷特征,但是从整体而言基本符合争议解决当中“数字正义”关于物理、程序辅助以及数据收集、使用的特点。
三、网络仲裁程序司法审查困境及反思
(一)网络仲裁司法审查的实践困境
目前网络商事仲裁审查的案件可划分为两种类型进行讨论:一种是先予执行的案件;另外一种是非先予执行的普通网络仲裁裁决案件。早期网络仲裁的司法审查争论点集中在“先予仲裁”的有效性上,先予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的同时,预防纠纷,双方当事人通过约定特定仲裁机构就合同所涉及的内容提前仲裁的一种商事仲裁形式。此类仲裁主要解决的纠纷为网络贷款纠纷,其模式的运行为确保借贷双方在履行过程中确定其权利及义务,保障借款人权益得以实现,避免签署协议之后贷方违约之时再去仲裁或者诉讼带来的麻烦,因此当事人在签订及履行合同阶段且未发生纠纷前,已向仲裁机构依据双方签订的现有协议作出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早期司法审查拒绝承认与执行先予仲裁的仲裁裁决事由主要围绕着违反法律规定、违反仲裁程序以及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三方面,〔36〕李佳意:《先予仲裁的效力研究》,载《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8年第5 期。而后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作出《关于“先予仲裁”裁决应否立案执行的请示》,对于网络商事仲裁作出的“先予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案件能否作为执行依据,该审判委员会认为“先予仲裁”并不等于民事诉讼法、仲裁法规定的仲裁裁决,不应予以执行。而对于此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作出《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该批复于2018年6月12日施行。该批复支持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观点,认定先予仲裁的仲裁裁决无效不予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先予仲裁”性质并非为法定仲裁模式是因为仲裁的本质在于有争议或者纠纷实际发生,无争议即无仲裁,仲裁的启动必须以实际发生争议为前提。早期司法审查在先予仲裁问题上存在争议,此后有关“先予仲裁”的审查在实践当中基本上不存在争议。
对于非先予仲裁案件目前网络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仍存在争议点,其争议点目前主要围绕在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利的认定上,具体体现在书面审查及电子送达效力的争论。规范性文件有关网络仲裁程序能否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问题,仅仅停留在网络借贷案件。2019年11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规范网络借贷仲裁裁决执行的通知》,2019年12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规范网络借贷仲裁裁决执行及司法审查工作的通知》。根据上述文件,关于保障当事人基础权利的衡量标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网络借贷合同存在通过格式条款免除网络借贷平台和出借人责任,加重借款人责任,排除借款人主要程序性权利情形,仲裁机构未审查的;第二,无充分证据证明已向当事人送达文书告知其基本程序权利的;第三,未给当事人提供合理期限即缺席裁决的;第四,无充分证据证明已向当事人有效送达裁决书或调解书的。其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意见特别指出申请执行人不得约定弃权条款,否则视为无效条约。但是以上规定仅适用于网络借贷案例。而对于其他非网贷案件,关于保障当事人基础权利的司法审查案例存在书面审理以及电子送达方面的争论。在书面审查上,部分法院以仲裁机构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损害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利或类似的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网络仲裁裁决。〔37〕例如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7 执77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2019〕黑1282 执1212 号执行裁定书,还有部分法院以类似理由裁定驳回执行申请,例如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 执285 号执行裁定书、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5 执234 号执行裁定书、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9 执260 号执行裁定书。司法审查意见认为,中国仲裁协会并没有制定相应的网络仲裁规则,同时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均没有对网络仲裁作出具体的规定,仲裁机构通过制定仲裁规则的形式以独任方式不开庭审理,其裁决过程缺乏对被执行人基本程序权利的保障,违反法定程序,不属于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仲裁。在电子送达方面,部分法院的司法审查意见认为〔38〕例如参见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7 执70 号执行裁定书。采取电子送达的方式在未明确表示是否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收到电子送达的材料的情况下,径行认定电子送达缺乏对被执行人的程序权利保障,构成程序违法。
以上反映了在实践当中,网络仲裁程序的司法审查严格按照线下传统的商事仲裁审查标准进行审理。本文认为尽管在实践中司法审查一方面客观上纠正了因网络仲裁程序创新导致的当事人程序权利不足,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审查困境,即如果完全按照线下仲裁程序的审查标准,则容易忽视网络仲裁程序的特点及优势,不利于发挥网络仲裁的效率价值。网络仲裁程序的司法审查困境本质上反映了争议解决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与争议解决效率需求的冲突。
(二)网络仲裁程序司法审查反思
目前司法审查标准说理上存在一定的瑕疵,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5 条、第75条,并未明文禁止仲裁程序不得在线进行、书面审理等程序,并且授予仲裁机构在不违反《仲裁法》等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自主制定仲裁规则的权利。此外,当事人在协议当中约定通过网络仲裁的方式解决该争议,双方一旦形成合意意味着接受了仲裁规则上一揽子约定。理论上认为,对于类型化的意思自治应予以认可,在审查的时候不能仅仅关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忽略仲裁机构自治与仲裁庭自治。〔39〕刘晓红、冯硕:《论国际商事仲裁中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冲突与协调——以快速仲裁程序中强制条款的适用为视角》,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2018年第5 期。因此,司法审查标准以中国仲裁协会、法律法规并未制定相应的网络仲裁规则为由否定网络仲裁裁决效力,存在一定的说理瑕疵。
其次,当前司法审查标准忽视了网络仲裁程序接近“数字正义”的价值。笔者认为,网络仲裁程序上的监督不能完全按照线下仲裁的审查标准对线上仲裁进行监督。在数字经济时代,科技改变了一定的经济运行模式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线上等纠纷,传统的争议解决机制不能完全满足大量争议解决;同样在司法审查上若按照传统的司法审查标准对网络仲裁程序进行监督,表面看似保障当事人程序的绝对公平,实际上忽视了对于大量的线上、小额等纠纷难以通过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争议的事实,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接近正义。基于前文网络仲裁程序符合接近“数字正义”的三个转变特点表明网络仲裁可以实现接近“数字正义”。因此在司法审查标准的设定上也需要从接近“数字正义”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应当促进网络仲裁更大化地接近“数字正义”,让更多的争议通过技术与正义机制的结合得到广泛与高效地解决;另一方面关注“数字正义”带来的潜在问题——例如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算法歧视致使的结果不公以及数据等问题。
四、网络仲裁程序司法审查的建议
司法审查应如何关注网络仲裁的接近“数字正义”同时保障程序及实体上的公平?不同网络仲裁审理方式所具备的争议解决能力以及存在的潜在风险具有差异,其审查标准需要具体分析。本文认为司法审查应该根据不同的网络仲裁审理方式设定相对应的审查标准。因此从可行的路径上出发,首先需要划分不同仲裁审理模式的适用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仲裁审理方式存在接近“数字正义”的潜在风险制定司法审理标准。
(一)规范网络仲裁审理模式的准入范围
网络仲裁存在三种不同审理模式。本文对比我国部分仲裁机构网络仲裁规则,发现仲裁机构并未对不同模式作出相对应的适用条件,仅有“当事人约定”或者“因网络交易产生的争议及非因网络交易产生的争议”〔40〕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网络仲裁规则》第4 条。的广泛性规定。然而不同的审理模式在程序上规则的规定、空间的转变暗含影响当事人的感知与行为会影响到程序及结果,在仲裁规则当中划分准入适用范围具有必要性。
首先,对于智能仲裁的准入适用条件最苛刻,其适用范围应当集中在大量且重复率高,能被机器所识别判断的法律纠纷。因为智能仲裁的可审理范围受限于数据(案例)挖掘的能力以及算法应用能力。数据挖掘问题方面,民事仲裁具有保密性特点,多数情况下仲裁从立案到裁决都具有保密性。与司法大数据不同,保密性特点增添了实现对仲裁案件的数据挖掘的难度,使得智能所需要的训练集受限。有限的训练集将其审理范围局限在可提供的类型有限且数量巨大的仲裁案件。然后是算法的应用能力,算法与上述数据训练集相联系。算法只是用以决策的程序与公式,为一个机械化的循环计算过程,〔41〕Rich M L.,Machine Learning,Automated Suspicion Algorithms,and the Fourth Amendmen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2016:871-929.将输入转换为输出的指令序列,换言之算法难以理解复杂案件背后的价值判断问题,例如部分纠纷还需要注重当事人心理活动。若争议涉及当事人复杂的心理活动及诉求,则不适用智能仲裁。此外,算法的不透明还可能会导致算法歧视,从而最终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无法应用于所有的案件类型。
其次,对于全线上仲裁模式而言,其准入范围应围绕数据(证据)的产生等状态以及法律关系复杂程度划分。前者是因为物理空间的转变结合区块链等加密技术查证证据三性的难易程度决定,线下产生的证据,例如传统的线下合同纠纷,有可能涉及大量纸质货单,甚至需要进入质量鉴定程序,上述情况下,并不能麻木运用网络商事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麻木运用网络仲裁甚至通过书面审理的方式进行审理,显然难以查明证据三性。相反,在线发生的纠纷所涉及的合同签订、合同履行、证据形成均在网络上,呈现出的电子化、数据化特征,通过目前加密技术保障其真实性。而后者则是出于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角度考虑,复杂的法律关系若通过书面审理则难以查明,需要充分保障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
最后是线下仲裁网络化的审理模式,其适用范围最为广泛。其本质属于线下仲裁的网络化,适用范围仅为不能突破《仲裁法》强制性规定以及目前网络仲裁规则的规定,即可仲裁范围不可突破《仲裁法》第2 条、第3 条的规定范围。相应的网络商事仲裁的可仲裁范围也需要在法定的可仲裁范围内,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此外,出于公平原则而言,线下仲裁网络化的审理模式还受限于网络仲裁条件,例如当事人约定网络仲裁的,应当具备网络仲裁所必需的设备条件及技术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使用电子邮件及其他电子通讯工具、参加网络视频庭审等)。〔42〕根据《深圳国际仲裁院网络仲裁规则》第5 条。若不满足条件则转换为线下仲裁模式审理。
(二)依据审理模式的差异划分不同司法审查标准
基于以上仲裁审查准入使用范围,根据审理模式划分不同的审查标准及侧重。首先,对于智能仲裁的审理,应更侧重数据挖掘范围及算法标准。智能仲裁与其他两种审理模式的明显区别在于部分程序上应用算法取代人工干预,即技术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而是提供了一定的价值判断;保障当事人能获取最终结果公正的正义解决的关键侧重于算法应用,追求争议解决的效率,甚至随着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取代部分程序而不影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及结果正义。智能仲裁在程序审查标准不必严格按照线下仲裁程序标准审理,但是需要侧重关注在此过程当中所涉及的数据的挖掘以及算法标准。具体而言,司法审查首先需要留意数据集合是否具备时效性,有无因数据集合无法及时更新从而产生的算法偏见问题,在此过程当中司法审查需要对算法进行审计、评估与测试。
其次,对于第二种网络仲裁模式而言,证据平台更关注效率带来的公平价值。其可审理范围围绕着证据,依靠区块链技术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举证质证环节,在此基础上简化部分程序并不会导致结果有失公平。这体现的是一种通过提高效率而实现公平的纠纷解决机制。
最后,对于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体现在将线下纠纷解决转移到在线环境解决,本质上还是传统的仲裁模式。在疫情期间,部分法律关系复杂原本为线下仲裁的案件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搬到在线视频进行解决,保证了纠纷不受到疫情影响而拖延审理。此类仲裁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涉及法律事实难以查明以及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因此需要充分保障当事人等基础的程序性权利,仲裁庭及仲裁员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答辩意见,对证据进行充分举证及质证。相应的按照严格的线下仲裁的司法审查要求承认与执行此类仲裁裁决。
(三)司法审查需关注争议解决当中的数据保护与共享
司法审查对于仲裁程序的监督不应仅仅涉及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审查,还需要关注网络仲裁在争议解决当中衍生出的数据新问题。接近“数字正义”强调的第三个转变,从精简数据及数据保密转变为关注数据收集、使用和反复利用。网络仲裁依托网络仲裁平台解决纠纷,网络仲裁平台(也称为“网络仲裁服务平台”“网上仲裁云平台”)是网络商事仲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平台运行当中所产生大量数据被收集、使用和反复利用。网络仲裁在广义上属于商事仲裁,并未突破《仲裁法》的强制性规定,需要遵循保密原则,根据《仲裁法》第40 条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换言之,在没有得到纠纷当事人一致允许的情况下,仲裁机构在整个仲裁案件处理当中,只允许仲裁庭成员及秘书、双方当事人、仲裁参与人(包括当事人的代理人、证人、鉴证人、翻译人员等)参加,审理过程不允许他人旁听,裁决结果不公开,全程亦不允许新闻媒体采访与报导相关案件的内容。网络仲裁的保密原则与线下仲裁相比结合了网络传送中数据保密的特点,对于保密要求更高,保密的范围更加宽泛。其强调“案件数据的在线传输提供安全保障,并采取为案件数据信息加密的形式为案件信息保密”。但是随着约束性网络仲裁平台与非约束性网络仲裁平台合作,同样与司法机构签署数据共享协议,仲裁信息需要得到保密的同时也需要得到有条件的共享。司法审查在监督上需要平衡网络仲裁数据的保密与共享界限。从整个仲裁监督体系而言,司法审查是仲裁监督最后一道防线。在数据保密与共享机制的划分标准而言需要划分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司法审查需要在强制性义务的范围内有限度介入该领域的监督。
结语
目前网络仲裁部分司法审查案例体现了司法机关以审慎性标准审查网络仲裁程序,具体表现为其按照线下仲裁的司法审查标准审查网络仲裁程序,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然而如果完全按照线下的司法审查标准容易导致忽视网络仲裁程序的特点,该审查标准从而无法完全发挥网络仲裁的效率价值,不利于网络仲裁的发展。本文认为,网络仲裁的司法审查标准需要结合网络仲裁的特点,平衡网络仲裁程序权利价值以及争议解决效率价值。数字正义强调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接近”,并且需要保障合理、合规的数据、算法技术应用实现“正义”。首先,数字正义强调争议解决的三个转变特点,第一个就是空间上从物理空间转变为虚拟空间中解决争议;其次,科技从一种争议解决的工具逐步转变为解决争议的科技第四方;最后涉及注重数据的收集与反复利用。网络仲裁程序特点基本符合了接近“数字正义”理论中强调的三个转变特点,本质上是一种接近“数字正义”的体现,同时也存在接近“数字正义”的潜在风险。相对应,司法审查标准一方面需要发挥接近“数字正义”的价值,同时需要关注接近“数字正义”过程中潜在程序权利保障、算法正义以及数据等方面的问题。针对目前网络商事仲裁程序的司法审查存在的不足,结合理论及实践情况,其完善路径为首先根据网络仲裁三种审理模式规范其准入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审理模式制定不同的司法审理标准,灵活监督网络仲裁程序保障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利及其效率价值,最后司法审查不仅仅需要关注网络仲裁程序本身,还需要关注到程序当中衍生出的数据收集与利用问题,划分网络仲裁数据的保密及共享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