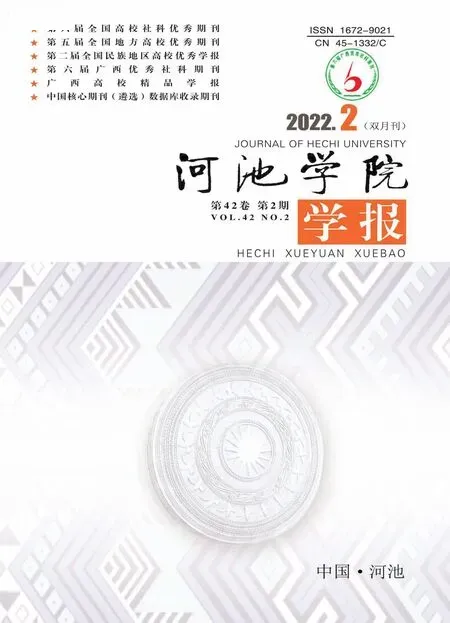论壮、汉民族语言共生的成因、表征与价值
韦亮节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广西壮族自治区常住人口中,壮族人口占31.36%,汉族人口占62.48%①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详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官方网站《广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网址:http:∥tjj.gxzf.gov.cn/syyw/t8851196.shtml.,壮、汉民族共占自治区总人口的93.84%,所以搞好壮、汉民族关系是广西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关键,也是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中之重。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再一次明确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1]。这个赞誉将激励广西继续发挥民族团结的示范作用。民族团结是多重因素合力的成果,语言共生是关键因素之一。所谓语言共生,即“不同区域、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语言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相互尊重与交流、兼容并包、和谐发展的语言文化形态”[2]。在我国民族杂居地区,语言共生主要指各民族语言不但共生并存,而且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都得以较好使用。单就广西而言,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是广西语言文化形态的主体。故而,本文拟探讨哪些原因造成壮、汉民族语言共生,语言共生有哪些表征,语言共生在新时代又有哪些价值?
一、壮、汉民族语言共生的成因
(一)语源密切奠定语言学基础
邢公畹系列文章②其中《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luk试释》《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出自《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别离”一词在汉语台语里的对应》,载于《民族语文》1983年第4期;《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的研究》,载于《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台语-am、-ap韵里的汉语“关系字”研究》,载于《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从调类、助词、构词法、复辅音声母等不同角度探讨汉语(广州话)与台语(包括壮语)的密切关系。戴庆厦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角度出发,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并加以论证,认为“粤语中存在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壮侗语)成分,这是形成其独特个性的重要因素”[3]327-343。李锦芳对广州话中的诸多实例进行分析,认为粤语中的部分词语是壮侗语言的底层词,即粤语吸纳了部分壮侗语词汇,如[a]韵中表示“找、摸索”“占、张开”“说”“雌、母”“对儿、双生”等词,[am]韵中表示“跺(脚)”“倒塌”“软”“蜘蛛”等词,[ap]韵中表示“眨(眼)”“罩、扣、盖”“咬”“欺负”“蛙”等词,[ε]韵表示“(广)批擦、蹭,(壮)舔”“背负”等词,[ou]韵表示“老人,成年男性”“不、没”等词,[ɔ7]韵表示“竖立”“垫、架起”“洗涮、漱”“傻”“小母鸡”等词,[i]韵表示“别、不要”“这”“一点儿”等词,[uk]韵表示“柚子”“(猪)圈”“扎、捅”等词,[a:m]韵表示“刚好、合适”“跨”“蟒蛇”等词[4]。班弨认为在收录约7 000词条的《广州话词典》中可确认215个侗台语(壮语)底层词,如“跺”“打”“肥”“秆儿”等[5]。黄小娅从语言文化学出发,主要探讨了“栏”“墟”这两个广州方言中的底层词,“通过对它们在广州方言中的留存、变异以及衍生出来的系列词语的考察,不仅可以探索它们从少数民族语言(壮语)进入到汉语的过程,更能深入地了解粤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6]。蒙元耀的《壮汉语同源词研究》[7]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壮、汉语中语源相同的词汇,着重探讨了身体部位类的头部、躯干、内脏、四肢的名称词,动物名称类的兽类、鸟类、水生类、爬虫类、渔猎手段的名称词,植物名称类的竹木、果类、花草、农作物的名称词,日常事物类的天象、建筑、日用器物的名称词。无论是壮语与粤语还是与古代汉语,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提供了语言学基础。
(二)空间互嵌提供现实可能
首先,跨民族通婚家庭为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提供了最小的互嵌空间。笔者2020年以来跟踪调查广西忻城县思练镇新练村板朝屯的一个跨民族家庭:户主WCS为壮族男性,其妻QXZ为高山汉(当地亦称“湖广人”),二人育有一儿一女(皆为壮族户籍)。WCS与QXZ之间,QXZ与其儿女之间的交流均使用汉语(湖广话与桂柳话夹杂使用),而WCS与其儿女交流时则使用壮语。WCS与QXZ组成小家庭前,其与父母等村中壮族亲属的交流使用壮语。而与QXZ结合并有了儿女后,小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习惯发生了变化,成为较典型的壮、汉双语家庭。其次,某些多民族杂居的村落为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提供了更大的互嵌空间。罗彩娟考察广西象州县的纳禄村“纳禄两头贾”的居住格局后指出,该村在语言上交流互通,主要是该村落内壮族人普遍使用汉语的现象[8]。黄凌智、黄家信则考察了桂西村落间的族群分布关系,他们发现稍晚迁入壮族世居地的高山汉形成了族群岛,而在高山汉的族群岛内还存有壮族村落,形成了民族居住空间与民族关系的“岛中岛”[9]。显然,村际的民族互嵌为壮、汉语言共生提供了村际空间。再次,乡村集市(又称圩场,壮语称haw,音近“贺”)为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提供了互嵌式交流空间。圩场是广西乡村地区一定范围内人们从事商品交易、信息互通、娱乐消费等活动的重要场所。笔者2021年考察广西忻城县的圩场发现,无论是壮族还是汉族,为了照顾对方的语言习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往往愿意使用对方民族的语言,如壮族长者在购买商品时,汉族卖家往往会用不太标准的壮语与之交流;同样,对于用汉语来讨价还价的购买者,壮族摊主也会用汉语来与之交谈。总之,壮、汉通婚家庭、杂居的村落或村际、圩场等民族互嵌空间为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三)民族“互化”排除民族障碍
罗彩娟把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汉族的少数民族化合称为民族“互化”[10]。在广西,壮、汉民族的“互化”现象较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为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排除了族际障碍。质言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受对方民族文化的濡化,杂居地区的壮族与汉族已相互认同,故而很自然地使用对方的语言,从而促成壮、汉民族语言共生。就壮族的汉化而言,其历史由来已久,土司时代的壮族土司们就攀附汉裔,如思陵州韦氏、东兰韦氏、恩城州赵氏、龙州赵氏、南丹莫氏、罗阳黄氏、安平州李氏、下雷州许氏等土司均称其祖源于山东青州府,思明府黄氏自谓其祖源于湖广黄州,忻城莫氏言其祖迁自江南太仓,田州岑氏言其祖源于浙江余姚,那地州罗氏称其祖自江西迁来[11]59-648。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壮族民间对汉文化的吸收,使得诸多壮族民众自觉使用汉语,自主学习汉文化。现今杂居地的某些壮族村落就出现完全讲汉语而不讲壮语的现象。而讲壮语的壮族村落中,某些家庭也有意识地让孩子学习壮、汉双语。就汉族的壮化而言,主要与广西历史上的汉族移民有关。古永继认为元朝时迁入广西的有蒙古、色目和汉族人,明朝则以汉族人为主兼有部分蒙古族、回族人,清代主要是汉族人并有少量满族、回族人。元明以军事移民为主,而清代主要是经济移民[12]。这些入桂的汉族人后来部分被壮化。忻城县地名志记载,该县思练镇练江村的大板荒屯(现改名为“大进屯”)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李氏始建,祖籍广东”,而属思练镇新练村的六闷屯为“清康熙年间李氏从大板荒迁此始建”[13]58。显然,此二村的李氏是清朝时的广东经济移民。笔者2021年暑假实地走访了大进屯(原大板荒屯)与六闷屯,发现大进屯杂居有罗、黄、卢、蓝、麦、钟、韦、郑、梁等姓壮族,而六闷屯杂居有莫、韦、黄、唐、蓝等姓壮族。在长期的杂居中,这两个自然屯的广东李氏已完全壮化,民族成分均已改为壮族,通村使用壮语,文化习俗与当地壮族无异。总之,在民族“互化”过程中,壮、汉民族自觉排除民族属性障碍,自然而然地运用对方语言,所以造就了语言共生现象。
二、壮、汉民族语言共生的表征
(一)语言共用:“夹汉”与“夹壮”
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最生动的表征在于日常的语言运用中。语言实际中,部分母语为汉语的人讲壮语时会出现“夹汉”现象,而部分母语为壮语者在讲汉语时则会出现“夹壮”现象。这种语言“互夹”现象表明语言共生的活跃性。一方面,如以汉语为母语的圩场摊主、汉族干部、嫁入壮族村寨的汉族媳妇在使用壮语过程中,由于不会使用某些壮语词汇,本能地将该词汇所对应的汉语直接镶嵌到句子中,形成了夹杂着汉语词的句子表述。现实交际中,由于熟悉对方的语言背景,开放包容的壮族人并不认为这种“夹汉”现象有何不妥,而会在交流过程中主动帮助语言“夹汉”者修正。此外,部分壮族民众沉浸在某种普通话环境与诸多汉语媒介之中,会对一些不经常使用的壮语词存在瞬间遗忘现象,为了成功交流,他们有时也会用相应的汉语词来替代,从而造成“夹汉”现象。另一方面是壮族人讲汉语时的“夹壮”现象。这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王均、蒙元耀、梁敏、陆文富等人较早就“夹壮”问题展开了探讨①这些研究主要有王均等人著的《壮语及壮汉人民怎样互学语言》,民族出版社,1979年出版;蒙元耀著《“夹壮”成因》,载于《民族文化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梁敏、张均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民族语言的互相影响》,载于《民族语文》1998年第3期;陆文富《浅谈壮族同胞汉语普通话中的“夹壮问题”》,载于《关于提高壮语地区教学质量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覃凤余调查发现,以壮语母语者(泛指跨民族的壮语使用者,如广西某些地区的汉族、瑶族、仫佬族等就以壮语为母语——引者注)讲汉语方言的情况为:讲官话者有33.11%,讲粤语者(广西白话)39.56%,讲客家话者1.71%,讲平话者桂北有0.33%,讲平话者桂南有3.69%[14]107。在汉语的使用中,“夹壮”现象时有发生。杨玉国认为:“说壮话的人说的‘夹壮’这种不标准的普通话不是汉语的方言(或地域)变体,而是汉语普通话的一种民族变体。”[15]340语言的“民族变体”就是语言共生的一种重要体现,它揭示了民族间在语言文化上的深度交流。总之,“夹汉”与“夹壮”现象表明人们在语言文化交流中是互相学习与促进的,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各民族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文字依存:汉字与古壮字
文字是语言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壮、汉民族语言共生必然表征在文字上。由于长期的历史交流,壮族民众对汉字的学习较为深入。然而,汉字所表示的汉语与壮族人所使用的壮语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为了更好地表示壮语,壮族人借鉴汉字的基本形态与造字方法,创造了一种“类汉字”文字——古壮字(又称“土俗字”或“方块壮字”),故而在壮族地区出现了汉字与古壮字的共生现象。汉字与古壮字的依存关系如下:如壮族人仅借汉字笔画“乚”之形以象壮族生活中的勾子,故造就读ngaeu、表“勾子”的古壮字“乚”;仅借汉字“古”的读音以表示读gou/gu、表“我”的古壮字“古”;仅借汉字“歌”的意义表示壮语语境中的山歌,造就读fwen、表“歌、山歌”的古壮字“歌”;借汉字“金”的粤语读音(gam1)与意义以表壮语读gim、表“金子”的古壮字“金”;借汉字偏旁“艹”的意义(表植物类范畴)与汉字“勾”的读音,通过形声造字法,构成读gaeu、表示“滕”的古壮字“芶”;借汉字“水”的意义与汉字“口”的意义,通过会意造字法,表出水之口,造成读mboq、表“泉”的古壮字“呇”;借汉字“了”的形以表以左为前、以右为后的人形,借汉字笔画“乀”表示与“了”相对的位置,通过指事造字法,造就读laeng、表“后、后面”的古壮字“孓”;等等。此外,韦庆稳认为《越人歌》可用壮语加以解读,且该歌词只有一个音义双借字(占3.00%),其余全是汉字的借音字(占97.00%)[16]23,说明古老的汉字歌本中也蕴含古壮字。覃晓航统计了清代古壮字抄本《唱舜儿》(全书2 450个字),认为通过汉字造成的古壮字占76.33%(1 870个),音义双借字占23.67%(580个)[17]80-81,表明壮族歌本中,直接借用的汉字比例相当高。总之,古壮字与汉字拥有不可分割的渊源,说明文字依存是壮、汉民族语言共生的重要表征。
(三)文本互生:汉族书籍与壮族歌本
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更宽泛层面的表征是壮族与汉族民间所阅览文本的互生并存,也就是说在广西壮、汉民族杂居地区,人们既会阅读汉族书籍,而壮族民众又会利用古壮字编制壮族相关民间歌本,且部分壮族歌本是汉族书籍(特别是民间故事)的壮族化书写。笔者自2019年至今,先后在忻城县民间搜集到的古壮字歌本共60余部,其中部分故事歌本就源于汉族书籍,如秦朝汉族民间传说《孟姜女》的壮族歌本为《孟姜女与范喜良》,元朝郭居业的《二十四孝》故事之“孝感动天”被演绎为壮族的《顺(舜)儿故事》,明代洪楩编的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被改编为《董永和仙女歌》,清朝如莲居士的“薛家将”系列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所衍生出的古壮字歌本分别为《薛仁贵征东歌》《薛丁山征西歌》《反唐》,汉族剧本《李旦兴唐》(潮剧)、《铡美案》(楚剧)、《四下河南》(楚剧)也分别被再创作为壮族的《李旦壮歌》《秦香莲》《四下河南》等。虽然汉族书籍用汉字写就,而壮族歌本用古壮字书写,但是二者所书写的内容紧密相关。在同一个故事母题的不同民族文学演绎中,人们可以在文学乃至文化上相互吸纳,并最终使他们的审美情趣、情感价值等不断趋同;而作为载体的壮、汉民族语言文字自然在书写、阅读、吟唱中获得共生。
三、壮、汉民族语言共生的价值
(一)促进壮、汉民族杂居地区的团结协作
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打破民族间的语言壁垒,消除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中,由于语言不通、文化相异,某些汉文献记载包括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时多用“犭”加以贬低,如壮族曾被封建统治者称为“獠”“獞”“狼”。历代汉官文士对壮族文化习俗的相关记载多出于猎奇的文化心态。如宋人周去非记载壮族人的“巢居”时称:“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唯有一牛皮为裀席,寝食于斯。牛豕之秽,升闻于栈罅之间,不可向迩。彼皆习惯,莫之闻也。”[18]155显然,这是对壮族传统干栏建筑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的记载,因与汉族异,故认为牲畜的气味令人难闻。又如,清人王言纪所编《白山司志》记录白山司(今南宁市马山县)腌渍酸笋的场景:“四五月采苦笋,去壳置瓦坛中,以清水浸之,久之味变酸,其气臭甚,过者掩鼻,土人以为香。”[19]这是对壮族独特腌食的记载,因与汉族相异,故称“其气臭甚,过者掩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政策,让壮、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真正平等,壮、汉民族语言可以顺畅运用,故而壮族传统建筑与饮食等渐渐被汉族民众所接受,如以酸笋为配菜的柳州螺蛳粉不仅深受广西各民族人民所喜欢,而且还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此外,语言共生还能促进壮、汉等民族在生活中的协作。广西乡村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语言互生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民族间的文化与心理距离,可促进小到结朋交友、信息分享,大到经贸合作、政务办理等事务。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壮、汉民族杂居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需要壮、汉等民族积极协作,从而达成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
(二)促进壮、汉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发展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共生不但保障了民族间语言的多样性,而且使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得以有效传承与发展。如壮族民间传说人物歌仙刘三姐(又称刘三妹、刘三姑、刘三娘等)的故事遍及广西、广东及周边地区,1960年苏里导演的电影《刘三姐》更是将壮族刘三姐的故事传播到全国各地。故事的流传主要通过语言来传播,壮、汉民族语言共生使传播成为可能,传播之后还需要跨民族语言再创作,加上地域民族的主体想象,才使得刘三姐这个文化意象得以落地生根。可以说,语言共生与故事的借鉴,使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壮族歌谣文化得以在壮族以外的民间传播,壮族喜爱唱歌的民族性格也对其他民族有所感染。又如历史悠久的稻作生产催生了壮族的“那文化”,直接体现在某些含“那”(或写作“纳”,即壮语“水田”之意)的壮语地名上。虽然这些含“那”的地名现均用汉语加以规范,但壮、汉语言共生使人更容易知晓这些地名所承载的地方文化意涵,如百色的那坡(Nanzbox)县,即坡地上的田(或梯田)的意思。壮族地区使用汉族语言文字、学习汉文化,除了民间改编的汉族故事之外,壮族作家也大量用汉语进行创作,如陆地创作《美丽的南方》《瀑布》等作品,韦其麟在壮族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写就叙事长诗《百鸟衣》,韦一凡创作《劫波》《被出卖的活观音》等小说,黄佩华创作《瓦氏夫人》《生生长流》《杀牛坪》等小说,凡一平创作《一个小学教师之死》《跪下》《寻枪记》等小说,韦俊海创作《大流放》《春柳院》《异性的土地》等小说与诗集。总之,语言共生较好地弘扬了壮、汉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与创作,促进了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发展。
(三)促进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民族工作提高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45-51的高度。对以壮、汉民族为主体的广西而言,语言共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促进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谓共同体意识,就是特定聚合关系中的成员,在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基础上所具有的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凝聚意愿。”[21]一方面,壮、汉民族语言共生使这两个民族在“特定聚合关系”中拥有“自我”与“他者”意识,使具有差异性的民族文化得以较好保存;另一方面,在壮、汉民族语言共生地区,无论是非壮族人讲壮语,还是非汉族人讲汉语,人们都将语言视为一种交流工具和用语习惯,而不会刻意区分语言背后的民族属性,因为成员们更在意他们所处的“共性条件”以及共同拥有的“共善价值规范”。例如,壮、汉语言文化中共有的孝文化就是一种共善价值规范。壮族孝子一般被称为童灵、东英、东行、通灵等,主要出现在《么(唱)童灵》《东英大孝》等民间文本中,其故事内核基本一致:古时食死人肉,孝子受黄牛(或水牛、羊)产崽痛苦的启发而感孝于父母,待其母(或父)死后偷偷下葬,不给众人分食,将食葬之风改为土葬。澳洲学者贺大卫(David Holm)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壮族古代中的孝子名称实际上是对汉族孝子“董永”名字的借用[22]。有意思的是,壮族版董永故事则把壮族孝子改食葬故事又添加在汉族孝子董永身上,如上述的忻城文本《董永和仙女歌》。此外,在语言共生与转化中,壮族还与汉族一样形成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如笔者收集来自忻城县的古壮字歌本中就有壮族歌者赞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文本,如《共产党解放歌》《共产党新歌》《解放军为人民战斗而解放》《铭记党恩情山歌》等。显然,语言文化的共生与互通使壮、汉民族深刻意识到“自我”与“他者”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且在共性条件与价值规范下自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3]广西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各种正确观念的树立、对中华民族等的认同都离不开语言这个重要中介,所以,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重要前提。研究发现,壮、汉民族语言共生源于语源关系密切、空间互嵌、民族“互化”等因素。壮语与汉语的跨民族共用,汉字与古壮字的依存,汉族书籍与壮族歌本的互生是壮、汉民族语言共生的重要表征。语言共生促进了壮、汉民族杂居地区的团结协作,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讨壮、汉民族语言共生不但契合新时代的国家民族工作要求,而且可在语言接触、地方文化、区域经济等向度上为广西壮、汉民族杂居地区未来的发展提供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