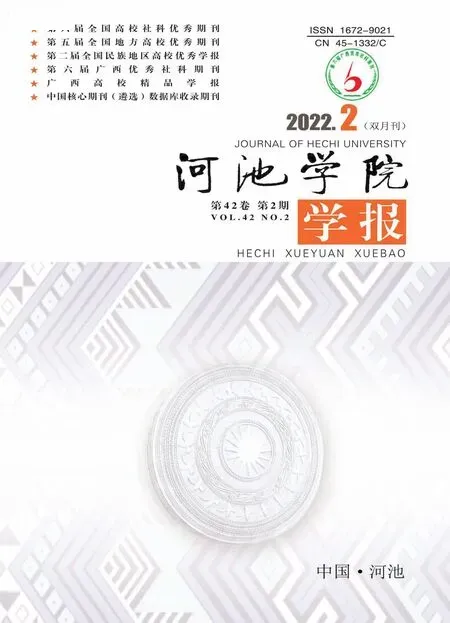诗意·隐喻·个人化: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的叙事空间
姚志林,王 慧
(1.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广西 桂林 541199;2.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河池 546300)
恩格斯曾指出:“任何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及时间,离开时间的存在和离开空间的时间,是同样的大的荒唐。”[1]55电影的存在以及艺术表达都依赖于空间和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就是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艺术,只不过在某些电影类型中,空间表现的分子展现比时间分子更为活跃。电影“善于把时间性叙事转换成富有视听冲击力的空间性叙事,即善于在线性叙事的链条中寻找营造空间意象的一切机会,通过强有力的叙事空间的表现,来把故事讲得富于情绪感染。”[2]18电影的空间性叙事较时间性叙事而言更执着于通过营造空间意象来增强情绪感染力。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本文研究对象仅限于真人演绎长故事片)也惯于进行空间建构,特别是强调对诗意空间的构筑。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如《童年的稻田》(2011)、《天琴》(2013)等作品,无论是从影片空间、场景空间、镜头内空间或者是从镜头空间、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间都呈现出了一种个人化、隐喻性的诗意。这种个人化、隐喻性的电影诗意既有着诗电影的内涵,也有着后现代主义电影空间叙事的个性。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表征的空间与艺术家创作的联系是较为紧密的,“表征的空间是生活的空间,是象征和意象的空间,常常与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相关。”[3]30因而电影的诗意性和隐喻性则更多地体现在表征的空间之中,正是因为表征的空间与艺术家创作联系得更为紧密,因而其也更易于产生个人化的印记。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的诗意空间,也是一种对表征的空间的展现。这个空间有着诸多的话语蕴藉和隐喻性特征。而电影中并置、重复、闪回、象征化、意象化等手法则是营造诗意空间、增强话语蕴藉的重要方式。通常,这个诗意的空间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异托邦的民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们惯于在电影中以民间视角去观照整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在电影中,创作者们独特的文化心理、文化立场以及自由的表现形式,造就了一个主观性较强的民间化诗意空间。
一、一种碎片化的隐喻呈现
“电影是表现诗意的最有力的手段。”[4]61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有着明显的诗意性。这种诗意性与空间的隐喻性是暗合的。电影的诗意性赋予了空间隐喻一种碎片化的表征。此种碎片化空间隐喻,因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又有着零散化、无序性、模糊化的特征,整体“表现为空间的流动和分裂。”[5]280在叙事空间上,这种艺术表现刻意强调复调与间离,并以淡化情节、并置、闪回、陌生化、主观介入等方式达成结构上的零散和主旨上的多义。换而言之,电影从富有诗意的镜头空间开始,通过蒙太奇空间的技法来营造富有隐喻性的意象空间,最终形成一个多义而复杂的意境空间。由此看来,这也是一种富有隐喻性的表征空间。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诗意空间的基本架构是这样的:物理空间——镜头空间——意象空间——意境空间——心理空间或者画外空间。在对这几层关系的建构中创作者常以抒情化、意象化的手法,诗式的结构和独特的蒙太奇表现(偏重于运用表现性蒙太奇)来构筑一个碎片化的象征空间。
电影中并置手法的运用在塑造碎片之时也丰富了空间诗意的内涵。这种表现手法的表层呈现出一种断裂和重复之表象,却又有着构筑强调、多义表达之内核。电影《壮乡木棉红》(2010)以平行蒙太奇的形式将同一时间不同场景的事件并置,同时又通过将“木棉红——人——生存”这个关系链进行“叠化”处理,构造了一种多层次、多义化的表征空间。在电影《童年的稻田》(2011)中,创作者同样不以一个完整而有序的镜头语言来进行叙述,反而以抒情化的镜头语言和诗性(无序)的结构加以凸显。从造型空间上看,创作者强调以写意、唯美、朦胧的格调来打造一个异托邦的诗意空间。同样在《月色》(2017)、《童年的稻田》(2011)、《天琴》(2013)等电影中,创作者们看似执着于追求营造镜头的空间诗意,实则他们更是希望达成一种隐性诗意即情感空间的诗意、心灵空间的诗意。电影《月色》(2017)中的月色内涵是零碎且多义的,月色是不同物象的隐喻,不同物象的杂糅似乎使得这个表征的空间是零散的,而其呈现的主题却又是同质的。与之类似,在电影《天琴》(2013)中,天琴以复现式蒙太奇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叙事时空之中,创作者将叙述的中心聚焦于天琴,却无形之中又割裂了时空,而电影中刻意打破某种连贯性的主观介入也使得电影本身具有了某种断裂感,这种断裂感在看似无序的空间表征之中又具有一种诗意的表达。
在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的部分作品中表现性蒙太奇的表达是有意在碎片化中寻觅诗意。这种诗意性因为重于强调情感和意境,所以少了历时性的时间线索,多了几重共时性的空间诗意。上世纪80年代处于探索时期的广西少数民族电影出现了《雾界》(1984)、《鼓楼情话》(1987)、《神女梦》(1989)等佳作,这些电影也有着显著的诗意特质。这个时期的诗意性表征中心是较为明显的,从电影的叙事空间来说,其叙述是有序的。它们相较于新世纪早期的部分作品如《碧罗雪山》(2010)、《天琴》(2013)也少了一些消解的意味,多了一种民族志式的叙事表征。而新世纪以来的广西少数民族电影在空间诗意的表达上似乎更倾向于对一种碎片化情感流或是一种意识流的营造,也更乐意从电影内部去渲染或者构筑一种独特的意境。与上世纪80年代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相比较,新世纪的作品似乎也更希望去强化一种情绪化和意象化的表达,由此在艺术呈现上也就形成了某种层面上的碎片性的表征。这种诗意性消解了线性时间,也消解了叙事中心,故意淡化戏剧核的在场作用,在叙事空间上它整体呈现了无主轴、无显性线索串联的表象,而在表征空间、造型空间上又裹挟着某种“偶然性”与“拼凑感”。
电影复现式蒙太奇的运用对这个诗意空间的达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复现式蒙太奇空间在镜头空间里具有一种前后呼应的串联效果,使得看似松散而碎片化的结构又具有了些许内在的关联。在诗意空间的叙事中,并置、重复也是电影营造碎片化隐喻的重要手法。电影《童年的稻田》(2011)中,稻田镜头的多次出现,构筑了一种复现式的镜头空间。这种间断性的重复、并置和叠化,既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散文诗式的形态,又在间断性的强调与复现之中达成了多义的效果。因此,在这部电影中复现的稻田意象很直观地给读者构筑了一个包含生命意识、生活诗情、民族生存镜像等多种主题寓意的话语空间(即画外空间)。
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从物理空间到镜头空间,再到象征空间都刻意营造一种碎片化的隐喻。镜头空间看起来是无序且非逻辑性的,但其表意的内在空间又是自洽且合理的。电影通过镜头来表达一种情感或者构造一种意境,这是一种偏于感性的表现手法。情感流是其存在的基础,这也使得这些电影又充斥着一种对非理性、无序性以及偶然性的独特呈现。
在镜头空间的声画造型上,《童年的稻田》(2011)以高饱和的暖色调为主,辅之以抒情的、轻缓的纯音乐,营造了一种温暖、平静、舒适的氛围。创作者也藉由此营造了一个清新、淳朴的意境空间。与之类似,电影《月色》(2017)中构筑的关于月色的情景空间也是重于对一种意境的渲染,整部电影裹挟着浪漫、幽远的氛围,电影意境清新静穆。而这些电影正是以此种方式,从一种镜头诗意上升到了情感的诗意。部分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在叙事时,并不刻意讲求故事情节的完整无缺。在构筑诗意空间时,它们更多的是强调立象造境,以感觉、梦、情感、意识为索引,去烘托某种氛围,渲染某种意境,进而完成对叙事空间的构筑。电影《童年的稻田》(2011)就是在回忆中渲染了一种关于童年家园的诗情。这部电影因重于抒情所以在叙事上并无剧烈的戏剧冲突,更多的是生活流的展现。这部电影也因轻于情节叙述,导致了在情节设置和人物行为逻辑上有一些缺陷。《童年的稻田》(2011)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弟弟因犯错怕被父亲骂,悄悄离家去外地找爷爷。从整部电影的叙述空间上看,这个情节的设置略显生硬和零碎,它既起不到很好的串联作用,也没能更好地推动剧情发展。然而,这些零碎叙述空间,却又像一个个小插曲,通过拼接和锻打完成了对一个情感空间或者意境空间地浇筑。因而,看似拼凑感十足的碎片化故事空间,也并未对电影中营造平和静穆的意境美以及深化侗族生命诗情的主题有所影响。因为在此处,意境的营造与情感的抒发才是创作者真正要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情感流的肆意流放似乎解构了时间,解构了叙事空间的中心线索。与此同时,电影诗性却又偏偏通过情感流建构了一个整体。电影中,创作者通过情感化、碎片化的镜头空间,围绕着“人、稻田、家园、民族”等要素,达成了对生命以及生存的隐喻。因而这种诗意空间看似松散但其内在确又是环环相扣的,且其思想主旨的表现也是集中的。在这里,电影通过感性的情绪表达达到了理性的思想升华。这种诗意往往也是有着很强的附着力,因而即使是在松散的意象之中,每一块碎片都有明显的诗性存在,而且每一个存在又都附着某种寓意。而这种碎片化且多义性的表达,也多是在并置、重复之间得以实现。在电影《月色》(2017)中,“月色”指的是月亮、壮族女孩、歌曲,因而电影在此构筑了一个浪漫、静穆、纯洁的诗意空间。在这部电影里,这些零碎的意象在不断地串联、复现、叠加之中,完成了关于爱情、民族等主题的隐喻。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惯于以此种并置、闪回等手法来展现多重空间诗性。后现代语境之下,电影空间特别是象征空间、画外空间,呈现出了异质性和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碎片化的诗性,是源于电影抒情化表达的需求,而这些又无意识地在个人化的民间表达里构筑了诗意空间的另一侧。
从符号学角度而言,电影符码“是唯一具有三重分节的符码,[6]508”一个单独的画格通常有三重分节,即象形图象、象形符号以及象形义素。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电影的空间世界里,从图形到符号再到义素都有着自己的空间。在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中诗化、碎片化的图像或者物象,即使是离散的、局部的,却也能以一种诗性的情绪化的电影语言,将这些碎片化的东西构筑成一个完整的诗意空间。而这个碎片化的诗意空间往往也就有了后现代主义“用无中心来充当中心;用不确定来给予确定;用零散化来构建整体”[7]3的特征。
二、一种个人化的民间表达
作为具有诗性特征的电影而言,其电影的语言是“自由的、间接的主观化”[8]7,而这种主观化或是个人化的表达也恰是诗意电影的重要特征。因而从空间理论的角度来说,在电影中营造出来的空间也就是一种主观化色彩浓郁的诗意空间。在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里,这种主观化诗意空间又多了一种民间表达的内容。在电影中,民间空间里自由自在的品格与帕索里尼在《诗的电影》中强调的自由和间接的主观化,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同质性的东西。这两种自由的审美品格在电影表现中同样重要,因为“艺术创作中一旦消失了对于美、自由的追求,艺术也就难以称其为艺术了。”[9]164同时,电影中的这种民间表达也具有明显的民间性、主观抒情性的特质。这种民间表达希冀在自由自在的民间土壤中去建构一个关于生命诗意、生活诗意、文化诗意的诗意空间。因为在创作者们看来这里的“‘自由’主要是在民间朴素、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中体现出来。”[9]163而电影中“自在”的表现主要是指对民族文化或民间文化中的生存逻辑、伦理法则、生活习惯、审美趣味等内容的呈现。
约翰·麦登(John Modden)在《诗电影》中概述了其所谓的主观性或者主观化。他认为“电影是服从于‘诗人’,即导演的,电影中出现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属于导演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0]74。在电影《童年的稻田》(2011)中,导演以阿秋的视角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我”的童年世界。这里的“我”有浓厚的导演介入色彩,这种介入有时候是直接的,如电影中的大部分旁白,其实是导演借阿秋之口直接来交代自己的“乡愁”。这是导演旅居异国多年之后,对故乡的一种回望,其实更是一种寻找。而这种带有创作者强烈主观性的寻找主题在《寻找刘三姐》(2009)、《梦回三江》(2012)、《月色》(2017)等电影中也有所呈现。从整体上看,虽然上述这三部电影都在试图构筑一个民间诗意,也都在试图寻找民族民间之魂,但其宣传式、猎奇式的目标指向导致电影少了些许话语蕴藉,也失去民族最为本质的民间审美追求。从诗电影的角度来说,在《童年的稻田》(2011)、《天琴》(2013)等电影中主观介入和主观抒情性的表达,其本身就能建构起一个诗意的空间。同时,创作者的这种主观介入其立场是民间的,如在《童年的稻田》(2011)里创作者就是站在侗族民间里的主观表达。由此看来,这种诗意性与民间性又是相互依存的。通常电影里的民间化是以自由自在的形式去展现底层社会空间的原始生命力。因此这种诗意的民间空间,既有着浓厚的主观色彩,同时也有着自由自在审美特质以及源自民族文化深处的生命诗情。
在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中,大部分创作者的视点是民间的,其选材多是来自边地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在‘民间文化空间’里洋溢着自由自在的美学品格。”[11]21民间的土壤让创作者获得了自由自在的表现空间,因而这些创作者似乎也更能将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个人化表现手法加之实现。从某种层面上看,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的民间空间就是诗电影里的个人化、诗意性空间。因为它的内容也是在自由自在的美学品格之上构筑起来的。在《童年的稻田》(2011)中导演朱晓玲这种主观介入是一种主观化、情感化的直接表达。直抒胸臆的表征以及表意直接的旁白、独白,都构成了这种显性介入。在诗电影的范畴中,主观介入是营造电影诗性的重要手段。作者以主观的介入,情绪化的表征手法,立身于民间之中,在主题上以自由活泼的形式,表现民间生活的面貌和底层人民的心灵情感,从而构筑了一个诗性的民间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民间化的诗性电影,这种电影能尽情地、自由地展现“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9]163。在电影《童年的稻田》(2011)里创作者正是在关注侗族民间过程中,去展现侗族人民围绕着“稻田”而衍生出来的生命诗意、生活诗意。在这部电影中民间化的诗意空间始终浸润着侗族人独特的生命观念——生命像是一条平静河流。因而,电影在对奶奶去世这个情节空间进行阐述时,又夹杂着创作者个人化的诗情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民间化的超然。稻或者稻田对于侗族人而言就是其生命的全部,他们的生死都与稻相关,生活以及生命的一切都围绕稻田、稻米、稻苗,从洗头用的糯米水,到作为维持生命的补给的稻米,再到奶奶去世的地点以及最终下葬的墓地——稻田。稻即是肉身所存的依靠,也是灵魂的归处。稻贯穿于侗族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精神等方方面面。从整体来看,电影的叙事有着“作者电影”强烈的个人化表达,这种表达更是在创作者的情感注入中逐渐显现出来。在这部电影里,创作者尽力地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其中,并以这种诗情来呈现民间的空间。因而电影中展现出来的民间化语体也就契合了个人诗化电影的内涵,同时这种语体也恰切地书写了关于侗族的生命诗情与生活诗话。
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们有意淡化情节的发展,从而通过主观情绪化的镜头空间和自由自在的民间笔体来构筑叙事空间。这些电影空间集体呈现出了个人化、碎片化、民间化的特点。这种碎片化的诗性呈现,却又恰切地表现了本就自由多态的民族文化内涵。在《碧罗雪山》(2010)中创作者以主观抒情色彩浓厚的镜头语言来营造民间化的诗意空间。电影有着对于民族民间文化习俗的展现,例如关于婚俗书写。在这里电影呈现了民间文化“原始”“封建”的特性。电影个人化的直接表达肇始于创作者追寻关于民族生命力的诗情。这种强烈的创作倾向,使得电影有了强烈的个人主观印记。在《碧罗雪山》(2010)中创作者观照了在社会变革中的一个族群,一个生命体,也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民间文化。在这里,民间立场也是创作者的个人立场,也是创作者执着于呈现的个人化的东西。因此,这个民间化的叙事空间往往也就有了创作者的个人色彩,而个人化的诗意空间也有了民间的内涵。同时,这种民间化和个人化的空间诗意,也是多层面的,它通常浸润在电影的镜头空间、物理空间、文本空间以及心理空间之中。而最终创作者也正是旨在以此种自我抒情色彩浓郁的镜头语言来塑造民间化的诗意空间(心理空间)。因此,电影中以母语(傈僳语)来进行叙述,不仅为观众营造了一种猎奇的空间氛围,同时也为观众构筑了一个新奇、陌生化、异托邦式的画外民间空间。
对于电影诗意空间的构筑,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们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汲取营养。强烈的主观抒情式诗性呈现,强调了个人化的主观表达,而重于抒情和造境的表现手法,在对民间的诗化上,也为电影增添几分诗性。“诗歌,其诗意性指的是它在节奏和韵律音乐美中,抒发情感、创造意境的特性。”[12]104中国传统诗歌重情感而轻于叙事,尤其重于主观化的自我抒情。这种传统诗词中的诗意性,延续到了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中,并在那里构筑了一个民间化的话语空间。在镜头语言上,电影重于造景立象,重于自我情感的表达,再以此去造境、明旨。在电影《壮乡木棉红》(2010)中,创作者通过多处空镜头来描摹壮美且险峻的山,并以此表现手法来配合情节叙事的发展,从而渲染一种悲壮的情感。这种情感裹挟着创作者对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壮族儿女的崇敬和赞叹。“抒情诗即是个别主体的自我表现”[13]191,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诗电影如抒情诗一般,这些情感也是创作者个人化的自我表现。而这些情感的内容既是电影试图给读者构筑的画外空间,也是创作者的情感空间。
在电影表现中创作者以空镜头、远景镜头来表现环境以及舒缓的节奏进行叙述,也是其诗意构筑的重要逻辑。在电影《童年的稻田》(2011)中,关于侗族梯田、侗寨等的远景镜头、空镜头也有着来自民间的主观抒情性。在这部电影中,创作者在交代了奶奶去世之后,随即便切入了风吹稻田的空镜头。这个镜头的内部空间铺衬着遍地的金黄、风吹稻浪、节奏舒缓等元素。在此创作者并未藉由演员表演或者叙事空间的戏剧冲突来展现奶奶去世这个情节,而是通过平静舒缓的空镜头节奏来展现淡淡的感伤之情。在平静的抒情中为观众勾勒了一个关于生存诗话以及生命诗情的话语空间。从粮食到生命,创作者的立场是民间的,在淡淡的感伤中,电影围绕着粮食(稻)展开了关于生命主题的探讨。在这个异托邦式的民间空间里,民族的民间文化展示了自身生存的逻辑,伦理法则以及审美趣味。这些内容都与主流的思想观念、文化逻辑有着明显的差异,如在电影《碧罗雪山》(2010)中婚俗、信仰、人物行为逻辑等方面呈现出来的“异”一般。这些“异”并非是创作者有意或者无意的臆造,因而也就不存在逻辑上的谬误。换而言之,这种“奇异性”其实是符合某种民间文化逻辑的,正是因为它在这种民间文化语境里所获得的合理性,所以其镜头空间的逻辑也是能自洽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电影《童年的稻田》(2011)里作者在交代奶奶去世这个事件时用一组具有诗性的且又非常规剪辑逻辑的镜头来呈现。个人化的民间表达呈现出来的这种“异”是源于民间的,是有着个人化的诗意色彩的。这种诗意性的表达也正是在“诗”与“异”之间获得发展的土壤,从而才展现出来一种自由自在且具有原生态美学的内容。类似的电影表现手法在少数民族电影题材的作者电影中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新世纪以来的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特别是作者电影呈现出来的个人化创作倾向“突出了个人独立的声音、语感、风格和个人间的话语差异”[14]23,从而呈现了精彩纷呈的诗意空间。诗意空间中呈现出来的思辨、梦幻、哲理,都以民间化、民族性为支点,然后加以个人化、主观性的表达,展现出了一种独立精神内涵以及对人性阐述的诉求。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这种诗意性源于早些年我国的诗意电影,却又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诗歌写作潮有着某种契合,只不过在表现内容上,前者更注重在个性中强调民间、民族因素,后者则更注重对作者个人的个性的表达,二者侧重点不一,但殊途同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世纪的广西少数民族电影的个人化民间表达也是一种民间的个人化表达,也正如上文所言,正是这种民间的立场,个人化的姿态才营造了不一样的诗意空间,从而也才使得在这个艺术范式下创作的作品,无论是表现民族、梦幻、神秘、异托邦还是表现原生态、疏离、个性,皆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张力。
“电影的叙事空间是一种复杂流动而又灵活多变的假定性世界。”[2]19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以其诗意性空间叙事表现手法,展现了新的活力。这些电影无论是从镜头空间、场景空间、单一故事的叙事空间还是影片整体叙事空间都营造出了一种碎片化、隐性的诗性特征。电影中重于情绪化的镜头语言和意境渲染,也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电影对于民族、民间的探索,对于展现自由的民间土壤和对民族原始生命力的执着,也揭示了其对生命诗情、民族诗境一如既往的追求。同时,部分优质电影中呈现出来的独特的个人化、隐喻性诗意表达对当下陷入发展困境的广西少数民族电影来说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电影创作者们匍匐于民间大地,营造诗意空间,展现民族精神诗意的艺术表征,也将是未来少数民族电影艺术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