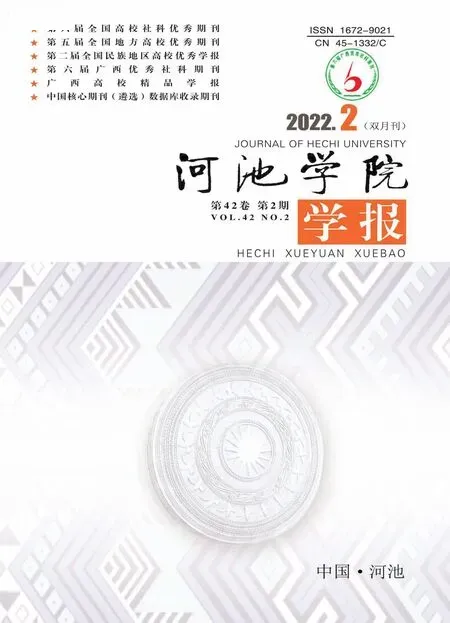宋贤精神:陈寅恪史学实践的一个参照坐标
魏宏玉,贺根民
(1.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部,广西 南宁,530023;2.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旧学加邃密,新知转深沉,20世纪上叶的中国学术呈现一种众声喧哗的时代表征,各界学者纷纷立足文化转型关口,寻求革新与突破,以创建新的的学术范式来引领后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彰显了西学东来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文化张力,提供一套完整的学术操作系统,指明现代新汉学的发展途辙。与其桴鼓相应,陈寅恪、傅斯年等学人大力褒扬“宋人之史学”,有意在竞言古史的现代学界别张一军,倡导探索富有近世色彩的宋代文史之学,以各自特有的学业和精神操守揭橥“新宋学”大旗,另辟蹊径来消解汉宋之争。思想在同光之间、治不古不今之学的陈寅恪独立苍茫,刻勒大写的人格符码,无论是其振聋发聩的史识,抑或勤劬的史学实践,宋贤精神就是他著书立说的理想参照和情感寄托。爬梳陈寅恪与传统文化的关联素为陈寅恪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与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二作均认为陈寅恪赓续了其所推赞的宋贤史学路径;王水照《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与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二文亦断论宋贤治学品格直接影响了陈寅恪的史学实践。在当下陈寅恪研究的深化期,面对前哲时贤的发掘实绩,我们既需重回历史现场验证,又得立足于新的视野来积极推进陈寅恪研究。作为一个时代高标的陈寅恪现象,个中诸多待发之覆仍须我们贴近学术生态来多向钩沉。
一、崇仰民族志节与自由思想
我国思想文化的近世转变,打造了中庸内省、开放兼容的经世理念,逐渐沉淀为张扬世俗精神的宋型文化谱系。辉煌灿烂的中国文脉蔓延至宋朝文化天空,因为宋太祖不杀士人的誓训而获得超越千载的蓬勃能量,加快了近世文明意识的觉醒步伐。陡然飙升的幸福指数改变了士人的生存规则,其从崇尚道义自觉向砥砺名节的群体意识跋涉。宋代名臣中不乏重视人格修养的引领风潮之士,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与担当,提升了宋人志节的高度。欧阳修《朋党论》裁定成为君子条件有三:道义、忠信和名节,在其看来,名节是君子进德修业的关键。山崩地裂的朝代更替最能检测士人的气节,若盘点在国破之际为本朝殉节之数,当以赵宋为最。据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在宋元的崖山海战中,敌军压境,大海茫茫,自觉跟随末代皇帝赵昺蹈海而亡者竟达十万人之多,何其惊悚!这从侧面传递宋代士人彰显气节的集体意识。《宋史·忠义传序》载:“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真言傥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1]13149宋学作为一种学术体系,其所承载的社会指向塑造了近世国人的价值图景,表彰宋人志节,推重宋代的自由精神是陈寅恪的重要追求。早在1909年,陈寅恪留学哈佛大学之际,他就力主扭转宋代为“衰世”的观念积习,推重朱熹对宋学的突出贡献:“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意大利哲学家。——引者注),其功至不可没。”[2]103朱熹其人其作及其对理学的突出贡献的影响,重塑了近世文人的精神谱系。而后,此类崇宋情结不断具象为陈寅恪的情感寄托和角色自喻,直至1964年,历经坎坷的陈寅恪依然坚信:“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3]182好议论的思辨倾向铸造了我国学术的哲理传统,并标举汉学与宋学双峰对峙的学术格局。一旦具备了自由的治学环境,宋贤“以意说经”就成为可能,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宋贤精神铸造了后世难以企及的人格高标。
宋朝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座巍峨昆仑,后世社会体制的转型前兆多伏脉于此,职是之故,治宋史者先须了解宋学,现代学人多视宋代为近世社会的起点。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转折假说”大力体认宋代对近世文化的引领作用,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近代学术导源于宋,不识宋学,则无以知近代。1941年钱穆对弟子李埏的谆谆教导奠定了后学的学术宏业——“鄙意不徒治宋史必通宋学,实为治国史必通知本国文化精意,而此事必于研精学术思想入门,弟正可自宋代发其端也。”[4]379李埏之所以在宋史研究界享有盛誉,钱穆的引领之功不可抹杀。此类荣幸亦波及宋史专家邓广铭,他在回忆自我的学术之路时反复强调,正因为陈寅恪为其著作《宋史职官志》作序,自己才醍醐灌顶,确立投身宋史研究的学术志业。欧阳修直面北宋弊政,有意借史学书写来整饬人伦。陈寅恪有意将其放置于民族文化维度来评价:“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3]182《新五代史》既借圣人之言来张扬义理建构,又关注士人的道义追求,折射了宋代的学术生态。
陈寅恪“续命河汾”,其治史看重历史人物的民族气节。1964年夏,其弟子蒋天枢南下广州“问疾”,“奄奄垂死”的陈寅恪作《赠蒋秉南序》一文,并将一生学术事业尽托于他。在非常之际撰写这饱含身世之感与现实之叹的性情文字,原本就是托出其深植于心底的崇宋情结。陈寅恪不仅张扬了欧阳修等宋贤推重义气的历史影响,还援引司马光行事来凸显宋代士人捍卫人格大节的立场,其《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载:“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3]168揆诸史实,陆游之祖陆佃,先出入王安石门下,后又跟随司马光,位列元祐党人之中。陈寅恪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来坚守司马光式之“迂”,心系天下,敢于担当,追踪那些革故鼎新的宋贤轨迹,慨然以忠厚自牧,承续士人大节。
追根溯源,韩愈是宋学发凡起例的表率。1954年,陈寅恪撰《论韩愈》一文,从6个维度来体认韩愈对宋代新儒学的发倡之功,其以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奠定了宋学发展的基础。这6个维度可细分为:“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5]319-332。陈寅恪借韩愈的个案分析,以凸显气节对于铸造宋贤精神的重要作用。韩愈建立道统、重塑人伦,俨然为启发宋贤推重气节的先驱。从韩愈到欧阳修的砥砺宋贤气节,成为陈寅恪著书立说的一个心理基底。
陈寅恪以广义的宋学来考察它与近代的关联。他之所以断论宋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巅峰,正是因为宋代开启了近世中国社会体制、文化传统等领域的整体转型。早在1935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开设“欧阳修”一课,并视其为研究宋史的起步。据其受业弟子卞僧慧的记载:“本课程就欧阳修以讲宋学。所谓宋学,非与汉学相对之宋学,乃广义的宋学,包括诗文、史学、理学、经学、思想等等。所讲不专重词章,要讲全部宋学与今日之关系,而所据以发表意见之材料,不能不有所限制,故开本课,实为研究宋史第一步。”[6]169陈寅恪为此做了不少功课,援引《新五代史》与《六一居士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来核证史家言说,而其《五代史记注》作为该课程的结课之作更是考释欧阳修议论的主要凭借。就其授课计划而论,拈出宋史编撰的关键人物来仔细琢磨,或许是落实宋史研究的宏伟规划的一条恰切途径。而后,陈寅恪提倡建立新宋学,呼唤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其基础又的确伏脉在宋史研究之上。
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之光,坚持学术独立往往是保持学术个性的一种方式。若要充分张扬不羁世俗的学人个性,就得有与其匹配的自由思想。秉持自由精神,势必会凸显史学研究的学科本位。陈寅恪一生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这不单呈现在其著书立说的笃守上,其交友行事亦处处推重与践履之。他与“平生风义兼师友”的王国维惺惺相惜,正在于对宋代文化自由向度的追慕。宋代文人享有前朝未有的自由环境,或许就是他推重宋代的心理折光,其后期著作像《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均不约而同地礼赞自由思想。《论再生缘》盘点时世与文学发展的关联,就直接在“自由思想”上立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3]72-73。陈端生挑战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传统三纲,陈寅恪赋予其穿越时代的“了解之同情”,正在于陈端生的女权意识蕴含着独立精神的内核。在陈寅恪的接受视野里,赵宋为最具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朝代。晚清乱局刺激宋学复兴,华夏文化历经战火而不坠文脉、弦歌不绝,正因为有不少学人孜孜赓续宋学文化传统。晚年的陈寅恪倾注大量精力研讨陈端生的《再生缘》、笺注钱谦益和柳如是诗文,亦借此提振民族文化使命。我们拷问现代文化界的“陈寅恪现象”,无不关乎他对自由思想的守望。博洽自谦的现代学人备受社会风浪的冲击而岿然不倒,全在于其如陈寅恪般矢志不渝坚守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
二、接续长编考异之法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历时19年修成、体大思精的编年体通史。它之所以能媲美《史记》与《汉书》,一则源于该著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史料,合传、表、志于一体,标明历史事目,开创史书编撰的新格局;一则在于长编考异之法。考异法是司马光考订史料的一大创造,《资治通鉴》参考200余种正史、杂史材料,抉摘幽隐,综合归纳而编成长编。这一长编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刘攽负责汉史长编,刘恕撰写魏晋六朝隋史长编,范祖禹负责唐、五代史部分。为了达到考异求实的目的,司马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注重史料的取舍,将分散在其他史书的相关材料提取整理,反复甄别各种史料之间的差异,删其繁冗,择其优者并以时间为序来重新组合,对前朝史著作一番考辨性总结,推动了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侧重以长编考异之法来进入史料现场并考察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是现代学人推重宋代史学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位中国史学现代转换的关键人物,陈寅恪视域宽广,自由出入中西之间,博收杂取,转益多师。他接续乾嘉学派重视考据的优良传统,又步武德国兰克史学派属意考辨原始史料的理路。而宋贤的治史方法更是他接续传统、融化新知的重要途径。
对于治史者而言,材料丰赡与条理明辨向为研治史学的基本凭借。出入卷帙浩繁的史料海洋之中,保持方法论自觉不失为开创史学研究新貌的绝佳方式。如前所论,陈寅恪在不同场合推崇宋代史学,称颂“宋贤史学,古今罕匹”[7]134。为了进一步发扬宋贤治史传统,他甚至以此为度来评价和引导后学,其《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云:“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乃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8]262广搜群籍并考订史实,可以明圣人之言,知圣人之行。长编考异之法则凸显了因史料差别而作比较的锋芒。1936年,陈寅恪在开设“隋唐史”一课时也反复强调《资治通鉴》的考订成就:“初看似无足异,若就其取材之原料对比着看,就可以知道其审查材料用功之勤。又如《通鉴》标明年、月、日,看起来好像枯燥无味,而不知其考证极精,是其最用力之处。”[6]365如此穷尽研讨,以致达成材料和史识的圆合之境,遥接了好言义理的宋儒章法,长编考异之法强化了考据的存在价值,实现了史料与史观的融合。
通过以史事来印证言论,长编考异之法实现了信实与推理的统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运用该法的典范。至于如何操作,司马光的《答范梦得》一文阐述得甚为详尽,兹录于此:“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舍彼之意。”[9]161-162陈寅恪推崇宋贤史学成就,效仿其治史之法本就是他接续前贤的重要考量,其受业弟子王永兴的断论颇有参考价值——“陈寅恪先生史学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学术传统之中,特别是宋贤史学。宋代史学是陈寅恪史学的主要渊源。宋贤史学的代表为司马光和欧阳修,在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两方面,寅恪先生直接继承了这两位大师,并有较大的发展。”[10]5在王永兴看来,宋贤援引长编考异之法可分三个层次:修丛目;比较异同,有所取舍,修长编;考证是非,解释矛盾疑滞,互相参证,撰著成文[10]111。长编考异之法侧重客观求实,讲究合本于注,宋贤之法允符了陈寅恪治史的期待。陈寅恪赓续传统并推向前进。较之于宋贤,晚清民初的采史范围更为宏阔。地下之实物、佛道典籍、医学等自然科学成果纷纷进入陈寅恪的采史视野,特别是域外史料替他洞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赋予他以纵横中外的比较视野,博收约取而超拔前行。
毋庸置疑,准确的史料素为治史的基础,它往往影响到学人史观的生成及其高下之别。长编考异之法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作适当取舍,有利于彰显治史者的学术襟抱。陈寅恪平时的品史、读书体悟,不乏展示其对该法的熟稔程度。其《资治通鉴考异之部》中“卷三晋纪武帝咸宁四年”条载:“晋书傅玄传实谓玄迁太仆在‘泰始’五年,后崩在咸宁四年也。故玄传不误。劳干晋书校勘记已证温公之偶尔疏忽。”[11]99学如积薪,后出转精,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陈寅恪运用考异之法断论司马光的错讹,其本身就是开疆拓宇的时代进步。汇集古史资料,凡与其事相涉者,即加以注明,过多不害。如此考异多见于其阅读札记和读史札记一类。取材广阔,考证精细,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根脉,实现了外来学说与本土传统的融合。对此,王永兴的概括十分到位:“他继承了宋贤的史学思想、治史方法,以超乎寻常的开拓创造精神,较唐宋诸贤更上一层。而所以能如此者,先生精通华夏民族传统的学术文化,预时代学术之流,吸收外来学说,发展宋贤长编考异之法当是重要原因。”[10]126陈寅恪既以他山之石来拓展考异视野,又不忘民族文化传统本位,深悟宋贤精神并发展了长编考异之法。《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就是他光大其法的明证。
三、古典与今情的汇通
建筑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体制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德本意识,家国同构的文化取向打造了文史哲融合的学术生态,对于学问淹博的现代学术大家而言,局限于某一学科视域挖掘其学术成就与社会影响,或许不得要领。立足于当下去体认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高度,我们更应从其所称许的文史角度去打量。对此,傅璇琮的《陈寅恪文化心态与学术品味的考察》一文指明了思考问题的方向:“要研究自清末特别自‘五四’以后,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怎样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以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那么,陈寅恪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但作为一代大师,陈寅恪的意义绝不限于在专题领域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他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超出于具体成果的更值得人们思考的启示。陈寅恪树立了一个高峻的标格,使人们感到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一种理性的文化心态。”[12]3显然,单从史学专题领域出发,抑或局限于文学研究路向,均不足以彰显陈寅恪作为文史大家的光采与锋芒。厕身史实不断提炼富有时代色彩的史识,陈寅恪是现代富有历史感与时代精神的史学大家之一。他依据所占有的丰富而可靠的史料,接续宋贤治史传统,“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对古人“赋予了解之同情”,以诗史互证来追求古典与今情的会通,长此不懈推动传统文史之学的现代转换。即便是在目盲足膑的艰难境遇之中,他仍捧出像《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等如此厚重的文史杰构,以“颂红妆”来借传修史,沉淀一段“哀伤”的文化记忆。
在一堆繁复而杂碎的史料面前,注重史学方法的自觉和积极拓展研究视域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王震邦的论述可作参考:“陈寅恪在描述陈端生和河东君的过程中,取证方法回环曲绕,展现出史家所能用尽的史料和方法,环环相扣,终在两位女性身上,特别是河东君身上得出的交集: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构成的‘理念’,绝非单纯的考证文章所能蒇事。”[13]97-98在考证之外给予充分的情感投放,跟古人同气共求,深入她们的心灵世界,适时加以“假设”,也就实现了史家以古鉴今的文化期待。毋庸讳言,陈寅恪客观的学术论断因为情感投放而出现了某些位移,“在其著述中也存有按其理想和情感勾画出的历史画面,在关乎宋史、宋学的多次论述中,即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环境、宋代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14]154-160缘于古典与今情的融合,“被美化”的宋代文化就成为兼备吸收外来学说而不忘民族本位的理想期待。其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倡导侧重古人著书立说的时地,窥斑见豹,以今情去钩沉古典:“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8]279如前所论,即便是“广搜群籍”的长编考异之法,史家的搜罗视野亦不能穷尽一切,设身处地,神游冥想至古人的同一境界,或许因为史家的“今情”,会领略别有洞天的风景。陈寅恪所倡导的“古典今情”理路运用长编考异之法来阐释诗文,在笺诗中证史,有利于从史料中去彰显史识。
在现代学人队伍中,陈寅恪素以考据精深见长,将研求问题寓于翔实的史料考订和钩沉之中,实现史料梳理和问题探究的统一,这恰是宋贤治史的路子。古典与今情汇通,古史的价值借诸今人的钩沉便获得鲜活的文化生命:“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借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8]280与陈寅恪有两代姻亲、七年同学之交的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道出陈寅恪之所以反复推重司马光《资治通签》的治史路径,是因为司马光在史料中探求史识,不无凸显自我对考据和史识的注重力度。陈寅恪并非简单地取径乾嘉史学,而去遥接宋贤精神,注重史识就是其中关钥。职是之故,他乍一发现陈垣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就似曾相识,颇有惺惺相惜之感:“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辞。欲藉是略言清代史学所以不振之由,以质正于先生及当世之学者。至于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则读者自能知之,更无待于寅恪之赘言者也。”[8]270带着情感进入历史现场,再功利的历史也演变成有情的文化记忆。
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赋诗言志传统,援引文学材料来佐证史学研究,打造了学科交叉的方法论场景,也折射文学作品作为另类史料的存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说,历史记忆之所以能隔代复活,缘于方法论本身就具有独立自洽的演变规律。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所创作的“三吏三别”,被誉为一代诗史。但诗史互证作为一种谋就史学与文学交叉、汇通融合的研究方法,通常被认为起源于宋代,宋人的解史阐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宋人诗话大力体认杜诗为“诗史”之说,他们乐意爬梳杜诗文字来透视唐代社会的变迁,此类“以诗证史”、挖掘微言大义的笺注方法常见于时人的注杜实践。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激于《旧五代史》体例之不精当、断论过于简单,另撰《新五代史》,大量采撷诗歌、小说入史。在司马光的史学视域中,“实录、正史未必皆有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15]295,他在主编《资治通鉴》之际,广泛搜罗诗赋等文学文献,并综括了使用这些文学作品的方法。欧阳修、司马光的史书编撰大量援引诗歌和小说,就凸显了文学典籍的史料价值。
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讲究诗与事的参证,金末元初元好问的《中州集》借诗存史,而后清人钱谦益笺注杜甫诗集与黄宗羲力倡“以诗补史之阙”观点初步确立诗史互证的理论构架。而大面积放大诗文的补史、证史功能,并赋予继往开来的现代学术色彩,至陈寅恪才真正完成。陈寅恪认为与历史的勾连是中西诗歌一大差别,我国本事诗各自为诗,缺乏必要的综合统摄。其在所开设的“元白诗证史”一课中特意提及:“就白香山之诗而论,综合性尤嫌不够,需作再进一步之研究。综合起来,用一种新方法,将各种诗结合起来,证明一件事。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联贯起来可以有以下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16]483-484陈寅恪站在宋贤的肩上,由点及面,以诗文综合来考察一时代的风云变动,强化古典与今情的关联,对“以诗文证史”作了深入的理论阐述,拓宽了现代史料学的研究领域。照实说来,陈寅恪所倡导的诗史互证之法,既强化了诗文的史料价值,又凸显以史释诗效能,展示诗史会通的特质。与此相关,陈寅恪的诗学观亦注重古典与今情,偏重古典与今典、古典与今事相互证发的宋诗风格。他首肯江西诗派的诗学观念,并在诗史互证的实践中以古典与今情的融合作为评估好诗的标准。
四、结语
历史文化记忆作为过往岁月的祭坛,致力于呈现逝水年华的社会面相。穿越“秦时明月汉时关”,跨过“荔枝点缀的王朝”,赵宋一代的国力自然无法与汉唐媲美,但是欧阳修等宋贤“承续先哲将坠之业”,标领一场“新古文运动”来进一步强化道统意识,在制度文化诸方面却超迈汉唐气象。坚守民族文化本位,陈寅恪推重宋贤精神,既有“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冀盼,又不乏面古思今、构筑一处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场景之诉求。陈寅恪关于宋代史学的钩沉,虽嫌琐碎,但片言只语往往包孕深远的文化哲思,惠泽后学无穷。其追步宋贤高境,抒发了尊德崇节的人文理想;其接续宋贤的长编考异之法和诗史互证理路,拓宽史料的蒐罗范围,在历史中寻觅教训和提炼史识,铸造了富有现代意味的新宋学;其设身处地去领略宋贤风采,讲究古典与今情的会通,强化文化探索与史学方法的融合,助推“有情的”文化史学去开拓区宇。陈寅恪深入领略宋贤精神并积极践履宋贤治史家法,近承晚清史学的经世致用余绪,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之中,转益多师,融传统与现代于一炉,以卓越的史学成就和爬罗剔抉的历史洞察力,凸显了宋贤精神绵亘不绝的文化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