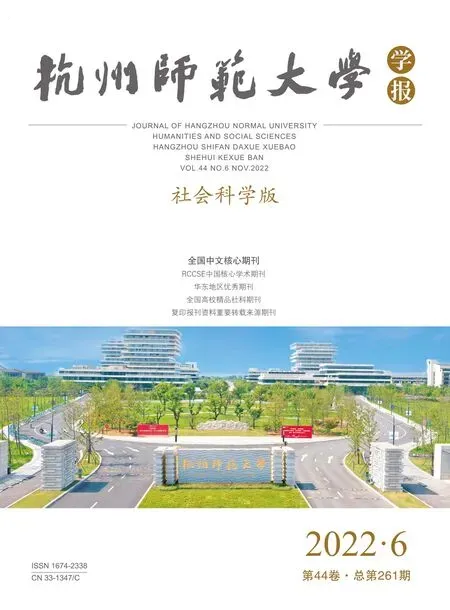垃圾与拾荒者的文化阐释:以《高兴》为中心
周 敏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
作为人类完整生存环节的一个部分,垃圾乃文明之镜像,也是文化的表征。正是“垃圾”,这一人类生活中的不可回避之物,体现了作为物的商品的生产与被抛弃,以及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人类社会的兴衰浮沉。斯贝曼(Elizabeth V. Spelman)甚至认为:“没有垃圾的生活是不值得研究的。”[1](P.324)垃圾也是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书写对象,“自《荷马史诗》始,垃圾一直是欧洲文学中的在场,从格伦德尔的手臂,到约里克的头骨,再到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尘埃’。西方文学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关注存在于文化产品中的垃圾”[2](P.4)。中国文学对垃圾这一主题也并不陌生,比如庄子关于“无用之用”[3](P.59)的著名论断。而在当代,对垃圾的文学再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高兴》。
《高兴》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哈曼(Brian Haman)在《亚洲图书评论》(AsianReviewofBooks)中称赞《高兴》具备“拉贝雷式的幽默,其中丰富多彩的民工形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愿望和缺点”[4]。徐德明从民工形象[5](P.186)、江腊生从城乡生活冲突[6]、杨小兰从主人公的精神困境[7]等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解读。而对于小说中的垃圾书写,则鲜有学者展开深入研究。本文主要聚焦小说中的垃圾主题,探究小说中垃圾以及拾荒者的文化内涵:在现代性的列车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垃圾以及有关垃圾的一切常常是被遮蔽的,而拾荒者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废弃的,然而这种被遮蔽的在场和废弃的生活并非没有意义,相反,他们的存在与小说中拾荒者居住地的名字“剩楼”一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和都市化宏大进程“大楼”中所“剩”下的阈限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则构成了洁净辉煌的城市空间中的一个异托邦。
一
贾平凹把《高兴》的小说背景设置在新世纪初,从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刘高兴的梦想:从乡下人变为城里人。高兴一心想克服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这种二元对立所代表的身份、文化和阶层,却最终意识到,就算进了城,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在城市里以捡垃圾为生的“废弃的生命”。小说对高兴的城市生活给予了既幽默且现实的刻画,真切反映了一代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历程,正如加斯坦(Clifford Garstang)在《华盛顿独立书评》(WashingtonIndependenceReviewofBooks)中所指出的那样:“《高兴》是一则现代中国的故事。几十年来,现代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有增无减,可以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8]事实上,在都市化的宏大叙事中,保证了城市清洁的拾荒者的故事几乎缺席。《高兴》最早出版于2007年,2009年改编为同名电影。与小说相比,电影版《高兴》更像一出廉价的闹剧式喜剧,观众反响不佳,而小说则堪称一部讲述乡下人进城的现代史诗。问世10年后,小说由韩斌(Nicky Harman)翻译成英文,书名是HappyDreams(《高兴的梦想》)。最初,韩斌把题目译为Happy,也就是中文的“高兴”以对应中文版。但由于存在同名图书,在出版社的建议下改为现在的题目。除却市场与版权问题的考虑,HappyDreams的确是更为合适的题目,因为小说内容的确就是关乎一个一贫如洗的拾荒者高兴的城市梦想。
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垃圾问题所困扰的历史,“从中世纪充斥着垃圾的护城河到今天堆积如山的垃圾填埋场,垃圾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一个持久的问题”[2](P.1)。垃圾不会自动消失,所以如何处理垃圾一直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早在17世纪,垃圾处理就是一项强制性要求。在奇波拉(Carlo Cipolla)关于前工业时代公共卫生与环境的著作中,他引用了意大利政府关于垃圾处理的法令, “我们命令你们立即……清除辖区内的所有秽物和垃圾……而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垃圾,应由社区派代表进行清理,并且运送至不会对城镇、村庄和城堡造成伤害的其他地方”[9](P.81)。商品的泛滥加速了垃圾的产生,也使得垃圾处理愈发重要,正如上文所示,对社区来说更是如此。拾荒者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点可以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撰述的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关于19世纪巴黎拾荒者的描述中看出:
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仔细地编撰纵欲的年鉴,描绘垃圾的日积月累。他把东西分类挑拣出来,加以精明的取舍;他聚敛着,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这些垃圾将工业女神的上下颚间成形为有用之物或令人欣喜的东西。[10](P.98)
受益于拾荒者的劳作,被城市抛弃、丢失和鄙弃之物再度物得其所并焕发了或者有用或者令人欣喜的崭新存在方式。巴黎的这些拾荒者也借此获得了一种浪漫化的救赎感。然而,《高兴》的主人公在西安以拾破烂为生的命运却与本雅明所描述的浪漫存在并不相同。在小说中,高兴刚进城不久时,住在宾馆里的一个姑娘让他去收一个废煤气灶,但是门卫不让高兴进宾馆的大厅:
门卫说瞧你那鞋!
我鞋好着呀,鞋尖没有破,鞋后跟也没有磨成斜坡,只是上厕所时鞋底沾了些泥,我蹲在那里用树棍儿刮鞋底的泥。我说:同志,让我进去吧。门卫说:不能进。
我说:泥刮净了还不让进?
门卫说:不能进。
我说:不会是嫌我是拾破烂的吧?
这回门卫却被逗笑了,他允许了我进去,但必须光了脚进去。
……
我的头虽然在玻璃门上撞了个疙瘩,但终究还是进了宾馆大厅。大厅的地面是石板,擦得能照见人影,我的脚踩在上边,立即有了脚印。走过大厅,上到十五层抱着一台废煤气灶再走下来,热成了王朝马汉,吓,大厅地板上的脚印还在。[11](PP.30-31)
因此,高兴只好光着脚爬到15楼去收取煤气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高兴并没有因为进楼前需要脱鞋而难堪,反而因自己在大厅地板上留下脚印而兴奋。那个上午,在收到废煤气灶后,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再接着去收破烂,因为他无法忘却自己在豪华酒店的地板上留下的脚印,并且挂念着自己的脚印是否被服务员擦掉了。傍晚时分,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自己的伙伴五富,在他的叙述中压根就没提他光着脚爬上了15楼,而是惊叹于宾馆的“豪华”。
这是多么豪华的宾馆,我的那些脚印一定会走动的,走遍了大厅的角角落落,又走出了宾馆到了每一条大街小巷,甚至到了城墙上,到了钟楼的金顶上。[11](P.32)
留在宾馆大厅地板上的脚印象征着高兴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短暂在场,但很快就会被抹去。高兴只是一个收破烂的人,没有“资格”进入富丽堂皇、干净整洁的宾馆。他清洁了城市,却被城市视为不洁。然而,高兴并未因为进入宾馆大厅被拒而感到难过。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脚印留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显然,刘高兴和其他拾荒者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共同体空间的重要一环,但是城市对他们是漠然的,生活的地方也占据了城市共同体的边缘地带,高兴和他的同伴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剩楼”的寓意即在于此。作者将他们的居住之所命名为“剩楼”,即取拾荒者被视为垃圾,或废物之意。因为,“毫无疑问,垃圾就是所剩之物。它是美好的、丰硕的、有价值的、有营养的、有用的东西被取走后剩下的东西”[12](P.13)。尽管拾荒者对于城市之运转意义重大,却是城市正常生活的“剩物”,不被城市所容。除了上述情节,小说中还有不少细节表现出了城市人对待拾荒者的漠然,以及拾荒者被遮蔽的存在。城里人日常对待垃圾的态度就是“眼不见为净”。“虽然我们可能会看到街道上的垃圾和污垢,或者从过度膨胀的垃圾桶中探出头来,但我们看不到这一切的开始和结束。在城市里,我们真的可以忘掉垃圾——事实上,我们也被敦促这样做。”[12](P.163)事实上,正是受益于高兴这样的拾荒者,城里人才能远离垃圾。诚然,城市里有专门的垃圾处理机构和专业处理垃圾的工人。但是,可回收垃圾依然需要像高兴这样从农村到城里讨生活的农民工来接手。他们就像是拾麦穗的人,在丰收后的田野里捡拾剩余之物。高兴并没有因为自己只是地位低下的拾荒者而羞愧,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对于城市的重要性:“我们是垃圾的派生物。不,应该是城市需要了我们!试想想,如果没有那些环卫工和我们,西安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11](P.28)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用高兴及其同伴看见的骇人听闻的垃圾堆做了回答:
我压根没有想到,在大垃圾场上竟会有成百人的队伍,他们像一群狗撵着运垃圾车跑,翻斗车倾倒下来的垃圾甚至将有的人埋了,他们又跳出来,抹一下脸,就发疯似的用耙子、铁钩子扒拉起来。到处是飞扬的尘土,到处是风里飘散的红的白的蓝的黑的塑料袋,到处都有喊叫声。那垃圾场边的一些树枝和包谷秆搭成的棚子里就有女人跑出来,也有孩子和狗,这些女人和孩子将丈夫或父亲捡出的水泥袋子、破塑料片、油漆桶、铁丝铁皮收拢在一起,抱着、捆着,然后屁股坐在上面,拿了馍吃。不知怎么就打起来了,打得特别的狠,有人开始在哭,有人拼命地追赶一个人,被追赶的终于扔掉了一个编织袋。我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倒后悔我不该来到这里,五富和黄八也不该来到这里。五富在大声喊,他在喊我,原来他和黄八霸占住了一堆垃圾。我跑过去,五富弓着身在那里扒拉,他满脸脏泥,又出了汗,脸就像个戏台上的大净,而他撅起的屁股,那缝上的裤裆又开裂了,露出那一吊东西,但这一切在这里却并不显得刺眼。他扒拉出什么了就给我扔了过来,我一件一件整理,那些纸箱片全是湿的,废铁丝上又都连着未砸碎的水泥块,塑料鞋编织袋破铝壶铝盆臭气难闻,而一只没了耳把的砂锅也扔过来了,锅里的一节发霉的鸡肠就摔落在我的头上。……
我们终于安全地扒完了那堆垃圾,收获还算可以,但人已经不像了人,是粪土里拱出来的屎壳郎。[11](PP.272-273)
这是多么罕见的垃圾和废物的表演性呈现!在这里,每一件垃圾似乎都被赋予了生命力,破塑料片、油漆桶、铁丝铁皮等共同演绎了一场垃圾的表演。而垃圾则已经独立于意向性,获得了一种崭新的主体性。毕竟,垃圾不是生而为垃圾,而是被转化成了垃圾。这段对垃圾堆的长篇描述令人震惊,生活于城市中的读者有多少人能够想象这样的场景?生活在城市里的隐形群体互相争夺,把废弃的垃圾转化为有价值之物。鲍曼(Zygmunt Bauman)对此有独到的见解: “废弃物可以被形容为我们时代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13](P.20)这些以垃圾场为生的男人、女人、孩童和狗确实令人痛心。这却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城市里大多数人都看不见垃圾场,就像“高兴们”的住所名字为“剩楼”所象征的那样。那些帮助我们处理所剩之物的人却被遗弃、遗忘了。在这里,人、狗和垃圾混为一体,绝然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与虑及之处。
与此同时,通过对垃圾堆的深描,作者揭示了垃圾的另一维度:作为怪怖者(the uncanny)的垃圾。弗洛伊德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怪怖者》(TheUncanny)中,把怪怖者描述为既熟悉又陌生之物。怪怖者通常指情境的含混,或引发不适、压抑感觉之物。《垃圾论》(OnGarbage)的作者指出,怪怖者概念所内蕴的含混性使其成为理解“垃圾”的合宜理论。[12](P.36)根据斯坎兰(John Scanlan)的说法,垃圾为现代生活提供了一部秘史。在现代生活中,垃圾的产生条件和使其不可见的手段,让其成为不受欢迎的幽灵。垃圾是人类的困扰,即使我们竭力把它压抑成一个秘密,也永远无法摆脱它的潜在威胁。垃圾“能够诱发恐惧,因为它对于个人身体和社会秩序的预知的危害,反而表明了他们的脆弱性与短暂性”[12](P.36)。这正是于垃圾骇人听闻的描述中所揭示的事实,作为怪怖者的垃圾,尽管被抛诸脑后,却并未消失,只是被压抑成暂时的不存在。
人类所生产的垃圾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亦是理解当下之匙。正如拉什杰(William Rathje)和墨菲(Cullen Murphy)所分析的那样:“人们所拥有的与所丢弃的,往往比他们自身更能精确、详尽、真实地说出他们所过的生活。”[14](P.73)垃圾堆也是如此。它们也是珍贵的信息节点,映射出过去社会以及当下我们所处社会的本质。贾平凹通过揭示城市垃圾的怪怖,也揭示了中国城市目前面临的挑战,即垃圾处理的结构性问题。什么是最环保的垃圾处理方式?在这篇小说出版时,中国还没有真正落实处理垃圾的方法,但西安市这个可怕的垃圾堆暴露了城市未经分类之垃圾的潜在危险。像高兴这样的拾荒者的确可以帮助消化城市中可回收的垃圾,但垃圾依然是个问题,这一点从垃圾堆之巨即可见一斑。2018年,中国开始禁止垃圾进口。2019年,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开始实行强制垃圾分类。以后的拾荒者,如果他们继续存在的话,可能不再会经历高兴和他的同伴们在垃圾场的上述经历了。
二
去西安捡破烂前,高兴是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清风镇的农民。刘高兴想成为城里人的动机就算不是闻所未闻,也是极其戏剧化的。他把自己一个肾卖给了一个西安人,因此他想象着自己也自然成了西安人。像唐·德里罗(Don DeLillo)在《地下世界》中的那颗著名的棒球一样,这颗被出售的肾成为了这部小说中的叙述力量与核心隐喻。高兴之所以卖肾,是因为他的相亲对象要求他盖新房,手头拮据的他只好卖肾来换取盖房所需的资金。在卖肾前,他已经卖了三次血。在听说卖血会感染乙型肝炎后,他不再卖血,转而卖了一个肾。令人难过的是,当他最终用这笔钱盖好房子以后,他的结婚对象却跟别人结了婚。这次卖肾是他的一个秘密,他只告诉了他最好的伙计五富。“肾”与“身”同音。在某种意义上,刘高兴“卖肾”就等同于“卖身”。肾也是人体重要的器官,据中医所言,肾主理人的精、气、神,是生命力的重要来源。
高兴的“都市化”开端于身体器官的商品化,这一器官亦是其生命力之源。然而与上文论及的脚印一样,与常人的理解不同,对高兴来说,卖肾并不可悲,而是他为自己种下的一颗成为城里人的梦想种子:
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的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我就坐在城墙外一颗弯脖子的松下的白石头上。[11](P.5)
此后,他就一直想去城里寻找他那颗已经卖掉的肾,因为他相信这颗肾仍是他自我的一个部分。这种自我混杂着自卑,也混杂着自恋,因为毕竟他自我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了城里人。高兴并不认为失去了一个肾就是人生悲剧。相反,他感到骄傲,好像这颗肾的新主人现在已经成为了他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另一个自我。这个新的“自我”体面、有文化、富足,正是他所幻想成为的那个自我。在小说中,高兴捡到了一个钱包,在钱包主人来取钱包时,高兴感到钱包主人似曾相识,于是脑子里闪现了一个玄妙的想法:“这是不是移植了我肾的人?判断是那么的强烈。是这个人,肯定是这个人!”[11](P.174)他一厢情愿地认为钱包主人就是买了他肾的那个人,把他视为另一个自我:“我终于寻到另一个我了,另一个我原来是那么体面,长得文静而又有钱。”[11](P.175)高兴认为买自己肾的人是韦达,这人正是高兴的爱恋对象孟夷纯的常客。最终孟夷纯(1)高兴爱恋对象的名字孟夷纯与“梦夷纯”(梦想对方是纯洁的)同音。这个名字从某些方面表明高兴对她的爱恋只是梦一场,因为她并非他认为的那种纯情女性。相反,她在美容美发店上班,通过与韦达的肉体交易挣钱谋生。告诉高兴韦达移植的是肝而不是肾。这种错位并非偶然,它实质上隐喻了刘高兴成为西安人梦想的荒谬性。高兴对此并非全然不知。在第十九章,在城里捡拾了一段时间垃圾后,高兴感叹自己还是农民,他憎恶自己的命运:
那一刻我突然地为我而悲哀。想么,那么多人都在认为我不该是拾破烂的,可我偏偏就是拾破烂的!……我已经认做自己是城里人了,但我的梦里,梦着的我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我当然就想起了我的肾。一只肾早已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11](P.127)
高兴并不满足于只在城里拾破烂,而是想成为一个体面的城里人。对他来说,进城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如果人生的光景是分节过的,清风镇的一节,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麦草,风一吹就散了,新的一节那就是城市生活。”[11](P.8)尽管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高兴仍渴望具有美感与文化的生活。他阅读经典小说,吹奏传统乐器箫(2)英文版中,除了斜体出现时,韩斌大部分时候把箫译成flute,并将其解释为竖着吹的笛子。但事实上,箫和笛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乐器。,偶尔会失神地陶醉于天空中的云彩。他喜欢城市的干净和优雅,并被其现代性和时髦感所吸引。他自我认同为城里人。在家乡清风镇,他卖血卖肾讨生活,但是来到城里以后,他甚至能注意到太阳下的烟影照在地上是黄色的:“我敢说,这个世上那么多吃纸烟的人,能注意到烟影是黄的恐怕就我一人。”[11](P.23)高兴相信自己在城里,哪怕是捡破烂,也会生活得很好,因为他有时间与精力沉耽于审美体验。
此外,吹箫的爱好也帮助高兴确认了自我的存在。因为吹箫,高兴感到自己获得了某种尊严,他可以因之忘记烦恼:“我是把箫别在了后衣领里,就像戏台上秀才别的扇子。嘿呀,韩信当年手无缚鸡之力而挎剑行街,最后被拜为大将军,刘高兴现在一步一个响声地走,倒要看看谁会来再羞辱我。……别以为从清风镇来的就土头土脑,一脸瓷相,只永远出苦力吗?见你的鬼吧!”[11](P.116)对于高兴来说,箫是其武器,赋予他对抗城市之残酷和漠然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箫赋予他一种摆脱 “乡巴佬”身份的自由,帮助他赢得城里人的尊重。有时,他甚至不去拾破烂,而是去为街上站岗无聊的交警吹箫。对高兴来说,箫是一个精神阶梯,使他充满活力,帮助他超越拾破烂的底层生活,并使他与那些“土头土脑,一脸瓷相”的乡下人拉开距离。这也是一种自觉的审美努力,令他超越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与严峻现实。这让我们想起了本雅明对巴黎拾荒者的描述:
当然,一个拾垃圾者不会是波西米亚人的一部分。但每个属于波西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隐秘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的会同情那些动摇着这个社会根基的人们。他在他的梦中不是孤独的,他有许多同志相伴,他们同样浑身散发出火药桶和啤酒桶的气味,同样尸冷战场。他的胡子垂着像一面破旧的旗帜。在他四周随时会碰上mouchards(密探),而在他的梦中,这些密探却得听他摆布。[10](PP.39-40)
对于本雅明来说,拾荒者是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隐秘讽喻。在拾荒者的梦中,这些密探要任由其摆布,这种梦中的摆布也是一种反抗。拾荒者与波西米亚人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都在反抗社会,在都市化的宏大叙事中,他们都没有一席之地。并不只有高兴一个人在追寻着城市梦,很多民工都梦想着进城。都市化意味着人口流动。然而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城乡之间的流动并非易事。高兴仅仅是一个拾荒者,他的任务就是让城市变得干净整洁、体面优雅,但他从未被城市接纳过,他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他的命运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工的缩影。
三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高兴对于城里生活的认知与他的真实处境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我们看到高兴为了实现他的城市梦,卖了一个肾,但他在城市里仍然只是一个捡破烂的无名小卒。虽然他有文化品位,有能力,但依然是“乡巴佬”,只能光着脚才能进入宾馆大厅。在小说的最后,与高兴一起收破烂的五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唯一知晓他卖肾秘密的朋友,因为无法负担手术的治疗费用,在城市的医院死去。五富死后,高兴想把他尸体背回家乡。到达火车站时,被警察拦住,并从身份证上认出了他的名字:刘哈娃。这是他出生时的名字,一个典型的乡下人的名字。警察并不认可他为自己起的名字“高兴”,在警察的眼里,他还是那个农村人“刘哈娃”。高兴背着他同伴尸体返乡的结尾揭示了刘高兴成为西安人梦想的破灭。那时乡村是中国的另一面,是与城市完全不同的中国的一部分,象征着一个更早的时代。虽然高兴可以跨越空间,从乡下来到西安市,却无法穿越时间,从早期的农村跨越到现代中国。在小说的结尾,当他带着五富的尸体回家,他并不仅仅只是从城市回到了乡村,他做了一次穿越,成为了“赶尸人”。“赶尸人”就是把尸体带回家的人,这是前现代中国的一个习俗,也是前现代中国农民的一个职业。高兴不仅在空间上回到了农村,他同时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他出生时的农村世界。
高兴与其朋友的进城故事不是他们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千千万万个为了更好的生活离乡背井的中国民工的故事。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都市化进程叙事中,这是一个不能说完全被忽略,却较少被关注的故事。《高兴》所创造的文学空间展现了这种都市化进程中的异质性,而小说中刘高兴的生活则构成了都市化空间内部的“异托邦”。异托邦是福柯(Michel Foucault)于1967年为建筑师做演讲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社会中各种“中断普通日常空间的表面连续性和正常性”[15](P.4)的地方。异托邦不同于乌托邦(Utopia)。乌托邦是一语双关的希腊语,被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用来指“乌有之乡”和“美好之地”(ou-topos vs. eu-topos)。在福柯看来,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是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16](P.54)如果说乌托邦是美好但并不真实存在的地方,那么异托邦则是一个真实而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允许人类固有的不可预知性来扰乱这个空间。如果说乌托邦因为美好的承诺而成为一个令人欣慰的地方,那么异托邦则因为它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而更令人不安。异托邦因此一般指的是与主流空间相反的他者的文化、制度和话语空间。由于其作为他者的特点,它带有一种令人不安、不相容、矛盾或变革的性质。它们是空间中的空间,或世界中的世界。高兴在城市的生活空间就是一个异托邦,它存在于城市生活的主流文化和话语空间之中,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存在,它观照着并扰乱着主流现实:在干净整洁的城市空间背后,存在着高兴和他的同伴们居住的“剩楼”。“剩楼”里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在现代中国城市生活的叙事中,这一“剩余的”异托邦“将异质性注入到日常社会的同一性和普通性中,注入到日常社会的话语空间”[15](P.4)。
小说通过对这个异托邦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另一重空间,这种空间映射出在我们生活的空间内,存在着刘高兴等拾荒者,敦促读者对都市化进行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刘高兴就像鲍曼所说的“废弃的生命”,作为非实体,是不为人所见的。废弃的生命,或生命的废弃,在鲍曼看来,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经济进步和追求秩序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而这正是现代性的特征。城市贫民区、难民营和监狱的废物处理机制让我们看到自身的脆弱性和不安感,也是它们被憎恨的原因。正如鲍曼所言:“我们用最极端但有效的方法去对付多余的东西”,而“现代生存——生命的现代模式生存——依赖于垃圾处理的灵巧性和专业性。” [13](P.21)我们不去看使其不被看到,不去想使其不被想到,《高兴》却使我们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城里人并不信任高兴及其同伴,在这背后是害怕像高兴这样拾荒者的废弃的生命威胁他们所享受的有序生活。莫里森认为,垃圾既是文明的他者,也是文明的痕迹或提醒。[2](P.9)拾荒者或许亦是如此。他者化在他们身上同样发挥着作用,就像其他无权无势的群体被他者化一样。“那些帮我们清理污秽的人,反倒成了污秽。”[2](P.97)在这个异托邦里,我们可以看到,垃圾清理工是如何被当作他者而践踏,因为“垃圾收集是不稳定的工作,通常由那些尚未在城市里扎根的人从事”[2](P.99)。拾荒者被“废弃”是因为他们处理了我们的废弃之物。正如鲍曼著作的副标题一样[13],他们也是弃儿,而高兴和他在城市里捡拾垃圾的同伴也是如此。更甚者,事实上高兴和他的同伴不为城市所接纳。我们在上文中提到,高兴以“身体的完整性”[17](PP.75-87)为代价,卖掉了一个肾,高兴体验到的是,作为器官出售者,他的身体延伸(就像有两个身体一样)到了城市,但同时这也让他的身体有了缺陷,成为废物。在珍贵的、有用的部分被出售和使用以后,剩余的部分则被城市拒绝。另一方面,这跟高兴想要留下永恒的脚印,让脚印去开启新生活一样。高兴梦想着对城市产生影响。如此一来,城市也是一个拾荒者:它从被它视为垃圾的人身上拿走有用的,扔掉剩下的。它不仅拒绝了少了一个肾的高兴,也拒绝了五富的尸体。
通过刘高兴和其他拾荒者在西安的故事,贾平凹应和了如前所述的波德莱尔对于19世纪巴黎的拾荒者的理解。这正是高兴及其同伴在西安城里所做的事情:对那些被扔掉、丢失、嫌弃及破损的东西进行分门别类,并把它们转化成有价值的、有用的、令人满意的东西。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得以改变对价值的理解。这一点可以从高兴的日常细节和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骇人听闻的垃圾堆中看出。这些情节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垃圾。我们知道,事物的价值“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可以改变的”[18](PP.Ⅵ-Ⅶ)。被丢弃的无用的东西可能会被变废为宝,而这正是拾荒者劳作的重要本质。通过一种神秘的“文化炼金术,把无用之物变作有用之物。而这归功于‘一些有创造力的,希望改善社会地位的人’”[19]。是他们把废物从垃圾箱中捡拾出来,并把它们变成我们光荣遗产的组成部分。[19]正如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所认为的那样,垃圾并不是简单的价值耗尽后剩下的东西,“垃圾箱里的东西还不是垃圾,在社会进程和实践合谋将其从流通中剔除,不再进行考虑之前,丢弃物不会成为垃圾”[18](P.Ⅶ)。
事实上,垃圾问题伴随着当代中国从经济、政治到环境问题的重要价值转变,因为“价值形式不仅表征社会关系,而且有助于维持权力和等级制度”[18](P.Ⅶ)。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深入发掘这些转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高兴如何通过审美实践与周围环境和平相处上。这也是我们在上文提及的箫在这部小说中重要的原因所在。在离开家乡清风镇之前,箫就是避难所,刘高兴通过吹箫找到平静和价值。他用卖血卖肾的钱终于建好了房子,而相亲对象却又转嫁他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吹了三天三夜的箫。在城里,他继续吹箫,用来忘却自己在城市里边缘化、无声化的生存方式。在不自觉中,审美实践成为连接或逾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桥梁。对于贾平凹这一代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作家来说,审美体验和实践意义非凡,是通向个人主体性的重要媒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10年“文革”把很多艺术实践视为小资行径而备受谴责之后,人们终于有了沉溺于审美体验的权利。20世纪80年代的整个10年,见证了全社会的文化和艺术的热潮。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消费文化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初出版的《高兴》一书为刘高兴等农民工提供审美工具,彰显了作者对审美实践代表个体救赎和希望时代的怀念,却也削弱了小说对农民工在城里生活的异托邦描写的审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