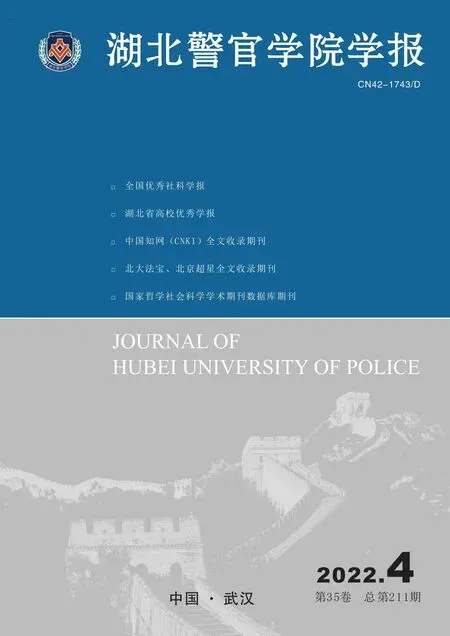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犯罪主体“身份性”的考察
张 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前言
近年来,乘客抢夺公共交通工具方向盘的案件屡见报端。包括“重庆公交车坠江案”在内的一系列案件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重大人身、财产安全,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社会公众期望通过《刑法》规制相关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2019 年1 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以及驾驶人员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与乘客厮打、互殴,危害公共安全的,均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但是,一方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应当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具有相当性,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大部分妨害安全驾驶行为通常表现为言语上的侮辱或者轻微肢体冲突,其法益侵害性远远低于前者,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评价相关行为未免有过度严苛评价之嫌,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一方面,应当明确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第114 条和第115 条的兜底性罪名,而非《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性罪名,并非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可以以本罪进行评价。基于此,于2021 年3 月1 日正式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修(十一)》)第二条规定了妨害安全驾驶罪,本罪的设立在保证行为评价和刑罚处罚两方面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将未达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规定的危险程度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纳入到了《刑法》的规制范围,此举是我国《刑法》以积极主义刑法观应对当前风险社会的具体体现,使得我国《刑法》在交通领域的规制更具体系性,有助于我国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在司法实践中更加准确地适用妨害安全驾驶罪,本罪的各构成要件要素都需要进一步释明。本文尝试界定本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并对本罪犯罪主体的身份性进行考察。具体言之,根据《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和第2 款的规定,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对正在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的行为人;其二是“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人;其三是未能履行安全驾驶义务而擅离职守的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 条之二: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方面,单从《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的文字表述,难以确定本罪前两类犯罪主体的范围。《指导意见》第1 条第1 款明确将实施“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和“殴打、拉拽驾驶人员”两类行为的行为人之身份限定为“乘客”。[1]因此,有学者主张将《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的两类犯罪主体的身份也限定为“乘客”,[2]但是如此理解极易让人对本款所规定的犯罪主体产生误解,即认为只有“乘客”实施了本款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才能成立本罪。但是除乘客外,非因乘车目的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人,比如售票员、乘务员、随车安全员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工作人员,甚至不具有特殊身份的社会一般人,能否成为本罪的适格犯罪主体存在疑问。而且此两类行为在行为本身和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两方面存在相当的区别,将此两类犯罪主体的范围作相同理解是否具有合理性亦存在疑问。另一方面,《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规定的“驾驶人员”,内涵清楚但外延模糊,而且本款通过规定“擅离职守”提高了“驾驶人员”成立本罪的门槛,那么具体应当如何认定本款所规定的“驾驶人员”的范围?本文尝试厘清上述问题。
二、《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无需限定行为人之身份
《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未对本款所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的两类犯罪主体的身份性作出明确规定,即既未明确规定“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的行为人的身份性,同时也未明确规定实施“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人的身份性。诚然,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实施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行为人多为乘客。根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统计数据,自2016 年至2018年,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共计223 件,其中,“乘客”作为被告人的案件占比达69.96%(司机作为被告人的案件占比22.87%,其他第三人作为被告人的案件占比7.17%)。[3]本文以“妨害安全驾驶罪”为搜索词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结果显示,自2019 年2 月至2021 年9 月,全国范围内共计225 件相关案件被审结。[4]其中,乘客实施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案例有218 件,约占案件总数的97%。但是,仍有少部分非乘客实施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案件发生,因此如若仅将《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所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的两类犯罪主体解释为“乘客”,或者说行为人在实施本款所规定的两类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时必须具有“乘客”之身份,无疑是限缩了本罪的成立范围。
刑法之所以区分身份犯与非身份犯,是因为身份犯中的特殊身份“与一定的犯罪行为相关的作为犯人的人的关系的特殊地位或者状态”[5]密切相关,“能够表明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身份)”[6]。即在身份犯中,特殊身份对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实质违法性或者行为人的可处罚性具有实质影响。
根据身份在定罪、量刑阶段的不同效用,可以分为构成身份和加减身份。以构成身份加功于犯罪主体的犯罪被称为纯正身份犯,以加减身份加功于犯罪主体的犯罪则被称为不纯正身份犯。具体言之,分为四种不同的情形:(1)只有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主体实施了特定的行为,该行为才具有法益侵害性;(2)只有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了特定的行为,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才能达到值得科处刑罚处罚的程度;(3)“为了保护特定的法益,将某种犯罪作为加重处罚类型,而规定特殊身份”[7];(4)对于不作为犯罪而言,只有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主体,基于正当业务行为或者法令行为,才能产生作为义务。质言之,具有特定身份而不履行作为义务的人,才是成立不作为犯的实质性根据。
基于此,本文对《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所规定的两类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的身份性分别进行考察。
(一)对“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的行为人身份性的考察
“乘客”似乎是“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的行为人的应有之意,但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乘客应当是与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提供者成立交通运输服务合同并接受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人。然而,对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对正在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以及实现“危及公共安全”之结果而言,正在接受交通运输服务的“逃票者”以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工作人员等与“乘客”并无任何差别。
以付某某妨害安全驾驶罪一案为例,被告人付某某因误会与公交车驾驶员张某发生冲突,并在张某驾驶车辆期间用拳头击打其肩膀。①参见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2021〕黔0203 刑初95 号刑事判决书。在本案中,行为人并不是接受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乘客”,而是非因乘车目的出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但是其行为完全有可能导致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不能正常履行安全驾驶义务,进而对公共安全造成抽象的危险。
基于上述内容,可以得出结论:行为人在“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时是否具有“乘客”之身份与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之间无任何关联性,因此即使行为人在实施此行为时不具有“乘客”之身份,依然可以成为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再扩大一些,行为人在公共交通工具“外”“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同样可以干扰驾驶人员履行安全驾驶义务,进而造成危及公共安全的结果。那么,对于实施上述行为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行为人则更不需要拘泥于“乘客”之身份。
以张某某、曾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为例。被告人张某某、曾某某因琐事与被害人李某某发生纠纷,随后被告人张某某、曾某某伙同其他同案犯先后三次在被害人李某某驾驶公交车时向其车内投掷石块,致使被害人及部分乘客受伤。②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2019〕桂1302 刑初762 号刑事判决书。本案中,行为人在行为时并没有出现在公共交通工具内,更不属于“乘客”,但是对“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之危险结果的实现而言,与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对驾驶人员“使用暴力”的乘客或者其他第三人别无二致。
因此,作为《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之一,对于“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的行为人,无论其在行为时是否具有“乘客”之身份,也不论其在行为时是否身处公共交通工具“内”,对于“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之结果的实现而言,并无任何影响,皆可以认定为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
(二)对“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人身份性的考察
对于行为人通过实施“抢控驾驶操纵装置”行为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而言,一方面,在行为时具有“乘客”之身份的行为人是本罪的当然适格犯罪主体。以顾某妨害安全驾驶罪案为例,乘客顾某搭乘公交车过程中与驾驶员李某某因琐事发生争吵并拉拽公交车方向盘,李某某随即刹停车辆。①参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7 刑初696 号刑事判决书.在本案中,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乘客”之身份,即正在公交车内接受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存在疑问。
另一方面,与通过“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之范围相类似,即使行为人在实施“抢控驾驶操纵装置”行为时不具有“乘客”之身份,依然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以陈某某案为例,被告人陈某某作为某大型普通客车的乘务员与正在驾驶大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邱某因琐事发生争吵并实施“用脚踩车辆档位杆”“用脚踩邱某放在方向盘上的手臂”等行为。②参见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 刑初505 号刑事判决书.本案的行为人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负有其他职责的工作人员,而并非乘客,但是其行为同样削弱了驾驶人员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控制力,并使之在履行安全驾驶义务时遭遇不合理障碍,进而对公共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另以王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为例,在承载数十人的大客车行进过程中,被告人王某以拽方向盘、拧车钥匙的方式妨害驾驶员安全驾驶。③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 刑终169 号刑事裁定书.本案中行为人在行为时同样不具有“乘客”之身份,但是其行为同样具有足以造成“危及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同样可以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因此,作为《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第二类犯罪主体,行为人在实施“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时,同样不要求其具有“乘客”之身份。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实施“抢控驾驶操纵装置”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范围,不宜与“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范围作相同解释,原因在于此两类行为在行为本身的特点和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两方面存在差异。
从行为本身的特点上来说,对于通过“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情形,“暴力”行为的存在形式多样,行为人可以采取与被害人直接接触的方式实施,比如直接利用肢体或者手持工具击打被害人等;也可以采取不与被害人直接接触的方式实施,比如向被害人投掷物品等。本罪的犯罪主体在实施上述行为时可以身处公共交通工具之内,也可以身处公共交通工具之外。而对于通过“抢控驾驶操纵装置”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情形,行为人在实施“抢控”行为时只能采取与驾驶操控装置直接接触的方式。“抢控”的含义为“抢夺和控制”。[8]对于“抢夺”,应当理解为通过强力从驾驶人员手中强行夺取,这一过程必然包含着行为人与驾驶人员之间存在“争夺”的过程。而“控制”则意为行为人强行代替驾驶人员对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操纵装置进行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实力支配,包括支配公共交通工具的动静状态和行进方向等。因此,无论实施“抢夺”行为还是实施“控制”行为,本罪的此类犯罪主体都只能身处公共交通工具之内。
从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来说,对于通过“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情形,行为人所使用的“暴力”行为的指向是“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的注意力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此时的驾驶人员更具被攻击性,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都会对其安全驾驶义务的履行造成障碍。因此,即便行为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对驾驶人员实施暴力,也会造成“危及公共安全”的结果,因此也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但是对于通过“抢控驾驶操纵装置”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情形,“抢控”行为的指向是“驾驶操纵装置”,其包含方向盘、变速杆、手刹、油门踏板、刹车踏板、离合器踏板等,[9]这些装置全部存在于公共交通工具之内,行为人很难在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实现对“驾驶操纵装置”的直接抢控。因此,作为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第二类犯罪主体,行为人在实施“抢控驾驶操纵装置”行为时必然处于公共交通工具之内。
综上,本文认为,对于实施《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所规定的两类行为而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而言,无论行为人在行为时是否具有“乘客”之身份,对于“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之结果的实现而言并无实质性影响,故皆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具体言之,在不法阶层,无论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乘客身份与否,只要实施了上述两种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之一的,都会影响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进而造成危及公共安全的结果。在责任阶层,《刑法》对实施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也不依赖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乘客”身份与否。简言之,“乘客”之身份既非本罪的定罪身份,也非本罪的量刑身份。因此应当认为,《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为非身份犯,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但是,作为本款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两类犯罪主体的范围,对于“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的行为人而言,无论其在行为时处于公共交通工具之内还是处于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皆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而对于实施“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人而言,其在行为时必然处于公共交通工具之内。
三、对《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所规定的“驾驶人员”之身份实质解释
(一)《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犯罪主体的本质
《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规定了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成立本罪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款中规定的“驾驶人员”与第一款规定的“驾驶人员”在内容和涵摄范围上完全一致。本文认为,本质上,界定《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犯罪主体等同于厘清对不作为形式的妨害安全驾驶罪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人的范围。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规定: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与他人互殴,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①《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2 条第2 款。但是在随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以下简称《二审稿》)中修改为驾驶人员实施互殴行为成立本罪要以“擅离职守”为前提。②《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第2 条第2 款。应当认为,“擅离职守”这一限制性规定进一步保护了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免受不法侵害。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擅离职守”的意思是未经许可即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论理解释的角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许永安处长认为,对妨害安全驾驶罪规定的“擅离职守”可以作出如下解释:驾驶人员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控制车辆,擅自离开驾驶位置,或者双手离开方向盘等。[10]以周某某、齐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为例,被告人周某某在驾驶公交车过程中因琐事与被告人齐某某发生口角,被告人周某某置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于不顾与被告人齐某某互殴,致使其驾驶的公交车失控。③参见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2015〕镜刑初字第00365 号刑事判决书。在本案中,周某某作为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没有采取合理措施控制车辆,违反安全驾驶义务”的情形就应当被认定为“擅离职守”。
本文之所以主张“擅离职守”的规定保护了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是因为如此规定为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提供了正当防卫的空间。[11]基于该规定,驾驶人员在尽到了安全驾驶义务的前提下(比如在合理区域内及时对车辆采取了制动措施)离开驾驶位并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即便最终因为履行安全驾驶义务而对无辜第三人造成一定程度的人身、财产损害的,也绝不构成此处的“擅离职守”。通过对检索到的相关案件进行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结论。以徐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为例。被告人徐某某因琐事与正在驾驶公交车的驾驶员周某发生冲突并强行拉拽方向盘,驾驶员周某为避免造成严重后果而及时采取了制动措施。①参见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7 刑初1763 号刑事判决书。在本案中,驾驶人员履行了安全驾驶义务。尽管在此过程中对其他乘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身损害,但是仍然应当认为其行为构成紧急避险,阻却犯罪成立。本文认为,如此立法的价值考量在于:尽管驾驶人员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过程中,其注意义务的程度要明显高于普通人,但是《刑法》对其要求不能过高,即当驾驶人员驾驶公共交通工具过程中遭受不法侵害时,《刑法》不能期待其持续性忍受该侵害,否则将违背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
《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在“擅离职守”之后,规定了“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对此,梅传强教授认为,“擅离职守”意为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未能完全履行安全驾驶义务,进而危及公共安全。但是这一表达过于抽象,为将这一规定具体化,基于客观现实中的通常性,规定了“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因此,《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为本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犯。[12]本文原则上赞同这一解读。②之所以是原则上赞同,是因为本文认为如此理解存有瑕疵。具体言之,“擅离职守”与“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是两个“行为”,损害了两种法益。前者是“不作为”,后者是“作为”;前者损害的法益为“公共安全”,后者损害的法益为“公民人身权利”。如果认为本款设立的目的仅着力于前者的“不作为”,那么如果后者的“作为”构成犯罪,则两个实行行为造成了两个法益侵害结果,应当数罪并罚。但是根据《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三款的规定,只能成立一罪。因此,如此解释可能会在本罪条文内部出现冲突。
首先,从法条内容来看,立法者对本款的着力点似乎确实不在惩治“作为形式”的“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因为本款虽然规定了“作为”,但是并未规定与之存在因果关系的结果,如果基于此将《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解释为“行为犯”,则驾驶人员入罪的门槛奇低,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其次,殴打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或者对社会管理秩序的妨害,如果本罪的规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或者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则本罪应当被规定在《刑法》第四章或者第六章。但是本罪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而且本罪前两款规定的结果要件同为“危及公共安全”,则意味着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公共安全”。驾驶人员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时擅离职守,客观上直接危及的也是公共安全。最后,如此解读恰好印证了上述对“擅离职守”规定的理解。毕竟驾驶人员可能基于正当防卫而“殴打他人”。这是从《刑法》分则上限制驾驶人员入罪,与本文之主张即本款提高了驾驶人员入罪门槛相符合。
(二)对《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所规定“驾驶人员”之身份实质解释的展开
如所周知,作为义务人不履行作为义务或者违反作为义务,即认为作为义务人具有实行行为,质言之,只有具有作为义务的人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主体。如此理解,似乎无论纯正不作为犯还是不纯正不作为犯,都是身份犯。事实上,不作为犯是身份犯这一命题由来已久,比如韦尔策尔(Welzel)就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是需要具备保证人身份的纯正身份犯。[13]但是,这一观点也备受争议。例如我国学者栾莉副教授认为,将不纯正不作为犯确定为身份犯,直接会对身份犯的概念产生混乱的负面影响。[14]陈兴良教授认为,争议的原因在于对身份犯的理解不同。[15]刑法中的“身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身份是独立于行为而存在的身份,比如警察、医生等。而广义的身份则必须伴随行为而存在,比如司机。《日本刑法典》中所规定的“身份”为狭义的身份。①《日本刑法典》第28 条将身份规定为“特定之个人要素”。而《德国刑法典》中所规定的“身份”则为广义的身份。②《德国刑法典》第28 条将身份规定为“特定身份关系、资格及情况”。我国《刑法》没有对“身份”作明确的规定,但是,从作为义务来源“实质的三分说”的内容来看,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没有涉及独立于行为而存在的身份③“实质的三分说”认为,不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包括:(1)基于对危险源的支配产生的监督义务;(2)基于与法益的无助(脆弱)状态的特殊关系产生的保护义务;(3)基于对法益的危险发生领域的支配产生的阻止义务。。因此应当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身份也是广义的身份。
基于上述内容,本文认为,《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是身份犯,此身份为广义的身份,即只要行为人在“擅离职守”之时正在实际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即可,因为包括乘客在内的其他社会成员有理由对任何正在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驾驶人员之身份产生合理的信赖。
从本质上讲,“被害人有理由对行为人产生合理的信赖”就是为保证人地位寻求实质化根据。不同国家的刑法学家为寻找“保证人地位实质化根据”作出了诸多努力,提出了数量众多的理论,甚至有学者将其称为“保证人地位之实质化运动”[16]。其中代表性观点是沃尔夫(Wolf)提出的“本来的依存关系说”和威尔普(Welp)提出的“特殊的依存说”。[17]根据上述学说,基于作为义务人的“先行行为”,作为义务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了依赖或者信赖关系,也就是被害人对作为义务人产生了信赖。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许玉秀教授对上述学说提出质疑,并认为只有法律的禁止或者命令才能产生信赖,而上述学说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保证人地位寻找实质化依据,具体言之,“本来的依存关系说”和“特殊的依存说”的逻辑是先基于社会伦理产生信赖,再基于信赖产生法律义务,因此有本末倒置之嫌。[18]但是本文认为,法律的禁止和命令不是产生信赖的唯一途径,人类社会个体间信赖的建立必然早于法律的出现。在文明社会,基于人类生产活动所形成的默示契约同样可以产生信赖。比如仍在中国农村地区存在的“长老统治”[19],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老幼尊卑的社会阶层体系,年幼者与年长者之间就存在一种信赖与被信赖的关系,这种信赖的产生并不依赖于法律的命令性规范或者禁止性规范,但是信赖关系客观存在。再者,当前社会化分工日益细化,处于不同角色分工的人与其他社会成员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被信赖和信赖的关系,这其中有一部分并未被法律所囊括,如若以法律未明确规定为由否认该信赖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则是违背客观事实和规律,掉入法律万能主义的陷阱。因此,本文认为,“本来的依存关系说”和“特殊的依存说”可以为“保证人地位实质化根据”提供理论支撑。
对于《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犯罪主体的身份性而言,从形式上讲,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身份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驾驶人员具有与所驾驶车辆相匹配的驾驶资质;其二,驾驶人员所从事的公共交通运输业务来源合法、有效,包括但不限于自营或者租赁公共交通工具从事公共客运业务、受雇于特定的公交公司从事公共客运业务、挂靠于特定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共客运业务等。但是是否意味着必须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的驾驶人员才具有防止“危及公共安全”结果发生的保证人地位?对此,在逻辑上存在两种理解:一则为肯定说,即只有具有准驾资质并且公共交通运输业务来源合法、有效的驾驶人员才具有防止“危及公共安全”结果发生的保证人地位、具有履行安全驾驶的义务。二则为否定说,即在居于防止“危及公共安全”结果发生的保证人地位、履行本罪要求的安全驾驶义务方面,并不以驾驶人员具有准驾资质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来源合法、有效为前提,只要驾驶人员正在实际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即可。为方便叙述,本文将前者称为“驾驶人员身份形式说”,将后者称为“驾驶人员身份实质说”。
“驾驶人员身份形式说”和“驾驶人员身份实质说”之争在本质上属于构成要件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之争。毫无疑问,当前实质解释论是主流观点。而且,如果对《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所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范围采“驾驶人员身份形式说”,无疑是不合理地限缩了驾驶人员成立本罪的情形,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无论正在从事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驾驶人员是否具备上述两点要素,只要其在履行安全驾驶义务的过程中与他人发生激烈的肢体性冲突,都必然侵害公共安全。因此,本文主张对《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所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范围采“驾驶人员身份实质说”。
对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作实质性判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不作为义务人必须具有保证人地位。处于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人在有能力履行作为义务且在履行完作为义务后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的前提下不履行作为义务时,就能构成基于不作为的实行行为。[20]耶赛克(Jescheck)教授同样认为,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保证人被赋予了避免结果发生的义务,违反避免结果发生义务的保证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21]其二,作为义务人在不作为之前,基于先行行为,设定了其不作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观点由日本学者日高义博教授提出。[22]换言之,即不作为义务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支配性。对此,西田典之教授认为这种支配必须达到“排他性支配”的程度。[23]对于驾驶人员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而言,首先,只要特定的驾驶人员正在实际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该驾驶人员就处于保证人地位,对该领域内发生的危险具有阻止义务,因为其对法益侵害发生的领域具有支配地位,与驾驶人员本人的驾驶资质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来源是否合法、有效全无关系。其次,无论驾驶人员是否具有准驾资质,也无论公共交通运输业务来源是否合法、有效,其擅离职守前正在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行为就已经预设了其后的“擅离职守”与“危及公共安全”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毫无疑问,“擅离职守”的驾驶人员对“危及公共安全”的结果具有排他性支配。综上,只要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在能够继续履行公共交通运输职责时“擅离职守”、违反安全驾驶义务,进而危及公共安全的,就可以构成本罪。
基于上述推论,针对《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所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具有准驾资质并且承担合法、有效的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驾驶人员,在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过程中,基于正当业务行为居于保证人地位,具有安全驾驶的义务,能够成为本罪的适格犯罪主体,自不必言。
2.对于不具有准驾资质,抑或是公共交通运输业务来源不合法、无效的驾驶人员,比如冒充公交车司机驾驶公交车从事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或者隶属于A 公司的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甲,非基于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或者借调合同,代替隶属于B 公司的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乙从事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由于乘客及其他第三人完全有理由基于其先行行为,即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而对其“驾驶人员”身份产生合理的信赖。即只要其正在从事公共交通运输业务,就必须履行与具有准驾资质并且承担合法、有效的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驾驶人员同等的安全驾驶义务。因此同样可以成为本罪的适格犯罪主体。
综上可知,《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为身份犯,具体言之,任何处于防止危及公共安全之结果发生的保证人地位的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即为本罪的适格犯罪主体。
结语
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犯罪主体的身份性而言,《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规定了两类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即“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和“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对此,“乘客”似乎成为了本罪的当然适格犯罪主体,但是行为人在实施上述行为时,无论是否是“乘客”都不影响“危及公共安全”之结果的发生,故对本罪而言,是否“乘客”之身份并不影响本罪的定罪。再者,本罪并未规定对具有“乘客”身份的行为人加重或者减轻处罚,那么“乘客”之身份也不影响本罪的量刑。因此,《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1 款为非身份犯,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但是通过实施此两类行为成立本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有所差异,具体言之,通过“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而成立本罪的行为人在行为时可以处于公共交通工具内,也可以处于公共交通工具外;通过实施“抢控驾驶操纵装置”而成立本罪的行为人在行为时则只能处于公共交通工具内。《刑法》第133 条之二第2 款是对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成立此罪的规定。本款虽然既规定了作为(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又规定了不作为(擅离职守),但是结合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及本罪条文在《刑法》中的体系位置,应当认为其规制的重点在于后者。作为广义的身份,只要作为义务人在“擅离职守”之时具备实质意义上的“驾驶人员”身份即可,即正在实际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因为实际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行为已经基于社会一般人的认识向乘客及其他第三人表明了其“驾驶人员”之身份。因此,任何正在实际履行公共交通运输业务的驾驶人员都为本罪的适格犯罪主体。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擅离职守”的规定提高了驾驶人员成立本罪的门槛,具体言之是为正在遭受不法侵害的驾驶人员提供了正当防卫的空间,充分保障了驾驶人员的合法权益。“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设立,充分体现了我国科学立法之精神,贯彻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合理解释、适用的前提下,本罪的设立必在我国交通领域的刑法规制中发挥巨大能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