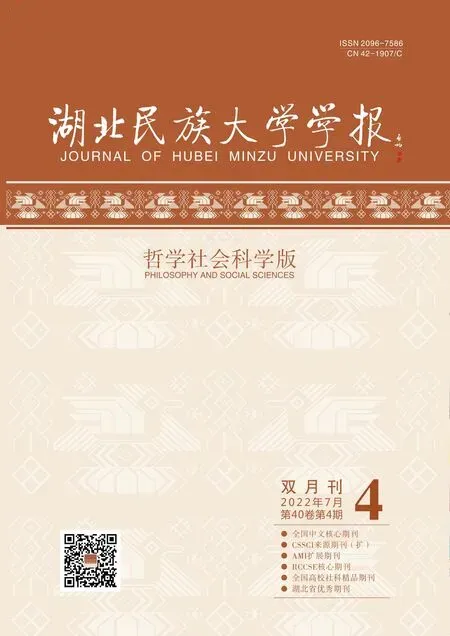族裔文化身份的建构:《拥有快乐的秘密》中塔西的自我探寻之旅
郭建飞
在《拥有快乐的秘密》(PossessingtheSecretofJoy,1992)中,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944— )探讨了女性割礼的权利问题和道德问题。(1)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主要存在于西方学者中,并由此形成两大阵营,以乔治(Olakunle George)为代表的一方支持沃克之于女性割礼的批判和谴责,而以古尔丁(Angeletta Gourdine)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沃克实质上是干预了非洲的内部事务,其做法展示了她的后殖民主义情感。参见:George, Olakunle. “Alice Walker’s Africa: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vince of Fi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53,no.4,2001,pp. 354-372; Gourdine, Angeletta KM. “Postmodern Ethnography and the Womanist Mission: Postcolonial Sensibilities in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African American Review,vol.30,no.2,1996,pp. 237-244.通过聚焦于女性割礼,她迫使读者去感受这些女性所经历的痛苦,并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割礼过程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共谋关系。(2)郭建飞、许德金:《引导、评论、深化文本主题——〈拥有快乐的秘密〉中的类文本及其叙事功能分析》,《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1期。同时,她恳求读者思考,非洲裔美国女性能否像黑人男性付诸暴力对抗白人的压迫一样,她们也可以抑或说有权利付诸暴力来反抗种族内部的压迫。另外,《拥有快乐的秘密》也是一部关于当代非洲裔美国群体在与主流文化相分离、试图融入部落文化时遭遇困难的小说,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裔美国群体(尤其是非洲裔美国女性)观念上的演变,以及沃克之于建构族裔文化身份的独特见解。
一、分离:非裔美国人身份建构的思想指引
在《接续时代:美国黑人小说中的60年代》(ConnectingTimes:theSixtiesinAfro-AmericanFiction, 1988)中,哈里斯(Norman Harris)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非洲裔美国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造等问题。他认为,非洲裔美国作家在该时期的创作范式,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反思:因为在美国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他们笔下的人物通常感到不幸福,所以他们致力于改写将他们排除在外的规则,希望“美国梦”能将自己囊括进来。换言之,这些人物不管多么富有反抗精神,他们都试图融入美国,期冀在西方文明的辖域内占有一席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哈里斯所描述的非洲裔美国作家的创作范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与20世纪60—70年代小说中的人物不同,现当代非洲裔美国文学中的主人公不再为了获得与白人一样的平等权益而试图改变西方的价值体系,相反,他们尽其所能地来摆脱西方文化的束缚。(3)McLaughlin, Andree Nicola: “Black Women, Identity, and the Quest for Humanhood and Wholeness: Wild Women in the Whirlwind.” Wild Women in the Whirlwind: Afro-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naissance. Ed. Joanne Braxton and Andree Nicola McLaughli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90. p.169.他们认为,如果能够通过“放弃西方价值观”、与非洲祖先“重新取得联系”来更新其非洲精神,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完整。(4)Shakur, Assata. Assata: An Autobiography. Westport: Lawrence Hill, 1987. p.75.显而易见,与20世纪60年代文学作品中的融合主义主题相对,充斥于现当代非洲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是分离主义。例如,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 1931—2019)的《爵士乐》(Jazz,1992),爱丽丝·沃克的《拥有快乐的秘密》,格罗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 1950—2016)的《贝利小餐馆》(Bailey’sCafe,1992)等小说均体现了非洲裔美国人之于主流文化的拒绝这一书写主题。
实际上,对非洲裔美国群体而言,分离主义并不是滋生于现当代的新思想。非洲裔美国群体的分离主义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奴隶制时期,第一批来到美国的奴隶渴望结束被奴役的生活,重新回到非洲家园。虽然他们之于逃离奴隶制的渴望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脱离白人压迫者的掌控、保持非洲身份和重回非洲家园的渴求,早在19世纪初便为分离主义运动的开展播下了种子,并随着1919年“红色之夏”(red summer)运动的到来而达到高潮。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 1887—1940)督促黑人群体“首先要爱自己、重视自己、为自己而战,并最终通过黑人国际行动,解放自己及家园”(5)Harding, Vincent. The Other American Revolution. Los Angeles: Center for Afro-American Studies and Atlanta: Institute of the Black World, 1980. p.108.的演说。需要指出的是,加维所参与的分离主义运动,是此类运动的“第一例,也是唯一的、真正的群众运动”(6)Franklin, John H.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Negro Americans.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69. p.492.。然而,随后而来的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生活在美国的所有族裔带来了同样影响,从而造成非洲裔美国群体已获得了平等权益的假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非洲裔美国群体的分离主义呼声,二战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黑人运动的目标在于融合,而非分离。(7)Hall, Raymond L. Black Separ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nover: UP of New England, 1978. p.93.当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 1925—1965)进入政治舞台中心时,分离主义再次获得势头,并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新高潮。这一时期的信仰体系核心是,白人大体上都是邪恶的,黑人大体上都是善良的,白人将会不遗余力地阻止黑人取得成功或种族团结。此外,非洲裔美国群体坚信,白人无意分享他们通过奴役黑人而获得的财富,故而黑人获得救赎的第一步便是远离“白人魔鬼”(white devil),与白人相分离。
虽然20世纪90年代黑人中产阶级的数量较之于30年前有了大幅提升,但贫困和不平等仍然是萦绕黑人社区的主要问题:“尽管担任公职的黑人数量显著增加,尽管我们可以在过去看不到黑人面孔的地方就座、用餐、出行、投票和上学,但我们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实际上,我们的相对状况是变得更糟糕了。”(8)Bond, Julian. “A Tale of Two and One-Half Decades.” Dream and Reality: The Modern Black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Equality. Ed. Jeannine Swift. New York: Greenwood, 1991. p.5.换句话说,非洲裔美国群体的境遇确实有所改观,但还远远不够。如果雷蒙德·霍尔(Raymond Hall)关于“从历史的角度看,黑人分离主义是白人排斥黑人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结果”(9)Hall, Raymond L. Black Separ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nover: UP of New England, 1978. p.17.言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美国已做好准备迎接分离主义运动的又一次复苏。
哈丁(Vincent Harding)认为,1975年标志着黑人权力运动的终结,这意味着分离主义运动将就此消亡。然而,分离主义似乎只是经历了短暂的蛰伏期,它正等待时机,蓄势而发。从奴隶制时期之于重回非洲的梦想,到加维,再到马尔科姆·艾克斯,分离主义信念均以暴力革命或不满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加维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则是霍尔称之为“压制分离”(10)Hall, Raymond L. Black Separ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nover: UP of New England, 1978. p.75.的分水岭——20世纪60年代是对分离主义思想的推崇期,20世纪70—80年代是“压制分离”的时期,而20世纪90年代是分离主义的复苏期。究其原因,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甚至扩大了。故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许多非洲裔美国群体而言,分离主义似乎再次成为一种可行的社会变革手段。另外,对大多数非洲裔美国群体来说,较之于融合主义,分离主义能更好地表达其意愿,而“接受融合主义如同否定黑人性一般危险”(11)Lemann, Nicholas. “Black Nationalism on Campus.” Atlantic Monthly,vol.271,no.1,1993,pp.31-47.。
不可忽视的是,分离主义的复苏也意味着,有着不同背景的美国群体及少数民族更加坚信他们不可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也不可能相互理解或尊重彼此。尽管如此,自加维起,分离主义便成为凝聚非洲裔美国群体的指导原则。作为20世纪60年代“黑即美”思想的前奏,加维鼓励黑人群体欣赏自己的黑皮肤,教导他们发现自己的美,并鼓励黑人通过与非洲取得精神上的联系,恢复自己的非洲性(African-ness),从而肯定自己的精神价值。随着分离主义的盛行,非洲裔美国群体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之根,并拒绝其文化遗产中的美国化部分,以此“维护族群身份认同或社群归属感”(12)桂榕、刘虎飞:《仪式的超越表征研究——以河口瑶族度戒仪式为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与此同时,非洲名字和非洲服饰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还变成了拒绝白人文化的活宣言。
加维抑或是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分离主义思想,经由文学创作表现出来,便成了虚构人物之于非洲文化根源和自我完整性的精神探寻。正如哈里斯所言,文化自觉的关键是,主人公将自己与主流文化成功分离,“越是能更多地浸润于民族文化的人物,越能更好地解决矛盾冲突。”(13)Harris, Norman. Connecting Times: the Sixties in Afro-American Fiction.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1988. p.5.换言之,在哈里斯看来,这些虚构人物实现精神完整的唯一途径在于拒绝西方价值观,在精神上与白色文化相分离,并想方设法与非洲精神相联系,重新获得非洲身份。他们必须“放弃所有违背人道主义的西方形象和思想……为了捍卫未来、走向自由,必须弥合西方文化在黑人共同体、历史和非洲精神之间所造成的脱节。”(14)Shakur, Assata. Assata: An Autobiography. Westport: Lawrence Hill, 1987. p.175.
爱丽丝·沃克的《拥有快乐的秘密》便书写了一位非洲裔美国女性试图通过分离主义以“收复部落领地、历史、语言和文化等所有关乎人性及完整生存的要素”(15)McLaughlin, Andree Nicola: “Black Women, Identity, and the Quest for Humanhood and Wholeness: Wild Women in the Whirlwind.” Wild Women in the Whirlwind: Afro-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naissance. Ed. Joanne Braxton and Andree Nicola McLaughli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90. p.176.的故事。在奥林卡部落受到欧洲文化侵袭的境遇下,村民们认为西方思想使塔西成了“怪物”,为了平息村民们对自己的“奚落”和“耻笑”,为了寻找失落的文化身份,塔西决定接受割礼,她认为这一古老的仪式能把自己和部落永久地联系在一起。(16)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120.因此,塔西向施割礼者(Tsunga)玛丽莎寻求帮助,她坚信玛丽莎能使她与非洲、与自己的文化之根重新连接起来。在塔西看来,“她认识到这是奥林卡传统中仅存的一个印记……她觉得,这个手术……会把她和那些想象中坚强的、不可战胜的女性联系在一起。真正的女人。真正的非洲人。真正的奥林卡人。”(17)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p.60-61.然而,割礼并不是她获得奥林卡文化身份的方式,而是压迫和支配女性的标志;割礼也并未为她失落的灵魂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让她的身体变得残缺不全,为她留下了永久的精神伤疤。
究其根源,是因为在与西方文化相分离,随后与部落文化再次取得联系的过程中,塔西没有认识到少数族裔女性的完整性生存,不仅取决于对白人主流文化的拒绝,还取决于对同族裔男权文化的反抗。作为非洲裔美国群体流散历史的起源地,非洲成为将所有非洲裔美国群体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空间,其特定的文化和仪式则成为想象再次回到单一的、原始的非洲之地之必要媒介。然而,认为非洲是非洲裔美国群体终极家园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错误的信念,即从未离开过非洲的黑人生活在乌托邦中。通过《拥有快乐的秘密》,沃克质疑了非洲是黑人终极家园的思想,抑或说粉碎了他们的非洲乌托邦信仰。
二、融合:接受割礼以融入奥林卡部落
史密斯(Felipe Smith)曾指出,“‘拯救生命’是爱丽丝·沃克的创作中心。在她的作品中,‘拯救生命’已超越书写主题,成为其美学核心”(18)Smith, Felipe. “Alice Walker’s Redemptive Art.” African American Review,vol.26,no.3,1992,pp.437-451.。根据史密斯的论述,“拯救生命”不仅表现在沃克的创作主题上,还体现在沃克与虚构人物的精神联系上。在《拥有快乐的秘密》中,这种精神联系便体现在沃克与塔西之间,通过塔西,沃克与“每年被施行割礼的8000万女性”(19)Wilentz, Gayle. Binding Cultures: Black Women Writers in Africa and the Diaspora. Bloomington: Indian UP, 1992. p.16.联系了起来。另外,沃克与塔西的精神联系,还将她与流散于全世界的所有非洲裔群体联系在了一起。缘于非洲及其流散地被奴役、殖民和压迫的苦难历史,非洲群体及其后裔对他们的文化身份有着复杂的理解,他们与曾同样被殖民、受压迫的美洲群体或拉丁美洲群体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因为非洲裔美国群体的历史建立在与故土分离的基础上。他们被强行带离自己的家园,继而被剥夺身份而遭受奴役,但作为土著非洲人的后裔,他们通过维护传统价值观念与祖先的精神保持着紧密联系。于是,正如上文所言,非洲成为一个浪漫的、神话般的特定起源地,成为将所有非洲裔美国群体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空间,他们想象着回到单一而固定的非洲,再回到遥远且古老的非洲去。
爱丽丝·沃克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重返非洲、与祖先文化取得联系这一书写主题。例如,《日用家当》中被子所承载的非洲传统文化,充斥《紫色》文本的黑人方言,“试图通过与祖先建立联系达到走向未来目的”(20)郭建飞:《记忆是救赎的钥匙——〈殿堂〉中的诺姆之力与记忆主题探析》,《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的《殿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沃克对重返非洲持有极为复杂的感情,正如《拥有快乐的秘密》所传递的思想一样,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理空间上的重返非洲,都会引发对非洲的误读问题。因为在沃克看来,虽然非洲是非洲裔美国群体的文化根基之所在,但它是父权制的。
对流散于世界各地的非洲裔群体而言,《拥有快乐的秘密》所描写的非洲绝不是他们的理想家园或梦想之地。在这里,他们想象中的非洲,不再是梦幻般的乌托邦,而是被填满罪恶、压迫、伤害和自我伤害的压抑空间。然而,从梦幻乌托邦到压抑空间,从终极家园到压迫之地,这一祛魅过程并不容易。
在一篇题为《寻找荣格:拥有快乐的秘密》(LookingforJung:WritingPossessingtheSecretofJoy)的文章中,沃克明确指出,荣格给了她揭示女性割礼的灵感和力量。1990年,沃克离开阿姆斯特丹,专程拜访了荣格在瑞士伯林根的塔楼别墅。这一时机后来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她设法进入了通常被锁着的庄园,获得机会通过触摸荣格的象征超验的“炼金术之石”(alchemical stone)与他进行精神交流;并且,她感到做好了使用“代表转变和超越的石头”信息的准备。沃克解释道:
我感到特别满足。我知道这是我在开始写《拥有快乐的秘密》之前必须要进行的旅行,这个故事的主题让我感到害怕。它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故事,甚至是一个禁忌,是一个古老的也是一个现代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将呼吁荣格的精神,以帮助我面对一种我们时代中的(也是数千年前的)对身体和心理造成巨大破坏的做法。(21)Walker, Alice. Anything We Love Can Be Sav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p.126.
女性割礼主题之所以是个棘手的问题,是因为其目的令人深感不安。“沃克和其他人理性地认为,割礼文化意图是绝对明确的,它意在剥夺女性性行为的快乐。”(22)Gates Jr. Henry Louis & K. A. Appiah.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Amistad Press, Inc., 1993. p.28.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女性容忍并自愿遵守这种做法。“用铁罐、玻璃碎片或打磨锋利的石头刃、在肮脏的地板上进行手术的图像是如此生动,如此伤人,如此辛酸,但更为突出的是,它是女性沉默、被操纵和自我厌恶的隐喻。”(23)Gates Jr. Henry Louis & K. A. Appiah.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Amistad Press, Inc., 1993. p.34.值得玩味的是,女性关系(尤其是母女关系)是沃克文学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例如,在《梅丽迪安》中,由于母女之间交流的缺失,青少年梅丽迪安不得不与传统妥协,结果给其带来了极大的身心伤害。较之于梅丽迪安以晕厥、脱发等表现出来的“身心伤害”,塔西所受到的伤害让沃克“感到害怕”,因为,受害者和受害者母亲参与了整个施害过程。因此,如果与荣格的炼金术之石没有象征性的联系,沃克会发现自己没有勇气来讲述女性如何被煽惑去参与破坏自身生理、心理和精神的故事。
事实上,沃克的担心不仅在于是否有勇气来讲述故事,还在于听故事者会做何反应。乔治(Olakunle George)对此进行了分析:“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本小说复制了传教士的傲慢而名誉扫地——将它视为一个开明的西方人解救黑人妇女于父权制的案例”(24)George, Olakunle. “Alice Walker’s Africa: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vince of Fi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53,no.4,2001,pp.354-372.。与此同时,乔治指出也可以从“自由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该小说,将沃克的文学实践与政治意义上的行动主义联系起来。那么,这便体现了她作为一名行动主义者,始终将“拯救生命”作为文学创作宗旨的做法。正如埃尔德(Arlene Elder)在一篇关于非洲女性通过写作来反抗不公平待遇的文章中所写到的那样,“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涉及艺术家的社会功能问题”(25)Elder, Arlene A. “‘who can take the multitude and lock it in a cage?’ Noemia De Sousa, Micere Mugo, Ellen Kuzwayo: Thee African Women’s Voices of Resistance.” Moving Beyond Boundaries: Black Women’s Diasporas. Ed. Carole Boyce Davies.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5. p.256.。沃克创作该小说便体现了作为艺术家的社会功能,她所讲述的故事足以动摇许多非洲部落的传统和文化之根。沃克的目的是执笔为剑,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改变妇女的被压迫状态,从而将文学创作与行动主义相联系。然而,正如上文所言,沃克在《拥有快乐的秘密》中所要拯救的塔西,并非单纯的受害者或被压迫者,让人费解的是,塔西主动参与了施害过程。
对此,成年塔西以回望的角度解释了青少年塔西急切地遵从社会的期望,主动接受割礼的根源所在:与西方文化相分离、对归属感的需求驱使她甘愿被施行割礼。皮弗(Mary Pipher)在《拯救奥菲利亚,拯救少女的自我》(RevivingOphelia,SavingtheSelvesofAdolescentGirls)中描述了青少年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波伏娃认为,青春期的女孩们意识到男性权力的存在,并认为她们唯一的力量来源是同意成为男性们顺从的崇拜对象。她们并非因为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阴茎嫉妒而痛苦,而是因为权力嫉妒。波伏娃说,‘女孩们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26)Pipher, Mary. Reviving Ophelia, Saving the Selves of Adolescent Girls. New York: Ballantine, 1994. p.22.皮弗继续解释,“女孩们变成了女性扮演者,她们试图把自己放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里,充满活力而自信的女孩变得害羞、怀疑,她们不再思考‘我是谁?我想要什么?’的问题,而是‘我该怎么做才能取悦别人?’的问题”(27)Pipher, Mary. Reviving Ophelia, Saving the Selves of Adolescent Girls. New York: Ballantine, 1994. p.22.。塔西既渴望成为一个完美的奥林卡女人,又想获得她的“西方”朋友亚当和奥利维亚的喜爱,并因此而左右为难。最终,她选择“变成”部落想要她成为的那种类型的人。
皮弗继续解释,青春期的女孩在压力下分裂为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女孩们被鼓励“放下真实的自我,只展示一小部分天赋”(28)Pipher, Mary. Reviving Ophelia, Saving the Selves of Adolescent Girls. New York: Ballantine, 1994. p.22.。塔西不知道,在努力与西方文化相分离、与自己的(非洲部落)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她最终将不得不分裂为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在她儿时的爱人和后来的丈夫亚当的记忆中,塔西“总是笑,爱编故事,或者在她母亲身边兴高采烈地跑来跑去”(29)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24.,他从未料到自己熟悉的塔西会消失。“消失的”塔西正是她放弃的那部分“真实的自我”——天真、乐观、无忧无虑;剩下来的“一小部分天赋”则和“曳步走”(30)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61.永远拴在了一起。
三、反抗:成为女勇士以抵制部落文化传统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ell)解释了个人经常会误解的某些类型神话的功能:“神话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秩序。有一种神话把你和自然以及自然界联系起来,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种神话属于严格的社会学的,它把你和一个特定的社会联系起来。”(31)Campell, Joseph. The Power of My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8.
塔西和部落里的其他所有年轻女孩一样,不知道“洗礼”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知道塔西急于成为一个革命者,做出和男人一样的牺牲,因此部落承诺塔西,她将被允许去模仿勇士们的做法。因此,塔西做了纹面,随后她的举止开始变得强硬,她此时的行为举止展示了她对权力的嫉妒。塔西从未想过勇士神话与理想的奥林卡女性神话之间有什么区别,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她相信所有的女人都是潜在的勇士。作为孩子,塔西忽视了她从来没有见过女勇士的事实,然而她所接受的思想不允许她对长辈试图通过操纵她成为一名革命者的愿望以达到宣传目的的做法进行质疑。塔西后来承认:“我当时很傲慢,姆贝尔夫妇派了一头被俘的驴子给我骑”(32)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30.,并且叛军让她“加入”他们的事业,这让她受宠若惊。受到强大的勇士神话的诱惑,加上青春期的不安全感,塔西最终成为奥林卡社会神话的牺牲品。然而遗憾的是,直至最后她才认识到,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勇士。由此产生的震惊和背叛感在塔西的自我发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己曾经骄傲的步姿变成了曳步走”(33)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61.。
显而易见,塔西急于保护的奥林卡传统,以及部落允许自己去做勇士的承诺,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神话编织的谎言。社会神话举着部落利益的大旗,堂而皇之地通过残害广大女性达到维护男性权益的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塔西的悲剧根源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神话,但是在塔西的直系亲属中,所有的男性都是缺场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就连塔西的父亲也是隐而不见的,在塔西的原生家庭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女性(母亲、姐姐和塔西)。或许,沃克在此想要传达的思想是,当青少年塔西飞蛾扑火般去接受割礼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神话,不仅是男性编织谎言的结果,也是所有女性共同参与的结果。换言之,沃克提醒我们,塔西的悲剧既归咎于男性,也归咎于女性。
塔西的母亲拒绝为塔西进行割礼,但她从未透露姐姐杜拉是因“洗礼”流血致死的实情;尽管玛丽莎认为塔西在母亲的保护下免受割礼之苦后又主动要求被割礼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她仍然鼓励塔西进行割礼。塔西深信:“玛丽莎为我做的这件事,表现了我以我的人民为骄傲;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男人会娶我。”(34)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179.塔西信任母亲和玛丽莎,但多年后,当玛丽莎承认自己当时说了谎时,她感到震惊。玛丽莎说,当她说女勇士们正在进行突袭时,其实她们早在几周前就已经怀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当这些妇女来到这里后,她们被要求做饭、打扫卫生,像在家一样被压榨着。当她们认清情况后就离开了。换作是我,我也会离开。玛丽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瘸腿说。”(35)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187.
尽管玛丽莎鄙视自己以及自己所做的割礼工作,但为了革命目的,她愿意牺牲塔西的幸福:“他们正在建造一个传统的奥林卡村庄,并打算以此为据点,因此他们需要一个会施割礼的人。他们派人来找我,给施割礼者一个工作,给社区一个象征目标。”(36)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187.玛丽莎的忏悔表明她无法抗拒自己被需要的欲望,她所在的社会环境使她无法保护塔西和部落的其他女人。同时,玛丽莎也意识到了男人们的虚伪:“难道我们的领袖没有保留他的阴茎吗?有没有证据表明他哪怕只切除了一个睾丸?”(37)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188.。然而,她们都不确定神话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迷信从哪里开始。
根据皮弗的阐释,塔西是一名典型的、在文化身份受到威胁时、没有父母引导的青少年的代表。强烈的归属感使她无视母亲的警告,“她只会说,只有努力才能填补空虚”(38)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26.,后来塔西承认,“我以前没有理解她的话”(39)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26.。在此,沃克重新回到关于女性之间进行交流的必要性这一主题,并提醒广大女性,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神话,会给她们的幸福带来巨大灾难。因此,女性必须学会区分这两种神话,那些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牺牲女性利益为代价的神话应该受到质疑;要想促进意识的转变,老年女性的经验和见解必须被分享,因为“你的沉默不会保护你”(40)Walker, Alice.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Womanist Prose.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275.。
沃克认为,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神话的“抵抗”必须从女性开始,她们不仅要打破沉默,恢复自己的声音,而且每一位女性都必须面对接受自己的挑战。沃克还认为,是荣格让她意识到每个女人都必须自己去判断文化信仰的真实性。因此,在小说中,心理医生梅泽伊是荣格的化身,他借梅泽伊之口,对塔西及其丈夫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梅泽伊提醒塔西:“你是自己最后的希望”(41)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95.。作为自己最后的希望,塔西需要回到事件的原初场景,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只有理解了所有事件,才能真正获得被拯救的希望。
塔西-伊芙琳(42)在小说中,塔西的名字有“塔西、伊芙琳、塔西-伊芙琳、伊芙琳-塔西、塔西-伊芙琳-约翰逊夫人、塔西伊芙琳约翰逊灵魂”六种变体。塔西指称的是遭受割礼摧残并由此而变得沉默不语的非洲女孩;伊芙琳指称的是美国公民的成年人塔西;塔西-伊芙琳指称的是一位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美国黑人妇女,而她在非洲时的经历占主导地位;伊芙琳-塔西指称的是美国化的黑人妇女;塔西-伊芙琳-约翰逊夫人是将自我意识、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相融合的塔西;最后删除了各种称谓中间的连字符且加上了“灵魂”指称的是彻底摆脱了社会和文化的束缚、获得了自我意识的塔西。参见水彩琴:《分裂与整合——〈拥有快乐的秘密〉中塔希的多重人格》,《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最终变成了一名勇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所反抗的是男人们试图维护的文化传统,她所抵制的是被视为旨在恢复黑人非洲性的文化传统。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和疯癫之后,她回到非洲,杀死了玛丽莎。这对塔西来说是一种象征性的胜利:她独自一人承担起了结束施割礼者工作的责任。从此,她从与世界分离的状态中幸存下来,通过重新控制自己的思想而获得力量,并从自己的行为中找到答案——“反抗是拥有快乐的秘密”(43)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215.。
在众多的历史事件中,谋杀有时会受到称赞,有时则会招致批判。一些同胞视塔西为救世主,而另一些人把她看作杀人犯。在《拥有快乐的秘密》中,沃克并未言明塔西是否料到自己的行为会招来同胞们的敌意。毫无疑问的是,在小说所设定的故事背景中,塔西的谋杀行为最终促使她成为一名勇士,一位英雄——她从残忍的割礼中幸存下来,继而在疯癫中迷失方向,最终发现了有助于理解自己生活的意义及力量源泉。塔西回到非洲的同时,也为她的国家带回了一份礼物,一条送给她的国家和全世界女性的讯息。不幸的是,她成了一位永远回不来的勇士或英雄。塔西-伊芙琳的讯息是极具革命性的,如果得到重视,它将结束几代人的痛苦。然而,她所选择的方式对既有权力结构造成了困扰,她所传达的讯息因此被置若罔闻。男人们从内到外对她进行痛击,迫使她像以前那样,遵守社会的既定规则;他们理解塔西反抗的原因,这也是为何他们要将她处死的根源所在。沃克并未对塔西的判决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安排成百上千名女性排队跟在她的后面,借此让塔西明白她们理解塔西为所有女性所做的牺牲。因此,《拥有快乐的秘密》的结局更像是对那些试图成为勇士或英雄的女性发出的警告。
在小说中,沃克为我们展示的塔西是一个趋于灭亡的非洲部落的成员。她看到了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传统部落生活的影响,她坚持维护自己的非洲传统。在她年轻的头脑里,没有讨论和商量的余地——她从未考虑割礼手术的痛苦,以及它会为自己带来的后期影响,她所关心的只是保护奥林卡人的生活方式,保护奥林卡的古老传统。
然而,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那样,为了加入女勇士的队伍、为了保护奥林卡的传统,塔西自愿进行割礼。而正是当塔西“自己曾经骄傲的步姿变成了曳步走”(44)Walker, Alice.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1. p.61.时,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让她突然明白,进行割礼并不能让她成为勇士,被施以割礼也不能成为她为保护部落传统而战的筹码。
四、结语
当文化身份受到欧洲文化的威胁时,塔西以为切断与白人的一切联系,与其保持距离,继而试图通过“能将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45)Allen, Paula Gunn. The Sacred Hoop: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5. p.49.的部落仪式,就能实现文化身份的建构。因此,她将割礼视为与非洲文化之根相连接的唯一途径,认为割礼仪式能将自己“转变”成“真正”的奥林卡人。为了拒绝白人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塔西求助于她唯一知道的、可以确保其非洲性的方式,而她所不知道的是,这一方式不仅没能恢复其文化身份,甚至还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性。由此可见,塔西在与非洲文化重新连接的努力中,忽视了部落文化中的男权主义思想,忽略了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殖民过程,首先是以铲除其母系氏族文化之根的史实:“入侵者不遗余力地将女性从当权者的位置上赶走,消除一切有关母系氏族社会制度的记录,确保没有任何人知道1800年之前母系社会曾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运行方式。”(46)Allen, Paula Gunn. The Sacred Hoop: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 New York: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5. p.19.
在爱丽丝·沃克看来,非洲裔美国女性想要免受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压迫,最根本的改变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名英雄(勇士),而不是受害者,这需要她们分清社会神话和女性神话之间的区别,让她们认识到社会神话是为了伤害妇女而创造的事实。这一简单但极具革命性的行为,终结了父权制社会中严格的性别对立。小说之于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的书写,对于反思当代世界中人类普遍面临的身份焦虑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