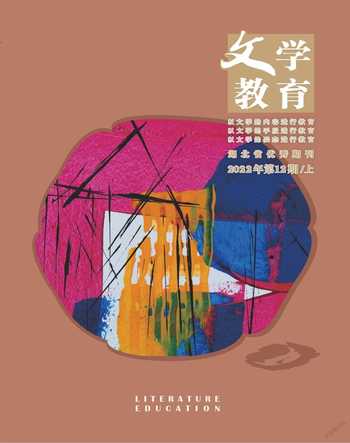李佩甫《生命册》中吴梁人生活群像
曾叶 李胜清
内容摘要:《生命册》是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终结篇,在这部作品中,他以一个吴梁孤儿进入城市后的奋斗历程为叙事主线,展开城乡双轨对照书写。作者运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刻画了民间生存困境下平原儿女的顽强灵魂,表现了在城乡文明冲突下个体生命的轻盈与沉重。小说人物在寻找与漂泊中逐渐异化的心灵,隐喻了乡土广阔图景背后的生存经验。
关键词:李佩甫 《生命册》 吴梁人 群像 城乡文明冲突 生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传统的中国社会确有这一明显特征。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飞速的发展进程迈入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行列,传统田园牧歌式的瓦片篱笆被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取代,小桥流水人家的恬静安然被高楼林立的威严肃穆置换,过去的故乡成为永远的“乌托邦”,在每一个现代“游子”的脑海里留存。当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变得支离破碎面貌全非时,当代作家在“乡土何处寻”的困惑与茫然中,开始重新审视和书写这片黄土地。其中,河南籍作家李佩甫从写作初期就带有明显的“平原印记”,他通过自己的系列作品认真记录了现代化浪潮下的乡土裂变,以及在时代潮流裹挟下这些父老乡亲们的悲喜人生。特别是《生命册》这部作品,以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的叙事构型,展现了吴梁儿女在现实生存规约下的悲喜人生,挖掘出这片土地孕育出兼具诙谐与庄重的生命特质。
《生命册》以单数章节书写“我”的城市经历,以偶数章节记录无梁百姓生活。写城市的笔调急促而又粗糙,大多是印象型的而稍显空洞;写熟悉的平原土地则是经验性的真实深刻,节奏平缓且笔触细腻。小说主要塑造的人物有七个,其中城市篇以“我”和“骆驼”为主,“我们”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寒门子弟”。乡村篇每章一个主要人物,分别是蔡国寅、梁五方、虫嫂、杜秋月、春才,以及由这些人物延伸出的相关家庭成员。以上人物主要可以分为离开土地的“流浪者”、“乡土化”的城市阶层、融入城市的“异乡人”、“被异化”的乡野小民四类。
一.离开土地的“流浪者”——身份认同危机
关于身份认同,西方早有相关理论论述,例如萨义德指出:“身份……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扯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扯到对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①小说中“我”和“骆驼”从离开土地那一刻起,就一直存在身份认同危机问题。
文本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我”——吴志鹏,一个吃吴梁村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从故事开篇,他就表达了自己急欲脱离这片土地,成为一个正牌“城市人”的愿望。但一踏入城市,他又面临着无所适从的“惶恐”。“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呼吸着寒森森的空气,就像走在荒原上一样,满心的凄凉和荒芜。”②5现代性都市带给他的体验是陌生和荒芜,他以一种敬畏又怀疑的态度打量这座城市。安家立业,无疑是让自己融入城市的唯一途径,吴志鹏努力让自己在城市扎根。但在一切初有起色的时候,一连串的电话打断了他的奋斗计划,来自吴梁村民们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让他手忙脚乱。一个初到城市还未站稳脚跟的青年,经济实力和人脉关系都不足以支撑起乡亲们的诉求,但吴梁近三千村民的“人情债”却也让他感到既可悲又无奈。一方面,他惭愧,吴梁的每一个村民对他有养育之恩;另一方面,他懊恼,他一直为自己扎根城市的目标努力奋斗,却还被领导指责“一身的农民习气”。当现实的欲望战胜了内心的愧疚时,吴志鹏选择了从吴梁这张“亲情网”中出逃。正是这次辞职上京,他与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骆驼,开始了追求金钱的疯狂之旅。骆驼原名骆国栋,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到经商谋划时步步为营的缜密果断,无一不表现出极高的个人天赋。但随着“身价”的水涨船高,骆驼也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迷失自我。他通过收购“空心”药厂,成立上市公司,投机倒把操控股市。他多次触及道德和法律的边线,玩转权术人脉,利用金钱利益关系一次次跨越壁垒,最终“失手”后选择跳楼自杀。
聚焦两人的城市奋斗史,可以看到他们努力在“塑造”和“阐释”自己的城市身份。吴志鹏极力融入单位集体,却始终被他人“另眼相待”,后来他才恍然明白:黄土印记早已刻进骨血之中,使他无法融入城市,只能成为一个都市的“流浪者”。而骆国栋,出身贫寒加上天生残疾,也许正是深藏心底的自卑和不甘落后的好胜,促使他对金钱的渴望早已到了無以复加的地步。他们都太想成功,也迫切希望得到他者的认同与尊重,但两人之间还是存在本质差异,即对待故土的态度截然不同。吴志鹏始终背负着养育他的土地前行,即便最初他也想要摆脱吴梁,但当在城市寻求不到归属时,他才发现能依托的只有乡土。正如贯穿全文的“白条”,就是乡土羁绊的现实隐喻。“我身后是有人的”,这些人是吴梁的父老乡亲们,是这片土地赋予他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所以他能清醒地及时止损,重回旧地寻找梅村。同样出身农村,骆驼却是个背弃土地的游子,在金钱、权利、女人这些充满了欲望的符号面前,他无止境地扩张自己的欲念,在成功之后也逐渐迷失自我,将与自己同出身的底层人民视为“下人”。他的狂妄自大蒙蔽了内心,也因此埋下祸根,导致了最终惨败的结局。一个不知“来处”,心中没有故乡根基的人,是永远无法站稳脚跟的。
二.“乡土化”的城市阶层——土地同化魔力
吴梁村有两个以“外来”身份踏入这片土地的人——蔡国寅和杜秋月,他们一个是军官,一个是知识分子,却在平原的日晒雨淋中,逐渐被同化成一个“土生土长”的吴梁人。
蔡国寅上过战场立过功,文中说他是“高薪阶层”,却因为迷恋上吴梁女人阴差阳错丢掉了军籍,成为吴梁村的上门女婿。“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他与吴梁的任何一件物事都浑然一体......当年的上尉连长蔡国寅自从脱了军装后,已经是吴梁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②48发生巨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婚姻带来的无限苦闷和一地鸡毛。婚前吴玉花对成为一个军官夫人的想象,和婚后发现自己嫁了个农民的事实,让她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也因此打心里看不起丈夫。后来的“裤腰带”事件作为引发二人矛盾的导火索,让这段本就不幸福的婚姻生活“雪上加霜”,他也因此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老姑夫就此蹲了下来。在吴梁,老姑夫入乡随俗的第一个姿势就是‘谷堆。‘谷堆是个象形词,就是蹲下的意思。”②61在婚姻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蔡国寅当初在前线屡立战功的威风早已被消磨殆尽,蔡国寅变成了“老蔡”。
杜秋月是因为“犯了错误”被下放到农村改造的,初入吴梁,他既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迂腐清高,又有一种被拿住“小辫子”的胆小怯懦。在所有当地人视同穿衣吃饭一般寻常的琐事里,这个“五谷不分”的知識分子显得格格不入。刚开始被安排在村里挑尿,他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楚,戴口罩穿胶鞋的装束也被人嘲笑。后来到小学教书时,杜秋月找回了一点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价值,但很快就在“红袖章”的批斗大会中被整治地抬不起头来。婚后生活也不如意,“刘玉翠本以为她是嫁给了‘文化,可‘文化中听不中用,成了一个摆设。”②328在所有需要农村经验的生活里,他的那套知识彻底“失效”了,衣食住行样样都得依靠妻子。获得平反后的杜秋月大有“扬眉吐气”之感,他开始对自己的“糟糠之妻”感到不满,于是设法办理了离婚,事后恍然大悟的刘玉翠大骂他是“慢毒药”。但即便杜秋月主观上决不愿再回吴梁生活,但现实并没有让他“如愿以偿”。在同刘玉翠“你躲我追”的拉锯战中,杜秋月最终扛不住身心压力瘫痪在轮椅上,晚年只能依靠前妻照顾,又回到了当初在吴梁的生活状态。
不得不说,这片土地似乎有一种魔力,解构“高大神圣”归于“凡尘俗事”。实质上,这也同样存在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吴梁虽然没有“排外”倾向,但这个脚蹬皮靴开着吉普,满嘴东北普通话的军官,以及穿着皮鞋系红色围巾,喝醉了就背诵《离骚》的知识分子,显然都是与吴梁民间生态迥然不同的。对于“外来人”自身而言,他们先前的一套知识体系并不足以很好地适应当地生活。而乡土社会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土著居民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生活模式和土地经验,去顺应自然变化维持更好的生存。“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就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③31实际上,城市有城市的经验,乡土也有乡土的文化,当“外来人”走进吴梁时,为了更好地融入族群生活,只能半主动半被动地去接受当地的文化习俗,所谓“入乡随俗”就是这个道理。
三.融入城市的“异乡人”——都市气质转化
“农民市民化是指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社会变迁过程。”④除了吴、骆两人是“背井离乡”的打拼者,还有刘玉翠、蔡思凡、吴大国兄妹三人也是主动离开乡土,拥有市民新身份的“异乡人”。
刘玉翠是在机缘巧合下被撮合与杜秋月一起生活的,没想到在漫长的婚姻岁月里,丈夫全然“无用”,日常生活全靠她一人操持。当老杜因为平反的事缺钱又撇不开面子时,她毫不犹豫出面向乡亲借钱借物凑齐资金。但杜秋月竟然在事成之后想要甩掉她,刘玉翠咽不下这口气跟丈夫较上了真,从县城到省城一路“穷追不舍”。而在她的“围追堵截”之下,老杜不仅工作不顺,身体也每况愈下。从前瞧不起小学教师的杜秋月,竟然连小学资质都荒废掉了,最后只能提前退休,成了半个“废人”。反观刘玉翠,因为踏实能干在城市逐步扎根,结尾说:“刘经理在省城已买下了三室一厅的房子,买下了户口,已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了。老杜得了脑中风住医院后,穷困潦倒,身边也没有什么人了,着实也离不开刘玉翠了。”②346
蔡思凡最早是离家出走懵懂闯入城市的,她本名叫“蔡苇香”,是老蔡最喜爱的三女儿。但也许是父母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她厌烦,又或许是春才自我阉割使她受到了震撼,她成为了一个乡土的“反叛者”。文中说到蔡思凡十七岁突然失踪,很多年都杳无音信,在城里的洗脚城出现时,已完全是城里人打扮了。后来她因为砸了洗脚城的玻璃被抓到看守所,要吴志鹏去赎她。此时蔡思凡已怀有身孕,但不知道是谁的孩子,话语眼神里全是对老蔡乃至整个吴梁的恨意。但多年后,她再次回到吴梁是作为一个成功者的身份归来的,乘着出租车衣着光鲜地进入村庄,给家里修了全村第一个三层的楼房,让村人羡慕不已,后来更是摇身一变,成为板材公司的“蔡总”。
吴大国兄妹是虫嫂的孩子,因为父亲残疾,全靠母亲一人撑起整个家。三个孩子在独立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母亲断绝联系,和吴梁划清界限。从成长经历上来说,从小受人冷眼,被同龄人欺负,自然让他们对名声极差的母亲并无好感,不被尊重的遭遇也让他们更加爱惜自己的脸面。可笑的是,从未尽孝的三兄妹,听闻母亲死后突然出现“遗产”时,争相返乡要为母亲行孝。事后三人大吵一架,彼此间再也不来往了。故事结尾处,吴大国和妹妹三花因老蔡葬礼回村了一趟,此时大国已经是县民政局的副局长,吴梁人都尊称他为“吴局长”,再也没有人提起他母亲的“不堪往事”。
刘玉翠和杜秋月夫妇的身份转化固然显得滑稽可笑,蔡思凡和吴大国兄妹人前人后的反差也极具讽刺意味。蔡思凡从小被母亲灌输了对父亲的敌意和憎恨,她的一切反叛行为都成为老蔡的“一块心病”。但在父亲死后,蔡思凡风光操办迁坟仪式,全然一副孝女模样,让村人啧啧赞叹。而从未关心过吴梁一草一木的吴大国,在葬礼上看到老蔡的多块军功章,发觉这是自己故乡的“荣耀”,连夜向书记和县长汇报,想要把老蔡树立为全县的“典型楷模”。这些都发生在老一辈吴梁人去世之后,而当吴志鹏再一次回到吴梁时,发现物是人非,乡土已不再是过去的模样,弥漫在他心头的是一种“无处归依”的虚无与迷茫。
四.“被异化”的乡野小民——世俗眼光排挤
吴梁有两次“群体性疯狂”,都与这些“被异化”的乡野小民有关。“只要不自由的社会仍然控制着人和自然,被压抑和被扭曲的人和自然的潜能只能以异在的形式表现出来。”⑤乡土社会有其固有的一套规约维持着地域的稳定,它更多地是以道德形式和观念力量无形地施加在人们身上。正是这样一些带有吴梁特质的群体性“世俗”眼光的排挤,引发并最终导致了这些平凡人物的悲惨遭遇。
虫嫂无名无姓,文中只说她被吴梁人称作“小虫儿窝蛋”。因为身材“袖珍”,她从刚嫁入吴梁时,就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在无梁,‘虫儿就是小的意思,也是低贱的意思。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②220第一次集体劳动,她就偷拿公家“财产”。后来一次偷盗被抓,老光棍以性作为交易放过她后,再遇困难时,虫嫂几乎习惯性地以“宽衣解带”作为解决路径。文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虫嫂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了。她破罐破摔了。”②229但虫嫂很快就遭到了吴梁女性的报复性围堵,她赤身裸体在雨中奔跑呼救,身上流血不止,男人们却只敢默然旁观。但就是这样的虫嫂,靠这些并不光彩的“物资”,在艰难岁月里把三个孩子养育成人。后来她又靠卖血拾荒给孩子们挣学费,但即便如此,身份的低劣和满身的臭气,虫嫂也从未赢得孩子们的感恩,最终落得无人问津的结局。
梁五方是个手艺高超的匠人,因雕刻麒麟脊而名扬四方,却也因此越师自立门户。梁五方以为这是件好事,却实际为他的命运悄悄埋下了祸根。“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③75梁五方在吴梁村显得十分“不合群体”,无论是建房还是结婚,他都没有让乡民们参与。众人对他的不满在“公社运动”中得到了集中爆发,从揭发“罪状”到施加暴力,最后梁五方被没收所有财产。此后,他独自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曾经赫赫有名的“龙麒麟”沦为了一个“流窜犯”,一个彻底的“流浪者”,最后打着“半仙”名号,靠四处给人算命维持生计。纵观其一生,梁五方的命运轨迹显得荒唐又滑稽,曾经少年意气行事莽撞,论能力也算“佼佼者”,却只落得人生惨淡收场。
春才是小说中最具荒诞色彩的一个人物。无论外貌条件还是编席手艺,春才都堪称优秀,但他却因为自身无知和本能羞耻,堕入了人生的修罗场。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在吴梁已婚女性“半含半露”的性语言挑逗下,性意识开始觉醒。他与同村的蔡苇秀情投意合,本应是段好姻缘,却因为蔡母放出话来要找个“城里人”做女婿,春才不敢贸然戳破窗户纸。“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③79在“洗澡偷窥”事件之后,众人的揣测和流言蜚语,让春才为自己无法压抑的性本能而感到羞耻,于是在望月潭里完成了具有“审判—惩罚”双重意味的自我阉割。对于这一行为,吴梁人疑惑、恐惧又嘲笑,疑惑他的这一自戕行为,恐惧望月潭里的神秘力量,嘲笑并得出吴梁的一句歇后语“春才下河坡——去逑。”曾经众人争相抢购的春才炕席,也因为贴上了“不祥”的标签而无人问津。后来他的手工豆腐也在市场化竞争下被淘汰出局,生意惨淡晚景凄凉。
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在现实的观照下,透出诙谐又悲凉的底色来,但小说中却说“这也是我们家乡人的最大优点,那就是用戏谑的口吻,微笑着面对失败。”②157实际上,这种“笑”既包含了对生存的希望,也有对现实的无奈,既有反抗命运的挣扎,也有沉沦人生的颓丧。“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化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这就是狂欢式的笑。”⑥这些乡野小民不过都是被世俗异化的可怜人,虫嫂以强大母性支撑她背负家庭重担在夹缝中努力生存,梁五方满身傲骨在人生齿轮的滚动下只剩滑稽与荒凉,春才在本能宇宙和道德规范的冲突下沦为命运的囚徒。当个人追求和公共道德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只能走向命运的边缘。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吴梁百姓的命运书写,真实展现了现代性冲击下人与土地的裂变与阵痛。关于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譬如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个人与时代、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文明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西方哲学家早有相关探讨和反思。康德就提出了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二律背反,辨析了其自身蕴含着合理和不合理的双重质素。一方面,现代都市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潜力对年轻人充满了诱惑,新一辈的平原儿女在这种对城市的无限想象和向往中,主动脱离土地走进城市;另一方面,在城市苦苦打拼多年的经历却告诉他们,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无法带给他们真正的归属感。但当他们想要重回养育自己的那片黄土地时,却又突然发现随着老一辈平原儿女的逝去,曾经的故乡也湮没在现代化的时间进程中。这时弥散在他们内心的是一种无法言明的漂泊感和无根感,游子“流落异乡”的愁苦变成了“失落故土”的苦闷,没有归属的迷茫转变为无处寄托的惆怅。“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恰如波曼所言: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⑦我们无法阻挡现代化进程的激进步伐,却也能够通过当代作家的作品,观照到这些处于时代转型下真实的民间生存史和个体生命录。
参考文献
①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26.
②李佩甫.生命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8月北京第1版,以下原著引文均出自这个版本,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M].青岛出版社,2019年10月第2版.
④张传泉.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4(5).
⑤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C].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12.
⑥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4.
⑦齐格蒙特·鮑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3-4.
本论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项目“新世纪中国形象文学书写的传统文化元素研究”(编号:XSP18ZDI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