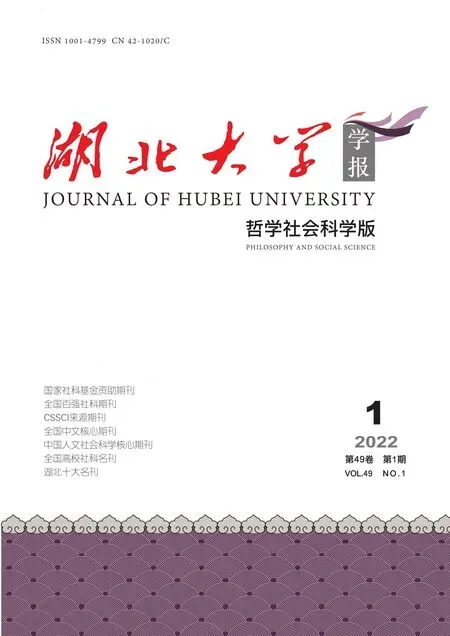反谱系学、多元体与非地域化
——德勒兹“块茎说”的伦理学阐释
张 能
(西南大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重庆 400715)
德勒兹(Gilles Deleuze)那里有伦理学吗?若有,是何种伦理学?这是在德勒兹思想研究领域颇具争议的问题。德勒兹一生研究涉猎学科极广,但在其生前出版物中,少见有关于伦理学的专门言述,我们似乎很难说有一种“德勒兹的伦理学”。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其没有伦理动机和伦理关怀。对于德勒兹来说,对伦理学的思考并不意味着要立大部头著作去引发伦理学思潮,他的哲学思索虽没有冠以伦理学的名义,但都可以视为其迈上伦理致思道路上的步骤。譬如,德勒兹对块茎(rhizome)这一思想理论的大篇幅概述,就是其生态伦理学思想的奠基。德勒兹的块茎理论是追求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内在价值支点,是洞见德勒兹生态伦理学的重要维度。探讨德勒兹的块茎理论,我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考量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与各种物种及不同领域间应有的平等关系,以一种共生互融的伦理观念重新考察并规定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重视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揭示生命整体的内在价值,克服对自然孤立式的认知和分析,将德勒兹的块茎理论深深地嵌入生态伦理学的论域当中加以审视和确定,据此才可揭示德勒兹块茎理论所涵摄的生态伦理思想要义,从而透显出德勒兹块茎理论之“生态伦理”的独特旨趣。
一、“反谱系学”:拒斥二元论和理性主义
生态伦理学是联系现代生态学与伦理学的新兴交叉科学,它的主要功能是塑造和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就建立起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但是随着人类对大自然不断展开疯狂掠夺,一系列生态问题开始产生,人们逐渐认识到,据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偏狭构成了地球生态伦理环境恶化的本质。人类要想提升地球生态伦理坏境的质量,就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及伦理关系。仅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优先视角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要想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还有待形成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即块茎思维。“块茎”原指一种植物茎,德勒兹和加塔里在著作《千高原》(1980)的前言中,用“块茎”这一语词来描述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哲学据于因果关系、等级体系、二元结构进行思考的思维方法。不过德勒兹创立块茎思维,并非要对抗西方传统主导思想,倘若如此,只会创造出一个二元区分(区分正确与错误的思维方式),也并非试图用“块茎”思维一统天下(1)Damian Sutton,David Martin-Jones,Deleuze Reframed:Interpreting Key Thinkers for the Arts,London:I.B. Tauris,2008,pp.3-4.。为了更清楚地刻画和描述这一思维特征,德勒兹将“块茎”与两种类型(形象)——“树-根结构”与“侧根结构”——进行了对比。
第一种类型是“树-根结构”。在此结构之中,所有的东西都从中央树根分支出来,小躯干从较大的躯干中分离出来,如此这般,然后回到坚固的核心。这会涉及到一种有关权力集中的形象,或者说它不仅仅指向了这一形象:它表象了一种集权的模式。根据德勒兹,在树-根结构的模式中,庞大的概念体系是中心化的、统一的、等级制的。关键这一基本形象直接隐射到“中心主义”或“二元中心论逻辑”的根基统治。“树有各式各样的特征:树有起点、胚芽或中心;树是二元机器或二分法原理……,权力总是树状的”(2)Gilles Deleuze,Claire Parnet,Dialogues,Paris:Flammarion,1996,p.33.。
第二种类型是侧根系统,或须根。侧根或者须根自身不是主根,虽然主根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其根的统一性仍然是存在的。这种须根系统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摆脱源自于统一性的控制,毋宁说它是一种“替补的维度”,而这种“替补的维度”亦标识着更高的、矛盾的统一。根据尤金·W.霍兰德(Eugene W. Holland)的分析,这种“替补的维度”并不是保有其坚实性作为一个生命所必须的维度。德勒兹和加塔里则聚焦于坚实性,坚实地存在(con-sist)是要一起存在而不是意外着“敞开”:共存,多重的“和”与“一起”的逻辑,而非单独是“存在”(being)的逻辑(3)Eugene W. Holland,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A Reader’s Guide,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3,p.12.。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反复强调一种“多”(“和”与“一起”),而不是“一”(单独“存在”)。德勒兹指出:“‘多’是必须有待形成的,但不是通过始终增加一个更高的维度……在n-1的维度上写作。这种类型的体系才被称为块茎。”(4)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t,Milles Plateaux,Paris: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80,p.13.译文参考了德勒兹、加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德勒兹认为,在对“多”的生成论的构建中,不能以一种叠加的“替补的维度”来获取一种表面性的“多”,“多”的实质是在减法里,而不是在加法里。因为,只有在简单的减法当中,作为根基的“一”才能作为“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统的思想当中,“多”总是作为“一”的流变产物或者现象而得以规定的。现在德勒兹要颠转这一思想传统,即,将统摄“多”的“一”还原到“多”中去,“一”也不再独尊其大。相反,根据德勒兹,“多”构成了 “一”,继而变成了“单一的多重性”(5)戴米安·萨顿(Damian Sutton)指出,我们不应该总把事物简化为“一个事物与它的诸多他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而是多构成的一;不是一和多重他者的关系,而是单一的多重性”。具体参阅Damian Sutton,David Martin-Jones,Deleuze Reframed:Interpreting Key Thinkers for the Arts,pp.4-5.。
然而,不同于“树-根结构”与“侧根结构”,块茎指认了这样一种思维范式,即,不再将事物看作是基于主体中心设定的事物,不再将事物看成是僵化的、等级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单元化的系统,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如植物的根茎或者“洞穴”式的多元结构。在这种多元性的结构当中,没有等级性的关系存在,只有繁复流变的共存的“单一的多重性”。块茎是一个去主体化、去中心、非等级和非示意的系统。它不再是二元分化的,它没有“开端”(commence)也没有“末端”(boutit),它始终执着于“中间”(milieu),在事物之间,在存在者之间。这其中,根据德勒兹,“中间”、“之间”并不是表示一种中间的均值,相反,它指示的是一种地方。在这个地方,事物可以不断地作加速运动(“解域—再结域”)。而且事物之间也并不意味着某种关联,而是一种方向,一种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勒兹的块茎结构与树的组织结构存在根本性的区分。但是德勒兹试图说明,块茎不是一种对抗性的思维模式。森林与树这两种比喻性的意象表征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德勒兹也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块茎”,树的思维模式充其量只是使用了“块茎”一个方面而已。这种表征没有等级关系及谱系的“块茎说”是要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万物一同处于一种流变共存的自然共同体内,没有所谓的“单一的人类价值尺度”(“一”)。植物、动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并不能被“单一的人类价值尺度”所剥夺或者内化。整个生物圈内只内存在于“单一的多重性”,并在这种“单一的多重性”相互渗透,使得整个生物圈中的不同个体协调共生。或者说,道德关怀的范围并不是建基于一种类人性质的体系。恰恰相反,应该将价值视域和道德扩展到整个人类生态系统,而不单单拘泥于自然中心体系。但是,“人们习惯于根据对自己的有用性来评价事物。由于受脾性和情境的摆布,认为自己是大自然至高无上的造物”(6)David W. Ehrenfeld,The Arrogance of Human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76.。由此,我们知道德勒兹的“反系谱学”的块茎所涵摄的伦理要义实质就是强调一个整体的生态坏境系统,它是建立在整体主义立场基础上的,并且主张价值是内(在)生的。
进一步,块茎 “同时也包含了对二元论和理性主义的否定”(7)Damian Sutton,David Martin-Jones,Deleuze Reframed:Interpreting Key Thinkers for the Arts,p.4.。笛卡尔作为二元论的典型代表,认为动物就是“没有思想的野兽”,是机器装置,是机器。既然动物与机器不存在某种区分,那么对于动物而言,人类无须承担任何相应的道德义务(8)在给纽卡斯尔侯爵的一封信中笛卡尔写道:“如果动物像我们一样具有意识,那么它们就会像我们一样具有不死的灵魂。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相信某些动物具有不死灵魂但不相信所有动物都是如此,这是没道理的。而许多像牡蛎和海绵这样的动物太不完美了,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具有不死的灵魂。”具体参阅Anthony Kenny,Descar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08.。但是不同于动物,人类是有灵魂的,这种灵魂并不显露在其外,而是蕴藏于松果腺之内。因此,在二元论者看来,动物并不会和人类一样能感知到痛苦或者快乐的激情,或者说,动物缺乏这种情感感知的能力。动物只会对外界作出一种机械的反应。以此推论,人类在屠杀动物时,动物发出嚎叫只不过是对屠杀行为本身的一种机械式的反应,并不是因为感知到痛苦。利奥诺拉·罗森菲尔德(Leonora Rosenfield)说道:“(笛卡尔式)科学家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对狗进行殴打,并且取笑那些怜悯这些生物的人,好像他们也痛苦一样。他们说这些动物是时钟;敲击时它们发出的叫声只是被触摸过的小泉发出的声音,但是整个身体却没有感觉。他们将可怜动物的四只爪子钉在木板上,检查它们的血液循环,这引发了很大争议。”(9)Leonora Rosenfield,From Beast-Machina to Man-Machina,New York:Columbia,1968,p.54.相较于二元论,理性主义则以理性能力为主要考量标准来进行道德划界。在理性主义者看来,道德地位的优越性取决于理性的能力。比如人的道德地位优越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康德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认为只有人在进行理性思考时,才能获得道德关怀。由此,道德关怀的获得与是否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关联,动物由于不具有理性推理的能力,故不应获得相应的道德关怀。不仅于此,康德还认为,动物不作为道德主体,但人关于动物负有间接义务,即任何虐杀动物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10)在康德主义内部,围绕着“人关于动物负有间接义务”存在许多争论,批评者们往往认为康德将动物视作为“事物”而与人的理性特征区别显得过于狂妄与冷酷,并忽视了动物的感受,他们试图赋予动物以道德地位,这就已经站在了整个康德义务论体系的对立面。出于自然的可传达性的同情可以实现将间接义务还原为直接义务,而无需赋予动物以任何道德地位,亦无需借助道德情感或道德类比,或进行同一性论证。出于自然的可传达性的同情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直观,由此作为我们不能虐待动物并且需要善待动物的依据,这也表明了“人关于动物负有间接义务”并非与我们道德直觉相去甚远。具体参阅叶骏:《人关于动物是否有义务?——从康德义务论体系谈起》,《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7期。。然而,德勒兹的反谱系学的块茎作为一种思维范式直接克服了二元论和理性主义的短视。根据德勒兹,无论在时间次序(先后)还是在空间次序上(中心与边缘)都在块茎当中消失殆尽。由此,凡是具有生命的,就应该值得我们去尊敬和呵护,所有的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并且一律平等。因为,在块茎中只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维度,维度与维度不存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差异,而这也是由于块茎本身就是作为“反谱系学”而决定的。德勒兹的块茎生态伦理思维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人类只是作为一个成员而不是主体的成员参入到自然的进化中来。因为,就其自然创造的实现而言,大自然的整个系统及其构成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有其自身价值的。关于这一点,德勒兹与当代动物生理学家唐纳德·R.格里芬(Donald R.Griffin)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唐纳德·R.格里芬看来,“一旦我们对问题进行反思……,一个动物越是能更好地理解其物理、生物和社会环境,它就越能调节自己的行为,已完成其生命中很重要的任何目标”(11)Donald R. Griffin,The Questions of Animal Awareness:Evolutionary Continuity of Mental Experience,New York: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Press,1976,p.85.。换言之,鉴于意识的生存价值,人们必定会期待它呈现在许多物种那里,而不仅仅是呈现于人类物种。
二、“多元体”:去人类中心主义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块茎结构“代表着后现代思维的模式,它是动态的、异质的、非二元对立的。块茎意味着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是朝着多个方向而不是朝着一个方向流动的;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永远处在运动之中;它是非地域化的(12)参阅冯俊、弗兰西斯·弗·西博尔、高宣扬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27页。。根据德勒兹的考察,在块茎的多元体系中,任意的两点都存在连接的可能性,并且必须被连接。诚如让-克莱特·马丁(Jean-Clet Martin)所言,“它不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相反它在每一端点处都是遭遇一种新的路向,并且在每一端点都能敞开一种新的连接,这种连接是朝向外部开放的”(13)Jean-Clet Martin,Variations:The Philosophy of Gilles Deleuz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p.130.。这种块茎不同于树或者根,因为无论树或者根都固定于一个点,树状的逻辑强调的是系动词“to be”,或者说强调的是一种主词逻辑,而块茎的逻辑构架则依赖于连词“(et)and…(et)and…(et)and”。德勒兹说:“ET(和)甚至不再是连词或者特定关系,它引出了一切关系;有多少个ET(和)就有多少关系;ET(和)不仅使一切关系摇摆不定,也使是、存在,使动词摇摆不定。ET(和),‘ET(和)…ET(和)…ET(和)…。”(14)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8-49页。这种ET(和)的结构即意味着多样性(或者“异质的多元体”结构形象),意味着对中心的摧毁,它既非成分也非总体。它同时也是一种力量,一种生活和思想的力量。块茎的逻辑建构总是介于两者之间,是交界线,是逃逸线或流动线。也正是在这条逃逸线上,事物在产生,生成在进行。因此,块茎建立的是一种ET的逻辑。《千高原》的根茎概念或游牧思想具有反基要和二元论的特质,呈现出一幅德勒兹式的思想游牧空间的审美图式。然而,不同于块茎的逻辑建构,树或者根都固定于一点,然后以中心化的方式展开,这种固定于一点的树状模式或者根状模式都是以一种姿态或者说以一种中心论的特征而呈现出的,它指认了中心论、规范化和等级化。这种中心论、规范化或者等级化是传统伦理学的主要论域。或者说,这种固定于一个点的树的结构代表了人类中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即,生态伦理学的终极目的在于作为核心价值主体的人,一切道德价值评价活动的作出都与人的利益有关。这就使得传统的价值论固守于人类中心这一范围,价值判断也是一种以人类中心作为根本依据所发出的评价活动,而事物只有当与人类道德主体发生关联才能进入价值体系。由此,事物存在的价值必须以人类作为其基本依据,没有其独立的道德主体地位。在这里,德勒兹是在暗示我们要警惕人类中心主义(15)有关这种价值论的核心观念我们可以主要概括为:首先,突出人类自身的利益取向,或将人的利益作为其制定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彻底否定了人类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因此,我们在设计或者选择一项道德原则时,先考虑的是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者利益需求;其次,大多数人类中心主义都主张,人类是作为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生存物没有任何生存价值,如果说有价值也仅仅只是具有工具论价值。这样一来,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投射的一种产物,其自身根本上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及意义。据此,大多数人类中心主义都否认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人类中心主义核心论点就是,将人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的价值尺度,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主张从根本上忽略了自然的内在价值,或者说,人类中心主义只是把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条件而加以看待,否认了人类对自然的道德责任。。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来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具有理性推理能力的人才能配得上拥有自然的权利,因此,作为具有理性推理能力的人成为了唯一的道德主体,也即,自然界充其量只是作为一种人类的工具而存在,大自然创造生命是有其目的的,就是服务人类。就此而言,相对于人类而言,大自然没有任何道德地位可言。譬如,自然的目的论就认为,自然的一切存在物只有工具价值,人类不必对其负有任何道德义务。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动物和植物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人类提供必要的食物和衣服的保障。在此意义上,自然目的论将自然的内在道德地位或者独立于人类功用性的自然的内在价值也一并给剥夺了。并且,这种伦理论据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作为某种根据的人能够组成社会系统,能够开创一个文明形态。人类中心主义聚焦于人类对自然的现实关注,固守于人的道德价值评价活动。由此,价值论域的界限也就是人的界限,它不可能超越于人,人作为一切存在物的价值评价主体,外在于人的存在物只能权充人的目的或者手段,也就是说,外在于人的存在物仅作为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而具有工具价值。
德勒兹坚持认为,块茎标识的是异质性多元化的生成,而且其连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块茎不断地建立连接,这种连接据于符号链(chanons sémiotiques)、权力组织(organisations de pouvoir),关联到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的状况”(16)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t,Milles Plateaux,p.14.。块茎与作为权力标志的语言学模式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它自身可以展转于多种错综复杂的连接,它是一种异质性、多元体的存在。事实上,块茎是一个由线条构成的地图,它是一系列同步发挥作用的不同的线。块茎的任何一个点都与其他的点相连接(17)如果说“树-根”思维总是划定一个点,固定一个程序,而块茎思维则会向外发散出多个点与线,而且其中任何一个点或线都能够、而且也必须与其他事物的任何一个异质性的点线相链接,从而形成多方向多路线的逃逸姿态。随着块茎思维在多个点线与其他异质性事物发生事实上的链接,块茎思维在形态上产生多样性,在功能上实现了增值性。在这多样性的增值过程中,块茎思维的运行既不存在主体,也不存在客体,其中也没有物质或精神的界限,甚至它从来就不会产生一个自足性的整体结构。参阅胡志明:《司徒空〈诗品〉与德勒兹的“块茎”概念》,《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线条是沟通任两个点之间的桥梁。在块茎中,所有的线条和结点都是一致化无区别的。在优先性的意义上,它们相互独立;在现实的意义上,它们却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并且,在这些线条和结点中不存在任何的等级秩序和定律。
德勒兹认为,只有当“多”作为多元体,它才能终止与“一”之间的关联。这种多元体是块茎式的,因此它是真实的多元体。德勒兹说道:“一个多元体只存在规定性(déterminations)、量值(grandeurs)、维度(dimensions)。”(18)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t,Milles Plateaux,pp.14-15.这种“规定性”、“数量”和“维度”都是抵制于统一性的,在这种多元体中也绝不会存在统一性的观念。但是在德勒兹看来,一个块茎或者多元体是不允许自身被“超编码”的,不会拥有一个超越于与这些线连接在一起的数的多元体之上的“替补维度”。这种“替补维度”与统一性相关,即关联到“超编码”。但恰恰多元体不需要这种“替补维度”,因为它自身已经占据了其所有的维度,或者说这种维度即是对多元体的一种界定。“一个多元体不是凭借其那些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它自身的广延)或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它的内涵)而得以规定的,而是凭借其自身所具有的‘强度’(intension)之线和维度(dimensions)而得到规定的。如果你变换了其维度,或者说增加、减少维度,那你就改变了多元体”(19)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t,Milles Plateaux,p.297.。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一个多元体容贯的平面。这种平面只有经度和维度,速度和个别体。它也是一内在性的或由伦理与政治的逃逸线以及趋向这一方的生成所勾画的平面(20)Eugene W. Holland认为,多元体容贯的平面也即内在性平面由两个维度所构成。一个维度是由伦理与政治的逃逸线及其趋向于此维的生成所刻画;另一个维度则根据经度和纬度来进行描述:由身体构成的各种元素以及它们的相对速度(经度),作用与被作用、施动与被施动的能力(纬度)。参阅Eugene W. Holland,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A Reader’s Guide,p.112.。并且德勒兹还认为,无论它拥有多少维度,它绝不会拥有一个在它之上所发生事物进行增补的维度。由此得出:它既是自然的又是内在的。这种对“内在自然主义”的强调无意间揭示了德勒兹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在旨归,即,只要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就可以通过“解辖域化”这一机制,实现生命的自由流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道德情感带到一切领域当中,在这个融贯的平面上,一切可能都应该被重新激活。
其实,德勒兹一直强调异质性的“多元体”的存在及对其异质性存在的接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告诉我们:
首先,整个生态系统要承认和接纳异质性的存在,所有异质性的存在构成了整个大的生态系统圈。块茎本身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多样性与异质性。这种多样性与二元论所建构的伪多样性存在本质性的区分,块茎完全彰显或肯定了纯粹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这与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有关自然生态伦理学的某些观点十分相似。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试图通过论证异质性存在也具有客观价值而赋予异质性多元体道德主体的地位。在他看来,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都拥有其自身的客观价值。并且这种内在价值是客观的,并与人类的利益无关。罗尔斯顿试图以这种生态伦理来激发或实现人对自然的德性之爱。
其次,根据块茎其自身不断生产、或源源不断发展出的新的连接及其多元体构型来讲,我们要将自然界的生态伦理系统进一步扩展开来,抵制“弱人类中心主义”(weak anthropocentrism)(21)“弱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环境伦理学拜伦·诺顿(B·G·Norton)提出的。在诺顿看来,弱人类中心主义旨在限制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过度消费。诺顿主张将人类中心主义界划为强人类中心主义和弱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形式。前者以“感性偏爱”作为价值依据,后者以“理智偏爱”作为价值依据。也就是说,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强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价值批判的尺度,或者说,它更注重理智的指导作用及其对感性偏好的限制。虽然,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价值与人类相关切,但是,应该对人类的感性偏好及愿望的满足加以充分而必要的限制。。弱人类中心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改良。它一方面坚持认为自然具有内在的价值,我们人类必须呵护其价值主体性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提出相应的措施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缓解生态危机,但是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生态危机的救治。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与人类中心主义看似不同,但在本质上,服务人类构成了其根本性的旨归。我们可以说,弱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一种资源利用的层面,进而忽视了两者关系的非资源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自然并不只是具有某种可供人类利用的经济价值,它还应该具有科研价值、生态系统价值及自然审美价值等等。
最后,依据德勒兹,块茎所建构的“多元体”,不是表征数量上的一种增长,相反,它是对维度和数量级的扩展。块茎就是一个由维度与数量级所构成的系统机器。在这个系统机器内部,块茎就是一种充满流溢的运动,并不是某一个实体。就此而言,按照生态伦理学的话语构境,块茎所显示的就是一种生态整体论。但这里的生态整体论不同于生态中心论,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仔细地区分开来。虽然,无论是生态整体论还是生态中心论都强调赋予自然内在价值及道德主体的地位,但是在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两者的主张迥异。生态整体论关注的是生态系统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的布局范围,进而显现的是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诉求;生态中心论则关注的是生命个体的道德权利,不能将整体利益凌驾于个体之上。生态中心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辛格看来,自然的内在价值及平等的道德主体地位只能赋予那些“有感觉的动物”(22)辛格主张将动物平等对待,但是他将感受能力与价值进行了正向关联。也就是说,相较于低级动物而言,高级别的动物因其感受能力强,因而其内在价值就大,进而获得的道德关怀就愈多。他说:“一个生物如果具有自觉、有能力从事抽象思考、规划未来、进行复杂的沟通活动等等,那么说他的生命比一个不具有这些能力的生物来的有价值,并不算是恣意专断。”参见彼得·辛格:《动物解放》,孟祥森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7页。。因此,按照辛格的理论,没有感觉的动物,如山河大川,不属于赋予道德权利的范围。根据辛格,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不再是理性,而是感觉(或感受能力)。进而认为主体范围的扩展是有一定边界的。这一主张显然暴露了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
三、“非地域化”:道德扩展主义的诉求
块茎其自身不仅预示着对表征统一性主根系统的终止,而且还包含有反谱系 及“非示意断裂”这一价值指向。非示意断裂预示着:一个块茎在其任意部分之间被瓦解、中断,但是它会沿着自身的某条线或其他的线而重新开始。为什么能够(重新)开始呢?因为块茎自身不仅包含着“节段性的线”(des lignes desegmentarité),而且还包含“解辖域化之线”。德勒兹的“解辖域化”思维将生成的思想事件置于无限的创造与差异的挑战之中,这就是以差异运动来挑战现成事物,并重新思索可能成为新的事物的表达方式。“解辖域化”奠基于敞开,正是这种敞开使其“解辖域化”的运动成为了可能,并且“这种敞开并不是否定性地敞开,它是肯定的。这种敞开也不是作为‘封闭’的对立面而规定的,或者说这种块茎的机械特性(machinic character)产生于虚拟(the virtual)并且它自身是由动态性的连接组成的”(23)Adrian Parr,The Deleuze Dictionary,Revised Edition,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233.。
从德勒兹的描述来看,“节段性的线”表征的是片段性的、情节性的。但是这种片段性的总是处于一种过渡性的阶段,它自身总是关联着新的开端;而“解辖域化之线”即意味着一种逃离,逃离于现实力量的枷锁,逃离于固定的联结,也逃离于企图对之实施的控制、规训。那么作为包含了“解辖域化之线”的块茎便可以爆裂为一条逃逸之线,这种在块茎当中就会出现断裂,但是这种断裂会很快被块茎以新的形式得以重新开始联结。不过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在其上有可能重新遭遇组织,这种组织企图对一切事物施以再度层化,重新赋予一个构型,指向权力的构型,重新构成一个主体的属性——任何事情你所喜欢的,从俄狄浦斯的出现,直到法西斯主义的固化。”(24)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t,Milles Plateaux,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80,p.16.这一危险即是说明存在着这样的组织,总是试图对这种块茎施以“辖域化”,“危险”是“辖域化”潜在的表现形式。但是,块茎总是能沿着“解辖域化之线”,不断地逃逸于这种潜在的危险而进入另一过程。这种不断逃逸说明块茎是运动的,块茎的本性是一个正在运动的母体(25)Adrian Parr,The Deleuze Dictionary,Revised Edition,p.232.。
但是,“解辖域化”也同时伴随着“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这二者之间相互关联。德勒兹为了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彼此联通与生成,引用了兰花和黄蜂这两个异质性的要素(一个作为植物,一个作为动物)来加以解释。为什么要用两个相异要素来说明呢?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通过与相异的实体接触(联系),身体和事物会不断地呈现新的维度;用这样的方式,“根茎”概念标志一个相异的概念化世界的方式(26)Adrian Parr,The Deleuze Dictionary,Revised,Edition,p.234.。我们说,兰花“解辖域化”而形成了一个形象,该形象是对黄蜂的“模仿”(calque),这种模仿即是说明在这两者之间(动物的组织结构与植物的组织结构)存在某种相似性。德勒兹认为,模仿只存在于具有相同本质的现象中。对于具有一种完全不同本质的现象来说,模仿是一个异常拙劣的概念,因为在德勒兹看来,它是依赖于二元逻辑的。模仿是一种再现,亦如柏拉图所说的可感世界是对可知世界的模仿。在柏拉图那里,模仿是为了解释现象世界为什么是存在的这一问题,即模仿使得可知世界与可感世界发生关联。可知世界是作为可感世界的本质、被模仿的对象存在的。这种模仿本来就是二元中心论逻辑的一种显示——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
但是德勒兹不同意这种二元论、中心论,他遵从一种多元论、生成论,而块茎就是这种多元体和生成论的象征(27)德勒兹的生成概念本身就隐含着“伦理”的旨向。根据德勒兹,生成并没有外在于自身的目的和根据,在生成的所有潜在形式当中,生成并不带有某种任何主观性的预设或者目标。就此而言,这种生成论要求我们在进行价值评估时应该从任何人类或者目的之中解放出来。据此,这种生成拒绝价值上的任何可能成为潜在标准的事物。恰恰相反,生成的最终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新的感知形式或者生成一种新的创造。对于德勒兹来说,生成直接叩开了生命的原初的封闭状态。生命并不起源于封闭的有机体,而是起源于一种恒久的流动。当块茎被视为一种多元体和生成论时,也就意味着,块茎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要义。。然而黄蜂这个形象上“再辖域化”,即黄蜂从“模仿”的形象转换成其自身的动物形象。但黄蜂也被“解辖域化”,它自身通过传授花粉变成为兰花繁殖器官的一部分。然而正是这种传播花粉的过程,使得兰花“再-辖域化”,从对一个黄蜂的“模仿”形象转换至其自身的形象。这样一来,按照德勒兹的话说,兰花和黄蜂便形成了块茎。当我们说,兰花模仿着黄蜂,其实是一种“代码的捕获,代码的增值(plus-value),价(valence)的增长,真正的生成(véritable devenir)”(28)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t,Milles Plateaux,p.17.。德勒兹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说,兰花模仿黄蜂,兰花得以“解辖域化”,使黄蜂“再-辖域化”,然而黄蜂同时也被“解辖域化”,通过传播花粉,黄蜂又使兰花“再-辖域化”。即,一方的“解辖域化”总是伴随着另一方的“再-辖域化”。德勒兹的原话是:“兰花的生成——黄蜂,黄蜂的生成——兰花,每一种生成都确了其中一方的“解辖域化”和另外一方的“再辖域化”,两种生成相互关联,在密度的循环中形成一种传递替换(relayant),而此种流通则总是将解辖域化推进得更远”(29)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t,Milles Plateaux,p.17.。说来说去,这个关于兰花与黄蜂的例子无非摆明了一点:任何“解辖域化”都会伴随着“再-辖域化”。当遇见黄蜂,兰花亦非完全是其自身,它会产生“解辖域化”,即生成黄蜂的过程,但是由于兰花的花粉被黄蜂带向了异处,它也发生了“再-辖域化”。这一过程反过来,即,黄蜂的“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据此,所有这样的相遇创造了一种聚合现象,而聚合的两种事物之间则产生了双重生成(30)Damian Sutton,David Martin-Jones,Deleuze Reframed:Interpreting Key Thinkers for the Arts,pp.6-7.。或者这样说,两个异质性的要素构成了作为聚合、装配的块茎。同时,“再-辖域化”是为了更好地推进“解辖域化”。但是,生成不是成为,而是在于找到邻近的、难以辨别的或者未区分的区域。也就是说,兰花生成黄蜂,并不是说兰花成为了黄蜂,而是找到了介于兰花和黄蜂之间邻近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你无法区别于一个黄蜂或者一朵兰花。德勒兹认为,黄蜂——遇见——兰花,在这里,所有不定式动词(如遇见)都是不受限制的生成。动词“是”就如同具有反射“我”的原初性瑕疵,这个“我”超编码“是”,并将“是”置于直陈式的第一人称。但生成——不定式没有主体:它们只反射事件的“它”,即只表达事物或事物状态的属性,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本身被归属于事物的状态,这类事物状态体现的就是一种集体、装配。根据德勒兹,所有的不定式具有一种围绕其所是的“外—是”(extra-être)(31)Gilles Deleuze,Claire Parnet,Dialogues,pp.78-79.。
德勒兹所列举的黄蜂和兰花充分表达了其生态伦理学的情怀。黄蜂和兰花虽然属于不同物种,来自于不同的两个领域,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相互包含的关系,它表达的就是一种混合物或集体、装配。由此可以推论出,大自然的一切物种都是处于平等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或者说,大自然的一切处于一种“共生平等”、集体装配的关系之中。德勒兹在这里拷问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扩展我们的生态圈,进而培育一种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技术生态深度融合的大生态伦理情怀。德勒兹的块茎生态伦理学作为一种价值观引领,认为整个大自然应当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因此,人不仅对人负有权利与义务,对于自然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人类利益与自然的益产生矛盾时,人们理应将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协调性、稳定性作为最高伦理原则。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大概是持此立场的最著名的思想者,他提出了“尊重一切生命”的著名伦理信条。德勒兹的块茎生态伦理学在承认人类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同时,又主张进一步将这种道德关怀延伸至非人类的自然世界,珍视一切生存意志所属的生命。这种伦理学开始从道德上关注无生命的自然生态系统以及非人类的自然存在物。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德勒兹的块茎生态伦理学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就如同德勒兹对块茎的定义,块茎就是一种多元体的维度,在此,德勒兹已经洞察到传统的生态坏境伦理学的那种狭隘。德勒兹展开块茎思维模式,就是要扬弃传统环境伦理学的偏狭视野,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将自然共同整体的善规定为最高的道德原则。
四、结语
综上,德勒兹对块茎的大量阐述展示了一种生态伦理情怀,这也是一种整体的生态主义伦理学,这种主义认为,从道德情感上关切无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生态系统以及自然过程。德勒兹的块茎伦理试图建立一种共生的大地伦理学体系,在这种大地伦理学体系之中,一切生物都应该是相互平等的,都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关怀。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通过相互融合来不断地扩展我们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使之包括一切生物和不同物种的领域,或由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大的生态块茎整体。德勒兹的块茎理论告诉我们: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共生、共同生长的生态系统,每一个包含生命的或者无生命的机体并不存在某种对位的关系或者对抗,恰恰相反,每一个有机体的生命都应该得到一种互通的道德关切感,它们自身即可以作为其生命的目的中心(32)值得一提的是,Jakob von Uexküll对自然的看法得到了德勒兹的拥护。Jakob von Uexküll举例说,歌手和乐器之间相互依存的声音就像自然的生态一样。虽然每种声音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却构成了一个崇高的整体。而德勒兹欣然接受了Jakob von Uexküll的看法,由此推断自然界是一种内在的、普遍存在的巴赫式的感性(Bach-like sensibility),或者至少在大自然的乐谱上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将人与自然界划开来。参阅Andrew Ballantyne,Deleuze & Guattari for Architects,New York:Routledge,2007,pp.48-49.。德勒兹块茎生态伦理学要求我们重新去审查作为生态的人类,而不是作为单纯理性或者感觉的存在物,不但要关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更要关切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世界。人所应该具有的伦理观念应以共同体或整体作为其内在价值指引,扩大人类道德共同体的权利。德勒兹的块茎其根本意指就是要消除一种等级及谱系结构,因此,这种伦理学所要求的伦理整体或者共同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面意义上的生态自然系统,这种伦理是一种由相互依赖的部分所组成的生态整体伦理学。由此,它改变了以往人类在共同体中的所扮演的角色,人类不再以一个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相反,人类在这个整体的生态共同体之中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平等的一员(33)德勒兹的块茎(生态)学与奧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一书中所提出的大地的伦理(The land ethic)不谋而合。在利奥波德看来,应该将整个生态系统纳入伦理关系中——自然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与人之间有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大地伦理学要求人们从生态的视角理解自然,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他说道:“一个事物,当它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必错。”参阅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0,p.189.。它本身就揭示了对每一个成员所应该持有的尊敬,也包括对整个生态系统整体的尊敬。根据德勒兹,块茎就是一个多维面的多元体,这是一个基本的生态学概念,大自然所有的存在物应该一律平等,一律有资格得到平等的尊敬和爱。要言之,德勒兹从生态伦理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消解了各种二元论、理性主义、中心论、等级体制等等,进而确立了有机整体的生态学伦理观。这种有机整体的生态学伦理观也是一种生态生存论。生存论生态哲学坚持“从现实出发”的历史研究方法、“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价值核心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共赢实践取向,力图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学术构建与理论基础(34)参见刘福森、梁镇玺:《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兼论生态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理论探讨》2021年第6期。。我们从生态学伦理的角度对德勒兹的块茎这一概念进行了全面解读,指出了块茎本身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意涵。在生态坏境日趋严峻的今天,块茎生态伦理的实践性体现在:超越人类的道德感和创造了一种博物学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