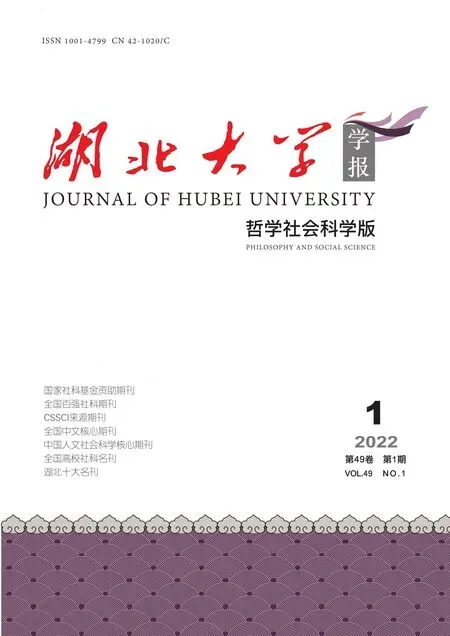宋代植物审美中的草木精神与天地气象
丁利荣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中国传统美学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植物由此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认知与审美对象,植物审美也成为中国美学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先秦以来的植物审美传统形成了比德、移情、畅神等基本审美模式,随着中晚唐禅宗思想和宋代理学的兴起,植物审美又有了新的理论视角,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宋代植物审美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将移情、比德与畅神植根于清明的理性上,从而丰富了植物审美的理论内涵和哲学品格。明代受心学影响,植物审美中的理学精神有所消褪,晚清在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下,植物审美开始注重向现代科学观的转变。
在植物审美历史的流变中,宋代理学的理气论、格物论和心性论思想为植物审美提供了系统的认知模式,因此,宋代植物审美理论更加深入,审美表现更为成熟,逻辑体系更趋完整,可以说,宋代植物审美是古代植物审美思想的集大成,其所体现的美学精神空灵而生动、亘古又常新,在现代植物审美的理论建构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宋代植物审美的双重维度:观物与返性
观物与返性是宋代植物审美的重要理论维度,它将植物审美中物与人的对话推进到更深层的性理层面。观物是观物之性理,返性是克己复礼,重返人的天地之性。如何能返求人性中精纯澄彻的至善本性,对此,理学家尤其强调要“观天地生物气象”(1)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叶采集解,严佐之导读,程水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页。,观天地生物气象即包括观草木精神。周敦颐窗前草不除,弟子问之,则云“与自家意思一般”(2)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第360页。,言下之意即“观天地生物气象”可以观“自家意思”。“自家意思”带有较强的禅学色彩,意味着人的自性,在理学这里,则指人所具有的天地之性或天理。
“天地生物气象”与“自家意思”是指物性与人性中都有天性天理的一面,这涉及到对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关系的理解。天(道)性即天地之性通过草木的生长得以体现,我(人)性中也有天(道)性的一面,但我(人)性常为情执欲念所蔽,失去清明的自性光辉,看不清宇宙生意的通达,而通过观生物气象,人可以返观自性,可以“存天理,灭人欲”,灭人欲不是禁欲,而是通过去除过度的欲念走向返己复性之路,若体会此理,便可见“自家意思”如天地之性一样敞亮。
能观“天地生物气象”则能观“自家意思”,能观“自家意思”则自家的气象便能显现出来。“杨子曰:‘观乎天地,则见圣人。’伊川曰:‘不然。观乎圣人,则见天地’”(3)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4页。。杨子强调的是圣人能观天地之道,法乎自然;伊川强调的是唯圣人能开显天地精神,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尤其是圣人,能体会天地之道。二人阐释角度不同,但都强调了天地、圣人与“自家意思”有一致之处。
可见,观物是在物性与人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从中学道、体道、行道。周敦颐窗前草不除,实则是通过观草木之性而获得一种学道与体道的功夫,宋代植物审美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建立起来,通达天人之际也就成为了植物审美的最终方向。
就观物与返性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观物需要澄怀,另一方面观物可以返性,从而观天地性理与自身性理。观物是出发点,返性是目的地,观物是自然气象的开显,返性是圣贤气象的形成,将自然气象与圣人气象融为一体,是理学家特有的气象美学思想,而植物审美正是理学气象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观物可以返性。人通过观物来返性,是物对人的开显,而不是人移情、比德于物。今人受移情说的影响,大都认为比德是以己德移情于物,物皆著我之色彩,实际上是今人将比德的方向搞反了。比德,不是将人的品德情性投射于物,而是以物的德性来移人的性情。正如梅兰竹菊四君子被简单说成一种道德象征后,就遮敝了它的来路和本义,对此我们需要正本溯源,还原其生成的语境。
物的德性之所以能移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观天地草木是一种减损的功夫。人要以物为本,去观察其生长变化,体会其规律,感悟其精神,而不是去赋予它很多人为的东西。如花展是要展现花本身的美,而不能以花为工具和材料,去表达一个预设的观念和主题。人们只能让它更纯粹地展示自身,只有完全放下自己,才能观物之形神,只有得物之形神,人才能走在返性复性的大道中,能体悟返朴归真之妙。其次,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的相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有持续的内外之功,既要内修心性,同时要外观物性。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情感对象化过程,也有身心脱落、与物一体的至乐之情,体会到“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的妙境。物我感而遂通的时刻会如灵感闪现,也会倏忽而逝,但介入的经历改变观者。片刻的体验如果加以时时的止定与涵养,那么醇厚精纯的人格就树立起来,生命的风景将因此改变。北宋诗僧道潜在《题净慈诠上人荷香亭壁》中说:“然人心清浊,感物乃尔,而为道者,安得不择其所居?……资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兴可见矣。”(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宋代理学家、士大夫及其他文人雅士也多好游历自然山水、观花草树木,在山川草木中体会天地气象,这构成了宋代植物审美中最雅正的部分。
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从审美客体而言,正是由于受理学观物思想影响,纳入宋人审美中的植物越来越多,如荠菜、茅草等寻常草木都能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中。宋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格物热情,各种植物谱录在宋代大量涌现,古代植物学和本草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对植物的产地、形态、类别、种植及制器尚用等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对草木的色形味与性理和性情的关系都有深入系统的阐释,宋人对草木的审美表现也更加细致、缜密,植物审美理论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从审美主体而言,宋人在植物审美中更注重养精炼神、涵养德性。宋人诗画中对山水花木的表现,除了传统的托物言情之作,更多的是力求对物性自在本真的展现和追求。一些经典的宋代山水花鸟画也成为理学文化宇宙图式和人伦图式的视觉呈现,体现着宋人的审美理想和哲思。
总体来看,在植物审美中,宋人更注重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的开显、发现与生成,这是宋代植物审美关涉的三个重要层面。其中,物性是指事物形态、属性的自然呈现以及人们对物的认知特性,我(人)性是人与植物在情感世界中的关联及意象表现,天(道)性是指物性敞开的天地性理及人对天命性理的领悟。这三者并不是分裂的,而是内在相互贯通,最终指向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的融合。
二、宋代植物审美中的岁寒之美
在对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的观照和体悟中,宋代植物审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对岁寒之美的欣赏,这是在继孔子的“后凋松柏”之后,再次从性理之学上对其加以理论的自觉重构,并成为宋代流行的审美精神,也是后世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趣味的鲜明体现。
“岁寒三友”的称呼出现在宋代。宋人林景熙《五云梅舍记》云:“即其居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5)林景熙:《霁山文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740页。对梅花的欣赏在宋朝达于极盛,杨万里在《洮湖和梅诗序》中谈到:“南北诸子如阴铿、何逊、苏子卿,诗人之风流至此极矣,梅于是时,始以花闻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苏黄,崛起千载之下,而躏藉千载之上,遂主风月花草之夏盟。而于其间首出桃李、兰蕙而居客之左,盖梅之有遭,未有盛于此时者也。”(6)陈景沂编:《全芳备祖》,程杰、王三毛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页。对梅的欣赏多与“冷香”、“影寒”、“岁寒”、“孤洁”、“冷蕊疏枝”相关,如辛弃疾《临江仙·探梅》“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与花的形态相比,更注重雪的精神。与“岁寒三友”齐名的梅兰竹菊“四君子”的说法虽然出现在元代,但对它们的欣赏在宋代已成风尚。如范成大等《范村梅谱(外十二种)》载言,“菊独以秋花悦茂于风霜摇落之时”(7)范成大等:《范村梅谱(外十二种)》,刘向培整理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274页。,“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说以谓岁华晼晚,草木变衰,乃独烨然秀发,傲睨风露。此幽人逸士之操,虽寂寥荒寒,而味道之腴,不改其乐者也”(8)范成大等:《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293页。。可见,对岁寒及与此相关的幽独精神的推崇成为宋代植物审美中的重要风尚。造成这一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自然气候环境来看,宋代出现的对寒林雪景的审美和艺术表现潮流与当时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梅花在宋代被称为花中之魁与其时气候变冷有重要关系。气象学家竺可桢从唐宋两朝的物候常识推断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其研究发现:唐代属于温暖期,8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9世纪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而到宋代,11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苏轼咏杏花诗有“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之句,王安石咏红梅诗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之句,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9)竺可桢著、施爱东编:《天道与人文》,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88-89页。。程民生《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研究也表明,宋元易代之际,气温有很大变化,“开封在北宋时期尚处于温暖时期,在宋神宗后期和宋哲宗前期达到高峰。而在此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均无温暖季节,可见北宋后期气温的急剧变化”(10)程民生:《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5页。。由这些研究成果可知,北宋后期,即徽宗、钦宗时期开封正处在从温暖期到第三个寒冷期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常出现冬天极寒、春秋寒甚至夏寒等恶劣特殊气候,气候环境的变化也会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感受和艺术表现中。
其次,从社会环境来看,岁寒审美也与社会家国和个人的遭际相关。气候的变化引起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的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感受、艺术表现,乃至哲学精神。尤其在北宋灭亡后,文人多借荒寒之景写民生疾苦,表救世之心,寄一己之肠。宋元绘画也多表现出荒寒之境,如李唐在乱离南渡之时,身心俱受疾苦,寒冷凄厉的风物景观与寒凉悲郁的黍离之情相应和,形成了萧寒荒远的画风。能欣赏荒寒幽寂的人,必定有顽强的生命活力,这其中包含着中国文人最深层的生命体验。苏轼因陷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人生最困顿的时期完成其华丽的转身,写于此时的《雪堂记》(1082)记下了苏轼内心深处最深刻的自我追问和心路历程,从此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平淡、旷达的“散人”,而不再是一个为物所缚的“拘人”,人生开出一种新气象。
再次,从哲学层面来看,理学思想赋予宋代岁寒美学不同的哲学精神。晚唐形成的禅宗美学对荒寒之美有一定的影响,“它开辟了一种淡泊、凄清、冷峭的美的境界,刚好符合相当一部分士大夫文人处在失意不得志情况下的心境”(11)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新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91页。。但除此之外,理学为宋代岁寒之美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念。宋人尚理,理与天地之性密切相关,天地之性即生物之性,天地之理即生生之理,植物的岁寒之美即与天地生生之理有重要关系。理学家善“就草木来说明宇宙”(12)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8页。,如朱熹认为:
天地之心,……只是生物而已。谓如一树,春荣夏敷,至秋乃实,至冬乃成。虽曰成实,若未经冬,便种不成。直是受得气足,便是将欲相离之时,却将千实来种,便成千树,如‘硕果不食’是也。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时,疑若树无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敛在下。每实各具生理,便见生生不穷之意。这个道理直是自然,全不是安排得。只是圣人便窥见机缄,发明出来。(1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729页。
万物生意即天地的生生之意,生生之意四时皆有可观,然四时之中最可观者在何时呢?朱熹认为,“万物之生,天命流行,至始至终,无非此理。但初生之际,淳粹未散,尤易见尔。只如元亨利贞皆是善,而元则为善之长,亨利贞皆是那里来”,“万物生长,是天地无心时。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时”(1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1、5页。;“万物生时,此心非不见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丛杂,无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难见。若会看者,能于此观之,则所见无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复时万物皆未生,只有一个天地之心昭然著见在这里,所以易看也”(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790页。。不难看出,朱熹认为生意虽无处不在,然最可观之时,即是淳粹未散、最精纯无杂之时,此时是元气之发端处,即“复时”,也就是复卦中“复见天地之心”的道理。
“复见天地之心”的“复”不是“又”的意思,复卦是十一月卦,此时天气严寒,天地一阳初生,正是阳气生发的时候,也是生意最可观、最能观、也是最难观的时候。最可观,是指阳气初露端倪,如种子萌动时;最能观,是生意从无到有,最易见之时;最难观,是指人往往易于花繁叶茂时见其生意,而在元气待发未发时最易被轻忽。故说“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16)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第11页。。于岁寒之时更见生生之意,这一思想对宋人植物审美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传统所强调的自然的生生之德外,就是在四时中尤其推崇对“寒”意的审美,如对寒梅、寒林、雪景的欣赏。朱熹曾谓“冬间花难谢。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蜡梅,皆然。至春花则易谢。若夏间花,则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开得一日。必竟冬时其气贞固,故难得谢。若春夏间,才发便发尽了,故不能久”(1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62页。。这是因为冬日阳气精粹未散的缘故。
这种岁寒精神既体现在对植物的审美中,也体现在人生态度中。人既要能观自然岁时中的复卦,也能观人生际遇中的复卦。人处于困顿时,求无可求,得无可得,万念俱泯,心中寂寥,也最容易见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自我的本来面目。反之,人在得意时,则容易被那点成功、喜悦的念头冲昏头脑,以为世界尽在于一己之手,以为天下之美皆归于己。反而人越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其内心可能更坚定,那就是自己最淳粹未散的元气了。由此可见,在大自然的冬天与人生际遇的冬天最易见出那一点仁心。
对社会中隐逸之士的看法,也可以从这里加以理解。天道至诚无息,指自然的生生不息,元气不间断,人世间的至诚无息,是指人世间的元气也会生生不息。人世间的元气体现在哪里?即便在乱世之中,自有一丝元气尚存。如历史上的退隐高士,并不只是一种消极避世而已,而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保留一息元气,这不仅不消极,而是一种可贵的对浩然之气的存有。“有为”是一种勇气,“有所不为”也是一种勇气,某些时候,“不为”需要一种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力量。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也,晚唐司空图建休休亭隐居于世,依然可以为山中宰相,依然可以“泉石殉君王”(李馥《过司空表圣墓》),是隐逸中节义之人,正是乱世中尚存的一息元气。
岁寒精神是在困顿中见出一丝生意,是自然、人生和社会中的仁心和元气的发端处。正如黄庭坚在《画墨竹赞》所写:“人有岁寒心,乃有岁寒节。何能貌不枯,虚心听霜雪。”(1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7册,第316页。通过对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的体察与贯通,从而达于澄明之境。
三、宋代植物审美中的澄治之功
澄治的原意是使水由浊返清,植物审美中的澄治之功是指在对植物的观照中,借由观草木生意返观“自家意思”,从而涵养性情、变化气质,强调对植物的观照具有移情养性的功能。
朱熹的《观书有感(其一)》是一首学道体道、明性见理的理学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的“书”既是指先贤典籍,更是指天地山川草木虫鱼这部自然之书。“半亩方塘一鉴开”,既是指福建南溪书院的半亩方塘,也喻指澄澈清明的人心之镜,澄明之心方能与天光云影共徘徊。心性的清澈在于人的澄治之功。“源头活水”指的就是“元初水”(19)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第18页。,元初水指人性中本之于天地的至善。元初水是从天地之性流注于人之性,可谓之“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经·系辞上》)。圣人用字精准,用一“继”字,而不用“付”、“受”字,是大有深意的:
盖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之理,全付于人而人受之,……但谓之付则主于天地而言,谓之受则主于人而言,惟谓之继,则见得天人承接之意,而付与受两义皆在其中矣。(20)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下)》,冯雷益、钟友文整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477页。
可见,“继”与“付”和“受”不同,“付”偏于“给予”,主动义,“受”偏于“承受”,被动义,而“继”则是天人的承接关系,是天人之际的承传与接受,“付”与“受”两义皆涵摄其中,这也是宋代理学思想所要建构的天人之际的关捩点,天付之,人受之。
由观草木生意可以见出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三者之间的“继”“成”关系。两宋之际抗金名将李纲在《种花说》中借种花者之口对“嗜花之说”、“种花之道”和“养性之理”进行了系统阐述:
梁谿暇日过而问焉,曰:“子之嗜花有说乎?”乐全曰:“然。人之嗜花,为物所转,玩颜色之美好,嗅馨香之条鬯,足以悦可其意,斯已矣。吾之嗜花,独观其变。雷风之所震荡,日月之所照烛,雨露之所滋润,雪霜之所凌挫,或茁其芽,或敷其英,或归其根,或成其实,四时之变无穷,而花之变亦无穷也。方时未至,若闲若藏,不可强之使开。及时既至,若愤若怒,不可抑之使敛。开已而谢,则虽天香国色,飘零萎落,复为臭腐,莫可得而留也,况其余乎?吾尝以是观之,则生生化化之理,在吾目中矣。”梁谿曰:“然则子之种花有道乎?”乐全曰:“然。人之种花,助之以人,动摇以观其踈密,爬剔以验其死生,而花之憔悴者已过半矣。吾之种花,全之以天,相其土壤以培壅之,时其旱干以灌溉之,遂其根本而封植之,顺其枝叶而芟治之,不益其生,不害其长,莳之若予,置之若弃,任其自然而不敢容私焉。……习于其性,而人之与花相得于思为之表,则远方绝域花之植于吾圃者,不异植于其土也。虽欲不硕茂而蕃滋,得乎?”梁谿欣然曰:“吾闻乐全之言,得养生焉。自吾一身观之,由少得壮,由壮得老,爪生齿长,筋转脉摇,无须臾停。而发之鬓黑者浸假以白,肤之充盈者浸假以皱,生灭之法,念念迁变,而况于吾身之外宠辱穷达、是非利害耶?其来莫御,其去莫止,是物之傥来寄也,不似夫花之荣枯代谢乎?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不以人灭,择其善而固执之,则仁、义、礼、智之端油然生矣。……然而人之赋性亦各不同,……各适其适,而相忘于江湖,则其性得矣。若夫屈折羁束而强其所不然,其不病者几希,不似夫花之得性则遂茂,而失性则枯槁乎?虽然,观花以变,而有所谓不变者存;全花以天,而有所谓相天者亦不废焉。内求诸身,则所以养生者亦若是而已矣。”乐全曰:“唯唯。”因叙其语,为《种花说》以自警云。(2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2册,第168-169页。
由上可见,嗜花之道旨在还原物性,观生物之理,而不仅仅是赏花之貌,悦己之情;种花之法重在“全之以天”,“任其自然不敢容私”,亦即要顺其物性,不过多人为干扰;以此方能悟养生之道,以花之荣枯代谢、得失消长反观万物之性的变与不变,从而体察适性养生之理,领悟安生立命之道。《种花说》涉及到植物的物性、审美的情性与体道的澄明三者的关系,可称得上一篇关于植物审美的理论纲要。
人在对植物的审美中,很容易将一己之情投身于物,即“以我观物”,物的意象成为人的情感的对象性显现。以丁香意象为例,“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如果从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意象向前回溯,会发现诗词中的丁香意象大多和郁结的情绪有关。
古人心思细腻,不知是谁发现丁香的花苞极似人的愁心,便开始有了“丁香结”的意象。李商隐(813—858)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二首(其一)》),牛峤(约890年前后在世)的“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感恩多·两条红粉泪》),尹鹗(约896年前后在世)的“寸心恰似丁香结,看看瘦尽胸前雪”(《拨棹子·风切切》),李璟(916—961)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摊破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愁心好似打了结的丁香花苞,再也无法舒展。
这一批意象密集在9世纪后半叶,丁香结难道是晚唐愁结哀怨的心声吗?《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22)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8页。看来,丁香的郁结也与社会治道相通。
另有一首著名的丁香词,王安石的儿子王雱(1044—1076)的《眼儿媚》: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23)徐培均评注:《唐宋词小令精华》,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
愁肠千回,令人心碎。据宋人笔记记载,王雱有奇才,但体弱多病,性情乖张,总猜疑自己的儿子长得不像自己,以致折磨死了孩子,冤屈了妻子,自己也不得解脱。王安石同情自己的媳妇,就做主把媳妇嫁了出去,这就是王安石“生前嫁妇”的故事。王雱的词写于妻子再嫁之后,他的追悔、眷恋、深情和化不开的郁结寄情于丁香枝上,豆蔻梢头。最后自己的生命也终于33岁,令人婉惜。王雱的丁香情结,可谓是声音之道与性情相通,令人动容。
植物的审美意象固然会与人的性情和社会治道相契合,但从根本而言,这种“以我观物”依然是耽溺于一己之情中,而没有超拔透脱出来。这种物我关系依然存在对物本身的遮蔽,物本身的遮蔽也意味着自性的不明。花的郁结意象是人移情于物,这一过程中物性与人的本性存在双重遮蔽。澄心观物则会敞开物与我。陆龟蒙(?—约881年)《丁香》诗云:“殷勤却解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春风催开丁香的花苞,繁花压满枝头,香气随风飘散,花并无郁结一说。
人与花如何看?金圣叹说:“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销陨在花里边去;花看人,花销陨到人里边来。”(24)金圣叹:《金圣叹文集》,艾舒仁编次,冉苒校点,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50页。销陨有消融、脱落之意。人看花,把人的情志消陨在花里;花看人,以花的无心消陨掉人的我情;人花俱忘亦俱在,最终合于澄明之境。这同身与竹化的道理是一样的:“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植物审美到更高的境界,是由感伤而至于超脱、达观,是放下自己去倾听它、去感受它,才能获得启发,从有执走向无执,同归于大化,道家叫“以天合天”,宋人叫“以物观物”。经由此超脱、达观而回望此时、此刻、此地,就会时时处处有一种珍惜、爱养之情。“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宋人赏落花之美更增了一份健朗达观的理性之美,唯其如此,才会有醇厚饱满的味外之味,惜物之情体现为尽心尽性。人情悲喜已经被沉淀、被超越,在人情之上开出澄明的道情之境。
植物审美正是将物的世界、人的世界与道的世界相贯通起来。美学是一种感性学,研究人的感性认识的完善。感性是基础,情感是核心,完善是方向。植物审美可以通过对植物的观照,舒解人的情感,提升人的境界,使人格越来越完善,性情越来澄彻。
四、宋代植物审美中的性理之趣
宋人植物审美具有嗜理成性的鲜明特点。宋伯仁作《梅花喜神谱》,谓“昔人谓一梅花具一乾坤,是又摆脱梅好而嗜理者”(25)范成大等:《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62页。。墨梅的创始人华光道人作《画梅谱》,具象化地将梅花的象数与义理哲学统一起来,以天地运化的象数理论阐释梅花之象,形成独特的赏梅、观梅和画梅理论。传为宋人鹿亭翁所著《兰易》,仿《易经》体例写成,将《兰易》分为《天根易》和《十二翼》两大部分。《天根易》以《周易》中十二月卦为兰之十二月令,分别讲述十二个月中兰的不同生长规律和种植之法,类似于易的经卦部分。下卷为十二易翼,讲述兰之性情德业和养护事宜,类似于易传部分。《兰易》以复兰开始,复兰即复月(十一月)的兰,以坤兰为终结,坤兰即坤月(十月)的兰。复兰意味着天地一阳生,是阳气的开始,生命的发端,“天根大始,兰退藏于室,元亨”,系曰:“‘知用知藏,易之道也。’藏兰勿用,又何咎也。兰,然后可大,亦可久也。复者,易之终始,君子艺兰以自考也。”(26)范成大等:《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100页。坤兰意味着阳气返终,含藏于内,“万物终始,藏于天根”,系曰:“‘阳月华胎,灌宜肥也。’戒之为分种后时也。阴往阳来,气含滋也。藏于月窟,复于天根,是为阴阳之枢机也”(27)范成大等:《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102页。。阴阳变化,原始返终,归根复命,终而复始,自然之道。所谈虽为兰,然“悟此可以养生,可以格物”(28)范成大等:《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106页。,善养兰的人,是懂得格物之理的人,育物育人道理相同,都要遂物之性,物尽其性,人尽其才。由此可见,宋人善在植物审美中探求物性人性的理学意趣。梅、兰是如此,他物亦是如此,可见一花一世界,一物一太极,穷其物理可以通乎人事。
宋人对物性物理的理解自然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中对植物的审美倾向。日常生活中对植物的利用取舍与古人对植物的属性与功能的认识分不开,与此相应,艺术表现和审美取向也在此基础上生成。以松为例来看,松在养生服食中属于神仙上药,松脂、松子、松黄、茯苓等等,服之可助长生不老。其中道理,苏辙在《服茯苓赋》序中讲得很清楚。原因最重要的只有一个:松是长青长生之树。
大概三十二岁时,苏辙始有意于养生之说:“晚读抱朴子书,言服气与草木之药,皆不能致长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为草木之性,埋之则腐,煮之则烂,烧之则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既汩没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则试求之草木之类,寒暑不能移、岁月不能败者,惟松柏为然。古书言松脂流入地下为茯苓,茯苓又千岁则为琥珀,虽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于是求之名山,屑而瀹之,去其脉络,而取其精华,庶几可以固形养气,延年而却老者。”(2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93册,第351页。这一段话将服食养生背后的思维方式清晰呈现出来。草木岁有荣枯,且易腐易毁,草木自身都不能长生,又怎能让人长生呢?金丹可令人长生不老,但世俗中人,哪里能求得到仙丹呢?唯有求之于那些寒暑不能移、岁月不能败的草木,如松柏,岁寒不凋,千年不死。苏辙认为物性与人性相通,松的长青长生是与人的长生长寿相感应的,这种取譬连类的思维方式是由建立在气化论基础上的感应论所决定的。
宋人认为只有长生不死的植物才能有助于人的延年益寿,而经历岁月的古松也自有其独特的形态。《淮南子》言:“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丝。”茯苓出于大松之下,为松脂流入地下而成,茯苓千岁则为琥珀,所以,伏苓、琥珀服之可以固形养气,延年却老。
这一形态反映在宋代的艺术作品中,还具有一种社会秩序和人伦之理的隐喻。宋画中的松树上大多挂着兔丝或其他藤本植物。如《静听松风图》、《松风楼观图》中高大的松枝上都挂着兔丝之类的攀缘植物,可见此松皆为古松。《听琴图》画面正中一棵苍松,枝叶繁茂,松边种着一株凌霄,攀附而上,花开艳丽,恰是陆游所吟“庭中青松四无邻,陵霄百尺依松身”(《陵霄花》)。松与藤的意象,与《诗经·樛木》中樛木与葛藟的意象相类:“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樛木与葛藟是乔木与附藤的关系,王夫之认为此诗的深广大义是“圣人不绝报施之情”,“受者安,报者不倦,咸恒之理得,上下之情交”,“报施者人道之常也,奚为其不可哉!”(30)王夫之:《诗广传》,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5页。施与报体现在樛木与葛藟的关系中,也体现在天人、君臣、父子、夫妇等普遍的关系中,上下相感,阴阳相和,报施之情,是自然之道,也是人伦之常,天地草木君臣夫妇,相距又相亲,相别又相依,这正是天地的教化流行,体现出万物一体的有情世界观。
又如苏汉臣的《秋庭婴戏图》,庭院中有一假山高大坚硬,顶天立地,支撑起画面,也仿佛去撑起整座花园、整个家的父亲,而依偎在假山周围的木芙蓉则像温柔娇媚的母亲,假山和花草形成了既有安全感又充满温馨的氛围,环绕着孩子们(31)宋丽萍:《发现历史的美——读懂中国传世名画(二)》,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5页。。乔松与凌霄、樛木与葛藟、山石与芙蓉,它们是草木相感、木石相依,也是天地教化的流行,这是古人所推崇的礼乐教化。草木之情、夫妻之情、父子之情、君臣之情,这是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伦的秩序,天地间和风弥漫,人世间安宁和乐。
可见,对植物自然之理的体悟贯穿于宋人的日常生活、艺术表现及社会伦常中。
五、宋代植物审美中的天地气象
宋代植物审美具有重视岁寒之美、澄治之功和性理之趣的鲜明特点,而其最终境界是要呈现出一种天地气象。天地气象,从自然而言,是天地的生生之意;从人而言,是能遵从天地生生之理,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将这一精神践行出来。天地气象是理学家所推崇和追求的圣人气象,是圣人人格的最终完成,也是理学美学境界的最高体现。
自然气象与圣人气象相反相成,相互开显。程颐讲“观乎圣人,则见天地”(32)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14页。,是指从圣人气象中见出自然气象与天地精神,强调圣人对天地精神与自然气象的开显,没有人为天地立心,天地终究也是无明的存在,而对自然气象的领悟将有助于我们对圣贤气象的理解。可见,圣人气象与自然气象可以互相发明,从而在对方中彰显自身。如黄庭坚称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33)脱脱等:《宋史》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11页。,朱熹在《濂溪先生像赞》中赞周敦颐“风月无边,庭草交翠”,这正是以自然气象与植物精神对圣人天地气象的表达和形容。
其一,植物可以构成圣人气象与自然气象相通的内在根据。二者相通的内在根据是理学关于天人之际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我们可以通过理学家对自然中的“元”和人性中的“仁”的论述加以理解。《近思录》中有“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34)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第9页。,朱熹在《仁说》中指出“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35)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79页。。可见,四德指元亨利贞,从自然的维度而言,指元气的发端、亨通、畅遂和完成,元为四德之首。五德指仁义礼智信,仁为五德之首。在自然层面,可以通过植物来体会元亨利贞的生命过程和自然物性;在人伦层面,则有仁义礼智信的中正气象。“元”与“仁”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取譬设喻,而是根性上的相通,“仁”是社会中的元气,“元”是自然中的仁意,“元”与“仁”的会通是天人之际的连接点。因此,观万物生意可以恢复人的清明本性,宋人爱花,善莳花艺草,是宋人深通物性与人性通达之理。可以说,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的性理,向内发现了人性的性理。
其二,圣人气象与四时春秋气象的互显。程颢首次将古代圣贤气象与自然气象相比拟,提出:
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材,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36)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第348页。
孔子,天地气象;颜子,春之气象;孟子,秋之气象。这里为什么没有夏气和冬气呢?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如起承转合,夏承春而来,是生长的季节,冬承秋而来,是含藏的季节。周敦颐说过:“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37)周敦颐:《周敦颐集》,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82页。又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38)周敦颐:《周敦颐集》,第71页。由此可知,春夏是阳生万物的气象,秋冬是阴成万物的气象,前者重在“生”,后者重在“成”,一进一退,一息(阳进)一消(阳退)。概而言之,春、秋气象与阳、阴气象是相应的。
孔子如“元气”,元气是冲和之气,涵四时气象,变化万千。颜子如沐春风,化生万物;孟子似秋气肃杀,凌厉森严。“夫子大圣之资,犹元气周流,浑沦溥博,无有涯涘,罔见间隙。颜子亚圣之才,如春阳盎然,发生万物,四时之首,众善之长也。孟子亦亚圣之才,刚烈明辨,整齐严肃,故并秋杀尽见”(39)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第348页。。元气含藏万有,无所不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贵能得其时也。春气和畅,滋养万物;秋气萧杀,威严耸立。元气如至圣大德,生意通达而不着迹。“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无迹,指圣人不着相、不拘泥。有天地之德,方能不着相,这是圣人的最高境界即天地气象。天地气象“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如满天繁而不乱的树叶,各有生长的空间,万物各遂其性,正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地仁心的体现,此即海阔天空、鸢飞鱼跃之境。
二程门人亦以春、秋气象论二程。门人以“如坐春风”喻明道,“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40)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26页。。刘立之师从程颢三十年,称“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41)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第361页。。程颐则称程颢“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42)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第355页。。概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程颢如颜子,如沐春风,有春生气象;程颐如孟子,程门立雪,森严肃穆,有秋杀气象。
当然,春秋气象也与时气有关。时气既指自然的时令,也可指社会的时气。就大自然时令而言,春之后有秋;就社会的时气而言,古人认为社会的治乱一如春秋相继,所以春气之后将承之以秋气,也是“时”的原因。气象的不同因时势所变,一时有一时之气象。如:
古之被衣冠者,魁伟质厚,气象自别。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称。盖自是气有淳漓。正如春气盛时,生得物如何,春气衰时,生得物如何,必然别。今之始开荒田,初岁种之,可得数倍,及其久,则一岁薄于一岁,此乃常理。观三代之时,生多少圣人,后世至今,何故寂寥未闻,盖气自是有盛则必有衰,衰则终必复盛。(4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46页。
然人处岁时变化之际,更当有岁寒之心,这样才能体悟生命中的通达与乐适之情。“伊川归自涪州,气貌容色髭发皆胜平昔。门人问何以得此?先生曰:‘学之力也。大凡学者,学处患难贫贱,若富贵荣达,即不须学也。’”(44)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30页。学恰恰要在贫贱中学,伊川从被贬之地涪州归来,气貌容色更胜平常。这正是岁寒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使其能在贬谪流放之地粹炼而成,依然能独立自得,这种转变根源于理学精神的通达,这与唐人在流放贬谪之后多有无法排解的抑郁之情有着时代精神上的区别。
其三,天地气象与植物审美中的至乐之境。至天地气象这一境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乐”,这一最高境界回到了理学最初的追问:“寻孔颜乐处”。这种乐是学道、体道、得道之乐。理学诗中对此多有表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程颢的《春日偶成》、《秋日》和朱熹的《春日》:
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秋 日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春 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三首诗都与对自然和植物的欣赏有关,而“闲”、“静”、“乐”更是诗中的关键字眼,体现了主体的学道功夫和体道境界。以《秋日》为例,“闲”并不是无事可做或不做事时,而是心能得“闲”,因为心的安定与闲静,既能让物呈现出自性,亦能观己之自性,能见出万物的四时景致与人性相通。道通达天地有形与无形间,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中的天理是一样的,在天地风云的变化中可以体悟这一道理,如此才能富贵不移贫贱乐,人能至此境便是英雄豪杰。
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也提到了植物审美中的适性之趣与真乐之境:“‘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45)罗大经:《鹤林玉露》,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9页。可见,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如果失去或缺少了自然的一维,生活会怎样?没有草木虫鱼,诗的世界就会少掉一半,人的智慧、情感和趣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就会枯竭干涸了。自然的维度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是培养仁的土壤,是有关乎本源之思和深层教养的重要维度,生在自然中的植物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宋人喜谈“乐”,有富贵之乐、山林之乐,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孔颜乐处之“乐”与此都有所不同,是“忧中乐”、“乐处忧”:
或曰,君子有终身之忧;又曰,忧以天下;又曰,莫知我忧;又曰,先天下之忧而忧。此义又是如何?曰: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故魏鹤山诗云:“须知陋巷忧中乐,又识耕莘乐处忧。”古之诗人有识见者,如陶彭泽、杜少陵,亦皆有忧乐。如采菊东篱,挥杯劝影,乐矣,而有平陆成江之忧;步屧春风,泥饮田父,乐矣,而有眉攒万国之忧。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46)罗大经:《鹤林玉露》,第273页。
“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忧与乐如何才能并行不悖?这个问题在宋代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关注,这与古人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先有出世之心才能有入世之志相关。以朱熹对“绘事后素”的理解为例来看,绘事后素出自于《考工记》:“凡画缋之事,后素功。”(47)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8页。学界对绘事后素的理解历来有不同解读,大体而言,有两种:一是从技法上来理解,先绘五彩再以素粉勾勒;二是从质素上来理解,先有素帛再绘五彩,实则是文与质的关系。朱熹即是从后一角度来阐发。朱熹认为是“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4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3页。。朱熹的注解毫无疑问具有理学的时代色彩,意即先有天地仁心,然后才有礼乐文章。就其理学背景来看,他是将天地美质推到了时代思潮的前台,将人性的底色(闲淡乐适)置于礼乐文章之前,以此才能忧乐不悖,才能达于至乐之境,这也是宋代艺术精神尚冲和平淡的深层意蕴所在。这一境界要求艺术家既要能深入人生又要能超越人生,在审美理想上,才能“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简易中包罗万象;在哲学精神上,则体现出一种世出世间的圆融智慧,葆有内在圆融广大的生命自由和生命境界。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与植物共具天地之性。从根本上来说植物与人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类比或比喻、象征,而是一种存在的相遇,人与植物的对话是人与存在的世界的对话,借由植物审美可以通向无限的审美之维,而达于个体的生命与宇宙的生命本源的融合。宋代植物审美注重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的内在相通,通过观物体道、涵养性情,达于澄明之境,触及到古代植物审美最内在深层的意蕴,从根本上完成中国古代植物审美的理论体系。宋代植物审美于草木中见天地心、圣贤心,将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相通达,将天地自然气象与圣人气象相贯通,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审美理想上体现出一种广大自由的天地境界,这正是中国古典美学亘古常新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一个民族对植物的审美可以反映该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而不同民族的植物审美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宋代植物审美中体现出来的三个突出特点,即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感通之力、天人之际的岁寒之心和人由此所体悟到的不改之乐,在当代植物审美文化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植物审美文化涉及到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等多方面因素,体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当前中西方博物学的复兴也为植物审美的研究带来更加系统、整体和开放的视野。古代植物审美是在理气论、感应论与心性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植物审美如何在当代继续发展,需要面对当代植物学、生态科学和现代科学思维所带来的最新成果,古与今、中与西如何对话、对接,是一个需要继续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