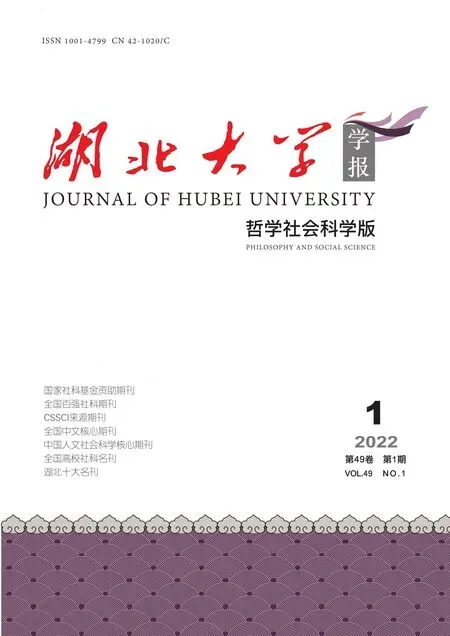论“译名之争”对《尚书》西传的影响
——19世纪中西文化争与合的一个案例
毛耀辉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肇端于17世纪的“礼仪之争”和19世纪愈演愈烈的“译名之争”,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两大重要文化现象,不仅深刻影响“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客观上也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起到重要推进作用。虽然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时争夺“文化话语权”的体现,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思想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之争衡。但较之于宏观的“礼仪之争”,“译名之争”更为具体,表明此时争论逐渐从文化比较深入至语言文字辨析,即从宏观进入微观,从概念进入史实,从西籍进入中籍,从某种程度而言“译名之争”可被视为“礼仪之争”下相对独立的一个子议题。
贯穿“礼仪之争”始末曾发生过两次“译名之争”:第一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关于核心概念“Deus”译名的争论,其结果是经1628年嘉定会议初步讨论,至1704、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XI,1649—1721)颁布教谕,最终确定“天主”为正宗译法,废弃“天”、“上帝”等译法;第二次是19世纪前半叶基督新教关于《圣经》中“God”译名的争论,其结果是历经英、美新教教士反复论证,针对“神”、“上帝”的择选无法达成一致,只好各持所见,各自为是,最终导致《圣经》多译本出现。
本文旨在以“译名之争”对《尚书》西传的影响为线索,探讨19世纪中西文化的“争”、“合”过程。关键问题有四:其一,“译名之争”与“礼仪之争”有何关系,进而对中国典籍西传有何促进作用;其二,《尚书》缘何会进入19世纪“译名之争”的纠纷中来;其三,接触《尚书》对来华教士各自主张产生了何种影响;其四,在对待中国文化、利用典籍文献时,不同派别及主张的传教士有何主观倾向,其背后深层根源主要关涉哪些方面,进而对中西文化交流有何借鉴意义。
一、“译名之争”与“礼仪之争”的关系
“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具有冲突性的文化现象。学界通常认为,它起始于明末清初来华教士有关“祀孔祭祖”礼仪的争论,终结于1939年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1876—1958)“众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谕的颁布。关于“礼仪之争”所应涵盖具体范围,由于研究视角不同,中西方学者在认识上有所差异。有西方学者认为,“礼仪之争”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中国人对家族祖先的祭拜,二是对孔子的祭拜,三是对帝制礼仪的践行(1)Paul Rule,“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A Long Lasting Controversy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History”,Pacific Rim Report,No.32,2004.。中国学者对此持有异议,认为“礼仪之争”还应包括“译名之争”(2)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页。。张西平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曾明确指出:“‘礼仪之争’最初仅是一个译名之争。”(3)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74页。可见,上述观点不同主要在于“译名之争”的归属问题。
诚然,就中国“祀孔祭祖”和其他传统礼仪能否与西方天主教相容,的确是争论初期的核心议题,但有关天主教对造物主“Deus”的称呼,除“天主”外,能否还与“上帝”、“天”等中国传统概念匹配,同样是“礼仪之争”发生初的一个重要争论点。专注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曾直言:“礼仪之争的全称当是‘中国礼仪与译名之争’。”(4)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可见,广义的“译名之争”应包含于“礼仪之争”内。
但具体而言,“译名之争”与“礼仪之争”并非“支流”与“源头”的关系。原因有三:第一,争论表层聚焦点不同。“礼仪之争”涵盖范围显然更广,涉及中国传统习俗、宗教意识以及传教方式等方面;而“译名之争”则主要是藉由语言、文字讨论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文史渊源。第二,争论所反映核心问题不同。“礼仪之争”呈现出基督教自身“排他性”,表现为它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而“译名之争”呈现出的则是传达教义时的“择优”倾向,即承认中国文化足以表述基督教教义,进而对更为合适的用词加以甄别并予以采纳,其背后显然具有某种文化融合性特征,进而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排他性”(争)形成了对应的“合”。第三,争论发展样貌不同。“礼仪之争”历经三百余年反复、断续的发展,争论主题基本未变;而“译名之争”则随来华传教团体变化,争论主题也随之变化。由此可见,第一次“译名之争”实属“礼仪之争”的一部分,但19世纪后来华教士已脱离旧的天主教徒身份,更多是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教士,所以第二次“译名之争”仅可作为“礼仪之争”的回响,因为争论内在属性已然发生变化。
整体上看,相较于宏观的“礼仪之争”,“译名之争”的出现标志着来华教士在讨论中西文化时,找到了一条建立于文字、语言层面上的具体路径;其身份特征随之愈加丰富,开始逐渐向文献译介者、典籍传播者、文化研究者过渡,进而成为中国文化向西方传递的桥梁,对中国典籍跨文化传播有着重要影响。不同时期传教士有关译名问题的讨论,实际正是两种异质文化不断深入碰撞(争与合)的必然结果,这就使得以传教为宏观目的的“西学东渐”,也必然包含“东学西传”的成分。伴随“译名之争”的逐步展开,来华教士普遍在中国典籍中挖掘所需论据,间接促进中国典籍及其所含思想远传西方,恰是“译名之争”对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所在,两次“译名之争”与中国典籍西传的联系是清晰且直接的。
第一次“译名之争”发生于17、18世纪天主教士来华传教时期。由于此时欧洲通用传教语言为拉丁语和法语,因此,大量有关中国典籍的拉丁文、法文译著在这一争论催动下相继问世于欧洲。譬如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编纂的《中华帝国志》就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正如有专家指出,“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典籍西译的一个重要著作,也是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代表性著作”(5)张西平:《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国际比较文学》2019年第3期。。但需要注意的是,杜赫德本人并未到访过中国,其《中华帝国志》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正是由于搜集、整理了当时大量天主教耶稣会士们的信笺和著作。这足以说明,此时传教士有关中国问题的相关探索,对于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典籍在欧洲持续传播,17、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大陆逐渐出现“中国热”文化现象,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第一次“译名之争”将中国典籍传至西方对早期欧洲汉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作为法国启蒙时期“中国热”学者的杰出代表人物,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1694—1778)就曾于《风俗论》中多次表达对中国古代文明及历史高度重视、极力赞美甚至是急切辩护之情:
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典籍《五经》中说,在伏羲氏以后第4个帝王颛顼的时代,已观测到土星、木星、火星、水星和金星的一次会合。现代天文学家对这次会合的时间有争论,其实他们不必争论。即使中国的这次天体观测错了,也是错得有价值的。中国的经书中特别说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已知道金星和水星绕太阳运转。除非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的人才看不到,这样的知识是要经历千百年才能得到的,哪怕这种知识仅仅是一种怀疑。这些古籍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总之,不该由我们这些远处西方一隅的人来对这样一个我们还是野蛮人时便已完全开化的民族的古典文献表示怀疑。(6)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1-242页。
不难发现,伏尔泰内心深处浓厚的“中国情结”与此时典籍西传关系颇为密切。即便其中某些论述后世看来并非客观属实,但却深刻影响当时西方看待中国的宏观视角,也进一步促进了当时崇尚东方文化的整体学术氛围。
第二次“译名之争”发生于19世纪前半叶。此时英美基督新教教士来华,所用传教语言转换为英语,关于中国典籍的英译作品也在此时集中出现。曾深受理雅各影响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便是一位杰出代表人物。他于1867年在上海出版《汉籍解题》(NotesonChineseLiterature),就提要式介绍了二千多部包括古典文学、数学、医学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中国古代典籍(7)Alexander Wylie,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2,pp.viiii-x.,该书是由西方人编纂具有较高价值的中国文献参考书目。但与早先天主教士们不同的是,随着西方“中国热”逐渐褪去,在第二次“译名之争”背后还多出一层将中西文化对立思考的萌芽。对此,学界已有专家指出:
“中国与欧洲的对立性”这一启蒙时代所产生的认识也体现在一些长期占据欧洲学者思维的问题上,比如中国为什么古代先进而近代落后?中国的专制主义结构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年?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几千年不变?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是以中国和欧洲处处相对立为前提……正是这些基于两种文明对立性认识的问题构成了19、20世纪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时的切入点,以及思索中国问题时所置身的基本框架。(8)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2页。
可见,这种对立看待中西文化的视角,使得这一时期来华教士在进行具体争论时,已很大程度摆脱了早先仅针对单一神学问题的探讨,或对中国古代文明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的盲从,而逐渐向具体的文化比较研究过渡。相较于17、18世纪,神学争论逐渐向文化争论演进是这一阶段“译名之争”的重要特征,反映在具体研究上,就是将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献等研究领域作为一系列独立议题来探索。此外,19世纪“中国热”逐渐消退下的中西对立视角,不仅使得这一阶段的争论更具系统性,向学术化初步迈进,为日后“文明形态历史观”、“文明范式”(9)该提法源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提出“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把国家仅仅看作是文明的生命中相当次要和短暂的政治现象的原因。国家正是在文明的怀抱中诞生和消亡的”。参见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文明范式”一词较早由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讨论“文明冲突论”时,进一步深化提出了“文明范式”概念。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8-19页。等文化研究视角提供了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使得日后西方殖民主义倾向(或欧洲中心论思想)初见端倪。
二、19世纪“译名之争”初期西方人眼中的《尚书》
正如前述,发生于19世纪前半叶的“译名之争”包含三个重要特征:一是英语国家传教士介入(主要是英、美两国);二是神学争论向文化争论转变;三是中西对立视角下比较研究倾向凸显。这三个特征都与这一时期西方的两部《尚书》译著密切相关。具体来说,这一阶段的“译名之争”缘起于新教来华教士对早期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圣经》中译本的修订意愿,代表性事件是1843年8月22日来自多个新教教会的传教士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是如何重新译定《圣经》,但究其本质,仍是关于基督教核心词汇,即英文“God”或希腊文“Theos”如何进行汉语翻译的争论。此次会议中,不同教会传教士按所持观点可分两派,正如美国学者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对此总结道:
一派赞成使用中文经典中的“上帝”或就是“帝”来表达“God”,用“神”来表达“Spirit”;另一派则主张用“神”这一词来表达“God”,用“灵”来表达“Spirit”。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究竟用哪一个词来作为“God”的译名。裨治文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主张用“神”,而大部分英国传教士,除了理雅各以外,主张用“帝”或“上帝”。(10)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3页。
同时,《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也对此次会议记录道:“由于很难在中文中找到最合适的译名,因此每一个传教站当下可自行决定所倾向的译法,并留待总会作最终裁决。”(11)“Meeting in Hongkong for Revising the Bible in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2,No.10,1843.关于“God”译名的争论仍悬而未决。
但与早先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对自己所持立场进行辩护时,往往引经据典,“一时之间,对中国的《四书》、《五经》、子书、类书、文集等的探讨与诠释在传教士当中蔚为风气,麦都思、文惠廉、娄礼华等的论文征引的中国文献都达数十种之多。双方都企图从中找出最有力的论据”(12)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由此不难看出,关于“译名之争”与《尚书》西传二者背后应存在如下逻辑关系:“译名之争”间接导致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的追溯,进而使他们将目光投向中国最早历史文献《尚书》,并对其中有关“上帝”的记载进行深入研究,最终致使他们对《尚书》进行译介。关于此,最直接例证便是早期传教士对《圣经》的中译实践。
作为早期《圣经》中译本的重要参译者,米怜曾深刻影响之后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1803—1851)、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等人。在第二次“译名之争”初期,他屡次提及《尚书》与基督教“启示”间的联系。譬如,在1820年出版的专著《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的十年回顾》(ARetrospectoftheFirstTenYearsoftheProtestantMissiontoChina)中,米怜就曾直言《尚书》记录着人类远古时期的“神圣启示”:
有人曾断言,在中国最早的一些著作中,清晰且明确地包含着关于“神圣存在”(divine being)的看法,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可以公正地被证明的……例如中国的“五经”,尤其是其中的《书经》,它是远古时期(primitive ages)中国人的著作,当时传统的“启示之光”还尚未被偶像崇拜或迷信所蒙蔽。仁慈之上帝俯身将其神性与意志以启示方式部分地授予人类祖先,并随着他们的后世子孙传播至世界各地。(13)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p.25.
次年,米怜又将上述看法与此时“译名之争”相联系,并在《印中搜闻》(TheIndo-ChineseGleaner)上发表专论,谈及《尚书》中“上帝”一词与基督教“最高主宰”的关联性,他着重强调道:“‘上帝’一词,从它的古老性、从它所散发的敬畏之义,以及屡屡为《书经》和其他古籍所使用的情况看,它所表达出的‘最高主宰’(supreme ruler)之义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且我们并不应该为它被采用而感到遗憾。”(14)William Milne,“Chinese Terms to Express the Deit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7,No.6,1838-1839.
其实,摆在当时传教士面前有关“God”中译名的备选词汇主要有三:一是“天主”;二是“上帝”;三是“神”。而米怜在争论早期就认为将《尚书》中“上帝”用作“God”中译名颇为适宜且合理,一方面体现出此时新教教士在“译名之争”中的早期立场;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在接下来主张“上帝”译法的传教士当中,深入中国经典挖掘文献“证据”的趋势已然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它清晰体现出“上帝”派教士与“神”派教士在论辩倾向上的不同:前者力图于历史文献中找寻中西共同文化之祖;后者则努力证明中西文化不同,进而突出捍卫基督教信仰的纯正与神圣。正是在这种“合”与“争”的纠缠下,主张“上帝”译法的传教士将目光转向中国“五经”,尤其是《尚书》。例如,1834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于《中国丛报》上发表专论《中国古代典籍的特点与概要》(CharacterandSynopsisoftheChineseClassics),就是受到这一趋势的直接影响。虽然它在发表时间上与米怜的专论相隔13年,但其中关于“上帝”即“最高主宰”的认识,显然就是米怜早先观点的翻版。他在文中如此说道:
在中国“五经”中,《书经》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一部。它由一系列对话所构成,藉由这些对话,我们可以一窥从尧时代至孔子时代的中国历史……这些对话发生在尧、舜、禹以及夏、商、周的君王、大臣们之间。许多高尚的大义都能在这些语录中找到。英雄们将它们所完成的历史伟业诉诸于“上帝”这一“最高主宰”(supreme ruler),并力求得到其认可。《书经》毫无疑问包含着相较于其他中国古籍更加纯净的道德(思想)。(15)Charles Gutzlaff,“Character and Synopsi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No.3,1834.
此外,同年郭士立在另一部专著《中国沿海三次关于暹罗、科雷亚和卢丘岛的航行记:1831、1832、1833年》(JournalofThreeVoyagesalongtheCoastofChinain1831,1832,&1833withNoticesofSiam,Corea,andtheLoo-ChooIslands)中,他更是坚定认为,中国远古时期确曾展现出对“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认知与崇拜,只是随着历史发展,中国人逐渐忘记了它,以至中国成为一个异教国家:
我们可以追溯到的是,有关对“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原始崇拜是被安放在“上帝”名下的……对“上帝”的祭祀,似乎是一种对诺亚及其后代祭祀的仿照;但是由于时间太过久远,若想准确判断出作为圣光和恩典源头的“God”对中国人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深,实在很难。即使《书经》、《诗经》中一些段落已间接提及有关“最高存在”的全知全能,但同样也有数量极多的古籍使得我们认知到,偶像崇拜(idolatry)已然发生很久了……即使是后世的“五经”注疏家们,也经常通过解释的手段,消解其中神圣真理,并将其替换为错误解读,从而曲解文献真实含义。(16)Charles Gutzlaff,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Corea,and the Loo-Choo Islands,London: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1834,pp.370-372.
五年后,在那篇《尚书》综述的结尾部分,郭士立再次点明《尚书》中“上帝”概念与基督教“God”的关联性:
由此可见,正如基督教历史学家一再证明的那样,多神论思想并非立刻发生于大洪水之后,它是被逐渐引入并驱赶了对真正“God”的认识,诺亚所有的后代本都与之熟悉。在本书中,他屡屡被提及,且总是被致以最崇高敬意,若有人认为,(中国)古老传说中的“上帝”即“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看法仍需被证明,那么他只需深入了解《书经》便足以释然。怎会有人胆敢断言,中国人没有关于“God”的名字,这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的。(17)Charles Gutzlaff,“Review of the Shu King,or Book of Record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8,No.8,1839.
作为在第二次“译名之争”中主张“上帝”译法的重要一员,郭士立的上述一系列看法足以真实反映出一个明显趋势:此时西方传教士若想深入古籍来更为精准地找寻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共融之处,对《尚书》进行研究,尤其是翻译,必然是一条重要且不可忽视的路径。例如郭士立在综述《尚书》时,就部分翻译了多个篇章,其中包括《尧典》、《大禹谟》、《汤誓》、《盘庚》、《太誓》的相关段落。
总之,由于《尚书》在19世纪后新教教士眼中深具“远古性”(high antiquity),因此,他们一方面以比较视野审视其中古史成分,以至于稍后形成“疑古”、“信古”两种倾向;但另一方面,一旦结合此时“译名之争”,又往往需要从《尚书》中获取其立场所需论据,为“God”找寻中国历史文献中的依据,以至于将《尚书》视为具有一定真实性的信史文献。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性,实质就是西方异质文化试图融入中国时极难调和之内在矛盾的外在反映。不可否认,此时西方人对中国文献资源的运用,对《尚书》在19世纪后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三、“神”派教士对中国历史的忽视
在麦都思《尚书》译著问世前夕,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和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1819—1847)曾于1845年至1846年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数篇关于译名问题的专论(18)分别为:Comparative View of Six Versions of John i:1(《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六种不同中文译本的比较)、Queries Respect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ds God,Spirit,and Angel(《关于“神、灵、天使”的翻译问题》)、Remarks on the Words God and Spirit,and the Transference of Proper Names into Chinese(《关于“神”、“灵”以及“专有名词”汉译的评述》)、Revis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and Remarks on the Words Spirit and God(《〈圣经〉中文版修订本以及关于“神”、“灵”两个词的评述》)、Words Demanding Attention in Revising the Bible(《修订〈圣经〉时需要注意的词语》)、The Words Shin,Shangti,and Tien,Exami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Version of the Bible(《参照〈圣经〉版本对“神”、“上帝”、“天”进行审查》)、Remarks on the Words and Phrases Best Suited to Express the Names of God in Chinese(《对中文中最适合表达上帝名字的词和短语的评述》)。。作为主张“神”译法的两位代表人物,二人的观点基本了反映当时主张“神”译法教士的主流看法;同时,由于这些专论在发表时间上与麦都思译著最近,因此很大程度也与麦氏对《尚书》的译介存在关联。
在对裨治文和娄理华的观点进行总结前,需首先简述二人的关系。娄理华作为美国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其来华时间是1842年5月27日,并且与比之更早的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来华教士裨治文关系密切(19)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Shanghea: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129-130.。在初到中国澳门时,他便暂住于裨治文住处(20)参见陈伟:《杭州基督教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第2页。。娄理华同样参与了上述1843年8月的香港会议,关于译名问题,他坚定主张采用“神”译法。但从娄理华的研究经历看,他对中国文化更深层的理解应稍显逊色。正如雷孜智对他的判断:
娄礼华在1842年才到中国,因此,几乎可以断定他的大部分观点是出于裨治文授意。作为《中国丛报》的主编,裨治文显然希望在这场争辩中置身幕后,即便实质上他是主张“神”这一译法的主要鼓吹者。(21)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第226页。
据此可知,娄理华关于译名问题的论辩很大程度是在为裨治文发声。同样,他在《中国丛报》上关于译名问题的观点当多受裨治文影响。承接前述,此时裨治文和娄理华关于译名问题的主要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五条:(1)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类似,古希腊有不计其数的神(gods),中国亦是,即中国在古代是“多神论”的(22)E. C. Bridgman,“Revis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and Remarks on the Words Spirit and God”,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5,No.4,1846.。(2)关于“God”译名的问题,首先应是一个关于“翻译模式”(the mode of translating)的问题。任何足以指代“God”的译名,都应具有“神性的原始性”(represent the original),而不仅仅是“某个神性代指”(the name of any one deity),因而它应是一个足以表达单数和复数的统一词(23)W. M. Lowrie,“Remarks on the Words God and Spirit,and the Transference of Proper Names into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4,No.2,1845.。(3)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一词,若抛开它所表达“最高法则”(high rules)之义,并不能体现出“原始性理念”(the idea of the original),即使它足以说明古代中国人确有关于“真神”(the true God)的理念,而且也的确使用“上帝”一词来对其进行表达,但仅说明“上帝”只是一个专名(the name)或头衔(title),因而“上帝”一词仅相当于英文的“The Lord”、希腊文的“Zeus”或罗马文的“Jupiter”,并不能表达神性本身理念(24)W. M. Lowrie,“Remarks on the Words God and Spirit,and the Transference of Proper Names into Chinese”.。(4)中国典籍中的“神”一词,若抛开任何“性状形容词”(qualifying adjective)修饰,便足以表达“God”的含义(25)W. M. Lowrie,“Remarks on the Words God and Spirit,and the Transference of Proper Names into Chinese”.。原因在于,“神”在中国典籍中是可被作为类名或普遍概念来使用的(in the same generic way),可以表达出非局限于某一民族专有之“最高主宰”的内涵,而这一点正与《圣经》中“God”在含义上相契合,同时也是其他词汇所不具备的(26)W. M. Lowrie,“The Words Shin,Shangti,and Tien,Exami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Version of the Bibl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5,No.6,1846.。(5)使用具有综合性的类词“神”来表达基督教“神性”(divinity),以及指代“Jehovah”(耶和华)或“God”,是符合所有基督教国家传统的,可以有效避免使用“上帝”所带来“将基督教最高主宰与中国本土独有之最高主宰对等”的倾向,从而维护基督教“神性”的独立性(27)W. M. Lowrie,“Remarks on the Words and Phrases Best Suited to Express the Names of God in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5,No.12,1846.。
从逻辑层面审视上述观点,可发现,这一阶段“神”译法支持者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争论多从文字、语法、概念出发,从而使论据多限于理念层面。例如文章中关于“类名”和“专名”的比较、关于中国本土“最高主宰”和基督教“最高主宰”的比较,以及有关“神性本身”和“神性分有”的区分等,皆为理念层面的互异比照。第二,争论重视演绎逻辑思绪,而相对轻视归纳逻辑思绪。即便某些专论,如《对中文中最适合表达上帝名字的词和短语的评述》胪列了儒家、道家、佛家、史家文献中有关“上帝”、“帝”、“天”、“神”的大量例证,但一旦进入结论阶段,则立刻回归概念层面,从而使用演绎思路得出支持“神”译法的论据。第三,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古史部分)的整体认知相对匮乏。例如裨治文在《〈圣经〉中文版修订本以及关于“神”、“灵”两个词的评述》中认为,中国在古代如同古希腊一样是多神论。显然,他以“多神论”作为逻辑推演的基础,在当时近乎独断,因为关于中国早先是否是多神论在当时存在不同声音,例证之一便是前述郭士立在综述《尚书》时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裨治文本人并非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在1841年的《中国丛报》上,他曾专文介绍了记载中国传说时代至明末历史的纲目体通史《纲鉴易知录》,并着手翻译该著序言部分(28)E. C. Bridgman,“Value of Chinese Historians,and Notice of the Kang Kien I Chi,or History Made Eas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No.1,1841.。随后,在1841至1843年的《中国丛报》上,他还接连发表一系列针对中国历史的专论,详细勾勒了上至“三皇时代”下至清代的历史脉络。因此,有理由相信,裨治文此时在争论中表现出对中国古史的认知匮乏,一方面或许是源自其争论立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对中国古史的不确定。例如在《中国历代帝王年谱及目录》中,他曾坦言道:“‘三皇时期’即使在中国人看来,也全然属于是神话传说的范畴”(29)E. C. Bridgman,“Chronology and List of all the Dynasties of the Chinese Monarch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No.3,1841.;“‘五帝时期’的五个政权,虽然被多数史家所认可,但当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却很少能被真实地确认”(30)E. C. Bridgman,“Chronology and List of all the Dynasties of the Chinese Monarchy”.;“具有439年统治时长的‘夏代’,针对其历史记录的真实性也颇为存疑”(31)E. C. Bridgman,“Chronology and List of all the Dynasties of the Chinese Monarchy”.。学界有观点认为,“重视儒家传统和典籍的教士皆赞成‘上帝’一词,而‘神’派却流露‘民俗学’的视野”(32)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1807—187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1年,第358-359页。。事实上,前述三个特点最终表达出:美国籍主张“神”译法的传教士企图降低中国文化地位,抬高美国基督教文化地位的用心。吴义雄对此做过深入分析:
他们的这种倾向,与美国带有民族特征的宗教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当时,美国教俗各界均认为,他们年轻的民族受到了“特别的神佑”,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宗教、道德和精神生活要远远高于“异教徒”,也高于旧大陆。因此,他们不能同意将他们的“God”与中国人的“上帝”相提并论,更不能容忍用后者取代前者。同样,也正是由于美国传教士具有这种独特的民族意识,他们才在与英国传教士之间的争论中绝不退让,反对由麦都思等主导《圣经》中译这一重要任务。(33)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由此可见,在前述三个特点中,第三点尤为值得关注。表面上看,它可被视作是前两特点的深层原因,即由于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古史)整体认知主观或客观地忽视,所以有关译名问题的争论多局限于概念层面的演绎推导;但更深入来看,它实际就是一种美国传教士天然所秉持“民族优越论”的直接体现。正如美国历史学者韩德(Micheal H.Hunt)在讨论19世纪中期美国“天定命运”、“上帝选民”思想时给出的材料:
我们国家的诞生是一种新历史的开始,是一种从未尝试过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和演进,它将我们与过去分开,只与未来联结;只要谈到人类自然权利的整体发展,无论是在道德、政治还是在国民生活的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度注定是未来的伟大国家。……在全世界的居民中……上帝选定了最高贵血统,即不列颠大家庭的萨克逊人,他们注定要定居在这个国度。(34)参见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34页。
在这样的意识下,当共同面对其他民族进行文化输出时,即便参与对方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英国人,若相互间发生意见分歧,在此时美国教士看来也应与其争长论短。但实际结果却是:当面对中国这样高度成熟且极其稳固的文化环境时,一厢情愿的“优越”只是一种“狂妄症”;较之明末已注重外在文化形态上与中国求同(儒服)的天主教士,此时脱离历史、文献依据而只作演绎推导丝毫无助于他们的传教,甚至是传教策略上的“退步”。也正是这种忽视,不仅无法说服英国籍主张“上帝”译法的传教士,更是为其留下重要争论空间,即“上帝(或帝)”在中国历史及文献中是深具根源性的。
四、“上帝”派教士对中国古史的重视
19世纪中叶,英国籍新教传教士麦都思和理雅各先后完成两部风格不同的《尚书》英文译著,出版时间相隔近20年,正是“译名之争”由逐步展开至白热化讨论的阶段。1843年8月的香港会议曾做出一项重要决议:“关于神性(Deity)词汇的中文译名,将提请由麦都思和理雅各组成的委员会讨论商议。”(35)“Meeting in Hongkong for Revising the Bible in Chinese”.显然,二人在第二次“译名之争”中具有重要影响,而他们的《尚书》译著也多显露出与这次争论的关联。
(一)麦都思译著与“译名之争”的联系
麦都思的《尚书》译著问世于1846年,正值“译名之争”逐步展开之时。作为“上帝”译法的主要支持者,他与当时主张“神”译法的传教士们展开激烈论辩。整体上看,麦氏坚定认为,使用中国典籍中“上帝”一词来对等翻译《圣经》中“God”是深具合理性的,并试图从两方面着手对此提出论据:一是词汇概念层面;二是词汇历史层面。在麦都思看来,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他对于词汇历史渊源的重视,一方面体现出“上帝”派教士在论辩时的主要倾向;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此时“译名之争”与早先西方人关于中国“古史之争”间的内在关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倾向也与他对中国古史看法的前后转变关系密切。
在《尚书》译著完成前,麦都思于《中国的现状与前景》(China,ItsStateandProspects)中明显表达出的是一种对中国古史的怀疑倾向:他当时认为,中国有关尧舜至大禹时期的历史记录不应被视为信史。但早期这一看法在其《尚书》译著问世时发生重大转变。与《中国的现状与前景》时隔8年,麦氏将《尚书》引申译作“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或历史的典籍:作为中华帝国最古老且真实的编年史),明显表露出的是一种将《尚书》内容视为信史的主观倾向。同时,进一步结合他在“译名之争”中的立场,以及其译著问世时间——正值“译名之争”逐渐展开之时,可知此时麦都思将《尚书》完整译介,并认可其中古史部分的真实性,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希冀通过《尚书》来证明中国人很早就有关于“最高主宰”的认识,而且这一认识在文献中的具体表述就是“上帝”。这一点,在麦都思随后一系列专论中都有所印证。
在麦氏《尚书》译著问世次年,新教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二次译名讨论会。作为第一次“香港会议”的延续,第二次“上海会议”所涉问题更为深入,“双方运用各自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中文的知识进行讨论,并将讨论延伸到对神学和中国几千年文化和宗教的理解方面去”(36)程小娟:《〈圣经〉汉译中“God”的翻译讨论及接受》,郑州: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1页。。会议期间,麦都思于1847年9月14日在《中国丛报》上发表《赞成使用“上帝”翻译“God”》(RemarksinFavorofShangtiforGod)一文,系统反驳了以裨治文和娄理华为代表“神”派教士们的看法,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五条:(1)在所有具备参考价值的中国典籍中,“上帝”一词明确包含“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含义。(2)倘若在北美-印第安文化中,本土词汇里有一个足以指代“伟大精神”(great spirit)的词汇,它将比任何普遍表达“偶像”、“半神”的词汇更应被首先采用,而深具远古性、真实性的中国本土词汇“上帝”,就是这样一个指代“最高存在”的较优选择。(3)依托于对中国本土文献审慎且广泛的观察,“神”并不具备“合一性”(unity)、“至高性”(supremacy)、“无限完美性”(infinite excellence)的理念,“神”所表达出的简单性与原始性,仅能普遍指代“属灵的”(spiritual)和“无形的”(invisible)之类的存在,甚至是一种“低等级秩序”(an inferior order),仅类似于罗马文化中的“永生者”(dii immortales)、阿拉伯文化中的“灯神”(djin)或西方文化中的“魔仆”(genii)。(4)根据中国古代语言特性,一个词一旦用于指称“众多的”、“普遍的”概念时,它便很难再被用于指称“单数的”、“专有的”概念。在任何一部中国典籍或中国正统著书家的著作中,去掉了前缀形容词(standing alone without qualification)的“神”,都不可避免具有着泛指含义,甚至在日常对话中,它传递的仍是复多理念,因此“神”不足以代指唯一且真存的“God”或“Jehovah”。(5)从“译名之争”的历史来看,早于新教的天主教已放弃使用“神”译法而转向“天主”译法,更说明“神”译法并不完善(37)Walter Henry Medhurst,“Remarks in Favor of Shangti for God”,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6,No.1,1847.。
不难看出,通过这篇专论,麦都思对裨治文和娄理华早先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从整体逻辑层面看,相较于主张“神”译法的传教士,双方共通之处在于:麦都思同样重视从概念层面对“上帝”、“神”与“God”进行辨析。例如文章中关于“泛指”和“特称”的比较、对中国语言中“泛指”和“特称”转换关系的比对等。但不同之处有两点:第一,论据偏向归纳思绪,如文章以北美-印第安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传统天主教看法来归纳出他所支持使用“上帝”一词的合理性。第二,观点更具“重视中国历史”、“植根中国本土文化”的倾向,如文中看法大多依托于对中国文献、典籍的总结而得出。并且,麦都思颇为留意对这些材料进行甄别,他不止一次强调“经典名著”(every Chinese book of note and worth)、“古代权威”(ancient authority)、“中国本土思维”(Chinese cultivated mind)、“中国典籍或中国正统著书家”(Chinese classics and standard writers)对于寻找论据的重要性。言下之意,麦都思认为,此时裨治文和娄理华所采用的支撑文献是不准确的。
可以补充的一点是,麦都思对文献“权威性”、“正统性”颇为重视,在其《尚书》译著中也有深刻体现:麦氏所采用底本是中国宋代蔡沈的《书经集传》,而《书经集传》虽持疑辨视角审视五十八篇经文,却仍然完整保留孔安国古文《尚书》全貌。这在中国经学史,尤其是中国本土《尚书》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38)参见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5页。。
综上可以看出,与前述1845、1846年主张“神”译法的美籍传教士不同,麦都思针对“上帝”译法所寻出的论据更具历史性且深含归纳思绪。因此,在第二次“译名之争”中,它是一次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论据发掘实践,体现出了这一阶段英、美传教士之间截然不同的两种特点。同时也不难发现,当“译名之争”将问题引申到追溯中国古史问题上时,《尚书》进入传教士视野似乎是一个必然。而在此节点上,麦都思完整将《尚书》译为英文,便是向对方辩者投出的一个有力论据。
(二)麦都思对理雅各及其《尚书》译著的影响
麦都思《尚书》译著问世的1846年,既是他本人关于中国古史认知发生转变的一年,也是他对中国人信仰认知逐步发生变化的一年。此时“译名之争”仍在进行,尚未有丝毫将要结束的征兆,各持所见的传教士们毫不退让。即使麦都思已将译著出版,并希冀将它作为“上帝”译法的有力论据,但还是可以看出,在大环境的影响下麦氏仍“有所保留”。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在《尚书》译著中,他对“上帝”一词的翻译有所保留,即他没有冒然将“上帝”对等地译为英文“God”,而是使用了“Supreme Ruler”一词;二是对《尚书》是否体现出中国宗教情怀的看法有所保留,例如他在译著前言中坦言道:
(《尚书》)有一个不足,就是对于宗教向往的缺失。“至上”(the supreme)本身及其掌管人间事物(的迹象)虽常被提及,但这一“庄严的最高权威”却常常与物质化的天相混淆,进而与山神、河神、先祖以及英烈的英灵联系在一起。(《尚书》)没有灌输并要求人们该如何去爱上帝这位圣父,也未提及若上帝发怒人们该如何调和,这样一个有关“上帝——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尚书》)构建起了一个绝佳且来自于一个独立渊源的“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样本,它并不教人关注灵魂的或是永恒的部分。(39)Walter Henry Medhurst,The Shoo King,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ea:The Mission Press,1846,p.viii.
麦都思此时的“有所保留”,一方面说明译名问题仍未达成统一认识,因此,即便他将《尚书》认可为一部信史文献,且其中确有关于“上帝”即“最高主宰”的表达,但仍未冒然将“上帝”与“God”等视进而等译;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麦都思自身对中国宗教看法的不断发展,因为在这部译著问世仅一年后,他便公开承认,中国古史时期是具有宗教成分的。这一点,在前述麦氏1847年的专论,以及同年问世的专著《论中国人的神学》(ADissertationontheTheologyoftheChinese)中都有所体现。通过将麦都思《尚书》译著前言与《论中国人的神学》对读,可知其认知变化核心在于对中国古代“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成分的承认。例如他在书中认为:
同样,中国经典文献保存有许多关于“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记载。就对其认识程度而言,中国人已有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有关“最高存在”之属性与美德的认识架构,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并非对于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完全无知。诚然,他们的这一套观念在获取特殊启示上存在着方方面面的缺陷,正如它本初的那样,随着历史的推进,常常被迷信活动所腐化。但归根结底,我们确实找到了许多有关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的基本事实,就如同古希腊、古罗马圣哲们所表述的那样,“God”的影子从未在东方消失。(40)Walter Henry Medhurst,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the Chinese,with a View to the Elucidation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Term for Expressing the Deity,in the Chinese Language,Shanghea:The Mission Press,1847,p.2.
对中国古代宗教认知的变化,预示着麦都思试图将此时关于“译名”问题的争论,藉由对中国古史的追溯引入到一个更高、更古且更加宽泛的层面,即中国古代“自然宗教”与基督教“启示”(revelation)的关系上。这显然对于他所主张的“上帝”译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麦氏关于“《尚书》建构起了一个‘自然宗教’样本”的认识,对于理雅各的《尚书》译著,以及他在译名问题上的论辩深具启发,以至于重返香港后的理雅各在“译名之争”中的立场发生重要转变,从支持“神”译法进而转向支持“上帝”译法。
简单来说,自然神学是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以英国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等思想家为代表人物的一种神学思潮,是反对“唯《圣经》论”的。在洛克等人看来,《圣经》并非人类获得启示的唯一通道,上帝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洛克曾提出观点,认为“全世界所有的人,只要他们不是对自己与生俱来的一些本能漠不关心,只要他们不拒绝接受自然的引导,那么他们便具备了足够的天分,就能够在自然界里发现上帝及其神迹”(41)John Locke,Essays on the Law of Nature,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4,p.155.。这一脉思路被之后英国基督教哲学家帕勒(William Paley,1743—1805)等人继承,帕勒进而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自然神学与特别启示(special revelation)间的关系。至于自然神学对理雅各的影响,学界已有专家指出:“苏格兰哲学家威廉·帕勒的主张在理雅各的头脑里也留下了印记,他提出造物主在古老的中国可能也留下见证。这个由自然神学转向特别启示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使理雅各努力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去寻找上帝与启示。”(42)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在这一时期的“译名之争”中,理雅各深知此时麦都思抛出“《尚书》建构起了一个‘自然宗教’样本”的看法,并非是要将问题重新拉回到18世纪初,那场发生于天主教内部有关中国是否具有“自然神学”的讨论范畴中(43)18世纪初,西方学者与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们曾针对中国是否具有自然神学的议题做过一番讨论。当时对于该议题的讨论范畴,仍多局限于宋代理学思想与自然神学的异同。例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与天主教传教士龙华民,曾关于“道”、“理”、“太极”、“太一”等宋代理学概念,与“善”、“恶”等基督教概念进行讨论。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第287-306。,而是希冀依托中国古代文献,将讨论范畴扩大到更古老的中国历史中去。这与麦氏在译名问题上“重视中国历史”、“植根中国本土文化”的倾向是一脉相承的。但可惜的是,此时主张“神”译法的传教士并未延续麦都思的思路对中国古史中的宗教思想进行纵深探索,而是仍把论辩重点放在宋代理学思想上,进而证明其与基督教思想背道而驰。在理雅各看来,后世宋代理学思想并不足以完整反映中国宗教思想的全貌,换言之,同麦都思一样,他也认为此时主张“神”译法的传教士们未能参考真正反映中国传统宗教观念的原始文献。因此,延续麦都思对译名问题的讨论路径,理雅各颇为重视先秦典籍中有关“上帝”的记载。他先是从概念出发,认为“‘God’一词即便在西方语言里也根本不是一个类属的表达,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真正的意义来自上帝与其所主宰的人和自然所构成的世界的关系”(44)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第237页。,随后更是坚定坦言道:“中国人原本就对真正的上帝有所认知,我欣喜地发现中国经典中的‘上帝’,以及中国人(观念中)的上帝,就是那个唯一至高且永恒的‘God’。”(45)W. J. Boone,“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 Elohim and Theo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9,No.7,1850.理雅各此时所提到的“中国经典”,自然就包括《尚书》。
在理雅各《尚书》译著问世前夕,他已明确提出《尚书》包含大量有关“上帝”记录的看法。在1852年,他专门针对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的观点撰写了一部专著——《中国人的上帝观与神灵观》(TheNotionsoftheChineseConcerningGodandSpirits)。在该著第二章中,理雅各特意引用麦都思关于“舜摄行天子事,类告昊天上帝”中“上帝”的含义,并结合苏格兰哲学家麦考什(James McCosh,1811—1894)关于“天意安排”(providential arrangement)与“神圣统治”(divine government)在人与物质世界间表象的论述,得出了“自然神学足以显现‘上帝’的存在与属性,且中国典籍文献有效确证了这一事实”的看法。随后,他更是进一步补充道:“倘若我把中国典籍中所有关于上帝统治(the rule ofShang-Te)的段落于此胪列,那么我文章的一大部分将被《书经》和《诗经》所占满。”(46)James Legge,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fense of an Essay,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Hongkong:The Hongkong Register,1852,pp.99,100-101,101.
理雅各《尚书》译著问世于1865年,分别被收录于“中国经典”和“东方圣书”两个系列。作为“上帝”译法的坚定支持者,他做到了麦都思未曾做到的事情——在《尚书》译著中把“上帝”一词直接与“God”对等翻译。从“中国经典”系列出版至“东方圣书”系列问世,其间时隔14年(1865—1879),但无论哪个系列,理雅各都始终坚持这一译法。不仅如此,据学界统计,依据合适的语境,理雅各将中国“五经”中“帝”、“上帝”直译为“God”的次数共计148次(47)参见岳峰:《理雅各翻译中国古经的宗教融合倾向》,《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此举自然引起当时主张“神”译法传教士们的强烈反对,进而联合起来对理雅各进行口诛笔伐:
70年代年末期,当理雅各要向穆勒(F. Max Muller)主编的《东方圣书》贡献其系列译本的时候,24个传教士(包括8个神学博士与5个硕士)联合签名要穆勒拒绝理雅各的《书经》、《诗经》的译本,认为其中诠释中国文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理雅各在译本中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中所说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并把中国古代经典的“帝”译为“God”。(48)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第111页。
但理雅各丝毫没有退缩,在1880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TheReligionsofChina,ConfucianismandTaoism,DescribedandComparedwithChristianity)一书中,他自信所坚持看法并非偏执之见,并重申道:“我们非常欣喜地发现了《书经》、《诗经》中存在有关上帝及其统治的记载,这一点是我们丝毫不需要怀疑的。”(49)James Legge,The Religions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80,p.248.
五、结论
在宏观“礼仪之争”背景下,来华教士有关译名问题的论辩使大量中国文献及其思想被西方世界所了解。在他们眼中,深具“远古性”的《尚书》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思想等的一部重要且核心的元典。伴随19世纪愈演愈烈的“译名之争”,《尚书》向西方传播绝不仅是一次关乎经典古籍的翻译实践,更是一种以西方文化视角阐释中国经典的解释实践。藉由这次争论,《尚书》在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经学地位虽一定程度被降低,但作为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史料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思想价值却在西方人的阐释中被大大提高。这场争论映照出的是整个中西间文化争衡的缩影。
宏观上,在这一文化争衡中,不同教派、不同国籍、不同主张的传教士以一种近乎对立的争论形式,讨论了《圣经》中“God”与《尚书》中“上帝”的关系,有效补充了“上帝”派和“神”派两种主张各自所需的理论依据;讨论了《尚书》中原始思想与中国后世思想的异同,间接引发了传教士在争论时对所引中国典籍的甄别意识。微观上,传教士个人针对《尚书》的看法,前后也呈现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样态,以至于他们对中国原始宗教信仰体系、中国原始文化内涵得出了发展性看法。
其中值得深思的是,美国籍“神”派教士与英国籍“上帝”派教士,二者表面似乎只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忽视或重视而导致观点产生分歧,始终对立且很难取得统一,但其背后关涉的却是一个更深层的对立倾向:前者论辩时倾向于对基督教“正统性”的推崇与维护,突出捍卫基督教信仰的纯正与神圣,因而相关讨论核心表达出“概念化”、“理念化”甚至是抽象演绎的思想过程,但严格来看,既不符合中国古代文献考据的思维逻辑,更无法说服对方辩者;后者则努力于中国典籍中搜寻“上帝”的意义,希冀在中西文化中找寻契合点,因而译名问题的论述更多体现出考据意识与历史研究特征。总之,正是这种对立、反复、冲突的争论样态,为后世提供了一条关于《尚书》是如何进入英语世界的可考路径:中西间文化争衡(即“礼仪之争”)引发“译名之争”,进而“译名之争”关于“God”译法的主张引起传教士针对“上帝”、“神”在中国典籍中的追索,这一追索使得主张“上帝”译法的传教士最终将目光聚焦于《尚书》,并对其进行译介。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世纪来华教士对《尚书》的译介,无论是介绍性著作、节译著作还是完整译著,大致都与“译名之争”存在关联,而他们在这场争论中的主张与站位深刻影响着对《尚书》的阐释:无论是主张“上帝”译法还是“神”译法,传教士们在解读《尚书》内涵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基督教视域,以及争论立场所赋予的前见。因此,这一阶段《尚书》向西方的传播含有一定生硬比附和牵强附会的成分,其中有些理解甚至是“荒诞”和“幼稚”的。此外,从根本动机来看,他们在认识中国历史、传播与阐释中国典籍时所持仍是传教目的。即便相较明末天主教士囿于外在文化形态上与中国的“求同”,以及技艺层面上向中国的“示新”,此时新教教士已然进入文化传教的较深层次——如英国籍“上帝”派教士试图从中国历史中找祖宗、找契合,表达出一种进步的“文化融合”倾向,但在这种“争”与“合”、“保守”与“改革”之间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仍能被清晰感知;尤其是美国籍“神”派教士在面对异质文化时表现出的“民族优越感”,对于真正文化交流——本应源自于对异质文化真正理解和认同,对多元文化自身历史和发展道路的尊重,都无丝毫助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