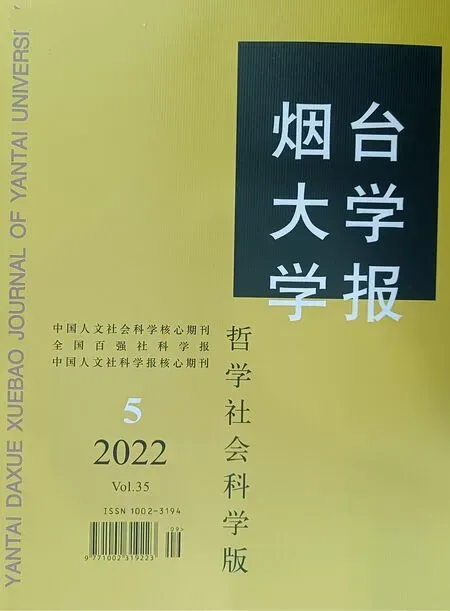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中的“世界图像”
——兼及图像批判问题
刘笑非,张 运
(1.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2.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珠海 519082)
2003年《文艺争鸣》杂志第六期刊发了一组关于“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专题文章,以此为标志,国内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场大讨论在2004年达到高潮,直到2005年末才基本落幕。(1)对这场大讨论的缘起以及学者们争论的主要问题的说明,可以参看陆扬:《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章“何以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议题实际上最初来自西方,例如韦尔施在其1997年出版的《重构美学》一书的开头就向我们指出:“毫无疑问,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美学的勃兴。它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2)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4页。这里“美学的勃兴”指的是我们称之为“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现象。就术语的命名来说,“审美化”是对这一现象基本性质的规定,指“将非审美的东西变成或理解为美”(3)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13页。,而“日常生活”则界定了现象所及的范围,表明它已经深入到最广阔的大众生活中。
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来说,我们最切身的感受毫无疑问是图像的增殖,越来越丰富的图像充斥着现代人生活的每个角落。王德胜的《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一文最为直接地以日常生活中“图像”(视像)及其快感的合法性为中心描述和建构了一种与古典时代“精神的美学”相区别的“眼睛的美学”,是为“新的美学原则”。(4)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但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所关注的主要不是这种现实的图像,而是从这些现实的图像中衍生出来的“图像性”(如符号性、虚拟性、建构性等抽象性质)。在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西方理论源头那里,韦尔施的《重构美学》和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都对图像性问题有不少讨论。韦尔施从图像的虚拟性和建构性中看到了一种“认识论的审美化”的可能,费瑟斯通则是借助波德里亚和拉什等人的理论从图像性的角度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内在逻辑呈现出来。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有很多,如金惠敏在《审美化研究的图像学路线》一文中就明确批评了这种图像性,认为“由图像所造成的审美化是在哲学上,在哲学认识论上被批判、被否定的,这是说,图像之罪,图像—审美化之罪,在于其对认识对象的遮蔽甚至模拟性取代”。(5)金惠敏:《审美化研究的图像学路线》,《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图像批判就是以这种图像性为基础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图像”在这些讨论中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性质,超越了单纯的视觉图像的含义,但对其更进一步的哲学基础的思考却显得相当不足。“图像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学者们往往会从这种图像性出发批判图像对人的控制性?海德格尔在其《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发展出一种以“人成为主体”和“世界成为图像”为核心的“表象—图像”理论,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中的图像性问题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此文虽然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如果我们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对“世界图像”和“图像性”这两个概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恰恰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图像性的角度进行的图像批判也可以在”世界图像“的理论视域中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持。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中的图像性问题
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扑面而来的是大量夺人眼球的图像:电影、电视中呈现的影像越来越细腻、精致,书籍、报刊的页面日益为图片而不是文字所填满,大型商场中的巨型海报无时不在吸引着“闲逛者”的目光,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如果没有吸引人眼球的图像作为外包装则很难让人产生购买的欲望。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由于图像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中的核心地位,相应地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中,“图像”也成为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概念。韦尔施区分了两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浅层的和深层的。浅层的审美化包括现实的审美装饰,以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为目的,这是作为一种经济策略的审美化。在浅层的审美化中,图像实际上是被用作进行装饰美化、提供感官享受以及提高商品销售量的手段。这些对图像的使用方式显然并非当代社会的专利,只不过由于机械复制时代图像生产的便易性,我们对图像的利用要比以往一切时代都更加彻底和深入。审美化之所以能在当代进入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对图像的依赖不断发展的结果。不过,对图像的依赖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对图像的现实使用上(装饰、享受等),更重要的是,图像已经成为我们将世界“理想化”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韦尔施在“深层的审美化”中所强调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建构’”。韦尔施说:“一度以为是古板不变的现实,已被证明是可变的,可作新的结合,纵使审美的想象天马行空,千奇百怪,亦有可能实现。……从今日的技术观点来看,现实是最柔顺、最轻巧的东西。”(6)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8-9页。无论是计算机对现实的模拟和预测,还是现代传媒对“事实”的报道,都成为人建构现实的一部分。在这里,图像一词褪去了它本来的含义,而成为虚拟性、建构性的代名词,也即一种“图像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韦尔施进一步提到了“最激动人心、也最深刻的审美化”,(7)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33页。即“认识论的审美化”。
韦尔施认为,从康德开始到尼采,直至今天的哲学乃至科学实践,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认识论的审美化提供了例证。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都是从“美学”的角度出发的,而是说他们的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对“图像”的那种抽象意义的理解上:对人来说,现实是一种“图像”,是被人理解和建构起来的,而非固定不变的客观实在。按照韦尔施的看法,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审美化理解,因为时间和空间作为构成知识的先验形式首先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一种直观形式,“我们的认知和现实所能达到的限度,一如这些直觉形式的延伸程度”。(8)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34页。尼采则更直接,他认为“现实是我们产生的一种建构,就像艺术家通过直觉、投射、想象和图像等形式予以现实的虚构手段”,(9)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34页。人是“会建构的动物”,因而世界也是被建构的世界。诚如韦尔施所说:“‘诗性化的文化’……知道我们的‘基本原理’都是经过审美构成的,因此整个儿就是‘文化制品’,只能够比照其他文化制品来作审度,永远不可能比照现实本身。”(10)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37页。这种看法的确是对传统哲学的一种挑战,因为传统哲学几乎都认为在人们所认识的现象背后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根据,后者才是真实可靠因而值得追求的,而现象则只是一种对这种根据的歪曲或不完整的呈现,因而与真理无关。然而在韦尔施这里,在“认识论的审美化”中,这种作为真理的试金石的客观根据消失了,因为现在存在意味着“理解存在”,现象本身就是真理的试金石。
如果说韦尔施对“认识论的审美化”中呈现出来的图像性的看法更偏向哲学,那么相比之下,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中的观点则更偏向社会学。费瑟斯通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赋予了三层含义,即“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以及“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1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8页。第三种含义是费瑟斯通重点加以论述的,而我们所要讨论的图像性也正是这一部分的主题。费瑟斯通援引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的观点,认为影像在现代消费社会占据了核心地位,并且“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美化的社会也就是波德里亚所说的由“拟像”(Simulacrum)造就的“超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图像不是对现实的模仿,不是对实在的遮蔽,而就是现实的实在本身,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也正因此,波德里亚认为在当今社会,我们所生活的每个地方,实际上都已被现实的“审美光晕”所笼罩。这里,“审美光晕”就是指作为拟像的图像给现实带来的那种真假难辨的虚拟性:没有所谓的“实在的现实”,只有“虚拟的现实”或“审美的现实”,“美学的神奇诱惑无处不在,……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12)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第99页。我们看到,费瑟斯通和波德里亚对图像性的看法实际上与韦尔施不谋而合,他们都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中看到了现实的“虚拟性”,强调人的理解对现实的建构功能。费瑟斯通还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借助拉什的现代性理论来追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源头,但与韦尔施不同的是,他是经由“现代性”这条路径来不断向前追溯的,而“现代性”的主题在费瑟斯通看来实际上是“情感的控制与反控制”,正是中产阶级对“有控制的情感宣泄”的要求造就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些早期表现形式。这一问题虽然与图像性问题有关联,但并非本文讨论的核心,因此就不一一介绍其中的细节了。
韦尔施和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不仅都关注图像问题,而且对图像问题的探讨都没有止步于单纯现实图像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了“图像性”的问题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虽然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但对图像性更进一步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依然有所欠缺,因此在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内部的图像批判提供哲学层面的支撑时显得单薄。而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学说,将会在这些问题上获得新的启发。
二、海德格尔论作为“表象—图像”的“世界图像”
如果要给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找出几个关键词,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计算”“表象”“主体”和“摆置”(stellen)。将这几个关键词连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篇文章的主旨:进行计算的主体表象(既作为名词,也作为动词)着存在者,因而摆置了存在者。“世界图像”中的“图像”一词,指的正是这种“主体之表象”。实际上,“世界图像”(Weltbild)这个词在日常德语中一般可翻译为“世界观”,这个词本身就有人对世界的理解、看法的意思,因而与“表象”的含义也比较接近(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表象”)。所以如果仅就“表象”这层含义而言,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图像”其实并非海德格尔的专利,而是几乎形成共识的观点。海德格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表象”理论产生的根源追溯到近代自笛卡尔以来的形而上学所树立的“主体”观念那里,将“世界成为图像”作为“人成为主体”的一个结果来看待,并且突出了“世界图像”中的“摆置”因素,从而为之后的图像批判指明了方向。
海德格尔从对现代科学的考察入手来讨论“世界图像”。他认为现代科学是一种基于数学的、要求精确计算的研究(forschung)活动,既不同于中世纪的“学说”(doctrina),也和古希腊的“知识”大相径庭,因而是一种只属于现代的现象。这种研究活动具有两个本质性的特征。其一是程式化,即人对存在者的筹划要求一种数学意义上的严格性和精确性;其二是对象/表象化,即将存在者表象为人的某种“对象”,从而使存在者成为“属人的”存在者。科学的研究活动之所以具有这样两个特征,是为了使存在者作为可控制的实验物,进入人所追求的“规律”“法则”中,以便最终实现科学对存在者的完全可靠的支配目的,这同时也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存在者的某种支配。
然而人何以会、甚至是必然会走上这样一条对存在者的控制和支配的道路呢?海德格尔认为:“当且仅当真理已然转变为表象的确定性(Gewißheit)之际,我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最早是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了。”(13)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5页。人对存在者的对象化以及进一步的“控制欲”,在海德格尔看来其实已经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奠基了。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近代以来,为了从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中解放自己,人将自己树立为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主体”,这是一个对人的本质所作的根本性改变。因为这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14)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96页。这也就是说,人成了一切存在者的关系中心,成了存在者存在或不存在的裁决者。这是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的重大改变:现在,人既不在古希腊的“觉知”的意义上与存在者照面,也不在中世纪的“受造物”的意义上理解存在者,而是作为“主体”对存在者进行表象,从而将整个世界图像化。对物(包括自然和历史)要求绝对的客观性,同时又不断强调人的主观性(无论强调“理性”还是强调“非理性”,其本质都是强调“人”,即“主体”),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15)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102页。海德格尔指出,这种同时要求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做法虽然“初看起来”十分荒谬,实际上二者对于“世界图像的时代”来说不仅没有互相矛盾,而且互为补充:只有在把人(主体)不断变得强硬的同时让物不断地变得“柔软”(只有绝对客观的物才是对人来说易于计算和控制的,也才是“柔软的”),“世界图像”才真正成为现代的一种本质现象。
“人成为主体”和“世界成为图像”是世界图像化的两个方面,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一进程中,“主体”的诞生及其“表象”(作为动词)活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两个核心事件。但仅仅有这两个事件还不足以作成一幅“世界图像”(更进一步说,还不足以构成海德格尔对“世界图像”进行批判的理由)。在海德格尔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主体在表象的过程中对存在者的“摆置”,即将存在者看作是主体的可计算、筹划和支配的对象。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世界图像”中的“世界”是指包括宇宙、自然、历史以及“世界根据”在内的“存在者整体”,这也就是主体的表象活动所涉及的诸存在者领域;而“图像”则是指“从自身而来把某物摆置到面前来,并把被摆置者确证为某个被摆置者”。(16)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119页。
“世界图像”所具有的这一“摆置”特性具体是如何窒息了存在者的存在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有海德格尔对“世界图像”的批判一说)?海德格尔轻车熟路地将目光转向了古希腊,通过分析古希腊人对存在的理解来获得这一问题的答案。而如果要讨论古希腊思想中的存在问题,巴门尼德显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因为他给出了古希腊思想中关于存在问题最早的表达,即现在学界一般翻译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那句话。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翻译实际上并非巴门尼德原意,而是一种现代主体性思维指导下的“词语转渡”,因此他将这句话译为“觉知(Vernehmen)与存在是同一者”。(17)马丁·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页。其含义是:“由于为存在所要求和规定,存在者之觉知归属于存在。”(18)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99页。古希腊人的“觉知”与我们所说的“思想”之所以是不同的,其关键在于我们人作为一种存在者是否失去了与存在的原始关联。海德格尔认为,由于觉知者的古希腊人作为在场的存在者聚集着其他自行开启的存在者,同时又与存在保持着关联,因而始终遭受着一种自身的“分裂”,即“人归属于存在,却又在存在者中保持为一个异乡人”。(19)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105页。与之相对的,进行“思想”的现代人将一切存在者都摆置为主体的对象,包括人自身在内的存在者成为了纯粹的在场者,而失去了与存在相关联的这一维度。(20)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笛卡尔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rgo sum)实是“我表象故我在”,因为笛卡尔所说的“思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思维”,而是包括我们与物的任何一种关系(如意欲、采取立场、感知等等)在内的人的表象活动。如果说古希腊人的存在方式是基于存在之“自身性”(Selbstheit)的,那么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则是主体的“自我性”(Ichheit)占据了主导地位。主体之表象活动对存在者进行“摆置”的后果正在于切断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者与存在自身的原始关联。这就是海德格尔通过回溯到古希腊的存在理解,对现代以来的世界图像进行批判的关键所在。
三、“世界图像”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图像批判
从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理论转回到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图像性问题的关注,我们会发现“世界图像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一种不谋而合的对应关系:“世界”对应着“日常生活”,表示这一现象不是某一地域或领域,也不是某一阶层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关涉整个世界的、深入到人们最广阔的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审美化”对应“图像”,表示世界/日常生活经由审美化/图像化而呈现出虚拟性和建构性。这种对现象进行描述的内在一致性体现出的是学者们对这一现象之本质认识的一致性。但正如托马斯·米歇尔(W.J.T. Mitchell)所指出的:“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现在已经进入视频、控制论技术与电子复制的时代,这个时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发展出了视觉拟真(simulation)和幻觉艺术(illusionism)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对图像的恐惧,那种对‘图像的力量’甚至可能最终毁掉其创造者和操作者的忧虑,又与图像制作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21)W. J. T. Mitchell,Picture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15.这里“图像的力量”指的就是隐藏在图像背后看不见的“控制性”,这种内含在图像性中的控制性既是海德格尔讨论“世界图像”的目的所在,也是学者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进行图像批判的主要理由。实际上,表象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经潜藏着这样一种被用来进行控制的危险了:被表象(作为动词)的东西本身总是与表象(作为名词)显现出来的样子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源在于表象活动始终只是一种“再现”或“代表”,是通过在场的某些符号来指示不在场的存在者自身,而这就意味着它始终不可能是存在者自身(否则就不成其为表象了)。正是存在者自身与其表象之间的差异给出了可操作的空间,使得进行表象的人可以通过对表象方式的选择来实现能指与所指的错位。表象可以不与被表象的东西本身相对应而同时声称自己具有这种对应关系。这一看法与当代符号学家的研究是一致的,即“能指链(Chains of signifiers)总是指向其他能指链,而不是指向某种原初的所指”。(22)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38页。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来说,被大量生产的“图像”的问题就在于:事物存在的丰富性按照进行计算和控制的实际需要(这种需要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图像化”的一个结果)被敉平为某些“特征”“属性”(这些特征往往被要求最好能是“美的”),通过对特征的计算和安排,不仅是物,而且还包括使用这些物的人都一并进入了预先设定好的“游戏规则”中。在这个规则中,被控制甚至被扼杀的绝不仅仅是我们的审美敏感力,(23)彭锋:《重回在场:哲学、美学与艺术理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288页。更重要的还有我们自身存在的丰富性。
除了这种由于人类将自己主体化从而将世界图像化而产生的控制性(“人控制了物”),在更直接的意义上,图像的控制性还可以指表面光鲜亮丽的图像背后的控制意图,即通过图像来达到某些特定的目的(“物控制了人”)。这种意义上的控制性尤其体现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中,因为以“美”的面目呈现出来的图像往往更加有控制性,而且这种控制性也在“美”的庇护下更加隐蔽。但这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中大量出现的“物控制人”意义上的控制性从属于“世界图像”中“人控制物”意义上的控制性,前者基于后者才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对海德格尔从“世界图像”中引申出来的关于“作为体验的艺术”的看法来说明这一点。
海德格尔说:“现代的第三个同样根本性的现象在于这样一个过程:艺术进入美学的视界之内了。这就是说,艺术成了体验(Erleben)的对象,而且,艺术因此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24)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83页。现代社会中的艺术不同于海德格尔所推崇的那种作为真理之发生方式的艺术,因为现代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通过艺术把物“体验”为自己的某种感觉(即一种对物的表象),通过这种艺术的“感觉”,物变成了“属于人的物”,变成了一种可以被人计算的东西。这种艺术实际上成了主体对客体进行控制的中介,而非存在的真理。人与物的关系现在成了一种干瘪的、线性的函数关系,只是在这样一种现成的(vorhanden)关系中,物才可能被利用而反过来控制人,其中就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中出现的那种通过“美”的图像来激起人的欲望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的控制。当今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中作为“设计”的艺术就是这样,“设计师们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验、计算机数据处理获得美的标准,然后再按照美的标准进行设计,最终生产出完全符合美的标准的产品。”(25)彭锋:《重回在场:哲学、美学与艺术理论》,第297页。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那些“美”,大多都是由这些经过精确计算和设计、带有某种控制意图(吸引注意力、激起购买欲等)的“图像”所组成的。
不过,虽然我们从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理论出发,就“控制”的问题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中的图像性有诸多批评,但这并不等于说从形而上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就只能如此这般对图像性持否定态度。这些批评应该被看作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论逻辑而来的一种推论,而非本文最终想要给出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展示一种从形而上学角度切入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图像研究的方式,而非给出一个定性的评价。韦尔施提醒我们:“走进这一新的紧迫的审美话题,其最便当的行为方式便是否定现象。……摆脱当务之急的种种问题,你发现自己是身处在传统问题的安全港湾里。这类逃避主义对于焦虑的灵魂来说,恐怕是势在必然的。但是它对于美学的哲学理解,却没有什么好处。”(26)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13页。在面对一种新的现实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否定还是肯定,最重要的都是对现实本身的关注和研究,而非对结论的斤斤计较。实际上,对图像性中可能包括的控制性进行批判固然不错,但也有不少研究者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那种虚拟性、建构性意义上的图像性保持乐观。例如前面提到的韦尔施虽然认为我们的世界有被过度审美化和图像化的嫌疑,但他同时也希望我们能从传统哲学对美学的狭隘定位中走出来,将审美真正看作是一种既存的现实本身,而非仅仅是某种对现实的补充。因为“传统的现实知识追根究底,力求客观,但事实是哲学认知中,审美的范畴诸如外观、可操纵性、歧义性、无根基性抑或悬念性,其实都是现实的基本范畴”。(27)陆扬、张岩冰:《译者前言》,见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5页。这意味着承认和接受那些不为传统哲学所正视而只在“审美的梦幻”中才被允许的东西。如果我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那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将是一种激动人心而非令人担忧的现象。(28)海德格尔反对在表象的意义上对世界进行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人去理解世界,恰恰相反,人理解世界这件事是此在(人)的“不得不”,它属于此在的实际性(Faktizität)。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的全部目标就是要阐明人究竟是怎样理解世界的。他反对那种从笛卡尔式的主体出发的、理论化的、表象式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传统哲学从柏拉图直到胡塞尔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世界的),而主张人只能在一种非意向性的、无法明确加以说明的实践背景中才能理解世界和自己(即“在世界之中存在”),也只有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世界”才可能通达存在。应该说,韦尔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图像性持一种乐观态度的,这一点在《重构美学》中就能找到不少证明。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需要留待之后再作深入的探讨了。
四、结 语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发生在当代但决不仅仅属于当代的现象。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早在笛卡尔将人作为主体从而使世界成为图像的时候,日常生活审美化就已经奠基并因而成为某种必然发生的现象了。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图像性问题的种种争论,无论是持赞同的态度欢迎它,还是持批判的态度抵制它,都不应该把目光仅仅局限在当代,而更应该从整体上通过对其形而上学基础的认识,从更加基础的问题中导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和看法。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虽然不能等同于“世界图像”的问题,但也并非与“世界图像”毫无瓜葛,二者在深层次上都与“人如何理解世界”这个基础的形而上学问题紧密相关。从形而上学层面对“图像性”的不同理解,会导致人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持肯定或否定的不同态度,而从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理论逻辑出发所生发出的批判并不天然地否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合理性。而如何更加合理地认识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中的那种“图像性”,这正是本文所尝试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