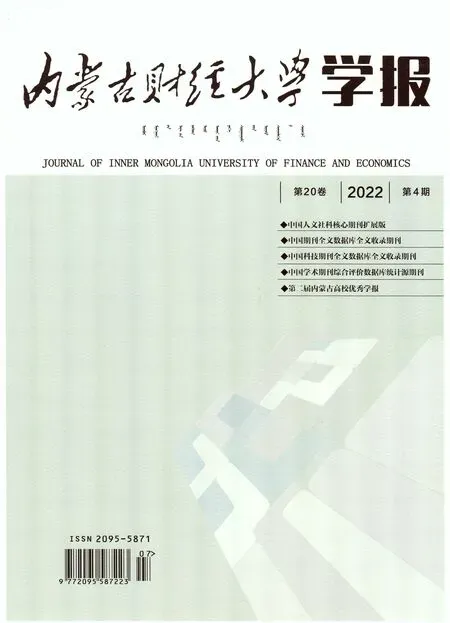试论川端康成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
连悦廷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是一位才华横溢、颇具魅力且极具独特气质的东方作家。作为日本文学界“泰斗级”人物,他创作了多部为后人仰止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其创作风格及写法技巧也影响到中国的莫言、余华等一批当代作家。而被赋予中国文坛“鬼才”之称的作家贾平凹同样在多种文学场合,都明确地表达出对川端康成的喜爱和推崇。在包括川端康成在内的众多域外作家影响下,贾平凹的创作理念、审美姿态和书写方式等都有了明显变化。
一、 根植民族文学的创作理念
在中国民族文学的土地上,贾平凹作为一棵能持续保持鲜活生命的“大树”,始终饱含着他自觉清醒的创作认识和独立敏锐的文学实践。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青年时期的贾平凹就已被灵敏的文学神经感官驱使着走向复杂且开阔的创作领域。一种朦胧的民族意识在早期的中短篇作品就已若隐若现,但是民族文化心理与文本构创时的相撞排斥提醒着他视野应当横扫六合,应当登高望远。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贾平凹从日本川端康成的创作中受到启发:“川端康成作为一个东方作家,他能将西方现代派东西和日本民族传统的东西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境界,这一点太使我激动了。读了他的作品,始终是日本的味,但作品内在的东西又强烈体现着现代意识,可以说,他的作品给我启发,才使我在一度大量读现代派哲学、文学、美学方面的书,而仿制那种东西时才有意识的转向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学习。”[1]“没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是站不起来的文学,没有相通于世界的思想意识的文学同样是站不起来的文学。用民族传统的美表现现代人的意识、心境、认识世界的见解,所以,川端成功了。”[2]如果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无法相融,那诞生出来的必然是无根无魂的作品。这种“日本的味”正是川端康成以民族文学为创作基础的体现,他自觉地做一个日本作家,主动继承日本美的传统,从而开辟了伟大的文学事业。川端康成的作品处处体现了“物哀”精神,这是一种来自于日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性审美情结,日式之哀美使文本弥漫着一如那“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忧怅。
受到川端康成启发的贾平凹,更具体地将目光注视在商州土地上,故土作为中国生活变革和意识形态的一处缩影,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意识像一只赶不走的“幽灵”萦绕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构成领域。商州这块由秦汉古老文化滋养而来的“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地方”,促使贾平凹成为一名不断求新求变、敢于突破既成小说模式、特色且高产的作家。无论是早期紧跟农村改革潮的《腊月?正月》,还是书写现代文明仄逼乡土的《秦腔》等,皆是把握住瑰丽厚重的古老历史以及挖掘到地域文化的内在底蕴,以此表现出清新纯朴的商州在生存冲击下经历“巨变”的隐痛,从而凸显出某种民族意义上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现实矛盾。这便呼应了贾平凹曾提出的一个主要原则:“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3]可以说,这种中国之美的表现观念,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川端康成的文本创作中采取了日式审美思维的影响。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评价:“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4]作为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川端康成通过视、听、触、嗅等感觉的细致刻画,将笔墨倾注于人物内心,把人物接触外部世界所引发的情感悸动进行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化表现。
川端康成主要是通过展示特色文化元素来传达出植根民族文学的创作理念,如《雪国》中艺妓和《千只鹤》的茶道等。这种带有日本文化独特印记的“符号”,承载着可以超越国度而被认知的日本传统民族精神,其中《古都》尤为代表。“古都”指名城京都,历来被日本人视作精神故乡与文化象征之地。川端康成在《古都》中以京都的四季变换、自然民俗和名胜古迹作为基底,选取了日本传统的古朴建筑如清水寺、鞍马寺、青莲院等,灵活地将春日八重樱、夏日红霞、秋日胡枝子花、冬日北杉林,这些四季代表性自然美与人物心灵美相融,赋予了京都风物新美学内涵。同时,赏樱、拜社、游园、品茶等节日庆典与祭祀活动贯穿全文,将精美考究的日式传统手工的和服腰带织锦与男女青年的爱情命运巧妙交揉。其实,纵观川端康成的作品,里面渗透着物语文学、和歌俳句、插花茶道和寺院庙堂等书写,这些均深刻地彰显出日式的诗情画意及艺术灵光。川端康成曾表示日本文学虽随着西方文学潮流而动,但传统始终是潜藏的河床,他的作品正是扎根于民族大河床之上,才能挖掘出熠熠生辉的独特“宝藏”。贾平凹受此启迪也明确表示:“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5]
在中国土地上,贾平凹说:“我写作品,在境界上借鉴西方的东西,在具体写法上,形式上,我尽量表现出中国人的气派、作派,中国人的味。”[6]所以,贾平凹一方面以瞭望式思维,吸收借鉴域外方法和技巧,用独特的话语体系及审美方式写出了中国之味道,另一方面坚持纵向思维,指向民族文学,完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的接洽。贾平凹在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及古典文学的潜移默化下,通过不断地融合并加以自我见解,使多数作品呈现出富有民族性思考意义的深刻内涵。於可训教授也有相关阐述:“他的作品都十分注重从现实变革中挖掘历史文化的积淀,而且在艺术上也偏重于向中国古代笔记、小品和话本、传奇吸取经验,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和风格神韵。”[7]由长篇小说《废都》可见,贾平凹运用古典世情小说的写法,通过写主人公庄之蝶众叛亲离、女性人物错付深情、龚靖元神经错乱、阮知非双目失明和孟云房沉迷方术等,形象地塑造出一批精神荒凉且价值迷惘的知识分子。书名“废都”二字具有地理与时代的双重意义,西京(西安)曾是十三朝古都,是具有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发祥地,但它昔日的繁花似锦已时过境迁,今朝的浮靡颓败充溢着“黍离麦秀之悲”[8],这岂不是与川端康成笔下的“物哀”之情互通吗?在这座荒败皇城中的知识分子用躯体狂欢来缓解灵肉分割的撕裂感。那么对于一个人抑或是一个民族而言,“无根灵魂”的结局终是毁灭,这实在令人感伤至极。再看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秦腔》,这不但是对现代文明冲击下故乡棣花街的一段追忆与思考,更是一首悼念传统乡土和民族文化的挽歌。秦腔作为民族传统戏曲之一,它的由盛转衰映射着文化凋零与乡村不在的现实悲哀。文中白雪与夏风婚姻的破败也象征着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的隔膜,而“怪胎”牡丹的生理缺陷正折射出传统文化的衰落与无奈。《土门》则把关注点放在了城乡之间,大胆揭示乡村城市化的巨大问题。中国历古千年都是农业大国,农民将土地的依恋刻于灵魂深处。尽管传统农业文明具有惰性和过于保守的负面效应,但是回归家园的寻根意识依旧根深蒂固。仁厚村被拆迁,村民仿佛丧家犬般鸟兽尽散。面对暴力无情的城市文明与落后保守的乡村文明,我们又该何去何从?这是作家对一个民族文明前途的深切担忧。这些均能够说明民族观念在贾平凹的创作中经历生活的洗礼与现实的碰撞,一步步更加成熟且中国化了。
二、 浸润禅宗意蕴的美学气质
与其说贾平凹创作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倒不如进一步说贾平凹是真切地喜欢川端康成。在1985年的《答〈文学家〉编辑部问》中,当被问及“从作品气质上讲,你是一个更多地受到东方美学思想影响的作家,那么,对你产生最大影响的文学家是谁?”时[9],贾平凹不假思索地罗列出包含川端康成的大批作家。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1980年,那时贾平凹就对川端康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他曾在陕西图书馆的一张借书单上写:“只要有川端康成的作品,一本书中有一篇亦借来。”[10]或许是因为川端康成悲惨凄惶之命运使贾平凹产生共鸣,抑或是孤僻敏感之性情将创伤感投射于心,那么大体可以推断出川端康成创作中表现的美学气质,在无形中调适着贾平凹的审美旨趣——这便是禅宗意识。川端康成坦言:“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下成长的”,“那古老的佛法的儿歌和我的心是相通的。”[11]川端康成在1968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发表的演说《我在美丽的日本》中,更是引用了不少禅师的著名诗句,展露出物我合一的禅境和超逸脱然的旷达胸襟,他正是“以卓越的感受性,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12]。
在这里并不是说贾平凹创作中禅宗意识的形成直指川端康成,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因素,断不可简单概之,但可以判断的是川端康成创作时对自然的艺术化审美所产生出文道禅宗的感悟,引发了贾平凹内心深处的触动。川端康成的作品几乎都传递出一种幽玄且物哀之精神,流露出浓郁的虚无死灭的悲怨情绪。从中可以发现川端康成的美学走向是以禅入文,观物态度是用禅感应,借禅宗的思维方式发掘自然禅趣。这种美学气质的形成与他“天涯孤儿”的性格经历及日本佛教文化中“虚空无常” “纤细悲怆”的审美观密不可分,其中《雪国》尤为体现得淋漓尽致。作品中生之徒劳、死之缥缈的情绪贯穿全篇,文本中所有人物都在淡淡的伤感中将虚无思想刻入骨髓。岛村玩世不恭,虽说致力于西洋舞蹈的研究,但仅限于沉溺文字和照片所创的虚幻舞蹈,认为人生万般皆徒劳而对现实若即若离。岛村对待驹子的爱并没有太多真情实感而是主观臆想,所以表现出的官能克制只是不愿破坏自我想象,而对于叶子也仅仅是追求那映在火车玻璃窗中虚幻非现实之美。驹子看似对生活努力不纠结,就如她常对着空山弹奏三弦琴,“要是没有剧场的墙壁,没有听众,也没有都市的尘埃,琴声就会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彻远方积雪的群山。”[13]但她将充沛爱恋与真挚感情寄托于“虚无”的岛村身上,最终逃不过 “美丽徒劳”的命运。至于叶子则是镜中无可形容的绮丽,连死亡都是如梦如幻,刻画她就是塑造一种不可捉摸的空虚意境。由此可见,川端康成是对于禅宗的“虚无”进行了内在顿悟与消化,形成了典型的日式东方审美。这种禅意与文心相融的美学表达,自然也给予了坚持探寻世事沉浮与人生体验的贾平凹一定程度上的启迪。
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就尤为展现静默的自然禅思,创作出一批质朴灵动、真切自然、有限中意蕴无限的作品。90年代以来,贾平凹则主要是通过禅宗解悟,安妥现世灵魂,建构人生境界。如果说,因贾平凹自幼内向孤僻且饱尝世间冷暖,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他对世界与人生的思考中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那贾平凹主动地进行古今中外的广泛涉猎与阅读研习,则是由于他内心始终被一种强烈的不断超越的“上升力”驱使着前行。正如在《夜在观云台》写道:“水蓄在这里,为的是流下山去,水都恋着山下的田地庄稼,何况人呢,你要寻什么,又要摆脱什么呢?”在贾平凹笔下世人所要的一切答案皆可找寻,这是他秉持的虚静观照态度来实现自我生命体验及生存感悟的书写,即是对文道禅宗的一种解说。贾平凹将禅意渗入文本,在文学世界中建立的“静虚村”,是“不以所已藏害将所受谓之虚” “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14]。贾平凹创作思想中的“静虚”不是悲观避世,而是致力达到一种高层次成熟的思想境界,也只有虚怀若谷和广采博纳,才可获世事全方位把握。
贾平凹入禅宗,不是要皈依宗教,而是通过吸收佛理哲学中养料来完成自我审美追求和艺术修养。他之所以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是因为无论中国或日本在禅宗的认知上多为相通。而当贾平凹驻立于商州土地时,他便用淡泊虚远及宁静超脱的观物方式,将人物置于原生自然,进行了多部感知天地合一的作品。如《浮躁》《太白山记》《烟》等,在《浮躁》中,贾平凹对抗浮躁情绪的内核是“静虚”与“修心”。《物不迁论》中说:“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不离动。”[15]正是禅宗要求人们以静制动和以虚心养性,要从变幻的外部去感悟动中所藏的虚静真谛。《太白山记》里《寡妇》写死去的父亲在幼年的儿子眼里夜夜来与寡居的母亲行房,还有声有色,可母亲醒来后一点也不晓,显示出佛家的灵魂不灭说。《挖参人》写吝啬多疑的挖参人在外出挖参时,往家中院门框中安了一面照贼镜。妻子每日在镜子中看见丈夫与小偷搏斗,三日后得到消息丈夫卖了参怀揣一沓钞票死在城中的旅馆床上。荒诞不经的故事隐含着生活中顾此失彼的失衡心态,折射出社会环境下人们无处安放的躁动情绪。其中“防贼镜”正是运用了佛家对于镜子赋予的内涵——以镜喻心。据《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二之三曰:“坐禅之处,多悬明镜,以助心行。”[16]在僧人坐禅的禅堂中,通常悬有明镜,旨在借助镜子明亮能照物现像或光影投射的功能,帮助修学者提高心行。《烟》主要写人进行三世轮回的故事。石祥经由梦境与现实度过三世,前世是山大王,现世当边防战士,最后到来世死囚。“三世轮回”就是运用佛家禅理去探寻生命奥秘,而虚无缥缈的“烟”也是寓意无形无体、无生无灭、无时无空的佛家智慧。这是禅文化对自然和人生的解悟,也是对世事莫测的虚无观照。
三、 把握时代脉搏的现代书写
文学的建构总是与“人”息息相关的,而人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体”总是和一定的时代环境中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也使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运动形成不同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那么,对于一个作家,要做的不是成为把握政治经济走向的专家,而是能够敏锐捕捉到流溢于社会生活中的时代情绪,以此把握丰富的历史内容下具体的时代心态。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的创作处在一个不断反省和调整时期,他从最开始田园牧歌式的轻盈书写,到世态炎凉的痛苦思索,直至洞察人性的剖析批判,这一步步都是他建立自我精神平衡的过程。贾平凹开始是模糊非自觉的现代意识,随着感受力和理性思辨力的不断强大,其现代书写已经被打磨成熟且深刻,曾经的“痕迹感”也化为自然的“血肉”。而在这个过程中,贾平凹一方面深入社会生活,完成了与改革农民紧密相连且情感互通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三部中篇,另一方面从拉美文学和日本川端康成的创作中受到极大启发,他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事业不应该是封闭自足的土特产,也不是脱离中国的洋品种,而应该是具有时代光环的精神产物。那么,放眼二战后经历精神创伤的川端康成,“日本的战败也略略地加深了我的凄凉。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死去了,自己的骨头被日本故乡的秋雨浸湿,被日本故乡的落叶淹没,我感受到了古人悲哀的叹息。”[17]这是遭受到巨大的价值观冲击,战败的屈辱和心灵的崩溃如剥皮抽筋般折磨着所有人,时代灾难加重了经历生死浩劫及重大磨难后人们的生存焦虑,使民众对生存意义产生了怀疑与否定的情绪。川端康成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着眼于时代脉搏及文化心理,直指现代心理模态,认为战后的国土更需要民众去继承日本之美,从而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
川端康成发表一系列作品,如《千只鹤》《湖》《睡美人》等,均展现出他在这个悲哀时代——“幸运是短暂的,而孤单却是永久的”[18]之主题,川端康成多选用哀而不伤的语调去表述“死亡问题”。其中代表作《千只鹤》主要讲述一段涉及两代人的畸恋故事,用三谷菊治父子与几位女性的情感纠葛来表现爱与道德的冲突。川端康成曾坦言:“我的小说《千只鹤》,如果人们以为是描写茶道的‘心灵’与‘形式’的美,毋宁说这部作品是对当今社会低级趣味的茶道发出的怀疑和警惕,并予以否定。”[19]的确,战后不论茶道或花道等日本传统文化,皆在外国文明冲击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遗落,这给热爱日式传统文化的川端康成造成了浓郁的感伤和仿佛青春被毁而消逝的颓丧。《千只鹤》被诺贝尔文学委员会认为是人类文学中当之无愧的杰作,是“散发着腐败果实一般的芬芳气息”。那么何为丑恶,何为美丽?在丑恶的土壤里,能否结出美丽的果实?文中“反道德、反理性”的人物刻画,是川端康成透过“丑陋的罪行”,在表达生死寂灭的深层悲哀的同时达到一种生命的极致体验。就如一位日本评论家所指:“在三谷菊治和太田夫人身上看到的父子两代人侵犯了性的禁忌的人间像,令人厌恶。川端通过这些想要描写的是性、死、爱等与人类的存在紧密相连的最根本的问题。”[20]川端康成在战败后进行浓烈且极具现代意识色彩的思考——如何在破灭中自救、如何去诠释存在的意义、如何在哀愁中探寻再生的可能,都是川端康成在时代“焦灼”中不断索求答案的过程。此等触动,同时让生长在中国土壤里的贾平凹不禁发出疑问:“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面对着这个世界所发出的心声,要受到阶级、民族、政治、社会制度、地理、习惯的制约,而我们中国人的心声又是什么呢?”[21]
这就是作为具有锐细感知力的作家贾平凹,在面临时代巨变和看到交错叠压的社会图像时,所发出的关于对人类生存状态及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刻沉思。他认为:“一个作家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他的身世所致,另一方面是所处的社会的心理状态所致。川端正如此,换句话说,作家要重视发现自己的气质、同时要研究社会,准确地抓住社会情绪、社会心理。”[22]诚如川端康成处在日本战败后的凄惶命运,贾平凹的父亲在的一场文化浩劫中所受牵连被开除公职,致使家道中落尝尽世态炎凉之辛酸。同样是一场“灾难”带给时代不可小觑的冲击力,使80年代社会在开始剧烈的转型与变化。与此同时,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贾平凹的思维视角开始更深入时代与人类命运共呼吸的博大境界,在创作上不断地展开人类共通问题的追问以及社会认同危机的感喟。此时,贾平凹作为一名具有时代自觉和现代意识的作家,不得不提及一部作品《浮躁》,这是一部试图从宏观上全方位把握时代律动,从整体上对时代情绪进行准确概括的重要作品。描绘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艰难变革,精准地展示了人们在面对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碰撞时深层心理的微妙变化。通过生活的种种丑恶现象,将肆意弥漫的“浮躁”心态曝之于众。它敏锐地揭露了包括金狗在内的国民性弱点和经历时代脱变时的痛苦,比前期《小月前本》中的才才与门门等人物刻画更加饱满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就容纳了丰厚的时代内容。紧接着,贾平凹自《浮躁》以来的小说就“从现实生活中抓住当时的时代社会心态问题”[23],真实地记录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原生态样貌,并准确地再现了生活心态和现代精神,同时也艺术地展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进入90年代后,贾平凹在一次次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过程中,将文本的时代性与超越性进行交融,完成了《废都》《白夜》《土门》等具有现代性反思意义的佳作。《废都》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精神异化,深刻揭示当代人在都市消费中的灵魂落魄和无家可归的生存窘境,表明了一个作家理想被现实冲击后的空虚无力与声色犬马中的自我放逐,从而剥丝抽茧地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价值批判。文人越想放弃背负的一切,去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就越被盛名所累并在灭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时,由于良莠不齐的竞争所带来的双面影响,是时代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说,在旧有观念颠覆与新兴观念冲击下的社会,俨然是一群灵魂无依的“魑魅魍魉”所构的一幅“百鬼夜行图”。《白夜》则是贾平凹再次注目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吞噬以致时代转型中国人灵魂的痛楚与蜕变。就像文中梦游患者般的夜郎,终其一生都在找寻安置灵魂的栖息地,从而通过找寻失败去表达深沉的忧世情怀及对世道的愤恨与否定。到了《土门》也可看出贾平凹对于现代性反思叙述进行了某种深化,他是同时展开对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的双向批判,从而写出难以阻挡的社会经济化及农村城市化的必然趋势。由此可见,由于时代潮流裹挟下的精神异化与道德败落,已经成为当时民众的一种灵魂状态。贾平凹曾坦言:“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24]由此可见,“为时代而歌”是对一个作家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学的核心灵魂,创作者应该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前提下,用现代化眼光审视生存空间,在实现主体能动和尊重客体世界的同时,发展更高层次的文学艺术追求,从而完成更符合现实生活和人性本质的创作。
概言之,文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川端康成能够对贾平凹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与启发,不单单是由于作家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文学感知力,更是因为拥有跨越国界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创作洞察力。与此同时,转益多师的贾平凹不仅能够在学习借鉴后进行个性化吸收与调适,而且能够巧妙地结合自身艺术禀赋,进行独立自觉的文学实践,最终自成一家。无论从创作理念、美学气质和书写意识等角度去探讨川端康成和贾平凹创作的内在联系,都有助于我们以世界性眼光去审视文学大舞台,从而也有利于更加准确且全面地把握贾平凹文学世界的丰富与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