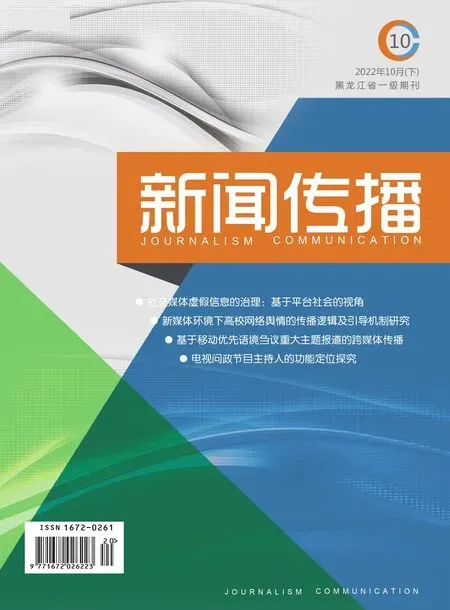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治理:基于平台社会的视角
陈小燕 任书丽
(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 江苏 215009)
桑斯坦曾说“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是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但都会是受害者”。他的前半句指出互联网的兴起让谣言变得俯拾皆是,后半句则指出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深受谣言的毒害。现代社会以微信、抖音、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人们日常信息交流的重要阵地。社交媒体平台的任何用户都可以传播真实或非真实的信息,这种传播方式使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但是也为虚假信息的繁殖提供了土壤,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2022年3月22日晚,有关“上海将封城7天”“全封4天”等不实言论在微信群大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去年11月,一位名为“飞哥在东莞”的网友盗用申女士和其外公拍的写真造谣二人为“老夫娶少妻”。2020年7月7日,杭州一便利店老板造谣少妇出轨快递小哥。以上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信息发布者都是社交平台的个人用户,信息内容生成简单,真真假假,且图文并茂、夺人眼球,但实质是主观臆造的产物,属于虚假信息的范畴。在社交媒体平台欣欣向荣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看图编故事”的造谣污蔑屡屡发生?社交媒体平台相较于过去传统媒介是否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本文将基于平台社会的视角讨论社交媒体平台虚假信息飞速传播的原因和治理措施。
一、对社交媒体平台虚假信息治理的现实必要性
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不仅降低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影响社会安定,危害社会秩序。数字媒介时代,媒体的信息来源趋向多元。信源多样化虽然有益于提高新闻生产的效率,但是也提高了新闻虚假的风险性,迫使媒体间接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帮凶。虚假信息的文本内容夸张、故事性强,公众极易受其误导。在“上海封城7天”的谣言中,造谣者将国务院督查组当天抵达上海的新闻进行拼接,主管臆断地推测出上海拟出台大动作大搞封城,这是利用官方新闻为谣言的可信度做背书,尤其是在官方通告发布之前抢先发布,极具蛊惑性,迷惑了不少市民,甚至引发了生活物资抢购的恐慌。在“老夫少妻”造谣事件中,“88万礼金888万二房公寓”等夸张的语言引起网友对照片中女性的讨论。对女性彩礼标准的议论也随之而来,女性拜金的言论甚嚣尘上,更有甚者将此事件上升至性别对立,危害社会公序良俗。媒介形成的网络裹挟着大众,人们对于媒介的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在媒介化社会,虚假信息的野蛮生长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社交媒体平台虚假信息飞速传播的原因
(一)技术可供性为虚假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
可供性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吉布森提出,用以描述动物与环境的关系。与传统媒介时代相比,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生产者不再全是专业的从业人员,自媒体的崛起就是媒介技术可供性发展的结果。学者潘忠党将吉布森的可供性概念改造成一套指标,用于界定新旧媒体,涵盖移动可供性、信息生产可供性和社交可供性三个维度。将以上三个维度应用于社交媒体平台虚假信息的原因分析中可以发现:移动可供性意味着手机等移动设备为虚假信息的生产提供便利,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依靠报纸、电视等媒介传播信息,社交媒体时代仅需一部手机便可实现信息的传播,信息产传门槛大大降低,这是虚假信息飞速传播的首要原因。信息生产可供性意味着专业的准入制度遭遇冲击,虚假信息生产者激增的同时,其素质更难保障,社交媒体平台信息失真的风险性更高。社交可供性意味着媒介技术赋予平台的社交功能使得虚假信息传播范围更广。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性更强,主要体现为无处不在的用户评论。一方面,用户阅读虚假信息后经过评论将其传播给他人,扩大了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另一方面,用户的评论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延长了虚假信息存活的时间。技术可供性使虚假信息的生产者激增,拓展了虚假信息的传播渠道,奠定了虚假信息飞速传播的技术基础。
(二)社交平台的双重属性为虚假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提供驱动力
社交媒体平台表面上是受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地,究其根本它只是平台公司用以盈利的商品。为了盈利,平台运营商不择手段地增加平台的流量,听任虚假信息的泛滥。因而,社交媒体平台自身的双重属性就会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内在驱动。荷兰学者范·戴克在其所著的《平台社会:连接世界中的公共价值》一书中提出了“平台社会”的概念,“用以强调在线平台和社会结构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此意义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范·戴克倡导的“平台社会”意在强调商业平台与社会公共价值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社交平台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交平台本质上是商品,商品不能赚取利润就会被淘汰,而依赖商品生存的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除此之外,社交平台标榜言论自由、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其背后的资本却为了引流纵容虚假信息的传播。
社交媒体平台的三大机制助推虚假信息的蔓延。平台运行的三大机制即数据化机制、商品化机制、选择机制。社交媒体平台结合数据化机制和选择机制为用户推送个性化内容导致虚假信息的精准投放。平台运营商根据用户的点击识别出用户的兴趣,为用户挑选、过滤,提供给用户“你可能喜欢”的信息,但是平台的选择机制无法识别披着真实外衣的虚假信息,以致虚假信息被精确地推送给用户,这类虚假信息主要表现为虚假广告。另外,用户和数据是社交媒体平台经济价值的体现,用户的数量和点击量是衡量社交媒体平台流量的重要指标,流量高者在经济活动领域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因此,为吸引更多的用户,谋取更多的利润,社交媒体平台倾向于放任虚假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平台备受关注的“标题文章”就是社交媒体平台无视和放纵虚假信息产传的实证。
社交媒体平台的审核机制和自我规制放纵了虚假信息传播。社交平台的算法机制通过分析用户兴趣、偏好等数据为用户推荐个性内容,但是算法技术只能识别既有代码规定不能传播的内容。一旦虚假信息的文本和形式发生变化,算法机制无法识别,就会导致虚假信息的传播。社交媒体平台自我规制的缺位也是造成虚假信息广泛流传的原因。规制即监督与管理,自我规制即社交媒体平台的自我监管。随着清朗运动等网络治理专项行动的开展,国家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管控愈发严格,社交媒体平台的审核压力不断加重。为了摆脱审核的负担,社交媒体平台倾向于将审核任务委托给第三方审核机构。这样的做法存在一定风险,一旦第三方机构懈怠,就会导致虚假信息的传播。
(三)行动者网络形成的媒介生态为虚假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提供适宜的环境
行动者网络理论包括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两大要素,在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构成的异质网络中虚假信息呈现出“繁荣”的态势。拉图尔认为非人行动者具有同人一样的行动能力和地位,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共同形成了异质网络。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意见领袖就是实践活动中的行动者。微博大V作为有粉丝基础和内容生产能力的用户在信息传播中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是大V用户可以是真实信息的传播者,也可能成为传播虚假信息的共犯。在利益驱动下,有的微博大V利用煽动性的虚假信息吸引粉丝获取高额广告收入,沦为“伪意见领袖”,成为虚假信息的助推者。快速进步的媒介技术则是非人行动者。传统媒体报道所用的图片由摄影师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而成,而在社交媒体时代,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使手机成为主要的拍摄工具,行动者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报道所用的图片。那么,社交媒体平台看图编故事的谣言是行动者造成的?还是非人行动者导致的?拉图尔“人与枪”的命题认为“杀人”这一行为既不是人主观意图的结果,也不是枪的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两者结成的行动者网络的产物。社交媒体平台虚假信息的广泛流传既不是意见领袖持续生产的结果,也不是媒体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是用户与媒介技术共同形成的媒介生态的产物。
三、社交媒体平台虚假信息治理的三种模式
(一)技术治理模式
区块链技术是虚假信息治理的重要手段。有学者认为用区块链的“技术把关”取代传统的“价值把关”,可以避免人工把关存在的信任、权威、情感的负面影响,使把关机制更为客观、更具理性,进而减少社交平台虚假信息的传播。区块链技术有别于算法技术,其准确性、客观性强于算法技术。研究证明基于区块链技术增加审核者的数量,建立激励机制和审核者审查机制以保证审核者的素质,可以有效地提高把关的严谨性,降低虚假信息传播的风险。由此可见,区块链技术在虚假信息治理领域的应用研究集中于信息审核和把关层面,但是区块链技术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透明性、不可更改性、可追溯的特点。去中心化和透明性意味着链接中的每一节点都能储存信息,都是平等的,都有监督信息生产的义务和权利。如一方想要修改信息必须先经过其他各方的同意,因而信息更改的程序更为繁复、难度更高,可以断绝链接中某一方散播虚假信息的可能性,预防虚假信息的生成。区块链的可追溯性和不可更改性则有利于平台或政府追溯虚假信息的源头,进行事后问责,提高虚假信息治理的效率。
(二)法律治理模式
仅通过技术治理净化社交平台的虚假信息是不现实的,基于法律的治理是社交平台虚假信息治理的一项可持续的和长期性的举措。我国治理虚假信息的法律措施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原有的法律制度不再适用于社交媒体平台虚假信息的治理。2015年,修订的《刑法修正案(九)》将传播网络虚假信息定义为犯罪行为,此举加大了虚假信息传播行为的惩罚力度。2019年,国家网信办出台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虚假信息治理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综合以上法律法规,我国虚假信息治理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强调平台在虚假信息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二是强调政府在虚假信息治理中的管控作用;三是强调公众在虚假信息治理中应尽中的义务。除国家出台的法律法规之外,天津市和浙江省也分别发布了关于地方网络信息治理的文件。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善的虚假信息治理的法律体系。法律法规的颁布使得虚假信息的治理有法可循、有法可依。
(三)自治模式
自治模式是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进行虚假信息治理的模式。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受众从机械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集信息生产、发布和接收于一体的人,因而受众在虚假信息治理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从受众本身的角度看,谣言止于智者,在全民皆媒的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虚假信息治理要求受众提高辨别能力,对信息形成独立判断,截断虚假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再者,从教育者的角度看,虚假信息治理需要教育部门加强网络道德的宣传,需要学校开展提升媒体素养的课程,需要家长言传身教,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另外,虚假信息的治理还需要平台和政府部门联合加强对意见领袖的管理和培训,让意见领袖成为虚假信息治理的促进者而不是阻碍者。这要求政府加大意见领袖虚假宣传的惩处力度,建立激励机制和退出机制,对传递真实消息、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意见领袖给予鼓励,对屡教不改和影响严重者直接作封号处理。奖惩分明、严宽相济才能更加有效地管理意见领袖的队伍。
(四)三种治理模式的比较
1.治理主体比较
技术治理的主体是平台,平台可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完善的审核制度,在源头上截断虚假信息的传播。法治模式的主体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是行政法规的制定者,也是法律的执行者。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管理平台,严控虚假信息的传播,也可以鼓励受众参与虚假信息治理,关注受众的反馈,形成政群合力治理。自治的主体是受众,在社交媒体平台,受众既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生产者和发布者,因而,受众也要承担虚假信息治理的责任。
2.优缺点比较
技术治理模式依靠区块链技术拦截虚假信息,使信息生产传播更为公开透明,其优点是客观、效率高、操作性强,但是我国的区块链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技术难度高。法治模式是利用法律规范管理信息生产者和社交平台,以减少虚假信息的数量,阻断虚假信息传播的模式。它的优点是长期性、稳定性、意义深远、惠及后代。自治模式是受众提高自身素养以减少虚假信息产出的模式,其优点也是长期可操作,缺点则是见效慢。
结语
相较于传统媒介时代,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生产的成本更低、技术门槛更低、平台的监管更为宽松,因此“看图编故事”的谣言频频出现。虚假信息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不断繁衍,降低媒体公信力,不利政府工作的展开,影响社会安定,危害社会秩序。对于虚假信息的治理,我们应该从其产生的原因出发,将全面长期性策略和短期针对性手段相结合,将技术治理、法治、自治相统一,三管齐下,才能有效防治社交媒体平台的虚假信息,净化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