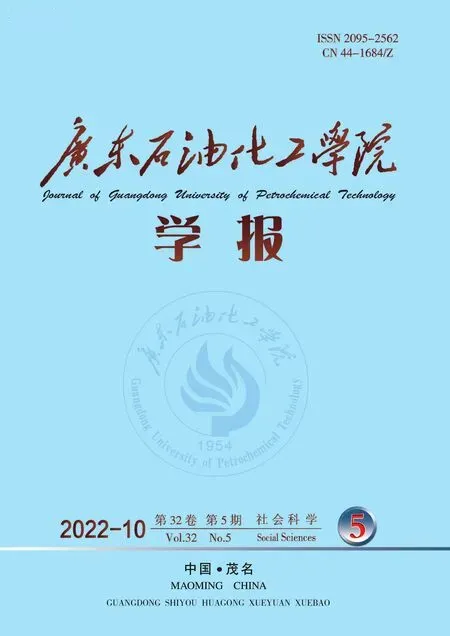《海商法》视域下涉外邮轮旅游承运人的识别
朱艳菊,王艺
(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266000)
1 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邮轮市场处于发展初期,并以出境旅游为主,同时邮轮公司也是以外商投资居多。基于我国特殊的市场准入限制,我国旅行社与邮轮公司创立了特有的邮轮船票旅行社包销模式。在包销模式下,旅客主要是通过与旅行社签订邮轮旅游合同来购买产品,如此一来,邮轮旅游活动便涉及三方主体,即邮轮公司、旅客和旅行社,三者之间法律关系复杂。这也导致理论界产出了两大学说——混合合同说与合同联立说,其最大的分歧主要集中于邮轮旅游合同的性质。基于这两种学说,理论界关于邮轮旅游中承运人的识别存在争议:前者将邮轮公司识别为(缔约)承运人,后者则将旅行社与邮轮公司分别识别为(缔约)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
此外,邮轮旅游承运人的识别问题也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以“海洋量子号”“蓝宝石公主号”案为例,由于纠纷均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选择适用中国法,最终法院依据中国法以及中国加入的国际公约进行相应判决。“海洋量子号”案中,上海海事法院将旅行社与邮轮公司识别为《旅游法》下的组团社与履行辅助人,旅行社与邮轮公司均不能享有海商法中赋予承运人特有的责任限制。在“蓝宝石公主”号案中,该院却作出完全不同的判决:邮轮公司与旅客在事实上存在一定的海上旅客运输关系,邮轮公司应认定为“履行承运人”(即实际承运人)”,尝试将邮轮公司拉到海商法的责任承担体系中,使其成为运输责任主体。可见,司法实践中对于邮轮旅游活动中何者为承运人同样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邮轮旅游大多具有涉外因素,具体表现为邮轮旅游合同的主体涉外以及客体涉外,即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涉及外商投资邮轮公司、合同标的于公海或者国外挂靠港履行。在当事人选择适用中国法的情况下,由于邮轮旅游具有运输与旅游的双重属性,实践中法院往往以《民法典》《旅游法》《海商法》等中国法以及参加的国际公约《1974年雅典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准据法进行审理,且《旅游法》与《海商法》下的旅行社与邮轮公司法律地位不同。鉴于邮轮的船舶特性及海上特殊风险性,理论界一致认为涉及邮轮旅游的问题应通过《海商法》第五章“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为基础进行调整[1]。此时,在《海商法》视域下进行邮轮旅游承运人的识别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关于邮轮旅游承运人识别的学说
2.1 邮轮公司承运人说
邮轮公司承运人说产生于理论界关于“邮轮旅游合同”性质的合同联立说。该观点以胡正良与孙思琪等人为代表,认为邮轮旅游合同符合合同联立的情况。合同联立是指多个合同之间仅仅为单纯的文字上的结合,多个合同之间可以相互分离,又彼此独立。正如前面提到的邮轮旅游服务合同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合同联立说的学者们认为,这两个合同是依存关系式合同联立,其中一个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另一个合同的效力[2]。在邮轮旅游中,邮轮船票通常是旅行社包价旅游产品的一部分,如果邮轮旅游合同无效,那么以邮轮船票为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自然也会无效[3]。
此外,持该观点的学者进一步阐述了在前述情形下邮轮公司与旅客之间存在一个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而且该合同的存在与否可以通过船票来证明。基于邮轮船票、邮轮公司与旅客之间形成了海上运输合同关系[4]。此时邮轮公司便符合缔约承运人的法律定位,从而单独作为运输责任主体。
2.2 旅行社承运人说
旅行社承运人说产生于理论界关于“邮轮旅游合同”性质的混合合同说。该学说是理论界占据主流的观点,以郭萍、陈琦等学者为代表,其主张在邮轮旅游实践中,与旅客直接签订合同的是旅行社,该合同具有“混合属性”。混合合同说的学者们认为邮轮旅游合同是一个无法被分开的单个的合同,且是类型结合型混合合同[5]。在邮轮旅游合同中,旅行社作为一方当事人向旅客销售包价旅游产品,该产品不仅包括海上观光服务,而且还涉及岸上观光服务,由此“混合合同说”的众多学者们认为其分别包含了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和旅游合同的内容,而此时的旅客仅在购买相应产品时向旅行社支付一定的价款即可,符合上述提到的类型结合型混合合同的特点。
此外,持该观点的学者们进一步提出,旅客与邮轮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而且邮轮船票亦无法证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存在,邮轮公司与旅行社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旅行社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缔约承运人,邮轮公司则被降格认定为实际承运人。
2.3 评析
上述学说均对承运人的识别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但本文并不赞同邮轮公司承运人说认为邮轮公司与旅客之间存在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并将邮轮公司认定为(缔约)承运人的主张。总的来说,邮轮公司承运人说与《海商法》并无冲突,邮轮公司承运人说既不符合中国法律体系,也很难与实务对接,值得商榷。而且目前我国邮轮船票销售仍以包销为主,将旅行社排除在《海商法》责任承担体系之外将严重危害旅行社的利益。当然邮轮公司承运人说也建议通过法律赋予旅行社一定的赔偿责任限制,但一项权利的赋予往往需要考量多种因素,且学说也应当符合我国邮轮旅游的实际情况。在论证学说时,不能仅从理论方面进行狭隘地分析,而应考虑是否能与现有的邮轮旅游制度相衔接,不能与《海商法》的原则与价值相抵触。尤其是在《海商法》已经规定了比较完善的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制度的情况下,本文认为旅行社承运人说的观点更合理。当然旅行社承运人说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我国《海商法》并未明确规定不实际从事运输的主体是否符合承运人的条件,因此该说在将旅行社识别为缔约承运人时论证不够充分。
其实国外并不排斥旅行社的承运人身份,如邮轮旅游相关法律比较完善的欧盟。欧盟《2015年包价旅游指令》第14条第4项和第5项中规定:如果适用于欧盟各国的某国际公约针对包价旅游合同范畴下的旅游经营者设置了责任限制,那么旅游组织者也享有这项权利。前面提到的责任限制主要存在于欧盟的相关海上旅客运输法《海上承运人责任条例》中。前述规定仅仅通过相关旅游指令赋予旅行社一定的责任限制,并不能直接证明欧盟将旅行社认定为承运人。这是因为外国邮轮旅游以直销和代销为主,旅行社并不介入邮轮公司与旅客之间的合同关系。此外,宋美娴在2021年的《海商法》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修订研讨会中提到,在英国亦是将旅行社看作缔约承运人。遗憾的是,由于国际邮轮旅游涉及的法律关系简单,承运人界定清晰,外国实践中暂时没有相关案例。
本文认为,我国邮轮船票以包销为主,而且我国《旅游法》于2018年刚刚修订,通过上述法律赋予旅行社一定的赔偿责任限制并不现实。因此,在《海商法》的框架下明确旅行社与邮轮公司缔约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 对邮轮旅游中承运人的识别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108条可知(缔约)承运人的认定应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合同的订立应当是以承运人本人的名义;二是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实际承运人也应当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受到缔约承运人的委托;二是要实际从事旅客的运送工作。基于此,本文结合前述认定条件以及旅行社承运人说的内容,分别认定旅行社与邮轮公司的法律地位。
3.1 旅行社为无船承运人
我国《海商法》关于承运人的定义中仅规定了相关合同的订立应当以承运人本人的名义进行,却没有对承运人进行详细的阐述,很难认定作为并未实际承担运输的旅行社是否符合承运人认定的第一个条件。但是借鉴《公约》关于承运人的规定与海上货物运输中“无船承运人”的概念,那么就可以认定旅行社符合缔约承运人的第一个认定条件。一方面,《公约》比《海商法》的界定更加宽泛,其中规定缔约承运人的部分如下:“不管这项运输最终是由其自身实施还是通过其实际承运人实施”。由此可以看出,《公约》明确指出,承运人可以是没有实际承担海上旅客运输的人。另一方面,依据对海上货物运输中“无船承运人”的概念理解,旅行社符合无船承运人的特征。无船承运人收益来源是其向托运人收取运费与实际承运人向其收取运费之间的差额。在船票包销模式下,对于不实际拥有船舶的旅行社来说其盈利的方式与前述类似,即旅行社没有遵循传统的模式仅靠完成邮轮公司的委托而获取收益,进一步讲其收益来源主要是依靠销售船票所得的差额。
此外,旅行社与旅客之间签订的“邮轮旅游合同”在性质上应被认定为混合合同,包含了海上旅客运输的内容。一方面,混合合同是由多个典型的合同或非典型合同的若干要素相结合而成立的合同。因此邮轮旅游合同为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这一典型合同与旅游合同这一非典型合同结合而成的“旅游+海上旅客运输”类型结合型的混合合同。另一方面,由于邮轮船票的相关规定并未明确其对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存在的证明究竟是初步证明还是最终证明,因此当船票的内容与合同的内容不一致时,船票的证明效力的顺位无法确定。而且,根据合同法的基本理论,旅客不能根据同一个合同标的与邮轮公司、旅行社这两个主体之间分别订立两个不同的合同[6]。值得注意的是,邮轮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乘客票据合同或航行合约等条款对于其是否具有合同的主体地位规定得也比较模糊。因此,邮轮旅游合同应当是混合合同,且包含了海上旅客运输的内容,旅行社符合承运人认定的第二个要件。
综上所述,旅行社符合无船承运人的认定条件,并基于合同向旅客承担赔偿责任。
3.2 邮轮公司为实际承运人
实践中总有学者针对邮轮公司与旅行社两者签订的邮轮船票包销合同究竟是不是委托合同而争论不休。主要原因是这两者之间没有订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委托合同,“邮轮船票包销合同”也不是一个非常符合形式条件的委托合同。学界针对缔约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如何认定出现了“广义说” 与“狭义说”这两种学说。狭义说认为,如果一个主体想要被认定为实际承运人,其需要与相关的承运人之间严格按照形式要件订立一个委托代理合同;广义说则认为,缔约承运人与其实际承运人之间真正订立委托的情况非常少,两者之间订立的合同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运输合同[7],不应该片面地将“委托或转委托关系”的解释总是局限于两者存在书面的委托合同上面,而应该对其含义进行广义上的解释。上述观点为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也是本文采纳的观点,即《海商法》中的委托跟合同法中委托的含义不同,其并不以存在委托合同为前提,只要承运人与该主体之间订立了合同并实际交付给对方运输,便是前面提到的委托。
此外,邮轮公司实际从事全部或部分运送,并不意味着邮轮公司与旅客之间成立“事实合同”。在“蓝宝石公主”号案中上海海事法院认为两者在事实上存在一定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事实合同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豪普特提出,其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合同的成立可以不用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而且订立合同的时候也不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同的意思表示,只要合同在成立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实施过程,那么该合同便可以成立[8]。拉伦茨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典型契约理论”,他认为合同的产生并不一定需要表现出其真实的意思,只要通过一定的事实行为就能够建立合同关系,而且其以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的照顾给付为客体内容。梅迪库斯则将事实合同认定为“无需意思表示的行为”[9]。
本文认为,引入事实合同理论来认定邮轮公司与旅客之间的关系是不适合的。首先,何种事实导致实施合同关系的存在不明确。邮轮兼具旅游与运输双重属性,并提供运输、住宿、旅游观光、餐饮、娱乐等服务,因而比一般的交通运输来得复杂。其次,我国海商法已经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关于实际承运人的规定,当包销模式下两者没有直接订立相应合同的情况下,可以适用该制度来规制邮轮公司的行为。最后,承认邮轮旅游中事实合同的成立可能会影响交易安全。一旦在邮轮开航前有人不法进入邮轮,邮轮公司或许还要对此人承担没有空余的舱房带来的违约责任。因此,认定邮轮旅游中不存在事实上的合同,不仅有利于法律体系的稳定还有利于保障邮轮旅游安全,保障真正的旅客的权益。
从法理上分析,实际承运人的出现打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海商法》通过法律的相关规定将实际承运人亦看做承运人的责任主体,从而该主体也能够享有承运人相关的权利,承担承运人的各种风险,进而与承运人履行相同的义务并承担一定的责任。在邮轮旅游中明确邮轮公司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可以防止没有与旅客订立合同的邮轮公司轻松地逃脱相关法律制度的调整,保护旅客的权益。而且这样可以将邮轮旅游中的相关主体尽可能地全部放在海商法的承运人责任规则体系里规制其责任,能够进一步避免相关主体受到不同法律下不同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规制时产生冲突。
综上所述,邮轮公司符合实际承运人的认定条件,基于法律规定向旅客承担赔偿责任。
4 对我国《海商法》第五章的完善建议
2018年修订的《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六章曾设置了“邮轮旅游的特别规定”等8个条文,首次在我国立法中尝试建立邮轮旅游民事法律制度。遗憾的是,经过多方讨论,最终删除了与邮轮旅游直接相关的全部条文内容,仅调整第107条的相关内容[10]。随着海上旅客运输的旅游化倾向,《海商法》适当修改创设相关规定以适应邮轮旅游的发展,能更好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4.1 增加邮轮旅游合同的定义
目前我国邮轮船票销售大多还是以包销为主,修改后的《海商法》应对邮轮旅游合同进行规定,这样可以使邮轮旅游中的法律关系更加清晰,摆脱有学者认为《海商法》只能调整邮轮旅游的运输部分的误区。增加邮轮旅游合同的定义只是为了更好地理顺邮轮旅游法律制度的规范逻辑,所需要的法条数量不多,而且也不会影响修改后的《海商法》第五章的整体属性[11]。因此修改后的《海商法》对于邮轮旅游合同进行专门的规定,厘清旅行社、邮轮公司与旅客之间的法律关系,澄清理论界与实践中对于邮轮旅游法律关系的误解,最为典型的便是将邮轮公司识别为缔约承运人,旅行社不是运输责任的主体。基于以上理由,修改后的《海商法》第五章可设置一条规定邮轮旅游合同的定义,具体内容可以参考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以及政府规范的相关规定,如《上海市邮轮旅游经营规范》等。
4.2 明确邮轮船票的初步证明效力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110条的规定,船票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来说都不能称其为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本身,但是船票可以看作是该合同存在的书面证明。但是该条文没有进一步阐明该船票究竟是合同成立的初步证明还是最终证明,而且当出现船票与合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两者的效力也存在问题。我国《民法典》等一般法也没有解决上述问题。此外,上海等地在2018年也开始试点“登船凭证”,尝试解决船票的隐形化问题,但是“邮轮登船凭证”作为仅用于登船的一张纸与邮轮实践中通常是以小册子为基本形式的邮轮船票不同,并不是船票性质认定困难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基于以上理由,本文认为修改后的《海商法》第五章应表明船票只是相关合同能够成立的初步证明,当其内容与其他合同约定不同时应当处于较后的效力顺位,以此为邮轮旅游承运人责任主体的法律地位的认定扫除障碍。
4.3 细化承运人的定义
我国《海商法》中承运人的定义模糊,不利于旅行社法律地位的认定。在邮轮旅游这种新式旅游出现以前,一般只会将缔约承运人认定为拥有船舶的人、经营船舶的人或者租赁船舶的人。而针对具有“无船承运人”特征的旅行社的法律地位,则会出现认定模糊的现象,并且《公约》中明确规定海上旅客运输的承运人可以是不实际从事运输的人。基于以上理由,本文认为我国《海商法》第108条承运人定义的最后应当加上“不管该项运输实际由其实施或由实际承运人实施”,从而为邮轮旅游实践中旅行社无船承运人法律地位的认定奠定基础。
5 结语
本文立足于我国特有的邮轮船票包销模式的现状,主要研究邮轮旅游活动由《海商法》调整时的邮轮旅游承运人识别的问题。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增加邮轮旅游合同的定义、明确邮轮船票的初步证明效力、细化承运人的定义等措施调整《海商法》第五章相关规定,从而为解决邮轮旅游承运人的识别问题扫清障碍,为进一步落实旅行社与邮轮公司的运输责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