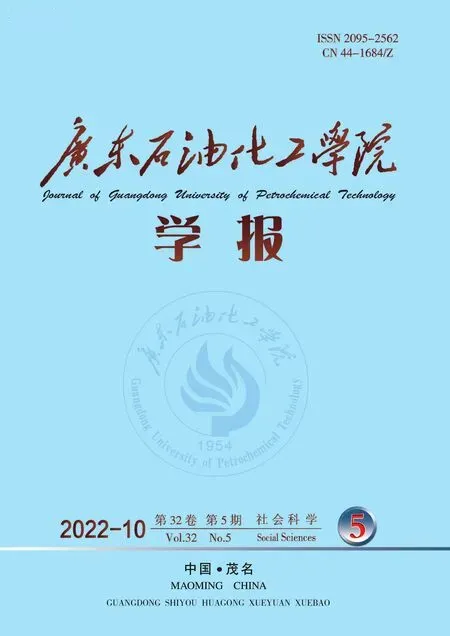“生态人”法律人格塑造:法律主体、权利能力与人格利益
侯巍巍,马波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文法学院, 广东 茂名 525000)
我国民法理论中通说的法律上的人格,即法律人格。学者对于私法上的人格构造存在着不同认知,有学者认为概念内涵应为“三元”结构,亦有学者主张“四元”结构。人格概念的“三元”结构,指的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民事权利能力以及受保护的人格利益[1]。也有的学者提出私法人格概念应为“四元”结构,即作为技术人格的权利能力、作为法律人格的法律主体、作为事实人格的人格权以及蕴含伦理人格的人之尊严条款。该说强调“从伦理人角度”剖析人格内涵,认为人格说到底是伦理的存在,最为重要的价值维度判断不可或缺。笔者认为,“生态人”作为一种更加契合新时代生态文明诉求的人性预设,其人格构造更应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生态人”法律人格的平等性,即对于每个具体存在的“生态人”来说其法律人格都是平等的,也都应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与制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生态人”法律人格的理论塑造因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诉求。因此,对于“生态人”的人格构造,我们拟采用通说的“三元”构造,重点从“生态人”如何成为法律主体,“生态人”是否具备权利能力,“生态人”怎样享有人格利益三个维度进行回应与论证。
1 “生态人”是否可以成为法律主体
法律主体与法律关系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法律逻辑上讲,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应包括主体、客体与内容(权利与义务)三个构成要素。法理学通说认为,法律关系主体只有同时具备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才能称之为法律上的主体。法律主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学说史上从“法律人格”概念演化而来。“法律主体是人在法律上的必然存在,权利则是法律主体对于主体能力实现的一种保证。”胡玉鸿教授在考察了凯尔森提出的“法律义务与法律权利的主体”、格雷命题的“生物意义上的人”等法律主体概念后,将法律主体概念概括为“既享有权利,也负有义务,并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的人”。在他看来,法律主体作为法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一种法律凝练与抽象”[2]。他认为,“法律上的人大多都是在法律关系网络中活动的人”,但法律关系主体并不等同于法律主体。他认为,法律主体之间如果没有涉及权利与义务,并不一定就参与到具体的法律关系之中。因此,法律关系主体只是法律主体的一种主体类型而已,而不是法律主体的全部。
在回答“生态人”是否可以成为法律主体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法律主体,这或许对探讨“生态人”的法律主体资格具有一定借鉴意义。2021年7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布《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草案)》对人工智能首次进行了法律上的概念界定。随着以智能主体为载体的“人工智能”的兴起,其一方面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给法律带来了巨大冲击,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法律的功能性“死亡”。“法律如果被算法所取代,这或许将是法律死亡的预言。”[3]笔者认为,除了法律功能性的危机,恐怕不得不提的还有“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问题,这是目前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人工智能既带来了社会建设的新机遇,但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诸多法律认知与实践层面的新挑战。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借助人脸识别技术,对他人的人格权客体加以不当利用,使得民法所保护的人格权(生命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保护等)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促使我们思考,是否需要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以主体资格呢?例如,2016年欧洲议会就提出了“电子人格”的法律地位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第四编)独立成编,是民事立法的一大亮点,但适用范围亦明确为“民事主体”,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我们认为,“生态人”与“人工智能”不同,“生态人”的着眼点在于“人”,而“人工智能”的着眼点在于“物”。“生态人”既可以是主体,也可能成为客体。“生态人”的着眼点在于“人”,指的是人的模式的抽象,而“人工智能”的着眼点在于“物”,“人工智能”是由人创造与操控的,还不具备“人”的主体特质。因此,这种“人”与“物”的划分并不是对“主体人法律人模式”的简单否定,而只是一种映衬比较的方法而已。“生态人”无疑是法律的创造物,是法律所创造出来的对具有生态文明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本质的“人”的一种抽象与表达;“生态人”存在于环境法的场域之中,拥有规范化的人格特性;“生态人”也具有“自为性”,也就是能动性、目的性与创造性,这意味着“生态人”是有意愿将环境权利付诸实践的人;最后,“生态人”无疑也可以成为联结法律和现实的桥梁。环境法律之中的权利、义务、责任,都必须借助于“生态人”的行为才能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因此,笔者认为,“生态人”的内涵界定满足了胡玉鸿教授所提出的法律主体的四个特性标准,可以成为法律主体。
2 “生态人”是否具备权利能力
法律上所谓的权利能力,是指法律主体开展活动所需要具备的实质性法律资格。《奥地利民法典》第一次在法律上使用了权利能力概念,而《德国民法典》则真正确立了权利能力的法律概念。梁慧星教授认为,民法上有三种能力,即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民事权利能力,也称法人格。”[4]江平教授则认为,权利能力和人格不是一个概念。“人格重点在于可以成为权利主体的资格,而权利能力则强调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5]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权利能力与人格进行区分。前文已述,“生态人”可以成为法律主体,是对“生态人”在环境法上地位的一种法律表达。德国学者汉斯·哈腾鲍尔在其著作《民法上的人》之中提出,权利能力不是自然人成为法律主体的资格,而是法律主体承载权利和义务的资格。柳经纬等也都认同该观点,只不过他们是基于民法(部门法)的视角予以阐释,而笔者则将其运用到环境法(部门法)之中而已。柳经纬认为,民事法律主体资格与权利能力资格的界定各有侧重。“人格解决的是主体之所以为主体的资格问题。而在主体人格确定的前提下,民事主体能否享有权利或承担哪些义务,则由权利能力来解决 。”张保红同样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权利能力概念始终在主体资格与权利资格之间徘徊,这种双重角色扮演已经造成了理解上与适用上的困难,有必要进行制度重构。对此,我国最为重要的民事立法《民法典》也予以了确认。如《民法典》中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显然,这里说的是自然人与法人的人格问题,即他们具备民事法律的主体资格。而我国《民法典》则继承《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一如既往地规定“自然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法人也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始终强调的是自然人与法人的权利能力资格以及权利能力的平等性问题。“民法对所有人进行平等的保护,而不考虑人与人之间在知识、经济能力上的差异,这也就是权利能力的平等性问题。”[6]
我们认为,“生态人”是一种抽象的“人”,是环境法上具有生态文明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按照蔡守秋教授的说法,“生态人是从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出发所进行的人的类型与形象抽象”[7]。“生态人”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学术研究旨趣而逻辑抽象出来的“人”之形象,她来源于现实,但又不同于现实的自然人。“生态人”并不是完全的理论抽象,同样也是由与生态环境要素结成“生命共同体”的具体的人组成的,政府、企业、团体以及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生态人”,也都是具体形态的存在。
3 “生态人”是否享有人格利益
人格利益是由“人格”+“利益”构成的。人格是指人的尊严及价值,而利益就是能够使社会主体的需要获得某种满足的资源。人格利益则是民法人身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人格权保护的对象,一种受保护的法益。“人身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不是物、行为或者智力成果,而是法定的人身利益。即法律规定的主体因享有人身权而在民事活动中能够得到的切身利益。这些利益是无形的,没有外在的实体形态,不能以物、行为等形态表现出来。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8]质言之,人格利益是人格权所保护的客体,体现的是人的尊严价值的精神利益。“生态人”是否享有人格利益,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生态人”是否享有人格权。蔡守秋认为,如果采用传统的“法律人”模式,公民或自然人的环境权纳入生态人的人身权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采用“生态人”模式则是顺理成章的。对于“生态人”是否享有人格利益,能够从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虑,即抽象思维层面的“生态人”与具象思维层面的“生态人”。人格可以分为抽象人格与具象人格,分别对应的是人格在自然法上的确认与人格在实定法上的利益化。“人格抽象化强调的是大写的理性、平等与自由等内在于人的抽象话语。人格的个体化则是在抽象化的人格基础之上,认识进一步加深的结果。”[9]笔者以为,抽象维度的“生态人”指的是环境法上具有生态文明理念,生活在生态系统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抽象维度的“生态人”更多的是从生态整体主义方法论出发而进行的人的抽象,强调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中,都需要与其他人一同联结成为社会共同体。
我们认为,抽象维度的“生态人”对应的人格是“抽象人格”,“生态利益”是其重点需要保护的法益,而不是自然人个人拥有的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法益。尽管“生态利益”还只是一种应然利益,但“生态利益”却也与人身权密切相关。“生态利益指的是人类对生态系统所享有的非物质性的利益。”[10]对于抽象的“生态人”而言,享有肖像、姓名、名称、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似乎从法理上无法说通。“生态人”毕竟是自然人与生态法人的集合,是抽象出来的“人”,因此,所保护的法益定位于“生态利益”较为合适。对于具象维度的“生态人”而言,强调的则是由生态环境要素结成生态共同体的具体形态的主体构成,政府、企业、团体以及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生态人”的具体存在形态。故此,具象维度的“生态人”对应的人格是诸如肖像、姓名、隐私等的“具体人格”。我们认为,“生态人”不仅具备权利能力,而且能够成为环境权的法律主体,“生态人”还可以明晰环境权的基本内容,为环境权的合法化提供理论依据。例如,我国《民法典》第990条就明确规定了人格权保护的权利类别。
“生态人”是逻辑抽象出来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人之新形象,但“生态人”并不是不可触及的,而是与生态环境要素结成生态共同体的具体的人组成的,自然人当然也可以成为“生态人”。作为“生态人”具体形态存在的自然人所拥有的生命权、身体权等人格权所保护的法益是否与环境权益密切相关呢?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生命权、健康权之中都可能包含有环境权的某些权利要素。“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必要基础,健康权主要讲的是人的内部机体器官和生理机能的健康,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外在生态环境,生命机体的健康显然也无法得到实现。”[11]由于法人不具有自然人与人身密切相关的生命、健康、肖像等权利。因此,法人只能作为抽象维度的“生态人”来理解与适用。
4 结语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当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时,我们应有尽有;但当我们与生态系统背道而驰时,我们必定一无所有。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世界各地肆虐。中国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发文,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原因进行反思,强调“生态文明理念缺位, 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乏力”是应予检讨之重要问题。“法律赋予不同主体以不同的法律人格、身份、资格,造成社会演化的复杂性。不同形态的法律位格,其实只不过是法律体系根据自身需求而创设的沟通网络中的不同支点,也只是历史性语境中的一种概念建构。”[12]说到底,人格构造变迁是时代激变的历史产物。“随着来自环境、资源及生态方面的压力和威胁日益加剧,人们日益认识到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3]我们认为,“生态人”的法律人格构造探讨有助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前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民法上的人格概念关注的主要是“人在民法中的存在方式”,但“生态人”法律人格表征的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诉求,这也需要理论创新的更好因应与回应。
——兼论平等理念下现代法的权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