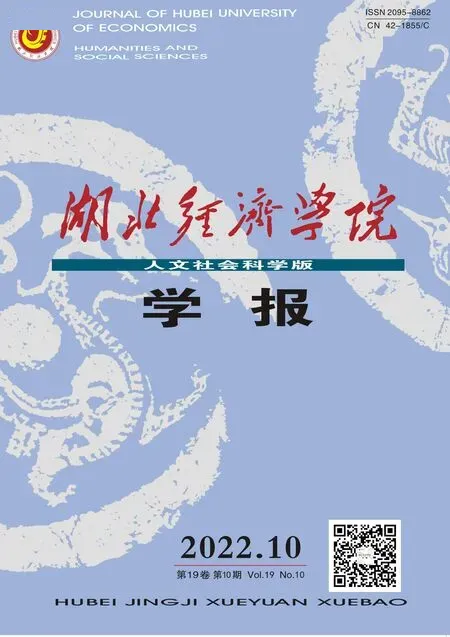我国遗产税开征问题研究
牛 晨(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202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8[1],已连续多年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①,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国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在我国分配制度中,初次分配是对收入的调节,是构建公平分配制度的基础。以财税为主要分配手段的二次分配是实现公平的最为关键的环节和手段。但我国税收是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为主,缺少以遗产税、房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导向。因而研究征收遗产税等财产税种,不仅有利于建立科学的税制结构,而且有利于化解阶层固化风险、完善分配制度,更好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
一、国内关于是否开征遗产税的争议
(一)赞成开征遗产税的主要学者及观点
从开征遗产税的时机来看,朱大旗认为,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积累大量财富,遗产税开征有较为深厚的经济基础;人们对遗产税有初步的感性认识,具备思想上的准备;征收遗产税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赠与活动和消费的增加,缓解我国需求不足、财富集中的问题,因此我国应适时开征遗产税[3]。张永忠提到,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等制度的建立健全、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和健全的财产税制度并不是开征遗产税的必备条件。我国的贫富差距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这一严峻的形势倒逼我国应尽快推动遗产税的开征[4]。
从开征遗产税的影响来看,禹奎认为,开征遗产税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财产分布的集中趋势,不会因为抑制储蓄和劳动供给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反而能消除盲点,改善税收调控功能,引导和鼓励慈善捐赠[5]。刘荣认为,虽然尚不能确定开征遗产税是否会阻碍民营经济发展,但只要科学、合理地确定遗产税的税负水平,遗产税就不会成为引发国内资金向国外异常流动的诱因,且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倒逼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和配套条件的改善[6]。
(二)反对开征遗产税的主要学者及观点
从开征遗产税的时机来看,贾康认为,遗产税是直接税里的一个重要税种,但是当前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官员的财产报告制度框架建设问题,征税机关无法堂而皇之地要求所有公民做财产报告并征收遗产税,不具备开征条件[7]。付伯颖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及遗产税本身的局限性,当前开征遗产税难以有效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目标,开征遗产税的最佳时机尚未到来。必须要全面评估征收遗产税带来的负面效应,夯实基础制度,做好征税的充分准备后方能开征遗产税[8]。
从开征遗产税的影响来看,马海涛认为,现阶段造成我国贫富差距大的原因是初次分配不均,遗产税对贫富差距的事后调节作用有限。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资本积累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开征遗产税可能对民营企业家造成一定的冲击,不利于经济发展。此外,征收遗产税的成本非常高,我国尚未形成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征收遗产税并不具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9]。孙成军认为,当前国情下开征遗产税并非缩小贫富差距的首选,难以有效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未必能实现均贫富的目标。外部环境尚未建立,开征遗产税反而将对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抑制储蓄、打击私人资本投资热情、制约积累财富的积极性[10]。
二、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分析
(一)完善我国税收调节体系的需要
当前我国税收体系中,个人所得税虽然是累进性的,但其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只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再分配能力非常弱[11]。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部分要用于基本消费品的支出,不得不大量承受所含的间接税负担。高收入阶层购买的更多的是房产、股权等资产,在总收入和财产中的税收负担反而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具有非公平导向[12]。富人源于购买房屋、奢侈品获得的增值收入,通过金融资产获得的资本利得收益等财产性收入,会逐步积累并资本化在个人财富之中,成为造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这些财产性收入难以被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覆盖,但能够被遗产税所覆盖。因此许多国家通过开征遗产税、房产税对其实施调节。我国现行税制设计缺少以遗产税、房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这些收入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税收调节之外,存在财产性收入调节失当问题,亟须通过开征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税来完善我国财产性收入税收调节体系[13]。
(二)发展慈善事业、发挥“三次分配”功能的需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促使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间趋向均衡[14]。2019年,我国捐赠额占GDP的比重仅为0.15%,捐赠数量仍然较少。慈善公益文化也并未深入人心,个人捐赠的比重不到40%,而西方发达国家则达到75%的水平。富人的捐赠意识也相对薄弱,多将财富通过代际传承的方式进行管理[15]。
国际上,推行遗产税的国家普遍通过扣除、免税的方式,对用于慈善事业的财产进行税收优惠。例如英国在征收遗产税时,捐赠者如果将其遗产捐赠给慈善组织而且能够证明其没有获取相关利益,那么对于捐赠者的遗产税是免征的。美国在征收遗产税时,将慈善捐赠部分予以扣除,促使财富持有者在不影响家族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慈善捐赠。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来看,遗产税通过倒逼机制鼓励社会进行公益捐赠。我国开征遗产税将有利于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发挥“三次分配”的均衡财富作用。
(三)缓解我国贫富差距的需要
目前我国居民的财产动态收入差距和财产静态存量差距都在日渐扩大。从2015年开始,我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比持续上升,从2015年的10.45倍上升到2018年的10.9倍,居民收入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在财产存量上,2015年中国前10%的高收入群体财富份额占比为67%,正在接近美国(72%),远高于法国(55%),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份额现在只比富裕国家略高,从绝对水平和国际上的相对水平来看,我国的财富集中度都在不断增加[16]。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国际警戒值之上,悬殊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公众对社会不满情绪升级,引发心理失衡,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近日频繁爆出的艺人偷逃税事件中,舆论除了对逃税行为进行攻击外,更多地落在了艺人的巨额收入之上。经传播媒介宣传放大之后,更加重了人们心里的不公平感。征收遗产税能够减少巨额财富在代际之间传承,限制社会财富过分向少数人集中,发挥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三、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分析
(一)经济基础分析
遗产税的开征需要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税源支撑。根据瑞信研究院在2020年10月22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财富报告》来看,中国家庭财富总额仅次于美国,超越了日本,位居第二。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有580万名百万富豪,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的居民多达21807人——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中国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数量首次突破500万户。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增至202万户。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增至13万户,未来10年将有17万亿元财富传给下一代[17]。
除关注财富总额外,由于遗产税是针对最富裕群体征收的,还要关注最富裕群体的财富比重。从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及高净值家庭财富报告》来看,我国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社会总财富的60.6%,前1%富裕家庭的总资产、净资产、年收入远高于前5%的富裕家庭,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中。因此,我国居民家庭已拥有较多的存量资产,最富裕家庭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比高,意味着遗产税开征的经济基础比较稳定。
(二)法律保障分析
在公民财富数量不断增加、财富形式逐渐多样化的背景下,政府和公民本身都越来越重视加强对个人财产的保护。首先,国家宪法明确了对公民合法收入、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其次,2020年实施的《民法典?继承编》对遗产范围、遗产分割、遗产继承程序等问题做了进一步地修订,更加贴近实际生活。尤其是新增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明确了管理人清理遗产、处理债务的职责,为将来遗产税的开征做了初步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具体财税法立法的修订,也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财产再分配的基本法律保障。最后,2012年第三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2015年第三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提出加大税源监控力度,进一步明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提供的涉税信息范围,银行与涉税机关双向配合,为实现遗产信息网格化管理、遗产税信息资源共享打下基础。为完善与遗产税相关联的个人财产实名制、个人财产登记与申报制度、个人财产评估等法律体系提供了制度依据[18]。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两税制度和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不适宜开征遗产税,但问题本身并不能否定遗产税的可行性。相反,及时开征遗产税反而倒逼国家加速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督促行政部门及时部署工作、学习经验,以保证遗产税的顺利征收。
(三)社会公众的思想认知分析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13年对17449人进行开征遗产税的认识调查。结果显示63.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并表示遗产税的起征点不应设置过低。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征收遗产税会极大增加家庭负担,占比达51.2%。从反对理由来看,他们并没有认识到遗产税是小众税,只针对巨富征收的事实,且这些成员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10万元②,成为纳税人的概率不高。若遗产税的税收调节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自己反而是受益者。他们对此有清晰、理性的认识就会成为开征遗产税的支持者。
在国家税务部门追缴明星偷逃税款并作出行政处罚后,绝大多数人认识到依法纳税的重要性,纷纷自觉主动纳税。此外,“三次分配”“遗产税”等字眼再次出现在今年的会议中,媒体对此进行的大量报道。人们对遗产税的了解逐渐深入和全面,意识到征收遗产税能够促进财富平均分配,缓和社会负面情绪,使各个群体从中收益。社会公众对遗产税的认识更加理性,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思想准备。
四、遗产税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税制要素的具体设计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税制模式的选择问题。不同税制模式,其纳税人、税率等具体要素的设计思路和方法是不同的。从世界各国开征遗产税的经验来看,有总遗产税、分遗产税和混合遗产税三种模式。
(一)税制模式
1.总遗产税
总遗产税又叫“死亡税”,它是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进行各项扣除后,就其超过免征额的部分课征遗产税,剩余遗产分配给继承人的模式,即“先税后分”。该税制模式下,纳税主体为被继承人,税率设计只与遗产总额相关联,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或比例税率,不考虑各个继承人的具体负税能力,以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有利于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19],又具有税源集中且易于控制、操作简便、征管费用较少、有效避免偷税漏税的优势。缺陷是不考虑被继承人和继承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和继承人本身的负税能力,税负分配前欠缺合理性,难以充分体现公平原则。采用该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英国、中国台湾等。
2.分遗产税
分遗产税又称“继承税制”,它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先将被继承人的遗产根据遗产分配顺序分配给各个继承人,各继承人根据其所分得的遗产缴纳遗产税的制度,即“先分后税”。该税制模式下,纳税人为各个遗产利益获得者,税率设计上能够考虑到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和负担能力而做出不同规定,体现量能负担原则。但因为要考虑每位继承人的遗产分配状况和经济能力,无疑加大了征税机关的管理难度,提高了征税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分遗产税为继承人偷逃税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税基是各个继承人分配的遗产,一旦被继承人、继承人与他人恶意串通将遗产虚假遗赠给第三方群体,通过虚构受遗赠人数量以降低各继承人、受遗赠人的人均分配遗产数额,甚至降到免征额度以下,或者继承人先将大部分遗产给负担能力较低的人,税款缴纳完毕后再予以返还或重新分配,便能达到少缴或不缴遗产税的目的。采用该模式的国家有日本、德国、法国等。
3.混合遗产税
混合遗产税制是被继承人死亡后,先对其遗留的遗产征收一次总遗产税。待各个继承人完成遗产分配后,对各个继承人就其所得遗产再征分遗产税。该税制模式综合了前两项制度的优势,既能够保证税收收入,防止偷逃税的发生,又能根据不同继承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区别对待,体现量能负担,兼顾了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的价值。弊端在于对同一笔遗产两次征税,有重复征税之嫌疑。且税率设计复杂,程序又十分烦琐,不符合便利原则,征税机关也承受着巨大压力。遗产税在开征之初就备受争议,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开征遗产税是国家对公民私有财产的掠夺。二次征税的形式会因受到纳税人和征税机关的双重反对而难以顺利实施。受以上弊端影响,采用该模式税制的国家较少,意大利也曾因此在2001年停征遗产税。
4.我国宜采用总遗产税制
各种税制模式的价值导向不同,具体制度也不尽相同,带来的效果亦各有千秋。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不足,也均有相应的国家予以适用,这说明税制模式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福利,我们设置遗产税模式需要保持独立自主态势,结合目前的立法体系和基本国情,选择最具有可行性的模式即可[20]。
从立法体系化角度来看,遗产税的制度设计需要与我国《民法典》中的“遗产管理人”制度相适应。富人占有的巨额财富载体多样,分布范围广泛,债权债务关系较为复杂。为顺利实现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他们一般会请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管理分配。我国《民法典》已经明确了管理人承担遗产清理、保管、必要处分和分配的义务。这些义务的履行需要以遗产尚未分配为前提。甚至在遗产有损毁灭失可能的情况下,管理人需要事先对遗产进行物理上的占有而为保管处分。在完成遗产数量清查、清偿包括遗产税在内的各种债务之后,将剩余遗产分配给继承人。这与总遗产税的先纳税、后分配遗产模式相适应。
前文提到,当前的税收制度具有不能体现公平导向的弊端,未来的税收体制应更加强调税收公平和共同富裕。虽然分遗产税更加注重公平价值,但目前我国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尚不完善,税务机关缺少征管遗产税经验,征管技术相对薄弱,难以满足分遗产税的征收要求。总遗产税制公平价值虽有所不足,但课税程序简便,便于管控税源,节约税收成本,较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税收环境和征管水平。此外,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者众多,遗产税的免征额度宜高不宜低。居民对纳税的义务感不强,对遗产税的开征更是多有反对,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减少偷逃税的可能性。既定国情下的可行性是实现公平性的前提条件,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只能放弃分遗产税的绝对公平的理想,追求可行性前提下的总遗产税的相对公平[21]。
(二)具体税制要素设计
1.纳税人
我国对总遗产税制模式下的纳税人确定问题仍不够明确。李华、王雁认为纳税人为被继承人[22]。白晓峰认为纳税人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并不是遗产的所有权人,对其征税明显不当,因而不列入纳税人范围[23]。国际上,美国总遗产税制模式下的纳税人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
笔者认为,总遗产税制模式下的纳税人应为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因被继承人去世后即丧失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不能作为纳税人来为自己遗留的财产履行缴纳遗产税款的义务,必须由其他人或组织担当纳税人。受该特殊问题影响,只能由遗产税的税款缴纳人作为纳税人主体。该主体是在遗产税收债务已经产生、税款已经实现的条件下,仅仅承担将已经实现的遗产税款进行计算、申报,并缴入国库的作为义务的主体。因此,在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的情况下,被继承人去世后的遗产控制权在执行人与管理人手中,由他们担任纳税人履行缴纳税款的义务。当遗嘱未指定且遗产关系简单明确的,继承人成为总遗产税制模式下的纳税人,但是他们必须在遗产分割前缴纳遗产税。若继承人先行分割遗产,后对其继承所得征收继承税,这是一种所得税而不是遗产税[24]。
2.课税对象
结合富人的投资喜好,遗产税的课税对象应限定为被继承人的金融资产、不动产、奢侈品。据央行2019年调查,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70%,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20%[25]。中华遗嘱库于2013年6月对500位办理遗嘱登记的老人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95%的老人遗嘱与房产有关③。且我国已颁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征税机关对于不动产和个人储蓄的控制较为便利,课税对象应以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为主。这既能保证充分的税源,又能有效控制被征收成本,降低征收压力。对于名表豪车等可重复性使用的奢侈品,在其消费存在剩余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价值评估手段明确其剩余价值。认定房产、增值性奢侈品价值时应当以遗产缴纳时间的市场价值为准,以便将财产的增值收入纳入税基。
为防止被继承人通过赠与方式逃避遗产税,还应当对被继承人去世前一定时期内赠与他人的财产征收赠与税。考虑到征收便利性,赠与财产应与遗产合并为课税对象,使用相同税率。在期限规定上,结合我国相关诉讼法的时效规定,将继承开始前3年的赠与财产计入遗产以征收赠与税。
从课税对象的范围来看,我国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管辖权双重原则。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定期限的居民纳税人,应对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全部遗产征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定期限的非居民纳税人,应对其来自中国境内的遗产征税。
3.免征额
在对免征额进行探讨前,首先要明确免征额与起征点的区别。学者在设计税制要素时,有的适用起征点,有的适用免征额,但并未说明适用的原因,甚至有的学者混淆了二者的概念[26]。起征点标准中,遗产总额未达到规定标准的不予征税,超过起征点的,以所有遗产为税基进行征税。免征额对规定额度标准以下的遗产不予征税,超过规定额度时,只对超过部分予以征税。笔者认为免征额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应当予以适用。假设遗产税免征额为1000万元,AB二人遗产数额分别为999万元和1001万元。A的遗产数额在免征额以下,不予征收遗产税。B只需要就超过免征额的一万元缴纳遗产税。若采用起征点,B需要对全部的遗产缴纳税款,而A仍不缴纳税款。这会使仍要缴税的B明显感到税负不公平,强化了其偷逃税和寻租动机。
在总遗产税制模式和前文所述社会调查的意见反馈来看,免征额设置不宜过低。其确定标准有人均GDP标准、人口百分比标准、具体数值标准均等多种观点,学者意见不统一。谢枫认为过大的贫富差距会拉低我国人均GDP,且人平均数值不能反映富人和穷人的财产具体状况,依据该标准得出的免征额并不标准。他立足于全社会财富分布状况角度,认为应对财富顶端1%的家庭征收遗产税[27],笔者同意该观点。根据《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总量达132万人,将近占到总人口的1%。他们的各家私人银行的人均资产管理规模普遍超1000万元。因此遗产税免征额宜设置在500万元,以便在五级累进税率中,对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适用最高边际税率,实现均贫富的效果。
4.税率
税率的设计应注重横向公平,对纳税人一视同仁均予征收。同时注重纵向公平,对不同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给予不同的缴纳标准,遗产多少同税负重轻成正比。遗产税的税率设计主要有三种:定额税率、比例税率、超额累进税率。定额税率直接规定纳税数额;比例税率是不论数额大小,对同一课税对象统一按照一个比例征税;超额累进税率把课税对象的数额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就超过某一等级的部分,按其等级税率计算征税额,相比前两者更加灵活,更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美国、日本等多数西方国家均采用超额累进制税率。因此,我国也应当采用超额累进税率。
截至2013年,美国联邦遗产税采取的税率为18%至40%的12级超额累进税率;日本主要采取的是税率为10%至50%的六级累进税率[28]。遗产税开征初期易引起纳税人的抵制情绪,因此每一级的税率不能过高。同时考虑到征收便利,我国遗产税可设置五级累进税率。借鉴两国遗产税率经验,最低税率设置为10%,最高税率为50%。接上文免征额度,遗产额在500万至600万的,税率为10%;遗产额依次递增100万,税率提高10%。当遗产额超过1000万时,超过部分税率为50%。
5.扣除项目
扣除项目是依法应当从应税遗产的总额中扣除的必要费用。为了使遗产税的征收更加合理,各国都规定了一系列的扣除项目,我国其他税种也规定了相应的扣除项目。因此我国在征收遗产税时也应当设计相应的扣除项目。
借鉴国际上多数国家的做法,计征遗产税时应扣除以下项目:一是征收遗产税前期依法必须扣除的项目,即被继承人的丧葬费、遗产管理费、遗嘱执行费、被继承人死亡前依法应当缴纳的其他税款、罚款、债务等必须支出的费用;二是税收中规定的法定扣除项目,包括:公益性质的捐赠、配偶法定继承的扣除、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以及生活费用、父母的赡养费用、对有残疾或生活困难的人的特别扣除等。
四、结语
改革开放已过四十年,中国财富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分配不均的问题也逐渐显现。有蛋糕,有尊严,人民的生活有幸福。分配好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让人民的幸福更有尊严。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维护分配公平,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本文主要在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对遗产税开征的必要性、可行性、税制要素设计进行简要讨论。顺利实现遗产税的开征,不仅要有科学的制度为依据,还要有完善的征收配套措施进行保障,目前我国相关配套措施还不完善,如何建立与遗产税制度相契合的征收配套制度,仍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实践经验的积淀。但遗产税开征本身会倒逼财产申报、登记、评估、死亡报告等制度的完善,实现遗产税理论与实践的推进,需要我们去大胆尝试,不断开拓创新。
注 释:
①参见http://news.cntv.cn/2013/01/18/ARTI1358486197956843.shtml.该报道称,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我国2003年至2013年的基尼系数,均高于国际警戒值0.4。此后,国家统计局每年均在官网公布当年基尼系数值,直至2020年我国基尼系数仍在0.4以上。
② 参见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015/c40531-23204363.htm l.此次受访者的年收入普遍在5-20万之间。他们成为遗产税纳税人的概率较低,不能准确反映真正纳税人对遗产税问题的心声。
③参见http://money.sohu.com/20130930/n387494097.shtml.在此次调查中,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认为,该调查直接面对有继承需求的老年人,数据真实准确,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遗产税的关心还是建立在自己房屋的价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