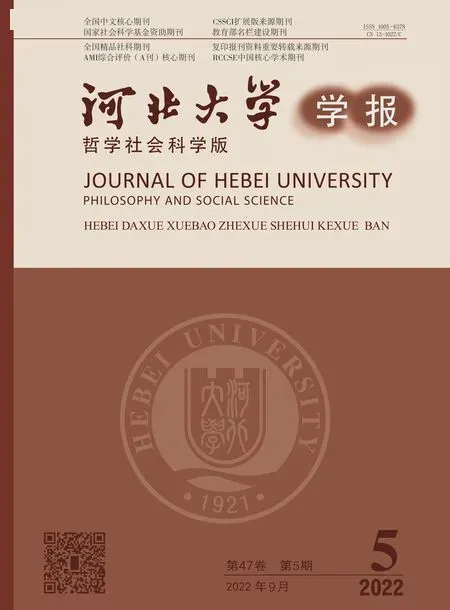“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彭新武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自秦代以来,郡县制成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定式。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明显具有地方性与割据性,因而,自秦汉以来,是否分封诸侯,如何分封诸侯,一直是朝野上下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皇权的长治久安、君臣关系、公与私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等等,一直是困扰最高统治者的难题。
一、血亲屏藩之悖谬
先秦时期的社会治理结构采用的是分封制(也称“封建制”),并以周代最为成熟和完善。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宗亲尽享封地之优渥和贵族特权,体现了“亲亲”之道;另一方面,则通过“封建亲戚以蕃屏周”[1],以“亲亲”维护“尊尊”,巩固了政权的基础。周代之所以国祚绵长,一定程度上正得益于这一宗法体制。然而,自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齐、晋、秦、楚为代表的华夏地理边缘国家,通过征服周边戎狄部落与异族小国,开始朝完全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如《史记·周本纪》所言:“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因此,分封制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在将权力关系播撒在王朝的角角落落的同时,也最终造成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局面。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各国国君为防范“亲亲”害于“尊尊”,对其亲子及直系子孙往往进行空间隔离甚至驱逐、诛杀,以减少其对君权的觊觎。正是在这种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各诸侯国内不断涌现出许多实力雄厚的强宗大族,即私家大夫。此后,春秋初“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逐渐蜕变为“自大夫出”,又进一步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2]。至此,温情脉脉的血缘情分已然被赤裸裸的政治利害关系所代替,分封制所预期的血亲屏藩最终走向幻灭,分封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在激烈的战国争霸过程中,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最终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纷乱局面,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而其政权的基础就是郡县制和官僚制。历史地看,秦帝国从封建到郡县的体质转换,解决了西周“王制中国”天子不能制诸侯的内在困境,可谓“古今一大变革之会”[3]1180。然而,固有的宗法制度虽然已经解体,但浓厚的血缘情怀、宗亲观念一下子难以断然消除。秦国初定天下,就是否沿用分封制的问题,曾引发了著名的“秦廷辩论”。在辩论中,李斯认为,正是分封制造成了春秋战国以来血亲仇杀、诸侯混乱的恶果,而只有实行郡县制,诸子功臣才不可能有非分之想,才能确保中央集权的巩固和统一:“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4]41在这里,李斯只看到分封制带来的诸侯割据纷争的负面性,而忽视了关东六国失势贵族潜在的反叛力量,以及对楚、燕、齐等偏远地区如何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而秦始皇基于避免诸侯割据、从制度上保证“权力通吃”的目的,故而采纳了李斯之议。在郡县体制下,地方长官职位不能世袭,中央和地方所有重要官吏皆由皇帝任免调动,定期加以考核,从而铲除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然而,秦始皇“任战胜之威”,急于兴作,严刑峻法,“以暴虐为天下始”[5]。秦二世继位后,更是变本加厉:“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4]54,结果秦帝国顷刻“二世而亡”。
秦王朝的短命而亡,正好为后来的分封论者提供了“口实”。刘邦初定天下,认为没有分封是“亡秦孤立之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为避免重蹈覆辙,刘邦着手剪除异姓诸侯,“大封同姓,以填天下”[6],建构起“皇子封王,其郡为国”[7]的郡县、封国并存的政治体制。此后,历代主张分封者莫不以秦亡为镜鉴,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譬如,曹魏时期,皇子“王空虚之地”,宗室“不闻邦国之政”[8],宗室曹冏曾上书《六代论》,认为不赋予皇族宗亲实权是秦朝、两汉的亡国之因,故建议曹魏统治者加强宗室子弟的权力。然而,曹魏没有汲取教训,政权终为司马氏所“禅代”。故而,西晋士人袁准指出,魏代无实封之国是曹魏失国的重要原因:“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既违宗国藩屏之义”[9]。同样,西晋名士陆机著《五等论》,认为实行分封制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可以“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10]。晋代士人之所以对三代的封建制赞美有加,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一方面,夏、商、周三代皆是实行封建制,且享国长远,只有秦、魏真正实行郡县制,但都是短命王朝;另一方面,两晋时期是门阀政治的顶峰,士族几乎可与皇室分庭抗议,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会严重削弱士族的既得利益。然而,从实践上看,无论是西汉还是西晋的分封,对于血亲屏藩作用的迷信,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其反面。汉初的封国都有固定的领土、人民,并设有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管理王国事务,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汉文帝时期,随着王国实力的增长,王国对朝廷的离心力增大,一些具有地理、经济优势的诸侯逐渐与中央相抗衡。汉景帝时,晁错极力鼓动“削藩”,直接剥夺诸侯王所辖的郡县,最终引发“七国之乱”。同样,西晋分封诸王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藩卫皇室,然而,由于诸王相互争权夺势,终于酿成“八王之乱”。
同样的故事依然在不断重演。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法古建邦”,分封诸多皇子于北方,以藩屏国家,诸王都可以控制军队,并付与“清君侧”的权力,以巩固朱家天下,结果却酿成燕王朱棣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变”。历史充分说明,宗亲屏藩是一把双刃剑,始终存在着“内讧”的危险。故而,朱棣上台后,一改宗室领兵驻守和出征的做法,且禁止宗室出仕:“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11],使之彻底失去与政权分庭抗礼的性质。然而,明王朝在消除政治隐患的同时,对宗亲的优渥待遇却制造出另一种社会恶果。明代中后期,诸王族属由于没有了政治追求,生活上大肆放纵,中央也是从物质上极尽优渥,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清代汲取了历朝的经验教训,虽然分封宗亲,但封而不建,让其聚居京城,藩卫清廷,但限定王府护卫亲兵,旗兵的领辖、征调权统归中央,从而避免了汉、晋、明等各朝宗藩颉颃王权、侵扰地方等弊端。同时,清代汲取了明王朝大肆分封造成社会负担的教训,封爵较严,高爵不滥:皇子不封以最高等的王爵,且严格控制王公嫡长以外诸子封爵的等级与人数;恩封诸王除奉特旨外,要世降一等,只有军功封王才可“世袭罔替”,等等。当然,作为一种特殊阶层,清代宗亲享有特权,生活优渥。唯其如此,宗亲子弟大多斗鸡走狗,生活腐化,最终也像明朝一样,整体走向没落。
二、“两制并行”与“两制综合”
无论如何,自“周秦之变”以来,郡县制已成为历代的基本定式。周代与秦代也分别成为两个纯粹实施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典型朝代。然而,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实现有效的管理,单靠郡县制存在着巨大的无力感。故而,既能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又能兼顾血亲屏藩作用的混合模式的出现便成为必然。
西汉初年,刘邦所建立的郡国并行制便是这种兼顾模式的典型。与西周的层层分封不同的是,刘邦所封刘氏诸王只有一层分封,诸侯王国以下依然是郡县制,每个王国领有三四郡、五六郡不等。由此,汉初的社会体制,除“皇帝—郡县”之外,还出现了“皇帝—诸侯—郡县”这样一种新体制。景帝平息了“七国之乱”后,尽收诸侯支郡,并着手取消诸侯王管理地方百姓的职权,让其只享有衣食租税的特权。此时,“郡”与“国”并行,诸侯国的大小仅为一郡之地。汉武帝执政后,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允许诸侯王进一步将土地分给子弟为列侯,使其势力大大缩小:“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12]在推行推恩令的同时,汉武帝还加设刺史官,对不法封王及有罪官吏进行严惩,并趁机对犯罪的诸侯直接剥夺其爵位和封地。此外,还颁布相关法律,规定诸侯国的官吏不得在朝内任职,诸侯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内活动,不能私自踏出封国,“不与政事”,不准接纳“宾客”,严禁官僚为诸侯王敛财并与之勾结。至此,诸侯王虽然依旧存在,但他们已经不具备任何政治势力,成了“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13]的阔佬,王国和侯国事实上已形同郡县。
混合体制的另一个典型方案是唐代颜师古提出但未能付诸实施的一个构想。贞观初年,唐太宗下令“议分封裂土之制”[14]963。各派意见歧异,论辩不已。为此,颜师古提出一种折中方案,提出一个统筹兼顾的君臣模式:封国不宜过大,使之与州县相杂,互相维持,“间以州县,杂错而居”;封国官吏一律由中央委派,诸侯“不得擅作威刑”[14]966。唐太宗非常欣赏这一方案,故而他一方面大力宣讲“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认为封赏太滥是“以天下为私”;另一方面又主张适当分封,以“熟穆九族”[15]:一是“封建亲戚,以为藩卫”,二是“远近相持,亲疏两用”,三是“众建宗亲而少力”[16]。这种设计虽然兼取“封建”与“郡县”之利,但在实践中遇到了不少难题,比如,当时唐太宗任命了一批宗室、功臣为世袭的州刺史,但许多受封者担心这种世袭封疆大吏的赏赐可能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故而拒绝接受。唐太宗无奈,只好收回成命。此后,唐太宗还把分封问题写入政治遗嘱,但他的子孙始终未能实现这一理想化的制度设计。
在历史上,除了“两制并行”的实践之外,还出现过综合分封制和郡县制的理论构想。譬如,明代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17]12的主张,具体而言:其一,“尊令长之秩”,就是选拔熟悉当地民情的贤能人士担任县令,并赋予其充分的权力,以增强县令的责任感,使其全心全意为其所管辖之民谋福利;其二,鉴于明朝中后期以来对于地方督抚、令、长的防范监察过于细密,地方官员逢迎上意、求全自保的现象,故而,为了充分增强地方官员的自主性和行动权力,顾炎武又提出“罢监司之任”;其三,“设世官之奖”,即凡所选拔的县令经考核为优秀者,可予以提拔并允许终身为官,甚至还可以将职位传给子孙或所举荐的贤人,以增加其责任心和使命感;其四,“行辟属之法”,就是用近乎乡举里选的原则荐举贤能之士,经考核试用录取贤能,以确保“世官”制度不走向歧途[17]12。总之,顾炎武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理论构想,兼采分封制与郡县制两者之长处,使其并存互补,旨在使分封、郡县两种制度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尽管这一构想依然局限于传统固有的政治体制框架,也未能付诸实践,但至少表明顾炎武已经开始跳出以往屏藩皇权的狭隘视角,而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角度进行了一次“综合两制”的尝试。
三、“公”与“私”的纠葛
在关于分封与郡县之争的诸多问题中,不少论者还经常涉及“公”“私”问题的讨论。其中,主要是以流行的“公天下”的这一崇高理念,为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一种伦理准则和价值评判。
历史地看,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变迁,不仅是一场社会存在形态的转变,也是一场精神形态的转换,即从春秋“尚礼仪”到战国“尚功利”的价值转换。如果说春秋五霸的“尊王攘夷”尚能够体现一种“内敛”精神,那么,在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的局势下,这种“内敛”精神也渐趋衰退,诸侯兼并和利益纷争的时代大潮,使得功利主义成为一种“主旋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各诸侯国通过国家法令授田于民,使私有制正式得到国家法令的确认,财产私有化迅猛发展,人们为争私利熙熙攘攘而上下奔走。既然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存在着功利的冲动,相互之间必然就会发生冲突。战国时期的“公私之辩”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在这场争辩中,儒家一般将“公正无私”作为道德修养的要求,认为君子应“能以公义胜私欲”[18];墨家则以增进天下、国家、人民之利为宗旨,主张不以私利害天下公利;而在道家那里,私、我、己与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很自然导出无己、无私的结论:“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19]总体来看,儒家、墨家和道家尽管在观念上有所差异,但他们在“崇公”上则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而在先秦诸子中,对“公天下”倡导最有力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当时的一些法家人士。法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利”的合理性,如商鞅说“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20]。但是,其基于富国强兵的宗旨,坚定地主张“立公去私”,甚至把公私问题提到国家“存亡之本”[21]的高度。这种将为天下众生谋福利转换成为国家共同体谋公益的思路,就是“天下为公”论。而当时“得民者倡,失民者亡”“立君为民”等民本思想盛行,“公”与“百姓”“众”相结合,便成为“公天下”论的基本思路。由此,先前比较具体的立君为“民”的民本观念也开始向比较抽象的立君为“公”、为“天下”转换[22]。
这种“崇公抑私”观念逐渐成为后世两千多年来人们处理“公私”问题的基本框架。柳宗元正是从“公天下”的立场出发,指出秦朝实行的郡县制从动机上来说固然是出于巩固个人权威、让天下人都服从自己统治的私心,但从制度本身来看则是最大的“公”:“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蓄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23]48这种“公天下”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革除了世袭制的陋习,面向全社会实施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机制。在柳宗元看来,分封制下的职位世袭,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在位者的贤能,故而很难确保为民服务的责任心:“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23]48通过对周代社会治理状况的历时考察,柳宗元指出,在封建制下,通常是政治混乱的多而治理得好的少,而周天子又不能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君,真正尽心治理地方、爱护人民的人,百无挑一,因此,周代的问题就出在封建制本身:“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23]47而郡县制下的地方行政长官由于实行选举制,“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23]48,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够随时加以撤换,即“有罪得以黜”[23]47。因此,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是进步的,有利于国家的治理,维护了“公”。
与柳宗元将郡县制的出现视为“公天下”不同,宋儒胡宏则认为,封建制才能够体现出“公天下”:“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顺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主所以纵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贼也。”[24]柳宗元和胡宏之所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其因在于:皇帝制度的“家天下”兼具“公天下”与“私天下”两种属性。柳宗元只强调了郡县制下的选贤与能机制对分封制下“亲亲”之道的替代,胡宏则强调了分封制下的分权而治的所谓“公心”,但他们都从根本上忽视了分封制和郡县制其实都是为了保持“私天下”:“封建、郡县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25]2095而明代的王夫之则重申了柳宗元的论调,认为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大势所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3]67在王夫之看来,郡县制为贤人政治开辟了道路,因此,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远远超越了他的“私天下”之心,守持的是至公之理、历史正义,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3]68。
正是基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常常以“公天下”的名义,强行褫夺地方权力,而成就皇权的“私心”,故而,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批评郡县制度为“自私之制”。在顾炎武看来,人性之私,乃人之常情;圣人之道,不在以公绝私,而在以私成公。只要君主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官吏视其所辖之地为自己之产业,必会尽心爱护和治理,从而就可以利用他们的“小私”以成天下之“大公”,使天下得到治理:“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17]15然而,这种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预期,因为即使将国家或封地视为自己的私产,并不必然导致善治。事实就是最好的明证,在分封制下,诸侯实行终身制、世袭制,但其未必都尽职尽责地去管理好地方事务;同样,郡县制下,皇帝以天下为家,但昏君的数量远远多于贤君,等等。与顾炎武一样,黄宗羲也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并深刻地揭露历代专制君主是如何把“天下为公”变成护卫君主一己之“大私”的工具:“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26]2在黄宗羲那里,无论是秦朝变封建为郡县,还是汉代的分封诸国,都出于君主自私之心,前者是因为“郡县得利于我”,后者是因为“可以藩屏于我”。黄宗羲正是出于“天下为公”的信仰,要求君主以公心治理天下,从而打破了“君为臣纲”的传统儒家教条。黄宗羲的立场是:民众的私利应该受到保护,但君主则应摒弃私利,“以天下万民为事”,“而己又不享其利”,并由此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26]2的论断。相应地,臣下也应该“以天下为事”而出仕君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26]5。在这里,明清启蒙学者显然已经隐约触及了“人遂其私”的专制政治制度,但就其实,这只是一种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却并未从根本上对君主体制本身发生质疑,从而也就未能进一步发展出“民有”“民享”“民治”的现代民主政治。
四、集权与分权的平衡
纵观历史上郡县与分封的历史演变及其论辩,唐代之前大都着眼于王朝的安全,基于“尊主安上”的宗旨,更多体现出的是“亲亲之道”而不是“权力制衡”。此后,关于分封与郡县的讨论,逐渐扩展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指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辩证关系。
唐玄宗时期,为了拒止周边各族的侵犯,大量扩充边防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帅权、财政支配权,以及监察辖区州县的权力,致使地方势力日渐膨胀。由于唐代君主及其中央统治集团并不满足于“弱干强枝”的局面,结果引起地方权贵的不满,招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军镇制度又扩展到内地。这些军事长官由于常常兼任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就成了实际上的地方行政长官,这就是唐代后期的所谓“藩镇”,又称“方镇”。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又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由他们分别统辖原来安史叛军所占据的地盘。唐代后期,这些强藩大镇各自为政、互相兼并,导致爆发大规模的“建中之乱”。唐王朝虽然最终平定了这次叛乱,却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为代价的。其后,各地节度使依然全面控制地方军政、财政大权,割据一方。柳宗元写《封建论》的意旨,实际上是面对唐朝安史之乱导致藩镇割据的局面,借批判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以弘扬郡县制来强化中央集权,树立朝廷的权威,维护国家的统一。
宋代立国之初,正是基于唐末以来王权衰微、藩镇割据、天下分崩的教训,故而极力强化君权,大幅度削夺各级官僚和地方权力,由此而形成了皇帝高度集权、中央严密控制地方的政治体制。为了消除对皇权的威胁,宋代的分封也显得较为“刻薄”:皇子亦不世袭,“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不过承荫入仕”,“或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25]2202,等等。宋代的统治方略造就了过度集权的体制,造成“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27]的局面。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这一局面很快向负面转化。当其时,辽、西夏、金先后崛起,对宋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由于宋王朝过度集权,边疆地方政府毫无自主性,致使对外应变能力差,日后遂成被动挨打之势,在与西夏、金朝的战中接连失利,而终被金国所灭。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犹以宋代积弱为由,一方面竭力加强集权统治,取消三省,废除宰相,由六部分管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由此直接干预、支配和控制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明朝中后期以后,社会上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再加上中央派出矿监、税使到全国掠夺财富,甚至对于普通人民赖以生存的营生皇权都要介入。故而,就在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之时,反君主专制之声也此起彼伏,郡县与封建之争再起。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大多亲身经历了明王朝分崩离析的惨痛过程,故而,在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表皮之下,他们将矛头指向专制王朝对财富与权力的贪得无厌,对百姓之利益的肆意侵犯,并赋予了封建制限制君权、实现地方分权的新内涵。譬如,顾炎武提出“分权众治”的主张:“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28]而王夫之更是设计出一套天子、宰相、谏官的“环相为治”的政体蓝图,具体而言:天子须以无为而治,其职责只须谨守国家典章,尤以考察宰相人选、任用宰相为重;宰相则应是国家行政首脑,统帅百官,梳理万机;谏官的职责则是专司监督君王;官之任用及罢免之权,操于宰相:“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29]王夫之的“环相为治”尽管并不能与现代“三权分立”同日而语,却显示出王夫之已朦胧地发现了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制衡原则。
郡县与分封之争的历史表明,在帝制体制下,唯有君臣权势悬殊,才能上下相安。而实行分封制必然导致君臣彼此猜忌、对抗与仇杀。历史地看,郡县制虽然是大势所趋,并成为专制王朝的基本定式,但是,郡县制又无法充分满足屏藩皇权的需要。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下,资源和权力被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中央,使地方政府很难有独立性和积极主动性。而一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失控,君主便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