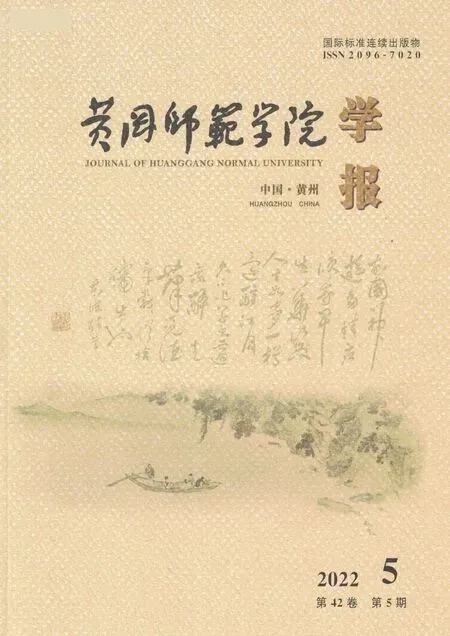兼:大学通识教育的中国方案
李建中,刘纯友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当我们在中国高校说“通识教育”时,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人文素质教育”,我们在说“博雅教育”。显然,“人文”与“博雅”都是中国本土固有的观念。虽然“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个“名”是从西方舶来的,“通识”一语的汉语之“实”却深植于本土文化根柢。古今汉语,“通”与“兼”可以互训:通者兼也,兼者通也。“兼”的原始义非常简单:只手持双禾为兼①。以“兼”为词根组成的词,诸如兼通、兼和、兼容、兼怀、兼包、兼备、兼融、兼成等语,既是传统中国文化及教育思想的精髓与要义,又是当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论及方法。“兼”的本义为“手持双禾”,故以“兼”为词根的汉语词多以“兼和两端”为意旨。就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来说,传统文化“理兼天人”的价值观、“情兼生死”的人生观与“事兼知行”的方法论,既构成了其历史性资源与底蕴,又彰显着其当代性意义与价值,更在人文化成、立德树人之层面上提供了通识教育的中国方案。
一、理兼天人
大学通识教育落到实处是通识课程设计,而课程设计的支撑则是通识教育理念及其背后的文化底蕴和教育思想。《庄子·大宗师》开篇有言:“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1]224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设计有两大问题域,一是“何以成人”,即如何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二是“何以知天”,即如何掌握自然规律和科学方法,如何理解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命伦理,在这个意义上说,“知天”也包含了“知人”,故曰理兼天人。作为通识理念之价值观层面的“理兼天人”,理应成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计及经典选读的根本性特征。
遍观国内,跨学科经典导读已然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元素和主要方法。对经典的选择可能会因时(不同时代或时期)、因地(不同国别或区域)和因人(不同设计者或执行人)而异,但“理兼天人”应该成为共同或共通的价值取向和通识理念。在“世界”的语境下考察,人文科学(人)与自然科学(天)兼通兼融是大学通识教育的题中之义;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和思想精华,其中包括历朝历代、各门各派的经典文本。
国内学界,无论是文化学还是教育学,讨论“天人合一”的成果已是汗牛充栋;但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理兼天人”,乃是从“兼”而非“合”的层面,对“天”“人”关系的新发现和新阐释。若说“合”强调的是天人一体、天人不分或天人无别,那么“兼”强调的则是天人有别、天人二分或天人两兼。手持双禾为兼,同样的道理,天人共存为兼。只有从“兼”的原始义出发,才能真正把握“理兼天人”的要义,也才能在价值观层面找到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根柢。
许慎《说文解字》释“天”为“颠(巅)也,至高无上”,段玉裁注曰:“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民于食,皆曰天是也。”[2]2如果说许慎对“天”的解释偏重于天地之天或曰自然之天,那么段注则更多地将“天”会意为“一”与“大”的“合二字以成语”,也就是说在“天”这个已完成的语义(即“成语”)中实际上兼含了双重义蕴:“大”和“一”。《说文解字》说“大”“象人形”,段注接着说,“人”这个字也是“象人形”,但只是“象臂胫”;而“大”这个字“则首、手、足皆具而可以参天地”[2]49。简言之,在“天”这个会意字之中,“大”为“人”,“一”则是“大”(即“人”)参天地时仰观之“天”。于是,“天”这个汉字,既在字形上“形兼天人”,更在字义上“义兼天人”,此即“理兼天人”。
先秦文化元典之中,从《道德经》到《庄子》,“理兼天人”一脉相承。《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在老子这个以“法”为行为中介、以“人”为行为主体的链条中,行为的对象虽然有四(“地”“天”“道”“自然”),实则为一(“天”,或曰“天地之道”或“自然之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法天”乃是原始道家对“理兼天人”的经典表述。若说老子的“人法天”是关于“理兼天人”的纲领性命题,那么庄子则对此有了更深入的论述,创生出以“天”以词根的系列关键词:天池、天籁、天理和天机。
“天池”出自《逍遥游》,说鹏鸟将从北冥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1]2。南方广阔无垠的大海,在天的视野下却只是一个“池”而已。这启示我们:生活在地上的“人”要有一个“天”的视角,要站在“天”的高处去鸟瞰“人”的世界。就像今人坐在飞机上俯瞰地面,一米多高的汽车和几百米高的大厦,都是一样的黑点;以广阔的空间尺度和漫长的时间尺度重新审视宇宙人生,我们斤斤计较的一切物与物之间的差异和分别也就消失了。可见庄子的“天池”既是人类所追求的“逍遥游”的兼融境界,也是人类所应秉持的“齐物论”的兼和思维。
“天籁”出自《齐物论》,是庄子在“齐”“地籁”“人籁”二“物”之后所臻之至境。《齐物论》先借子游之口界定“地籁”和“人籁”:“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1]49,然后借子綦之口界定“天籁”:“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1]50从字面上理解,“地籁”是自然界的风声、水声、松涛声等等,“人籁”是人吹奏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天籁”却既无发动者亦无接受者,故与其说“天簌”是音乐不如说“天籁”是境界,是老子所讲的“大音希声”的境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所追求的“理兼天人”的最高境界。“人”只有具备“天”的视野才能闻知“天籁”,或者说只有在徙于“天池”之后方能聆听“天籁”。
“天理”出自《养生主》的一个著名寓言:“庖丁解牛”。“庖”为一职,品有三等:族庖月更刀,良庖岁更刀,而历时十九年解牛数千且“刀刃若新发于硎”者,神庖也。神庖十九年不更刀而“游刃有余”,是因为他清楚地了解牛身体的“肌理”,知道该从何处下刀。庄子这个“解牛”的故事,所寓之意是人如何护养“生之主”即如何养神养心。世界是一头庞大的牛,个体的人则是一把刀,如何剖开这些错综复杂的筋骨皮肉,同时自身却不受伤害和磨损?这就要依据世界的规律,也就是“天理”;只有掌握“天理”,才能游刃有余。
“天机”出自《秋水》篇的一个有趣的寓言。一足夔羡慕万足蚿,万足蚿羡慕无足蛇,无足蛇羡慕无影风,风却谦逊地说:我虽然能吹折大树、吹跑大屋,却对指我、踏我的小小的手指和小小的脚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天地万物,各物自有各物的天机,无须羡慕它物,更无须胜过它物,因此郭象注曰:“恣其天机,无所与争……万物各自为,则天下莫不逍遥矣。”[1]594某物为它物所羡或自以为胜过它物,其实只是“小胜”,而忘胜负、忘得失、顺随天机才是“大胜”:“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1]594
天池、天籁、天理和天机这四个关键词看似谈“天”,实则是“理兼天人”,讲个体的“人”如何获得“天”的视角,如何遵循天理、顺随天机以臻天籁之境。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弥纶群言,“理兼天人”者既有老庄道家更有孔孟儒家。当然,儒、道两家的“天”又有所侧重或不同:先秦道家的“天”更偏重于天地自然,是自然之“天”,是人法自然,或者说是讨论自然语境下的人性;先秦儒家的“天”则偏重于人与生俱来、生而有之的天性,是讨论社会语境下的人性。作为社会中的人,人的“天性”又是很复杂的,在孔子那里是兼包“仁者安仁”与“智者利仁”,在孟子那里是兼怀“人性本善”与“食色性也”。
大学通识教育的课堂上,教师会经常性地遭遇“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的‘精致利己主义’”“如何面对后浪们的‘利他’之言与‘利己’之行”之类的问题。在破解这些现实难题时,“理兼天人”的价值观是可资借鉴的传统文化资源,无论是道家的“天”还是儒家的“仁”,其实讲的都是“人”,讲“人”的顺随天性、臻为大美,讲“人”的“安仁”与“利仁”,讲“人”的“为仁由已”和“仁者爱人”。而这些看似相悖相立却能相生相济的奥秘之所在,全在一个“兼”字。
二、情兼生死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通识教育又叫“全人教育”或“成人教育”。何为“全人”?何以“成(为全)人”?《西游记》中的唐僧,见人就说三句话:“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唐僧的自我介绍回答了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看似简单随意,实际上是人生终极之问,也是大学通识教育的“全人”或“成人”之问。说到底,大学通识教育就是要回答这三个终极之问。如果说,上一节“理兼天人”是在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兼通处探讨此终极之问的答案,本节“情兼生死”则是在人的来路(生)与去路(死)的兼通处回答这三个终极追问。
就大学通识教育的“情兼生死”而言,三个终极追问分属两大层面:“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是关于人的“生”(此来,此在),“我到哪里去”则是关于人的“死”(彼往,彼去)。无论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还是西汉年间的司马迁,他们写历史人物无一例外的要交待传主的谱牒世系、姓名字号、籍贯故里、山川地理、风土人情、风俗伦理……这是在回答“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同样,任何历史学家的历史叙事都要写到传主的归宿即死亡,这是在回答“我到哪里去”。对于旅行者希罗多德而言,三大追问中的“我”只是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是真正的“他者”;对于太史公司马迁而言,三大追问中的“我”既是笔下的人物也是他自己,尤其是在遭李陵之祸而身受腐刑之后,司马迁是向死而生,是真正意义上的“情兼生死”。司马迁《报任安书》详细地写了他在受腐刑之后的心理活动,他的身体和心理的巨大变化,以及他徘徊于生死临界线上的巨大痛苦,还有他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的生死追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通识课程如何讲授司马迁及其《史记》?当然要告知同学们《史记》的史学价值(成一家之言)和文学价值(无韵之《离骚》);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引导同学们如何用“兼”的眼光去认知和理解《史记》史学和文学价值后面的生命价值观,如何用“兼”的方式去体悟和把握太史公的“情兼生死”。在“情兼生死”的司马迁看来,一个人在死亡的时候,其肉体的毁灭与精神的升华是两个顶点,这两个顶点是同时达到的,也就是说,他死的一瞬间,同时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达到两个顶点:一方面是肉体的毁灭,是躯体的倒下;另一个方面是精神的升华,是人格的挺立,也就是在身躯倒下的地方屹立起一座人格的丰碑。个体的“人”,在“死”的瞬间获得永远的“生”,这才是“情兼生死”最为深刻的内涵。
从这个维度思考,司马迁受腐刑后之所以选择隐忍苟活,盖因他当时还不可能达到第二个顶点。我们从《史记》对死亡的描写和评价,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生死困境的超越。钱钟书《七缀集》有一篇《诗可以怨》,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将生前的创作“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采不表于后世’”[4]。人死了是会腐烂的,但如果发愤著书且传之后世,就不会“腐烂”不会死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永垂不朽”。《史记》就是司马迁的“防腐剂”,因为有了《史记》,司马迁永垂不朽,他用自己残缺的身躯,建立了一座文化和精神的丰碑。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司马迁这样在生死徘徊之际选择生存或死亡。当死亡变得不可选择时,生者如何面对一己之逝?当不可抗拒之死亡夺走我们周围人的生命时,生者如何面对逝者之死,这是“情兼生死”的更深一层意涵。《典论·论文》这篇经典不仅仅是论“文”,而且是论“生死”,是一篇“情兼生死”的美文。曹丕并不讳言“死”:“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5]若论帝王功业,魏文帝或许乏善可陈;若论“情兼生死”,曹丕远胜秦皇赢政和汉武刘彻,他和他的父王曹操一样,对生死持一种通脱理智的看法。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人文创造(文章)是不朽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最优秀的文章不需要依赖作者的权势和评论者的夸赞,就能让作者的声名流传万世;所以今天我们仍可通过《典论·论文》看见一个鲜活的曹丕。“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6],如果曹丕没有流传下他精彩的文章和诗歌,他就会像长安城边埋过的无数帝王将相一样,生前名噪一时,死后无人问津。在当时,是“魏文帝曹丕”创造了《典论·论文》;但今天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是《典论·论文》以及他的系列诗赋作品创造了“文学家曹丕”,赋予他以不朽的生命。“魏文帝曹丕”已死,“文学家曹丕”永生。“情兼生死”,不仅关乎中国古代生死抉择的个案,更关乎古往今来一切人类对“死生之际”的思考与理解。
三、事兼知行
《史记·太史公自序》曾引用孔子语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7]2856表面上看,“载言”与“行事”,孔子更看重后者;但事实上,强调知行合一,既是孔儒亦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太史公自序》全文引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老太史公品评先秦六家,所用也是“事兼知行”的尺度。司马谈说道家不仅兼有六家之长,更重要的是相比儒家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道家明显更加“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7]2848-2849。从今天看,司马谈对儒、道优劣的评鸷或可商榷,但“事兼知行”的方法论立场却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以“兼”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大学通识教育,其价值论的“理兼天人”和人生观的“情兼生死”,坐实到方法论层面则是“事兼知行”。就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设计及运行而言,一是要在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的设定中贯彻“事兼知行”的理念,二是要在课程形态、课程路径以及师生互动中实施“事兼知行”的方略。
中国古代文论有一部专讲博通雅致的经典《文心雕龙》,全书50篇,语涉“兼”字的有21篇,以“兼”为词根的术语有23个,诸如“兼包”“兼存”“兼气”“兼累”“兼通”“兼善”“兼雅”“兼解”“兼载”“兼总”“兼赞”等等。借用今天的话说,在《文心雕龙》中,“兼”是一个热词。刘勰文论体大思精,其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总不离“兼”:文学思想层面兼载儒、道、释,文学史观层面兼包“通”与“变”,文学风格层面兼存“奇”与“正”,文学修辞层面兼善“显”与“隐”……一部《文心雕龙》,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兼性智慧和兼性思维。
如果说身在佛门的刘勰以弘扬儒家文化为己任是“义兼佛华”,那么道法孔儒的刘舍人之舍“注经”而取“论文”则是“事兼知行”。在刘勰看来,儒家经典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就是体与用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文心雕龙·序志》:“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8]726在文学理论家刘勰眼中,中国文化是一株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其经典是树的根柢和主干,文章文学则是树的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学习儒家经典(包括诵经、注经和解经)还只是停留在“知”的阶段,只有使儒家经典成五礼、致六典并炳焕君臣关系、昭明军国大事,这才是真正的“用”。
“事兼知行”的刘勰是主张学以致用的。青年时代,刘勰的理想既不是做佛学家,也不是做经学家,甚至也不是做文学理论家。刘勰之所以要写一部《文心雕龙》,除了要阐明儒家文化与文学创作的“体用”或“知行”关系,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动机:在尚无科举入仕之径的南朝,出身寒门的刘勰只能用《文心雕龙》敲开仕宦之门,开拓事功之路。刘勰在《程器》篇坦言:“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8]719-720在“事兼知行”的层面上说,青年刘勰的人生设计和努力是成功的:据《梁书·刘勰传》,《文心雕龙》写成之后,因为当朝重臣沈约的“大重之”,刘勰离开桑门,走上仕途。
就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而言,《文心雕龙》的“事兼知行”对于当代大学的通识教育也非常具有启发意义。首先,“文心雕龙”这个书名就是“事兼知行”的。“文心”是“知”,是对“为文之用心”的“知”,也就是对诸如文学之本、文学之道、文学之体、文学之辞和文学之术等各种元素及其整体构建的“知”;“雕龙”是“用”,是“心之如何用”,也就是将对文学的各种“知”用之于文学创作,如何雕缛成体,如何垂帷制胜,用当代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如何“文本化”。其次,刘勰论文学创作以“神思”为关键词,而“神思”也是“事兼知行”的。神思也就是想象,只要是心智正常者,谁人不会想象?关键是如何在神思亦即想象之际,用“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8]493,反过说,如果枢机不通,则文学作品就无法状物更无法言志。因此刘勰的文学创作论特别注重语言之“用”,创作论二十余篇,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讨论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之“用”,诸如“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等等。第三,刘勰的文学鉴赏论以“知音”为关键词,《知音》篇一上来就感叹“知音其难哉!”知音之难,难在何处?难在“事兼知行”。在刘勰看来,像钟子期这样的知音者,不仅要深知乐论乐理,更要熟谙乐言乐情,不仅要“知”音“晓”音,更要“吟”音“奏”音。因此,刘勰对天下知音者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8]714若从字面上解读,“观千剑”是“知”,“操千曲”是“行”;若用“事兼知行”的眼光重读,则这两句是互文见义:你只有既“观千剑”又“操千曲”亦即“事兼知行”,你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知音”。
大学通识教育的精髓乃“跨学科经典阅读”,在此层面可以说,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培养中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经典的“知音”。在通向这一目标的途中,课堂方法的“事兼知行”又是非常重要的。大学通识教育课,无论是选修还是必修,一般情况下都是大班授课,讲台前的学生,少则六七十人,多则一二百人,师生互动非常困难,培养学生的能力更是一种奢望。通识教育如果缺乏师生互动基础的建立和对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那么这种通识教育是值得质疑的。因此,如何在“大班授课”的同时,创生“小班研讨”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就成了大学通识教育“事兼知行”的关键。
“多样性”是指小班研讨课堂形式的丰富多样,比如学术会议式、专题辩论式、艺术呈现式、PPT展示式等。“有效性”则是指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目的均在于提升学生的多种能力,诸如文献检索能力、学术书写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而诸种能力之中,最为重要的还是独立思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批判性思维。勿庸讳言,应试体制训练出来的高中生,他们走进大学时,头脑中装满了各类“标准答案”,而“标答思维”是他们心智健全、能力提升路途中的最大障碍。总体上说,“事兼知行”的通识课堂,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培养同学们如何用“兼”的目光和方法重审经典,重审世界,重审人生。同学们在通识课堂上独立思考出来的“知”,日后才能成为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行”。由此可见,大学通识教育的“事兼知行”,对于学生价值观的“理兼天人”和人生观的“情兼生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注释:
①《说文解字·秝部》“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页;《说文通训定声》有“手持一禾为秉,手持两禾为兼”,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2页。
——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