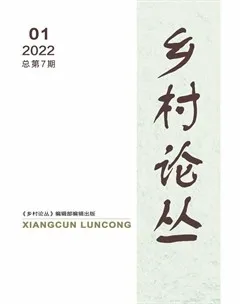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
摘要:海南因之孤悬海外,被隔绝与疏离于南海。汉族移民在迁徙海南的漫长发展进程中,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区域文化,其中移民村落宗祠与乡贤联结,形成海南传统特色乡贤文化。琼海马氏在嘉积镇田宛村当地就以“一处宗祠”与“一座古墓”为纽带,串联当地马氏移民族群的共同民间记忆,铸造呈现出当地特色乡贤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里,一方面表现为马氏子嗣在乡贤文化感召下所形成的家族荣誉感,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该荣誉感而形成的凝聚力,以“瀚苑”之名,教化宗族子嗣。当前,乡贤文化是区域文化的感召与力量之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之一,个案解读新时期农村乡贤文化,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落实新农村乡贤这一股中坚力量。
关键词:马氏 乡贤文化 民间记忆
海南独居南海一隅,因之海洋的隔绝与疏离,在赤土大陆板块之外,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人文景观。作为游人,倘若你行走在海南,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里,你总会与海南各个宗祠相遇,徜徉于这些间之于“人界”和“神界”的“家庙”,你会遇到海南独特的宗祠区域文化。“宗祠是指某一姓氏宗族在某一村落定居繁衍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单姓或主姓村落后,由族众共同建立的祠堂”。 汉人毛亨传曰: “春日祠,夏日抽,秋曰尝,冬曰蒸”,从古自今,宗祠都是一定地方重要的核心文化中心。海南作为一个移民岛屿,移民内核总有着一股尊崇祖德,传承文明的坚持,因此,村村有宗祠是海南全域范围内的汉族移民村庄的一个共有文化景观。
值得探究的是,海南移民村落不但以宗祠为中心崇古,移民宗族文化也特别“重今”。这里的“今”,特指移民海南之后,各个家族在当地的发展历史。其中,每个家族以自己族内优秀子嗣的成就为荣,于是,家族名人就成为区域乡贤。“功德言行,荣光乡梓,丰神仁意,山高水长。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 ,乡贤的言行会在乡村中树立忠良典范,可仰耆德,可维风教。宗祠与乡贤联结,形成海南传统特色乡贤文化。琼海马氏在嘉积镇田宛村当地,就以“一处宗祠”与“一座古墓”闻名遐迩,当地马氏以来自族群的民间记忆,共同铸造呈现出当地特色乡贤文化。
一、“一处宗祠”——马氏宗祠
马氏宗祠地处琼海市嘉积镇西北郊田宛村,东接下寨村,西临军屯村,南通万石,北连文田,为海南省东部地区典型传统村落。马氏宗祠就虚掩在田宛村这一片椰林与槟榔林的婆娑阴影里。宗祠规模不大,白色瓷砖装点红墙,墙头饰有苍翠晶莹的黄色琉璃瓦。远远望过去,墙体上密密麻麻都是文字。这种外墙以文字为饰的宗祠修建风格,是琼海地区宗祠建筑外墙的普遍形式。这些描摹或镌刻在外墙上的文字本身并不是为了修饰墙体,文字意不在装饰,而是作为宗族信息传递的媒介,把宗族中相关人士的各类捐赠,或奖励助学人士的姓名以及相应款项,以及宗族中子弟因表现成绩优异,升学被宗族奖励的人员的名字镌刻其上。密密麻麻的署名和记录,是对本宗族子弟功德的认可,更是宗族榜样的竖立过程,是宗族凝聚力的体现。
白墙簇拥之间,为马氏宗祠大门。宗祠大门风格简朴,无铜兽门环,瞪目石狮,但门上对联“世本金陵居国土”一句,蕴含着马氏一宗的富贵之源。马氏通过对联,强调其来源于金陵,把繁华古都意象悬置在偏僻的乡里林间,这无疑极大地烘托出马氏一宗的历史来源和社会地位,此处的马氏确实乃田宛村中的大姓。据田宛村村长马振涛所述,在人民公社时期,“因该村东边是大片田野,村落呈‘凹’字形,像是把这大片田野装在碗中,故名田宛(碗)。田宛村一共有六个生产小队,分别为龙堀水,塘圯,上园村,宛岭村,马路村,莲塘。其中马路村村民全部为马氏,上园、宛岭、马路、莲塘四个村小组村民有一半姓马。”
作为现行行政村——田宛村的村民,马氏一宗普遍不提自己为田宛村人,他们更愿意称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为“马路村”或“瀚苑村”。虽然当前琼海市区域地图没有“马路村或瀚苑村”的标志,但在马氏族人心中,他们马氏宗祠所建造之地,本该命名为“马路村”或“瀚苑村”。而马氏先祖迁居琼海该地居住,原本创建的村庄名为“瀚苑村”。该村源于当时位置显耀,为当时南来北往官道必经之处,所以,又称“马路村”。“马路村”或“瀚苑村”之名与马氏宗祠大门两侧的对联共同告诉了我们马氏一宗在平凡乡里的点滴传奇。
海南马姓同根同源,多为南宋及明初从福建莆田市甘蔗园迁入,在海南马氏分布较广,或务农,或入仕,或为商。而关于田宛村的马氏,据该村马氏长者的口耳相传,其最初乃以仕入该籍。虽无佐证,但在田宛村马氏族群的记忆里,田宛村马氏本为明朝洪武年间惠州知府马志善调任琼州乐会知县之后。海南马姓常在祭祖神龛里立 “扶风堂”牌匾以示族号。“扶风”得名于“扶助京师,以行风化”,本是陕西的一个地名。史载,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因战功显赫被封为“马服君”,其子孙后代改为“马服”,后再改为“马”。而当时马氏多在陕西扶风一带繁衍,有“马氏系承赵奢,望出扶风”一说,是以“扶风”二字为马氏族号。调研中,据田宛村当地马氏后人所录:东汉马伏波将军马援是赵奢的五世后裔,是马姓入琼始祖。其收复岭南及珠崖后,即返回大陆复命,在征战期间曾在海南繁衍生息,留有许多后裔,如马志善(马润通的爷爷),马润通等。其中,马志善曾任广东惠州知府,后来琼任命琼州乐会知县。由于海南地方志和史料记载非常有限,对于田宛村马氏这一说法,笔者及团队人员查阅诸多资料,亦无考据。但作为该地马氏一宗的集体记忆,说法的存在本身就是当地的一个文化印记。1925年法国学者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以社会记忆理论为出发点,从心理学角度审视人类的记忆,研究记忆链条所包含的人类活动意义。“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一既是一种物质现实,比如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 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 。田宛村马氏宗祠,承载着这一宗族的集体记忆,也赋予了宗族特殊的意义与内涵,她就是马氏乡贤文化之源,也是马氏乡贤文化之母,更是马氏乡贤文化承载的核心媒介,是对该村马氏宗族的文化起点的一个永恒界定。
于是,异于周边乡里的马氏宗祠文化被塑造起来。在田宛村马氏 “瀚苑村”之名的感召下,在“金陵”之后与“知县”之后双重不俗身份的影响下,田宛村村民以宗祠为单位,继续推行别于周边村落的宗祠文教,可以说,田宛村马氏的集体记忆为当地马氏宗族的重文教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促成该村形成海南典型村落的乡贤文化现象。
二、“一座古墓”——马国师墓
海南是悬浮海外之域,因之发展滞后,加之人口稀少,以及区域多贫瘠穷困,海南古墓较少。而在琼海,能作为文保单位被圈画出来,加以保护与维护的古墓更是屈指可数,“马国师墓”就是鲜少中之一。马国师墓位于海南省琼海市朝阳镇万泉河渡口北岸。现址可见,陵园有护墙和大门,石阶墓道,黄墙金顶,以坟为中心,墓园向东延迟40米,向西延长10米,向北延长15米,向南延长15米,面积一共约1500平方米。
现修复的马国师墓,大门建于九十年代为石米装饰风格,顶部配以琉璃黄瓦,石米门两侧涂黑漆书两联:“富甲一方重道尊贤与社稷,仁怀天下疏财仗义振朝纲。”该联是对墓主人马国师的缅怀,也是对其功德的评价。大门左边是一尊明代石刻翁仲,虽经500多年风雨冲蚀,卷云图案仍历历在眼。大门右边立一明代圣旨碑,阴刻楷书“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端庄苍劲,整座陵园庄严肃穆。门侧左墙是修建盖墓是的子孙芳名榜,右墙则以志的方式,篆刻马氏宗祠奖学福利基金会于1992年11月31日所拟《国师志》。
陵园内,果树葱郁,南国槟榔硕果累累,在微风中矗立。进入陵园,沿着石阶拾级而上,便到马润通陵墓。墓前立有石笔两条为今人雕刻,原右边石笔已遭毁坏,左边是明代石笔,左边石笔阴刻行书“通义达官思乃师”,古韵盎然;右边石笔阴刻行书“润民慰君心在国”。墓前香炉上香烛犹存,时常有国师后人或其他游客参观前来敬奉凭吊。
据碑文与马氏族谱所记,此处为马氏先贤马润通之墓。碑文所记之马国师之义举,在文献中皆确有考据,“正统八年八月辛亥,……琼州府民马润通、王公逊……各出谷千石有奇,佐官赈济。俱赐敕奖劳,复其家。 (卷107页2903) ” 。马氏先贤一直坚信“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马润通为弘扬马氏一族之瀚苑儒行,也为恩泽于乡里,于是有此佐官赈济的义举,因此被赐为马国师,成为田宛村乡贤的表率,他为马氏乡贤文化又贡献上了浓墨重彩。马国师之古墓,虽与田宛村马氏居处相隔甚远,但此处古迹,确为该村马氏族人的骄傲。因为马氏子嗣的心中清楚,该处古墓中埋葬的马国师,就是自命为“金陵之后”的马氏族人之一,亦为马氏史上有名的马氏乡贤。因此,马国师墓不仅是马嗣之后——乡贤马润通之坟冢,更是马氏乡贤文化推行与维护的一个马氏族群凝聚点。
三、马氏成就田宛村乡贤文化灵魂
田宛村之“马路村”一名,首先是对该村马氏定居选址原由的一个解释。自然,此处的“马路”一词,与当下的“马路”之意无关。当前我们使用的马路概念,是工业革命的一个产品,而此处“马路村”一名,则诠释着马氏选择之地的核心位置与重要位置。这是交通枢纽,亦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枢纽。在这个重要的区位垦荒建设发展的村庄,是一个有灵魂的村庄!在琼海市嘉积镇的田宛村,放眼望去,错乱布局俨然有序,家家户户之间的勾连与谦让,成就了这个村庄的“瀚苑”风采,“瀚苑”——就是田宛村的灵魂。
其一,马氏以“瀚苑”之名,教化宗族子嗣。马氏宗族移居该村落后,在宗祠以“瀚苑”之共名,对宗族开展文教与学养熏陶,子弟多本分躬耕,为商者,多有义举。马国师,就是宗族教育思想孕育的优秀榜样氏族子弟。据《琼海县文物志》与古时的《乐会县志》记载:“马润通,乐会执礼人,明弘治年间,年逢旱灾,庄稼无收,天灾国难,民不聊生,润通慷慨解囊,购米1200石,扶国救民,功高义重,被皇帝予‘义士’称号,润通卒后,帝立旨碑于墓前,‘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内中就提到马国师陵园前“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缘由,即:“明正统八年,由于旱灾降临,庄稼可谓损失惨重,大片田野荒芜,乞丐成群,不少奸商为牟求暴利,趁机屯粮,后猛抬粮食价格。润通见民不聊生,寝食难安,又见奸商趁火打劫,义愤填膺。便毅然购船出海,到邻邦购米1200石运回琼州献给州府赈济灾民。此等义行被上报朝廷后,皇帝龙颜大悦,当即敕旌表褒一道,而后朝廷又调查润通生平,知其素来为人忠厚仁慈,且是仕门后代,不久就召润通进京,敕封国师。由于已年过六旬,次年润通就病逝于京都,享朝廷俸禄不过一年,皇帝心生感慨,便下旨委派明师随棺寻风水地,将马国师灵柩运回琼州安葬,并赐下一块圣旨石碑立于墓前,令凡是路过此地的文武官员都应下马到墓前祭拜。”
这里记载的马国师,就是马氏家族文教和敦化熏陶出来的优秀宗族子弟。虽就其所旌表的事件看来,非如其他地方之乡贤考取科举功名之名声响彻,也不若安邦定国的大将大帅般轰轰烈烈,但马国师的义举,就是普通家族中最真实的骄傲和荣耀,所以,马国师就是马氏宗族的骄傲。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1200石大米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时,马润通能毅然决然地购米赈灾,这是何等的慷慨。正应了那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马氏家谱记载:“马国师,名润通,字仲余,生于明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祖居南京金陵,曾曾祖仲凯任过元朝闽中亚都元帅,曾祖父道训仕任元福建泉州府安溪知县,祖父马志善洪武三年任广东惠州知府,洪武七年调任琼州乐会知县,携家眷定居乐会县上北乡黄锦坡,后移居翰苑村。”由此记载得知,润通一家祖上世代为官,以书香门第之家。他从小就勤读诗书,牢记先辈的教诲,不议是非、乐善好施,素来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凡村里有耕无种者,他给以种,无牛者给以牛,有争斗者,他便登门告诫,无不劝其息仇还其厚德,所以村里的人们对马润通十分尊敬。马润通此等义行就是马氏“瀚苑”乡贤文教的成果,村名“瀚苑”一词是对该村马氏一族重视文教,有树人济世,安邦治国情怀的最好诠释。
其二,马氏以“马国师”之名,形成特色乡贤文化教化“田宛人”。琼海之于中国,若不是近年亚洲博鳌论坛这一盛事,本是名不经传的地方。琼海的嘉积镇并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瑰丽绝伦的秀丽风光,而坐落于琼海市嘉积镇的田宛村,无论在人文上,还是地理,亦无鼎盛的文风与辈出名流。诞生在田宛村这片土地上的,产生深远影响的名人鲜少,且遗留下来的精神及物质文化资源都极有限,因此,“马国师”这一名人文化在琼海,意义显得颇为重要。
马氏族人深知这一点,因此倍为珍惜“马国师”之名。于是以“马国师”之名,感召和团聚家族子弟。据马氏后人介绍,每年冬至,居住在海南各地的马氏子嗣,甚至是远居海外的马氏族人都会来到这里,团聚在园内举行扫祭仪式,将马国师的故事口口相传,望族人能以前人为榜样,在传授子孙知识的同时,不忘品格的培养,正所谓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所以马氏族内很少有为非作歹的恶霸,田宛村中村民之间和睦相处,日常里各自相安无事。
其三,马氏乡贤家学形成自己的宗祠文化圈。宗祠在海南就是一个家族存在的象征,也是在海南村庄中常看见的功能性公共区域。当地人一般把宗祠称祠堂,祖屋是供奉家族祖先,也是进行所有家族重要活动的场所,是一个家族的象征。开支为一叶,万“马”溯此源,马氏宗祠就是田宛村马氏家族最原始的根,也是田宛马氏家族以及其精神、信仰的载体,马氏的乡贤家学以宗祠为重要的传承纽带,在新时代形成特色宗祠乡贤文化圈。
在这个乡贤文化圈中,田宛村马氏有“瀚苑”之名的感召,有不约而同的家族荣誉感,也有基于该荣誉感而形成的凝聚力。虽当前田宛村的马氏家族没在再出高官和名人,但他们珍视自己的乡贤文化资源。据该村村民介绍,当时朝廷亲赐“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圣旨石碑有两尊,一尊置于国师墓前道侧,一尊置于翰苑村(现名为田宛村)坊牌内。后在文革期间,这两块圣旨碑文遭到人为毁坏。其中,在田宛村的圣旨石碑被丢弃到莲塘池里,现仅存石鼓石柱,无法再找回石碑。而在马国师陵园的那尊石碑,则在当时当地的学校建校舍时被当做石材。所幸,后田宛村的马氏后人马振炳和马业权花钱将其从学校“赎”了回来。而修复马国师陵园时,马振炳作为马氏子嗣,又自掏腰包租船,在朝阳至博鳌一带反复搜寻和寻找,最终寻得“圣旨碑”。
其四,马氏乡贤文化在新时代继续发挥教化作用。马氏宗祠曾于解放前办过私塾,当时学生人数有十余位,多为田宛村马嗣子女,但外姓子女也可以来私塾接受教育。据马氏后人所录,族人办学,资费不计,可以大米、番薯代替,也可以银子代替。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马氏的繁华已不再,但围绕着马氏宗祠所形成的乡贤文化圈仍发挥着积极的教化作用。1958年公社化发展过程中,马氏私塾办学被瓦解,大队改建田宛小学(后改名龙堀水小学,离马氏宗祠约二三百米距离)。
当前,虽马氏宗祠已不作为重要的宗族文教场所,但马氏宗祠还是获得了马氏子嗣的捐赠,于1989年在原地上重新翻建。翻建后的马氏宗祠,也以新的方式,继续发挥她在新时代的乡贤教化作用,具有积极的文教意义。与海南其它宗族重文教一样,马氏宗祠非常重视文教,且积极付诸于实践。乡贤文化所铸成的家族荣耀感和区域凝聚力,使田宛村的马氏成立“马氏奖学金福利基金会”。马氏奖学金福利基金会的发动者和创始人是马业东,1990年,在马来西亚经商的马业东参加马氏宗祠重建后的第一个宗祠活动,为鼓励马氏学子读书成才,提议成立该基金会,并带头捐赠二十余万元人民币。当时参加祭祀的马氏子嗣颇为高兴,一致赞同。
现基金会董事长马振炳先生在采访时曾说,“这个基金会是从当初的五元,十元,这样一点一点做大的。那时候大家都辛苦啊,五十元都算很多了。但是我们没有说要放弃,我们就是希望我们马氏学子呢,能够发奋图强,我们就是以这个马氏的奖学金来激励他们,希望他们成才!”海南马氏奖金福利基金会成立后,有来自田宛村的宗族子弟的支持,还有马氏侨胞的赞助,基金会有充足的资金,基金会每年都会协定时间,举行活动,鼓励后代子嗣勤勉学习。自1990以来,共募捐41.5万元,共奖励马氏学子322人,其中不乏有考上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的学子。
四、乡贤文化:区域文化的感召与力量之魂。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提出的重要战略,它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而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发展乡村,建设乡村。在琼海嘉积,都市化和现代化正在推进,乡村改造也在推荐。但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在于一时的政府举措与财政倾斜,而在于深入民心与民情,只有这样,民间才有志参与并坚决参与,才能实现乡村的伟大振兴。
而聚拢乡里民心民情的淳朴核心纽带,就是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高举乡情乡愁旗帜,吸引和凝聚乡村建设力量。由此看来,乡贤无疑是区域文化的感召与力量之魂。田宛村马氏在“瀚苑村”之名的感召下,有“金陵”之后与“知县”之后的身份荣耀,加之再有“马国师”奉旨受封,马氏家族在田宛村的影响非同一般,最终促使形成马氏形成特色宗祠乡贤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里,一方面表现为马氏子嗣在乡贤文化感召下所形成的家族荣誉感,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该荣誉感而形成的凝聚力。他们继续发扬自己的乡贤文化。我国较早研究名人文化的学者沙永胜曾指出名人具有高尚思想道德,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乡贤文化就是区域名人文化的一种显现。当前,乡贤文化作为一个单独的理论范畴,在我国还没有开展系统的研究,但区域乡贤文化的审视在当前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之下,已经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选题和议题。正如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所论述的一样,“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失去它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 而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有引领民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巨大内在力量,也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落细的一股中坚力量,海南琼海马氏宗祠所凝聚形成的乡贤文化圈无疑就是这个选题的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1】李斌,曾羽编.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贵州天柱宗祠文化述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55.
【2】王庆忠主编.长兴家风与乡贤[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
【3】刘亚秋.记忆二重性和社会本体论——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社会理论传统[J] .社会学研究.2017(1):149.
【4】唐启翠辑录点校.明清《实录》中的海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32.
【5】梁鸿.中国在梁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38.
(作者单位:琼台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