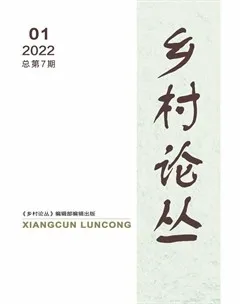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和参与路径研究
摘 要:当前,学界对于“乡贤治村”研究日渐充盈,主要集中在对“新乡贤”的内涵研究以及研究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关系等方面,但是在对乡贤治村过程中如何“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加强。在实践层面,乡贤治村也面临着诸如管理制度、乡贤文化、人才队伍等方面的缺失,亟需重新厘定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角色定位。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收集相关文献集中分析各地乡贤治村的成功经验,挖掘了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做法,为还没有更好开展乡贤治村的地区提供一些理论指导和经验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新乡贤 乡贤治村
当前,在我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新生力量,对推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发展意义深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新乡贤的参与为乡村社会治理水平提升提供了新路径,成为了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的一种有益探索。因此,国家高度重视新乡贤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便将“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纳入“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议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也提到“要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但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也还面临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要实现新乡贤有效融入乡村振兴,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凸显其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价值,以实现助推乡村社会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验证。
一、新乡贤的时代内涵与特征
(一)什么是新乡贤
乡贤者,乡中贤良之士也。在中国传统社会,乡贤多是乡里作风正派、品行端正、德高望重之人,是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随着城市化发展,乡村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乡贤日渐式微。尽管如此,乡贤文化依然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乡贤也被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也就是“新乡贤”。
目前,对于何谓“新乡贤”还没有形成确切的定义。2017年12月,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以“新乡贤与新农村发展新动能”作为论坛主题,并把“新乡贤”定义为“心系乡土、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一般包括乡镇经济能人、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财富、权力、声望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公益性是其精神内心”。因此,新乡贤应具备以下要素:其一,个人能力强,且有一定社会影响;其二,拥有资源或资本,具备回馈乡村的物质或经济基础;其三,有公益心,愿意为公众事务付出,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其四,有良好的个人品性和道德声誉,能起到行为示范作用。
(二)新乡贤的特征
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的继承和发展,其具有传统乡贤的一般特征,也具有富有时代内涵的崭新特征。一方面,新乡贤与传统乡贤一样与在乡村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热心村务、乐于付出的公益情怀。另一方面,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又具有一定区别,主要表现为,一是新乡贤则的身份范围更加广泛,传统乡贤主要为乡村在地致知识分子、家族长辈等群体,而新乡贤还包括离乡的企业家、学者、华人华侨等社会精英。二是新乡贤具有平民化特征,传统乡贤更加注重其家庭背景和政治地位,而新乡贤则注重其为乡村服务的热情和能力,对身份属性没有过多要求。三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形式更加多元,传统乡贤主要以在地施以政治影响为主要方式,而新乡贤可以通过捐资助学、带头致富、文化宣传等形式助力乡村发展。
二、新乡贤何以能够参与乡村治理
(一)历史传统和时代发展的选择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农耕文化深植社会方方面面,使得长期以来乡贤就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在乡村重28221ff3e10eeb148d6dad5d4c95baba大事项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要实现乡村的和谐稳定必须依靠乡贤力量。新时期,虽然我国国情和乡村基本情况取得了重大变革,但是乡村治理思维在一定层度上依旧呈现出沿袭传统治理逻辑的态势,乡贤文化也还深植于乡村社会,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得以保留。同时,历史的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满足了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需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乡村社会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社会发展促使乡村社会不得不紧跟时代发展需求,但又因为城镇化进程造成乡村本土人才大量流失,使得乡村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面临巨大的人才需求,内生需求呼唤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以此助力乡村社会进步。
(二)乡贤治村供需匹配合力的形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必备条件是新乡贤资源与乡村发展需求之间形成高度的供需匹配合力,新时期,在乡村人才需求扩大的同时,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供给力也显著增强。在供给上,随着社会进步,乡村人才的发展路径日趋多元化,相应的也带来新乡贤群体供给力增强,在乡村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的基础上,大量乡村能人在政治领域、商业领域、文化领域取得了良好的个人成就,而传统乡土情结的驱使下,这些能人具有强烈的参与家乡建设的内生动力;同时,他们熟悉家乡的治理格局和风土人情,能够快速融入乡村治理进程当中,进一步促使了他们加快回归乡村。在需求层面,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外来治理力量,乡村社会对新乡贤的接纳度更高,其原因在于,中国乡村沿袭了熟人社会的传统习俗,村民对本地能人的信任感和认可度更高,并且具有强烈的意愿让新乡贤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参与乡村治理,促进村庄治理水平和村民生活水平改善。
(三)社会精神文明进步的驱动
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价值追求也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社会精神文明取得快速进步,志愿服务理念、共同富裕思想深植人民的内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来自乡村社会的能人在自身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之后,他们渴望找到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途径,渴望通过一定的形式回馈社会发展、服务社会进步,而乡贤治村则为其提供了便捷有效的实现途径。最后,在精神驱动和路径优势的助推下,新乡贤希望也能够参与乡村治理,通过贡献自身力量帮助家乡建设,带动乡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一)政治功能
在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因此,乡村成为了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系统,使得乡村社会长期存在自治意识薄弱、自治能力不强等问题,乡村治理继续寻求新的实践路径。新乡贤作为乡村能人,在乡村政治领域具有良好的参政能力和群众基础,能与村民形成良性互动。一是新乡贤能够成为村两委干部或者参与乡村民主议事中的党员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发挥参政议政功能及政治监督功能。二是新乡贤通过参与乡村恳谈活动,发挥出桥梁纽带作用和社会沟通功能。三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民事的调解,发挥社会矛盾协调功能和社会和谐促进作用。通过以上方式,新乡贤能够在村民内部治理中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带动全村参与自治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强化乡村治理的内生性秩序基础,弥补农村居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不足,强化村民自治形态,提高乡村治理的效果。
(二)经济功能
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幸福,但乡村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缺失制约了乡村经济发展。新乡贤通过发挥自身在资源聚集与扩散上的优势,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产要素,能够在招商引资、技术更新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特别是通过发展合作经济能够有效帮助村民实现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快速提升,帮助村民利用当地地理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电商经营、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帮助乡村经济实现转型发展,带动农村整体经济实体提升和农民富裕。
(三)文化功能
我国农村正处于转型阶段,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开始打破,在此背景下,乡村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逐渐走向式微。重塑乡村道德规范,促进优秀乡土文化发展,加快乡村乡风文明建设成为了当务之急。新乡贤回流乡村,可以充分结合自身特点,通过融合现代社会主流精神价值,将乡村传统文化进行重塑,发挥培育思想道德、宣传主流价值等文化建设作用,加快弘扬和继承乡村优秀文化传统。新乡贤也可以借助其资源优势,以资源投入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和文化建设活动,带动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推动乡村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普遍形成和集体认同感的有效增强,切实促进乡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四)社会功能
我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社会问题的化解不能盲目采用现代城市治理的惯性方式。在乡村出现社会矛盾时,怎样才能快速响应、化解危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而在这方面新乡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乡村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矛盾高发领域,新乡贤,特别是在场型和平民型乡贤能够凭借良好的社会声望和高度的村民融合优势,调动各方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发挥社会问题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村民之间、官民之间的充分沟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五)资源功能
目前,我国城乡发展还不协调,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还存在众多问题,但由于社会资源的紧缺性,导致政府力量很难独自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在村民自治制度下,农村地区很难充分调动组织和财政资源来助推自身发展,乡村公共品的供给普遍缺失,乡村发展资源缺失困境长期存在。新乡贤是乡村群体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体,他们能够通过利用自身经济、人脉、管理能力,为乡村社会带来新的资源优势,帮助解决乡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提升了乡村公共品的供给能力,加快乡村公共服务水平。
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
(一)管理机制缺失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部分地区存在传统乡绅变质或被“劣绅”取代,乡贤治村演变成了恶霸治村、劣绅管村的现实。新时期,我国广泛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但是乡贤参与制度还不完善,乡贤治村管理机制还相对缺失,因此部分地区依旧存在村霸劣绅现象。同时,在部分地区为了追求村民自治的形式创新,将乡贤治村变成了生搬硬造的的政治任务,在参与机制设计、参与人员选择等方面走过场、搞形式,导致缺乏能力、品德的人员充当着新乡贤的身份,对乡村治理能力提升起到阻碍作用。
(二)新乡贤文化缺失
当前,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着文化缺失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相关主体没有形成乡贤治村意识。在政府层面,存在某些地方政府对乡贤存在认知偏见,在制度层面对于乡贤参与村务治理还存在壁垒;在新乡贤层面,部分新乡贤在参与乡村事务过程中还存在地方豪强思维和求名图利的现象;在村民层面,部分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不足,担心新乡贤在乡村事务参与过程中损害自身利益。新乡贤文化的缺失导致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路径还存在较大问题。
(三)人才队伍缺失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城市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吸引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定居城市,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人才流失让农村难以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乡贤群体;加之,在地乡贤的个人能力相对有限,在实际参与乡村治理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同时,由于缺乏对乡贤的有效管理,造成在地乡贤对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很难将个人能力转化为为乡村公共事业服务的行动。因此,乡贤治村面临着严峻的人才队伍缺失困境,难以形成普遍参与、行之有效的乡贤治村格局。
(四)资金支持缺失
乡村社会发展离不开资金投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才能实现其功能价值的有效发挥,但是由于乡村处于治理结构最末端,乡村自给自足获取公共资金收入的来源有限,而政府对乡村公共资金的投入也相对缺乏,导致在乡村在乡贤文化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产业发展等方面与乡贤治村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乡贤难以在乡村发展过程中有效将自身资源优势与乡村发展优势相结合,乡贤治村效能无法充分释放。
五、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困境的化解路径
(一)建立新乡贤管理制度
实现新乡贤更加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关键在于要有科学合理的长效管理机制保障。因地制宜视角。首要,应该制定乡贤评定和进入标准,从个人能力、社会名誉、道德品质、参与意愿等各方面制定出相应标准,避免出现少数人员以乡贤之名行劣绅之事,保障新乡贤群体的代表性、服务性、公益性。其次,要建立有效的参与平台,通过建立乡贤理事会等创新性平台,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便利的参与路径,同时借助平台将新乡贤的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协同参与将新乡贤的个人能力形成合力,共同助理乡村振兴。再次,要确保依法参与,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合理划清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参与范围和参与层度,避免乡贤治村对村民自治权利的损害,以乡贤治村来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和水平。最后,要强化监督机制,有效防范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能造成的基层治理权力滥用,要畅通和完善村民的监督渠道以及村两委的监督机制,以有效的监督规制新乡贤的行为规范,保证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公正与透明。
(二)培育新乡贤文化氛围
形成良好的新乡贤文化氛围对化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困境十分有益,因此,加快培育新乡贤文化变得十分必要。培育新乡贤文化,要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德治、礼治与自治的主体与引领作用。一是要引导树立乡贤光荣的社会氛围,要大力倡导培育新乡贤文化的自觉性,引导社会公众广泛认同和尊重新乡贤,营造出“知乡贤、学乡贤、为乡贤”的浓郁氛围。二是要引导培育乡贤治村的良好氛围,积极引导有能力、有品德的乡村能人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当中,对要乡村发展具有突出贡献的新乡贤进行表彰和宣传;三是,要着力挖掘文化资源,要通过历史文献、贤人故居等乡贤文化载体大力弘扬传统乡贤文化,同时,要通过“乡贤长廊”等载体树立一批具有教育示范意义的当代新乡贤代表人物。
(三)培育新乡贤人才资源
要形成新乡贤广泛参与乡村治理的格局,根本在于要形成一个能力强、德行好、规模大的新乡贤群体,因此,要加快培育一批有意愿、能胜任的新乡贤群体。首先,要培养优秀人才的乡村认同,通过宣传乡村社会的新变化、新成果激发优秀人才的乡愁乡情,促使其愿意回到乡村、愿意投身到乡村建设之中。其次,要加强政策激励,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吸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秀人才回归乡村或者投身乡村建设,引导他们通过回乡创业、投资兴业、文化宣传等方式参与乡村治理,融入乡村生活,逐渐培养他们成为新乡贤。最后,要强化对新乡贤的人才管理,要对新乡贤资料信息进行入库管理,形成有效的联络机制,及时了解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摸清新乡贤的需求,帮助新乡贤更好参与乡村治理事务。
(四)做好资金投入保障
资金支持是维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必要保障,充足的资金投入能够帮组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充分结合自身优势发挥能动作用,助理乡村发展。一方面,要调动各方力量,保障资金来源,通过强化政府财政投入、乡村本地的村民集资、新乡贤捐资等方式,多渠道满足资金需求。另一方,要形成科学的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通过专人负责、有效监督、及时公开等方式,促进公共资金的公平、合理使用;同时通过专款专用制度、减少行政审批手续等方式加快满足乡村治理所需资金及时有效到账,促进乡村治理事务高效完成。另外,要加大对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为优秀人才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以此吸引优秀人才回乡。
参考文献
[1]叶修政,曾起郁.乡村振兴视域下新时代乡贤治理的实现路径[J].台湾农业探索,2019(03):58-61.
[2]高万芹.乡村振兴进程中新乡贤的类型界定、功能实践与阻力机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21(05):87-95.
[3]蔡禾,胡慧,周兆安.乡贤理事会:村庄社会治理的新探索——来自粤西Y市D村的地方经验[J].学海,2016(03):46-54.
[4]段妍智,董嫚嫚.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研究评述[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01):33-35.
[5]赵亚楠.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研究述评[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39(07):8-14.
[6]付秋梅.乡村振兴视域下乡贤回归的价值与模式研究[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06):126-128.
[7]陈彬璐.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温州市为例[J].科技视界,2019(34):271-272.
[8]万渠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困境及其突破路径[J].大众文艺,2019(19):30-31.
[9]王亚民.现代乡贤文化的认同、培育与乡村振兴[J].晋阳学刊,2019(06):110-115.
[10]王生章,崔佳慧.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治理创新刍议——基于新乡贤地方治理的实践经验[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4):45-50.
[11]卢志朋,陈新.乡贤理事会:乡村治理模式的新探索——以广东云浮、浙江德清为例的比较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20(02):96-102.
[12]本报评论员. 着力提高地方治理效能[N]. 青海日报,2019-12-30(001).
[13]廖彩荣,陈美球.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7,16(06):795-802.
[14]王亚华,苏毅清.乡村振兴——中国农村发展新战略[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6):49-55.
[15]肖唐镖.近十年我国乡村治理的观察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06):1-11.
[16]车洪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17(13):77+80.
[18]郑运祥. 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N]. 安康日报,2019-12-30(002).
[19]陈彬璐.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温州市为例[J].科技视界,2019(34):271-272.
[20]朱光阳. 乡村治理需要乡贤更多参与[N]. 重庆日报,2019-12-04(010).
[21] 赵浩.“乡贤 ”的伦理精神及其向当代“新乡贤 ”的转变轨迹[J],云南社会科学.2016 年第5期
[22]裘斌.“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发展走向,甘肃社会科学2016 年第2期
[23]白现军,张长立.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11期。
[24]李利宏,杨素珍.乡村治理现代化视阈中传统治理资源重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8期
[25]张露露,任中平.乡村治理视阈下现代乡贤培育和发展探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8期
[26]徐晓全:《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 年第4期
[27]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 、作用与偏误规避,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
[28]万渠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困境及其突破路径[J].大众文艺,2019(19):30-31.
[29]付秋梅.乡村振兴视域下乡贤回归的价值与模式研究[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06):126-128.
[30]吴晓燕,赵普兵.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J].理论探讨,2019(04):158-164.
[31]莫申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24):167-168.
[32]李韬.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村庄结构性分化困境及其化解路径[J].社会主义研究,2019(06):133-140.
[33]王彩霞,王培培.新乡贤:角色期待、实践要求与培育路径[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4):51-63.
[34]张兴宇,季中扬.新乡贤: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与身份界定[J].江苏社会科学,2020(02):156-165+243-244.
[35]吴蓉,施国庆,江天河.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治村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J].宁夏社会科学,2019(03):130-138.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