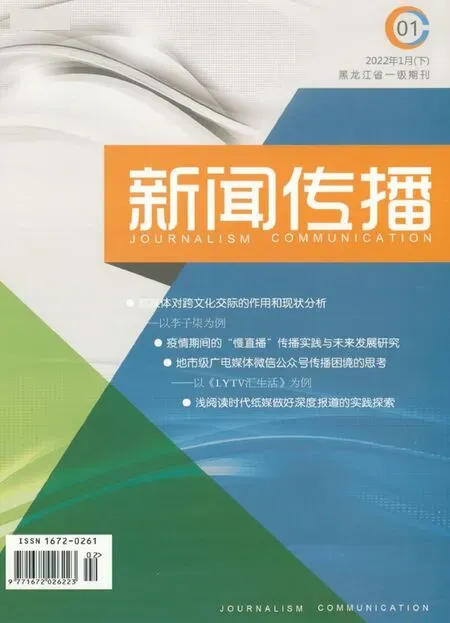商业电影运作中的粉丝式参与文化
高泽宇
(山西大学新闻学院 太原 030006)
一、形式与内涵:跨媒介叙事、参与式文化、粉丝文化
(一)跨媒体叙事
跨媒体叙事鼓励消费者加入协作叙事成为故事世界的参与者。它并非是同一文本的不同媒体“改编”,而是一个丰富的经过设计的“故事世界”,将故事的不同部分与线索散布于多种媒体平台中,等待着参与者将之串起。
这些平台既包括一些传统的线下平台,如书籍、漫画、主题乐园、影片取景地等等,也包含电影、游戏等现代数码媒体,任意一个媒体平台都可以成为这一系列产品的进入点。影视作品的观众们,最初可能从各种不同的媒介进入到故事世界中,而非局限于通过观看电影来成为参与者。这些不同的媒体平台共享着一个主题、一个背景、一个世界观乃至一个故事,却都只能从中看到故事的一角。
(二)参与式文化
参与式文化是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一书中所提出的,脱胎于“文化消费主义”,在早期有着草根文化面对传统文化工业抗争意味的名词。之后在《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一书中变为“邀请粉丝和其他消费者积极参与到新内容的创作和传播中来的文化”[1]。此时的参与式文化,是依托于新型网络社交媒介,通过粉丝间社群关系所建立的集体智慧。
可以看到,在跨媒介跨平台的叙事方法中,没有参与式文化就无法产生将不同平台的故事碎片串联起来的可能。在这不可见的“合作”中,创作者只负责在不同的媒体文本中留下线索,而受众在探索过程中将这些线索串联成为创作者心中的世界全貌。也正是在这样的探索串联中,故事文本被不断丰富,成为正如詹金斯所言的参与的力量。使来自改写、修改、补充、拓展的不同思路,赋予文本更广泛的多样性观点,然后再进行传播,将之反馈到主流媒体中。在这一正一反的双向补充中,叙事者和参与者缺一不可。
(三)粉丝文化
关于粉丝文化的讨论从早期对于书籍文本的爱好者划分就已开始,法国当代思想家米歇尔·德赛都认为,读者是游离于不同文本之中,对文本意义与自身体验相结合,挪用文本内容以获取新的意义的群体。而自称为“粉丝型学者”的詹金斯,既继承了德赛都的粉丝文化研究,并深受约翰·费斯克的影响,尝试建立一种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一书中认为,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受众以被动接受的定位,粉丝消费者是在不断“闯入”文本生产者所设立的文化禁区,并不断从中挪用对其有用的部分,再结合个人的喜好进行加工的群体。粉丝并非传统意义上可控、易控、缺乏思想的个体,而是一个呈现主动性、具有自身思考、能够积极消费的良性群体。参与式文化的语境之下,粉丝保持着与官方传播内容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粉丝使用自己对官方文本意义的解读,使其能指产生新的意涵,进而产生对官方文本的意义重组。
二、群体的狂欢仪式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仪式化特征存在于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当中,而这些文化形式中存在的仪式行为往往会表现为群体参与的狂欢。在粉丝们的“草根”文化无法与阶级固化的商业文化相接触时,参与式文化无疑给了粉丝群体一个集体参与的机会,无论是弹幕、评论类的即时参与,还是改编、鬼畜或同人类的创作参与,这一多平台文化仪式所提供的情感宣泄和身份认同才是粉丝们能够对参与创作乐此不疲的真正源泉。
(一)多平台带来的叙事变化
当今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互联网社交平台、内容平台乃至线下数字技术的井喷式增长,不仅使官方文本有了更加多样的传播渠道,更加广泛快捷地实现跨媒介叙事。同时使得粉丝文化得以有更加完善多元的表现形式,各类文化作品受众有了更多发声的途径和方法。因此新媒体时代的粉丝受众,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被发声渠道所桎梏,能够使用触手可得、制作简单的传播媒介在对文化产品的解读中展现更加多样化的参与行为。
拿星球大战系列举例,从1977年的第一部《星球大战:新希望》,到2019年的《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除了制片公司众多官方渠道(如电影、漫画、小说、动画、电视连续剧、周边产品等)的宣传之外,粉丝们也在利用着多样的平台进行自己的群体娱乐。无论是视频网站、同人小说、线上社交还是线下星战迷聚会,这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粉丝行为,才是让“星球大战”成为一个普遍知识的主要推动者。
(二)粉丝的情感宣泄
粉丝在作为一个参与式文化群体时,其集体组成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弱关系连结,并不是生活所必需的基础关系。但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个体来说,情感宣泄这一对自身状态的疏解却是必要的。因而在粉丝的参与活动之中,媒介文化所建构的空间成为了情感消费的场域,并从受众情感需求的角度出发,就相关文化产品进行制造与传播。
詹金斯在其早期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中,将粉丝行为的成因归结为对相应文化的迷恋及挫败感。“迷恋”显然主要是出于对文本主体叙事的喜爱,而“挫败感”也正是对于文本主体的失望或不满所带来的参与欲望,情感需求使得受众从被动的接收者变为了主动的创作者。因此可以发现,在粉丝参与式文化中,情感消费是其主要动力。
(三)个体与群体性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在现有研究中主要指主体对于自身的认知和描述,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下,可以被解释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社会身份的认同两方面。自我身份是社会身份构成的基础,社会身份则是自我身份的补充,两者共同组成了主体本身的认知。而如蔡骥所认为的,粉丝在参与创造媒介内容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于这一文化群体的归属感以及造物主式的创造快感[2]。他们在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加深了彼此间的情感联系,既通过创造实现了自我身份的建构,也在产生了群体归属感时达成了社会身份认同。
粉丝对于媒体文化的接受不可能也不会在完全孤立中进行,而是一个连结的过程。无论是官方文本的变化还是其他粉丝的活动产物,都会对一个粉丝对其的接受度进行改变,还有一部分则是由在社会文化社群内互动的欲望所驱动的。同时在粉丝群体之中,无论发布者现实当中的身份如何,对圈内文化内容长期稳定的输出就可以在粉丝群中获得一定地位,成为意见领袖。甚至会被内容版权方关注乃至嘉奖,这不仅是对创作者个人的鼓励指导,同时也是对这一创作模式树立榜样,对这一粉丝群体进行着“官方”维系。这使粉丝对自我价值会产生更高的判断,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也会借由所参与文化文本的关联而更加清晰。
三、新模式所诞生的“新商业电影
约翰·费斯克将粉丝文化称作“影子文化经济”[3],它不是本体文化的延续,而是其对应在自由创作领域的“影子”。它与文化工业有着对照性的相似之处,但却完全脱离文化工业,二者成为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在这种新的“共生”模式之下,“新商业电影”也随之适应演化而来。
首先是粉丝参与式文化造就了大量且繁杂的细节,许多甚至是商业文本自身都未曾考虑的。因为粉丝们的参与形式并不存在以往文化创作的高门槛,而是处于随意化、个人化制作特点明显的层级。其内容一部分基于粉丝对社群的关注而表现出高度的专业化,另一部分则因粉丝社群的庞杂而表现出极高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一包容开放的特性在商业电影系列的宣发之中就成为了极为重要的补充部分,《哈里波特》在原书作者J.K.罗琳完成原作的七部曲之后,书籍的读者以及华纳公司所拍摄的电影观众们成就了《哈利波特》庞大的粉丝社群,而这一庞大的社群规模也直接导致了衍生粉丝作品的数量庞大。超出书中本有的英国魔法世界,囊括全球的魔法世界观被架构起来。
同时粉丝参与式文化强调社区及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相较于传统自上而下的传播网络以及以市场为主要考虑因素的商业传播模式,参与式文化更有可能成为社会底层以及被忽略声音的发声通道。当对一文化内容的参与权被赋予这些社区成员时,发表意见和观点的话语权也同时转移到了他们身上。拿漫威来举例,部分在粉丝群体中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内容生产者,在一些活动中被授权进入漫威官方的测评环节甚至创作机构,直接参与作品的修改创作。
粉丝参与式文化所带来的独特符号化特征,使“新商业电影”的另一大特征体现为刻意塑造的符号化信息。符号化所产生的社会认同,特别是在文化的某一参与创造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符号,既能简化信息的传播,又很容易成为某一粉丝圈的群体认同标志。一些电影中的标识符号,已经成为了对应粉丝的群体暗语,在粉丝交流中成为了心照不宣的意会与幽默,粉丝们可以轻易通过这些符号辨认出相同的爱好者。这些符号有可能是缩写、代称,也有可能是某句经典台词等。而一个特殊的表现方式则是“彩蛋谜题”,在一些影片中,彩蛋犹如一种福利,“隐藏”在影片结尾的字幕表后,既像预告式的提前放送,又如同一种对坚持到片尾的观众感谢。而在一些影片之中,彩蛋更像某种谜题,当熟悉影片文本的粉丝发现彩蛋时,犹如一场属于爱好者的狂欢。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接受了相同知识的粉丝获得了一个共同的附加乐趣。彩蛋俨然成为了认真观看影片及在此前成为某一领域粉丝群体的奖励,这种心照不宣促使已经身处社群之中的粉丝深受激励,也促使初阶观众受探索彩蛋出处的欲望驱动而观看了更多的相关作品,与之相关的参与式文化也得以随之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