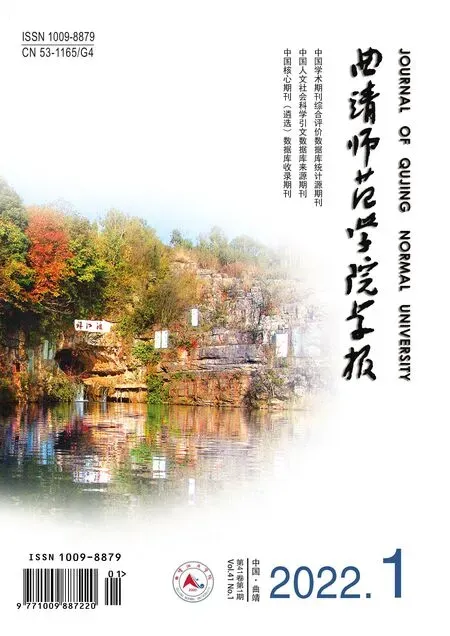文化与旅游融合下民族村落文化空间的重构
——以德宏州盈江县下勐劈傈僳族村为例
尹 敏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研处,云南 芒市 678400)
村落是村民生产生活的空间场所,承载着历史与现在,空间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产物,服务于思想和行动的工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中,文化空间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文化空间被认为是具有核心象征,体现意义、价值的场所、场景、景观,由场所与意义符号,价值载体共同组成。[1]集中展现着地域文化,容纳所有文化活动、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包括节庆活动、社会公共文化活动、文化氛围、符号、文化景观和文化设施等等,体现着民族的共同记忆与情感,联结着过去与未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民族村落的文化空间,就应该是兼具时空要素、物质与精神、民族性与普适性的复合。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使得农耕文明下的民族村落既可以是本地纪念主义演绎传统、传承民族文化、保留文化记忆及乡愁的平台,同时在旅游产业的升级中寻求与文化的结合,在文化旅游融合的市场需求和政策驱动下,也可以被视作为吸引游客关注而打造的被建构的“场所”,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是以文化资源为经济发展要素驱动村落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的重组,这必然伴随着村落文化空间的重构。
一、文化旅游发展中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空间的生境
“在现代化时空压缩背景下,大量村落正在遭遇空间清洗和重构,不仅改变了村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也改变了村落空间本身的内涵与品质。”[2]民族村落在全球化浪潮下,一方面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中,政策与经济的外部动力驱动乡村振兴与村民参与生产服务的内部动力驱动文化自信,尤其旅游产业的升级中市场对“另类文化”的需求,为重新发现与发掘乡村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价值,并重构乡村文化空间提供了机遇与条件;另一发面,在进入以资本为逻辑的市场体系之中,村落文化空间的重构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一)文化旅游驱动下民族村落文化空间重构的机遇
目前,西部地区仍有大部分村落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加之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在语言沟通上的制约及信息上的闭塞,被置于边缘位置,脱贫与发展仍是走不出的困局。其中物质的匮乏、劳动力的外流、主流文化的冲击也使得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传统民族文化内容、形式在缩减,文化功能在变迁,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空间逐渐式微。
文旅融合旨在寻求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产品的内容与形式,不仅是特色文化的展示与体验,而且将其文化内涵及其品牌符号附着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其他旅游产品上,提高其附加值,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而旅游产业带来的庞大外部消费市场,让被大众逐渐漠视的传统文化和被边缘的民族文化重回资本的视野,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城市对人的“异化”下,使乡村文化、民族文化等散发“异质气息”的文化尤其具有吸引力。对自然生态的追求、闲适乡土生活的向往和异域民族风情的猎奇使民族村落成为吸引游客目光的旅游目的地,各方利益主体纷纷着眼于其中的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活跃文化空间,活化传统民族文化向旅游产品的开发转化。
下勐劈村位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苏典傈僳族乡,全村57户,243人,是纯傈僳族的村寨。傈僳族拥有自己语言及文字,下勐劈村村名为傈僳语音译,就区位而言,距县城较远,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差,在开发前鲜为人知,到村寨来的外人寥寥无几,村中尚有部分不通汉语的老年人,文化差异较大,沟通存在一定问题。2014年盈江“5·24”“5·30”两次地震中,下勐劈村为严重受灾区,在实施灾后重建时,由于距离高山草甸景区诗蜜娃底较近,初期在政府主导下将下勐劈村的扶贫建设发展定位在乡村旅游上,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特色的傈僳文化,融合自然与人文,在下勐劈村打造集合自然生态、乡土风貌和民族文化于一体的乡村文化旅游村落。
在建设中以满足旅游服务的标准进行了村寨的统一规划,对进村交通、寨内道路、饮水工程、电力通讯等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建设及修缮;对村寨整体文化空间内大部分的物质载体进行重新修建,如阔时文化广场、文化传习馆、观景台、寨门、图腾雕塑等公共活动场所及公共艺术的打造,对村寨景观结合现代设计进行美化,全村改建民居,统一为突出民族标志性元素的“传统”木楞房。随后村小组自发建立乡村旅游合作社,统筹村落资源及资本,开设40家“牛棚客栈”由村集体设立服务总台统一管理,每年向参与的村民分成;村民将自家房屋收整打造农家客栈对外营业;村中开有3家农家乐,三种形式的经营上村民有较高的自主权。
文旅融合的大趋势下,为文化资源丰富的民族村落发展提供一个契机,通过有意或无意地重塑村落文化空间,以特色文化为旅游的竞争优势,强调以自身文化资源禀赋为依托,发挥地方特色,实现文化资源在地性的转化,激发文化传承的活力,实现村落传统民族文化的生产性保护,这也成为推动民族村落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二)民族村落文化空间重构中各方利益群体的博弈
民族村落的文化本质上还是乡村文化,它附着在乡土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民族传统之上,而今天又受到来自于外部的政府基层治理以及现代消费从消费方式到审美、需求等的影响。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力量上,民族村落及其主体往往处于弱势,现代主流文化的强势进入,民族村落自身的价值体系必然会受到冲击,这将直接体现在传统与现代对文化空间的争夺上,因为“社会空间不再是被动的地理环境,不是空洞的几何环境或同质的、完全客观的空间,而是一种具有工具性的、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种类的商品生产。空间成为消费行为的发源地,是大众媒介和国家权力等社会关系的生成物。对空间生产的规划和控制就等于控制了生产的群体并进而控制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3]文化空间亦然如此,各方利益主体将文化空间视为工具,在文化旅游的规划与开发中谋求各自的利益。
民族村落文化空间的重构,从民族村落的主体上来看,一方面,是本地村民追求现代社会生活生产方式而进行的自我调适,是内部的自省和价值观的转变;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对现代社会文化消费的迎合,通过文化空间的重构,在文化旅游的竞争中获益。这其中是自下而上的自主地“自我异化”,也是自上而下,在政治力量与市场需求面前按照来自强势的持有主流文化的他人的期待和想象来塑造自我形象和文化表达,在主流文化和消费市场的强势裹挟下,村落乡村文化民族文化主体的自主表达话语权事实上是被挤压,例如下勐劈村当地的阔时节主办权在政府手中,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节庆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而村民只是在参与的边缘。
下勐劈村在进行旅游开发前,相对闭塞,且村民缺乏发展的自觉性,民族乡土文化保存较完整,村落的文化空间基本服务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对外交流和通讯带来现代文化对村民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文化核心依然是传统文化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念。下勐劈村的开发是由政府主导的,前期建设经费由政府各个部门筹措,重构村落的决策权、建设的主导权都在于政府。在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力之下,政府作为权力主体的“他者”,有其自身的动机,通过文化空间的营造来强化特色的民族文化,发展村落,以期从中获得政治成就及实现对民族的文化治理。而政府在进入另一个文化体系下去规划和设计时必定会对本地“我者”的文化进行解读和重构,在规划、设计和创作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下会呈现出与“我者”的文化有一定差异文化景观。重塑的文化空间其服务重心被发展村落所取代,传统文化的展示放在了活态传承之前。
在文化旅游中市场需求不可避免地左右着文化空间的重构,在文化空间中呈现出消费主义特征,全部的日常文化生活的呈现为实现消费而服务,市场主体在文化空间的重构中将消费隐含于其中,扩展消费空间,谋求资本的增值。当消费与资本成为文化空间运行的逻辑之时,传统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将会在消费中被割裂,标准化、同质化的生产亦会对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压制。原有支撑文化空间的价值体系被资本解构之后,生活在其中的村民在面对自我文化的传承时可能会在资本下妥协或是形成冲突。
二、文化与旅游融合下民族村落文化空间的嬗变
“任何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特有的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的产生”。[4]文化旅游产业是第三产业,当它成为村落发展的支柱时,将意味着单纯的农业生产比重会下降,而更多的是以观赏、体验等形式,附在文化旅游之上。例如下勐劈村打造民族节庆、文化景观吸引游客,村民开设农家旅社、农家乐餐馆以及销售刺竹笋、草果、杨梅酱等生态产品,农业种植设计为农业景观,泥鳅养殖同时打造亲子体验摸泥鳅项目等等,这些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村民的生计方式在转变,但离土不离乡。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文化空间产生了新的诉求,重塑的文化空间在状态上、功能上、主体上发生着改变,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文化旅游发展下被调适的民族村落文化空间
1.状态上从相对封闭的内在空间向开放流动空间的转变。乡土社会延续下来的封闭和稳定性,使得民族村落传统文化能完整留存至今。在历史上文化空间自身也在不断地演变,但随着文化旅游市场挺进,在其带来的巨大外部市场和观念改变下,封闭性被打破,民族村落从世代相传相对稳定封闭的空间转变为在经济驱动下流动开放的空间,快速地实现从生产生活空间到商业空间的转换,文化空间的重构在其中急剧地发生,而文化空间的演变从传统驱动转向了政策和外部经济驱动。
传统社会中民族村落的文化空间亦是封闭性的,且带有强烈民族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排外的,但是在文化旅游发展中游客是具有快速流动性的,村落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公共文化空间,从民族领域向公共领域变化,使文化空间不再只是被它与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所界定,同时还被它与游客及游客带来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所界定。
例如节事活动,传统社会下民族村落的各项节事活动往往在村落内部自发举行,但在文化旅游中,节事活动成为重要的开发内容对外呈现。阔时节是傈僳族的传统节日,下勐劈村过阔时节从过去村民自发举行庆祝,到现在政府主导举办,主办权移交到拥有政治话语权的政府之后,对节庆的宣传和影响起到扩大的作用,政府还固定在国庆节期间举办乡村音乐节,文化空间得以扩展,多样的活动形式和节日氛围能吸引游客快速地进入村落参与到其中,在体验中了解进而成为傈僳族文化的传播者,使得原本封闭的文化能向外传播。同时在村落中建设文化场馆并对外开放,游客能在有限的时间,快速的了解傈僳族文化,进而在游览中观察到每家每户的火塘、穿着傈僳传统服饰的村民劳作生活等等这样的村落景观及村民日常生活场景时能加深体会,使得整个村落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展示、学习、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公共文化空间。
2.功能上从自我服务向对外文化展示及消费服务的转变。传统的文化空间本身具有强化认同、传承文化的功能,在文化空间下塑造集体记忆,通过娱乐、教育、习俗来承袭传统民族文化,塑造民族审美和共同民族心理,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调节社会稳定,这些功能都是为自我的文化、民族和地区发展而服务的。而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下,民族村落除了是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空间之外,还成为了旅游观光、文化体验和食宿消费的场所,于是村落的文化空间成为了集合本村村民和外来游客的宗教祭祀空间、民族文化娱乐与传习空间、文化展演空间、消费文化空间的复合体。这时民族村落的文化空间也逐渐转向了为展示特色文化以及促进文化消费而服务的空间。
村落文化空间在对外展示时本身也成为旅游产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被消费消解。“新米节”“刀杆节”“火把节”“收获节”“澡塘会”“拉歌节”“射弩会”等傈僳族传统节庆,在旅游开发中成为旅游产品中展示和体验的重要内容,宗教、歌舞、民俗等民族文化甚至会与割裂成碎片集中到阔时节等这样的大型节庆中进行展示展演。如刀杆节中“上刀山、下火海”的习俗,其活动本身是生活在高山之上的傈僳族,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培养的英勇不屈民族性格在仪式上的行为投射,而在表演之前的准备仪式是在传承和追忆傈僳族的历史记忆,但文化旅游市场需求下割裂的“上刀山下火海”表演,削弱了表演前的文化内涵的表达,宗教性减弱,着重“上刀山下火海”本身的展现,展演性和娱乐性增强,成为了招揽游客的工具。下勐劈村民组建了傈僳族歌舞文艺队,为游客歌舞表演,傈僳族群体性、自娱性的舞蹈,也成为吸引游客参与狂欢的体验项目。
3.文化空间主体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民族村落开发发展文化旅游,意味着将有各种身份的“他者”进入到村落,对村落文化空间产生组织配置和规制作用,而开发主体的多元化,也会使基于不同社会背景和立场的主体,对村落的文化空间的重构进行多样化的表达和认同。
在乡土社会,民族村寨的文化空间主体往往是本地村民,其中活跃者往往是本民族的村民。但在文化旅游的发展下,政府、资本成为活跃力量,同时还有游客的进入。此时村落要面临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的审视,当地文化表达与游客的接受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如此前提下,民族村落开发时需要把传统民族文化变成为“可读”“可参观”的文化,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问题: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保留还是舍弃的问题、为游客创造什么值得观赏体验的内容及场所的问题以及可以在原有的文化空间内增加什么内容的问题。
文化空间的多元主体,使得传统民族文化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文化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反馈使当地文化主体能够对自我文化进行反思。在阔时节、乡村音乐节举办期间会组织举办画展、摄影展等活动,不同的创作主体对傈僳族文化进行现代性理解和表达,是他者的艺术精英对当地文化提出的反馈,在展示中会影响到参观游客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也会引起本地文化主体对自我文化的反思,在这一重构的文化空间中实现着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互动。新修建的傈僳民族服饰馆、农耕文化展示馆成为为外来游客展示的文化空间,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着文化的传播互动功能,在向游客传递文化信息的同时,也能通过游客对于所见所闻的感受,从新的视角反观自身习以为常的文化事项。本地的文化精英通过绘画、摄影、书法等艺术形式,也让当地村民对自我文化的表达有新的启示,提升村民的艺术修养。
(二)文化旅游下民族村落文化空间的特征
1.民族性与现代大众审美的结合。在文化旅游重构下的少数民族村落文化空间在呈现出当地本民族审美的同时融入了符合旅游大众审美需求的特征。虽然少数民族村落及其文化空间本身是族群性的,但是在进行文化旅游开发时,既要满足游客对“他者”异质性文化的想象,又要还原对“他者”文化想象的真实,这就需要经过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大众化、现代化的表述,也是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将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表达,其结果就是重构的文化空间兼具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大众的审美取向。
下勐劈村的文化景观、村落环境、文化氛围上是经过艺术设计,呈现民族特色同时符合大众审美标准,是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呈现出来的,将典型的民族文化通过文化空间的表达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突出文化旅游中的特色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提升着文化氛围和村民的艺术审美。进入下勐劈村的寨门就经过一定的艺术创造,保留寨门文化,通过视觉设计,呈现原始古朴而又庄严神秘的特色;村内的民居客栈都是传统的木楞房,呈现傈僳族建筑特色,但是内部功能和住宿环境却是经过改造的,增加卫浴、空调等等,统一为现代的住宿标准,满足游客对住宿舒适度的追求和对异域文化体验的需求,而且民宿会进行统一的客栈管理、旅游接待等培训,以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除此之外,从“小木屋”客栈的名称上看,如“群山云抱屋”“香梦雅舍”“松下芳庭”等都受到汉文化影响,这和近年来傈僳族语言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汉语词汇相映照;村内通过广播系统建设,散布在村落主要干道,白天播放音乐,烘托文化氛围,有傈僳族民族音乐,也会有红歌和现代流行乐。
2.文化空间要素的集聚与分散。文化空间中文化以空间为介质和容器进行生产,其中凝结了象征、符号、价值观、历史记忆等要素,具有共同内在联系和精神内核的文化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共同体,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差异性的文化空间。文化旅游重构下民族村落文化空间中的象征、符号、价值观、历史记忆等要素的自然生成的节奏被打破,而在重构中经过规划设计,布局上呈现出既集中又分散的特点。
具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是被集体共同认可的,体现文化独特性、集体意识的景观、象征物等符号赋予了固定的意义,承载核心价值,如公共聚会空间、仪式场所、图腾表述等等。新建的阔时广场,集中展示了傈僳族的石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服饰文化、图腾文化以及傈僳族的祭坛、神柱,在旁边建有傈僳民族服饰馆、农耕文化展示馆,既是节庆活动的主要举办场所,是文化活动的空间,是民族文化展示的空间,同时也的公共艺术空间,在这个区域内实现了多重核心象征的集中和叠加。
符号是对文化的一种抽象和直观的表达,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在文化空间内传递着信息,唤起一定的情感,并能够成为一定文化的指代,让人们能直观的认识、了解其指代的文化。在为文化旅游而开发的村落,往往擅长于将文化符号投射到图腾、建设、节庆、服饰、景观等日常的方方面面,被设计安放到村落的各个角落。在下勐劈村,寨门、图腾柱、水磨房、栈桥等景观的布局以及在村落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安置着的雕刻着傈僳文字、图腾的石头,展示傈僳族文字及刻石祈福传统,这些文字记录着傈僳族繁衍发展的历史,都在以符号传递着傈僳族的民族记忆和价值观,这使得整个村落形成一个文化要素集中又分散的文化空间。
三、民族村落文化空间重构的思考
(一)文化旅游下重构民族村落文化空间的意义
民族村寨文化空间的重构,在商业与民族文化共同作用下,实现自我认同与市场认同。结合当下审美取向的同时提炼和不断强化群体标志性符号,以求差异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强调群体身份,沉浸在这种文化空间内,在地的文化和群体身份从被发现,到被认领并逐渐公开承认,再到被认可,这是唤醒并推动着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和担当,并能塑造和维护乡村的公共性,在村落的文化空间中使群体与个体在时空中发生关系,建立了一种强烈的认同和回归的“心理纽带”,重新找寻乡愁,使个体对精神家园的寻觅与依恋的情绪能得到安放,通过审视与思考走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焦虑和迷惘,在文化旅游发展的“流动”的环境下使村民能保有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在与作为另类文化携带者的游客在节庆仪式过程、活动、符号和场景的互动参与中,强化或唤醒过去的集体记忆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集体记忆,这种新的集体记忆融合多元主体形成共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辐射话语力量,所以文化空间重构的过程也是其传播的过程,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以经济利益为驱动,激发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实现对文化的保护。
而就进入到文化空间中的旅游者来说,通过对少数民族村落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凝视和异质性文化的体验,感受自然,了解他者的文化,一方面是体验的获得,另一方面也更能够引发对城市、对自我文化的对照与反思。
而文化旅游的介入,能撬动少数民族村落有限的社会资本,更能吸引外部社会资本进入,虽然在少数民族村落文化空间的重构中,将文化空间视作控制和统治工具,但文化空间也不可能会被完全的占有或控制,因为边缘化的文化空间会不断的形成,并始终影响着文化的表达,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形成有活力的村民生活和村民参与,新的文化空间既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也在通过消费文化空间,营造出更大的文化消费空间。重构下的少数民族村落文化空间成为守护民族文化传承、培育新的乡村美学、孕育良善乡风、振兴乡村经济的新助力。
(二)民族村落文化空间重构应注意的问题
1.文化旅游产业扶贫中市场需求与本民族文化表达的调合。围绕文化旅游产业重构民族村落文化空间在当下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扶贫,其目的是提高当地村民民生福祉和促进村落经济发展,带领少数民族群众实现整体脱贫及乡村振兴。这就要求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村民的利益应当放在首位,并关注其利益的可持续性,在重构时必须注重对于文化空间内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照,作为工具的文化空间,是需要特定文化支撑的,而民族传统文化失落将会是对文化不可逆转的破坏,呈现出的文化空间也必将是臆想的拼贴,失去其精神内核,所以,保持民族文化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生活性,处理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才能为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资源。文化旅游发展中各个主体间应通过良好的沟通机制达成共识,明确各个主体的权责边界,在已经成为公共空间的村落中实现文化空间的共享共建、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在市场需求的审美下去调整本民族文化的表达形式,在重构民族村落文化空间时注重大众审美和差异化的表达的调和,在发展定位上明确角色,突出娱乐性和体验性,以民族文化内涵的表达为规划的依据,寓教于乐,让“我着”的优秀本质更容易、更直接的方式被游客接受和认可,留住传统民族文化的文脉与乡愁,这样在村民生活的村落及游客进入到文化空间时才不会有不适感。
2.村民发展意识引导与产业发展的持续推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是要实现民族村落从对文化空间的消费向在文化空间中消费转化的,文化旅游的发展要素中对于消费是有需求的,村落文化空间也应发挥其消费性的功能,在文化空间的重构中提出更多的消费形式和产品设计,过度消费和缺乏消费对于旅游体验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新乡贤等应更多地持续地对村民与产业进行赋能,首要是提高村民参与文化展示和创造的活力,同是引导其在文化旅游中的生产及服务意识,提升主动发展的意识。政府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构建时,对民族文化的内涵系统认知应做好基础的整理工作,并引导当地人民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对其现代性表达的探索,持续性的增加对村民的技术、管理、创意设计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招商和吸引本地与外来的文化精英的入驻,组建多元主体构成的发展委员会,科学制定村落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及文化空间建设、运用、改造的原则。同时将民族村落的文化旅游纳入智慧旅游的体系中,注重旅游服务的提升及迭代更新,让民族村落文化旅游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在完成扶贫的基础上不断走向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