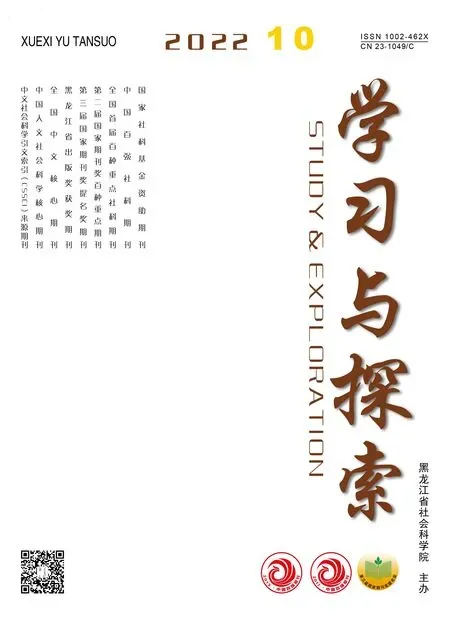诗是洞彻并发现经验的窗口
陈 爱 中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冯晏的诗是有一席之地的,在诗学意识和语言处理上,都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念。随着《镜像》《刺穿冰层抵达水》以及《小月亮》《意念蝴蝶》《焦虑像一列夜行火车》(“诗歌哈尔滨”诗集系列)等诗集的出版,她的创作似乎到了“诗歌年龄”,从质到量相对之前的创作都有本质性的提升。
一、多语性:语义张力支撑下的现代诗
怎么才能将文字识别为一首汉语新诗,尽管学界对此争论不休,但就音韵和象征的使用来说,基本能够达成共识,或者说至少目前认为这是一首汉语新诗必不可少的核心元素。但在冯晏这里,似乎并不为之忧虑。她所理解的汉语新诗是“发现奇迹的感觉”,是语词深层的思考,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求诗人要具备“忧郁、宽阔和思想”这三方面的出色条件,并进而阐释“忧郁”是“诗人的浪漫主义之根”,“宽阔”是“提取意象的视野”“宝藏的储存之地(时空、宇宙和精神)”,而“思想”则“是你纷繁创意的灯塔,为意象指引”,并由之而综述出“一首诗犹如空中出现的一个UFO(不明飞行物),你选用的意象是里面的外星人,各自承载着独立的思维,但是它整体出现的原因和给人们带来的惊奇,主要是它的思想”[1]166。这显然是一个个体性的诗歌定义,不是来自农耕的“缘情”或者“言志”,因为这两者强调的是诗歌的表达目的,尽可能实现在创作与阅读的链条上的完整性,所以注重诗歌语言阅读上的音韵铿锵、朗朗上口,同时也要在语词使用和诗歌结构上尽量贴近大众,无论是新诗的大众化还是现实主义的观念甚至是口语诗的长盛不衰,实际上都可以归结到这两个范畴,主题清晰、容易传播和记忆。冯晏的诗歌定义是现代的,这里有两个层面的考量,一是强调现代人成为一个诗人的前提条件——“忧郁、宽阔和思想”,这些都不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自然之物,而是来自于理性的孕育,“忧郁”的性格相对于明朗的性格更容易陷入安静的沉思,适应于个体智性有意识地同周围世界产生各种关联之后的经验累积。里尔克认为,“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很够了)——诗是经验”,并因之而谈到一首诗生成所需要的智性活动,“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2]93。这实际上也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到的诗人“完全成熟的时期”往往是要忘掉“个人”的,“在他的诗里是很重要的印象和经验对于诗人本身和他的个性也可以没有多大关系”,诗歌的存在要让“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从“知人论世”的评论套路里走出来,“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并进而阐发认为“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3]。显然,无论是里尔克还是艾略特,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现代诗人,在处理现代诗歌生成和诗人之间的关系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诗人的天分的作用的,而是强调后天经验和理性综合能力的作用。另一方面,百年汉语新诗的发展历程实质上就是西方现代诗歌的核心理念不停地在汉语领域生长的过程,里尔克和艾略特所代表的经典诗人的论述深深影响了汉语新诗写作。但众所周知的原因,除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和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以及90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这种影响在汉语新诗领域并没有实质性的映现,所谓的经典性的文本也多停留在徐志摩、闻一多等的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里。
冯晏提出的认识现代诗的方式在于发现生活中的“奇迹”的“思想”,彰显了新世纪以来汉语新诗在创作成绩上告别了依靠外在音韵和分行来实现自我定义的尺度,走向了以经验的复杂性、技巧的综合性和对语言的隐喻方式的重构的青睐上。在这个过程中,诗歌的使命不再是仅仅处理诗人简单的七情六欲,而是上升为对诗人与周围事物关系的呈现,在更为复杂和综合的层面上,彰显存在的意义。汉语新诗不拘泥于抒发性情或者表明生活态度的功利性,着意于对经验的智性表达,以更为“宽阔”的视野在“忧郁”的沉思中,习得崭新的存在经验,凝望未来的景象。这决定了她的诗是建立在扎实而多元的知识储备上的,其中的间接经验占据重要部分。而这些经验对接受者来说,需要一定程度的诗教基础,才能领会,所以,朦胧诗遭际的晦涩也就成了冯晏诗歌理所当然的“常态”。
我们今天再提朦胧诗的“晦涩”难懂,往往会归结为读者不了解朦胧诗,无论是隐喻的技巧还是主题的指向上,但凡对朦胧诗生成的文化历史稍有关注,就会洞然于心。这自然是新世纪以来国民教育的提升带来诗歌阅读水平提高的结果。可以说,相比于冯晏新世纪以来的新诗,朦胧诗的晦涩性之比,顿成云泥。这也是诸多诗歌批评者的共识。“面对冯晏的诗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无能为力”(张清华语),或者说“冯晏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我也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说实话,冯晏的很多诗歌,我看起来也很费劲,很费解”(姚风语)[4]。如果能够摆脱诗歌的确定性表述这样一个先验的阐释观念,这里的晦涩应该和其诗歌意义指向上的多语性相等同,从而给读者带来阐释惯性上的不安感。有学者曾以洋洋万言来分析冯晏的长诗《航行百慕大》,指出“《航行百慕大》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明面上的,它是对窄门的深沉书写,它是《航行百慕大》的表皮;另一个是深层的,它是对词语紧追诗绪这个诗学问题的反复强调,是《航行百慕大》的灵魂。正是主题的这种多声部,促成了、成就了一首不同凡响的诗作”[5]。
我们同样来看她的那首《复制或模仿》是如何呈现这种多语性特征的。诗篇开首“不断模仿或复制,从心脏/到喷泉,到画作中的血”,“原则上,任何艺术作品都能被复制,人类制造的艺术品,总可以被人复制”[6]2,“然而,即使最完美的复制,也必然欠缺一个基本元素:时间性和空间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6]4,这里的“独一无二性”也就是艺术萌生的“元”元素,也即是原真性。但如果去模仿独一无二的实存如心脏的跳动、正在运作的喷泉、画作中流淌的血,这些能够彰显最为疼痛的、最有冲击力的感受相关联的瞬时样态,那么这种模仿则就会如“蜘蛛的腿”,虽然在表现上是复制的,但却因为关联其唯一的实存,而变得具有仪式感,有了宗教般的虔诚,而得以“经过圆顶伸进一个教堂”。诗句后续出现的摩卡咖啡“复制原产地埃塞俄比亚”或者“复制身体飞起,/梦成为诱惑”,又或者“海市蜃楼复制幻象,/城市倒映天边”,在每个复制的动作背后都隐藏着瞬时的不可逆性和被复制意象的唯一性、主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复制”本身所具有的重复动作和数量上的丰富的定义的否定。这样,对于这首《复制或模仿》来说,本身蕴含着两种互为背反的主题:既可以在“复制”的原意上阐释“机械复制时代”带来的价值认知困境,以反讽的姿态反思技术文明,亦可以如上述所阐述的,从另外一个方面阐释复制表象背后,事物的“原真性”,从而构成一个多语性的文本结构。毋庸置疑,诗歌这种多语性特征显然是遍布阅读危险的,在语词设置的各种陌生或者碎片式的关联中,阅读者如果不能够找到恰当的切入视角或者具有较为丰沛的诗学修养的话,往往会陷入语词表现的陷阱,沉溺在晦涩的泥淖里不可自拔,不能够触摸到其中较为圆融的诗意经验。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就会是失败的文本,残缺而未完成的文本。因而说,阅读冯晏的诗是需要准备的,然后才能不会陷入语词的迷障。
比如诗歌《绿皮火车》,从表象上看,描述的是一次去图们的旅行,“夜晚,乘坐一列绿皮火车/去图们”。然后是从火车上看到的沿途的风景及感想,“一枚金元铜镜挂在空中/月亮面对你,发出脂粉的光”,接着看到窗外的草丛,由之而想起生物存在的细胞世界和繁衍生息的图谱,最后感慨于绿皮火车所代表的落后和历史的记忆,“绿皮火车,你登上去就意味着/一段历史还持续着,或者/一段旧情感,在铁轨下/想用拐杖站立起来,或暴露着”。单从现代诗的隐喻特质来看,这首诗显然不能只是如此,如果了解图们这座城市的濒临朝鲜边境,知晓两岸之间绿皮火车所曾代表的记忆共同体,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彼岸的“固执”,那么这首诗必然具有政治隐喻的属性,其间的绿皮火车、窗外春天的“遍地来生,族谱在植被中繁衍”等意象的主旨自然而形成一种对政治乌托邦的想象和重拾记忆之后的感叹,甚至还可以解读出人类的某种存在样态。自然,无论是《复制或者模仿》还是《绿皮火车》,在冯晏新世纪以来的多语性诗歌中,都是相对简单的,她的《航行百慕大》《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新馆开馆素描》《被记录的细节》《内部结构》等长诗,都是可以做细读的文本。我们无法深知诗人的创作是否具有难度,但阅读是一种难度,或者说是一种智性的探险。
毋庸置疑,冯晏的诗是深得现代诗的诗学观念影响的,是可以用较为流行的“元诗歌”的概念来框定其诗歌在汉语新诗中的价值的。她的诗在破解新诗晦涩的负面标签和现代诗语言隐喻的张力上提供了足够丰沛的经验。“诗歌写作,一路上都面临解决难题,一些曾经一闪而过的创作意象,你没能抓住,就说明你在观念中还没有意识到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你的思维还没有能力帮助你达到认识一些更高级事物的可能。”[1]1冯晏一直强调诗歌写作的观念问题,认为“写诗,只有在观念中才能越过日常思维”,“诗歌创作应该是最直接深入精神核心的语言表达”[1]2。这些于理性习得和智性综合而来的观念,一旦成为汉语新诗写作的核心,并在多语性的诗歌结构中得以呈现,就意味着汉语新诗在现代性身份的获得上剥离了来自农耕的抒情性写作,不只是停留在宣泄或者诉说的初衷上,而是在沟通诗人与世界的逻辑关系上,实现主体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如此,不仅里尔克的“诗是经验”、艾略特自我的隐匿的诗学观念要在汉语新诗中得以实现,而且荷尔德林的“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的使命也会得以彰显,从而让诗歌从现实功利中挣脱出来,具有未来性。这也是诗人先锋和试验的意图。冯晏曾说:“我对现代诗的理解总是不自觉地想使其摆脱针对古诗而言的现代诗概念。……‘现代诗’这个词应该是一种东方传统和西方传统综合突破后所延伸出来的创作成果……是一个动态的意象。”[1]212-213这也是诗人着力于在物理学、天文学、脑科学等现代认知领域各种驳杂的知识中寻找诗意的缘由,于是,在她的诗歌中,“银河”“时间隧道”“土星”“金星”“陨石”等超现实的意象蜂拥而至。
二、差异性症候:经验综合与知识性写作
建构多语性诗歌文本,需要诗人具有较高的获取经验的能力和途径,在超验的视阈内要么积累出别人不具有的经验,要么在众人视若无睹的风景里挖掘出新鲜的诗意来,才能以绵延不绝的质料创作出富有张力的诗歌结构。冯晏曾提出,理想诗歌或者诗人的美学特性是“我希望能看到他气质中的维特根斯坦式逻辑思维的透彻,以赛亚·伯林式的现实感,毕加索式的强烈而有序的意象和视野,迪金森式的对生活的感觉,策兰式的对每一个词语实现饱和与富饶的态度”[1]208,这几乎囊括了现代西方哲学艺术中在某些方面达至极致的特征:基于现代逻辑基础上的语词秩序,意象所指的宽阔、充盈、多意性,锐利而精微的现实嗅觉,等等。那么,从时空阅历的角度上说,要想具备这些特征,可能需要既具有印象主义画家莫奈那种让想象力粘附于单一静物,在凝视中深入并关联相关光影的能力,同时还需要空间上灵敏而大胆的挪移,以“在路上”的漂泊精神,占有尽可能多的静物。要实现这些,只能依靠间接阅读。魏晋南朝画家宗炳岁至暮年,体弱多病,“老疾俱至”,自然无法亲历名山大川,因而有在室内赏山水画作,“抚琴弄操”,“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这样才能“令众山皆响”(《画山水序》)。这种“卧游”,即通过阅读来获得诗意经验,几乎是“知识分子”或者“学院派”诗人共同的嗜好,也是现代诗生成的普泛特征。但在汉语新诗的历史上,这种依靠习得共识和想象力的经验综合常常被旧有的农耕经验置于否定的位置,“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汉语新诗中依靠间接经验来写作的诗歌,因为缺乏本土“在场”的细节和真实,“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曾经被视为“诗歌处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7]。同样沉浸于综合性知识和玄学的穆旦、袁可嘉等“中国新诗派”诗歌之所以没有同样的遭遇,恰恰就在于他们将这些诗学理念融入时代“在场”感中进行写作,也是在那样一个战火频仍,个人与时代、个人与集体“互渗”时代不可避免的选择。按照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理论,在现代逻辑思维之前的“原逻辑思维”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是不分明的,而是存在认知上的“互渗”甚至是“合一”的认同观念,“互渗的实质恰恰在于任何两重性都被抹煞,在于主体违反着矛盾律,既是他自己,同时又是与他互渗的那个存在物”[8]518,缺乏主体性的主观能动性和必要的间离意识,那么,也就是说,“眼见为实”、切身体察的认知逻辑并不能真正映现现代认知思维,从而陷入“当局者迷”的圈套。和冯晏同时代的诗人西川也表达过类似的感受:“我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中长大,又渴望了解世界,书本便成了我主要可以依赖的东西。书本的世界是无限的,它不仅向我们提供场景、人物、情节、对话,它还迫使我们去寻求世界的本质。它使得萨特甘愿生于书本、死于书本。它使得本雅明意欲告别独创,而用引文搭建思想的大厦。相形之下,现实世界仿佛成了书本世界的衍生物,现在时态的现世世界仿佛由过去时态的书本世界叠加而成。这种看法把我引向一种写作的雄心壮志:我似乎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天、地、人三方面展开工作。我因此受到指责:我因沉浸在文化想象之中而忽略了对于具体生活的观察,我未能使我的写作同时代‘语境’交融在一起”[9]1-2。
17世纪,笛卡尔趁着宗教统治弱势之时,提出“我思故我在”,人类认知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理性主义开启了人类告别中世纪蒙昧的大门。“何谓理性主义?简言之,就是一种认为理性地应用推理是人们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最佳向导的思想,它将自然和人类社会都视为理性组织的体系,其本质和运行可以为那些从事理性思维的人所认识”[10]868。站在这个视角,这种基于主体理性认知的习得经验自然可以成为构建汉语新诗诗意经验的重要资源,一如康德在柯尼斯堡仰望星空的玄想和思辨。诗人可以从博览群书中,重构对实存的自我想象,而不受具体时空的限制。冯晏诗歌的多语性结构,多得益于这种孜孜不倦的“卧游”,让诗歌的众多意象站在丰富的先验意蕴上融入文本中。比如《新圣女公墓》中出现的那种密集的文学意象,诗歌、小说、人物、“契诃夫”“波斯猫”,等等。“在契诃夫对面,《死魂灵》入口长满芳草/为了果戈理,特朗斯特罗姆用诗句/打碎过圣彼得堡,犹如打碎一块水晶玻璃。”单是这诗句就关涉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及其诗歌《果戈理》、俄国作家果戈理及其小说《死魂灵》,而特朗斯特罗姆在其诗《果戈理》中对果戈理悲壮一生的诗意描述,将其最闪光的时刻隐喻在“圣彼得堡和湮没在同一个纬度”的诗句里,这种感觉又被冯晏用“犹如打碎一块水晶玻璃”的譬喻,在“透明”而纯粹的通感上实现经验的转化,呈现数度解读空间。综合长眠在“新圣女公墓”里的各种关联意象,披拂以充盈的悲悯和洞彻黑暗的基调,“视线和嗅觉仿佛被忽略,有些可疑/然而,你更容易看清的是黑暗/而不是光辉”,从现实的“死亡”意象出发,《新圣女公墓》用“黑暗而不是光辉”以点见面、从小处做文章,隐喻出俄罗斯19世纪文学的常态。熟悉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不同领域和侧面的读者都可以在这首开放性的诗篇中寻找到绽放的诗意,流放、屠杀、落魄、失意等等。类似的诗篇还有《复杂风景——致维特根斯坦》《敏感的陷入——致荷尔德林》等,它们都是将阅读的间接经验融入辐射性的诗意结构里。冯晏诗歌呈现出经验的复杂性和多语性,也是福柯视野里作品的理想状态:“一本书产生了,这是个微小的事件,一个任人随意把玩的小玩意儿。从那时起,它便进入反复的无尽有戏之中;围绕着它的四周,在远离它的地方,它的化身们开始群集挤动;每次阅读,都为它暂时提供一个既不可捉摸,却又独一无二的躯壳;它本身的一些片段,被人们抽出来强调、炫示,到处流传着,这些片段甚至会被认为可以几近概括其全体。”[11]1
现代诗作为内时间意识流的写作,诗人对不同经验的驾驭和综合,会随着不同差异性经验的介入而增益诗歌文本的主题张力。在打破日常生活的惯常环境,从文化地域的角度有意识地实现差异性经验的融入,实地踏查的旅行自然是最为有效和便捷的方式,地域时空意义上的“纠偏”和“补充”,会重组诗人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和瞬间感受,产生新的诗意经验。相对于小环境之内的“采风”,冯晏的旅行堪称经典的文化体验之旅。以文学经典中的核心意象为中心,增加文学原型的现实化、个人化经验,西伯利亚大铁路、圣彼得堡、莫斯科、伦敦、加勒比海,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海明威、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乔伊斯等西方现代文学经典作家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或者作品中出现的物象符号,都在她的旅行地图上。她的旅行经验的诗歌实现了表现上的全球化,而这种组成全球化的题材和意识又恰恰是在地域性、差异性的角色里彰显其诗性的,在经过阅读想象、在场体验和忆念写作之后,这种旅行经验在汉语里形成独有的诗歌文本结构,从而在“非惯常生活”的陌生化书写中,达至对日常生活本质的更新、重组和创造。这种诗歌文本的生成,恰恰符合现象学的认知逻辑,“现象学的世界不属于纯粹的存在,而是通过我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我的体验和他人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体验对体验的相互作用显现的意义”[12]。各种素材在诗人主体性的主宰下,从时空的间离、在场到忆念中内化为诗意经验,在交互作用中形成新的综合性创新性汉语新诗文本。
我们再来看她的那首《阿赫玛托娃的厨房》。诗篇不长,但信息是立体的,互相融合之后的归一,“你故居的墙壁,列宁格勒/应该倒挂,向你致歉”,这里的列宁格勒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城市,同时也是阿赫玛托娃彰显“与祖国同在”思想的表征。阿赫玛托娃曾在一本名叫《列宁格勒》的杂志上发表诗歌,并因此带来祸患,被苏联高层领导人日丹诺夫粗暴地批为“颓废色情”的诗人,后被逐出作家协会,若干年后获得平反,命运跌宕起伏,翻云覆雨,这就是“阳光与记忆,在此仿佛仇人”隐喻的来源。“厨房,犹如一枚书签夹在暗处/炉子上,油渍略有幸存/米香已散尽,器皿早已失音”,在时空叠加的消隐中,忆念阿赫玛托娃时空荡涤之后的存留影像,斯人已逝,“指纹和唇印,你的真影像/已进入墙体。豆绿色涂料内部/静水倒映,明月重生”,穿越时光背后,则是精神重生,成为俄罗斯诗歌中的月亮,和被誉为俄罗斯诗歌中的太阳的普希金一样,熠熠生辉。冯晏按照对厨房的参观顺序,通过“黄色的铜盘”“磨砂陶碗”“煎蛋器”“老式的炉灶”等积淀阿赫玛托娃历史、现实乃至未来的日常意象,融合复杂的历史事件对阿赫玛托娃的一生做立体性的彰显。同样的诗歌结构亦出现在《夏日的伏尔加庄园》《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新馆开馆素描》《航行百慕大》《美丽的哈瓦那》等诗篇中。
冯晏大部分诗歌的题材来自于间接经验和想象力的重构,自然离不开理性的有机驾驭。阅读和诗意旅行都是刻意而为的,从题材到想象,都是在智性主导下积极营构的结果。冯晏诗歌的生成过程呈现为一种间离效应,从而剥脱了日常抒情的样式和语词,将情感客观化之后,实现物象之间的关联性呈现。比如在《刺穿冰层抵达水》中,她首先是“想跟鱼说话,进入它们的起飞与滑姿,/听蠕动,鱼鳃、鱼腹,/听一首章鱼触角协奏曲,/想接近牡蛎,吸盘/阻止拔起之力。/想留住那片被螺壳内季风搅动的波纹,/以及被水滴吸走的光。/想跟史前依然活在水底的怪物,/深刻交流一番”。这种强调准确性和细节的描述,将容易流于情绪的情感融入对事物的洞察之中,以“凝视”的笔法丰富而多元地表现对“水”亲昵的欲望,相对于“物我两忘”的写法,这里始终处在诗人主体的掌握之中。随后的“刺穿冰层,用三棱镩头,铁锤/用更多黑色模具钢,/神经借此进入透明”,或者“想潜入水下,变换一种呼吸方式”,或者“想跟浮力周旋,跟旋涡,白帆,/跟船长胸前佩戴的一枚巨齿”,包括“想跟硬度,跟地壳,地幔,/地核及岩石层”,等等,诗人不停地从不同角度将对“水”的关注寄托到关联意象上,最后冷静地将这种“凝视”归结为“虚无”,“今晚,或许我只想静一静,对视一会/跟一片空无,远游经过的紫色云雾,/白色落地窗,黄色吸顶灯,无色荷尔蒙”,从而实现“物我合一”从现象到哲学上的思辨。
冯晏长居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诗歌中,“雪”早已成为诗歌的公共意象和寄情母体。但在冯晏的《雪景都市》中,“雪”和“自由”“纯洁”等传统公共象征并无关系,而是注目于其中的一个元素,被描述为“白”的隐喻,“雪清空琐事,光消融着雪,/屋顶、窗棂,沥青马路以及安全护栏,/都市缩进冬季的白色情绪里”,由“白”而延伸出“空”的动作和状态,然后是“缩进”,进入“水分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客观物象,兼顾雪的宏观和微观景象, “一个路边雪人发出水分子裂变的神秘微笑,/怀疑并非表面”,将“雪”视为一个渐趋消融的过程,并进而引出“当失意成为记忆的借口,/语言成为它自身的反面”这样一个大道至简的朴素哲理,雪在这里成为一个过程性的动词。甚至可以说,在经过冯晏的诗意重组,现有意象剥脱了“农耕”表述,而进入到现代性的角色之中,比如《加勒比海日出》中的“日出”,全然是诗人来自细微身体感受图景的描述。从朝阳升起的冲击性感受开始,“殷红的裂缝撬开舷窗”,“我的灵魂总是冥冥中忽然遇见偷袭者”,太阳逐渐照耀的光线带来的震惊如“宇宙隐匿于神秘主义,/犹如惊呼”,而诗篇从大多数人依然沉睡在日出的早晨,“无人起床,无人洗漱”,落脚到“生活只是谜语的开始,情节断断续续”,从而否定了“日出”的进化论意义。冯晏甚至让诗歌从根本上否定意象叙事,而是让观念唱主角,完成诗意的呈现,比如《重新发现》,一组七首诗,分别以“星期一”“星期二”直到“星期日”等抽象时间概念来命名,任凭各种介入到想象力的元素和素材自由穿插,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国际事件等等以各种感觉方式出现的知识,统一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空中,来呈现生活的突如其来的实质,并在最后回到永恒的日常景象,“发现日出从窗口探入,手机充电呢已满”。类似的观念性写作还出现在她的《与幻觉无关》《一周以来》《一套丛书所围绕的》等等篇什中,这种写作也往往被誉为“超现实”写作[4]。
三、结语
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新诗,一直弥漫在解构的氛围里。“第三代”诗歌以为意象或者语词“去魅”的名义,试图重拾五四新诗的民间化路线,实现对朦胧诗的解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互相在不同的资源语境里隔空交锋,以不容置疑的“阶级立场”彰显存在;以论争和会议构成的汉语新诗史,注定是让青春的极致和彼此非理性的立场性拒斥起主导作用的。随着新诗失去成为社会公共话题的功能,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显然理性温和许多,既有“中年写作”的沉稳,亦彰显以知识为基础的智性写作的渐趋繁荣。这自然是汉语文化加速度融入现代思维体系、价值文化的结果。但汉语新诗能否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变化在思维和语言上带来的变化,能否在实质上而非口号上依然扮演先锋的角色,进而从诗歌结构和意象上实现与时俱进,在诗歌经验上摆脱“农耕”的抒情底色和生搬硬套的“洋腔洋调”,这显然是百年新诗汲取中西诗学资源,能否告别“翻译体”和格律体的评述困境的重要考量。
在这个意义上,冯晏诗歌中体现的强力主体性,理性而智慧的处理复杂现代经验的能力,以及对物象语词所指的关联性重构,将观念作为诗歌写作的主流,而非过度依赖物象的隐喻,都在昭示着冯晏的诗歌对当下的汉语现实有着较为通透的理解,对汉语新诗写作的未来性有较为可靠的预言。更重要的是,她的写作让汉语新诗在诗学理念和文本结构上出现了摆脱“青春期”的幼稚,走向晚景写作的可能,新诗也从强调天赋性的抒情性写作,走向智性的终身性写作,并体现出时间积淀的经验性意义,这也是现代诗的经典文本往往出现在诗人生命晚期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