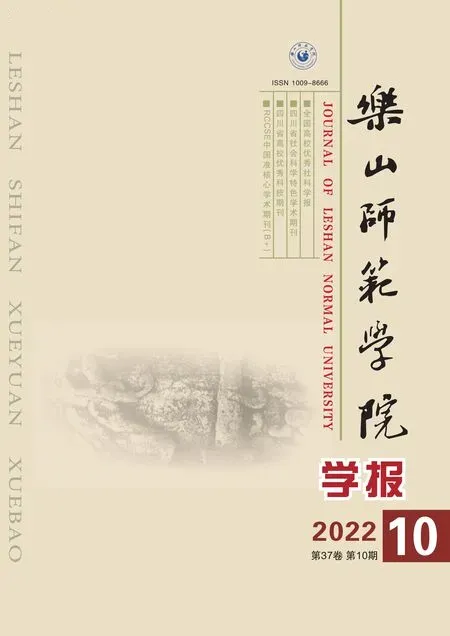书生议政到官僚治理之路
——详论苏辙役法思想的演进
苏祖川
(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重庆 400020)
北宋熙丰变法与元祐更化期间,差役法与募役法之争始终是各方斗争的焦点之一。苏辙有关役法变革内容的若干意见,向来被后世史家反复引用加以论述。但这些引用大多系片段引用,且论述中不乏误读之处。①而专门研究苏辙役法思想的文章反而较少。②已有文献主要并非考察苏辙本人的役法思想,引用及解读苏辙论述的目的是作为论述其他问题的依据,并以此来解读变法各方的观点及政治态度。因此,对苏辙役法思想的有做专门研究的必要。通过对原始文献的全面解读和深入挖掘,整体理解苏辙的役法思想,还原其役法思想的本来面目。
从苏辙自身政治经历和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苏辙役法思想的演进过程,体现出苏辙本人从书生议政向成熟官僚治理转变的过程。也即苏辙从较为空乏的理论议论,转变为思考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解读这个转化过程,也有助于理解苏辙的整个思想转变过程。本文以苏辙参与役法讨论的原始文本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史料,以图完整的展示苏辙的役法思想演进及其从书生议政到官僚治理转变过程。
一、苏辙任职制置三司条例司期间的役法思想
苏辙于熙宁二年(1069)三月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参与役法改革的争论,此时苏辙31岁。围绕着是否废差役法而采募役法,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辙强烈反对募役法,在当年八月所撰写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提出了多条反对募役法的理由,但大多从抽象出发,理论推演较多,从概念到概念,触及实际问题不够深入。苏辙这个时期役法思想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1]762
苏辙认为,乡户是本乡本土之人,差役法使用乡户服劳役,易于控制管理。且乡户服役更为尽职尽责,因其“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1]762并以捕盜官员为例,提出县尉管辖的弓手为乡户,其更为尽职。而巡检属下则非本土乡户,故县尉的捕盜效果明显好于巡检。但苏辙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并不涉及到募役与差役的区别。差役法与募役法并非在服役对象上存在区别,差役法固然使用本乡本土之人服役,募役法也并非不能募集本乡本土之人。募役法完全也可以雇佣本乡本土之人服役,而非苏辙所提出只能“用浮浪不根之人”。[1]762
(二)重复征税问题,即“今两税如旧,奈何复欲取庸”[1]762
苏辙的观点是,唐代原施行租庸调制,以庸作为劳役,在不服劳役情况下,可以纳绢代役。后改为两税法,已将庸纳入到户税和地税中收取;既然已经将庸这一劳役赋税并入到两税,就不应当再以货币方式收取免役钱(即苏辙所谓“庸钱”),否则就是重复征收。苏辙此种批评对唐代税制做了过分理想化的解读。其一,租庸调改为两税法后,租庸调制并未废止。[2]其二,唐代施行两税法后,在两税之外的劳役始终是存在的。[3]224其三,宋代的税负本身就有实物税与劳役两种。[3]284按苏辙的观点,既然两税法将劳役纳入了两税征收,则不应当再额外征收免役钱。此观点粗看具有合理性。但这一观点的前提却存在问题。如当时宋代税负中已没有劳役,仅为缴纳实物或货币的两税,则额外征收免役钱,系重复征税。但如当时赋税负担本就是实物税与劳役两者并存,则收取免役钱不存在额外征收的问题,仅仅是将劳役部分的负担变为货币形式缴纳。募役法之争涉及的系劳役以何种方式承担的问题,以货币方式承担则是募役,以劳役方式承担则是差役。苏辙此点批评未能抓住要害。
(三)上户下户的实际负担问题
苏辙提出,差役法保证了下户的利益。其理由是“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频,多者徭役简,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闲。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1]762按苏辙理解,上户少,所以每户劳役频繁,下户多,所以每户劳役相对较少;如果上户下户一律缴纳免役钱,反而加重下户的实际负担。苏辙的论断具有抽象合理性,也确有部分的正确性。但实际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募役法对上户下户的影响往往因时因地不同,不能简单的认为募役法一定对上户或下户有利。现实中的确存在苏辙所说一致的情况,但也由于诸多原因,与苏辙的认识恰好相反的实际情况也很常见。③
(四)财富集中于地主上层手中与集中在国家手中是否存在矛盾问题
苏辙认为两者不存在矛盾,“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1]763苏辙只看到地主上层与国家之间利益一致的一面。民富与国丰一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苏辙也能看到上层地主与封建国家的利益一致性和对维护政权的稳定作用,即“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1]763但苏辙未能看到地主阶级的兼并与封建国家的利益还存在矛盾性的一面,对“城郭人户”缺乏全面的分析。④地主土地兼并对社会生产力和国家政权稳定的破坏作用在一定时期内是巨大的。[4]这种为立论而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论证方式也是苏辙这个阶段作为缺乏实践的书生议政的一大特点。文章固然可以做得花团锦簇,但对应实际内容却存在较大偏差。
(五)关于官户服役问题
苏辙强烈反对官户缴纳免税钱,理由是:其一,宋代官户的劳役比前代加重。“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既已重矣”。[1]763苏辙认为,古时官户不过服三日之更,但宋代官员服三大户之役,实际劳役负担已经超过前代。故不应当再加重负担。其二,使用官吏重在使用其治理能力,故在劳役上应有所减免。所谓“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差役法,良有深意”。[1]763三是官户服役的计税基准问题。苏辙认为官户服役以人口为计税标准,在现实中缺乏操作性。官户外出做官,丁口未必在乡。若以人口计算,则难以确定人口准确数量,如不以人口作为数量,则官户的负担反而比民户为重。在官户的服役问题上,苏辙就官户而谈官户,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宋代现实赋税中非官户负担加重的问题。[5]脱离这一问题,空谈官户负担是否过重,也就脱离了讨论役法的实际背景和依据。
苏辙这个阶段的役法思想存在一定价值,在理论上也有可取之处,尤其是体现了苏辙役法思想中比较重视民生的方面,反对国家过分聚敛财富,“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1]464但其所列举的反对理由都比较抽象,对募役法的现实缺点分析并不透彻。其论述虽雄辩滔滔,但这些抽象概念和议论与现实之间存在脱节。其役法思想书生意气重,对实际缺乏比较切身的接触。故理论上分析固然有所道理,但并不能经得起具体推敲和现实检验。苏辙此前主要以读书应试为主,仅在治平二年担任过近一年的大名府推官[6]30,没有经历过较系统的政务训练,在其经历中也少有与赋税役法直接接触。苏辙虽以三司条例司官员身份参与了变法,但并非变法的核心决策圈子成员。苏辙的身份仅仅是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从事一些文书参谋工作。王安石用苏辙从事秘书文字工作,看中的是苏辙的文字功底。对苏辙的实际治理水平,王安石等中上层官僚是并不以为然的。苏辙此种为议论而议论的言说风格,恐也不为王安石等人所喜。
二、苏辙任地方官吏后役法思想的发展
熙宁三年,苏辙离开开封,开始地方官吏生活,此后15年间未在中枢机构任职。这一阶段系苏辙与实际接触从书生向官吏转变的过程。在其任职前六年,苏辙写过两篇涉及役法内容的文章,后九年则未见为文。这两篇文献的部分内容虽也多被引用,但对其作更全面深入的考察仍是有必要的。考察苏辙地方官吏前六年经历,其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为陈州教授,任职达五年。熙宁八年(1075年),改授齐州掌书记。[6]36-43苏辙担任地方官吏这六年间,应当说有了一些实际政事经历,对役法有了一些亲身体验。尤其是募役法于熙宁三年十二月开始施行,推知苏辙应当对施行以后的募役法也有一定的接触和了解。
苏辙熙宁四年作文《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此时苏辙为陈州教授,系讲授儒家经典的学官。且苏辙出任地方官吏两年不到,对实际政治接触仍较为有限。故文章内容主要是苏辙强烈反对包括募役法在内的四大变法措施,但这篇文献本身并没有深入论述募役法施行中的实际问题。仅仅是指责包括募役法在内的四种变法措施,声称“四者并行于世,官吏疑惑,兵民愤怨。谏争者章交于朝,诽谤者声播于市。”[1]768针对募役法施行后果,苏辙则讲到“百姓毁坏支体,熏灼耳目,嫁母分居,贱卖田宅,以自脱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无所告诉。加之以水旱继之以饥馑,积憾之民奋为群盗,浸淫蔓延,灭而复起。英雄乘间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众可得而聚也。如此而胜广之形成,此所谓土崩之势也。”[1]769虽然苏辙将募役法的后果讲得非常危险,但缺乏实际的分析。募役法到底有何弊端会造成此种严重后果,自己说法有何具体依据,所论从何而来,这些内容苏辙都无涉及。故此文更多的是表明一种政治态度,虽然文章写得文采飞扬。但流于空泛。我们可以认为这只是表明其政治立场的文章。但该文也可以反映出苏辙此时对新役法的思考仍不够深刻,其役法观仍流于肤浅,保留了较多其书生议政的特点。
而《自齐州回论时事书》所附《画一状》则更为值得注意。苏辙作该文的时间是为熙宁九年十月。此前苏辙担任了三年多年齐州书记[6]36-43,加上此前的学官经历,经过了六年左右的历练,对现实有了更为切实的接触。其反对募役法的理由已经更为具体,且能够触及到募役法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史料能直接反映出苏辙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其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的增加与丰富。一是其诗文反映出其交往的社会中下层人员有所增加,如乞丐、其他小吏、保甲长、底层书生等。[6]36-43二是对官员所面对的实际困境有了一些亲身认识,如记录“谁言到官舍,旱气裂后土。饥馑费囷仓,剽夺惊桴鼓。缅焉礼义邦,忧作流亡聚。”[1]108三是对民生疾苦有一定的亲身感性体会,曾记录地方洪水说:“熙宁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继作,桥遂大坏。”[1]108四是逐步接触到如狱政等实际的基层政事。[7]46苏辙这篇文章中的役法思想有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出钱与出力服役的相互替代问题
苏辙提出出钱与出力服役各有利弊,不同的具体情况下,差役和募役各有自身优缺点。在一般情况下,募役具有优点,但在一定条件下,劳役对具体承担人又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故“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专以钱。近世因其有无,各听其便。有力而无财者,使效其力,有财而无力者,皆得雇人。”[1]774
(二)劳动力无法及时转化为货币形式时的危害
苏辙认为,如果当民众无法将劳动力及时转化为货币时,则只能变卖家产缴纳免役钱。也就是其所说:“今也,弃其自有之力,而一取于钱,民虽有余力,不得效也。于是卖田宅,伐桑柘,鬻牛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1]774因募役法要求一律缴纳免役钱,当民众需要缴纳免役钱,但一时无法通过直接提供劳动力免除免役钱,也无法及时将劳动力转化为货币形式时,就会面临困境。这种情况类似现代社会,农民出现需要医疗等大笔现金支出时,会出现借债而陷入贫困境地。这的确也反映出当时募役法推行中存在的一大实际问题。
(三)“钱荒”问题
因募役法一律要求出钱代役,在某些情况下出现钱贵力贱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发达、银根充足和劳动力相对自由流动情况下,雇佣服役不会出现问题。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银根不足而又要求统一缴纳免役钱时,则会出现劳动力价格下降而货币相对升值的情况。这和古代谷贱伤农的基本原理一致,即苏辙所谓“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1]774。当时反对募役法的不少人都从钱荒这个角度做过阐述,后世史家蒙文通先生对此有过精当描述。[8]这是募役法在宋代的经济环境下存在困境的一大要害之处。宋代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但尚未达到可以主要通过货币形式解决劳役问题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讲,王安石变法对劳动力和货币的转化做了比较理想化的假设,而苏辙对此有着比较切实的体会。苏辙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但通过实际观察,能够提出部分感性体会问题。苏辙能够提出此点,恐怕也有接受同时代人观点的因素,但也应与其接受地方实际政务训练有一定关系。
(四)募役法与保甲法存在矛盾
苏辙虽仍然试图从两税法变迁上寻找理论依据,但已不是空泛论述两税法与庸的变化问题,而是进一步从兵役问题入手加以分析。指出:“盖自唐以来,民以租庸调与官,而免于为兵。今租庸调变而为两税,则两税之中兵费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纳钱免役也,以为终身不复为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于捕盗则用为耆长、里正,于巡防,则用为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将何以堪之。”[1]775虽然苏辙对租庸调制和两税法的理解仍然存有理想化的认知和解释,但他已能够看到募役法在施行中与保甲法存在矛盾,也就是当中下户缴纳了免役钱之后,仍然需要承担相当程度的劳役。换言之,募役法的推行与其宣称要实现的目标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苏辙的这一疑问针对募役法的实际效果而发,已非简单的从历史事件中寻找理论依据。
苏辙的这篇文章,比较明显的反映出苏辙从书生议政向官僚治理的过渡。其思考已能够触及到实际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更为全面,不是仅就问题的某个方面考虑,也开始从现实问题出发思考政策的实际效果。
三、元祐更化时期苏辙役法思想的变与不变
元丰八年(1085年),苏辙重返开封政治中枢,此时苏辙经过了十余年地方官员的历练,已经是较成熟的官僚。其直接论述役法的文献有多篇,另有多篇文献也涉及到与役法有关的人事问题。通过考察文献文本和相关史实,苏辙役法思想及政治策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役法思想体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工具性
苏辙此阶段的役法思想灵活性较大,其坚持废募役法的政治态度,将役法论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在具体政策上,又保留人事斗争与役法政策的分离,“阳废其人,阴用其策”。
其一,苏辙此阶段役法思想首重政治正确,即强调罢免募役法。传统官僚制度下,参与政策的论争首先要有一定立场。苏辙回归中枢不久就在《论罢免疫钱行差役法状》里清晰地表明罢免募役法的立场,提出:“近岁既行免役,民间之敝,耳目厌闻,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矣。”[1]783又言“乡户不可不差,役钱不可不罢”。[1]784清晰地表现出苏辙将役法作为参与党争或者说政治斗争的工具。后续文献中,苏辙也一直坚持这一政治态度。
其二,苏辙延续了此前对募役法弊端的指责。苏辙坚持指责募役法存在若干弊端,主要还是承继其在《画一状》中的观点。一是出钱出力应可以相互替代的问题。“国朝因隋、唐之旧,州县百役并差乡户,人致其力,以供上使,岁月番休,劳佚相代。”[1]849二是免役钱与劳动力转化和钱荒问题。“所取役钱,多收宽剩,民间难得见钱,日益贫瘁。”[1]849认为“百姓久苦役钱”。[1]849
其三,苏辙此阶段的役法思想又体现出较大灵活性。苏辙参与政治斗争,已脱离为反对而反对的书生特点。其役法思想也能够容纳政敌的观点。具体役法政策上已不限于人事纠葛。苏辙当时在政治上严厉打击政敌,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等多篇攻击政敌的文献,却在政策上又对政敌政策予以选用。对募役法在朝在野的代表人物,苏辙对其在人事上充分打击,但在诸多具体政策上,苏辙与后者已没有实质差别。这种“阳废其人,阴用其策”的政治策略表明,苏辙已经老练的参与官僚政治治理活动。其表达清晰的政治立场是为推行具体政策服务。在人事上,苏辙很深的介入了党争,但其又并不以人事作为选取政策的唯一标准。这是书生与官僚的重要区别。书生议政往往过分强调话语本身的神圣性,而官僚治理必然在话语与政策间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二)注重役法推行的可行性
在保证政治正确前提下,如何实际的推行役法政策,是苏辙此阶段考虑的重点。换言之,苏辙此阶段在思考役法思想和推行役法政策中,比较注重役法推行的实际可能性。具体而言包括。
其一,充分考虑恢复差役法的现实困难。苏辙不将差役法看作简单的一言而决的问题,而是事先提醒可能出现的现实困难。提出:“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习贯,兼差役之法,关涉众事,根牙盘错,行之徐缓,乃得详审。若不穷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1]792
其二,给予一定缓冲时间对如何推行差役进行详尽规定,为从容处置役法问题争取时间。苏辙建议:“差役利害,条目不一,全在有司节次修完,近则半年,远亦不过一年,必有成法。”且认为:“一则差役条贯既得审详,既行之后,无复人言,二则将已纳役钱,一年雇役,民力纾缓,进退皆便。”[1]792这既有政治策略的考量,也与苏辙对役法认识深入有关。
其三,以剩余免役钱来解决时间问题。苏辙的主张是用剩余免役钱在一年之内处理善后事宜。“欲乞朝廷指挥,将见在役钱,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却于今年之内,催督诸处审议差役,令的确可行,更无弊害,然后于今冬迤逦差拨,起自来年役使乡户。”[1]792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是一个老练的官僚处理实际实务的套路,一方面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也缓和了一定的矛盾。
其四,考虑财政上的可行性。苏辙在提出暂缓一年处理等问题时,提出了财政上能够保证的具体依据。如“臣窃见州县役钱,所在例有积年余剩。今年夏料虽已放罢,旧余剩钱犹足支数年。”[1]792这是实实在在在处理实际问题,能减少反对者的口实,也能更好地说服决策者采纳其观点。
其五,避免吏治腐败对差役法造成损害。苏辙承认,基层官吏徇私,会对服役者造成巨大损害。[1]849故要多种措施严格吏治,防止官吏侵害服役利益,以避免出现“旧俗滋长,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1]849。
(三)融合新旧役法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政治策略
随着元祐更化的深入,苏辙的役法思想与旧党领袖司马光的观念产生了一定差异。苏辙实际上对新旧两种役法采取融合的方式。但苏辙并未公开反对司马光的观点,而是在肯定差役法基础上,通过修正具体政策来影响决策。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是典型的官僚处理方式。苏辙首先仍然坚持肯定元祐更化役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苏辙的《论差役五事状》常被加以引用。但考察苏辙通篇文章,全文并无一字对元祐更化的役法加以否定。仅仅认为“其间小节疏略差误”[1]805,其对司马光役法大方向是肯定和支持的。这是一种圆熟的官僚策略。但苏辙此篇文献更重要的内容则是在抽象肯定元祐更化的前提下,通过具体策略的否定来加以修正差役法。苏辙此阶段的役法思想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衙前役仍旧雇人服役的问题。苏辙认为,应当保留募役法以免役钱和坊场收入雇人服役,而不使用直接劳役的方法。苏辙认为衙前差役法弊端太大,“破败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1]805募役法施行有很好效果,“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1]805苏辙特别指出,募役法下乡户虽然出免役钱代役会出现困难,但只要将坊场收入用于雇人服役,而不使用免役钱,则必然可以减轻募役法的弊端。苏辙还修正了自己在熙宁变法前所谓雇人系“用浮浪不根之人”的观点。虽还是说雇人服役“不如乡差税户可以委信”,但已经承认,“然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搔扰之患”[1]805。
其二,坊郭人户科配仍以从募役法为宜。苏辙提出,坊郭人户承担的科配,经过募役法变革,已经以免役钱代替实物买卖,“其法甚便”[1]806。苏辙又认为,募役法施行中要求坊郭人户代替科配的免役钱缴纳过重,政策难以持久;但也不宜全部减免此部分免役钱,否则坊郭人户承担的税负反而比乡户农民为轻。故苏辙提出,坊郭人户科配仍以缴纳免役钱代替,但减少部分免役钱数额,减少部分以坊场收入予以补贴。
其三,服役人员数量以募役法核定数量为准。差役法核定的服役人员数量过多,“熙宁以前旧法人数显是冗长,虚烦民力”[1]807,故应当以募役法所核定人员数量确定服役人员数量。如确实存在人员差额,也从坊场等收入中予以补贴。
其四,散从、弓手、手力等劳役仍按募役法出钱免役。因这部分人员旧法下服役时,“常苦接送之劳,远者至四五千里,极为疲弊”。[1]807而募役法施行效果较好,故还是应当依照募役法实施,并以坊场收入予以补贴。
其五,关于州县胥吏服役问题。苏辙的态度是根据其自愿,准许其缴纳免役钱或者以身服役。这也是苏辙在《画一状》中所谓“有力而无财者,使效其力,有财而无力者,皆得雇人”[1]774思想的一部分衍生。
其六,坊场收入用于补贴免役钱,减少民众负担。苏辙在论述到雇人服役出现免役钱不足问题时,始终强调国家应垄断坊场并将收入用于雇人以弥补免役钱的不足。其在讨论每项具体措施上,都提出了以坊场收入加以补贴的问题。多提出“于前项坊场、坊郭等钱内支还”[1]806-807。还另有专文讨论特殊地区的坊场补贴问题,提出:“不宜为边费夺坊场钱,专差衙前以困民力。”[1]835这体现出苏辙一贯对聚敛财富于国家的否定。这是其在役法思想上与熙宁变法诸公的实质区别。
可见,苏辙实际上在抽象肯定差役法的基础上,以募役法的诸多政策对差役法加以修正,以差役法旧瓶装募役法新酒。其役法思想中的政策取向已与募役法相差不大。更多是企图融合募役法与差役法的优劣做政策上的调整,使之更为适应现实。其具体政策又是对差役法的否定。
四、苏辙讨论役法思想的言说方式变化
元祐更化后,苏辙役法思想更加全面成熟,除役法本身内容外,其表达役法思想的形式也值得分析。表达形式是思想内容的外在反映。苏辙讨论役法的言说方式转变也能够反映出其思考方式的转变以及其政治治理水平的提高。
苏辙言说方式的转变大致有这么几方面的内容。
(一)从宏大问题转向具体问题的讨论
苏辙此前讨论的都是应当采取募役法还是差役法此类大问题,并未就役法涉及的具体问题加以探讨,无非笼统的全盘加以否定募役法。但元祐更化之后,苏辙则转为讨论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诸如,差役法施行时间,应当如何处理剩余的免役钱,各类人户和劳役项目如何处理。换言之,此时苏辙讨论重点不在于到底实行募役法还是差役法本身这一宏大问题,着重讨论的是针对诸如衙前役是否应当雇人这类具体问题。其所讨论的问题往往都带有实际操作性。用现代语言讲,其从宏观叙述的讨论,进入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进入到技术官僚的治理方式讨论。应当说,苏辙此时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成熟经验的官僚。当苏辙本身不具备决策权,仅具有一个秘书人员身份的时候,谈的都是宏大问题。当他进入到决策圈子,反而开始讨论一个个具体的实际问题。这个转变,耐人寻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苏辙之前不需要处理具体事务,可以放胆高论,但当处理具体事务时,自然需要对一项一项的工作进行具体落实。
(二)立论依据从厚古到厚今,从理论趋于现实
从苏辙立论的具体依据来看,也趋向于从实际发生的事实出发加以立论作为依据。而非以正确但较为空洞的道理来作为立论依据。从现实中寻找依据,而非从历史中加以比附。此前苏辙有关两税法等论述,固然显得学识渊博,但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并不强。对比苏辙的立论依据可以发现,在熙宁变法时期,其论证方法主要以抽象的理论演绎和比附历史事实为主,以圣人言说、文史观点等作为立论依据,如论述募役法的现实弊端,并没有深入考察和分析。此种论说风格是写文章的好方法,但未必是讨论实际政事的方法。但元祐更化后,苏辙则是从役法能否实际施行问题出发来寻找立论依据。此时苏辙讨论问题,一般都是从现实中提出相关的依据,以现实中存在的事实,作为支撑自己观点及推行政策的依据。如其提出要加强吏治,避免损害,就不是抽象的讲一番大道理,而是以“近日诸县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参上下费钱有至一二十千者”[1]855这类实际现象出发加以论述。
(三)役法言说中注重数据
苏辙后期役法言说,强调计算,也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数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翻检苏辙地段时期讨论问题的其他言说,也有此特点。仅就役法讨论而言,衙前问题的讨论中此特点表现就很充分。苏辙早期论述衙前问题无任何计算,但后期就对坊场收入、衙前役支出等进行详细计算,将数目计算比较准确,算出“今来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所得共四百二十余万贯,若立定酌中价例,不许添价划买,亦不过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贯。”[1]805-806再在此基础上表明自己的观点,这种重数据的言说方式是由讨论问题的具体性所决定的,探讨具体问题,不可避免的需要涉及到财政收支能否支撑。而详尽准确的数据,又可以为论说提供更为有效的论据。
(四)言说文风趋向平实沉稳
早期苏辙讨论役法的文风,还是保留战国策士之风,议论滔滔,文采飞扬。但后期文书文风平实沉稳。不追求以文字本身的华丽来说服他人,而是企图依赖自身的逻辑力量和现实依据达到论证的目的。这既反映出其文字水平的提高,也是其思想水平更为沉稳的反映。
言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思考水平和深度,反映了其思考方式的转变,其思考更为全面深入。苏辙这种言说方式的转变,与其长期担任下级地方官吏的后期经历有重大关系。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职,为签书应天府判官。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牵连苏轼诗案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辙被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6]46、55、67前述谈到苏辙役法第二阶段时论述过一些苏辙这个时期的经历。但应当说,苏辙此前还是更多的处理一些文字工作,担任的也是清贵学官和文字幕僚,对实际政务亲自参与处理不多。但自熙宁四年后,签判需辅助地方首长处理实际事务,盐酒税从事基层的基础工作。歙州绩溪县令则是地方长官,这些职务都需要亲身处理实际事务,与坐而论道的书生和以教学理论工作为主的学官,在处理方式、思维方式上都有本质差别。史料反映出苏辙这段时期多有处理实际事务的内容。如其自述担任盐酒税的生活,“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尺寸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1]507又如其在担任县令时,还需要处理马政事务。[7]53-54
这些基层的实际治理经历,为苏辙的役法思想转变起到较大作用。苏辙自己对此也有所领悟,苏辙诗讲“少年读书不晓事,坐谈王霸了不疑……归来掩卷汗如雨,平生读书空自误”。[1]210固然与当时苏辙对自己及苏轼政治失意的抱怨有关,但也多少表达其对于自己少时坐而论道,不晓实际政务的反思。
注 释:
①对变法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为论证其观点都注重引用苏辙有关役法的论述。代表文献参见漆侠:《王安石变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225页;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249页。
②现有专门研究苏辙役法思想的文献仅见杨胜宽:《苏轼兄弟役法改革异同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09-111页。在研究苏辙政治态度的文献中,有部分内容也涉及到苏辙的役法思想,参见李天保:《苏辙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37-46页。
③有关上户下户的争论文章较多,意见并不统一,但反映出现实中存在各种复杂情况,参见朱瑞熙:《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5年第7期,第23页。
④从苏辙文中“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的表述来看,这里的城郭人户显然是指具有兼并土地能力的中上层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