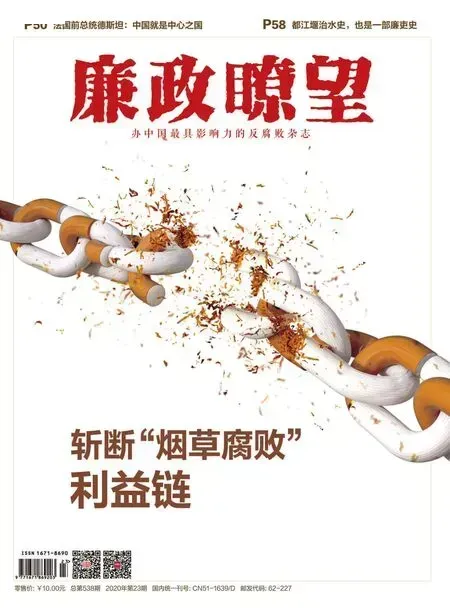苏辙骂皇帝不为拆台为补台
文 刘诚龙
有 人说苏辙是愤青,常搞激烈猛论,是他太年轻了,说话干活不老成。这么说,好像只有年轻,才那么莽撞,可是,“愤老”也挺多,“老”羞成怒的数不清。有怒则怒,当愤须愤,不关年老与年少,只关正义与奸邪。
苏辙20来岁时千里迢迢从四川老家来到京城参加科考。这次考试题目是:试论当下大宋在民生、军事、教育、财政、法制、行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题目好大,叫一个20 来岁的人来写,也是为难。以前科考,都是写一首或几首诗,顶多是写篇议论文,王安石当政后,改了科考内容,由作赋转为申论。毕竟从政,还真不需要什么诗词歌赋。
苏辙拿了题目,挥笔就写,洋洋洒洒,文不加点,一口气铺排了六千余字。苏辙先从宋仁宗骂起,接下来骂了宰相、三公、六部,再骂九卿、百司,从民政到军政到财政到行政,骂尽诸色。
他骂宋仁宗是这么骂的:“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这话翻译为市井语,便是说皇帝流氓成性,金屋藏了许多娇,基本不办公。苏辙还骂宰相:不用忠臣,多用奸猾,“宰相不足用”。
主考官是胡宿,他阅到这一卷,背脊嗖嗖发凉。胡宿担心自己受连累,不想录取这个考生了。另一位考官叫范镇,他说这位考生文采见识都了得,文胆尤其惊人,是个人才,这样吧,录倒是能录,但状元、榜眼、探花不能让他做,“欲降其等”,评个会元之类的吧。
到了司马光那一环节,他拍了桌子——不行,这般好文章,如何不给好名次?当上上等。你们不敢录取,我向皇帝陈情去:“文辞如何,臣不敢言,但见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则臣恐天下之人皆以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
录取官司先打到三司去。三司也是挨骂的,其时三司一把手是蔡襄,他笑了笑:“苏辙骂我,一部分批评得过了,大部分却正中三司之弊。”他认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面对这位考生的批评,只有惭愧,不敢怨怒。
有人叹,中国人的人性自先秦后,已由清澈转为恶浊,失言矣。不说人性,便是官性,在宋仁宗这时候,还算是澄明的。
录取还是不录取,高等次录取还是降档次录取,最后决定权归皇帝。宋仁宗看了这份试卷,先是脑门冒汗,随后又释然:“设制科本求直言,苏辙小官,敢言,特命收选。”朕多次说要求直言,直言来了却打压,那天下如何看朕?于是,苏辙被录取了,但档次没如司马光意,只取第四等。
苏辙这张试卷,除了批评过激外,其实还偏了题。题目叫他论如何行政,他却批评行政者个人行政不对。单此一条,不录取苏辙,也足可封天下口——偏题的,打零分嘛。
但苏辙批评不对吗?基本面是对的。官员懒政惰政、不作为乱作为、搞腐败有作风问题的还真不少。这样来看,苏辙没错。
可见,搞批评的关键在于批评到根本,苏辙洋洋洒洒不留情面的六千余字,纯出于忠君爱国,是想推动朝廷往前进,这个一定要分清。司马光看得准,苏辙虽批评过激,但他不是在拆台而是在补台,“独有忧君爱民之心”;宋仁宗也眼明心亮,看出了苏辙之根本,他就容许了苏辙之基本:“而辙也指陈其微,甚直不阿。虽文采未极,条实未究,亦可谓知爱君矣。朕亲览见,独嘉焉。其以辙为州从事,以试厥功。”

苏辙在科考中直言敢言,指出各种弊端。
--2015)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