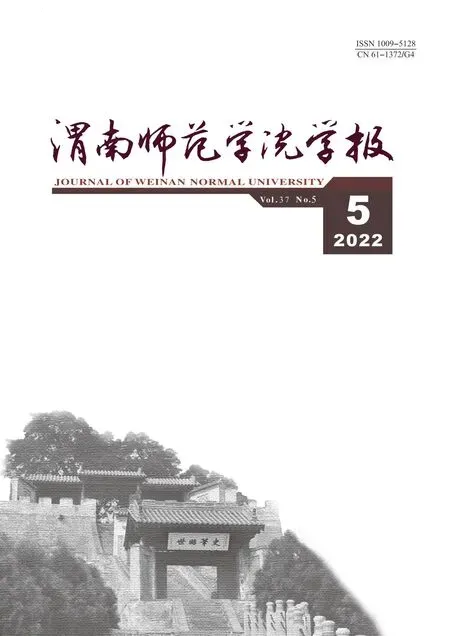简约语文理论的四重研究视野及其启示
汲 安 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南京 210044)
“简约语文”是当代语文名师丁卫军倡导与建构的一种语文教育教学理论。主张从教学目标制订、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流程设计、教学方法使用等方面,均要追求简约。简是形式,约是本质,在二者统一的过程中,达致语文教学的精约、博约、雅约之境,进而实现学生语文人生的丰美,达成学生生活的丰美,言语生命的丰美。
在当下众多的语文教育教学理论中,简约语文因为有对中国“博约”教育传统的个性化承继,对西方简约主义思想的辩证吸纳,对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育出现的浮华、错位之风的拨乱反正,对语文教育回归本真的呐喊,还有对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认真落实,对语文核心素养积淀的扎实践履,对学生言语表现与创造力牧养等重要理论话题的创造性回应,正愈来愈绽放其独特的魅力。丁卫军老师在全国20多个省市执教简约语文公开课不下300场,东北师范大学、南通大学、聊城大学、渤海大学、宝鸡文理学院等众多高校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将简约语文教学理论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的更是不在少数。山东师范大学曹明海教授称简约语文是“着力于语言建构的人气课堂”,把握住了“语用与生命同构的真义,彰显了语言建构的‘人气课堂’所特有的‘生命的魅力’和‘灿烂的亮色’”[1]。
其实,深入至研究视野层面,更能发现简约语文理论中蕴藏的简朴、宏阔、大气、灵动等亮色以及令人神往的思想生气。
一、简约语文的哲学视野
任何学科教育,上升到哲学层面,都是相通的。学科教育缺少哲学视野的观照,只能在低层次的感性经验中徘徊,难以触类旁通,行之久远。
简约语文理论蕴含的哲学视野,体现有三:
一是关于简约语文的本体性思考。本体性思考务虚、形而上,与偏于务实,比较形而下的教育策略、方法、技能等方面的思考迥然不同。如果说后者着重于教什么、怎么教的思考,前者则深入到了为何教的层面。落实到简约语文,则要思考语文教育为何“简约”。
这方面,丁卫军老师从老子的“少则得,多则惑”(老子《道德经》),孔子的“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戴胜编《礼记·乐论》),庄子的“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乱耳,使耳不聪”(《庄子·天地》),《易经》中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到秦砖、汉瓦、宋瓷、明式家具以及宋代马远画作《水图》和元代画家倪瓒《渔庄秋霁图》中渗透的简约之美,再到当下黄厚江、于永正等语文名师教育主张中的简约因子,非常清晰地回答了为何要践行简约语文的问题:与真善美相连,与人生的境界相关,这不仅是自然之道、人生之道,也是艺术之道、语文教育之道。
西方的简约主义思潮滥觞于20世纪初期西方的现代主义,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盛行于建筑设计领域,后向雕塑、绘画、音乐以及文学创作领域延伸,强调设计的元素、色彩、照明、原材料简化到最少的程度,并将之与简约语文打通,凸显其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魅力。
简约语文吸纳了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潘新和、李海林、周铭三、曹明海、程少堂等人关于“语文是什么”的思考后,对内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可以理解为简朴、简明、简要、简化、简洁、简练、简便,涉及语文教学的目标制定、内容选择、流程设计、方法使用等等方面。‘简’只是一种形式,‘约’才是它的本质,才是他的灵魂……简约语文的终极目标是以简约化的路径实现学生语文人生的丰美,达成学生生活的丰美,生命的丰美。”[2]8-9
简约语文的本体性思考,有对“简约”的语文教育哲学追问,有对语文学科史的精心梳理与审视,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聚焦和沉思。《简约语文课堂——走向内在的丰富与诗意》一书就明确提出: “文本被多元解读泛化,文本本身具有的精神内蕴丢失;文本被拓展延伸虚化,文本变成一种话题的提示材料;对话的肤浅化,阅读课堂多了一份热闹,少了一份沉思;形式的复杂化,阅读课堂多了亮丽的光彩,少了一份灵动。”[2]4对语文教育愈演愈烈的无本、无魂、无深度、无灵动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这种本体性思考,无疑是富有理论价值的。不管什么语文主张,也不管研究语文教育的什么领域,都必须基于语文教育史,进行自觉的本体性追问。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会通、历史与现实的会通。当下语文教育,乐于关注的多是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对形而上的本体性思考却极力排斥。比如,谈阅读、写作,常常聚焦于“读什么”“怎么读”“写什么”“怎么写”,就是不思考“为何读”“为何写”,觉得这种思考太空。这必然导致学生语文学习深层动力的缺失,过分在功利性目标的追求上乐此不疲,而教师则会在不知不觉中放逐“为修身”“为存在”的高远追求,斩断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优秀文化传统的联系,对西方教育文化中的先进思想也会持鄙夷态度,进而导致语文教育境界的狭隘与低下。
难能可贵的是,简约语文的本体性思考,也涉及中国先哲和西方简约思想的会通。在简约语文论者看来,中国先哲的简约思想,主要是指人和自然、社会相处时,所获得的关于简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西方简约思想则始于建筑领域,后来延伸到音乐、绘画、文学等领域。两相比较,前者更多地偏于思想层面,后者更多地体现于操作层面。如果说本体性思考让我们知道语文教育“为什么”,基于学科史的思考,让我们知道语文教育“有什么”“是什么”,那么注意中西母语教育贯通的思考,则会让我们知道语文教育“怎么样”“如何走”。
比如,谈到立足学情的教育,完全可以将孔子的“愤悱”思想与美国教育家布劳姆“增润教学”(Enrichment)理论会通——绝大部分(95%)学生,只要得到适切的教学,可以做到学业优秀,充满自信,因为学生的学习差异主要成因是环境因素引致。适切的教学自需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程序,对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励和增润,对能力稍逊的学生提供纠正和补救指导。[3]171自觉注意学情诊断,因势利导,因材施教。至于说人有我无,人新我旧,人家坚持,我们忽略的,也完全可以持“虚室生白”的心态去审视、吸纳、更新,创造性化用。当下语文课评价标准中,教师们越来越重视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教者所提问题的挑战性,学生回答问题的质量以及教者的评价质量,不正是对西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话理论的辩证扬弃,所形成的健康蓬勃的思想生态吗?
简约语文的本体性思考中,还涉及学科融合的思想。建筑、音乐、绘画、家具设计等领域中的简约思想,均有与语文教育贯通。《简约语文课堂——走向内在的丰富与诗意》一书要求语文教师要有艺术素养、科学素养,致力于学科的融合。这不仅契合了世界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方向,也顺应了语文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语文教育要想获得不竭生气,必须在学科融合中尽情吸纳各种思想营养。当下不少语文名师显然颖悟此道,教《采采芣苢》一诗,从节奏视角将之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休斯的《黑人谈河流》会通,以突出其与古典音乐、爵士乐不同的越来越快的抒情节奏,这是语文与音乐融合、触发的结果;教鲁迅小说《孔乙己》,从文本中两幅显在的孔乙己肖像画入手,联系两幅隐在画面——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孔乙己形象,还有落魄潦倒、凄惨离世的孔乙己形象,引导学生体味鲜活生命力遭遇凌迟的命运,这是语文与绘画融合,产生的全新审美气象。
当然,简约语文本体性思考,最终是要回归语文教育的现实土壤。任何一种语文教育理论,必须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且能提出行之有效的教育原理或对策。不能理论和实践两张皮,各自为战,自我封闭,自我陶醉。简约语文的基本特征:教学目标简明,教学内容简洁,教学过程简化,媒体运用简便,无疑为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了比较具体的思维把手,有效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会通。这正是日本学者佐藤学欣赏的“实践性见识(practical wisdom)”——是以教师对教学过程中展开的省察、选择和判断,进行反思和批评为中心的探究活动,与“××研究”相反,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对跨学科的综合性知识进行整合所形成的[4]7。
二是对语文教育终极目的的回答。关于教育的终极目的,中西很多先哲都有阐述:西周官学的教育目标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苏格拉底认为是“知识及道德”,赫尔巴特也把“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最高目的,杜威更是明确地宣称“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5]406-472。当下中国“立德树人”教育目标,与这些思想本质上是相通的。
但是,立德树人是所有学科教育的任务,语文教育的特色在哪里?2022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是这么表述的:“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有效地沟通、吸纳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素养,促进自身的健康成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着力发展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尽管提到了“感受语言文字及作品的独特价值”,但“语文特色”还不够凸显。科学素养、文化素养、终身学习能力、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的培养,这些说法更是淡化了语文性,因为这些内容,其他学科教育也关涉。
简约语文理论认为:“遵循汉语文的基本规律,在简约化的教学中达成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丰富学生的知识,陶冶学生的性情,锻造学生的意志,提高其人之为人的人格修养。”[2]8遵循汉语文的基本规律,达成语文素养的提升,这是在增强“语文”特色。学科融合需要追求,但是学科体性、特色更需坚守。弥足珍贵的是,简约语文还提出了“陶冶学生的性情、锻造学生的意志”的目标,使语文知情意素养的立体培育、有机培育变成了自觉,让语文教育有了情感的温度——当下语文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偏于“知”素养,对“情意”素养培育是有所忽略的。这一点,统编本语文教材负责人王本华在《新时代的阅读教学》一文中已经指出:“语文核心素养还可加上情感培育问题。在这个时代,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智力因素,更要关注学生的情商。”而对语文情意素养培育的重视,简约语文理论是一以贯之的。该理论认为:“关注学生的情感、兴趣、信念等学习动机的主要诱因,恰当地激发,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83所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激发学生学习积极的情感,成了简约语文永恒的教育追求。当下教育为什么缺乏温暖感: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渐行渐远,学生之间也充满了防范、算计,甚至出现校园霸凌、厌学自杀等极端异化的心理现象。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教育中情意素养培育维度的缺失,绝对难辞其咎。
在这种情形之下,简约语文注意情意素养的培育,绝不泛泛而谈,而是与文本的实际、学生心灵的实际紧密结合,且将之指向学生言语生命的牧养,有意识地培育学生的言语人格、言语情趣、言语信念、言语想象,从而在情意维度上也守住了语文体性,突出语文的特点。
三是语文学习方式的思考:占有,还是存在?占有式学习(to have)和存在式学习(to be),是美国教育家弗洛姆提出的两个重要范畴。占有式的学习偏于记忆、理解、积累;存在式学习是指在此基础之上,将知识积淀不断激活,走向独立的精神创造。这一思想在欧美国家得到了呼应。法国前教育部长吕克·费希就特别强调:“相较于‘占有’的逻辑,我们必须帮助孩子们赋予‘存在’逻辑以更大的重要性。”[6]40
但是,这一思想并未被许多教师所觉知。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了一百多年,分别经历了知识本位、能力本位时代,当下已步入素养本位时代。这体现了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进步,但是与存在思想比起来,境界还不够阔大。积淀语文素养固然没错,但是积淀之后呢?难道仅是为积淀而积淀,或积淀之后炫耀占有的丰厚,所谓“学富五车”吗?这不还是占有式学习的水准吗?理想的语文学习,一定是在占有、融通之后自觉走向言语表现与创造,让存在本位思想高扬,不断为言语人生、诗意人生蓄势,这才是语文教育之应然。
那么,简约语文理论是如何呈现占有式学习和存在式学习关系的思考呢?《简约语文课堂》一书引用了叶圣陶的观点,“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点在‘行’,能达到‘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主张语文“不仅要教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和语法规则,还要让学生去思考、表达、读写和做事,培养他们真实有效地运用语言的能力”[2]61。似乎与叶氏语文观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谈语用,但特别强调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并且倡导“面对文本,教师要机智地引导学生质疑,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这便有了存在式学习的思想萌芽。在《简约语文课堂的教师素养》一章中,论者又呼吁语文教师应成为智慧型的教师,“使自己的教育教学角度独特,路径清晰,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独特角度,就是在凸显自我精神生命的出场,这是存在式学习的本质。立足致用,又超越致用,再坚定地走向致在,这是很明澈、睿智的。
简约语文理论也受到了中国语文教育重创造传统的濡染。东汉时期,王充提出了“各以所禀,自为佳好”(王充《论衡·自纪》)的主张。虽然被当时征圣宗经的思潮所淹没,但并不影响有缘人得之。唐代韩愈就发出了“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的呐喊。民国时期语文教育家夏丏尊先生也提出:“文章是表现自己的,各人有各人的天分,有各人的创造,随人脚跟,结果必定抑灭了自己的个性。”[7]3当代学者潘新和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语文教育从表层看,是培养‘言语表现性和创造性’;从深层看,是培育人的‘存在性的言语生命意识’。语文教学就是对人的言语生命潜能的发现与唤醒。因为人是言语的动物,写作的动物。言语能力的发展是基于人的言语潜能,是一种生命冲动,是言语生命的自成长、自生长、自发展。”[8]291
简约语文理论对思维批判性、独特性的强调与践行,对破解现实语文教育问题的执着,正是对上述思想的呼应。
二、简约语文的语文视野
如果说哲学视野的审视,在宏观上完成了简约语文的本体性思考,那么语文视野的审视则更多的是在中观上完成了简约语文专业化、科学化的思考。这对当下那些看似高大上,其实空洞、浮华,无补于语文教育现实问题解决的所谓“××学”视域下的语文教育研究,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驳。
首先,关于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关系的思考。如何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始终是百年现代语文教育探讨的热点。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受传统大语文思想的影响,加上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语文科内容包囊万象,这令很多先觉者困惑:什么是“语文”的内容呢?夏丏尊认为体现语文科内容的就是“言语形式”——词法、句法、章法之类。国统区和解放区分治时期,语文教育又有了主副目标之说——主目标是读写能力的培养,副目标是情感意志方面的熏陶。因为后者是所有学科都承担的使命,读写能力才是语文科的独任。新中国成立后,又有语文名称的变化及其内涵的争论,从叶圣陶的“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到后来的“一语四文”(语言+文字、文学、文章、文化),至今没有定论。1963年,语文工具说开始出现,再后来人文说崛起。2001年,语文性质被定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21世纪,争论较多的是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可以说,这些热点基本都是围绕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关系展开的。渐渐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言语形式(形)和言语内容(意)统一的过程中,突出言语形式。
简约语文理论推崇这样的文本细读:“主要是对文本的言语、结构、主旨、象征、修辞文气、文体等因素进行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仔细解读。细读的过程应该是仔细领会言语内在的精细微妙之处,仔细品鉴言语的节奏、情韵和机理,仔细质疑隐匿于作品缝隙间的旨趣。”[2]50显然也是认同在形意统一过程中突出形,以捍卫语文体性的,且遵循了从言语形式到言语内容,再返回言语形式的解读路径。不过,与偏重于言语形式知识的观点相较,简约语文并未忽略言语形式表现的智慧——言语内在的精细微妙之处,隐匿于作品缝隙间的旨趣。这无疑丰富了“言语形式”的内涵,对“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王骥德《曲律·杂论》)的传统观念也是一种勇敢的突破。言语形式知识可授,言语形式表现的智慧可悟,并为此多多着力,这何尝不是存在式学习的别样表现?
其次,对类性辨识、篇性开掘的重视。类性指文本的文类特性,篇性指文本中体现的作者独特的言语表现个性与智慧。[9]注意类性辨识和篇性开掘,是语文专业性的集中体现。丁卫军老师谈的是文类的下位概念——文体,但因为前提不一,有时也指文类。他说:“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话语系统,引领学生走进文体的话语系统,需要找突破口。”[2]66并以微型小说《窗》为例,谈到一定要注意把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文体特点[2]66。这说明,他是很关注类性辨识的。
不过,简约语文论者的类性辨识主要是在遵类的前提下进行。对跨类写作、悖类写作的审视,似乎还不够。伟大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跨越文类的特征进行个性化创作,比如说郁达夫《故都的秋》。有的学者说郁达夫的思维很混乱,怎么开始的时候写故都的秋比南国的秋来得有味道,清、静、悲凉的特点很显豁,结尾又来一次,说这个南国之秋不如北国之秋有味,这就好像黄犬之于骆驼、鲈鱼之与大蟹,甚至要牺牲三分之二的阳寿来换取三分之一的故都的秋的零头,实际上是不懂郁达夫将诗歌的极化情感写法带入散文的跨类创造,通过首尾呼应的方式,将自己对故都之秋那种不可救药的痴迷全部释放出来了。
悖类,是跨类不成功导致的。现行语文教材中的选文,悖类的应该没有,但我们依然要引导学生注意悖类审视。因为在课外阅读时,难免会遇到此类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散文家杨朔的《荔枝蜜》就是一例:参观养蜂厂,与蜂农交流后回家,说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这是套路化的立意,十分矫情,诗歌的极化情感既未遵循生活逻辑,也未遵循情感逻辑。
篇性开掘在简约语文论者的教例或教例评析中表现得较为充分,比如《孤独之旅》中的“双色同体”——生活的磨难,冷色调,温暖的希望,暖色调;《春》文字中蕴含的诗意,婴儿眼光;《斑羚飞渡》中的心理留白和情感逆行结构,教师都带领学生挖掘到了。教学方法上,或艺术还原,或诗行呈现,或矛盾追问,做得风生水起。
再次,还关注语文性质的自觉落实——基于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言语性。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以数学学科为例,数学没有工具性吗?缜密思维、建筑测量、经济贸易,哪一样离得了数学,这些不都是工具性的体现吗?在数学学习中,感受数学思维之美,数学家的钻研精神和探索毅力,这些不都是人文性的体现吗?如此一来,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属性,数学学科也有,其他学科亦然。
潘新和认为“语文课程的种差就是言语性”,“这种言语性不但是实践层面、行为层面的特征,而是素养层面,动机层面的特征,是言语表现体现的人文性和存在性”[10]139。这种基于工具性、人文性统一之上的言语性,可以说是对语文科的准确定性,因为其他科无需承担彰显言语性的使命。简约语文理论也涉及语文科性质,虽然没有明确定位为言语性,但在教育实践中无不在渗透言语性。丁卫军老师说:“我和学生们认识到不指向写作的阅读是低效的,把阅读和写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读写共生。”[2〗4对文本细读,他强调要“品咂字里行间的滋味,借他人的文字认识自己的心绪,获得生命启示;写作回归本真,序列教学,力求丰富学生写作经历,积累写作经验,激发想象力,培养创造力”[2]288-289。
在渗透言语性的过程中,简约语文非常强调独立思考力的培养:不断地走向文本的更深处,挖掘篇性;不断地走向生本的更近处,培育学生灵魂的质量,努力借声发声,借力发力,借光发光。不过,这种致在维度,简约语文论者并未明确提出来。倘若明确下来,并积极探索,实现致用、致美、致在的浑然统一,简约语文应该会走向更加阔大、高远的境界。
又次,教学有非常鲜明的问题分析意识。简约语文论者对学生存在的问题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自觉,《简约语文公开课》一书中这样写道:“学生不是没有什么可写,而是缺少关注生活、思考生活的自觉,学生的肉眼打开了,心眼是遮蔽的。没有经过心灵过滤的生活,怎么会有个性呢?”可见对自己,作者也不放弃拷问。教学《人又少了一个》这篇文章,他通过和学生对话,剖析了自己的弱点——忽略学生主体的存在,有点自说自话。既审视学生的问题,又能拷问自我的不足,这不仅需要责任、智慧,更需要勇气。
最后,就是言语生命牧养的意识。简约语文不仅关注到学生言语表现知识、技能的培养,还关注到言语人格、言语情趣,并努力激情激趣,将为学与为人有机统一,将知情意素养的培育化为现实,这正是比一般语文人思考缜密和超前的地方。
三、简约语文的史学视野
如何具体有效地渗透言语性、辨识类性、开掘篇性,更好地牧养学生的言语生命呢?
这便触及了史学视野的观照:
一是立足语文教育史的观照。简约语文论者对中国先哲简约思想的梳理,对西方简约主义思潮的概述,对语文内涵界定的回顾,均有史学观照的意识,且努力将之纳入简约语文发展史的脉络中来。
语文教育需要聚焦现实问题,更需要立足学科发展史,这样才能既知道来路,又知道归路。以解读一篇文本来说,不知道历代学者对此文本的钻研有几种视角,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思考达到何种高度,再研究还能从何处突破,一味自我封闭,进行所谓的素读,真能有质的突破吗?素读固然重要,这是深度对话的前提。但是,如果完全撇开文本解读的历史梳理,想创造性地“接着说”,估计很难。
这是常识,可惜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一些所谓的名师,甚至在公开场合称“从不看建国以前的著作”。如此武断地切断学科史源流,还能指望其在语文教育中有所建树吗?自以为当下学者的书已经陶铸百家,融会贯通,为图捷径看看他们的书就可以了,这种把流当成源,本末倒置的做法,并非真正的基于学科史观照。真正的学科史观照,一定要将思想的触角努力伸向源头,尽最大可能地把握历代语文名家的思想,从而形成整体观照、动态观照的自觉。这样,真正的思想对话才会发生,学科史才会真正流过精神的河床,也才会真正吸纳前人思考的能量。
说到真正的思想对话,简约语文论者在梳理前人学术成果时,是非常自觉的。比如,在谈整合性的语文教学时,简约语文论者便将余映潮、于漪、王君三位老师的“整合观”带进简约语文的思考体系中来,和他们构成了一种颇有深度的对话。但是,对话并非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解决语文教育的现实问题,并能形成属我的思想创新。简约语文的哲学启悟来自先贤,但是丁卫军老师赋予了它语文学的内涵,这便是一种创新。其他诸如新范畴的提出,新理念、新教学法的归纳总结,与此同类。比如胡适先生当年提出的“活的教学法”——质疑、辩论、演讲,孙绍振先生提到的“还原法”——艺术的还原、历史的还原等。关于新鲜的教法,简约语文理论体系中有不少,值得好好借鉴。
二是立足文学史的观照。从文学史的视角观照文本,常能有新的发现。比如欣赏秦观、贺铸、周邦彦的词作,基于词创作史、文学史的角度来审视,会发现就意象抒情来说,已从李煜等人的单维度抒情,到了秦观、贺铸、周邦彦的多维度抒情。“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江春水,就是一个单维度的意象。“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则不是,它的意象是集团性的,是博喻式的,天女散花一般。就情辞关系来说,已经从词诞生之时的情胜,到后来苏东坡的辞胜,再到秦观、贺铸、周邦彦的情词相称,变化颇为了然。就心物关系来说,已经从“我—它”关系,如韦庄笔下的江南春色就是外在于心的存在;发展到“我—你”关系,如晏殊笔下的落花与燕子;到秦观、贺铸、周邦彦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我—我”的关系,如“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飞花、丝雨已经与我同构了。
简约语文理论中也有文学史的观照。比如讲朱自清的《春》,会将林斤澜的《春风》引进来;讲朱自清的《背影》,会和龙应台的《目送》比较。也就是说,将不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联系起来看,然后看他们抒情的力道、风格、主体、视角等方面的不同,这便有了自发的文学史观照意识,利于学生把握其间隐含的作家创作取向上演进的轨迹。尤其是散文抒情风格上的突围,自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后,抒情散文的风格基本上是唯美、温婉的,而林斤澜的散文则带有阳刚、生糙的风格,龙应台又有挣脱抒情散文,向哲理散文归趋的努力。倘若教者有意识突出文学史视域下的文本解读,应该会有更多的审美发现,也更能触摸到作家不甘平庸、勇于突破的言语人格,这自然会对学生言语灵魂的牧养起到重要的滋养作用。丁卫军老师教学中引用了华东师范大学倪文尖的解读,而倪氏解读的史学观照意识是很强的,在单篇的《背影》中都能见出“悠长的朱自清的生活史、情感史、思想史”。这种文学史视域下的审美观照,简约语文理论还可继续深入探索。
立足文学史的观照是纵向的,还要注意横向的互文性比照。比如讲柳宗元的寓言《黔之驴》,从文学史视野将之与先秦诸子寓言比较,会发现人物形象的塑造从漫画化走向了写实化,寓意从单维度走向了多维度。而进行横向的中西文化比照则会发现:西方的寓言塑造人物形象,天神、国王这样的“大”人物都无法幸免,而中国的寓言通常是些小人物、小动物;寓言传递的通常是一种共识性的认识,而中国寓言在传递共识的过程中,还会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与认识带进来——《黔之驴》何尝不是柳宗元自我生命的一种写照?像黔之驴一样,被“好事者”皇帝放到了一个不该放的地方,最后命丧他乡,有才也发挥不出来。这种横向比照的意识,简约语文论者也是有的。在讲《皇帝的新装》时,他引入了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儿女》中的相关论述,把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埋藏的哲理一下子很丰满、很独特地表达了出来。
立足文学史的观照,简约语文论者还注意了与学情的结合。他提倡品评作品,一定要“勾连生活,打开心灵,丰润生命”。生活主指学生的生活,生命主指学生的精神生命,只有丰润了学生的精神生命,语文教育的雅约之境才能实现。他认为“课堂即对话,是师生生命、心智的交往的过程”[2]27-66,因此,呼吁师者做机智的倾听者,捕捉教学的生成点。比如,教学《台阶》的生成点就是从学生所说的“父亲很可怜”切入的,由父亲的理想,再到闰土、杨白劳、旧毡帽朋友等人物形象折射的旧中国农民命运,以及当代农民的思想生态,将小说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时代性、超越性,很好地揭示了出来,讲得非常大气、饱满、通透。《学记》中所说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和易思”思想,古罗马昆体良的“节制自我力量,俯就学生能力”的思想[5]326,被他水乳交融地贯彻了。
四、简约语文的美学视野
简约语文理论中的哲学视野、语文视野、史学视野,最终都是融于美学视野的,这或许是其朴素却更容易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
美学视野的观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这一理念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神形象。宙斯虽为雷电之神,万神之王,但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偷香窃玉。为了达到目的,常会把自己化装成翩翩美男子,来俘获美女的芳心。比如,骗人间的美女西弥丽、欧罗巴,都是用的这种方法。后世美学家们从中获得启示:要想让自己的理论富有魅力,深入人心,必须注意理性与感性的融合。太理性抽象难懂,高处不胜寒;太感性,琐屑肤浅,难以给人启迪。
简约语文论者显然知晓其中奥秘。虽然注重感性、注重学情,喜欢抓住一些具体的细节展开教学,但其间的思索一直存在。比如教《社戏》时融入的五大追问:题目是 “社戏”,为什么还写了偷豆?极偏僻的平桥村,为什么却是“我”的乐土?双喜到底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六一公公的豆被“偷”了,为什么还那么感激?戏未必好看,豆未必好吃,为什么还那么怀念?这种感性与理性相融的追求,很能让学生挖掘出文本命题、形象塑造,还有立意上的篇性,提升他们的审美品质。在《背影》一文的教学中,丁老师引进了下述研究资料:朱自清的写作缘由介绍,清华附中特级教师王君整理的朱自清年谱(简约版),倪文尖解读《背影》的忏悔说,陈日亮解读《背影》的“沧桑感”说。为了增强感性,还把龙应台《目送》中的哲思性语段引入——“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这就为学生的审美提供了一个非常辽阔的视域,而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细节审美紧密结合在一起,更能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智趣和情绪的和谐共生。
二是熟悉和陌生的相乘。学者戎小捷提出了一个美感公式:陌生+熟悉=美[11]326。这一灵感或许得益于培根对艺术的定义:“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实际上,“相加”还带有外力嵌合的味道,远不及“相乘”所呈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与生成状态。所以,将美视为陌生与熟悉的相乘,应该更接近美的真谛。这一道理并不难理解。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注意熟悉与陌生的相乘,与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十分契合,教的内容有学生熟悉的,但又有他们不熟悉的,熟悉与陌生相乘,教学的张力、魅力便会悉数产生。
简约语文有这种努力。比如分析《斑羚飞渡》这篇小说,丁卫军老师引入了“情感逆行”的概念,说“小说总是力图打破人物内心的平衡,造成人物之间的‘感情的错位’,制造种种意外,与读者形成‘情感逆行’”[2]208,并启发学生思考:这篇小说有哪些意外造成了情感的逆行?于是学生发现了很多意外:《斑羚飞度》中刀头羚羊为什么要走上去,消失在一片灿烂中呢?很多老斑羚为什么成为年轻斑羚的垫脚板呢?为什么没有滑头的老斑羚从死亡的那波队伍里面转到新生的那波队伍里去呢?这种融入新理论血液的教学法与寻常的贴标签式分析人物形象,按情节四要素分析叙事共性,将小说分析得支离破碎,与千篇一律的做法迥异,更能揭示小说的篇性,是真正的应势教学——顺应文本内在的独特之势;真正应需教学——应学生精神生命生长之需,因而想不产生魅力都很难。
三是致用与致美的相谐。丁卫军老师简约语文是追求致用的,强调学了就要用,“知”是起点,“行”是终结。但是在“行”“用”的过程中,他非常看重个性化的“行”和“用”、创造性的“行”和“用”,努力做到致用与致在的统一。与此同时,他还追求致用和致美的统一。他提倡语用的回归,认为语用回归就是语文的回归,语用训练和思维训练要融为一体,但同时也强调“语文教师必须有艺术细胞,善于把文学和艺术沟通起来,实现大融通”[2]251。他非常欣赏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深厚的古文功底,能将数学之美、文学之美、物理之美融会贯通起来。这就说明: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有了学以致美、教以致美的信念,并尝试将美带入自己的语文教育,带入简约语文的理论体系中。他还倡导语文教师“以自己的聪颖伴着学生徜徉在语文的海洋中,汲取语文之灵气,自由地翱翔灵动的思维,让学生快乐地学语文,使语文学习成为他们彰显生命的有机组成,因投身而感悟,因感悟而增益灵性,因有灵性而成为阅读的主人,成为语文学习快乐的天使”[2]279,所以在存在式学习视域下,重构了健康的致用观,注意实用与虚用的统一,小用与大用的统一,专用与泛用的统一,近用与远用的统一,并较好实现了致用和致美的和谐,使简约语文的理论与实践共荣共生,不断走向了深美闳约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