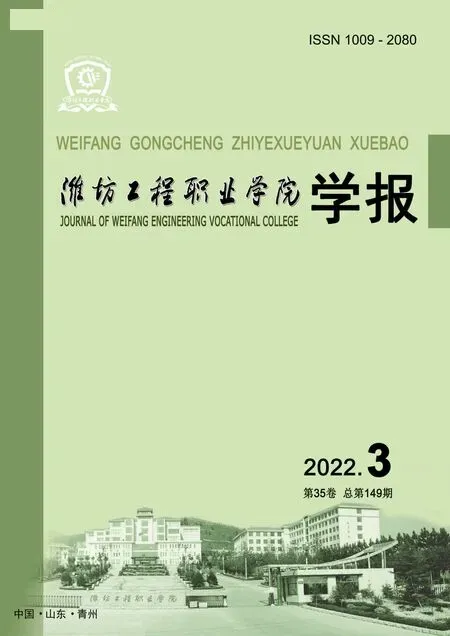论高密派诗人李怀民“寒士诗”的思想主题
张 怀 金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清代中期,乾嘉诗坛诗风极盛。神韵派余韵未消,格调派、性灵派轮番登场,三者皆称颂盛世太平景象。而生于齐鲁、远行粤西,创立高密诗派的“高密三李”,却对当时的诗学、诗风进行深入的反思,试图通过再度唤起山左诗坛冷静平实之风的方式,使乾嘉诗风复归冷静、平实。
高密诗派是清中期山左地区具有浓郁传统精神与鲜明地域特色的诗歌流派,诗派成员多是沉寂在士人阶级底层的寒士诗人。诗派开创者为李怀民(山东高密人,名宪噩,字怀民,号石桐),他生活在乾隆盛世,但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其所写“寒士诗”作为一种“盛世寒音”,表达了布衣寒士的不平之鸣。汪辟疆先生《论高密诗派》言:“李怀民生于乾隆国势隆盛之时,亲见举世皆阿谀取容,庸音日广,慨然有忧之。”[1]乾隆时期,诗坛以沈德潜、袁枚两家最盛。沈德潜继承王士祯衣钵,以格调说“温柔敦厚”的诗教应乾隆盛世之需,但其诗流于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陈腔滥调;袁枚标举“性灵”,宣扬性情至上,但其部分诗作粗鄙村率,使后进诗人沉溺于轻薄萎靡之习。而李怀民目睹潜伏在盛世表象下的社会危机,故而趋步中唐张籍、贾岛的苦吟精神,“救之以寒瘦清真”。其“寒士诗”是寒士风格的颂赞之音,是乾隆盛世的不谐之音,是下层文人的凄苦之音。
一、寒士风格的颂赞之音
(一)身份、经历的相似与个性的共鸣
袁枚《随园诗话》:“李怀民与弟宪乔选唐人主客图,以张水部、贾长江两派为主,余人为客……二人果有张、贾风味。”[2]李怀民仿照唐张为编《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将中晚唐诗人分为“清真雅正”与“清真僻苦”两派,奉张籍、贾岛为两派之主。
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中的中晚唐诗人,多属于仕途中的失意文人,身份、经历都与高密派诗人极其相似。以张籍为例,他出身贫寒,早年外出漫游求仕,却屡次碰壁,备尝人间冷暖。进入仕途后,也只是太常寺太祝这样的九品小官,俸禄稀少,生活贫苦。再加上长期患眼病,几近失明,被人称为“穷瞎张太祝”。姚合《赠张籍太祝》:“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多见悉连晓,稀闻债尽时。”及张籍《赠任懒》“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皆写出张籍穷愁潦倒、为病痛所折磨的惨淡状况。张籍之个性,正如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说》言:“余定中晚以后人物,有似于孔门狂狷,韩退之、卢仝、刘叉、白乐天,狂之流也;孟东野、贾岛、李翱、张水部,狷之流也。”[3]李怀民认为,中唐时期张籍、贾岛等诗人都属于狷之流,怀民狂狷的性格与张、贾等人远隔千年产生了共鸣。
(二)诗歌的典范与人格的颂赞
高密派后学刘大观在为石桐《主客图》作序时称“因以石桐为张客,少鹤为贾客。”是指在具体的师法对象上,石桐学张籍,其弟少鹤学贾岛。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张籍传》言:“水部五言,体清韵远,意古神闲,与乐府词相为表里,得风骚之遗。当时以律格标异,信非偶然。”写出怀民对张籍五言诗的推崇。其《过和州怀张水部》:“感缅张水部,格韵千载幽。诗义齐孟韩,岂止翱湜俦!诗之三十载,力罢道逾修。冷编藏怀袖,风尘谁见收。怅望古城在,遗踪应尚留。”[4]写诗人路过他诗法三十年的张籍之家乡和州,述仰慕之深情。可见,李怀民将张籍奉为清真雅正主,作为高密派诗人师法的对象,既有张籍在诗歌上的成就可为典范,也有对张籍人格的颂赞。
其弟宪乔尊奉的清真僻苦主贾岛,也属于寒士诗人。李宪乔《读贾长江诗》:“险僻时皆诧,孤清帝遣哦。全身生肉少,一卷说僧多。”是对贾岛险僻、孤清诗风的认可。其《再赠书田翁》:“贾孟骨已霜,冷径无人造。岂谓千载下,复得见孤峭。”赞美单书田继承了贾岛、孟郊等人的孤峭风骨。
石桐对贾岛、张籍等寒士人格的颂赞、诗风的肯定更见于其诗学著作《主客图》中。如清真僻苦派成员裴说《冬日作》:“粝食拥败絮,苦吟吟过冬。稍寒人却健,太饱事多慵。”李怀民评道“不惟诗格似贾,性情乃绝相近。”此诗写裴说缺衣少食,苦吟过寒冬,人格却刚健勇毅,石桐评价其同贾岛有相近的性情;另一成员林宽《哭栖白供奉》:“侍辇才难得,三朝有上人。琢诗方到骨,至死不离贫。”李怀民评道“著此二句起,以见不宜贫也。”“二句撰力纯是贾喻也,以此可赞高士。”诗写苦吟诗人虽穷愁潦倒,却琢诗至死,石桐评价与贾岛相似的高士精神充斥诗中。
生活上的困窘,精神上的孤寂,以及充斥在张籍、贾岛诗中的哀愁悲苦情绪,塑造了其孤寒的诗歌意境。这种意境对李怀民“寒士诗”有深远影响。而李怀民对张籍、贾岛诗风的肯定与寒士人格的颂赞,更多的是来自相同的人生遭遇和社会处境,精神的契合使他们远隔千年时空,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
二、乾隆盛世的不谐之音
(一)对格调说阿谀取容之风的批判
汪辟疆先生论及李怀民及其弟李宪乔作诗时言:“然誉其诗者日多,心中之慊愈甚……”体现出怀民特立独行、誓与世俗决裂的决心。
在古代,知识分子上可成为公卿大夫,下则为诗人或寒士,其中的分水岭便是科举考试。“科举是否成功,以及科名的高低,是士大夫生活境遇差异的根本原因。一个穷酸生员,一旦在科举上取得成功,并顺利进入仕途,就会从经济上得到彻底的改变。”[5]如明崇祯年间,寒门之士即便初举进士,也可以“有田数十顷,宅数区,家童数百指,动拟王侯。”科举失败者则不能摆脱原来的处境,贫困终生。最终,在士大夫阶层中,由于“士”阶层的渐趋贫困化,导致了“士”与“仕”的两极分化。沈德潜则是成功者的代表,其苦读诗书大半生,终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由“士”化身为“仕”。沈德潜本一介贫士,在读书求进之时,也曾抱有远大的志向,其诗歌也曾反映民间疾苦。如其《观刈稻了有述》:“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反映了天灾为患、生灵涂炭的场景。但其中了进士,备受乾隆恩宠,成为天子词臣,为感念皇恩,便极力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这注定了他诚惶诚恐、百依百顺的奴仆性格。其所写的应制、奉和之作,无非颂君王、扬纲常,多是一些歌功颂德之作。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言:“时天子天纵多能,喜与词臣辈更唱迭和,唯学士张南华能当上意,而归愚亚焉。”[6]写出乾隆帝雅好诗词,而张南华和沈德潜能仰体圣意,故能得到重用。
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李怀民一生清贫,却始终不肯与时俗同流合污,正是其追求“道”的体现。其《紫荆书屋诗话》:“近来又有以风雅自任者,开口便言《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旨。及观所作,不异土苴,皆无其气而强为言者。”当属乾隆盛世的不谐之音,对备受推崇的格调说进行了批判。在李怀民看来,沈德潜诗论的温柔敦厚、诗歌的歌功颂德以及骨子中的奴性,对诗风的影响是负面的。沈德潜言:“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词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人徘徊自得于意言之余。”[7]沈德潜重视诗歌的伦理道德价值,要求诗人性情优游婉顺、怨而不怒,以“微言”即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对朝政的看法,这是让弱者心甘情愿服从现实,不可有怨言,无须分辨是非曲直。李怀民却不同意这种诗歌理论,其《与某论诗》言:“所谓性情者,非必如海阳鞠慕周所谓致中和也。诗人性情只是不合于众,不宜于俗耳。略似古狂狷一流。”他反对诗歌表达性情的中正和平,认为诗歌表达的性情应是狂狷者的性情,应该不合于众、超出流俗。李宪乔更是言辞锋利指责沈德潜:“忧近今诗教,有以温柔敦厚四字训人者,遂致流为卑靡庸琐……夫温柔敦厚,圣人之言也,非持教者之言也。学圣人之言而至庸琐卑靡,是学者之过,非圣人之过也。”他认为沈德潜错误理解并使用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致使诗歌表达性情不真、诗风卑靡庸琐。
(二)对性灵说粗鄙村率之习的讽刺
清中期诗坛,袁枚以其“性灵说”诗论独树一帜,名噪一时。李怀民《北归日记摘录》:“诸人仰袁简老,如太山北斗。予每览其诗文,颇芜杂率易,不足惊喜。”亦属乾隆盛世的不谐之音。在李怀民看来,相比王士祯神韵派诗歌的涂饰柔腻、沈德潜格调派诗歌的歌功颂德和性情不真,性灵派诗歌的流入排倡、粗鄙村率,使后学诗人沉溺于轻薄游戏之习,确更应当批判。
首先,李怀民《论袁子才诗》:“子才游历江山,所至投谒大吏,以名猎取财贿,衣冠、饮食穷奢极糜,耄而好色,其于诗文赏?,矜才傲物,都乏静气,非真正读书人本色。”对袁枚的人格提出了质疑。他批评袁枚以诗名骗取财物,穷奢极欲,极力追求满足七情六欲的物质欲望,非真诗人本色。其实,李怀民对袁枚人格的批评,更多的是山左文人与江南文人的差异所致。俗语有云:山左多圣人,江南多才子。地气风土的差异,更容易引起人性的迥异。“山左乃孔子故里,以儒家为基础的传统思想对人们的性格塑造具有一种很强的潜移默化作用。”[8]山左地区的士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更注重“修身”,即人格上的自律与完善、行为上的循规蹈矩。李怀民一生穷愁潦倒,也仍怀有“古性原无怨,高情独有诗”的高古情怀。而袁枚则是典型的才子诗人,以自我为核心,主张脱离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多注重真性情的表达。正如袁枚所说:“诗,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为之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他认为诗歌要表达诗人的真性情,这种性情不应是经过伦理道德过滤之后的性情,而是表现出鲜明自我的性情。但这种自我性情的抒发只坚持真实性原则,不使用进步的政治道德加以规范,极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导致绮摩之风盛行。
其次,对于袁枚之诗格,李怀民也不甚认同。其《紫荆书屋诗话》言:“吾乡渔洋先生驰名海外,特兴风韵一派。然其流弊遂成涂饰柔腻,故身后声名日减。南人沈确士力矫渔洋习气,今袁子才亦痛诋渔洋,所恶于渔洋者为其涂饰柔腻也。若子才之诗格未必高于渔洋,而粗鄙村率不值渔洋一笑。”怀民认为袁枚性灵派的缺失在于诗格不高,诗格粗鄙村率,相比王士祯神韵说的涂饰柔腻,性灵说格调更低下,影响更恶劣。
综上,清中期乾隆盛世的诗坛上,李怀民对格调说的歌功颂德、性灵说的粗鄙村率进行了批判,当属盛世的不谐之音。
三、下层文人的凄苦之音
李怀民弱冠即砥砺致学,然其屡次落第,功名不显,其经历和心态都是典型的布衣寒士类型,充满了盛世孤愤者的不平之鸣,表达了下层文人的凄苦之音。如其《子乔自县中来,言单书田先生贫至食木叶,邀叔白各赋一首为赠》:“食尽门前树,先生空忍饥。只应到死日,始是不贫时。古性原无怨,高情独有诗。即今三日雪,竖卧又谁知。”诗中刻画了一位生活窘迫、贫至食木叶的寒士形象,热情赞颂了这位前辈诗人“古性”“高情”的气骨和安贫乐道的精神,既是下层文人的凄苦之音,亦是一首“寒士”的赞歌。其《高士裘》:“洛阳城中三日雪,袁生冻卧僵欲折……耻向泽中钓时誉,独揽登高吟晓寒。幸语高士卫尔冰霜骨,慎莫负薪傲炎月。”诗并序曰:“李五星苦寒竖卧,其有王熙甫、单子庸为制羊裘,强起游眺。余闻其事作《高士裘》。”此诗写李五星受困严寒的凄苦遭遇,诗人感其“冰霜骨”,为其作《高士裘》,借“袁安卧雪”的典故,热情歌颂了寒士的气骨风节。其《瘦骡》:“羸骖筋力少,知是主家贫。称作闲人骑,宜将病客身。寻诗同伫兴,步月亦怜春。瘦骨高如许,无劳鞭策频。”此诗是一首托物兴怀之作,诗人借瘦骡以咏贫士,筋力少、羸弱多病的骡子是诗人的自然观照,诗歌充满了自悯自怜之意,寒士生态的窘迫与心态的凄苦跃然纸上。
清代乾隆诗坛,地方性诗派的纷纷崛起、诗歌理论的全面繁荣,使清诗显得异常活跃与繁荣。盛世诗坛,主流诗风皆称颂太平景象,李怀民的经历和心态都是典型的布衣寒士类型,这使他的诗风很难与当时的主流诗风相趋同,故而其“自辟町畦,独标宗旨”,在众多的诗歌流派中独树一帜,其所创作的“寒士诗”作为一种“盛世寒音”,表达了布衣寒士的不平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