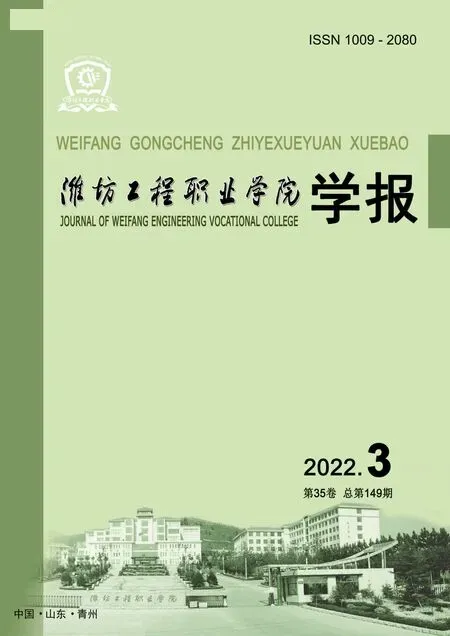楚辞在汉代传播与兴盛原因考论
蒋庆栋,付小政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青州 262500)
楚声楚辞乃战国楚地文化产物,作为新诗体原本主要流传于楚地,汉代时迅速在全国传播乃至兴盛,在楚辞滋润沃耀之下,两汉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逐渐发展成熟。楚辞之所以能够在两汉广泛传播乃至兴盛,一方面有社会政治思想诸方面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统治阶层的倡导推动以及文士学者的喜好认同等主观原因,同时亦与楚辞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强烈的感召力密不可分。
一、儒道糅合、并包兼容的思想文化土壤
屈原的楚辞作品中呈现出的思想内涵十分复杂,很难简单总结归纳到何别何派。实际上,屈原楚辞作品之中既有道家崇尚虚无、追求个体生命超脱的思想意识,又呈现出注重修身、忠君爱国和忧患意识等儒家思想。比如《离骚》之中驾驭玉虬、御飞龙、游乎四极、朝发苍梧、夕至县圃、徜徉往来等词语显然属道家神仙思想,正如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言:“君心已离,不可复合,则疏远而忘宠辱。修黄老之术,从巫咸之诏,所谓爱身以全道也”[1]。同时,屈原受儒家思想影响亦显著,其所赞扬推重的尧、舜、禹、汤贤人政治与儒家思想相合,其主张的“廉政”“有德者在位”“举贤授能”“内美”“修能”等亦与儒家思想有共通之处。《屈赋考源》中游国恩先生即提出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历史观念四大观念之说,他认为屈原这四大观念源于阴阳家与道家,同时深受齐文化影响。
秦代暴政之后社会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加之抗秦战争与楚汉之争对社会造成巨大创伤。而汉初外有匈奴扰乱侵袭,内部又矛盾重重,诸多因素影响下,汉初的经济和文化均处于一种凋敝待兴的状态。《汉书·食货志》中对此有所描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2]。上述背景之下,西汉初的统治者将休养生息政策作为治国方针,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文化学术发展也迎来宽松的环境。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诸家没有得到发展,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思想环境中,沉寂良久的诸子学说重新活跃起来,这其中儒、道、法、阴阳等诸家学说思想体系更为成熟和完备,儒家重道德教化主张仁政,道家则淡化政治意识推重“无为而治”,法家重法治,阴阳五行学说则与儒家思想结合后并入经学。诸家之中,儒家学派尤为活跃,比如高祖即有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鼓吹“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景帝时则有奉信黄老之说的黄生和儒生辕固生在朝堂之上争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汉代儒家学派在继承中又能够与时俱进,吸收其他学派的进步思想,比如荀子礼法并重的思想和阴阳五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随着儒家学派的发展和壮大,儒道交锋渐趋激烈,《史记·魏其式安侯列传》载:“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3]。窦太后死后,儒道之争形势也逐渐发生变化,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并有诸如召儒生、设五经博士、改革礼制、封禅等尊儒措施。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两汉正统思想。
即便如此,武帝后儒家思想也并非一枝独秀,如汉武帝令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深谙黄老之术的汲黯、纵横家主父偃等均受到重用,可见汉武帝重用儒生的同时并未排斥其他学派,下及昭帝宣帝等两汉的王朝统治者,均是在把儒家思想尊为正统的同时,又对道、法、阴阳五行等诸多学派有所利用,对诸家思想有所吸收,儒家温雅可用以揽民心,法家劲厉可用以实行政令,黄老、阴阳五行则可用其神秘装裱皇权。汉代汇集诸家学派学说的文化土壤,儒道等诸家思想和糅并存的意识形态使楚辞的传播具备可能性,而屈原糅合道家、阴阳家与儒家的复杂思想恰恰与两汉儒道互绌、阴阳谶纬盛行的复杂社会意识形态相契合,也为楚辞在两汉的兴盛不衰奠定了基础。
二、统治阶层的喜好与提倡
灭秦后刘氏立汉但并没有承秦朝之制,从文化意义的层面上看,渐趋完备成熟的汉文化实际是中原文化与楚地文化互相交融后的产物,在汉文化萌芽、发展以及成熟的过程中,楚辞也在统治阶层的喜好与提倡中广泛流传并繁荣兴盛,对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文学传播接受主体的汉代统治阶层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鲁迅言:“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4]。故土楚地实为楚人的高祖刘邦对楚辞楚声尤为喜好,《史记·高祖本纪》即载有刘邦归乡过沛作《大风歌》一事,虽仅三句但在汉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高祖之作正是受屈原楚辞作品影响的楚歌楚声。高祖后,景帝甚是爱好楚辞,《汉书》中班固记载其召见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辞’”,朱买臣被拜为中大夫,足见汉景帝对屈原楚辞作品的热爱程度。景帝后汉武帝好文学,且对楚辞尤甚。汉武帝对楚辞的广泛传播起到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汉武帝亲自创作《悼李夫人赋》《瓤子之歌》《秋风辞》等楚辞体式作品,其作深得屈原楚辞精髓,可以说是楚地楚声遗响。在汉人对楚辞的传播接受以及汉人骚体文学的创作发展方面,武帝诸作起到倡导推广作用。其二,汉武帝奖掖辞赋家促进了楚辞的传播,《汉书·贾邹枚路传》载:“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2]。汉武帝征召重用善写辞赋的枚乘及其子枚皋,同时代的一些辞赋家如朱买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也得到朝廷的重用,《汉书》对此有载:“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2]。武帝之后汉宣帝喜爱文艺,看重辞赋尤钟爱楚辞,并对楚辞评价极高谓“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王褒传》载汉宣帝召见九江被公诵读楚辞等事,对楚辞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两汉宫廷中好楚辞成风,如戚夫人、唐山夫人、华容夫人、乌孙公主等创作了韵味十足的楚歌,君王亦创作了数量颇多的楚歌,如燕王刘旦的《归空城歌》、广陵王刘胃的《欲久生歌》等。浓重的故土观念以及对楚地文化的情结,加之屈原楚辞中的忠君爱国精神,实为楚人的汉代统治者对屈原及其楚辞作品极力倡导,并投身于楚辞体作品的创作中,上导下应极大地推动了楚辞在汉代的传播。
三、汉人对屈原精神品格的深刻认同
楚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先秦成熟完备,并经秦“焚书坑儒”与“楚辞”不传而在两汉方兴未艾,与其蕴藏的丰富内涵以及汉人对屈原精神品格的深刻认同是分不开的。楚地处江汉流域一带,吸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商周文化,同时又汲取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吴越文化,而楚地丰富的物产、山高水阔的地势以及优美的自然景观也影响了楚人浪漫流溢的文化情怀,诸多条件成就了楚辞丰富的内涵,而其中所呈现出的爱国忠君思想、上下求索真理的精神、洁身自好的高贵品格以及深刻的忧患意识,更是得到汉人的深刻认同。从西汉初的贾谊、刘安、司马迁到东汉的王逸等对屈原皆有赞美颂扬之语。虽两汉间有班固“扬才露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多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等批评之语,但这事实上并未影响两汉文人学者对屈原以及楚辞的热爱和赞扬,实际上就连对屈原多有批评之语的班固在《奏记东平王苍》中亦有“灵君纳忠,终于抗身”“属子之篇,万世归善”等褒扬之语。这其中以东汉后期王逸最具代表性,其在《楚辞章句》中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志,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期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5]。
纵观两汉,儒家思想观念对文人学者的心态浸透和影响越来越深,虽然屈原楚辞作品中“廉政”“有德者在位”“举贤授能”“内美”“修能”等主张与儒家思想相合,但其中亦蕴涵着极为突出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怨骚”之精神,而这些是处于正统儒家思想之外的,被儒家思想观念影响渐深的汉代士人何以如此推崇屈原钟爱楚辞?霍尔巴赫言:“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未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消灭了。”[6]若基于人类所共有的心理情感体验就不难理解,汉人对屈原的同情实际上可溯源至对自身坎坷命运的悲叹和感伤,这其中寄寓着自身价值取向和对现实的咏叹感怀。基于此汉人推崇屈原由衷喜爱楚辞,从传播楚辞到模拟楚辞进行创作乃至花费巨力注解阐释训诂,这些都促进了楚辞传播热潮,成就楚辞学之滥觞。
四、对屈原“发愤以抒情”创作精神的共鸣
楚辞在两汉的广泛传播和被接受,除了以上原因外,也与楚辞自身所具备的强烈感召力有重要关系,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汉人对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怨愤精神的高度认同和强烈共鸣。
《惜诵》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谓“发愤以抒情”乃是诗人借诗歌抒发抱负志向不得施展而内心产生的悲愤与愤懑之情。这看似与《诗经》“家父作诵,以究王讻”的“言志”“美刺”精神一致,实质上两者有极大区别,儒家抒情言志讲求“止乎礼义”的原则,而屈原所谓的“发愤以抒情”并非“讽谏”“美刺”,其所抒发的乃是从创作主体出发的、关乎个人主体意识的情感。比如《离骚》中“帝阍”之不应与“求女”之不得,究其本质皆是屈原哀伤心境之投射,其内心深处“去”或“留”的矛盾则投映在“何所独无芳草”与“怀乎故宇”等词句中,而结尾之乱词“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7]更是抒发个人情感,概括旨归。同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哀怨和对坎坷命运的呼号蕴藉着沉郁的悲剧色彩,谢柏梁即说:“以《离骚》为中心,《九章》对悲剧人格的树立,《九歌》对悲剧意境的创造,《天问》对宇宙天地发诘难,都构成了自成体系的悲剧性幻想世界”[8]。这对去战国不远的汉人更增添了一层感召力。对“发愤以抒情”的“怨愤”精神,西汉的司马迁以“盖自怨生”来阐释屈原楚辞创作的内在情愫动力,“怨”源于屈原志向理想与现实两者之间无法解决、难以调和的矛盾,《离骚》《九章》等楚辞作品正是屈原“怨”情抒发之作,汉代文人学者对“发愤以抒情”的创作精神有高度地认同感,最为有力的证明就是汉代文人抒发哀怨时基本采用骚体形式,如与屈原遭遇相似的贾谊被文帝疏远时,渡湘水作《吊屈原赋》其意在“悯屈亦伤己”,其后又有刘安作《离骚传》、刘歆作《遂初赋》、杨雄作《反离骚》、崔篆作《慰志赋》、冯衍作《显志赋》、班固《幽通赋》等,此皆印证了汉人对这种创作精神的强烈共鸣与高度认同。尤其东汉末年政治环境混乱,多舛命途之中的文士对屈原无论是人格精神还是创作精神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同,其中王逸《楚辞章句》中对楚辞的训释表现尤为突出,王逸在为屈原楚辞作品作的每篇序文之中,都特别注重探究和揭示屈原创作楚辞的内在情感动因,比如《渔夫序》中即云:“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9]这些无不体现出汉人对屈原“发愤以抒情”创作精神的深入体察及服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