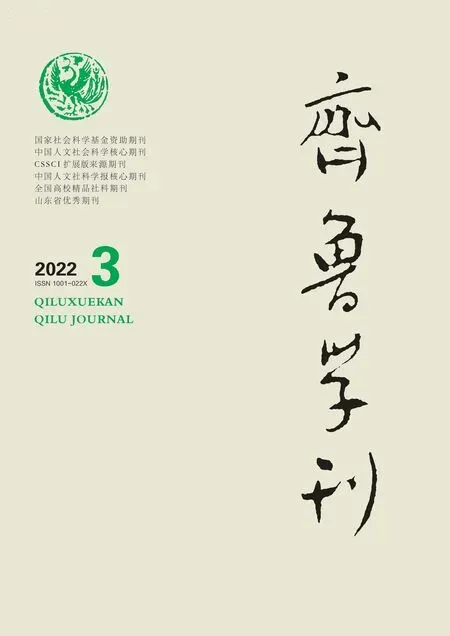清代地域性文学社群与高密诗派的形成及传衍
赵红卫
(潍坊学院 文史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高密诗派崛起于清代乾嘉年间,最初囿于高密一邑,诗人们因依地缘、亲缘,结社酬唱。伴随着高密“三李”、李秉礼、刘大观等诗派核心人物的避籍任官经历,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学交流与互动促成了高密诗派诗风的传衍。高密诗派最终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影响力遍及大江南北,诗脉绵延二百余年。高密诗派的形成与传衍是各种内外因素合力产生的结果,关于这一诗派的诗论诗风成因及传衍等问题,学者们已从多角度展开论述,成果丰硕,兹不赘述,本文仅就地域性文学社群对高密诗派形成与传衍的影响这一尚未得到应有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展开探讨。
一、地域性文学社群:明清诗文创作的原生现场
“社”字的本义是“土地之神”,后为地方基层行政单位,“二十五家”或“方六里”为“社”(1)《说文解字·示部》:“《周礼》:‘二十五家为社。’”《管子·乘马》:“方六里,名之曰社。”,“社”也便由此具有了“群体”之意。文人士子因共同志趣按一定组织形式组成的文学活动群体则称之为“诗社”“文社”,《南唐书·孙鲂传》即载:“及吴武王据有江淮,文雅之士骈集,遂与沈彬、李建勋为诗社。”(2)马令:《南唐书》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3页。至明清,文人结社纷起,文学社群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活动形式,如罗时进先生所言“明清两代,文人具有鲜明的群体化倾向,而地域性文学社团丛生是一个尤其突出的文化现象”(3)罗时进:《基层写作: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考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15页。。
文学社群,一般有组织实体,有社约规范。文学流派的成立则需具备三个要素:流派统系、流派盟主(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4)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与文学社群相比,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要有流派统系,有领袖人物,有共同的创作理论或创作风格,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不必有严格的组织结构。与文学流派相比,文学社群则不必有领袖人物,不一定追求社会影响力,也不一定要求成员有一致的创作理论、创作风格,甚至不一定以文学活动为目的。二者是不同层面上的文学现象,区别明显。但二者又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即很多文学流派是在文学社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吴奔星《文学流派试论》言:“文学社团不等于文学流派。但是,某一文学社团产生有风格并有影响的作家,得到别人赞赏,从而有人继承、发展,则可能成为文学流派。”(5)吴奔星:《文学风格流派论》,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88页。陈文新亦认为文学流派形成的一种方式就是由文学社团发展而成(6)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第9页。。高密诗派在其形成过程中,文学社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视之为由文学社群发展而成的诗歌流派。
文学流派的形成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文学社群不必然会发展成文学流派,但明清时期,地域性文学社群纷起,成为明清诗文创作中的一个突出文化现象,文学流派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处于基层的文人群体,大多身处乡邑,他们或为洒脱自适的布衣,或为屡试不第的士子,或为致仕归乡的官宦,其活动空间多局限于乡邑,难与外界交通,参与地域性的文人社集,成为他们抒发心志、展露才华的重要途径,由此,地域性文人社集成为诸多地域基层文人的一种创作组织形式。“事实上,明清两代地方作家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力量,地域社群是文学创作最活跃的群体,地域共同体是文学作品最高超的生产基地。”(7)罗时进:《地域社群:明清诗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第140页。高密诗派的发源地高密县邑亦复如是,有清一代,高密地区诗社接踵,参社人数众多,社集活动频繁,文学社群活动成为高密诗派形成的直接动因。以地域性文学社群作为考察高密诗派的一个维度,可以走进历史语境,增进对高密诗派形成及传衍等问题的认识。
二、家族文学共同体:高密诗派形成的重要纽带
地域性文学社群的形成主要依托于地缘、亲缘、师生、僚属等网络关系,通过家族传承、师门传唱、乡邦传播等方式来实现其代际传播。而地缘与亲缘的影响力远大于其他因素,可以说“明清地域文学群体本质上是地域文学共同体,而家族文学共同体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8)罗时进:《地域社群:明清诗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第139页。。在高密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家族文学共同体就一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康熙至嘉道近二百年间,高密一域诗社接踵,光绪《高密县志》载:“诗社之兴,兹为后劲计,自清初以迄嘉道,密之能诗者数百家,名宦高人,连镳接轸,其陶淑性情,荡涤物欲,得力于诗者居多。”(9)罗邦彦等:《高密县志》卷十《杂稽》,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这些地域性社群的成员基本为同邑或邻邑诗人,同时,他们之间又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具体到高密诗派的代际承递,家族关系便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康熙初,王飏昌、綦汝辑诸人会诗于单若鲁之秋水居(园在城西门外)。雍正间,宫胜律、单含等十余人会咏城西芜园及单知宜野趣园(园在感化寺东)。致仕名流读书贵介俱出其中。诸先生既殁,南园诗社继之,南园精舍在城南二里,为李孝义先生别墅,亭池竹石之胜甲于一邑,其子李长疄与同邑王立丰、单烺、李师中等四十余人唱和其内,名为通德诗社。莱郡守洪公肇懋月以马递征诗,一时称盛。继起则‘三李先生’也,李怀民与其弟宪暠、宪乔以中晚唐律诏后进,海内宗之,称为李高密派。”(10)罗邦彦等:《高密县志》卷十《杂稽》,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康熙、雍正年间秋水居、芜园、野趣园的诗社集会可以说为高密诗派的形成积蓄了必要的结社和创作经验,至“通德诗社”(又名“南园诗社”)兴起时,社群已达四十余人,影响广远,“一时称盛”,直接开启了之后以三李为代表的高密诗派。诗社成员,多为高密单氏、李氏、王氏等名门望族,他们之间有祖孙、有父子、有舅甥,可谓少长咸集,师友相从。
单氏家族最早有诗集传世的第十世诗人单若鲁,在其秋水居兴诗社,成为单氏家族诗学之始。其后辈诗人受家学滋养,十二世诗人单楷、单宗元为高密诗派开风气之先,“高密三李受学于单书田先生、宗元”(11)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2页。,即师事单楷、单宗元。单氏十三世诗人单烺与李氏家族的李师中、李长疄等成立通德诗社,影响至整个莱州府。李师中为高密三李的族叔,李师中的胞兄李廓园、胞弟李亭午、族叔李文在、孙子李大凯均为通德诗社成员。且李大凯为单烺舅父,与单氏又有姻亲。王氏家族中王立丰与李元直为郎舅,李元直是高密三李之父,王氏与李氏亦为姻亲。王立丰之孙王熙甫为高密诗派“后四灵”之一,也是高密诗派的代表诗人。单氏家族中单烺及其父单凤文、族兄单履晋、族孙单维等均为通德诗社成员,单烺之子单可玉亦秉承父学。单可玉的舅舅即为高密三李,单可玉之子单为鏓亦是扩大高密诗派影响的重要人物。继通德诗社之后,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三兄弟以其父李元直别墅待鸿庄为社集之所,论诗宗法中晚唐,诗学张籍、贾岛,于王士禛、赵执信之后,自辟町畦,独标宗旨,一时青齐间称诗者翕然从之,时人谓之高密派。高密三李的出现意味着地域性文学社群经过长期的发展酝酿,已发展成了有诗派统系,有领袖人物,有共同诗歌理念与风格,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成熟的诗歌流派。
高密三李之后,李氏家族李怀民族子李诒经立西园诗社,又主盟高密诗派三十余年。单氏家族的后辈诗人单华炬、单鼎、单应奎等又师从李诒经学诗法。诗社的成员先后有“三单”“三李”“后四灵”“王氏五子”等称誉,均标示着家族文学共同体在地域性文学社群中的重要作用。如汪辟疆所言,“高密诗派之起,奖掖提携则同里单书田、单青侅、单绍伯开其先;诗派成立,则石桐少鹤抉其奥;羽翼酬倡,则以王氏五子为专功;绍述光大,以后四灵为独至”(12)汪辟疆:《论高密诗派》,《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由此可见,在高密诗派形成与长期传衍的过程中,地域性文人社集活动以稳定的家族亲缘关系及文化世家之间的姻亲世交关系为纽带,秉承特定的地域文化气质,促成了高密诗派二百余年的传衍发展。
三、高密诗派的地域文化特质
地域性文学社群处于一定的地域文化体系之中,往往具有相对稳定的地域文化特质,而地域文化特质是否在文学社群的诗歌创作中得以呈现,正是文学社群发展成为地域诗派的关键因素。
地域性文学社群以基层文人为主体,社群成员的活动范围及视野主要以乡邑为主,而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一向安土重迁,人们长期、稳定地生活于特定地域,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都具有稳固特性,这就使得地域性文学社群与一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关系密切。“晚炊几处村烟起,人影诗情在翠微。”(13)单烺:《大昆嵛山人稿》,《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43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78页。乡邑的田野空间和生活方式成为高密诗派诗人笔下惯常的写作素材。文学社群雅集的乡园别墅,诸如高密南园、西园、李园、待鸿庄、芜园、涉园、东亭等,既是雅集的场所,也是诗人们吟咏的对象,他们流连其中,“无间雪与月,亦复昼连夕”(《复理东亭,改归云亭,为感旧示子乔并序》)(14)李怀民:《石桐先生诗抄》,《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32册,第500页。。高密的百脉湖、胶水、胶西道、青牛涔、西崖等自然山水,纸鸢、奇石、栗子、“咸豆辛姜辣菜根”(《独酌》)(15)单楷:《太平堂诗草》,《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43册,第714页。等地方风物,韩信坝、晏子墓、高密古城等丰富的人文景观,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高密文人社群的诗歌中,俯拾皆是,不取诸邻。
一地之山川风物的气质风貌是相对稳定的,从中形成的人文环境也往往带有长期传承下来的特质,而且与自然的地理环境相比,人文环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更大。王水照先生说:“环境对于学术文化、文学创作的影响,乃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构成环境的人文的、自然的或两种交融的诸要素中,地域的人文性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常是最直接、最显著的。”(16)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第74-75页。高密地处齐鲁故地,而儒家文化又发源于齐鲁,诗人们思之所及,多经世济民之至德要道。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启发着诗人的情思,高密诗派的现实主义诗风也可以说是渊源有自。
地域文学社群以基层作家为主,他们身处乡野,能切身体会到民生维艰,这也推动着诗人去关注现实,关心民瘼。当他们结社酬唱之际,儒者之文学的现实精神也就自然流露出来。如通德诗社诗人、高密诗派成员单烺,在其《雨后呈同社诸先生》诗小序中说:“旱既太甚,自上岁九月至于是月,而上岁淫雨伤稼,哀鸿遍野,诸先生共抱隐忧,社中高会殊落落矣。六月初一日大雨浃夜,人庆更生,同社置酒相劳苦,且以叙致契阔,咸谓不图再睹此景象尔。”(17)单烺:《大昆嵛山人稿》,《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43册,第775页。乾隆间高密夷安九老社诗人、高密诗派成员王烻《草子并引》记:“乙未岁大歉,饿者收草子作糗糒,穷日扫刮,仅给一餐,弗敢饱也,诗以哀之。”(18)王烻:《碻诗钞》,《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29册,第286页。诗人的悲喜忧乐与民生休戚相关,这种与“诗三百”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正是高密诗派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地域性的文人社集本身即带有地域文化的稳定性特质,这种地域文化特质成为地域性诗歌流派长期传衍的重要动因。罗时进先生认为:“对明清地域文学社群作家需要从公共事件和文学空间两个不同方面中加以考察,如此方可比较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性情与品格。地域本身并不能给作家群体带来地位和声誉,只有其在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和在文学空间中的活动,才能形成社会和文坛评价,同时也形成人们对他们所处地域的印象。”(19)罗时进:《地域社群:明清诗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第138页。单烺《高密十四先生咏·李南园先生》提及李长疄创立南园诗社的动机,即言“大雅久沦落,牛耳主斋盟”(20)单烺:《大昆嵛山人稿别集》,1927年高密单氏石印本。,其成立诗社的目的即为复兴大雅,换言之,大雅正声是这一地域文学社群的自觉追求。李怀民在《重订中晚唐主客图》中表达其诗歌主张:“余读贞元以后近体诗,称量其体格,窃得两派焉:一派张水部,天然明丽,不事雕镂而气味近道,学之可以除躁妄,祛矫饰,出入风雅;一派为贾长江力求险奥,不吝心思而气骨凌霄,学之可以屏淫靡却熟俗,振兴顽懦。”(21)李怀民:《重订中晚唐主客图》,清咸丰四年(1854)赵氏补刊本。此处所推崇的张籍之风雅,贾岛之气骨,正是儒家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是诗派成员在基层写作中“以风节相砥砺”(22)李宪乔:《少鹤先生诗钞·单鉊序》,光绪十二年(1886)西安郡斋刻本。之创作态度的理论表述。对于某一作家而言,地域文化特质可以塑造其独特的文学风格,而当多个作家或一个文学社群共同呈现出这种地域文化特质时,就容易形成有特定审美倾向和创作风格的文学流派。
四、地域性文学社群的写作形态与高密诗派的诗论诗风
高密诗派以基层文人为创作主体,其诗论诗风也与诗人群体的基层写作形态关联密切。高密诗派对唐代诗人孟郊、贾岛及南宋“永嘉四灵”的推崇,固然有欲以其苦吟诗风力纠时弊的用心,其主要原因则是高密诗派诗人的个人生活遭际与苦吟诗人的诗歌书写相契合。李怀民《子乔自县中来言书田单先生贫状至食木叶,邀各赋一首为赠》记其师单楷:“食尽门前树,先生空忍饥。只应到死日,始是不贫时。古性原无怨,高情独有诗。即今三日雪,坚卧又谁知。”(23)李怀民:《石桐先生诗钞》,《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32册,第470页。诗歌借后汉袁安卧雪的典故,歌咏了单楷安贫乐道、持节自守的高洁情怀。另一高密派诗人单为濂《怀香堂词·廉泉自序》云:“又数年无所遇,困顿归家,益落,病屡作,呻吟于败梋残絮中,辄累月不能起。”于贫病交集之中,单为濂“感念平生历艰食苦,稍悟世情,于是爽然而起曰:‘丈夫不有令德丰功,至于希贤饱食,已自非人,况放浪若是乎,乃开敝箧,以诗古文词自遣。’”(24)单为濂:《怀香堂词·廉泉自序》,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诗人于艰难困顿中,排遣之途径仍然是坚守风雅,醉心于“诗古文词”以自遣。李少鹤《题后四灵集》把高密诗派的四位成员与南宋“永嘉四灵”相比,称之为后四灵:“族子五星(李诒经)、王生熙甫、丹桂、单生子固(单鼎),共学为张、贾格律,皆有家法,予目之为后四灵。”(25)李宪乔:《少鹤先生诗钞·少鹤内集》,光绪十二年(1886)西安郡斋刻本。后四灵中诗歌成就卓著的诗人李诒经,少孤苦,性孤僻,不仅喜贾岛、四灵诸人之诗,而且喜孟郊、贾岛之为人,故诗风肖之。南宋四灵皆官位不显,际遇冷寂,李诒经在心灵上与他们颇有共鸣,其《读四灵诗》云:“五字最清苦,流传今几时。古心独能得,异世苦相期。没后名方重,生前位亦卑。悠悠千载下,重起更为谁。”(26)李诒经:《卓庵吟草》,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格庐刻本。李诒经诗风清寒,诗情凄切,也正是与其人生际遇有关。李宪暠评李诒经诗“清冷到骨”(27)李诒经:《卓庵吟草·莲塘先生评语》,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格庐刻本。,李宪乔亦称李诒经“一身即孟东野也,以东野学东野,安得不工哉”(28)李诒经:《卓庵吟草·少鹤先生评语》,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格庐刻本。。这种身世遭际的相似性是李诒经推崇孟郊、贾岛与“永嘉四灵”的主要原因,也是其诗风清冷的主要原因。
地域性的文学地理空间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文学之于地理的价值内化,“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超越、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象征意义”(29)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36页。。文学家通过自己的审美观照,赋予地理空间以某种品质,构建起某种价值观与审美观,从而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象征意义。
在高密诗派诗人的诗歌中,诸如苦吟、酸寒、贫、穷、冷、僻、寒、饥、孤吟、苦、清苦、闲、孤、寂、孤僻等字眼频繁出现,具有清寒气质的梅花意象受到他们的格外喜爱(30)刘培:《南宋华夷观念的转变与梅花象喻的生成》,《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第57-66页。。至于苦吟,则是其惯常的创作情态,如“世路空悠悠,谁念苦吟者”(《单青侅太守见过即事酬短句》),“孤吟知兴远,闲坐亦深更”(《冬暮村居杂咏寄叔白》)(31)李怀民:《石桐先生诗钞》,《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32册,第471、474页。,“穷巷稀人迹,阒然耽苦吟”(《题李五星诗卷却寄》)(32)李秉礼:《韦庐诗内集》卷三,道光十年(1830)知稼堂刻本。,“每从谏院想儒林,下直垂帘自苦吟”(《哭王熙甫侍御》)(33)刘大绅:《寄庵诗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1页。,“愧无事业比英雄,苦吟啾唧如秋虫”(《读石桐先生病中吟书寄》)(34)单鉊:《薖庐遗诗》,《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44册,第51页。,“性与时人异,平生惟苦吟”(《题处士李五星诗卷》)(35)刘大观:《玉磬山房诗集》卷一,清嘉庆道光间刻本。等等,都是高密诗派诗人基层创作情态的形象写照。他们本身生活的清苦及多舛的人生际遇,直接影响了其尚风雅、重写实、清寒瘦削的诗风。
基层文人对这种看似困顿的处境并非抱持着完全排斥的态度,从他们“耽苦吟”的创作情态就可窥见一斑。高密诗派的成员不仅多为基层文人,而且多为生活寒苦之士,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不顾生活之困顿,而能淡泊名利,醉心于社集酬唱呢?基层文人社集的创作环境及其带给诗人的精神自由,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地域性文学社群处于静谧乡邑,远离喧闹的名利场,出现在诗人诗歌中的景色是优美的,他们的心境也是恬淡的。春花秋月的美景固然是诗人陶醉在其中的原因,但相对而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基层写作环境远离官场倾轧与名利纷争,诗人身处其中,能够保持“飞鸟相与闲,远心静秋露”(《秋日郊游遂诣西禅寺》)(36)单襄棨:《梦筑堂诗初集》,《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44册,第251页。一般的远离世俗、恬淡自适的精神状态。
通过参与文人社集等活动,这些身处乡邑的诗人从与社群成员心灵相契的酬唱中感受到精神的自由和自适。如高密诗派的领袖人物李怀民诗云:“野会少拘忌,贫家足精洁”(《冬日会西庄示弟》);“言言当心语语合,不觉意气增百万”(《喜王生见过赠以诗》)(37)李怀民:《石桐先生诗钞》,《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32册,第479、483页。。李怀民又以这种精神的自由与诗派成员共勉,其《族子诒经访予芸磵置酒示诸生》一首云:“濩落非世用,屏迹在田园。汲汲二三子,谬推为时贤。馆之清溪侧,花发溪中妍。溪南多乔松,松下无杂喧。辄复摘章句,晨夕相穷研。孺子来何所,求我林水间。适有盈觞酒,更谋通夜欢。诗歌究夙好,探讨发古编。嗟汝贫苦居,并日乃一餐。如何慕闲逸,甘以辞冕轩。及身感沦没,宁问千岁传。尚务储世资,勿效风露言。诸英幸努力,覆辙今在前。”(38)李怀民:《石桐先生诗钞》,《山东文献集成》第3辑第32册,第482页。虽明知只有贫苦自甘,没有高官厚禄,但毕竟有屏迹田园的闲适安逸,还有疑义相析的师友相伴,清寒的诗风由此而具有了自适、恬淡的味道。
总之,地域文学群体在一种有组织、有纲领的社群化创作方式下,成员的交流唱和以社群为中介,在文学统系选择上互相影响,诗论诗风彼此趋同,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成为了一种自然而又自觉的事情。
五、高密诗派成员宦游地的文学社群与高密诗派的传衍
高密诗派在乾嘉年间趋于鼎盛,其影响力突破了地域的局限,追随者遍布大江南北,诸如山东、广西、江西、山西、河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辽宁、四川、河南、台湾等地,甚至远达朝鲜。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有一项重要的任官制度——避籍制度,即指某些职级的官员按规定不得在原籍任职的籍贯回避制度。这一制度在清代被执行得尤为严格,督抚直至州县一级官员均需避籍任职,“在外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39)崐冈、李鸿章等:《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七《吏部·汉员铨选》,清光绪刻本。,甚至具体到任所与原籍距离需在五百里以上。这一任官制度对区域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带来了深远影响。对于高密诗派的传播与传衍来说,在避籍制度影响下,避籍任职的高密诗派成员的生活地理和文学地理都发生了变化。在宦游地,他们通过领导或参与任职地的文学社集活动,促生了新的文学社群活动中心。这些在异地先后兴起的文学社群以高密地区早期兴起的文学社群为效法对象,它们在创作主张、诗歌审美特质和精神文化上具有一定的承继性,从而有效地促进了高密诗派的传播。由此,高密诗派走出了高密一域之藩篱,实现了高密诗派在多个地域的崛起,最终成为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歌流派。
高密诗派传播较广的地域主要集中在广西、江西、江苏等地,这些地域的基层文人社集活动也相对比较活跃。李宪乔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任广西岑溪知县,又先后在广西省的梧州、归顺州、宁明州、柳州等地任职,所到之处,即与当地文人结社酬唱。李宪乔与李秉礼、刘大观、朱小岑等人交厚,又弟子众多,其中声名较著者有童毓灵、童葆元、唐昌龄、袁思名、陈鉴、叶时晰、高秉文等。在李宪乔带动下,广西诗坛极一时之盛,广西亦遂有高密诗派。李宪乔曾记高密“三李”在广西与诸士子结社雅集之盛况:“忆岁庚子(1780),余至岑溪。壬寅(1782)至苍梧。癸卯(1783)复还岑溪。吾家石桐、叔白两先生汲引多士,为诗社会甚盛。”(40)李宪乔:《李少鹤日记·丙辰丁巳过岭北旋纪程》,清稿本。在广西诸州县任职期间,李宪乔兄弟在各地留下了与当地诗人社集的足迹。他们曾在岑溪钟氏园集会,李怀民作有《七月七日与子乔会岑诗人于钟氏园分韵得十蒸,去年叔白有此会》,李宪乔作有《再过钟氏园感怀》,李宪暠则在《雨中游钟氏园》中记录了宴游岑溪钟氏园的场景。从这些诗作,不难窥见当时诗歌唱和活动的活跃程度。
李宪乔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任归顺州知州,又于乾隆六十年(1795)再任知州,两牧归顺,其政务之暇,亲自教诲士子,“一时风雅称彬彬焉”(41)封赫鲁等:《民国靖西县志·宦绩·李宪乔传》,1948年刊本。。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载:“州人童九皋、唐梦得两明经皆从之游,奉中晚唐主客图为埻的……九皋弟葆元,亦少鹤门人……同里袁子实上舍思名,从少鹤学诗,专师贾长江刻苦幽峭……马平叶亮工上舍时晳师事少鹤,执弟子礼。”(42)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3页。这里提到的童九皋、唐梦得、童葆元、袁思名、叶时晳均为师事李宪乔而文学成绩卓著者。李宪乔任柳城知县期间,又创立仙弈诗社,与诸门生社集酬唱。李秉礼《题仙弈诗社图》记载了李宪乔与长洲孙顾崖、嘉兴王若农以及柳州门生龙振河等在仙弈山的一次社集:“仙弈山,子厚记中柳州近治可游之一也,吾宗子乔暇日与孙顾崖、王若农及其弟子三人游之,寻弈石不得,取壁间赵宋王安中仙者‘辍弈鹤驾翩’句于洞宾洞中分韵,余一字无所属,因请洞宾降乩足其数,子乔绘图,并诗以寄余,为题云。”(43)李秉礼:《韦庐诗内集》卷四,道光十年(1830)知稼堂刻本。诗中描写了社群成员社集赋诗时“兴酣气豪斗险语,拊掌一笑同飞仙”的惬意。通过与游宦地的文学社群开展文学交流,高密诗派的诗论诗风被当地的文学社群广泛接受,乃至成为一种创作模式。在这种文学交流的同时,高密诗派也完成了文化扩散。
在广西期间,李宪乔与李秉礼、刘大观最相契厚,并称“岭南三友”。李秉礼,字敬之,江西临川人,寄籍广西桂林,从李宪乔学诗法,“生平与子乔最契,内集皆以点定。子乔殁,凡未经点定者,则编入外集”(44)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卷九八,1929年退耕堂刊本。。刘大观,字正孚,号松岚,山东临清邱县(今属河北)人,初官广西永福县令,“与李少鹤州牧、松圃郎中最善。五言诗以张水部、贾长江为宗,清能彻底,瘦可通神,高格自持,名句有味”(45)吴嵩梁:《石溪舫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55页。。刘大观曾署柳州府融县令,补桂林府永福令,署柳州府首县马平令、象州知州、平乐府贺县令。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调补镇安府首县天保令。乾隆五十三年(1788),尝摄府篆。因其官位较达,又亲为李宪乔校刊遗书,故在高密诗派流播过程中,刘大观可谓中坚人物。李秉礼、刘大观接受并学习高密诗派,他们又通过自己的交游进一步扩大了高密诗派的影响。如李秉礼之子李宗瀚“守其家法,并及高密二李绪论”。李宗瀚后成为道咸时期广西诗坛的支柱。李秉礼后裔、晚清李瑞清,字梅庵,曾侨居金陵,仍以高密诗学为家学,又以其家藏钞本《中晚唐诗主客图》传授于寓居南京的安徽和州籍诗人胡翔冬,“胡氏《自怡斋诗》亦远宗张贾,近法石桐,并以身丁世变,枨触万端,辞旨诡谲而不失于正。至其穿天心出地肺之语,见之者罔不惊走却步……盖胡氏正从高密出也。然则高密二李之诗派垂二百年犹未绝也”。汪辟疆又言:“胡森亦以江西人,与少鹤往来,自是江西诗人多有传其《中晚唐诗主客图》者,于是,江西有高密诗派。孙顾崖以吴人官粤西,而最服膺石桐少鹤诗说……于是东吴有高密诗派。”(46)汪辟疆:《论高密诗派》,《汪辟疆文集》,第263页。可见,高密诗派在当时传衍甚广。
相对来说,中国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方式亦不发达,文化传播的迅捷有效性也深受限制,而在清代,文官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群体,避籍任职制度直接促成了大规模的文官文人群体的宦游,他们的文学文化活动,有效促进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与传播。清代基层文人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地域性文学社群是最活跃的文学创作团体,随着高密诗派成员的宦游足迹,高密诗派成员与宦游地基层文人广泛交游,领导或参与宦游地的文人社群活动,促进了与高密诗派有着紧密关系的新诗学中心的形成。地域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交流促成了高密诗派的广泛传播,高密诗派由囿于一隅发展到影响力遍及南北,在这过程中,高密诗派成员宦游地的文学社群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