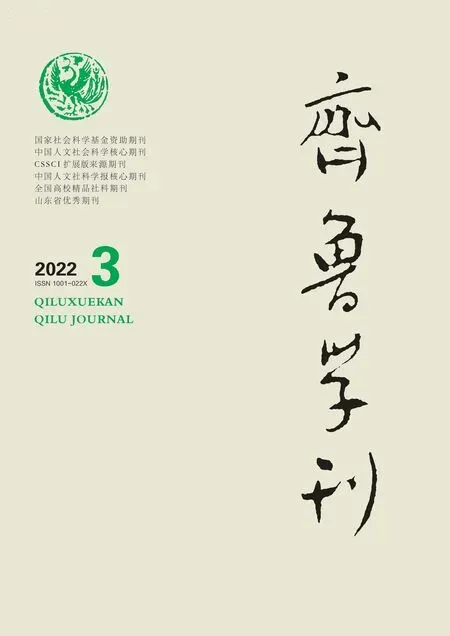我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实施路径分析
徐淑萍,熊黎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一、 我国实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合理性
(一)算法使用对避风港规则的冲击
避风港规则作为全球网络版权责任分配蓝本,始于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The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以下简称DMCA),后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纳,如欧盟《电子商务指令》(E-commerceDirectives)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94—1197条均采纳了避风港规则。DMCA强调,网络服务提供商作为“技术中立”者,仅提供“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服务,不能对作品内容是否侵权作出准确判断,且由于互联网发展初期的技术水平无法与网络内容的高效流动性和复杂性相匹配,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信息管理能力不足以承担版权的事前审查义务,因此平台仅对不知或不应知晓的网络侵权内容负有“通知—删除”义务。
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了算法的进步。内容相似度算法、内容个性化推荐算法的大规模运用,导致由“算法泛在”走向“算法主导”的互联网产业与版权产业之间出现“利益差”问题,对避风港规则下的版权责任配置模式造成系统性破环(1)Annemarie Bridy,“The Price of Closing the ‘Value Gap’: How the Industry Hacked EU Copyright Reform,”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 Technology Law,(2020:4):326-328.。为应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被动注意义务问题,版权人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算法技术主动查询、识别侵权内容,并向平台发出移除通知。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商为迎合算法通知的广泛适用,防止产生因未及时删除内容而承担的侵权责任,利用内容相似度算法对网络内容进行版权过滤,通过版权事前审查手段监测、处理侵权信息。算法过滤措施降低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预防侵权责任的成本,尽管当前技术仍存在不足之处,但依旧表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信息管理能力在不断提高,势必会影响避风港规则责任配置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呈断层式爆炸增长的算法通知迫使网络服务提供商抛弃人工“移除”手段,将避风港规则下的“通知—移除”程序彻底转变为“算法通知—算法移除”。然而,“通知—移除”方式的转变可能会导致反通知机制的失效。反通知作为一种人工救济手段,与算法通知相比具有滞后性;并且在版权内容过滤措施下,用户无法对已经被过滤的网络内容发出反通知,较版权人而言,具有不对等性。内容个性化推荐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通过分析网络用户的行为特点,主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以解决信息过载的问题。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获取流量经济,其身份从仅提供技术服务的“技术中立”者转变为积极参与的传播者,避风港规则的理论基础受到冲击(2)朱开鑫:《从“通知移除规则”到“通知屏蔽规则”——〈数字千年版权法〉“避风港制度”现代化路径分析》,《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5期,第42-52页。。
(二)内容过滤技术的进步
当前,内容过滤技术主要包括网络内容分级平台过滤(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简称PICS)、文件哈希值过滤、内容关键词过滤以及基于内容比对的过滤。PICS与互联网运行原则相违背,无法控制用户的恶意侵权行为;内容关键词过滤存在报错率高、纠正成本高等缺陷;虽然文件哈希值过滤使准确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但仅能识别相同哈希值的信息,容易产生用户通过更改哈希值以规避过滤措施的行为(3)Junichi P.Semitsu,“Buring Cyberbooks in Public Libraries,”Internet Filtering Software vs. The First Amendment Stan L. Rev.52 (2000:2):513-519.。基于内容比对的过滤,能够有效消除以上措施的弊端,通过语言分析、图像处理等技术对版权内容进行识别并建立索引,从而判断是否对其进行过滤。尤其针对文字、图像、音视频等网络内容,基于内容对比的过滤能够不受媒体格式、编码方式的影响,不仅报错率低,而且效率高(4)马胜男:《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过滤义务研究——以欧盟立法实践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为视角》,《社会科学动态》2021年第1期,第64-72页。。如YouTube的Content ID系统,仅需将作品(文字、图片、视频等)纳入过滤系统的作品特征信息库,一旦用户上传与其实质内容相重合的信息,系统便会迅速作出判断。
作为一种事前审查方式,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成本,主要包括开发成本、维护成本以及纠错成本。其适用的合理性应当与措施的成本、侵权行为的发生率以及危害性密切相关。在算法发展初期,信息闭塞,交互缓慢,侵权发生机率低,网络服务提供商仅通过人工审查即可满足版权保护的需求,当且仅当侵权行为的损失大于内容过滤措施的成本时,网络服务提供商采取内容过滤措施才具有正当性,以避免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从而阻碍互联网的发展。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内容过滤系统已逐渐走下神坛,系统成本也在不断降低。此处的成本不仅指网络服务提供商开发运行以及维护的经济成本,还应包含“用户或公众因网络传输效率、个人自由等受到限制”而产生的社会成本(5)崔国斌:《论网络服务商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第215-237页。。一方面,确定实施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网络服务商类型,以免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如要求提供基础技术服务的网络平台承担过滤义务,不仅可能侵犯用户的隐私自由,而且会对互联网传输效率带来实质性伤害。于是,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DirectiveonCopyrightintheDigitalSinglesMarket,以下简称《版权指令》)将过滤义务主体限定在“以营利为目的,将提供储存用户大量版权作品作为主要目的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另一方面,对于大型网络内容分享平台而言,内容过滤系统的支出较整体的收益而言所占比重较小,平台宁愿支付高昂的过滤成本以防止承担巨额侵权赔偿。虽然中小网络内容分享平台可能无法凭一己之力承担过滤系统的费用,但可以选择抱团取暖,由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共同开发使用,以达到分担系统成本的目的。
(三)促进网络版权秩序的健康发展
为缓解互联网产业与版权产业之间的矛盾,欧盟2004年《知识产权执法指令》重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负的法律义务,规定侵权行为的临时和预防措施;德国在指令的基础上于2017年颁布《改进社交网络中的法律执行的法案》,进一步细化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义务范围,增加每半年向公众例行报告的义务(6)孙禹:《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规规则——以德国〈网络执行法〉为借鉴》,《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第47-51页。。欧盟2019年《版权指令》首提网络内容分享平台的版权内容过滤义务,开启网络版权责任配置模式新发展。
在传统“通知—删除”规则下,版权人仅能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就侵权信息进行查询识别。一是维权成本过高。二是智能时代逐渐削弱了版权人的专有控制权,单枪匹马地对抗不计其数且变幻莫测的侵权信息已成为常态。这种被动注意义务无疑进一步增加了版权人举证的难度,因此,将主要防范侵权行为的义务施加于版权人的规定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三是作为弱势一方的版权人基于资金、技术等原因无法对侵权做出准确、有效的回击,网络版权的保护力度不足以震撼侵权者,从而导致不断滋生网络侵权行为的恶性循环。《版权指令》将网络内容分享平台的被动注意义务转变为主动的事前审查义务,未“尽最大努力”的网络内容分享平台承担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7)A Abbott, et, 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Unchained: Why Copyright Law Must be Updated for the Digital Age by Simplifying It,” Released by the Regulatory Transparency Project of the Federalist Society, October 27,2017.。此举符合利益平衡原则,减少了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分担了版权人的举证责任,将注意义务主要集中于具有优势地位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从制度上避免网络平台出现能为而不为的现象,有利于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利,以促进网络版权秩序的健康发展。
二、 我国实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挑战与平衡
(一) 对当前网络版权保护的省思
我国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首次引入避风港规则,在互联网技术兴起的初期,促进了网络服务产业的飞速发展。当前,由于算法技术的发展,版权人逐渐失去了对作品的有效控制,避风港规则“移除单个侵权内容”的运行方式已无法应对数以万计的网络侵权,在“通知—删除”的免责条款下,版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利益关系愈发失衡。无论是大陆法系抑或是英美法系,均要求对避风港规则下的责任配置模式进行适当调整,使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相应的审查义务,如欧盟《版权指令》中规定了网络服务商承担实施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义务。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认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未主动对用户侵权行为进行审查的,法院不应因此认定其有过错;《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则延续了网络服务商“通知—删除”的被动审查义务,但未将制止重复侵权措施和确定标准技术措施作为避风港原则的适用前提,不利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发展(8)虞婷婷:《网络服务商过错判定理念的修正——以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确立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19第10期,第123-133页。。
司法实践中,法院为平衡网络版权利益关系,开始逐渐否定网络内容分享平台不承担事前审查义务的规定,以达到实质上的公平正义。自《规定》生效至《民法典》生效之前(已废止的《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对“知道”的过错形态负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避风港规则成功抗辩的一审案件仅占网络侵权案件的19.7%(9)熊皓男:《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审查义务》,《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6期,第37页。;法院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施加“更高的注意义务”以要求其承担事前审查义务。国家版权局《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同样要求对重点作品的版权保护采取技术措施,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民法典》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过错形态从“知道”扩展至“应当知道”,与《规定》第9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侵权的条款遥相呼应。如何在《民法典》的指引下平衡版权人与网络内容分享平台的利益关系,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二)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与合理使用的界限
网络内容分享平台通过正版作品数据库对用户上传的信息进行扫描对比,以确定是否对其内容采取过滤措施,并阻止侵权内容的重复上传。就内容过滤机制本身而言,在降低平台应对网络侵权信息成本的同时,可能会导致对非侵权内容(合理使用)的屏蔽或删除,从而产生假阳性错误(10)假阳性错误即错误的肯定。,阻碍合法信息的有效传播。欧盟《版权指令》第17条以及条文解释(66)第4段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需尽最大努力获得版权授权,否则将对侵权内容承担连带责任。这可能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商为避免承担侵权责任而产生过度过滤的情形。我国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就合理使用规则依旧坚持类似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列举方式,但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作为兜底条款,以提高合理使用的灵活性。我国早在2011年《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突破了法条有关例外情形的规定,采取美国高度灵活的四要素平衡法以及转换性使用来判断网络内容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11)《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考虑作品使用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等因素。”。而以版权内容过滤为代表的算法技术意在强调确定性,不符合合理使用的灵活性要求(12)蒋舸:《作为算法的法律》,《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第65-66页。。以“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为例,内容过滤技术可以通过算法来设置侵权行为的数量标准,但无法判断该数量范围内是否存在作品“质”的部分。
虽然网络版权过滤技术尚且无法成为“芯片上的法官”(a judge on a chip),但可以通过算法在合理使用的不确定性中寻求“定量分析”(13)熊皓男:《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审查义务》,第37页。。算法通过创建识别例程,并对以往案例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找到合理使用所遵循的司法决策模式,避免算法合理使用的僵化。这种不预先设定合理使用指定值,将算法结果纳入适用范围的计算方式,意在追求版权过滤措施符合合理使用范畴的高概率性,而非精确性;并且,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准确性也会大幅度提高。此外,就美国四要素平衡法而言,算法就“作品的使用目的和质量问题”可以通过域名以及用户上传信息的标记类型来查询网络内容分享平台的性质(14)华劼:《自动版权执法下算法合理使用的必要性及推进》,《知识产权》2021年第4期,第34-44页。。对于用户作品“使用的质和量部分”,如果过滤措施所识别的量大于预先设定值,即便目前技术无法判断量的范围内是否存在质的部分,但是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佐证“质”而提供数据支持。对于“合理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可以通过算法设计来确定用户内容是否会对版权人作品造成市场替代。综上,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对合理使用的限制应当存在具体的判断标准,即最低限度的限制合理使用原则。
(三)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隐私认定标准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版权内容过滤措施对用户上传内容进行事前审查,技术复杂且不公开,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用户信息的控制程度是否存在算法偏见以及算法黑箱,目前尚缺乏法律监管以及公众监督。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简称EDPB)2020年度报告显示,该年度共发生461起投诉数据侵权案件,并于2021年9月要求爱尔兰Whats网站限期整改收集非用户数据的行为(15)EDPB,“EDPB requests that Irish SA amends WhatsApp decision with clarifications on transparency an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amount of the fine due to multiple infringements”,https://edpb.europa.eu/news/news/2021/edpb-requests-irish-sa-amends-whatsapp-decision-clarifications-transparency-and_en.。2021年8月,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改变了个人信息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该法第58条增设了网络平台保护个人信息的“守门人义务”,要求重要互联网平台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成立独立机构,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但就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而言,如何平衡版权人版权利益与用户的隐私权尚未被提及。
算法的进步打破了信息隐私权的传统二分法,私人与公共的界限不断模糊。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隐私权从个人独处的权利逐渐发展为控制个人信息传播的权利(16)Alan Westin,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Press,1967),17.,从实体财产领域拓宽至精神领域的“隐私合理期待测试”(17)朱晓睿:《版权内容过滤措施与用户隐私的利益冲突与平衡》,《知识产权》2020第10期,第64-76页。。隐私合理期待测试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对隐私权的范围进行界定,主要包括个人的隐私期待以及社会对合理期待的认可,即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权是为社会所认可的合理隐私期待。内容版权过滤措施造成的隐私边界问题本质上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公众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碰撞。利益衡量决定隐私权的范围,当个人利益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可能损害他人的重大利益或侵害多数人的合法权益时,必须对隐私权的范围做出合理的限制,以确保公共信息的自由交流,如个人隐私权不得损害他人的知情权。就实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目的而言,如果该措施的社会利益远大于合理限制用户隐私权的社会成本,那么过滤措施的实施就具有社会正当性。且基于算法技术的版权内容过滤措施仅能通过创建识别例程对版权内容进行数据分析,不涉及内容的文字解析,因此不会对用户的隐私权造成实质伤害。因此,为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设计合理的过滤目的和过滤方式,能够在保护版权人利益的同时符合用户的隐私权需求。
此外,为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司法实践将“第三方原则”以及“同意原则”排除在隐私合理期待测试之外。用户向网络平台(第三方)上传或披露个人信息,那么即可视为放弃对该信息的隐私合理期待(平台具有保密义务的除外)。同意原则下,用户有权通过明示(如网络服务协议的格式合同条款)或默示(明知使用和放任使用)的方式,向网络平台放弃个人的某些隐私权益。
(四)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言论保护审查
言论自由作为基本权利受到宪法保护,但言论自由并非一项绝对权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规定,禁止利用言论自由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等行为;第53条规定,公民具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早在引入版权内容过滤措施之前,各国均会对网站中危害国家安全、黄色暴力等非法内容进行审查和规制。如我国2010年《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对平台内容承担事前审查义务。前文提到内容过滤技术具有复杂性以及不公开性,政府将版权事前审查权让渡给私人的行为,可能导致程序的不透明性以及不公正性,从而造成对公民自由言论权的侵害。英美法系认为,版权内容过滤作为一项“事前限制”措施增加了言论自由的成本,即使限制措施具有实体的正当性,也并不能当然认定其程序的正当性。因此,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言论保护审查实质上是针对版权保护规则有没有充分保护合法言论的审查。另外,有关网络内容分享平台的版权内容过滤义务是否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商为避免承担侵权责任而对网络内容采取过度过滤,目前尚未定论。
与隐私权相似,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所保护的社会利益足以弥补限制隐私权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时,社会对该措施的容忍度将会大幅度提高。版权侵权是否能够构成限制言论自由的充分理由是两者博弈的焦点所在。具体到案件中,法院需要衡量运行内容过滤措施的后果与言论保护的收益,根据纠错成本决定对内容过滤措施的容忍度。比如,对于类似儿童浏览网站之类的网络平台,当且仅当过滤措施造成合法言论的实质损害时,法院方可认定过滤过当(18)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Library Assn. Inc. 539 U.S. 194, (2003),209.。故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并非追求言论自由的完全保护,而是根据措施所保护的合法利益的重要性,来调整社会对限制合法言论的容忍度(19)崔国斌:《论网络服务商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第215-237页。。另外,合理使用制度对保护言论自由具有重要作用,合理使用四要素平衡法以及转换性使用实际上可充分保护用户的合法言论。法院对用户作品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判定,尤其是对作品性质及目的的判定,基本可以满足用户的言论需求。即使出现限制言论自由的情形,用户依然可以寻求转换性使用,即对版权作品的替代性选择,因为过滤措施仅过滤文字内容,并不涉及作品的思想表达。
此外,市场机制会抑制网络服务提供商出现过度过滤的可能性。网络内容分享平台大小各异,并非采取相同标准的内容过滤措施进行版权过滤。平台通过衡量纠错成本与平台收益的比例,即比对历年侵权行为的数量以及赔偿金额,来调整过滤措施的标准。即使出现版权内容言论价值高于经济价值的情形,网络服务提供商依旧可以采取最小限度的版权过滤措施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毕竟版权人作为弱势一方,举证网络平台因过滤措施过于宽松而有过错的难度较大。并且,侵权责任并非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过度过滤措施的主要因素,市场的竞争压力要求网络内容分享平台必须优先考虑用户的体验感,过度的内容过滤将大大降低用户的体验兴趣,从而影响平台的商业竞争力,不利于平台的长久发展。
三、 我国实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制度构建
(一)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国际发展
算法技术的进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断提高版权注意义务,从“通知—删除”的事后审查逐步走向含有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事前审查。在国际层面,尤其是美国(自治规则)和欧盟(国家法律),遵循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20)李安:《智能时代版权“避风港”规则的危机与变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07-118页。。
美国DMCA一直坚持避风港规则,仅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施加“红旗”标准的注意义务(21)“红旗原则”最早出现在美国1998年版权法修正案中,即如果侵犯著作权(主要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是红旗一样飘扬,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以不知道侵权的理由来推脱法律责任。。为了迎合数字时代的发展,美国版权局于2020年5月发布关于DMCA的评估研究,认为完善版权立法可以实现通过私人间自愿的技术过滤等非立法方式解决利益冲突,主要包括市场采取的自愿协议和私人行动倡议(22)市场采取的自愿协议通常类指数个网络内容分享平台与版权人之间达成的版权合作协议;私人行动倡议是网络内容平台向版权人主动发起合作邀约,版权人可自愿加入。。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版权人之间根据意思表示所达成的“自治规则”(如用户创作内容网络服务商知道规则),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现有规则的不足,但需要注意该规则与合理使用、隐私权以及言论自由的界限。
不同于美国网络服务提供商较低的版权注意义务,欧盟要求网络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对用户上传的侵权内容进行审查过滤。首先,承担过滤义务的主体仅包括营利性质的网络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其次,《版权指令》要求网络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承担严格的版权注意义务,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版权作品不被其他用户侵权使用,以及尽最大努力防止侵权内容被再次上传。虽然《版权指令》并未直接要求网络内容分享平台承担版权过滤义务,但人工审查无法应对海量的侵权信息,故采取版权内容过滤措施是当前网络内容分享平台避免承担侵权责任的最佳方式。
(二) 我国实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理性选择
无论是自治规则的美国方式,抑或是国家立法的欧盟方式,均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相应的版权注意义务,实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成为国际发展新趋势(23)Benjamin Boroughf, “The Next Great YouTube : Improving Content ID to Foster Creativity, Cooperation, and Fair Conpensation,” Albany Law 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015:1):95-128.。我国当前已在不断推进版权技术的发展,但尚处于初级阶段。当前,版权过滤技术成本较高,如果强制赋予中小互联网企业过滤义务,一方面会阻碍互联网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可能造成中小企业成为新的风险来源,不利于网络生态的监管。因此,应理智对待版权内容过滤措施,既不能忽视版权技术发展对避风港规则的冲击,也必须正视我国现阶段的互联网发展水平。
我国《民法典》虽然延续了避风港规则“通知—删除”的归责模式,但第1197条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须对知道或应当知道,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款增加“应当知道”实际上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为我国实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故在立法层面,不应全盘否定《民法典》中有关网络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而应利用版权算法决策来促进避风港规则的有效实施,如借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的数据保护影响评价(DPIA)(24)DPIA是GDPR项下针对高风险数据处理活动对数据控制者设置的预警自查义务,帮助数据控制者提前识别和减轻隐私风险。,确保“算法通知—算法删除”运行的公开与公正。司法实践中同样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更高的版权注意义务(25)Alpha法律智能操作系统收录的网络版权侵权案件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避风港规则成功抗辩的案件仅占19.7%。。法院应当通过对《民法典》第1197条“应当知道”的解释,根据互联网企业的类型及规模,适当提高企业的版权注意义务,以促进版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版权过滤协议”的形成。“版权过滤协议”的发展又可以促进算法技术的进步,算法技术的进步则为网络版权过滤立法提供技术基础,从而形成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立法、司法及自治的良性循环。
(三)我国实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具体制度安排
虽然我国当前尚不适合为网络服务提供商设置法定的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但是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具体制度安排可以为版权侵权的司法实践提供方向。
1.适用主体的范围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就网络服务的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主要包括基础网络服务、内容存储服务、内容发布服务等。根据服务类型的不同,网络平台对用户内容的控制程度以及过滤成本的高低均存在明显差异,故不能将网络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一刀切地向全部网络平台施加,否则会抑制网络信息的自由交流,从而阻碍互联网的发展。以提供基础通讯以及技术服务的网络平台为例,如果对其采取过滤措施,产生的社会成本极高,不仅影响信息的传播效率,更有可能导致对用户隐私等合法权益的侵害。网络搜索和链接服务平台仅向用户提供搜索以及链接服务,并不涉及存储侵权内容本身。平台一方面无法对海量搜索内容建立正版数据库,另一方面也并非侵权行为成立的必要要件,即使对其采取过滤措施,也仅能做到防止侵权行为的扩大化,而非从源头上阻止行为的发生。而网络内容分享平台(如视频分享平台、音乐分享平台)作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源头,不仅能够快速、有效地控制用户上传的内容,而且对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直接的帮助作用。同时,网络内容分享平台的性质同样影响内容过滤措施实施的成本,对于非营利性的网络内容分享平台(如科普资源库),虽然依旧将提供并储存用户大量版权作品作为主要目的,但并不因用户上传侵权行为而获利,其运营方式与版权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因此,营利性网络内容分享平台符合实施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主体要求。
2.过滤标准的选择
立法作为一项确定性规则无法为网络内容分享平台设置具体、详细的过滤标准,通常将网络内容分享平台注意义务的解释权交由法院裁量,但法院仍无法为算法设计提供技术标准。网络平台过滤标准的选择,应当由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门的技术专家小组,针对不同规模的网络内容分享平台设置不同等级的过滤标准,并根据计算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首先,此处可借鉴欧盟《版权指令》第17条,根据网络内容分享平台的成立时间、用户访问量、营利收益、社会影响力等多方面因素,将网络内容分享平台划分为超大型、大型、中型、小型、超小型,通过评估网络内容分享平台实施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的成本,为每一类型的网络内容分享平台设置合理宽度的注意义务,并由网络内容分享平台在该限度内自由选择过滤标准(26)宋哲:《网络服务商注意义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页。。其次,在具体的侵权案件中,应由法院基于“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在有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内判断网络内容分享平台是否存在“应当知道”的情形。如此做法,既符合版权内容过滤的技术性要求,又保证了法院的最终裁判权。最后,由行政机关设置版权过滤标准,避免了美国“自治规则”下,版权过滤协议为追求私人利益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可能性。
3.错误过滤的救济
错误过滤的救济离不开人工审查的保障。我国《民法典》第1196条规定,用户收到通知时,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由网络服务提供商转送给版权人,并告知版权人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错误的版权过滤同样可以按照反通知的模式,由用户向网络内容分享平台提交错误过滤的异议申请书,网络内容分享平台本着善意和中立原则,根据异议理由对过滤信息展开人工审查,并于规定时间内向用户做出及时回复,用户和版权人均可对审查结果向有关部门投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视为对平台人工审查结果的认可。
结语
随着算法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平衡版权人与网络内容分享平台间的利益关系,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应运而生。在理清版权内容过滤措施与版权合理使用、用户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界限的基础上,关于版权内容过滤模式的选择问题,当前大致可分为欧盟“国家法律”模式以及美国“自治规则”模式。我国尚处于算法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过分强调学习欧美模式,会阻碍互联网市场的发展,不利于网络生态环境的监管。《民法典》第1197条增加“应当知道”条款,实际上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为我国实施网络版权内容过滤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司法实践通过对“应当知道”条款的解释,促进了版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版权过滤协议”的形成。而“版权过滤协议”的发展又可以促进算法技术的进步,算法技术的进步则为网络版权过滤立法提供技术基础,从而形成版权内容过滤措施立法、司法及自治的良性循环。因此,面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借鉴但不盲从,立足于我国当前网络版权保护的现状,明确过滤主体的适用范围,建立合理的过滤标准和错误过滤的救济机制,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版权内容过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