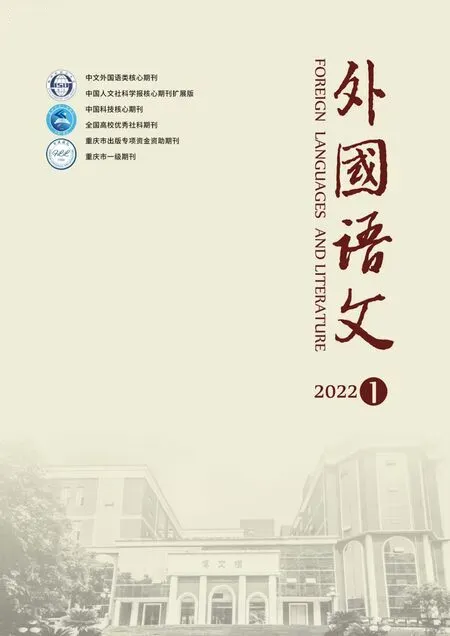亨利·詹姆斯《金碗》中的真实观
王楠 王欣宇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0 引言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小说的艺术》中强调,小说的至高价值在于“予人真实之感”(James, 1885:66),是表现生活的“真实”,“(应该)是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James, 1885:60),而经验(experience)是由许多印象(impressions)构成的,因此,印象就是经验(James, 1885:66)。在詹姆斯看来,生活本身是有缺陷、混乱无章的,需要萃取为和谐优美的艺术,“将生活转变成艺术需要艺术家对生活材料的掌握、选择和安排”(陈丽,2009:41)。而印象构成生活的“经验”(experience),是艺术有待提炼的表现真实的材料。作者必须具备对真实的感知能力,根据个人对真实的经验来写作。詹姆斯形容“经验”是一种“漫无边际的感受(sensibility)”,他将其比作一张意识之室中的巨大蛛网,时刻“捕捉着每一颗随风飘落在其中的微粒”(James, 1885: 64)。可见,在詹姆斯看来,小说应当记载个人对真实的感知经验,而经验由缥缈不定的感受构成,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世界中,真相往往波谲云诡,一经呈现难免造成虚幻感。詹姆斯的小说真实观便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编织联结的网络(陈秋红,2012:23),用虚构捕捉真实,也用真实塑造幻觉,让人游移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不得不多加揣测和思考。那么詹姆斯是如何记录“真实”的?学界普遍认为詹姆斯的作品通常带有象征和隐喻色彩,并不是直观的描述(Grossman, 1994: 311),詹姆斯通过描绘小说人物的想象和幻觉来呈现人物对真实的感知经验(Blackmur, 1983: 46),真实就蕴藏在充满意象的看似虚幻的意识世界当中,可以理解为“通过意象展示的苏醒了的‘自我意识’的真实”(陈秋红,2017: 23)。
本文认为,詹姆斯笔下的“真实”并非不可捉摸,读者可以通过追踪作品中人物对真相的认知体验来发掘詹姆斯小说中的真实。真相是有待发现的事实,而真实是人物意识世界中种种经验的呈现,它在人物走近真相的途中渐渐沉淀。本文聚焦《金碗》中主人公玛吉(Maggi)的经验描写,探讨玛吉是否获知“真相”又如何把握真实。笔者认为,随着小说核心意象金碗的出现和破碎,丈夫与继母乱伦私情的渐露端倪,玛吉对真实的感知不断深化,自我意识渐渐苏醒,她经历了从“无知”到“感知”的转变,再从“感知”到“认知”的提升,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对潜在事实的无知且不为,对真相的虚幻感知而有为,以及最终对真实的认知且无畏。
1 无知不为
《金碗》是詹姆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情节围绕两对夫妻展开,讲述了他们之间由前因后缘引发的伦理混乱的婚姻故事。小说分为两卷,第一卷侧重从亚美利哥(Amerigo)的角度描写,第二卷则着眼于玛吉的意识世界和经历,记录了玛吉对真实的认知历程以及认知真实后的行动。对于拥有上帝视角的读者来说,玛吉的丈夫亚美利哥与她的继母夏萝(Charlotte)之间显然暧昧不清,然而,关于玛吉本人是否知道亚美利哥和夏萝的乱伦私情,作者自始至终没有直接交代。读者被淹没在玛吉的意识活动里,和玛吉一同游走在真相与虚幻之间,只能试图寻找玛吉感知事实的线索,期待从复杂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的细枝末节之中发掘玛吉对“真相”的觉悟,而这需要依靠读者的想象力和判断力。
小说第一卷以亚美利哥的视角展开,对玛吉的心理描写几乎无处可寻,因而读者无法依靠玛吉的意识活动窥探其内心,只能凭借他人之口和玛吉本人所为了解玛吉。首先,玛吉最初的形象是天真的,他人的评价侧面体现出玛吉此时的“无知”。第一卷开篇,亚美利哥回忆起自己与玛吉的交往,他认为玛吉身上具有一种“超凡的美国式真诚”以及天真烂漫的气质(8)。天真(innocence)一词在英语中既可意为缺乏经验也可用于表示“无知”。对于意大利没落贵族亚美利哥来说,玛吉给他的最初印象是一位具有美国式纯真品质的姑娘,她的天真不仅在于她的真诚,也在于她对真实的“无知”( 8)。而她的“无知”在于“任何有关真实(veracity)、忠贞或是与之相悖的严肃话题,都会令她措手不及,好像这些问题对她来说过于陌生”(11),言外之意,玛吉缺乏对有关真实和忠贞问题的思考和经验,遑论认识真实,区别真假。所以当亚美利哥问玛吉是否相信他不是伪君子时,玛吉表现得手足无措。这段情节不仅体现了玛吉起初对真相的无知,也似乎为亚美利哥后来的不诚不贞埋下了伏笔。
另外,芬妮·艾辛肯(Fanny Assingham)是亚美利哥和玛吉的牵线人以及夏萝的旧识,她为读者分析主人公形象提供了很多线索。艾辛肯太太从头到尾都对亚美利哥和夏萝的关系了如指掌,得知夏萝在亚美利哥和玛吉成婚前来到伦敦,她隐隐觉得不安,担心玛吉知道真相后崩溃。她断言,倘若玛吉知晓亚美利哥和夏萝曾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恋情,“她会吓坏了”,因为“她天生就不懂邪恶这回事”(51)。此处的“邪恶”狭义上或可理解为亚美利哥与夏萝的旧情,或可视为二人对玛吉心照不宣的隐瞒,广义上则暗指与真实、忠贞相悖的一切隐秘龌龊。可见,艾辛肯太太对玛吉的看法和亚美利哥类似,都从侧面说明了玛吉最初对真实一无所知的状态。
而玛吉在此阶段的所为更是印证了她的“无知”。此时的玛吉不了解亚美利哥和夏萝的过去,也不曾考虑过有关真实和忠贞的问题,自然没有表现出对真实的感知和回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玛吉完全根据自己当下的判断行事,无意中为日后埋下了隐患。婚后的玛吉为落单的父亲亚当感到担忧,父女二人本来是相依为命、亲密无间的,她认为自己的婚姻改变了原状,对父亲来说是不公平的。为此,玛吉决定为父亲寻觅一个合适的伴侣,而她选择的对象就是好友夏萝。在玛吉看来,夏萝在品性、精神和生活方面都十分出色(51),她的加入对家族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同时也能满足自己补偿父亲的心愿。亚当与夏萝成婚后,夏萝在社交场上如鱼得水,不热衷于此的玛吉渐渐习惯了把社交事务抛给夏萝和亚美利哥,像往常一样无微不至地陪伴在父亲身边,本就对丈夫与继母旧情人关系一无所知的玛吉自然联想不到二人会因此旧情复燃,更不知道她所以为的家庭和睦背后藏匿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明真相的玛吉放任事态发展,亚美利哥和夏萝的交往日渐亲密。
艾辛肯太太作为此时唯一知道真相的旁观者,一直暗中观察着亚美利哥和夏萝,并发现二人关系微妙,她跟丈夫谈论玛吉一家时说到,一切都是玛吉起的头,是“她启动了恶性循环”(251)。根据艾辛肯太太的分析,玛吉为了补偿父亲,不仅促成了他与夏萝的婚事,还花费大把时间陪伴他,于是不可避免地冷落了丈夫亚美利哥。为了补偿被忽视的丈夫,玛吉放纵夏萝陪着他,以免他觉得孤单。可这样做又仿佛造成了年轻的继母与父亲的疏离,这又让她想要补偿夏萝。艾辛肯太太的说法暗示玛吉如今被蒙在鼓里盲目行事的情状,玛吉周旋在三人之间,自以为权衡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事情一直朝着她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阶段,玛吉因为对真相的无知,只能陷入自己臆想的假象中,逐渐偏离真实,她按照毫无依据的想象采取的行动实则是对真实的“不为”。然而,真相终会显露端倪,小说第一卷结尾处,作者借艾辛肯太太之口暗示了玛吉的醒悟。玛吉因何醒悟、如何感知真相、是否能够把握真实等问题,需要从她对真相的意识中探寻答案。
2 感知有为
小说第二卷,玛吉逐渐开始感知真相。在这一卷的前半部分,玛吉开始意识到他们四人的关系表面和谐,实则暗藏玄机,并对亚美利哥和夏萝的过密交往感到顾虑。此时,她隐隐感知到了真实,她的意识世界中不断浮现出有关真相的隐喻和意象,她试图在虚幻的想象中捕捉真实。在感知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接近真相,玛吉开始有所为。一方面,她向当事人亚美利哥和夏萝发起隐晦的拷问,提出让他们暂时分开的计划,以此试探二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她向旁观者艾辛肯太太求助,通过向他人道出怀疑更加明晰自己的感知。这些行动促使玛吉逐步接近真相,但由于缺乏实质证据,她在此阶段尚未抵达真实。
第二卷开篇,玛吉在波特兰宫等待推迟归程的丈夫从马灿回家,同时反思自己最近的处境和生活的改变。她的意识世界中浮现出有关真实的隐喻图像,这些意象描绘了她对真相的感知。在玛吉的想象中,她这几个月以来一直面对着一座“奇怪的高大象牙塔”,却“直到现在才渴望进去”(258)。“象牙塔”象征着四个主角之间复杂错乱的关系,暗示玛吉对自己婚姻处境的感知,以及她试图接近真相却难以如愿的状态(陈秋红,2012:56)。玛吉起初认为他们的关系是和谐且平衡的,如同象牙塔的外观一样,看起来纯白美好,赏心悦目。她觉得他们收获了幸福,正如那座象牙塔一样升得越来越高(258)。那时,玛吉是象牙塔的欣赏者,她丝毫不怀疑四人关系的和谐表象并为此感到欣慰,因此也没有前往其内部探知究竟的意愿。而近几个月以来,玛吉在面对“象牙塔”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迷茫无助,她觉得自己始终在围着“象牙塔”兜圈子,却找不到入口。此时,她面对这座具有象征意味的象牙塔时不再觉得舒心自在,这说明她对真实情况产生了怀疑:象牙塔可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的婚姻表面美满,实际却可能问题重重。面对亚美利哥和夏萝推迟从马灿回来的决定,玛吉的疑惑更甚,她开始感知到自己未曾关注的真实并试图捕捉它,于是玛吉不再围着象牙塔兜圈子,决定走进“象牙塔”一探真伪。
“象牙塔”作为玛吉意识世界中的意象,揭示了玛吉对四人关系的反思。真相是他们的关系暗藏纠葛,与玛吉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玛吉起先以为夏萝的加入成全了她安抚父亲的心愿,让她可以在献身于丈夫的同时又不舍弃父亲。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父亲迎娶夏萝之后,玛吉和父亲的关系亲密如初,却与丈夫亚美利哥渐行渐远,这给了亚美利哥和夏萝旧情复燃的机会。在反思他们的关系时,玛吉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马车”的意象。夏萝加入之前,她与父亲和亚美利哥的关系就如同一个三轮马车,夏萝加入之后充当了第四个轮子,问题在于,“亚美利哥和夏萝在努力拉着车子,而她和父亲却连推都没推一把”(270)。玛吉意识到,亚美利哥和夏萝成了他们四人中的主导者,而她和父亲都没有用心维持自己与伴侣的关系。父女二人将大部分家庭外事务和社交活动交与亚美利哥和夏萝处理,自己却独处事外,导致他们与各自的伴侣产生隔阂,间接造成亚美利哥和夏萝交往甚密。意识到这一点后,玛吉质问自己:“假如是我抛弃了他们呢?假如是我过于被动地接受了我们这种滑稽的生活方式呢?”(271)此时,玛吉认识到自己与父亲过度亲密的感情以及他们对各自配偶的忽视造成了如今的尴尬局面,他们看似和谐的关系不过是虚假的表象,这也是玛吉察觉出亚美利哥与夏萝乱伦私情的前提。
玛吉反思四人关系之后,开始怀疑亚美利哥与夏萝的过密交往,由此发现了小说中另一个隐晦的真相:亚美利哥与夏萝的地下情。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玛吉内心对丈夫亚美利哥产生一种极度渴望又十分愤懑之情:“突然有一天,那个已经装满的杯子,满到了杯缘,溢了出来。那是我需要你时的样子——那个杯子一整天都太满了,满到没办法端着。”(267)杯子溢满的意象也暗示玛吉对丈夫和夏萝的微妙关系有所感知,预示她即将采取行动。玛吉在她蛛网般的意识世界中捕捉到真实,它以意象的形式呈现在脑海当中,唤醒了她的自我意识。收获了感知体验的玛吉也在行动上有所作为,不再被蒙在鼓里,而是通过试探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态度进一步接近真相。
在亚美利哥与夏萝从马灿度假回来后,玛吉发起第一次拷问,迈出揭示真相的第一步。她装作坦然地问他们的马灿之行有何收获。玛吉敏感地捕捉到夏萝茫然无措的神情,并联想到亚美利哥从马灿归来当晚曾露出与之十分相似的表情。玛吉愈发怀疑两人的关系,同时亚美利哥和夏萝在玛吉发出拷问的暗示之后,试图继续维持若无其事的和谐关系,两人的合作密谋又使玛吉陷入无尽的痛苦,既求不得丈夫回头,又证实不了心中所想。她意识到“他们(亚美利哥和夏萝)愿意为了满足我们做任何事,只一件除外——让我们画条线把他们分开”(300)。为了打破两人不可分割的关系,试探自己的怀疑是否属实,玛吉做出下一步行动——提出让亚美利哥和夏萝暂时分开的旅行计划。
玛吉说服亚美利哥和父亲亚当去旅行,留她和夏萝在家里,并建议亚美利哥亲自向父亲提议。这样一来,玛吉成为实施分离计划的构思者,而亚美利哥是计划的提出者,整个计划与夏萝毫无关系,因此,玛吉提出这个计划不仅意在分开亚美利哥和夏萝,也是想把夏萝排挤在外。出乎意料的是,亚美利哥却拐弯抹角地建议由夏萝把旅行的事转告给亚当。亚美利哥的提议将夏萝重新拉回到他们中间,甚至给了夏萝维持或打破局面的选择(魏新俊,2014:74)。这破坏了玛吉的计划,令她愈发困惑:“我们唯一需要的人只是对方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拉夏萝进来呢?”(302)显然,玛吉的计划失败了,这也恰恰说明丈夫和继母的关系果然不同寻常。玛吉通过试探亚美利哥和夏萝的态度,愈发加深自己的怀疑,但当局者迷,仅凭当事人的感受还不足以验证猜想,所以她向旁观者艾辛肯太太求助,艾辛肯太太的反应让她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再度接近真相。
玛吉始终讳而不言自己对丈夫和继母的怀疑,面对艾辛肯太太,她第一次用言语表达近来的困扰,知晓实情的艾辛肯太太瞬间脸色惨白,这让玛吉确信她早就知情,此次试探使玛吉更接近真相。受惊的艾辛肯太太试图询问玛吉是否怀疑亚美利哥和夏萝的关系,但玛吉没有对此给出任何答案,因为真相在她的一步步试探中已经呼之欲出,但她还不忍面对残酷的现实。艾辛肯太太的一番评论可以用来形容玛吉现在的状态:“她(玛吉)不可避免地知道他们俩(亚美利哥和夏萝)之间有点儿什么。但是,她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走到’结论;那是她还没有做到的事,也是她坚持抗拒去做的事。”(337)换言之,玛吉已经确定亚美利哥和夏萝关系微妙,但她还没能证实两人真的有染,尽管她内心充满怀疑,却没有挑明真相,而是在虚幻的感知中与真相无限接近又不愿抵达。
詹姆斯通过大量篇幅以内心独白的形式让玛吉陈述自己对四人关系的认识过程,她在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意象都是她对真实的感知和想象。对真相的感知促使她采取行动,无限地接近真相。直到“金碗”作为证据不期而遇地出现,亚美利哥的不忠才得以暴露,玛吉终于看到了“真相”,但她却始终对“真相”保持沉默(Guerra, 1998: 64),选择与“真相”保持距离。似乎玛吉的自我意识提醒她“真相”本身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她意识到了“真相”的存在,而只有苏醒的自我意识才能帮助自己把握真实,因此,体认真相的玛吉没有纠结于真相,而是迂回地绕过它,转而发现真相背后的内涵,获得对世界的理性认知,并利用自己沉淀下来的观察和慧心解开困局,这即是玛吉体验真实的第三个阶段——认知而无畏。
3 认知无畏
认知作为人对外在现实和自身经验的理性看法,是人们对世界万物形成概念和意义的途径(王寅,2007: 8),玛吉正是在自己充满隐喻的认知之旅中获得了对真实的理性认识,渐渐实现自我意识的“苏醒”,而她的认知不囿于对真相的表层了解,而是囊括了她对周遭事物及其意义的更深层挖掘。在认知诗学视域下,隐喻是认知活动的核心研究范畴之一,文学中隐喻的考察不仅限于其诗学效果或曰艺术效果,还关注隐喻是否创造了新的意义,因为日常的意象转变为审美意象后有可能被赋予新的意蕴。此外需注意隐喻能否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改变其认知模式(熊沐清,2008:304;熊沐清,2012:458),这一观点或为解读玛吉对真实的认知提供理论视角。
“金碗”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具有鲜明的隐喻色彩和审美价值。它是一件表面镀金的水晶工艺品,看似精美却内藏裂痕,表里不一的形象隐晦地指向小说中暗藏的真相:徒有其表的没落贵族亚美利哥对婚姻不忠的事实(Penrice,1991: 351);看似美满的婚姻背后是难以启齿的致命隐患(王珊,2004: 89);表面和谐的家庭环境实际暗藏微妙错落的人物关系(魏新俊,2014: 73)。可见,金碗既是小说中存在的物质实体,又是别有深意的抽象能指,被赋予了道德“试金石”般的意味,它的隐喻联结了物质世界与意识世界,为戏中人和读者都提供了一把“知性的钥匙”(陈秋红,2012: 61)。玛吉便是利用此密钥,走出眼前的困境,直面人生境遇。对真相的认知过程也让玛吉收获理性的体悟,实现自我意识的苏醒,给予她足够的理智和底气来重构现实。
金碗在小说中仅出现过两次,但每次都出现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其寓意非凡。金碗的第一次出场是在亚美利哥与玛吉结婚前夜,夏萝以为玛吉选新婚礼物为由与旧情人亚美利哥秘密相会,二人在一家古董店见到这只金碗。冥冥之中,金碗的首次登场拉开了这场家庭伦理剧的序幕,而它的裂痕暗示亚美利哥和夏萝的关系为两段婚姻埋下的隐患(王珊,2004: 88)。金碗的再次出现暴露了这潜藏的危机。玛吉为父亲挑选生日礼物时,光顾了那家古董店并看中了金碗,她偶然从店主口中得知,亚美利哥和夏萝四年前曾一起来过此店,这说明他们早就相识,两人的暧昧关系昭然若揭。
如今证据确凿,玛吉终于看清亚美利哥与夏萝的关系,同时她也通过解读“金碗”这一隐喻,深度挖掘了藏匿在他们婚姻背后的隐晦真实,收获自己作为个体对世界的理性认知。玛吉把早已知晓事实的艾辛肯太太叫来对证,她自语般地对艾辛肯太太说,“亚美利哥娶我是靠着这整件事”,“也是靠着它,爸爸才娶了她(夏萝)”(361)。这里的“它”指造就两段婚姻的根本原因,也与金碗的隐喻密不可分。金碗在小说中既象征徒有贵族之名的亚美利哥(Snow,1963: 421),也寓意主角们貌合神离的婚姻(王珊,2004: 88)。而它本身是一件商品,华美的外表赋予其物质的属性。对父女来说,亚美利哥好似一件稀有的收藏品(9),其价值在于他的贵族身份标签,这是他们与之联姻的原因。而对于亚美利哥和夏萝,婚姻是他们换取金钱和地位的捷径(王珊,2004: 89),是迫于物质原因分手的他们做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给自己的婚姻贴上物质的标签,婚姻和金碗一样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最终只能如金碗般破裂,这是玛吉在“金碗”隐喻式的佐证下得出的认知,为角色和读者都提供了道德启示。尽管艾辛肯太太摔碎了金碗,意图销毁证据以蒙蔽真相,但玛吉已经看见真相,破碎的金碗已然象征失衡的婚姻,等待玛吉将它重塑。对真实的认知和体悟让玛吉变得无畏,她没有陷于真相,郁结难消,更没有向众人揭露真相,而是返归内心,栖宿在苏醒的自我意识中,以“苏醒”的自我直面现实,重新建构四人之间的关系。
“苏醒”的玛吉利用自己对真实的把握在丈夫、继母和父亲三人中周旋,逐步激活自我保护的认知经验和作为意识主体的行为能力。她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警告丈夫亚美利哥。她没有直白地告诉亚美利哥自己知道什么,而是讲述金碗的来历,暗示丈夫自己已知他与夏萝的旧情。玛吉对亚美利哥说,“我确定……你和夏萝有过,而且很长时间有过两段关系”(373)。玛吉的警告对亚美利哥来说出乎意料,但玛吉没有逼迫他做出回应,只是让他知道自己不再无知,让他了解她想要“没有漏洞的幸福”(388),而把尚未道破的真实和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了亚美利哥。玛吉对亚美利哥说:“我把自己想说的都说完了。其余的,你自己去发现吧。”(381)玛吉让亚美利哥自己去发现,其实也是要让他自我反思并在无形中给他施压。亚美利哥最终选择保持缄默,与玛吉共谋,让夏萝落入未知的深渊,困顿不已。这让玛吉愈发充满底气,她充分发挥自己作为意识主体的想象力,用真实建构想象,在意识世界中绘出这样一幅场景:受伤的鸟儿在镀了金的笼子里苦苦挣扎,自己则绕着鸟笼打转(396)。囚鸟的形象暗指孤立无援的夏萝,失去亚美利哥袒护的她被蒙在鼓里,无法获知真相,只能在徒劳的猜测中崩溃。玛吉刻意隐瞒自己已知真相的事实,为夏萝编织谎言的鸟笼,她绕着夏萝的笼子兜圈子,仿佛在酝酿一场不为人知的计划,预示着她将以捕猎者的姿态击溃夏萝。
此时,出于对真相的把握,玛吉已然变成四人关系的主导者,其他人该如何自处全赖于她的做法。得知真相的当晚,玛吉坐在角落安静地旁观其他人打牌,无声的审视令人战战兢兢。面对牌桌上各怀心思的同伴们,玛吉感到“他们心照不宣地把整个危机的烂摊子都交给她处理”(399),他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演员,为了维持幸福的表象做戏,认清真相的自己则像是这出戏的编剧,拥有把控剧情走向的权力。虽然表面看来,玛吉对真相讳莫如深,似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事实,实际上她对自己想要的剧本走向早已心中有数,苏醒的自我意识将为她赢得这场对峙的胜利。为了保全婚姻,玛吉计划以和父亲分离为代价,让他带着夏萝迁到美国,留下她与亚美利哥修复感情。玛吉没有直言希望父亲做什么,而是通过言外之意让父亲“了解她的最佳选择,并由此知道他自己的路”(420)。最终,亚美利哥选择缄默并退缩成“一道深沉的光”(408),亚当成全女儿的心愿带着夏萝离开,夏萝无力反抗,随亚当去了美国,这宣告这场伦理闹剧的终结,玛吉重塑人物关系的计划得以实现。
玛吉在认清丈夫与继母私情的真相后,没有陷入与真相本身的纠缠,而是深入挖掘真相之下的缘由和内涵,在苏醒的自我意识世界中建构隐喻与现实的联系,形成自己作为意识主体对外在现实和自身经验的理性看法,实现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并鼓起勇气改写现实。值得注意的是,玛吉向众人隐藏了自己的认知,她的认知经历注定是一次孤单的旅程,也只有依靠自己她才能实现自我意识的苏醒,把握真实,重构现实。而出于对真实的把握,玛吉可以在无声中压制对手:对亚美利哥,玛吉没有直接道破他与夏萝的私情,给了他反思和选择的余地;对夏萝,玛吉掩藏自己知道的真相,让她在无知中徒劳挣扎;对父亲,玛吉闭口不谈真实的情况,用弦外之音暗示自己的心愿。最后,所有人都按照玛吉的安排各得其所。利用对真实的认知和在感知过程中收获的智慧,玛吉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苏醒,不动声色地挽救了自己的婚姻,也完成了自己作为个体的理性蜕变。
4 结语
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强调,小说是个人对真实经验的记录,而经验是“漫无边际的感受”(James, 1885: 64),它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个体在虚幻与真实之间游走,在想象中捕捉真实,又通过真实建构想象,而读者为了探知角色的真实体验也需陷入虚幻的想象当中,只有细细考量,反复推敲,才能知其真味。《金碗》的主人公玛吉曾囿于无边的意识世界,通过不断的观察和反思,她逐渐积累了对真实的经验,提升对真实的感知,金碗的出现让她最终获知真相,使她突破虚幻的想象并把握了真实。同时,这段经验赋予玛吉理性的个体感悟,她利用对真实的认知重新建构想象,将对手比作笼中雀,将内心的愤懑转化为苏醒的自我意识,继而采取行动,最终得以重构现实,在虚幻与真实之间建立千丝万缕的关联,实现从“无知”到“认知”的理性升华。詹姆斯用充满隐喻色彩的语言编织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蛛网,用它捕捉真实经验,为世人留下历久弥新的文学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