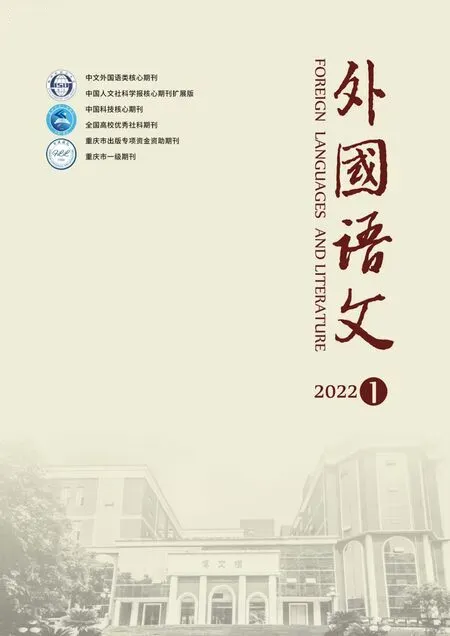抗战时期桂林俄文专修学校翻译人才培养考察
蓝岚 张旭
(1. 广西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 广西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1)
0 引言
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学等因素使然,俄苏文学翻译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翻译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1949年以前,我国可以直接从原文翻译俄苏文学的译者有三代,第三代成长于抗战时期,他们中只有少数集结于上海,大部分散居在重庆和桂林等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艾抒峤,2000:77)。桂林抗战文化城(以下简称“文化城”)时期(1938—1944年)的桂林俄文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桂林俄专”或“俄专”)培养了一批从事军事和文学翻译的译者。1949年以后,俄专毕业生成为我国俄文翻译和编辑界的中坚力量。遗憾的是,无论是外语教育通史、俄语教育史还是区域教育史专著,基本都忽略了对桂林俄专的介绍;已有的少量研究大多缺乏一手文献的佐证。俄专的史料散见于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物和后来各地的文史资料中。笔者通过资料爬梳与实地探访,研究该校翻译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式和效果,以期为区域翻译史、翻译文学史和翻译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1 培养什么样的翻译人才?
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其教学内容和形式;对于一所在战争时期快速建成的外文学校而言,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政治背景往往对人才培养目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1.1前期目标:从速培养俄文翻译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苏联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俄语教育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宁琦,2019:76)。1949年以前,我国有13所高校设有俄文系科(付克,1986:65),近半数位于东北,其他大多分布在西北和华东。1935年10月,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派出军事顾问和空军来华支援,中苏交流日渐兴盛,然而我国的俄文人才仍然奇缺(斯庸,2002:79)。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联军事顾问事务处处长张冲提议创办俄文培训学校,从速培养俄文翻译,以应急需(马雨农,2012:406)。1938年秋,以中苏文协名义成立的俄文专修学校在汉口开办,张冲任校长,苏联军事顾问处人员担任教员。武汉失守后,中苏文协迁至重庆。1938年,桂林俄专作为俄专分校成立,校址位于桂林市全善街兰井巷的一所小学,利用晚上进行教学。
张冲本人精通俄文,皖南事变前后为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作出过重要贡献,担任校长期间,他要求顾问处设在各地的办事处要兼顾好俄专工作;全国几处办事处中,以桂林办事处的规模为大(马雨农,2012:402)。1941年张冲病逝,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之后为表纪念,俄专总校和分校一律改称“淮南俄文专修学校”。俄专办学之初,师资多为苏联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的翻译。早期三位教师为楼钱江、楼湘江和卢席光,1939年以后有王学业、孙亚明、李德厚和李德才(蒋路,1987:145)加入。这些教师大多来自东北,俄文功底深厚,长期在中苏交往一线工作,具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楼氏兄弟1939年和1940年在桂林出版了两册《俄语自修丛书》教材,在第二册中作者提到“自从我们发动了神圣的抗战以后,两国因为都是站在和平和反侵略战线上的战友”,“俄话也跟着密切关系而一天天的感觉到需要”,“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几个大都市里设立了几个俄文学校”(楼湘江 等,1940:1)。
1.2后期目标: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俄文人才
1941年,孙亚明被俄专总校任命为桂林分校主任。他曾留学苏联和日本,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受到叶剑英接见,到延安新华社工作,兼任“抗大”和陕北公学教员。孙亚明精通俄文,成功打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先后任俄文首席顾问翻译和上校编审(孙亚明,1989:27)。苏联顾问陆续回国后,他又被派往桂林俄专工作(周恩惠,1998:26)。1939年11月,孙亚明翻译的苏联伯伯夫所著《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在桂林新知书店出版,介绍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各个阶段的特征。1942年4月,他在中苏文协桂林分会大会上发表演讲并被选为候补理事,“协助俄文专科学校,培养俄文人材”也被列为文协下一步的工作要点(佚名,1942a)。蒋路1938年到陕北公学学习,在“普通队”和以培养理论干部为宗旨的“高级部”进修。1939年夏,中共中央组织部动员他重返国统区,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工作。蒋路回到广西后于1940年入读俄专,1942年留校任教(中央文史研究馆,2001:329)。孙亚明主持校务的四年(1941—1944)被认为是桂林俄专的“鼎盛时期”(蒋路,1987:146)。这一时期,俄专由中共党员直接领导,其教学骨干在延安接受过理论培训,具有明确的思想倾向,同时,还有党员作家积极推荐青年入读。据俄专学生尤开元(2004:48)回忆,孙亚明当时“不仅要为我国培养更多的俄文人才,还要把它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阵地”,这种人才培养目标与孙亚明本人以及学校骨干教师的政治背景有着直接、必然的联系。
2 如何培养翻译人才?
1942年8月俄专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登的招生启事显示,学生入学资格是“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招生名额为“新班六十名各级插班生二十名(男女兼收)”(佚名,1942c)。基于这样的生源基础和招生规模,桂林俄专如何在进行俄文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从目前查阅到的材料来看,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有课内的课程学习、听报告和课外的读书会、自学等。
2.1课内推进教改,注重教材思想性
俄专初建时使用的教材是《俄文津梁》和《俄文文法》(梁建兴,1987:153),内容较为陈旧。孙亚明主持工作后,主张直接“从苏联报刊和文学作品中选取教材,使同学能广泛了解苏联的卫国战争、人民生活和历史概况,在认识上得到提高”(蒋路,1987:146),这种做法既是前期“从速”培养人才目标的体现,也适应了后期“培养社会主义思想人才”的目标。学校还邀请到访桂林的苏联记者或外交官作报告。1943年5月,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别德科聂夫一行三人到桂林,俄专举行了联欢大会(佚名,1943)。武官的秘书在会上介绍,“法西斯匪帮”对俄苏文学作品“深恶痛绝”,“随时随地要加以破坏”,有苏联士兵就在战斗中喊出了“为了普式庚/托尔斯泰”等口号;对于俄专学生提出的关于苏联妇女的问题,秘书回答,她们和男子一样工作,“邵力子夫人翻译的《丹娘》就是苏联妇女在敌后斗争的一个例子”(李中玉,1943)。武官秘书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向俄专学生强调研读俄苏尤其是苏联文学译作对于学习俄语、了解社会主义苏联的重要性。学校还很重视学习氛围的营造,在校门旁的墙上刷了大字的标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和“以俄为师”(尤开元,2004:49),激励学生学习俄文。
2.2课外苦练翻译,时事与文学兼顾
俄专学生在课外组织了“读书会”式的学习小组(尤开元,2004:48)。小组在每两周的周日聚会,主要活动是学俄文、学翻译和学时事政治(斯庸,2004:52)。组员平时对照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中文版本,从中了解苏联革命史,并揣摩翻译技巧,聚会时,大家轮流用俄文背诵每章结论。组员还研读了曹靖华翻译的苏联小说《虹》以及丽尼根据加尼特夫人英译本转译的屠格涅夫作品。他们把俄文原著和译本进行对比后发现,内容几乎没有出入,连文笔的优美程度也大体相当,由此对译者非常敬佩,并以他们为学习榜样(曾定之,1987:57)。小组还组织“专题报告”,题目自定,轮流主讲,主题包括果戈理、苏德战事和30年代国内的“翻译大论战”等。1943年,已留校任教的蒋路在桂林影响较大的《青年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谈学俄文》,建议学习者把优秀的中译本跟原文对照读和建立学习组织,这两点应是其学生时代在学习小组中的切身体会。有些学习小组是学生自由组合的。有学生回忆,他与同班四位同学每周末聚会,学习《新华日报》等刊物,从中了解苏联卫国战争、中共的主张以及八路军的战况等;他们研读的苏联文学译作则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丹娘》等。学生平时自学时的阅读内容也激发了他们的翻译热情。蒋路当时阅读并计划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但一是没有找到俄文原著,二是认为自己的翻译经验还不够丰富,所以没有付诸实践(凌芝,2016:221)。1942年他读了楼适夷从日文转译的阿·托尔斯泰所著的《彼得大帝》,又在苏联杂志上读到该书的书评,于是将书评翻译出来投稿到了文化城时期唯一的文学翻译刊物《文学译报》上(蒋路,2001:22)。
从以上关于翻译人才培养的情况来看,俄专的课内教学非常注重学习材料的思想性,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学生对于苏联近况的了解,以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倡导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兴趣与热情。俄专学生在课内外接受的注重思想政治内容的翻译教育,深刻影响了他们在各个时期所选择的翻译题材和人生道路。
3 翻译人才培养效果如何?
译作发表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翻译人才培养效果的重要指标。抗战时期俄专师生发表了大量译文,帮助读者及时了解苏联近况和文学动态,后期还创办了专门的翻译杂志,为文化城的翻译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抗战胜利以后,俄专师生继续奋战在我国俄文翻译和编辑事业的前线,他们的翻译工作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凸显了桂林俄专翻译人才的培养效果。
3.1抗战时期:以文学和时事翻译进行文化抗战
总体来看,抗战时期俄专学生的译作发表历经了分散发表、协办刊物到自办刊物三个阶段。一开始,他们的译文多是投稿到文化城较有影响的报刊如《救亡日报》(桂林版)和《大公报》(桂林版)等的副刊上。1940年杂文期刊《野草》创刊后,俄专学生伍孟昌和庄寿慈发表了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爱伦堡、马雅可夫斯基等人作品的译文;蒋路则在《文学译报》《文艺生活》等多家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阿·托尔斯泰、爱伦堡的作品以及介绍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人的文章,出版了《论静静的顿河》和《回忆托尔斯泰与高尔基》两部单行本译作。1942年5月,《野草》主编秦似与庄寿慈、伍孟昌合办了文学翻译刊物《文学译报》,俄专学生开始从“分散发表译文”到“协办翻译刊物”。秦似和庄寿慈、伍孟昌、蒋路三位俄专学生成为译文发表数量最多的四位译者,其他师生如孙亚明和陈斯庸也在该刊发表了译文。因为在俄专所接受的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教育,俄专师生的译文选择和具体操作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倾向。例如,在蒋路所译的《论〈静静的顿河〉底主题与形象》中,原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来称赞肖洛霍夫作品中的革命主题。当时国统区的图书审查制度明令禁止“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翻译和发表此类译文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通过审查,蒋路在译文中用“卡尔”替代“马克思”,用“伊里奇”替代“列宁”(谢尔宾拉,1942:47-50)。
1943年5月,《文学译报》被桂系当局查封,同年9月,文化城第二本翻译刊物《翻译杂志》创刊。虽然杂志没有明显标注俄专信息,但由于它的主编是孙亚明和俄专学生王易今(李伯纪 等,1986:143),主要译者还是孙亚明、伍孟昌、蒋路和庄寿慈等,它实际上是俄专师生以翻译服务社会的第二个载体,他们的翻译活动也进入了“自办翻译刊物”这一阶段。《翻译杂志》以时事翻译为特色,看似没有明确政治倾向,实际并非如此。1944年3月第1卷第6期刊登了两篇关于美、苏联政治的译文,编者在“编后记”中写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看看人家宪政的建立是如何认真如何有效,对于今天我国的宪政运动或不无裨益罢”(编者,1944:19)。就在1944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力求团结党外民主人士,以达到战胜日本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翻译杂志》的编者正是通过“编后记”等副文本的形式,强化了对当局“不认真”“没有效”的暗指,及时配合了延安的政治宣传。
抗战时期俄专师生的翻译活动无一不体现着学校在翻译人才培养上所强调的思想教学成果。他们在原文选择、译文处理以及译文副文本编辑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极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他们的翻译活动不仅有力宣传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并且对延安的政治宣传进行了有效的配合。1942年7月前后,共有400多人为俄专同学会捐款(佚名,1942b),其中既有桂林出版界的经理和职员等,也有身处延安、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会参谋长兼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桂林俄专的翻译人才培养成果及其翻译活动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3.2 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翻译和编辑界的中坚力量
1944年春,俄专所在小学失火,学校迁址;同年秋,日军进犯桂林,师生撤离,俄专办学随之结束。1949年以后,俄专师生继续以自己的翻译工作服务社会并产生了重要影响。1947年春,蒋路从重庆到上海。冯雪峰嘱咐他“好好译点东西”,于是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后来冯将此书推荐给巴金出版。年底,蒋路经戈宝权介绍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与苏联以“苏商”名义合办的时代出版社。在此之后,蒋路得到冯雪峰、楼适夷以及苏联顾问的指点和帮助,翻译水平提升很快,译出了史坦因的《奧斯特罗夫斯基评传》、高尔基的《忆列宁》、卡扎凯维奇的《星》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作品。《怎么办?》在此前有两个译本,分别是罗淑(署名“世弥”)的《何为?》和费明君的《做什么?》。前者从小说的法译本转译而来(巴金,1936:ii),后者是俄文到英文再到日文最后到中文多重转译本,“与俄文原本出入很大”(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80:77)。蒋路译本是该书在我国直接从俄文翻译的首个全译本。翻译计划起源于桂林俄专时期,1949年蒋路在上海找到俄文原著后才动手翻译(凌芝,2016:221)。从1951到1996年,译本共印14次,正版累计印数达25余万册(斯庸,2002:80)。其影响首先体现在“《怎么办?》”从此成为该书书名的定译,二是为新中国一代青年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激发了读者对俄苏文学的阅读兴趣,书中对革命“新人”的描写更是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榜样。作家肖凤(2017:6)回忆,20世纪50年代,“正是最早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她被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高贵情感和美好品格”所“深深地震撼和吸引”,从此“一本接一本地读”,“一发而不可收”。
蒋路1953年调入人文社后,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两部文论集(《论俄罗斯古典作家》《论文学》)以及《俄国文学史》(与孙玮合译)和《巴纳耶娃回忆录》(与凌芝合译)。《论文学》不仅是“我国文学界全面了解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成就的主要依据”之一(陈建华,2007:67),而且成为文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书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译文“灵魂奥秘的连续的独白”曾被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直接借用在对郁达夫的研究中;有的翻译家在刚刚起步时,也把《论文学》作为学习的范本(王培元,2007:82-84),可见该译本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俄国文学史》一书出版后,不少高校将其选为文学史教材或教辅,影响广泛(斯庸,2004:54)。相对于翻译工作而言,蒋路在我国俄苏文学甚至是外国文学引进、推广等方面所做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启动了“三套丛书”(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出版工作,这三套丛书规模宏大,是我国文学翻译、编辑、出版界的一个创举(叶水夫, 2001:54)。丛书最早的编委有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冯至、季羡林、钱锺书和楼适夷等,1976年以后,编委会又加入巴金、赵家壁、绿原、蒋路、董衡巽等人。蒋路担任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分管俄苏、东欧和西方各国的书稿,是这三套丛书编选和出版工作的实际参与者。1984年4月16日,《光明日报》以“我虽然少翻译一两本书,读者却得到了更多的书”为题报道了蒋路的事迹,文章写道,“那些书上,虽然没有他的名字,可他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马雨农,1984)。蒋路在人文社培养了很多翻译和编辑人才,他在外编室工作的时期也被称为“蒋路时代”(王培元,2007:93)。
人文社的桂林俄专毕业生还有伍孟昌和陈斯庸。伍孟昌1949年进入时代出版社,1953年也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编有《高尔基选集》10余卷和30多种俄苏文学作品,译作有《高尔基政论集》和《高尔基文学散论》等。陈斯庸1980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了20卷本《高尔基文集》的责编工作。他们二人在桂林俄专时期就翻译了数篇高尔基的作品以及评论高尔基的文章,对高尔基的热爱与研究持续终生。陈斯庸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编校了《牛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以及《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译作。共青团中央曾将《牛虻》作为优秀读物向全体团员和全国青年推荐,读者反应热烈,影响巨大;《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青春之歌》等作品一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和道德品质的形成(唐凯麟,2017:105-106)。《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出版两月之间印量达到105万册,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曾将书中主人公娜斯嘉勇于和无视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精神概括为“娜斯嘉精神”,要求出版社向广大青年介绍和推荐此书(斯庸,2004:54)。不仅如此,该书还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全国作协专门组织座谈,呼吁作家“干预生活”。以“马铁丁”为笔名的一系列批评慵懒作风与官僚习气的小品文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振;青年作家王蒙结合自身经历,仿效该书创作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彭龄 等, 2015)。三位桂林俄专的昔日同窗一起在人文社担任俄文编辑和翻译,他们一生的工作对我国几代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和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本身就是对桂林俄专人才培养质量和历史贡献的最大肯定。
其他毕业生在翻译领域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庄寿慈在抗战胜利后曾任塔斯社驻华分社的翻译,20世纪50年代调到北京,参与创办《译文》杂志,“选材、编辑、画版式、选插图、看清样……事事都干”,并且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高莽,2005:313)。在中央文化委员会编译室工作过的王易今、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工作并参加过《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编译工作的陆梅林和陈山、人民出版社的尤开元、商务印书馆的郭一民等知名俄文翻译和编辑也都是桂林俄专的毕业生。一些毕业生后来在大学和中学担任俄文教师,同样学以致用。对于一个战争年代创办、办学时间不长且只有百余名毕业生的地方俄文学校而言,这样的人才培养成果和社会影响无疑是令人瞩目的,而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极高的思想政治素质以及卓越的翻译能力,都与抗战时期在桂林俄专所接受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特点的俄文翻译教育紧密相关。
4 结语
桂林俄专从1938年创办到1944年结束的六年办学期间,正好也是桂林作为“抗战文化城”存在的六年。在俄文教育落后和俄文人才奇缺的战争年代,处于大后方地区的桂林俄专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水平高超的俄文翻译人才。抗战时期,这些译者大量翻译了俄苏文学作品以及反映苏联现实生活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笔耕不辍,成为我国俄文翻译界、编辑界的重要力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桂林俄专师生都为中苏交流合作以及俄苏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历史功绩不该被遗忘。对这所学校翻译活动的考察,无论是对于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深化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文学翻译事业和外语教育研究、增强文化自信和加强区域翻译史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