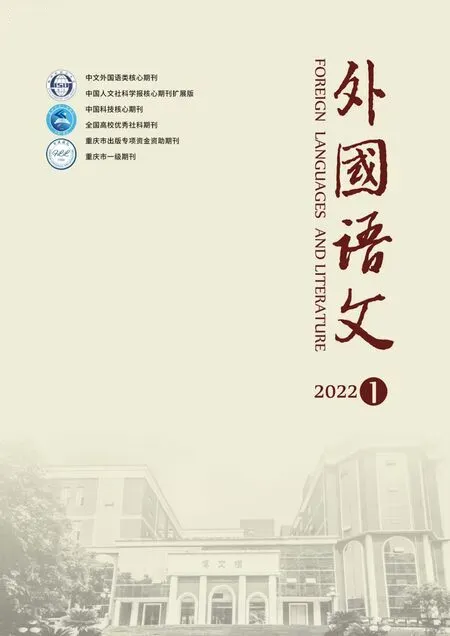汉英词典的文化词研究综述(2001—2020):回顾与前瞻
胡文飞 张俊
(1.四川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2.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文化词,也叫文化特色词(culture-bound word)或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指某个民族或某种语言中特有的词汇。文化词具有显著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其译义和例证等研究涉及语言学、翻译学和社会学,如Zgusta(1971)、Svensén(2009)以及章宜华和雍和明(2007)的相关论述。因此,基于历时视角对汉英词典的文化词进行综述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文化词是汉英词典编纂的重点和难点。汉英词典作为英、汉双语学习的工具,既蕴含西方文化的输入,也涉及中国文化的输出,是两种文化的双向互动。文化词是双语词典编纂的难点(Zgusta,1971;Svensén,2009),完善其表征模式对汉英词典编纂意义重大。
其次,目前对汉英词典文化词的研究散见于各类著作和期刊论文中,缺乏专门的系统研究。我们以“汉英词典”和“文化词”为主题,检索中国期刊网(CNKI),检索结果只有10条,可见该类研究较少。此外,汉英词典文化词研究蕴含于多部(篇)双语词典文献内,尤其关注译义研究(李明 等,2001;魏向清,2005a/2005b;胡文飞,2013b/2020)和配例研究(赵刚 等,2006;章宜华 等,2007;胡文飞,2020),但分布离散,没有系统的综述研究。
最后,汉英词典文化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对未来词典的编纂意义重大。对汉英词典文化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利于发现不足,完善汉英词典编纂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文化战略,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保护世界生态文明。
由此,本文将基于历时分析,对近20年汉英词典文化词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综述对象为中国期刊网(CNKI)中的期刊、硕博论文以及词典学专著,并立足于译义研究、标注体系和例证说明等方面进行回顾和前瞻。
1 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译义研究:从单一离散到多维系统
本文将立足于译义的结构特征和研究范式,从译义理据、译义本质和研究视角等方面进行归纳。
1.1译义理据:从传统的书证收集到系统的语料分析
译义理据涉及源语词目的语义与来源分析,对评判、分析和改进汉英词典的文化词译义结构意义重大。综合双语词典译义理论(Landau,2001;Svensén,2009)以及汉英词典的相关研究(李明 等,2001;徐式谷,2002a/2002b;胡文飞,2013b),我们从历时视角将汉英词典译义理据归为两类:书证收集论和语料分析论。
首先,书证收集论。21世纪初期的汉英词典,无论是立目还是译义,都以书证的收集和整理为主。编者往往按收集的书证确立词目、划分义项并进行译义(黄建华 等,2001;徐式谷,2002a/2002b;胡文飞,2013a)。书证收集对于早期的词典编纂意义重大,为编者整理分析其译义理据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译义表现出较强的依存特征,其译义内容和义项安排多以《现汉》为蓝本(徐式谷,2002a/2002b;曾东京,2003),译义结构依存性强(胡文飞,2019)。
其次,语料分析论。平行语料库利于解决传统双语词典中因为词汇空缺和文化空缺而形成的零等值问题。基于计算机和语料库在学习词典编纂中的应用潜势,学界(章宜华 等,2007;李德俊,2007/2016;胡文飞,2013b/2019)阐释了建立语料库的必要性及其对积极型汉英词典中文化词表征的作用和价值,如钟兰凤等(2010)认为可以通过增设“译项”来解决目标语译义问题,以及胡文飞(2019)通过中介语概括文化词的产出偏误和习得模式。此外,李德俊(2007/2016)还分析了平行语料库与积极型汉英词典的研编,涉及文化词的立目和译义等。
1.2译义本质:从单一对等到多维译义
对汉英词典文化词译义本质的理论探索,使学界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传统的单一对等观和现代的多维系统观。
首先,单一对等观。单一对等观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且立足于编者主观内省范式,但它对改进和提高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译义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李明 等,2001;章宜华,2006b;赵翠莲,2004;魏向清,2005b;章宜华 等,2007;胡文飞,2013b)已经概括出“对等译义”“仿造译义”“描述译义”和“综合译义”等多种文化词译义模式,但多指向单一的对等模式。
其次,多维系统观。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与应用助推了文化词译义的现代认知观,如魏向清(2005a/2005b)的系统译义观和章宜华(2006a)、胡文飞(2013b)的多维译义观。系统译义观(魏向清,2005a/2005b)基于系统理论分析了双语词典文化词译义的整体性、层次性以及动态开放性,对汉英词典译义的结构优化和操作体系有了初步探索。多维译义观(章宜华,2006a;胡文飞,2019)则从词汇语义表征的多维性入手,提出汉英词典意义驱动的多维译义模式,即“寻求交际模式的等值转化转换”以及“基于源语认知语义框架触发的跨空间的语义整合”。多维译义观强调文化词译义过程的动态整合性以及译义取向的辩证统一性,能帮助用户分解、映射并形成系统的语义网络结构。
1.3译义视角:从语义转换到跨界融合
综合而言,近20年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译义正从单一的语义转换走向跨界融合。
首先,基于译义本体的语义转换。长期以来,学界对汉英词典译义仍基于传统的语义转换观,关注等值性和自足性。一方面,聚焦语义转换的等值性。传统汉英词典关注源语(汉语)和目的语(英语)之间的语码转换。此外,多数研究(李开荣,2001;李明 等,2001;章宜华,2006b;魏向清,2005a,2005b;章宜华 等,2007)关注译义的存在模式以及等值特征等。另一方面,语义的层级特征客观上要求对汉英词典文化词进行系统的语义转换,并聚焦和关注语义的层级性(静态的语言意义和动态的言语意义)。然而,当前汉英词典在译义中多以静态的语言意义为重点,强调语义的自足性,对语境依存度较高的汉语文化词表征严重不足。
其次,基于语义、认知与翻译的跨界融合。近期以来,汉英词典对译义的研究视角不断融合,其跨界特征更加明显。一方面,语义学与认知语言学的融合。章宜华(2009)、田兵(2003)和马珊(2018)等基于认知语义框架,系统构建了多维译义观和语义框架分析模型。译义由源语认知语义框架触发,源语在目的语中的联想图式以“隐喻映射”的方式为被译义词提供理解或解释手段(章宜华,2009:243)。此外,编者还应提炼命题模型(马珊,2018),通过描写文化词核心框架元素进行语义重构。另一方面,语义学与翻译学的跨界。Steiner(2001)强调语言与文化的融合转换。因此,汉英词典文化词的翻译不宜过多使用解释性译义,而是要遵守替换性优先、体现源语文化内涵等,强调译义的拓扑原则和转换策略(胡文飞 等,2019)。最后,译义方法(傅一勤,2006;赵刚,2006)也是相关研究的关注重点,如逆向翻译利于确保汉英词典文化词译义的地道性,而扩注、标注等方法利于减少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性。
2 汉英词典文化词的标注研究:从编者主体走向用户需求
正确选择和适当运用标注是词典编者的重要任务之一(Zgusta,1971)。汉英词典对文化词的标注在内容上涉及语法、语义和语用信息等,标注的聚焦点正从编者走向用户。
2.1文化词的语法标注:从编者的理解机制到用户的产出需求
语法标注包括词法标注和句法标注,前者以词类标注为主,后者涉及词目在句子中的功能和作用,如组合特征、搭配结构等。
首先,词法标注。学界(丁炳福,2002;王仁强,2006/2010/2020;王仁强 等,2017)对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词类标注集中于标注理据、标注原则和标注方法等。
一方面,标注理据分析。相关研究(丁炳福,2002;王仁强,2006/2020;沈家煊,2009/2015)对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包括文化词)的理据分析主要关注其用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传统观点认为对汉语词类的标注应立足于语义结构(沈家煊,2009/2015),但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表明,用法和频率是汉语词类划分的根基。因此,王仁强(2006/2020)研究了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现状(包括个别文化词),并基于用法模式提出了改进措施。此外,词类标注理据还涉及“汉语本位法”与“英语本位法”之争,如丁炳福(2002)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标注方法分析。文化词的词法标注不可或缺,因为“词类标注在汉英词典编纂中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王仁强,2006)。但就标注方法而言,当前仍存有争议,涉及标注的简洁性、通用性和可及性。王仁强等(2017/2019)系统阐释了“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这对文化词的标注极具指导意义。此外,汉英词典应通过词类标注来映射、阐释文化词的功能多义特征,以此完善对目的语的系统表征(胡文飞,2013b)。
其次,句法标注是文化词语法标注的重要内容之一(Landau,2001;Svensén,2009),但当前的汉英词典普遍标注不足。相关研究(张春柏,2000;胡文飞,2013b/2019)表明,当前汉英词典文化词的句法标注研究较少,主要聚焦于标注的必要性和科学性。汉英词典提供语法信息是大势所趋,但多数学者所谓的语法信息,仍局限于词类标注。此外,学界也关注标注的科学性,并立足于用户需求进行改进和提高。积极型汉英词典需要在释义中用句法标注的形式来凸显文化词汇的论元结构特征,完善其交际场景(胡文飞,2019)。
2.2文化词的语义标注:开始关注用户的认知需求
汉英语言的非同构性以及文化的国别差异性增强了对应词的非等值性,因此语义标注成为文化词的一种有效表征形式。近20年来,相关研究(黄建华 等,2001;李明一 等,2011;胡文飞, 2019 )对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语义标注涉及类型和方法等,并开始关注用户的认知需求。
首先,黄建华等(2001)界定了限定性括注和说明性括注,并通过具体例证阐释了语义标注的使用范围及其在文化词中的认知功能。限定性括注以括号来限定目的语词概念意义,而说明性括注则补充目的语词的内涵意义、联想意义以及文化意义等,多用于百科或文化局限词。此外,李明一等(2011)分析了文化词的内涵义及其在汉英词典中的语义限制模式。
其次,近10年来,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语义标注开始转向用户,关注用户的认知需求,如胡文飞(2013b/2019)的相关研究。胡文飞(2013b)基于用户认知需求描述了学习型汉英词典对标记性语义的处理方法,如通过标注突显来完善文化词的语义表征结构,提高认知效度。此外,编者可在译义之后以“语义补充”“提示说明”等积极手段,突显其标记性语义特征并强化记忆效果(胡文飞,2019)。
2.3文化词的语用标注:逐渐顺应用户的交际需求
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语用标注涉及标注内容和标注体系,如赵刚(2006)、李明一等(2011)和胡文飞(2013a)等的相关研究,并开始顺应用户的交际需求。
首先,标注内容仍局限于传统语用描写。语用标注是汉英词典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途径,其常见的标注有:方言、贬义、尊称、谦辞、诙谐语、口语等(李明一 等,2011)。汉英词典对文化词的标注多局限于以上范围,尤其关注其功能特征和语用策略。特定的语用对策有利于解决词典中的特定语用问题,尤其是文化词(盛若菁,2006)。
其次,标注体系聚焦用户交际需求,涉及标注形式和标注方法。在标注形式上,汉英词典文化词以括注为主。译者可采取括注来克服和减少这种跨文化障碍,更好地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寻找文化对应词(赵刚,2006)。语用标注构成汉英词典文化词简明而高效的表征手段,但就标注方法而言,多数编者和用户都以简洁的表征模式和灵活的表征介质为主(李明一 等,2011;胡文飞,2013b)。
3 汉英词典文化词的例证研究:从言语转换走向文化映射
例证是译义的延伸,汉英词典的文化词关于例证的研究主要涉及研究路径、功能特征和配置机制等。
3.1文化词例证的研究路径:从言语等值到文化交际
汉英词典例证的相关研究(章宜华 等,2007;胡文飞,2020)显示,对文化词研究路径正从基于词典本体的等值模式转向基于用户需求的交际模式。
首先,基于词典本体的言语等值。基于词典本体的例证强调言语等值性,并在本质上蕴涵多维系统性。一方面,言语等值在内容上具有多维性,包括概念等值、功能等值、语义等值和文化等值等(章宜华 等,2007:310-318;魏向清,2005a)。另一方面,言语等值也具有系统特征,表现出整体性和动态开放性。双语词典(包括汉英词典)例证翻译强调在上下文和具体语境中的功能对等(黄建华 等,2001:160),整体性和动态开放性特征显著。汉英词典的例证翻译聚焦文化特征,它不仅是两种语言体系的接触,也是两种文化的接触(黄建华 等,2001;胡文飞,2020)。
其次,基于用户需求的文化交际。文化词例证在交际模式上具有层次性,包括语言交际和文化交际,涉及互文性和拓扑性,并从语言本体转向文化内涵。一方面,例证交际的互文特征分析。互文性理论已经应用到汉英词典文化词的例证翻译中,但互文性例证需要语境补充才能再现原型交际场景(胡文飞,2013a/2020)。此外,部分学者(曾东京,2003;赵刚 等,2006)还阐释了“准确性互文”和“创新性互文”对例证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汉英词典文化词亟须强化拓扑转换结构。当前,汉英词典文化词(如儒学词)例证在拓扑集转换中简化特征明显且拓扑转换结构具有较强的离散性(胡文飞 等,2019)。此外,文化词的例证转换也表现出虚化特征且系统性不强,进而影响其文化认知和交际功能。
3.2文化词例证的功能特征:从语码转换转向社会折射
无论是学界对例证功能的总体概述(李明 等,2001)还是分类阐释(Svensén, 2009;张宏,2009),都涉及语言知识和社会知识。综合相关研究(黄建华 等,2001;章宜华 等,2007;黄丽 等,2019),我们将汉英词典文化词的例证功能概述为语码转换功能和社会折射功能:
首先,语码转换功能。例证是对词目语义结构和用法特征的具体化。相关研究(黄建华等,2001;章宜华 等,2007)阐释了汉英词典例证的语码转换功能,包括对词目结构的语义补充、语法凸显、语体限定等,这对文化词更为重要。一方面,汉英词典的例证补充文化词的词义,并说明用法,包括语法特点、搭配范围和修辞色彩(黄建华 等,2001)。另一方面,汉英词典的例证具有语体限定功能和语用明示功能,这对于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尤为重要。汉英词典例证通过提供“正确或得体使用语词特定意义的语境”,有效限定语用范围,正确反映其使用场景和语义内涵(章宜华 等,2007)。
其次,社会折射功能。文化词语义内涵的复杂性、社会性客观上要求汉英词典通过例证来再现这种复杂关联和情景意义。词典的社会属性是语言社会性的镜像折射。一方面,汉英词典文化词的例证是时代的缩影,是社会的聚焦和再现,集中体现了时代的主题和热点。另一方面,汉英词典文化词的例证具有典型的民族性,是约定俗成的。语言是融入了民族个性的,总是会从本民族的思维、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反映出来(章宜华 等,2007)。此外,文化词例证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依赖于特定的社会规约,其形成、发展、转移和消亡都取决于社会的接纳和认可(胡文飞,2020)。
3.3文化词例证的配置机制:从语言基础到文化映射
相关研究(盛培林,2004;赵翠莲,2004;陈维红,2008;胡文飞,2013b)多从语言和文化视角来分析文化词的配例机制。
首先,基于语言信息进行汉英词典文化词的例证配置。供国内用户使用的汉英词典是编码型词典,它应尽量增加英语的语法信息、例证等,以满足使用者的查阅需要。汉语文化词内涵丰富,语义复杂,因此外语学习者对其交际语境、标记性语义和语用特征更为关注,所以对例证依存性更强。文化词例证的减少或缺失,容易简化该词的语言认知功能和交际功能,影响学习者对该类词的理解和使用(胡文飞,2020)。
其次,基于文化映射进行汉英词典文化词的例证配置。文化词在文化属性、语用意义和功能结构等方面标记性强,因此基于文化映射进行例证配置尤其重要。陈维红(2008)立足于用户双语心理词汇的混合模型和共享分布式非对称模型,倡导通过例证来映射文化词的语用信息。此外,文化映射对提高汉英词典例证配置和交际效果具有积极意义,如盛培林(2004)所倡导的“文化注释”法、卢念春(2017)的“文化图式法”和胡文飞(2020)的“文化意象模式”等。
4 汉英词典文化词研究的前瞻分析
基于20年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汉英词典的译义结构从离散走向系统、标注体系正从编者主体走向用户需求,而例证结构已经从言语转换走向文化映射。共时对比国外双语词典对文化词的研究走向,我们认为未来的汉英词典的文化词研究将着力于以下几方面。
4.1完善汉英词典文化词的交际功能
完善汉英词典文化词的交际功能,需要不断增强其文化传承功能和用户交际功能。
首先,基于语言本体拓展文化传承功能。未来汉英词典应不断凸显文化词的传承功能,即文化的聚合性、典范性和传承性。一方面,文化词集中反映了特定民族的语言交际和文化发展,是历史发展和文化积累的映射,其文化特征和属性以聚合体形式(例证)进入词典微观结构。另一方面,汉英词典文化词蕴涵着汉文化的典范,承载着汉语词在使用中所具有的独特社会意义或语境意义。典范性贯穿于词典编纂的每个环节,更应该反映在词典内容上(章宜华 等,2007:19)。此外,汉英词典的开放性和动态性突显了例证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其次,基于用户认知视角强化其交际功能。一方面,认知心理学界(董燕萍 等,2002)的双语记忆模型为未来的文化词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赵翠莲(2004)构建了不同的汉英译义心理模型,而胡文飞(2016)、章宜华和雍和明(2007)将心理词库的研究引入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译义,拓展了汉英词典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基于用户视角对汉英词典研究范式的创新为未来的文化词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相关研究(盛培林,2004;胡文飞,2019)关注汉英词典用户的接受视野、审美经验和查阅心理,并将用户的认知机制、加工策略等纳入文化词研究,积极探索其译义结构的认知模式和拓扑转换策略(胡文飞 等,2019)、提取和加工模式(胡文飞,2016)等。
4.2凸显语料库在汉英词典文化词中的驱动作用
未来汉英词典的文化词研究应基于大型语料库进行语境归纳,用系列规则集来管辖语词的常态性、规约性用法,通过短语驱动约束文化词的表征结构体。
首先,增强文化词表征的语料库驱动特征。对于汉英词典的文化词,我们将基于语料库词典学研究范式,从词典译义、例证配置等视角优化其表征模式。一方面,基于语料检索利于编者发掘新义项,不断完善源语词的义项结构(李德俊,2015)。此外,语料库词典学强调通过平行语料库提取大量具有互译特征的句对,并参照语境和对译现状获取对译词。另一方面,语言研究的描写主义原则以及定量分析特征使汉英词典对文化词例证配置转向语料库。传统汉英词典的例证主要通过单语词典取例和编者自造例(李明 等,2001),基于平行语料库编写的汉英词典例句更加丰富,更加贴近语言的使用(李德俊,2015)。此外,语言研究的定量特征也强化了汉英词典例证交际的语料库驱动特征。语料检索的自动化为汉英词典例证配置提供数据支持,强化编者对文化词的词频、词长、搭配以及语义趋向等内容进行定量研究。
其次,凸显汉英词典文化词表征中的短语学特征。短语驱动译义倡导以短语为载体进行语料分析,通过语料合并来提取规约性短语表达式。短语译义有利于防止义项收录不完整,也有效避免了义项之间的重复。基于短语驱动的语料库词典学(李德俊,2015)将结合汉英词典编纂现状,充分利用自建平行语料库进行自动抽取(涉及对应词和例证)。此外,基于短语驱动的模式分析法(Hanks,2013:115-134;胡文飞,2020)认为句法结构和论元信息是分析动词语境依存特征和词汇集的核心。文化词的高语境依存性及文化互文特性要求编者在译义和配例时保持论元结构的完整性和语境的丰富性,因此短语应作为表征结构主体进入译义和例证结构。
4.3优化汉英词典文化词的转换结构
首先,完善译义拓扑结构的系统性。文化的拓扑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因为文化就是变化和翻译的一个序列(Steiner,2001:448-449)。翻译具有拓扑性,翻译中的各种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了“变形中的恒定性”,即基于文化恒量相对固定基础上以语言变量为载体的译义结构的拓扑转换。一方面,传统汉英词典文化词以解释性译义为主,弱化了对等词的结构相融性(包括组合和聚合特征),形成孤立、离散的译义拓扑点,而基于论元结构的译义则完善了搭配结构,增强了拓扑集的组合、聚合能力,形成完整的译义系统。另一方面,汉英词典文化词将强化语言信息,重视语言拓扑点的扩展,防止因语境不足甚至残缺而影响了文化词的结构潜势(包括语境完整性和结构相融性),无法形成完整的拓扑场。
其次,强化例证转换结构的完整性。例证转换结构对于文化词表征意义重大,尤其是例证转换中的启动模式、结构转换等。一方面,未来汉英词典的文化词研究将不断优化例证结构,增强表征结构中的启动效应、突显其聚合特征,以此提高例证结构的转换效度,更好地服务于用户的产出需求。另一方面,强化对例证转换的定量分析,以此提高例证转换的完整性。未来汉英词典的文化词将基于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范式,通过词汇变异度分析、结构容量调查等方法,分析其例证转换的语言特征和信息结构,以此优化例证转换结构。事实上,基于大数据的词典分析模式(李德俊,2015;王仁强,2020),不仅拓展了词典定量研究的范围,也为未来汉英词典的例证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5 结语
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回顾,本文描述了近20年汉英词典文化词研究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一方面,汉英词典的文化词的译义结构从单一离散走向多维系统。文化词的译义理据从单一的书证研究到系统的语料分析,其译义本质从单一对等到多维译义,而译义视角则从语义转换到跨界融合。此外,标注体系已经从编者主体走向用户需求,而例证结构已经从言语转换走向文化映射。另一方面,未来汉英词典的文化词研究,将不断强化交际功能,凸显语料库在汉英词典文化词中的驱动作用并优化文化词中的转换结构。本文对汉英词典文化词的回顾与前瞻,不仅系统归纳了其发展模式和主要特征,有利于完善汉英词典编纂结构,还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未来汉英词典的发展指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