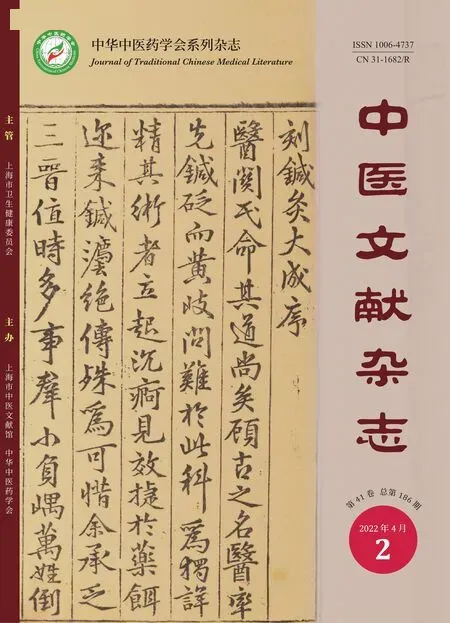宋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
朱思行 杨丽娜 魏春宇 尚 力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对中医药的发展有交互和促进作用[1]。早在秦汉时期,中印间即开始了物质和文化的交流。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商贸互贾的逐渐繁盛,中印交流至唐代达到顶峰,而从宋代开始衰弱。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对研究唐代的中印文化交流极为热衷,而鲜有论及宋代的中印文化交流,更不用说研究其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了,诚为遗憾。本文拟在回顾中印文化交流历史的基础上,以分析宋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特点作为切入点,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宋代中印文化交流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宋以前中印文化交流的渊源
在西汉时,印度被称作“身毒”。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2]可见,中印交流早在张骞之前就开始了。范晔的《后汉书》称印度为“天竺”[3]。汉明帝时,遣蔡音等18人赴西域求法。公元67年,他们从西域把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请到了都城洛阳,兴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魏晋时,高僧法显著《佛国记》,详细记录了当时天竺十几个小国的情况和小乘学的内容[4]。印人鸠摩罗什(344—413年)来华,成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第一个重要的佛经翻译家,先后译经达300余卷。至梁武帝时期,佛教在中国登堂入室,甚至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唐代,中印文化交流进入到鼎盛阶段。《旧唐书·西戎》将天竺分为五天竺,并详细记载了唐代中印之间的贸易往来。五天竺国曾27次遣使来中国,唐太宗、高宗、武后也数次派使者去印度。如《旧唐书》载:“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余部而归。”[5]玄奘(600—664年)取经返回后著《大唐西域记》介绍印度,其中,卷二更是从释名、疆域、岁时、邑居、衣饰、馔食、文字、教育、物产等17个方面记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
宋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特点
1.佛教的融合和同化
唐武宗时期,佛教遭遇了“会昌法难”等一系列灭佛运动,加上五代时期战争纷乱,各国帝王也大多排斥佛教,中印交流几乎中断,佛教也随之衰败。
自宋太祖之后,历代皇帝相继出台崇佛政策,并大兴佛事。宋真宗更亲作《崇释论》倡导佛学真意,佛教自此由衰转盛并发展迅速,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也逐步恢复。宋代曾派大批僧人到印度取经,著名者如继业法师宋僧曾在天竺刻碑纪念,今印度佛教四大圣迹之一的迩耶城摩诃菩提寺内仍保存了刻有汉文的五座石碑。宋真宗祥符八年,印度注肇派出以婆里三文为首的52人使团来宋通好,以后又连续3次遣使来宋。
宋代,本土的佛教译经活动仍持续不断。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渐衰落,宋代对佛教的研究逐步从唐代以翻译为主走向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内化,并对汉语词汇产生了影响。如无常、世界、回光返照、妄想、障碍等因翻译而创造的词汇,不仅融入了民众日常生活,甚至被中医药借用以描述病症[7]。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传统儒家思想的碰撞和融合逐渐产生,在“性命之学”“天人合一”“动静观”等哲学观念上迸发出新的火花[8]。宋代的理学家们通过对佛教华严宗、禅宗思想的吸收,实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使得中国的各宗教最后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交融,也是佛教在中国的融合和同化。
总之,自汉以来,直至宋代,在不断加深的交流中,印度佛教文化渐次大量输入中国,并完成了中国本土化的进程。
2.宋代海上贸易
南亚诸国自南海诸国往西,是印度次大陆,当时称为“西天诸国”。在今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一带有衬毗国,奎隆一带有故临国,在今印度东南部沿海有注辈国,今斯里兰卡有细兰国等。因临处于阿拉伯世界与中国贸易往来的交通线上,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来,往往先到故临停留,然后换乘大船,到南洋群岛及中国来,故印度次大陆是海上丝路的中转站。
晚于玄奘的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时已不选择陆路,而是往返皆从海路。其所著《高僧传》详细记载了当时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宋代以后,随着航海术的发展,赴印度路线逐步由海路替代,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催生出了“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佛教在印度逐渐式微,宋代中印两国间的交流,转而以贸易等形式继续发展。为促进商品贸易,宋代在主要贸易港口设置市舶司,专掌海外贸易事宜,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征税。宋代有关典章制度和海上交通贸易的著作《萍洲可谈》记载:“凡舶至,帅漕与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 谓之抽解。”[9]抽解,即是对贸易货物进行征税。北宋晚期按不同货物种类分为细色(贵重物品)和粗色(一般物品)进行一定比例的抽税。宋代不同时期,抽税的比例随时政和国家财政盈亏情况而变化,但总体而言,官方对细色物品的抽税比例远远大于粗色物品,以获取更高的税利[10]。《宋史》记载,南宋建炎四年 (1130年), 仅泉州一地抽买的乳香就高达86,780多斤[11],说明了香料贸易在税收中所占的重要比例。因此,宋代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支持和大量需求,大大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处于贸易中转地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促进中医学的发展
1.丰富中药资源,发展方剂学
胡椒作为一种香料,很早之前就已传入中国。在唐代,人们已经把在食品和药物中使用了香料[12]。
宋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发达,活跃的市舶贸易为国家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其中,以香料为主的药物贸易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受到了中印两国的重视。
有些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在印度人眼中只是生活物品,但在输入中国后,根据中医药理论,成为本草药物纳入中医药体系中[13]。如印度人作为调味品的阿魏,在输入中国后,因其具有“杀虫、消癥去积”的功效而被收入本草著作中。再如象牙、犀角等,早在唐代以前就被吸收进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中,其“凉血解毒”的功效更是在后世明清温病学的治疗运用中占有重要一席。随着犀角的广泛应用,其带来的药用价值和经济效益也影响着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如南宋时人张世南(字光叔)在著作《游宦纪闻》中曾记载了其对“犀”品种特点的考证,并对品种之间的品质差异进行了论述,从而间接补充了中药药物鉴定的理论[14]。这些外来药物的本土化过程,既是天然药物本草化的过程,也是基于中医药理论和实践反复验证和积累的过程。有学者认为[15],这是基于中医思维和原始应用相结合的验证。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对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均有一定的推进作用。随着印度等地朝贡和贸易规模的扩大,香料成为海外贸易应用最多的舶来品之一,与本土中药形成一定的互补性,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了中药资源。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作为宋代官方制药局的成方制备手册,其记载的方剂流传广泛。香料虽是进口物品,但因其价廉效著而常常应用于临床。如外科方剂中几乎首选的乳香,广泛记载于《外科精要》《证类本草》等多部宋代临床和本草典籍中。据初步统计,《太平圣惠方》中以芳香药物命名的方剂就达到100余首,至今仍在临床中广泛使用的苏合香丸、沉香散等名方均出自宋代[16]。而香药常以其药名作为汤头进入医方,如茴香汤、木香汤、豆蔻汤等,甚至被作为君药使用,如苏合香丸就是宋代香药在临床上最著名的应用,至今仍用于急救。此外,在以《博济方》和《局方》为代表的方书中,以香药命名的医方数量庞大,而《局方》中很多方剂虽非用香料药物来命名,但其组成中的芳香药物却比比皆是,如至宝丹、排风汤、八风散等。这些以香药为主组成的方剂被大量运用于临床,成为宋代方剂学发展中一个独特的符号。因此,香药的使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方剂学。
2.打破宋代临床用药格局
宋代疾病谱的变化对中医药提出了新的挑战。而香药的大量引入和其具有的较高药用价值,为其临床应用赢得了一席之地。在《局方》《伤寒补亡论》《本草衍义》《伤寒总病论》等医学著作中,记载了许多香药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方。此外,香药也有着显著的保健效果,如苏合香酒和气辟邪,可以达到防病的目的。通过香药沐浴,可驱邪辟病,“治伤寒寒热不能服药者”。如《幼幼新书》中载:“浴汤,莽草、丹参、肉桂各三两,菖蒲半斤,蛇床子二两,雷丸五十个,右水三升煮十余沸,适寒温浴儿。”[17]
据《宋史》所载,从印度进口输入中国境内的药物主要有犀角、象牙、琥珀、苏木及胡椒、豆蔻等香料,这为中医治疗“温病”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药物选择余地。以《局方》为例,其中以香药为主的方剂涵盖了内、外、妇、儿等不同科别的疾病。正是通过对香药在临床上的验证,其芳香化湿、辟秽化浊的作用逐渐为医家所熟悉并使用,从而流行开来。香药不仅影响了宋代医家的临床用药习惯,而且绵延至明清,在治疗温病的方药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
香料药物的使用不可否认地给中药资源库带来了新鲜血液,发展了方剂学,其芳香辟秽、化浊解毒的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药物在治疗功效上的不足,尤其是对一些湿邪为患、瘟疫邪毒等内伤外感疾患的治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医家面对寒温之争时,往往墨守仲景辛温热药之旨以治外感,此时大量香燥药物的引入更为其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香料药物兼具温补壮阳的作用,正与当时社会民众、医家喜用补剂、好服热药之性相合,因此不无风靡。在官方的推动下,《局方》《圣济总录》《圣惠方》等一系列由官府推行的药典得到了迅速普及,随之而来的是芳香药物的大量滥用所致的温燥成灾,这从金元四大家对《局方》芳香辛燥的奋起对抗即可看出。朱丹溪作《局方发挥》以批判《局方》香窜燥烈之时弊,因此成就了金元医学的异军突起。这不仅影响了明代温补学派的用药格局,更奠定了温病学派的用药基础,甚至左右了后世医家学者对中医学派起源划分的观点,从中医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而言,确实可谓影响深远。
3.促使成药的规范化监制
基于海上贸易所带来的巨大财富,也为了便于官方统一掌控,宋廷设立了以管理成药制作和售卖为主的机构“太平惠民和剂局”,目的是通过制定相应的炮制规范和标准,以便更好地进行成药的官方售卖。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颁布的成药药典及成药处方范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成药的规范化制售除了更便利地供百姓使用外,也为海上贸易服务,因此其规范化的制作,离不开药物规范化的炮制,更离不开处方诊治原则。《局方》所附《指南总论》开宗明义地提出知晓天地阴阳之道是诊病之先决,首开成药标准化制备的先河。书中对汤、散、丸各种剂型的作用和适应证分别作了精当的解释:“凡疗诸病,当先以汤荡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理顺阴阳……故用汤也。”又云:“散能逐邪,风气湿痹,表里移走。”再云:“丸药者,能逐风冷,破积聚,消诸坚症,进美饮食,调和荣卫。”[18]305- 306后又引雷敩之语晓以临证须审证用药及药证相符之道。
《指南总论》高度概括了在处方诊治原则指导以及药物规划化炮制下的成药制备过程。其中“论合和法”篇不仅强调了道地药材的重要性,指出其应是在“辨明州土”的基础上而来,并且指出古今剂量单位因“年代绵历浸远”导致了“传写转见乖讹”,当“务从简易,庶免参差”,以“合今时之行用”[18]306- 307。此外,对药物的修合也作了详细的说明,涉及煮汤之水,捣罗丸药易熟之法,汤、酒中诸石药之煎煮,渍酒药之密封等等。由此可见,《局方》对道地药材、药物剂量和炮制规范的重视程度。
《指南总论》“论用药法”篇对药物采摘时令提出了要求。如“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者”“华、实、茎、叶,乃各随其成熟尔”等等,并从中医取类比象的角度加以说明,使药物在采摘环节即有明确统一的规范[18]310- 311。药物的配伍也有原则性的要求,如“凡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指南总论》“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篇里对常用药物按部分类,对不同药材的炮制方法分别作了详明的规定,其炮制方法虽不尽统一,但皆具规范化。如“玉石部丹砂、雄黄、雌黄,凡使:先打碎,研细水飞过,灰碗内铺纸渗干,始入药用。如别有炼,各依本方”[18]314。
《局方》中的成药剂型丰富,涉及汤、丸、散、膏、丹等,对于各种剂型的制备,书中都有详细的规范化说明,且对成药的制备皆有严格的工艺流程和先后程序,这就为成药的标准化生产提供了依据,也保障了成药的药效品质。如青州白丸子的制备工艺十分繁琐,制备过程中药物需反复研、晒,如“日中晒,夜露至晓,弃水,别用井花水搅,又晒,至来日早,再换新水搅”[18]14。
此外,一些成药方中涉及不少名贵药物,如人参、犀角、虎骨、首乌、麝香、牛黄、龙脑等物,这些药物的使用,无形中也提高了成药的制作成本和售卖价格,提升了贸易量,增加了贸易金额,为朝廷增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
4.佛教影响中医学
佛教对中医学的影响,是通过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佛教经义的翻译带来大量新的词汇与概念,以及对事物的新的认知,影响中医学的发展。如李曌华在《佛教医学影响与“痰饮”词义、病位的转移》一文中梳理了“痰饮”一词在历代文献中的词义及病位的沿革和流变。在秦汉时期,中医学中的痰饮特指病位在肠间之饮,而在佛教医学汉译的过程中,其病位属性在魏晋及唐代发生了变化,即病位在胸和肠。后至宋代杨仁斋《仁斋直指方》,始开中医痰饮分而论之的先河[19],并沿用至今。痰饮分论的结果,必然导致痰饮分治,对痰饮证治的不同,势必也会直接影响医家遣方用药,从而更具治疗的针对性。这种对疾病认知的变化所产生的学术思想的转变,仍指导着当今临床的辨证思路和用药规律,由此可见其对中医学的影响。
佛教医学产生于印度,是一种宗教医学,也是一种医药学体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李良松认为[20],佛教医学是建立在古印度“五明”中“医方明”的基础上,以佛教理论为指导的医药学体系。中国佛教医学是以佛教理论和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为基础,以寺院传承的方药和诊疗经验为代表,吸收了古印度医药技术的医学体系。北大的陈明先生认为,佛教医学是在古印度生命吠陀医学体系的基础上,以佛教教义为指导思想,吸收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和临床特点,形成的一种非独立的医学体系,包含印度佛教医学和中国佛教医学两部分[21]。我们认为,印度佛教医学和中国佛教医学与中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佛教医学是中医学与印度佛教医学有机融合的结晶,既可以把它看作是印度佛教医学思想和技术中医化后的产物,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受印度佛教医学思想影响后形成的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佛教医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医学的影响,陈明教授认为其非独立的医学体系。因此我们认为,也可以从某一程度上把中国佛教医学归属于中医学的范畴。
中国佛教医学尤以骨伤科、女科及心理学等专科研究的成果为其特点。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22],中国佛教医学伤科的基础理论仍以中医的气血阴阳、脏象经络等学说作为基础理论,虽产生于魏晋,但成熟于两宋,并在望诊、四辨、手法及药物治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其中,望诊指的是“四望”,即望眼、望甲(爪)、望脚底、望阳物;四辨即辨穴道、辨特意征象、辨生死脉象、辨脏腑绝症。药物又以急救、正骨及内服外用结合的金疮方为其特色[23]。萧山竹林寺是一座始建于南齐年间的佛教寺院,寺院僧人研习医术始于后晋,盛于宋代,一直流传至今。《萧山县志》中有竹林寺静暹僧一剂而愈宋理宗之谢皇后病危的记载[24],由此竹林寺女科盛名海内,成为南宋著名妇科四大家之首,为女科之始祖[25]。如《萧山竹林寺妇科秘方考》一文中谈及性格偏颇、偏极而病,贪欲放荡、房室所伤,情绪刺激、气郁而化火三者皆为妇科疾病的病机,虽是从中医七情致病的角度出发,但也是佛教中讲的“烦恼有六”和“随烦恼二十者”。佛教中的人之智慧、烦恼的两种精神的对立,其中烦恼被佛教医学改造后变为怒欲为病的原因,即是包括中医的七情为病,根基于佛教明心见性、了却烦恼以及除去烦恼的佛学文化。在妇科疾病如月经、胎前产后中的精神卫生的调治[26],也是遵循佛教心理学的教义,以佛医治病首先“治心”,从而改善人的心理及身体问题[27],由此亦可见其对中国佛教医学的影响。
总 结
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由汉而宋,交流不断深入。随着汉明帝遣使西行求发归来,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魏晋高僧译经讲经蔚然成风,宋为唐代中印文化的交流在中国的兴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尤其是佛教文化的发展,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宋承唐韵,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佛教文化逐步占据了上层意识形态,并融入了本土文化。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促使了海上贸易的兴起,也间接促使了中印文化间进一步的交流,并由此对宋代中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上贸易,尤其是大规模的香料贸易,使香料作为临床药物被纳入到中医药体系,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药资源库,更促进了方剂的发展,使方剂的组方用药及功效作用发生了不同于汉唐的用药规律和使用风格,并呈现多用香燥的临床特点,为当时社会风尚的形成以及疾病谱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药物资源和临床手段,对金元寒凉学派的开创、明清温补学派的奠定和温病学的治疗思路皆有了积极的历史借鉴作用。中印海上贸易作为现实动力,在促进建立官方药局和颁布成药药典的同时,也促使了成药的规范化监制,为后世药物的标准化制备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此外,佛教文化对中医学的渗透融合,对中医学辨证论治疾病的思路、治则治法及遣方用药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佛教医学和中医学在中国大地上的有机融合派生出中国佛教医学,使中医学的自身发展得到反哺,甚至在伤科、女科及心理学等多项专科研究中丰富了中医学的治疗特点。因此,从对汉唐中印文化交流的梳理,至宋时中印文化交流特点的总结来看,中印文化交流对中医学在理、法、方、药各个方面发展的影响深远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