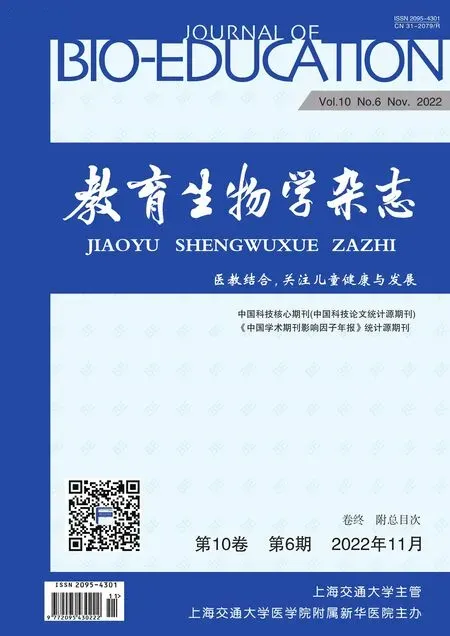抽动障碍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共病儿童的诊治与管理
余 婧,陈文雄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心理科(中国广州 510623)
抽动障碍(tic disorder, TD)是一种在儿童早期发病,主要临床表现为运动抽动和(或)发声抽动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分为短暂性抽动障碍(transient tic disorder, TTD)(发病率:5%~7%)、慢性抽动障碍(chronic tic disorder, CTD)(发病率:3%~4%)、图雷特综合征(Tourette syndrome, TS)(发病率:0.3%~1.0%)及分类不明的抽动障碍(tic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TD-NOS)(发病率:1.2%~4.6%)[1]。TD诊断有时被忽略,疾病的发病率估计可能偏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disorder, ADHD)与TD均为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与发育水平不相符的注意力缺陷、多动和冲动。我国儿童该病的总体患病率为6.26%[2]。半数以上的TD患儿常与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和(或)发育行为障碍共病,其中TD共病ADHD最为常见,其次为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及情绪障碍等[3]。共病的存在导致TD患儿的病情更严重及繁杂,也增加了医治难度。ADHD是最常见的使TD复杂化的共病。临床上,如TD患儿共病ADHD无疑增加了诊断、治疗及管理上的挑战性。故亟需针对这一人群相关领域的系统性综述。本文对近10年来有关儿童TD共病ADHD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早期识别及诊治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性综述。
1 儿童TD共病ADHD:流行病学
有研究[4]表明,在所有种族和人群中,TD的发病率基本一致。对1992年至2010年中国13项流行病学研究的meta分析结果[5]显示,TD、TTD、CTD和TS的患病率分别为6.1%(95%CI:0.036~0.100)、1.7%(95%CI:0.009~0.031)、1.2%(95%CI:0.007~0.022)和0.3%(95%CI:0.001~0.008)。目前,中国14亿人口中有20%以上处于0~18岁年龄段。据估计,中国有超过1 000万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某种程度的TD,而患有TS的儿童则多达100万[6]。TD与ADHD共病最为常见,占30%~50%,明显高于普通人群的ADHD患病率。TD与ADHD共病时,多动症的症状多在抽动发作之前发生,而晚于抽动发作的患者仅占1/3左右。约1/5的ADHD患儿进入青春期后其多动、冲动及注意力缺陷等症状会自然减轻。在一项对欧洲的神经发育障碍儿童的研究[7]中发现,TD患者中ADHD的比例高达60%~80%;即使在轻度CTD的患儿中,ADHD的发生率也比普通人群高7~8倍。国内回顾性研究[8]发现,TD患儿共患ADHD的比例最高,其中TTD患儿为14.6%,CTD患儿为51.4%,而TS患儿则高达58.0%,与国外同行研究的结果大致相同。
2 儿童TD共病ADHD:病理生理学机制
TD的发病可能是遗传、免疫、心理和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相关家族谱系研究[9]发现,与普通人群相比,TD患儿的一级亲属患CTD的风险增加了10~100倍。虽然已有相当多的TD分子遗传学研究,但迄今仍未发现明确的单一或复杂的TD致病基因。神经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回路的抑制性兴奋信号的失衡则被认为可能是产生抽动和相关症状的分子机制。例如,纹状体多巴胺反应过度或突触后多巴胺受体异常敏感,可能会产生抽动症状[10]。TD发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与多种神经化学和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其中最相关的是多巴胺能、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能、肾上腺素能和谷氨酸能途径[11]。神经解剖研究发现,TS患者的尾状核体积较小[12];TS患儿抽动的严重度与感觉运动皮质体积密切相关[13]。相关功能神经影像学研究[14]发现,TD患儿基底神经节活性降低,基底节葡萄糖利用率降低。目前研究还显示一些感染性疾病也与TD有关。其中,对A族β-溶血性链球菌研究得最多,与其相关的儿童自身免疫性神经精神障碍,称作链球菌感染相关的儿童自身免疫性神经精神障碍(pediatric autoimmune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associated with streptococcal infections, PANDAS)。有研究[15]提出,TD的病因可能与个体抗链球菌抗体与链球菌抗原的交叉反应作用于基底神经节有关。
同样,ADHD的发病机制也不完全明确,但大量研究表明,ADHD患儿大脑皮层儿茶酚胺的代谢失衡似乎起着主要作用。在动物研究[16]中发现,前额叶皮质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系统失衡与ADHD的发病密切相关。相关神经解剖学研究发现,ADHD儿童存在尾状核结构不对称性的缩小或缺失、大脑和小脑容积更小、胼胝体后部区域更小,或颞叶后部和顶叶下部皮层灰质增加等;大脑前部区域的差异尤其明显,表现为前额叶皮质体积更小、前扣带皮质的厚度减少以及双侧额上回区域皮质变薄。功能性脑成像显示,ADHD儿童的大脑整体激活度降低,且基底节和前额叶区域局部激活度降低[17]。
TD共病ADHD的病理生理学机制现尚不明确。基于TD及ADHD各自发病机制的研究,在解剖结构上,基底节的相关病变可能是TD共病ADHD的病因之一。基底节和丘脑的机能障碍,可能使运动及控制认知的通路受到抑制,进而在其所投射的皮质区域出现异常活动,并引起相关抽动发作[18]。这种皮质区域的异常活动亦与ADHD的发病相关。较多研究发现,TD、ADHD及其他多种神经精神障碍性疾病均与皮层-纹状体-丘脑-皮层环路异常相关。其相关环节发生障碍时,则会产生多动、冲动、强迫,以及抽动等相应的问题行为。其次,从神经递质角度分析,TD共病ADHD的出现可能与神经递质异常分泌有关,如肾上腺素能、多巴胺能等,导致用于调节皮质纹状体回路供给不足,从而无法抑制侵入性思维、感官输入和运动反应,最终导致冲动、多动以及抽动行为的出现[19]。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机体逐渐增多了中间神经元的抑制作用,可能弥补了之前额叶皮质在活动时抑制功能所显现的不足,进而整体上改善了皮质功能;由此,在进入成年后,大部分ADHD及TS患儿的症状会有不同程度的减轻[20]。
3 儿童TD共病ADHD:临床表现
TD多起病于儿童及青少年期,男性多于女性,最多见于5~6岁的学龄前儿童和学龄期儿童,8~12岁病情最重。ADHD亦是起病于儿童时期,主要临床表现是与其生理年龄水平不相符的注意缺陷、行为多动和情绪冲动,且症状在多个场合持续出现。TD共病ADHD的患儿,ADHD的症状常先出现,较TD的运动抽动和/或发声抽动早2~3年,并常见于重度抽动患者[21]。在一项针对患有CTD的青少年(5~18岁)的研究[22]中发现,有46%的患者表现出与学校有关的问题行为,而那些共病ADHD的患者出现学习困难的风险增加了近4倍。研究发现,共病ADHD的TD患儿在注意力缺陷、冲动行为、认知功能缺陷等方面更为突出。在匡桂芳等[23]的研究中发现,与单纯TD患儿相比,共病ADHD的TD患儿出现控制能力降低及注意缺陷主要是因罹患ADHD所导致;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可能与ADHD患儿存在神经精神发育延迟相关。TD共病ADHD的患儿更易出现情绪障碍及行为问题,对患儿的社会功能可能产生严重影响。由此,共病ADHD致使TD患儿的认知功能缺陷、情绪障碍等,是导致TD患儿自我意识缺乏、生活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24]。
4 儿童TD共病ADHD:诊断与早期识别
当前,并无特异性的生物学检测指标用来诊断儿童TD共病ADHD。无论是针对TD抑或ADHD的诊断均应遵循相关的诊断标准。目前国内外多采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 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 DSM-5]的诊断标准。DSM-5诊断标准倾向于使用暂时性抽动障碍(provisional TD,PTD)取代TTD。CTD是指运动性抽动或发声性抽动症状延续1年以上;TS的抽动症状最重,可分别或同时出现运动性抽动和发声性抽动延续1年以上;至于不能归类的TD,被认为是属于未分类的TD,如在18岁之后发病的TD[1]。DSM-5将ADHD分为3个亚型:注意障碍为主型、多动/冲动为主型和混合型。诊断TD与ADHD共病时,临床表现应同时符合两者疾病的诊断标准。
因为缺乏特异性生物学诊断指标来对TD以及ADHD进行诊断,其诊断主要基于临床现象学为主,即根据患儿抽动症状及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症状以及相关伴随的精神症状性来进行诊断[1]。翔实的病史及认真的临床观察是准确诊断的必要条件。存疑的病例,临床上的纵向追踪,有时辅以必要的相关症候的视频,可帮助厘清诊断。 全面的评估应该包括详细的围产史、发育史、家族史、药物史及心理社会史,及其伴随的共病等[1]。使用相关的标准化的心理评估工具有助于诊断及判别是否存在共病。评估抽动障碍的严重程度,临床上常使用的相关量表包括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ale global tic severity scale,YGTSS)、Hopkins抽 动 量 表(Hopkins motor and vocal tic scale, HMVTS)等[3]。对 于ADHD患 儿的诊断及功能评估量表,常用ADHD诊断量表父母版、Swanson, Nolan and Pelham父母及教师评定 量 表(Swanson, Nolan and Pelham rating scales,SNAP)-IV、Connors量表及困难儿童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children with difficulties, QCD)等[25]。
对一些临床发作形式难于与癫痫鉴别的TD患儿需要行进一步的脑电图检查,以排除是否存在肌阵挛性癫痫或简单部分性发作的可能性;此外,亦需要进行相关的实验室检查,以排除相关遗传代谢性疾病,如肝豆状核病变等[26]。
由于ADHD和TD均有遗传易感性,早期识别有高危因素的儿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减少疾病对患儿社会功能的影响。尽管TD共病ADHD的发病率高,当前,对如何筛查TD共病ADHD尚未达成共识。TD诊断有时被忽略,疾病的发病率估计可能偏低,有报道从起病至诊断的平均时间超过5年[1]。首发的抽动症状多为眼肌、面肌抽动,患儿多首诊于眼科或神经科等。临床上,如果对TD或ADHD认识不足,易延误诊治。反之,部分学龄前期或学龄早期ADHD患儿的首发症状可能表现为类似抽动的症状,如反复的肢体摆动等表现,此时需要临床医师认真甄别患儿患何种疾病抑或是存在二者共病可能。由于对于TD及ADHD的认识不足,致使家长/监护人认为孩子的抽动表现或多动的表现是孩子“调皮”所导致的,或认为孩子的异常行为是生理疾病所导致的,在骨科、耳鼻喉科或呼吸科诊治后未见好转,从而延误疾病的诊治。需提高相关领域的医务人员、教师乃至家长/监护人对TD及ADHD的知晓度、早期识别能力;加强多学科的交流与学习,加强门诊及社区宣教提高社会认知,做到医教结合。
5 儿童TD共病ADHD:治疗
TD及ADHD的患儿的治疗均需依据整体原则和个别情况来制定长期治疗计划。此外,需按时随访、评估和监测治疗效果;使核心症状得以缓解;治疗目标为最大程度减少功能损害,提高学习、生活及社交能力。同时,对于共病的治疗,应优先考虑目前主要影响患儿社会功能的疾病,先积极缓解相关程度严重的症状。对于轻度至中度TD共病ADHD的患者:优先考虑ADHD的治疗,因其可能会对当下孩子的社会功能产生更大的不良影响。对于TS或重度抽动共病ADHD的患儿:则首先考虑治疗抽动的症状,因为相较于ADHD症候,抽动的相关症候则更大程度地影响了孩子的生活质量;优先控制抽动的症候,对改善TS或重度抽动共病ADHD患儿的生活质量更为紧迫[22]。TD的综合行为干预是一种组合式干预,包含心理教育、行为分析、放松训练、习惯逆转疗法、社会支持和奖励系统等,注意家庭教育管理,消除抽动发作诱因,如健康睡眠、减少不必要的屏幕暴露等。同样,对于轻度及中度的TD患儿,亦多采用综合行为干预进行治疗[10],包括对于患儿个体的行为矫正、团体游戏疗法以及家庭辅导和学校支持等。
中度以上的患者如若行为治疗措施疗效不佳或难以实施时,则应给予相关的药物治疗。 采用药物治疗TD共病ADHD患者时,相关药物的选择尤为重要,需综合考虑兼顾治疗TD及ADHD两者的症状。α-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如胍法辛、可乐定等)均能改善抽动和ADHD症状,临床上,常作为TD共病ADHD治疗的一线药物。此外,由于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如托莫西汀等在控制ADHD的症状时,不增加纹状体的多巴胺水平,诱发或加重抽动的可能性小,推荐应用于TD共病ADHD的患儿。相关研究报道,服用中枢兴奋剂有可能加重或诱发抽动,提醒临床上需谨慎选用中枢兴奋剂治疗TD共病ADHD[3];但也有部分研究结果报道中枢兴奋剂的使用并不会加重抽动[27];中枢兴奋剂应用于TD共病ADHD患儿是否会加重或诱发抽动,需更多的研究加以厘清。
6 儿童TD共病ADHD:预后及管理
中国一项对TD患者预后情况的分析[28]发现:预后不良的TD患者约占1/3;影响TD患者预后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共病的存在,会增加治疗难度及负担,影响患儿预后。例如,与ADHD共病会影响TD患儿的认知功能、学习能力及注意力等。如前所述,因为TD及ADHD均存在遗传易感性,对儿童进行监测和早期识别高危因素,是十分重要的,也是TD共病ADHD患者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当孩子经专科医师诊断为TD共病ADHD后,患儿及患儿家长/监护人需消除自身的病耻感;提高患者及其家长/监护人对疾病诊断的接受度及治疗的顺应性,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及时记录孩子的抽动症状或ADHD相关症候的变化及原因,及时有效地反馈给医生;此外,亦需要与学校老师做好沟通,与老师一起正确认识抽动障碍及减少针对相关的疾病的诱因,如对TD患儿减少不必要的屏幕暴露等,淡化患儿在学校发生的抽动的症状等。与此同时,在TD患儿的临床诊治中,若发现存在与ADHD共病的可能,应告知患儿家长/监护人注意后续ADHD相关症状,对患儿家庭进行宣教,在后续的随访过程中加以确诊或排除;同样,在针对ADHD患儿的临床诊疗中,亦应关注存在共病TD的风险及后续的跟进措施;对确诊TD共病ADHD的患儿,应及时根据患儿症状制定个性化的行为干预及必要的药物治疗方案。TD共病ADHD的患儿诊治及管理流程如下(图1)。

图1 TD共病ADHD的患儿诊治及管理流程
综上所述,儿童TD共病ADHD常见,其发病机制可能与基底节病变、皮层-纹状体-丘脑-皮层环路异常等等相关。共病ADHD使TD患儿的病情更严重、更复杂。TD共病ADHD的患儿治疗前需进行系统综合评估;使用行为干预结合必要的药物治疗,优先缓解对患儿社会功能损害最严重的疾病。临床上对TD或ADHD认识不足,易造成对二者共患的诊断困难。早期识别及诊断、个体化的早期行为干预及药物治疗、长程的规范的管理对患儿的社会功能恢复十分重要。